與具體而不是抽象的人對話——答幾位批評我的同學_風聞
驱逐舰051-人民主体的历史和政治哲学。2021-08-22 03:03
我8月以來寫的有些東西就理論基礎來説,主要是對《共產黨宣言》中對資產階級把知識分子都變成它出錢僱傭的勞動者以及“兩個決裂”思想的一些理解和發揮,並且受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這些話的啓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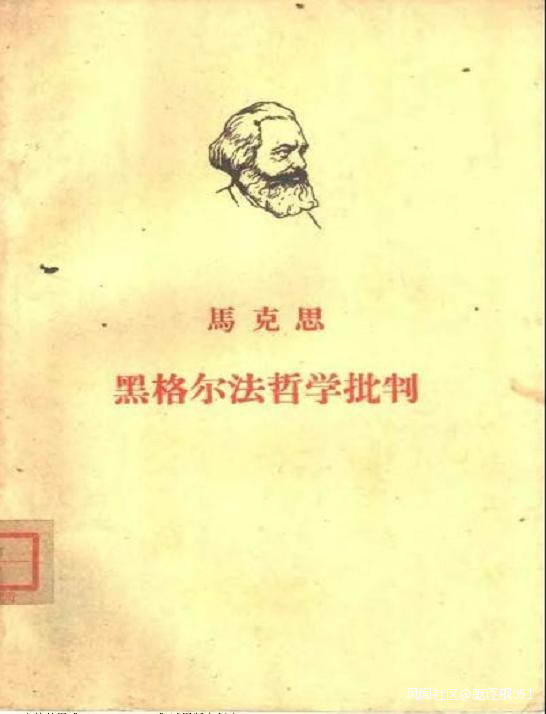
“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但是理論一經掌握羣眾,也會變成物質力量。理論只要説服人,就能掌握羣眾;而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説服人。所謂徹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
所以誰如果讀了我寫的這些而又認為有道理,應該歸功於馬克思而不是我——我只是一個轉述者,還不一定轉述得好。
所以説實在的,大家要真正提高洞察力和理論思維能力,應該聯繫實際多認認真真地讀一些原著,而不是隻看我或其他人寫的這些二手三手的貨色。這就像禪宗説的:以手指月,是要你看月,而不是要你看手指——據説有個禪師因為要讓人悟出這一點,當着盯着他手指看的人,把自己的手指剁掉了。
我上課也好,答問也好,寫文章也好,是盡一名思政教師的責任。這個責任,誠然不是也不應該是無限的,因為我的能力本來就有限。然而,在我這樣的老師所做的有限的、初步的甚至有不少缺陷的引導中,也正藴含了通向無限的可能性,而要將這個可能實現出來,需要你自己邁出勇毅堅決的步伐。
有同學對我説她們喜歡聽我講,可自已讀馬列就讀不下去,甚至感到很無聊。她可能以為這是在誇我,殊不知我聽到這話,卻頓時感到自己的所作所為都失去了意義。我有過這樣的經歷:
大學裏有些曾讓我認為很有思想的老師,到我自己真正去讀書,去思考的時候,卻發現他的很多見解是站不住腳的、不可取的,或者至少是可以商榷的。
而這樣的老師,往往又有些自負,聽不進別人的批評——搞哲學這塊的,需要一些執着甚至執拗,否則堅持不了,但一旦過了頭,也容易抱殘守缺,固步自封。
我知道自己是不能免俗的,但好在我知道自己那些想法的其來所自,如果有人能夠在探討共同關注的問題時對我進行認真嚴肅的批判,我會很高興。
有一次在課堂上,我故意用激烈的語氣批評一個學生的觀點,激起她為自己辯護,並對我進行反駁。不管她説得對不對,她目光炯炯如巖下電的樣子,才是有自己思想的人應有的神采。
但要讓這種神采持久不衰,是需要很深的底藴的。而讀書確實能給你這個底藴,因為在同樣的問題背景與實踐基礎上,它能支撐你拿出更有新意也更為嚴密周全的見解。
在我的空間裏,不時有很年輕的中學生、大學生來發表評論。這些同學一個最可貴的地方,就是極其認真地要弄清是非,追求真理——這正是黑格爾所寄予厚望的“青年的精神”。
黑格爾説:
“但我要特別呼籲青年的精神,因為青春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時間,尚沒有受到迫切需要的狹隘目的系統的束縛,而且還有從事於無關自己利益的科學工作的自由。——同樣青年人也還沒有受過虛妄性的否定精神,和一種僅只是批判勞作的無內容的哲學的沾染。一個有健全心情的青年還有勇氣去追求真理。真理的王國是哲學所最熟習的領域,也是哲學所締造的,通過哲學的研究,我們是可以分享的。 ”
不過,我從他們(此“他們”沒有性別意味,事實上其中有幾位經常發評論的應該是女性)的評論中,又能看出這樣一個矛盾:
一方面,他們希望看到其他人(例如我)的見解,看到自己所想不到的東西; 另一方面,他們又強烈地期待這些見解和自己已有的想法是一致的。
簡言之,既求異,又排異。
這並沒有什麼錯,因為思想與意志是不可分的。這就是説:一個人的一個觀點包含的不只這個觀點所陳述的語義內容本身,還包含了對這個觀點的確信,也包括説出這個觀點以及讓別人贊成這個觀點的意志——我最早是在休謨的《人性論》中關於知覺的“強烈、生動”和有關信念的論述中領會到了這樣一個思想:觀念本身不是在真空中存在,它是有力量的東西。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説,認為知中有行,比如(這個例子是我自己舉的)看到一個美女,當你認為她“美”的時候,這個“認知”就包含了行動,它意味着你喜歡她,並且想接近她,並且如果沒有其它因素(例如社會道德因素)阻止的話,你就會這樣做。——我們擁有一個觀點時,會像這樣有一些特殊的行動,但有一種行動是共同的,就是要設法使別人與我們一致。
這一點也使得我們經常想要站在他者的角度肯定自己。純粹的“自我”是虛無,或者至少是不值得信任的,因此我們要照鏡子,用他人的眼光欣賞鏡中的自己;我們要發朋友圈,而我們發到朋友圈的東西,都是根據他人的眼光而修飾和美化過的自己,我們希望以此得到他人的肯定。
因此當我們想要求同而排異的時候,我們其實已經設定了他人的存在,從而也設定了他人與我們不同的可能性,也設定了我們自身的有限性。但這時,我們是把“他人”當作一個無限的東西,這就是説:“他人”是對我的有限性的否定,是包圍着我的不確定的可能性,而我並不知道“他人”是誰。
與這樣的“他人”打交道是非常累的,而且我們除非把自己也變得虛無,是無法與這樣的“他人”一致的。所以我們要揚棄這個無限,把“他人”設定為和我們一樣的有限的、確定的東西——比如某一個個體,比如我這樣一個老師——他是一個“他人”,但他不是虛無縹緲或令人窒息的,你與這樣的“他人”才能進行真正的交流。
這樣的一個他人,與你有着堅固的、確定的差異,這會讓“求同排異”的你感到不適,因為他在否定你。但這不是一種虛無縹緲的否定,而是一種特定的、有內容的否定,你在這種否定面前,並不像面對不確定的他者那樣不知所措,而是可以採取真正的行動來將他征服的——雖然這意味着你自己也必然發生某些改變,但這種改變並不是讓你瓦解或虛無化,而是讓你獲得了更多的內容和確定性。
總之,你對某個人(比如我)發表各種評論的時候,説明你不甘於和一個無限、不確定的、不知道是誰的他人打交道,而是把他當作一個和你一樣有限而確定的他人來對話的,那就要注意他否定你(反過來説也是你否定他)的特定內容與形式,找到異中之同與同中之異,而不是把對那個不確定的“他人”的反感甚至恐懼加諸這個特定的、有限的人。 你堅持這樣做的話,一個一個特定的“他人”,就會被你不斷地從那個面目模糊的無限、不確定的“他人”中分離出來,你在自己變得豐富而強大的同時,會發現你對“他人”、“差異性”的不適與恐懼正在被解構和揚棄着。
這或許能夠打開每一個有限的自我通向真正健康的共同體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