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終於推翻“996福報論”, 卻沒能撕破早已佈下的一張網|文化縱橫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1-08-29 21:18
 ✪ 周安安 | 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
✪ 周安安 | 北京大學新媒體研究院
【導讀】過去一段時間以來,某知名企業家提出的員工加班“996福報論”備受爭議。近日,最高法、人社部聯合發佈10個超時加班典型案例,為企業“劃紅線”,明確指出“996”和“007”都是違法行為,“奮鬥”不是企業規避法定責任的擋箭牌。事實上,隨着世界進入“數字時代”,多種樣態的互聯網經濟模式漸次崛起,“勞動”本身也在經歷巨大變革。通過算法的操控,網絡平台對勞動的整體性支配也逐漸形成,在自由人的自由勞動的表象下,一個勞動者被越發盤剝卻又越發缺乏生存保障的時代,似乎正在降臨。
本文指出,互聯網平台勞動從創生到異變的歷史過程,展現了對未來勞動的自由、平等、協作的“烏托邦”想象,是如何演化為全面控制勞動者生活的“利維坦”的,並對中國互聯網發展的未來給予提醒:算法的不斷優化使互聯網平台得以將個體分散、參差多樣的勞動者有效地整合起來,體現着強大生產力,但最終卻讓人陷入了一張無處可逃的無形“巨網”之中。互聯網平台不僅是一套算法和編碼,更是一種生產生活的組織技術,其中所有的規則設定都根植於特定的歷史意識和制度條件。過去,中國在技術領域始終是一個追趕者,但如今,中國至少已經在互聯網算法技術和相關應用上走到了世界前列。面對這一不斷變化的領域,我們必須走出一條有別於技術中心主義的,始終讓技術服務於社會的道路。
本文發表於《文化縱橫》2021年第4期,原題為《平台勞動:從“烏托邦”到“利維坦”》。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諸君參考。
平台勞動:從“烏托邦”到“利維坦”
互聯網作為一種通過信息傳遞進行社會組織的技術,其技術社會史始終圍繞自由與控制這一對矛盾展開。從萬維網誕生以來,信息技術產業曾經催生過無數“未來的工作”,伴隨着一波又一波的技術樂觀主義浪潮,這些未來工作都曾在許諾一個繁榮經濟前景的同時,向勞動者宣誓更多的自我發展和自由。然而,在這一技術的誕生地美國,我們正在目睹“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不穩定就業趨勢和失業潮。而在中國,隨着移動互聯網基礎設施對國民生活的全覆蓋,依託互聯網平台進行勞動組織的新興職業從業規模在持續大規模擴張,許多新興的勞動爭議也日益浮出水面:
一是服務於互聯網平台的基層勞動者往往不具有正式的勞動身份,平台與被僱傭者之間並非法定的勞動關係,被僱傭者因此無法享受法定的勞動保障;
二是以算法為代表的平台數據反饋系統對勞動過程控制的精細化程度大大提升,一線勞動者被壓榨勞動力的程度更深了。
本文將着重分析平台勞動的兩個面向:
其一,簡要再現今日被稱為**“平台資本主義”**的勞動組織模式,是如何圍繞着西方社會思想中“自由與控制”這一組基本矛盾,被不同時期的信息技術相關人士反覆設計,最終脱胎於西方後工業社會中的歷史過程;
其二,分析當下中國的平台經濟發展模式與平台資本主義間的異同,指出中國實踐所藴含的未來可能性。
▍自由精英與不穩定勞工:平台勞動簡史
在互聯網平台勞動創生初期,幾乎與時下大眾媒體上對“算法操控”的批判完全相反,資方和大眾傳媒為其打造的話術曾勾勒出一幅勞動烏托邦式的藍圖:勞工與平台之間之所以不產生傳統的勞動關係,是因為雙方是更為自由的平等協作關係;算法規則是為了更有效率地規劃勞動過程,勞動者不僅多做多得、絕對公正,更可以選擇隨時關閉APP,根據需求規劃個人時間……這樣的藍圖並非全然是騙局,許多流水線工人選擇進入平台零工行業,理由之一就是:同為去技能化的工作,互聯網平台不僅能夠提供更豐厚的待遇,日常工作體驗也遠比嚴格進行人身控制、工作流程乏味枯燥的製造業流水線愜意自由。“網絡化的流動僱傭比工業體系更自由”,這樣一種關於勞動組織的技術社會想象有多個古老的思想版本,但與今日信息技術的勞動體系最直接相關的,還是上世紀50~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實踐。
彼時,從“二戰”末期到冷戰高潮,核威脅、系統化戰爭、大規模自動化武器的軍事需求催生了美國龐大的軍工聯合體,由打贏系統化戰爭的需求所催生出的技術系統,也越來越以高度信息化、自動化和排除人的政治與文化介入為研發理念。此一技術系統的設計實踐,使得在“二戰”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計算機都被認為是一項反人性的技術,意味着腐朽的官僚制、冷酷的封閉信息系統和分裂的理性人。從賴特·米爾斯、加爾佈雷斯到馬爾庫塞,這一支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工業社會批判皆基於這種技術想象展開:信息技術提供了讓權力集中化的技術手段。自這一批判中,誕生了反文化運動版本的信息技術路線。硅谷嬉皮士從東方主義式的致幻劑與瑜伽等精神體驗中得到靈感,希望將個人化的計算系統設計為“個體體驗轉換到另外一個世界”的技術手段。他們夢想以個人化信息設備替代大型中央信息技術設備,從而改變個體認知世界的方式,打破官僚集權,促進“自由人的平等聯合”。
這一技術設計的內在價值追求與美國曆史敍事中的建國神話亦深深契合,即理想世界是由一羣天才在新大陸創造的。在反文化運動的政治能量逐漸消退的後冷戰年代,中產階級的反叛孩子們回到大公司,讓這種技術社會想象藉由商業力量獲得新生:**理想世界的疆土在賽博空間,到達它的技術不再是航海術而是信息技術。這樣一種信息技術組織模式所召喚的“新人”主體,來自美國硅谷青年知識精英的自我想象。**在上世紀90年代曾紅極一時的未來學手冊《失控:機器、社會系統與經濟世界的新生物學》中,新時代的網絡工作模式被認為是“分佈式、分散化、協作化而有適應性的”。作者極少去描述那些在工業化時代最為重要的製造業工作,而是將大量篇幅落在知識工作者上,認為富有創業精神的工程師、科學家和其他自由主義精英,將會創造出一個更為平等協作的工作模式,實現新公社主義者理想中的伊甸園,真正從制度上反抗那些曾經主宰了美國的技術權威統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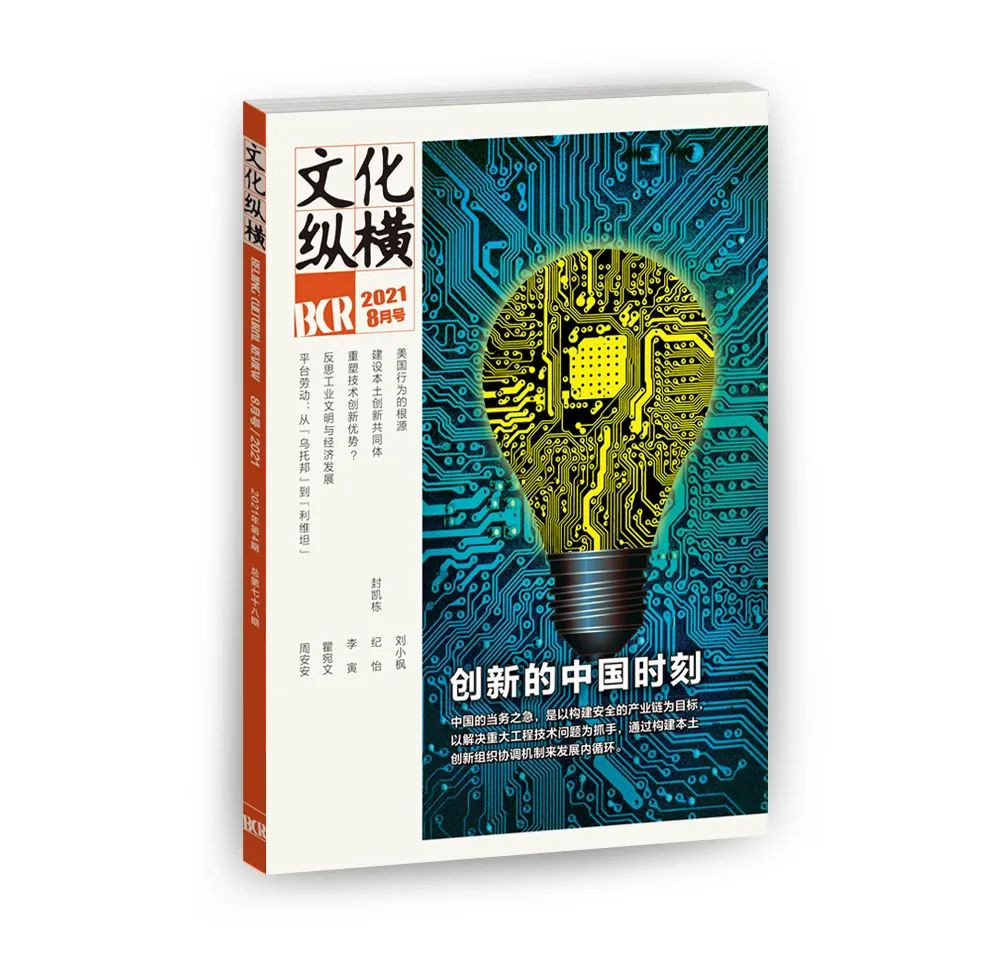 也正是在20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和信息產業精英開始將美國的未來發展與計算機、電信尤其是互聯網交織在一起。美國公眾前所未有地相信互聯網技術將破除市場監管和腐朽的政治規則,再度將市場變為政治與社會變革的引擎。移動通信和互聯網提供了一種超越等級制的、可能的商業組織前景:**人人自己做決策,人人都能從工作中獲得樂趣。**在具體設計產品模式以主導互聯網發展的硅谷創業者們的頭腦中,用信息技術去創造一種將商業的競爭性需求、工作者的自我實現與民主參與結合在一起的社會制度是可能的。計算機互聯繫統不再意味着那些在中央計算機上搜尋轟炸機的冷戰軍事人員和政府高層,而意味着由硅谷投資者和計算機技術人員組成的新一代知識精英。改變世界的英雄也不再是切·格瓦拉式的革命青年,而是整日與筆記本電腦、調制解調器和富有靈感的創意相伴的知識工作者。他們是天然適應無中心繫統的孤獨工作者,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和自我管理能力在扁平型工作組織中遊刃有餘;其中最成功者將在與他們同樣具有靈活稟賦的全球資本的助力下,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硅谷創新神話。
也正是在20世紀90年代,克林頓政府和信息產業精英開始將美國的未來發展與計算機、電信尤其是互聯網交織在一起。美國公眾前所未有地相信互聯網技術將破除市場監管和腐朽的政治規則,再度將市場變為政治與社會變革的引擎。移動通信和互聯網提供了一種超越等級制的、可能的商業組織前景:**人人自己做決策,人人都能從工作中獲得樂趣。**在具體設計產品模式以主導互聯網發展的硅谷創業者們的頭腦中,用信息技術去創造一種將商業的競爭性需求、工作者的自我實現與民主參與結合在一起的社會制度是可能的。計算機互聯繫統不再意味着那些在中央計算機上搜尋轟炸機的冷戰軍事人員和政府高層,而意味着由硅谷投資者和計算機技術人員組成的新一代知識精英。改變世界的英雄也不再是切·格瓦拉式的革命青年,而是整日與筆記本電腦、調制解調器和富有靈感的創意相伴的知識工作者。他們是天然適應無中心繫統的孤獨工作者,依靠自己的聰明才智和自我管理能力在扁平型工作組織中遊刃有餘;其中最成功者將在與他們同樣具有靈活稟賦的全球資本的助力下,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硅谷創新神話。
這種對理想工作模式的設想,完全不同於他們父母在戰後塑造的製造業僱傭制:由國家提供相應政策安排,個體在行業中擁有一份全職僱傭的工作,工資按級別增長,工作時間穩定,有養老、醫療和工傷保障。這是美國人傳統上對於工作的看法,也是戰後美國中產階級令人豔羨的生活方式,它曾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西方世界乃至全球對於理想平民生活的想象。這一工作模式和福特製下的製造業緊密相連,並在20世紀70年代達到高峯。
事實上,將員工視為公司資產、為其提供穩定發展路徑的管理模式,可能從未走出過製造業。在美國製造業達到頂峯後,電信業和大型計算機的發展促成了以計件工作為核心的全球化外包協作。**在製造業被分包到全球南方的同時,總部位於西方發達國家的大公司同樣可以把審計、歸檔、客户服務、人事管理等依靠信息處理的行政工作,轉移到作為前殖民地的發展中國家,以此規避工會和勞動法規的議價與監督。**在印度等人力資源豐富而廉價的地區,靈活的僱用和解僱都更為容易。這些調整會反映在公司的資本價值上,股東會將這一戰略變化看作是“非核心業務”開支的有效優化,能夠提升跨國公司的“投資回報率”與“核心競爭力”。
 與此同時,在美國本土發生的是中產階級開始逐漸被去工業化和外包掏空。在反文化運動後湧入勞動市場的知識精英和普通人大批量進入服務業崗位,以那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快餐店、零售超市(如麥當勞與沃爾瑪)為代表,這一服務業模式又在90年代以來的新一輪全球化中覆蓋全球。這一勞動組織模式轉換的歷史過程,與硅谷新精英們高歌猛進的自由個體的信息技術想象剛好發生在同一時期。
與此同時,在美國本土發生的是中產階級開始逐漸被去工業化和外包掏空。在反文化運動後湧入勞動市場的知識精英和普通人大批量進入服務業崗位,以那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快餐店、零售超市(如麥當勞與沃爾瑪)為代表,這一服務業模式又在90年代以來的新一輪全球化中覆蓋全球。這一勞動組織模式轉換的歷史過程,與硅谷新精英們高歌猛進的自由個體的信息技術想象剛好發生在同一時期。
與製造業崗位不同,服務業崗位從一開始就有強烈的臨時僱用特徵。早在萬維網誕生之前,由電信、電話組成的全球通信網絡已經形成了一個服務業勞務合同全球外包的龐大系統。互聯網的出現無疑深化了這一全球外包邏輯,大大加強了全球化公司在不同地區間分配資源的能力。《失控》是20世紀90年代跨國企業高管理解新經濟和新技術的重要思想資源之一,這一源於反文化運動並最終與新自由主義結盟的互聯網技術精英的組織想象無疑助推了上述過程:在雙方有意無意的合謀之下,“平台-互聯網-企業“結合的模式成為新世紀最顯眼的新經濟增長點。在這個財富神話中,網絡平台上自由的工作者是那些在自動化、共享經濟和物聯網領域工作的投資者與少數技術精英。由製造業轉入服務業的普通人,暫時還維持着繼承自70年代的生活水平和財富期望。
2008年金融危機曾讓大量依賴服務業的人口因舉債而無家可歸,但對這一危機的事後總結認為問題出在金融技術領域,人們並未進入對產業和勞動模式的反思。造就這一勞動組織模式的外部環境非但沒有在2008年後產生結構性的變化,反而進一步加強了。出於對公共債務的擔憂,政府依舊採用貨幣政策緩解經濟狀況。全球企業儲蓄的增加和避税港製度都釋放出大量剩餘資本,這些資本最為青睞的領域依舊是輕資產的科技公司。而西方世界中徹底的無產者增加了,他們只能被迫接受新興的平台科技公司所提供的大量臨時工作。“技術精英-全球資本-不穩定勞動力”由此形成一個閉環系統,由全球中下階層承擔了互聯網平台非正式工作的後果,形成了今日美國社會中由新信息技術所催生的不穩定社會系統的全貌。
互聯網平台技術改造了勞動模式之後,也開始反作用於其他社會生活領域。英國導演肯洛奇的電影《對不起,我們錯過了你》敏鋭地捕捉到了這一趨勢,描繪了在非正式工作環境下,一箇舊式工人階級的家庭難以應對日常危機從而逐漸解體。伴隨着這些社會危機,硅谷技術公司的公眾形象從屠龍少年轉變為新的惡龍,英語批判學界也開始將學術熱點轉移到全球外包和互聯網平台勞動所造就的不平等問題上。作為一種技術物的互聯網,在大眾文化中的形象再度從自由人的邊疆迴歸到異化的利維坦,歷史走過了一個輪迴。
▍中國:內嵌於基礎設施建設發展的互聯網平台
在90年代下半葉正式開啓的信息技術全球化中,印度等前殖民地國家在產業鏈上更多分得了商業流程外包等服務業,中國則獲得了製造業。1991年,後來成為印度總理的莫漢·辛格在班加羅爾設立了國家級的軟件外包產業園;次年,中國深圳電子製造業開始發力,大量來自農村的青年勞動力進入全球工廠,在低社會福利和不穩定僱傭狀態下支撐起了中國製造。經過二十餘年的發展,第四次工業革命的話語開始彰顯,科技應用依然是新社會願景的核心。但是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上一輪信息技術革命中的全球產業分工極大地影響了不同國家和地區對未來科技路線的偏好。
服務業鏈條的上下游國家都開始謀求製造業的迴歸,同時希望通過一些緩和性的政策手段繼續保持靈活僱傭制度下信息產業的優勢。Facebook 聯合創始人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在接受採訪時稱:“我們大談 Uber 司機、Lyft 司機、Postmates、零工經濟,就發展而言這些趨勢都是正確的,但是對於這些替代工作安排中的工人們來説,他們的收入是‘非常不穩定的’。”科技公司開始聯合對推廣“普遍基本收入”(UBI)計劃感興趣的政治力量,實行通過加強富裕階層徵税、向年收入不足5萬美元的窮人每月發放500美元現金的福利計劃。印度等處於信息服務業鏈條下游的國家則開始出現強烈的民族保守主義思潮,對中國的新興網絡產業持激進的反對態度:2020年美國大選前夕,印度緊隨特朗普政府對抖音、微信的禁止令,表現得比美國政府更加積極。
雖然由於互聯網平台業態與統計方式的不同,很難計算出各國從事互聯網平台服務業人數的具體數字,但中國具有最大規模的平台服務業從業者應是不爭的事實。與硅谷新精英類似,中國的互聯網平台企業從一開始也自帶強烈的技術精英色彩,並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全盤接受了新千年的全球化意識形態,將需求導向的靈活僱傭制視為以商業方式建構理想社會組織形態的真理。但在具體實踐中,與美國不一樣,中國互聯網服務業的發展並沒有伴隨着製造業外流,而是深深嵌入中國以製造業和基礎設施建設為核心的經濟發展進程。中國製造業的發展催生了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快速都市化進程,新興都市的服務行業始終處於供不應求的狀態,以淘寶為代表的平台企業在這個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輕工業製成品貿易網絡的角色。在2015年前後,大量以算法技術為核心的網絡平台服務業崛起,並且至今仍持續處於急速拓展市場的擴張狀態。在這個過程中,互聯網平台企業開始逐漸替代中國城市既有的服務業網絡,並引發一系列不同規模的社會矛盾。
**首當其衝的是互聯網強技術規則與基層社會的矛盾。**以約租車平台為例,數家自駕車平台依靠風險投資,在極短時間內完成了對中國大城市的市場佔領,成為中國人民日常出行的必備入口。其靈活用工的僱傭模式,也被地方政府認為是解決閒散人員就業的利器,政府因此有動力與約租車出行平台進行政策層面的合作。儘管自駕車平台在幾個超大規模城市中因為觸動出租車集團利益而被迫整改,其在地方政府層面依然受到相當的扶持。在這個過程中,急速擴張的互聯網平台企業所設定的服務規則,很快與基層社會的生活邏輯出現了矛盾。
以順風車領域爆發過的激烈衝突為例:因為引入了過多的社交因素且缺乏對司機的資質監管,在二、三線城市接連出現多起長途順風車服務過程中的惡性刑事案件。這一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源於快速擴張的互聯網平台服務業對不同地域生活邏輯的改造:平台企業試圖以出行技術平台為媒介,將大城市中相對安全的道路出行邏輯下沉到完全不符合這一邏輯的基層社會,無視了平台服務業是建立在本地基礎管理能力上的。儘管在受到輿論批判後,約租車平台很快叫停整改了順風車服務,但網絡平台持續市場擴張的基礎邏輯並沒有改變:平台技術樹立了一系列硬規則,並試圖以商業模式強行改變本地社會的運作方式。當二者發生衝突時,外部社會成本會被再度拋擲給傳統社會組織和個體工作者承擔,例如2021年初,某互聯網零售平台發生賣菜業務員工過勞猝死事件,並連帶引發網絡生鮮銷售平台剝奪個體商販經營者生存空間的相關討論。
目前中國網絡平台系統與中國社會之間尚未發生大規模劇烈衝突,原因之一可能在於快速城市化催生了大量服務需求,這讓新生的互聯網平台服務系統並未完全替代原有社會系統;加之以強基礎設施建設能力帶來的互聯網平等接入權,許多原有生活系統中的非正規工作者也會尋求通過中介制度進入互聯網平台系統。在這些綜合因素的作用下,互聯網強技術規則與基層社會的矛盾尚處於可吸收和轉化的階段。
當網絡平台的規模效應繼續擴張,在原有生態圈內找不到新的資本增長點,只能轉而尋求進一步改造其他生態圈時,矛盾和衝突就會以更激烈的形式爆發。互聯網平台系統上的信息流動會產生數據,圍繞數據的公共性發生了一系列爭議。當這些數據為傳統意義上的客户間商業交易服務時,它可以在商業私有的邏輯內被處理;但**當數據因其規模效應可以作用於商業交易之外的社會邏輯(如信用體系)時,所有制就成為一個問題。一些互聯網企業的消費貸廣告會引發廣泛反感,就是因為它入侵了商業之外的社會生活邏輯:消費貸試圖改造中國家庭傳統的儲蓄觀念,進而可能以信用系統為中介,改變社會倫理的運作模式,將商業規則確立為社會倫理的前置規則。**在信息系統已經全面改造了社會工作-組織邏輯的西方國家中,正是因為資本規則對社會生活的前置效應已經發生,這些國家的互聯網巨頭才會褪去進步主義的自由色彩,再度在公共輿論層面轉變為利維坦式的存在。
▍結語:平台及其未來
2021年3月1日,全國首部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的地方法規《浙江省數字經濟促進條例》施行。條例指出,數字經濟新業態人員以靈活就業為主,互聯網平台是否與其建立勞動關係存在爭議,難以按照現行法律法規參加工傷保險,亟須補齊制度短板。因此需“積極探索靈活多樣的用工方式”,平台經營者可以通過單險種參加工傷保險的形式為勞務人員提供工傷保險待遇。在此之前,廣泛存在非正規分包制以及工傷高發的建築業,就已做過類似探索,並且發展出了較為成熟的制度形態。平台務工模式中的“打零工”模式其實早就存在於各種行業中,只是規則制定者由看得見的包工頭變為難以觸及的大公司和不可捉摸的算法系統。在這個過程中,個體勞動者是更弱勢了,還是有了正規化制度保障的空間,取決於我們如何認識和處理平台經濟中一系列規則與社會生活的關係。
應當如何規避互聯網平台企業帶來的勞動問題,以及更嚴重的系統性風險?歐美進步知識界已經提出了平台合作化甚至更激烈的公有化主張,但這一社羣主義思想在自由主義政治倫理和平台規模效應的矛盾前難以落地。在網絡效應下,平台系統的規模和生活系統的規模是趨向於一致的,在同一行業內,小規模的合作平台除非完全自外於社會主流體系,否則永遠難以和壟斷平台競爭。正如本文指出,一套源於“自由-控制”二分法的平台勞動制度的實踐與想象,背後其實有着美國社會內生的強烈歷史與價值預設。甚至有激烈的批判認為:依照自動化與外包制等規則組織起來的互聯網技術產品,背後的潛意識來自資本主義悠久的奴隸制歷史;無論是製造業還是信息產業,都是在把最為繁重的工作轉移給其他社會羣體(或者轉移給機器人);美國全球化的過程就是不斷將低福利的重複性勞動通過信息技術手段不斷轉移到全球南方,並最終反噬自身的故事。
中國互聯網平台企業曾在技術構架上全盤接收了這一整套技術想象背後的社會想象,但至今還沒有出現大規模的失業潮和社會動盪,這很大程度上源於依然在擴張中的中國平台經濟立足於與美國完全不同的制度文化土壤,在一定工業發展階段內造成的系統性風險也完全不同。如果你去詢問一位在製造業黃金時期就業的美國中產階級,和一位曾經在世界工廠流水線上經歷過不穩定就業的農民工,他們對於網絡平台提供的不穩定勞動這一新生事物,觀感恐怕並不相同。後者也許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會將這種靈活工作模式看作比流水線更好的選擇——除非他失去家鄉,成為一個徹底的城市無產者。
技術中心主義的思考方式幾乎統御了我們身處其中的這段世界史。在過去三十年間,我們曾經相信,只要加強技術學習,就會獲得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案。而當今日中國在信息科技領域已經擁有了一整套獨立的技術人才系統和創新企業後,實踐中的成就和矛盾似乎都在提醒我們:**互聯網平台不僅是一套算法和編碼,更是一種生產生活的組織技術,其中所有的規則設定都根植於特定的歷史意識和制度條件。**過去,中國在技術領域始終是一個追趕者,不斷移植發達國家的技術方案及其組織模式。但如今,至少在互聯網平台技術領域,中國已經在算法技術和相關應用上都走到了世界前列。面對這一依舊不斷在實踐中變化的領域,我們能否走出一條有別於技術中心主義,始終讓技術服務於社會的道路?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4期,原標題為《平台勞動:從“烏托邦”到“利維坦”》。**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