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禁止他們歌唱?_風聞
音乐先声-音乐先声官方账号-解读音乐产业,见证黄金年代。2021-08-30 22:10
作者 | 朋朋 編輯 | 範志輝
塔利班又回來了,音樂又成了罪惡。
當地時間8月25日,《紐約時報》採訪了塔利班發言人扎比胡拉·穆嘉希德。採訪中,穆嘉希德表示,塔利班將禁止在公共場合播放音樂。隨後,阿富汗國家音樂學院被迫關閉,音樂家被威脅停止表演。眼下,阿富汗電台和電視台一直只播放伊斯蘭歌曲。

20年間,無數人冒着生命危險去滋養、構建的阿富汗音樂土壤,頃刻間灰飛煙滅。未來該何去何從,尚未可知。
燒不盡的音樂之火
時間追溯到1996年,塔利班奪權後曾對音樂進行過大規模的迫害:禁止電台播放音樂,磁帶被大量焚燒,收音機和電視作為塔利班射擊的靶子。音樂人們有的慘遭殺害,有的被迫流亡海外,有的向暴力投降,從此只表演塔利班歌曲。

直到5年後,在經歷了政權變革、憲法制定、議會組建和總統選舉後,阿富汗的城市裏終於再次響起了音樂。喀布爾電台得以恢復,沉寂已久的流行音樂迴盪在老式的晶體管收音機間。大街上,年輕人用隨身聽播放音樂,一邊走一邊打着節拍。在大巴扎舊址上,售賣錄音帶的店鋪鱗次櫛比。
這些音樂幾乎都是從巴基斯坦傳進來的,在那裏,阿富汗的難民們從未放棄他們的音樂夢想。隨後,阿富汗過渡政府總統卡爾扎伊向人民保證,只要阿富汗人民團結起來,同心協力進行經濟重建,阿富汗將擁有一個繁榮的未來。戰爭期間流亡到西方國家的文化精英們受到感召,紛紛回國,希冀在千瘡百孔的故土上實現文化的重建。
民族音樂學家艾哈邁德·薩爾馬斯特在澳大利亞取得音樂學博士學位後,於2002年回到了阿富汗。他創辦了一所音樂學校,為飽受戰爭蹂躪的孩子們提供專業的音樂教育。在外國當局和私人贊助者的扶持下,這所學校發展成為阿富汗國家音樂學院。

2010年,有“阿富汗貓王”之稱的流行歌手法爾哈德·達里亞從美國返回故鄉,貢獻了一場阿富汗史上最大音樂會,當晚有5000人目睹他的風采。
而在飽受壓迫的女性身上,也開出了倔強的搖滾之花。2003年,三位阿富汗女性組建了搖滾樂隊布卡,“我們都穿着布卡,你認不出誰是誰。如果你想和你姐姐打招呼,那也可能是你叔叔。”她們藏在罩袍背後,做阿富汗女性權益的殉道者。

儘管塔利班成員在全世界範圍內通緝樂隊成員,要將她們斬首示眾,但卻無法熄滅阿富汗的搖滾之火。
2011年,喀布爾舉辦了30年來首場搖滾音樂節。這場演出持續了6個小時,來自阿富汗各地的年輕人匯聚於此,逃避塔利班的毒害,和這世界上的其他年輕人一樣,暫時忘記戰亂,縱情享受音樂。

在音樂的組織者特拉維斯·比爾德看來,這場音樂節並不是為了給阿富汗人帶來僅一天的歡愉,而是點燃阿富汗年輕人對流行音樂的熱愛。
轉眼二十年,曾經靠音樂人視死如歸的膽識和真槍實彈的保障得以復興的音樂,塔利班如今則再次將它推進墳墓。
誰在禁止他們歌唱?
為什麼塔利班要禁止音樂?
此前,塔利班發言人説:“音樂在伊斯蘭教中是被禁止的。我們希望能勸説人們不要做這種事情,而不是對他們施加壓力。”
禁止音樂一旦成為宗教中的應有之義,在阿富汗的大部分民眾眼中便具有合法性。就像塔利班要求男人留大鬍子,女人全身裹在罩袍中裏,不讓女性上學,對於偷竊處以極刑,這些在阿富汗農村的百姓中毫無阻礙地推行着。

畢竟在這個國家的憲法中,赫然寫着“阿富汗的任何法律都不得違背神聖的伊斯蘭教之教義及其相關規定。”
對於阿富汗的民眾來説,要想保全音樂幾乎很難。目前,阿富汗的人均GDP是500美元,文盲率是63.7%,女性的文盲率則高達88%。再加上1979年蘇軍入侵阿富汗以來,炮火在這片土地上數十年連綿不絕。
在阿富汗目不識丁的窮苦百姓眼中,暴力是亂世中的唯一正義。在這樣的地方,跟他們強調音樂的價值,談愛與和平顯得有些不合時宜。唯有毫不顧忌地操作槍支、破壞秩序的人,才能在這個無序的社會中搶佔先機。

2001年,塔利班倒台後,阿富汗看到了重建世俗化政府的希望。總統大選吸引了900萬人來投票,人心思定,和平是主流意見。流亡在外的文化精英們看到了這一轉機,紛紛回國,試圖在這片被摧毀的土地上重建文化。
從小生活在伊朗的女導演薩赫拉·卡里米正是在此時回到阿富汗,但迎接她的並不是鮮花和掌聲,而是“曾逢迎可鄙的異教徒”的控訴。

同時,滯後的經濟發展和頻仍的政權更迭,也是低效和腐敗的温牀,文藝作品的出版發行面臨重重阻礙。在阿富汗電影協會的辦公室裏,卡里米想要借用燈光設備,負責人大言不慚地直接要求她行賄。在骯髒、低效的官僚主義中,不知有多少創作火苗早早夭折。
但卡里米負隅頑抗,完成了紀錄片《方向盤背後的阿富汗女人》,意圖用電影喚醒阿富汗女性作出改變。她還從零開始,舉辦了阿富汗電影節。她要讓阿富汗人知道,他們有自己的藝術,只是被戰爭中斷了。

相比之下,意圖破壞者只需要小小的動作,就能摧毀藝術家們的努力,使民眾達到絕望的目的。他們只需要謀殺一個演員、毒打一位詩人,用自殺式人肉炸彈摧毀一次演奏會,人們心中的恐懼就會被無限放大,化作淒厲的慘叫。
2014年,阿富汗導演索尼婭·納賽裏·科爾在拍攝電影《黑天鵝》時,保守派綁架了女主角,並砍掉了她的腳,以懲罰她對宗教的不忠。
同年,阿富汗國家音樂學院的一場演出中,校長艾哈邁德·薩爾馬斯特身後一位襲擊者引爆身上的炸彈,造成兩人死亡,多人受傷。
但即便遭遇重重險阻,這些藝術家們仍樂觀地認為塔利班的歷史不會重演,阿富汗還有一線希望。
7年前在接受訪問時,卡里米説“過去十年,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們,已經嘗過了自由的滋味,當人們可以自由地坐在咖啡店裏,可以聊時事看電影,人們不會輕易允許別人給自己戴上鐐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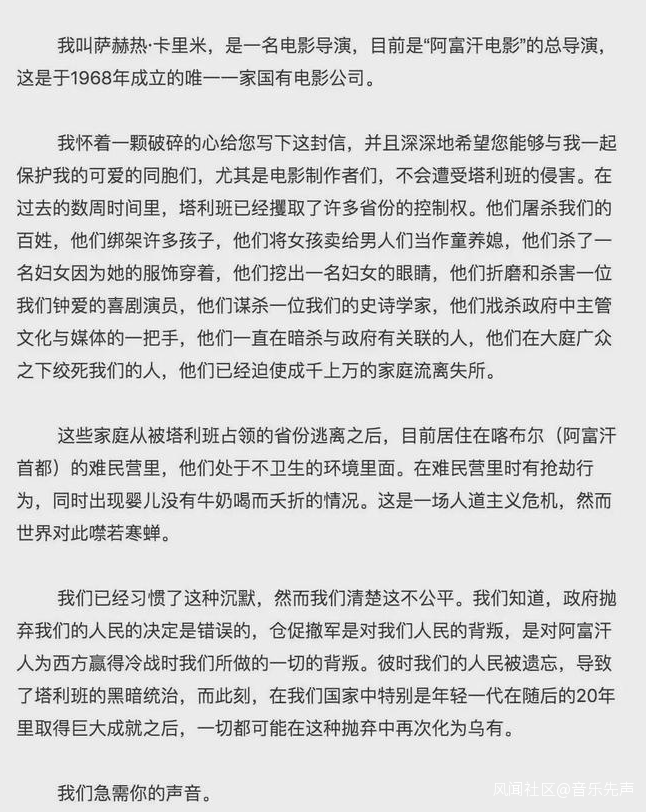
如今,塔利班捲土重來。現實打了卡里米們一記響亮的耳光,電影和音樂都沒能拯救阿富汗,徒留社交媒體上的一腔悲訴。“我在我的國家所努力創作的一切都將毀於一旦”,從此後“我們的聲音、我們的表達都將被子彈壓制到沉默之中”。
她只能向這個世界疾呼,“不要忘記阿富汗”。
有音樂,便有希望
美籍阿富汗裔作家塔米姆·安薩利在《無規則遊戲》中寫道:哪怕是在塔利班時代,人們也會趁着夜深人靜、門户緊閉的時候,拿出磁帶,放進收音機,調低音量,慢慢回味。
在無休止的戰亂和政權更迭中,音樂可以讓受盡苦難的阿富汗民眾喘口氣,享受短暫的浪漫與歡愉。我們很難估計音樂對阿富汗民眾的意義,對於布卡樂隊的三個姑娘而言,音樂是她們反抗壓迫,爭取女性權利的武器;對於阿富汗國家音樂學院的學生而言,音樂是他們擺脱苦難和戰亂的階梯。

我們也瞭解到,阿富汗15歲以下的人口占比高達42.3%,這些青少年生於塔利班倒台之後,他們享受過世俗化的娛樂和自由,除了音樂之外,一切藝術、體育和娛樂都是他們的夢寐以求,有些人甚至願意為此冒着死亡的風險。
塔利班攻佔首都喀布爾時,18歲的少年扎基·安瓦里從美國運輸機上掉落身亡,而他逃離阿富汗的初衷,不過是有個足球夢,想有一片綠茵場。

目前,塔利班政權在這片土地上勢如破竹,嚴苛的禁令之下音樂何時再寵愛這片土地還未可知。
我們只能為阿富汗祈禱,祈禱在這片沉默的土地上,年輕人還能夠不忘卻人性本真的渴望選擇音樂,選擇用藝術突破壓迫的藩籬,不再迷信暴力和極端宗教,還願意為現代化和世俗化努力。
畢竟,在阿富汗扛起吉他比扛起槍支更勇敢。
排版 | 安林
本文為音樂先聲原創稿件,轉載及商務合作,請聯繫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