屬於三代人的時代盲盒,為此我吃了上千袋乾脆面_風聞
福桃九分饱-福桃九分饱官方账号-同名微信公众号:futaojiufenbao。2021-09-14 14:15
飽弟都沒想到,2021年了還能聽到“精神鴉片”這個詞兒。
前不久對未成年人沉迷網遊的整治政策出台,有媒體再一次提出網絡遊戲是“精神鴉片”,引發了一點爭議。
對這個説辭,飽弟不能再熟悉了:呵,想當年我們集水滸卡的時候,也被人説是精神鴉片呢。

可這些水滸“鴉片”,到頭來毒害了誰呢?最起碼,飽弟沒有。
相反,那套卡片對我的意義,遠遠超過了玩樂本身。
甚至可以説,那段為卡痴狂的童年,永久塑造了我,決定了我今後二十年的人生道路。

© 老濕alwayswet
之前,有過好幾篇文章回憶1999年,統一小浣熊乾脆面開始贈送水滸卡後,全國中小學生為之瘋狂的日子。
他們常常提到的一點是,那時的水滸卡,是中小學生的通用社交貨幣,大家彼此交流、互通有無,其樂融融。
嗯……其實在我印象中,事情沒這麼簡單。

▲要你集卡氪金的手遊頁面,才有金燦燦的童年
© 《小浣熊百將傳》
要指望小孩兒像成年人一樣,進行彬彬有禮的資源置換,根本沒那麼容易。
孩子愛炫耀,炫耀引人眼紅,眼紅便要交換,於是有哄抬卡價、囤積居奇的,也有故意不換就是氣你的,自然引發爭端,所謂社交,往往以扭作一團,引來班主任沒收雙方卡片結束。
**對“貨幣”的反應,小孩和大人其實一樣。**為這一套卡,大家搞得雞飛狗跳不説,歐皇和非酋的分野,也無形中為走入社會的小學雞們,飛快劃分了階層。
當你手裏有十八張小遮攔穆春時,倒不會遭到多大嘲笑,但當身邊所有男生都有一張飛天大聖李袞而你沒有時,你難免會感到被孤立。

▲就這張!當時都集吐了……
更讓人頭大的是,你都不知道他們哪來的時間和錢,怎麼就突然攢下了比你多好幾倍的卡。
那時我還不知道,這一切問題要通過多吃多買才能解決,甚至靠這也不一定能解決——只是因為,你運氣不好。總之,玩卡的過程捲入了不可避免的攀比,交流就不太讓人愉快。
受困於這種焦慮,我早早退出了集卡競爭,自己玩自己的,提前用個二十年後的詞兒:躺平了。真是三歲看老。
然而,集卡的樂趣並未由此消失,相反,這份樂趣一下變得更大,也更讓人回味,甚至保留至今。
今天想想也好笑,那時我的沉迷,竟然把全家人都捲入了。
一開始,當爸媽發現我像其他小孩一樣沉迷於這東西時,自然想到了無數社會新聞,從而提高了警惕。畢竟,上一代“精神鴉片”電子遊戲廳被清出街頭,不過是頭兩年的事兒。

▲上世紀的電子遊戲廳
後果可想而知,自然是軟硬兼施,苦口婆心也有,口頭威脅“燒掉”也有,當然動手是沒有的了——最嚴重的情形,不過是我爸悄悄把我的一捆卡扔到簸箕裏,我媽也當我面撕掉過一張卡以示警告。
事實是,那張被撕掉的卡是重複的(我都有哪幾張卡他倆特清楚),何況,如果真想讓這東西永久消失,誰會把一捆卡扔在孩子書房門口的簸箕裏,連垃圾都不倒的!
想想也對,畢竟我和我哥之前唯一一次進電子遊戲廳,就是我爸帶着進去的,而且是他玩,我倆在背後看着。
當然,玩心再大,我們也不會光顧着玩卡而把乾脆面扔掉。如果附近真出了一個扔面的小孩,而他的家長竟然不加攔阻,這在我們一條街看來都是震驚而可恥的。
結果,這成了水滸卡不是“鴉片”的一個例證:鴉片越抽越瘦,而我勤勤懇懇、滿懷熱情地吃掉了每一包面,身形和收藏一起日漸豐厚。
有時看見我抱着麪餅咔嘣咔嘣,爸媽看我吃的倍兒香,都會忍不住掰下一塊嘗一口。
這一嘗不要緊,它真成了我們好些天的早餐——一家三口也不知道乾脆面與方便麪的區別,於是我媽愉快地把乾脆面煮了,還打了個雞蛋。

© giphy.com
這可不能怨我們,那時候的乾脆面是真材實料,麪餅實在不説,哪怕不撒料包都有味道。
小浣熊的烤肉味鹹中帶甜,五香牛肉味香氣足,香辣雞翅味辣不傷人,但小虎隊的羊肉串味更絕,那股味道煮了都不難吃,哪像幾年後什麼“魔法士”,麪條又細麪餅又膩,咬一口活像碎木頭!

▲小浣熊烤肉味yyds!
抱着對水滸卡和乾脆面的雙重喜愛,我的集卡生涯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而如此長時間的遊戲,背後沒有“金主”支持,斷不能持續——
我的乾脆面基本都是姥爺給買的,一次五包。
那段時間,每週末的五包乾脆面幾乎成了定例,而姥爺對買面集卡的熱情,幾乎跟我一樣。
他是個畫家,也教人畫畫,書櫃裏收藏了巨多的人物畫冊和線稿,還有大量的小人書,倒不是為了看,而是工作上的參照。

▲50年代人民美術出版社編繪的《水滸》連環畫
所以對水滸卡,老爺子也保持了一定的興趣,每次我拆出卡來,他還會擺在桌上,戴上老花鏡認認真真品評一下:
“行,這張畫得好。”説完像遞給學生滿分試卷一樣交給我。
“這什麼玩意兒!”一看出畫師偷懶,他就撂下不看,然後一張張疊起來拿給我,讓我去玩兒。
每當他誇的時候,我都聽不太懂,直到後來看了他書櫃裏的資料,才稍稍明白一點點誰畫得好與不好,雖然還是不明白陳老蓮為何把人臉畫得像樹皮,而任伯年的人物又常有一張扁臉。
而姥爺也經常看不懂,為什麼鼓上蚤時遷會把自己包得像個木乃伊,而且好像只有兩個腳趾頭——他收藏的畫冊資料裏,自然是沒有日本忍者的。

日復一日,我從大人身上看到了更多不知道的事。
每當我和我哥玩卡玩得天昏地暗時,家人總是不免批評幾句,只有爺爺對此幾乎不置一詞,也沒説過,也沒誇過。
直到某天,爺爺跟我們説:水滸卡嘛,我也有。
我倆不知這句話從何説起,可看着爺爺鄭重其事的表情,又不由不信。他取出一個老樟木盒子,掀開鏽黑了的銅鈕,取出一疊一寸長的小卡片兒,有的半新不舊,有的皺皺巴巴。
每一張背後,都印着“大新煙草公司”,顯然是我太爺爺解放前沒戒煙那會兒攢下的,有年頭了。我倆赫然看見一張呼保義宋江,直接傻了——
放在今天,這是多少小孩夢寐以求的至寶。

▲差不多長這樣,不過這位藏友保存得比我們家好
© 華宇拍賣
盒子裏頭還有一個藍皮小本兒,鉛筆字寫着那些沒集全的好漢姓名。從本子的花色來看,這次記錄的時間,不會比我倆出生早多久。
原來爺爺才是集卡大神!從此我倆就服了。
那段時間,電視台都趕着蹭熱度,央視版電視劇《水滸傳》一遍又一遍放,大家都看熟了,收視率也居高不下。
一個週日上午,我正趴牀上玩卡呢,我爸問我:電視上播《水滸》呢,看不看?老《水滸》。
我又一次將信將疑地跟去了。是從沒看過的一部《水滸》,畫面有點模糊,像老香港劇,演員穿得都挺舊,像唱戲,但有如連環畫裏的人物,個個有神。
我爸看得比我都投入。後來我知道,那是他的青春。

▲80年代山東版《水滸》,武戲是當年內地劇的頂配
後來有一天,我在書店裏翻開一本一百二十回《水滸全傳》,看到徵方臘時,史進和石秀竟然死於亂箭之下,心裏刷一下涼了半截。我很想知道,兒童書、電視劇、水滸卡上都沒講的故事裏,到底發生了什麼。
結果,那天出書店結賬,店員看看手裏一本精裝大部頭,又看看沒櫃枱高的我,問我姥爺:“您買錯了吧?”
我姥爺笑笑:“是買給我外孫的。”他從沒懷疑我能否看懂這本書。
拿回家我就不住地翻,略過不懂的“灑家”“則個”“奢遮”一些詞,硬啃下來了。那是我除了幼兒園背唐詩之外,讀過的第一部文學作品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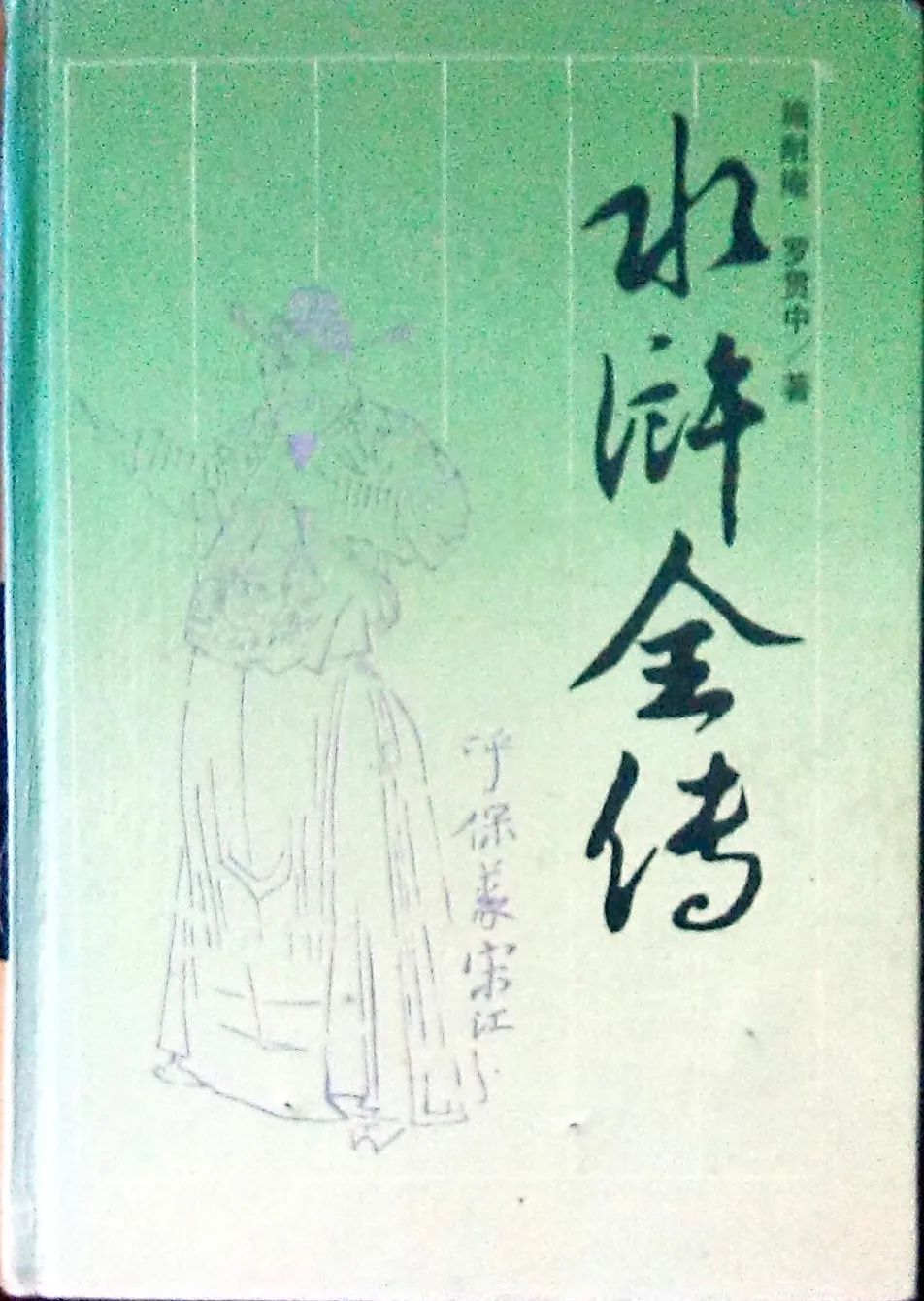
▲就是這個嶽麓書社的版本
雖然整個小學,我的每一位語文老師聽説此事,都認為我們是一家子吹牛大王,但從此爸媽對我讀課外書這件事,就放開了膽量。
結果是,我爸為我搜羅《水滸》相關讀物時,愣帶回一本學術隨筆——我倆根本對學術倆字沒概念,一個真敢買,一個真敢讀。
於是,那本書教會了我未來思考一些文化問題時,唯一能用上的粗淺功夫。
按説那時候,我們一家人不會想到,卡片對一個小孩的未來有多重要,尤其當新玩具流行起來,我把那套不全的卡片束之高閣後。
可後來,那段為水滸卡而着迷的日子,確實改變了我很多。
那之後我明白了,玩物不惟能喪志,有時反而能立志;
我明白了讀“閒書”是天經地義,人不能被課本上那點兒知識框住;
我明白了“玩兒”這件事不分年齡,就像讀書也不分年齡一樣。
長大後,聽了很多人的卡片被撕毀丟棄,連同記憶一起飄散的故事,我也明白,不是每個人都幸運如我,遇到了如此開明又富於智慧的親人。
那些水滸卡,爸媽今天還替我留着,乾脆面的味道,我也沒忘。
更不可能忘掉的是,他們在我七歲那年,決定讓我成為獨一無二的我自己。
水滸卡最終沒有害到我,就像無數被稱為“精神鴉片”的東西一樣。
也許這世上,本來也不至於有那麼多“鴉片”。
本文圖片部分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