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招待所的故事(二)_風聞
外交官说事儿-外交官说事儿官方账号-让更多人了解有血、有肉、有情怀的中国外交官2021-09-15 14:06
**作者:**孟京生,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員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調入外交部的幹部。
我父親在江西因心臟病嚴重,幾次差點兒就彎過去了。他心寬命大,雖多次情況十分危險,但都挺過來了,一直到2020年4月底去世,享年107歲。在世時他是外交部八九千離退休幹部中的第一老壽星。

孟英 (1913-2020年)中國前駐桑給巴爾、中非、蒙古大使。
1971年秋,父親獲准回京治病。翌年春夏回江西幹校,1972年11月再次回京治病。我母親一直同行。


父親母親年輕時的照片
這次回來我家住在老樓225房間,是在招待所最北側,臨東交民巷街面。
1973年初,招待所開始收拾老樓二層西北角的幾個大套間,又鋪地毯,又搬沙發。不久搬進來一些不認識的老者和中年人。
我們好生奇怪,外交部的幹部大都彼此認識,不認識的我們也聽説過,這些人是何方神聖?天天有服務員專門“伺候”,後來向服務員一打聽,説是外交部請來的畫家,給聯合國畫畫的,不是外交部的人。


黃胄先生及其作品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都是剛剛“解放”的,有的直接從外地的“五七幹校”來此報到的,都是大畫家。我年少孤陋寡聞,只知道有個畫驢的黃胄,還一個是李可染。黃胄住西北角的套間,李可染住我家旁邊隔一個門,據説是周總理親自安排的,待遇比外交部這些從幹校回來的人好多了,畢竟人家是為國家在工作。
平時看見黃胄老帶着幾個人,可能是他的學生。那年“五一”節看見黃胄穿上綠軍裝,戴着領章帽徽出來進去的,才知道他是軍人。黃胄穿上軍裝也不像個軍人,沒有軍人的風采。
那時候,剛剛被“解放”,從外地回京的大畫家們看上去都挺土的。他們的房門常常大開,過來過去的人可以看到外屋中間的大案桌,專門給他們畫畫用的。


畫家黃胄及其作品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黃胄年輕一點兒,跟服務人員關係特別好。房間的服務員、傳達室看大門的、食堂的廚師、迎送組的司機,黃胄都送過畫給他們,以感謝他們的服務。他長於畫新疆姑娘、葡萄和毛驢。我親眼所見兩個服務員拿着兩張他畫的驢,在比較評論着,是剛剛送給他們的。
那會兒這些畫家剛剛從“文革”的苦難折磨中解脱出來,見到普通人,大人孩子都挺客氣,沒什麼架子,我們也沒覺得他們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


畫家李可染及其作品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李可染的房門總是大開的,老者可能有時刻敞門的習慣。我每天都得經過個十回八回的,有時好奇往裏看一眼。
有一天,母親讓我下樓打開水,我拎着兩個暖壺就去了。回來路過李可染的房間,門依舊大開着,他自己一個人在畫畫。我也不知道動了哪根筋,徑直走了進去。他正在作畫中,瞥見有人拎着暖壺進來,連頭也沒抬説了句:“放那兒吧。”我説:“這是給我們家打的,我們自己還用呢。”他這才抬起頭來看了我一眼。
我那時年輕,也不大懂禮貌,直接就説:“從這門口路過進來看看畫畫,我就住隔壁一個門。”老者還真沒架子,客氣地説:“看吧看吧。”
當時只有老畫家一個人作畫,我也沒客氣,把暖壺一放,就站在旁邊看。他畫的是近處有一座矮山,山上有一個亭子,幾個人背身站在那兒指點着更遠的山。畫的大框已畫出來了,正在往山上畫樹木。他拿着一支粗毛筆,在紙上崴了三幾下,一棵樹就出來了,接着又連崴帶拐了幾下,一小片樹林就出現了。
我説:“好玩兒。”
李畫家問我:“上過山嗎?”
我直道:“哥們兒就是虎踞山出來的。”馬上覺得失言,又改口説:“我就是虎踞山出來的,湖南那邊的。”
李畫家又問:“有老虎嗎?”
答曰:“沒有,我是和我爸我媽一起去的‘五七幹校’,茶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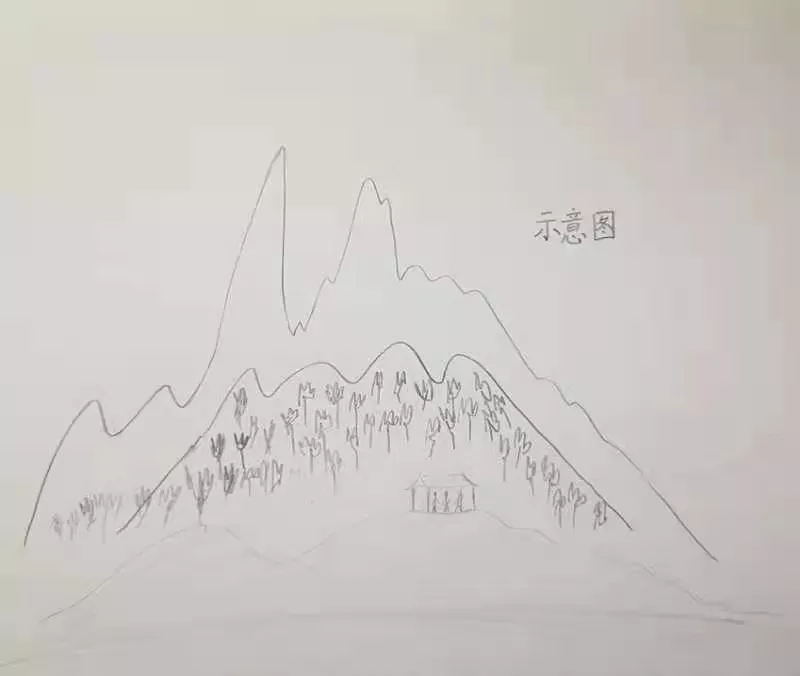
(作者供圖)
他一面與我聊着,一面繼續畫樹,又換了細筆畫亭子裏的小人兒,幾筆就點畫出來了。記不得李畫家是否説自己有否“下放”過,但能感覺到他對“下放”經過磨難的人挺同情的,可能他自己也有類似的經歷。
他一邊畫一邊給我講:“這幾個站在亭子裏的人在濛濛細雨中,看對面的高山呢。”
我問:“雨呢?”
李畫家真不愧為大師,拿起一支毛筆,胡亂在畫上抹了幾下,看上去就像下毛毛雨似的。
我對老畫家説了句找抽的話:“這不是挺容易的嘛。”
人家是大師,不跟我這不懂得深淺的毛頭小兒計較。
接着問我:“你們那個虎山有什麼花呀?”

我回:“湖南春天的杜鵑花好看着呢,漫山遍野的。”
李老畫家想了想,自語道:“這個季節可以。”我也弄不清老者是什麼意思。
李老畫家換了紅筆,好像比較細的筆,調了紅顏色,説:“給你畫些杜鵑花。”説着用一種顏色畫出來好幾種不同的杜鵑花。我那時是小孩子,只覺得挺好玩兒的,認為畫畫挺容易的,這有什麼呀?其實大師的功力我是根本不懂的。

李可染作品《蜀山春雨》
我這人天生膽兒大,遇到什麼場面也不怵頭,跟李大師就聊起來了。我告訴他我家有一張吳作人畫的駱駝,純黑的水墨畫,是兩隻並排站着的駱駝。

孟英大使夫婦與孩子們的合影
(外交部的大人孩子都知道“孟家五虎”,連周總理、陳老總也知道。)
吳作人作畫時問我爸,有幾個孩子,我爸説,五個兒子。他又在旁邊畫了五個小駱駝。我説,最小的那個駱駝就是我,畫上還有我爸我媽的名字。

吳作人的作品《沙漠駱駝》
下幹校時,我爸我媽把這幅畫存在在山東的老戰友張秉玉、常凱家。張秉玉當時在職,任國防部外事副局長。後來説,畫找不着了。
我家分析可能是讓他家的兒子張小五(張長勝)偷着給賣了。這傢伙巨能折騰,改革開放初期和葉飛的女兒一起倒賣進口汽車指標,事發東窗,給抓起來槍斃了。
我爸我媽掬着面子,再也沒有跟張家提過此事。我二哥、三哥1969年底當兵入伍都是張秉玉給辦的。
看完畫杜鵑花,我就説“家裏還等着我的開水呢!”,扭頭趕緊回家。現在想起來真丟人,連謝人一聲都沒説就走了,不懂事的混小子。

周總理與大使夫人王宏瑜(作者的母親)親切握手
從李大師的門出來,幾秒鐘就進了自家門。我媽問:“你上哪兒打水去了?怎麼這麼長時間呀?”
我順口答:“上隔壁李可染那兒看畫畫去了。”
我媽還沒説什麼,我爸就批評我不該去:“人家是給聯合國畫畫的,為國家工作,不要影響人家創作。”


李可染先生作品
(圖片來源:百度百科)
我滿不在乎地説:“我還去黃胄那兒看他畫驢呢!第一次敲門沒人在,第二次屋裏有好幾個人説話,沒畫畫。”

孟英大使(作者的父親)向桑給巴爾總統遞交國書
父親一聽就有點兒急,嚴令我以後不許去打攪人家。他知道我容易惹是生非,走到哪兒都得鬧出點兒動靜來,這種事發生過太多次了,他事先就得警告我。我一看他要急(他有嚴重的心臟病),只好悻悻無語。我在外面敢鬧,回家不敢。

孟家五兄弟與母親(右)、阿姨(左)合影
(大哥孟達林,二哥孟新海,三哥孟大慶,四哥孟和平,五弟孟京生)
幾十年過去了,我一直想找李老畫家的那幅畫,可惜未果。一是不知道畫的名稱,二是畫的去向是給了外交部,也許作為禮品送給了外賓,也許在聯合國或駐外使館某個地方掛着,我想有張照片或COPY也行。李可染在我心目中的印象就是一個普通的凡人,怎麼也跟中外聞名大師的名稱對不上號。
再後來的話,遇到畫畫的牛主兒,我就添油加醋地説 :“李可染給哥們兒畫過畫。”人家聽了,不信:“你丫算老幾呀?人家李可染可是大師,能給你畫畫?吹牛呢吧?”於是我就講這個故事,人家聽完了就不會覺得我吹牛呢,挨點兒邊,靠點兒譜。
京劇表演藝術家郝壽臣
再插一句,遇到梨園界唱戲的,我就提郝壽臣——郝黑頭,解放後當過中央戲校的校長,唱黑頭的,是與梅蘭芳、馬連良齊名的大家。我嬸兒的妹妹——我老姨嫁給了郝壽臣的孫子。我爸在輔仁大學上學的時候與郝壽臣的兒子是同學,因為家庭關係有點兒來往,但是不多。
人的經歷是複雜的,有些事情當你經歷時很不經意,不覺得什麼,隨着時間的沉澱,這些曾經平淡無奇的瑣事開始發酵,而且味道隨着年代的拉長,開始飄香。那些看來不起眼兒的、撂爪就忘的小事兒竟然成為值得回憶和品味的珍藏。
——寫於2021年1月
前文補遺

前文提到:“50年代初,我爸媽到國外任職,就把兩個哥哥放在外交部西郊幼兒園,由公家照看,頂多有父母的戰友故舊領他們去自己家住幾天。”
此照片是我的大哥、二哥與父母的合影。拍照後幾個月,父母就出國了。大哥託養在幼兒園。不到兩歲的二哥先在戰友王文軒、劉鳳家寄養,後長大一些也送去幼兒園了。
之所以寫這一段,是想告訴後人,當年外交官及家屬為國家的外交事業作出了很大的犧牲。不是我們一家這樣,建國初期那一批幹部都是這樣,“舍小家,為大家”,無怨無悔。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