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內訌升級, 中國用行動戳穿了西方謊言, 很多人卻渾然不知_風聞
文化纵横-《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2021-09-21 23:02
 ✪ 瞿宛文 | 中國台灣“中央研究院”
✪ 瞿宛文 | 中國台灣“中央研究院”
【導讀】中國作為一個底子薄、起步晚的後發國家,在追求現代化、工業化和追趕發達國家的過程中,卻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在西方發達國家眼裏,中國卻左右不是:西方自由派認為中國經濟發展背離了西方“典範模式”,國家干預之深,自由市場不存;西方左翼則批評中國的發展過程犧牲了生態環境、勞動者等方面的利益。為何會出現這種認知局面?未來又該如何認識和推動後發國家的經濟發展?
本文強調,理解後發國家的發展問題,首先要將對經濟發展的認識予以歷史化。西方憑藉其在全球的優勢地位,將後發地區捲入現代化進程,並形成了一套聲稱西方現代化模式就是“普遍、必然、常規的模式”的意識形態。但用西方今天的經濟社會制度來指導後發國家,既遮蔽了西方發達國家之所以發達的那段真實歷史,也忽略了殖民歷史和不平等的南北關係對後發國家發展所造成的巨大制約。作者指出,如今西方逐漸走向衰落,這一歷史性變化正是提醒後發國家不應,也不能再將西方視為天經地義的唯一模式,必須進一步審思西方模式的優劣點,如此才能反思並修正方向,掌握自身現代化命運。畢竟,西方的現代化只是現代化的一種方案,只有當各國都成功建立各自的現代化社會,才能構成“普遍性”現代化。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1年第4期,原題為《反思工業文明與經濟發展——後發者的視野》,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供諸位參考。
▍反思的時機
在新世紀進入第三個十年的時刻,新冠疫情席捲全球並且似仍難見到盡頭,異常天氣的頻現也讓人感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諸多因素都促使我們反思現代工業文明與現代經濟發展,思考人類文明的發展前途。
與此同時,全球既有的政治經濟秩序開始發生重大變化。“二戰”後,美國主導了全球資本主義體系。20世紀90年代初冷戰結束後,美國更是獨霸世界。然而近二十多年來,世界上發生着種種重大變化。**尤其在此次新冠疫情發生後,西方發達國家不但未能起領導作用幫助其他地區,其本身更未能做出“依據科學與理性,做出有序反應”的榜樣,其疫情嚴重程度竟高於很多一向以西方為學習對象的後發國家。新世紀以來,體量巨大的中國快速復興,實質上帶來對西方領導權的挑戰。**現實國際秩序的動盪也加深了人們對工業文明發展前途的疑慮。
**反思通常是帶有懷舊與浪漫情懷的。工業文明難以引發浪漫情懷,疫情下更易讓人懷疑現代工業文明的可持續性。**例如,在當今中國,“唯GDP論”“發展主義”“工業黨”等貶抑性新名詞多是為了貶低發展而生。同時,反思常是普世性的,不會特別區分先發者與後發者思考立場上有何差異。西方發達國家一般認為現代經濟發展是普世的、進步的,當然應從普世角度來反思;而後發國家作為跟隨者也多習慣於接受這樣的視野來反思自身。
然而,在此世界大變動之際,後發者必從後發視角進行反思,才能瞭解自身,掌握歷史動脈,真實且深刻地反思現代經濟發展模式。
數百年來西歐發展出來的現代文明,是人類發展歷史上的一環,其模式優勢甚為顯著,並已主導世界數百年之久。只是這一模式走到今日呈現出諸多問題。這些問題既內在於現代工業文明,也內在於西方的文明傳統。西方發達國家若要進行反思,必須要同時思考這兩個面向。對於後發國家來説,反思的面向除了包括上述面向之外,更要涵蓋自身學習西方現代化的進程與結果,才能脱離將西方模式視為普世的桎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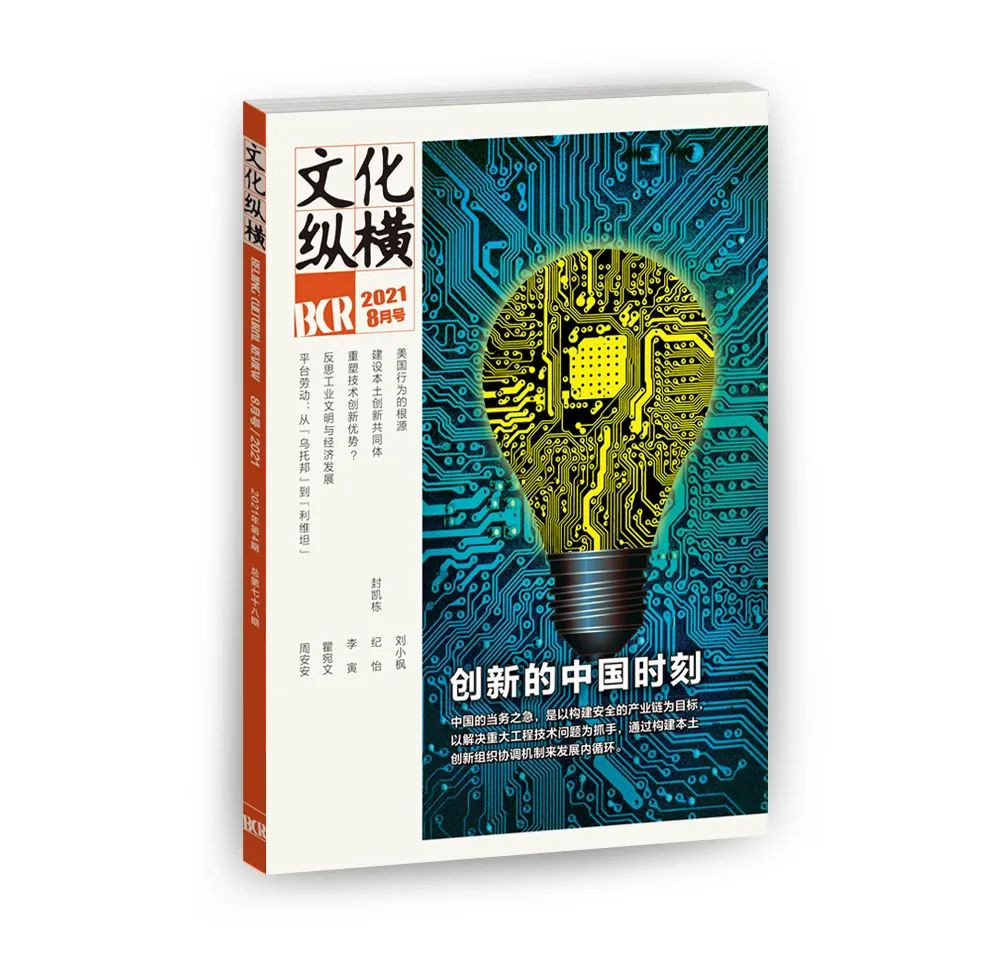 ▍一般的看法
▍一般的看法
對於現代經濟發展,現在一般看法多采取普世性角度,假設其為“常規性”的目標。即假設後發者追求現代經濟發展,是為了趕上人類進步的步伐。這樣的反思多為懷舊式或普世性的:懷舊式即認為現在不如過去,懷念農村小農田園生活;普世性則更專注於環保、生態、空氣污染、疫情、動物保護等面向,並常將其選擇的目標作為最優先的,甚至唯一的價值。**這背後有一假設:後發者對於現代經濟發展,可以有要或不要的選擇權。但是,這樣的反思不單是去歷史化的,並且也不具現實性。後發者追求經濟發展,是為了在西方主導的世界裏自救求生存。**西方社會的發展程度較高,而後發者的選擇空間受制於自身相對於西方的經濟實力。例如,19世紀西方相較於其他地區享有絕對優勢,因此其他地區幾乎皆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到了21世紀,其他地區的經濟力量已有所增長,但經濟實力仍是現實國際秩序的基礎。
現在經濟學一般的看法是以“生產力”水平來定義經濟發展,以人均產值或人均所得為指標。例如,依據世界銀行估計,在2019年美國的人均GDP是65298美元,我國是10262美元,這意味着以當期現值計算,美國的人均產值或生產力水平是中國的6.4倍。但由於中國經濟體量大,GDP總量為14萬億美元(全球佔比16%),達到美國21萬億(全球佔比24%)的三分之二;再加上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快,金融危機發生時的2008年,中國GDP全球佔比僅7%,到如今,十多年翻了一倍多;又積極推動產業升級,因此特別引發西方關注。
在經濟實力之外,意識形態的競爭也同樣重要。數百年來,隨着西方優勢力量主導世界,西歐現代化模式被廣泛視為人類發展的典範模式,不但代表人類的進步,更是普世的典範。這也是一個高度規範性的説法,即其他地區必須且應該努力追隨。換言之,這種模式被認為是人類進步下“常規性”並且“自然”的發展模式。這個典範模式包含以下因素: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民族國家、自由民主政治模式、公民社會、全球化。
本文提出的看法是,我們不應假設這種模式是“常規性”且“必然或自然”的,如此我們才能進行有效的反思,才能在自身推動現代化(仍為必要)的同時,尋求不同的路徑。
我們先檢視一下西方學界的發展經濟學。發展經濟學是“二戰”後發展起來的。“二戰”後許多殖民地國家在陸續取得政治獨立後,必須推動經濟發展,追求經濟獨立。西方學界發展了這一知識領域,立意為協助後發地區發展經濟,探討後發者如何向先發者學習、提高生產力,發展現代化經濟。這一研究思路的基礎是線性進步史觀,即假設西方發展模式為常規性的典範。此外,發展經濟學還有諸多重要的“中性”的假設:即不處理政治與社會的面向、先發及後發地區間的關係、殖民影響與當今的南北關係等。其研究的基本方向是針對後發地區經濟與成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距離,而要發展經濟,無非就是逐步建立市場制度,去除“非市場化”障礙。換言之,**其假設後發地區經濟落後,不是因為過去曾經被殖民且現今仍受制於不平等的南北關係,而是因為自身市場制度與政策不完善,教育落後,知識不足。**發展經濟學因此認為,當地政府若有意發展經濟,必然要接受由此理論推演出的政策建議。
顯然,**西方發展經濟學認定的經濟發展目標是非歷史化的,它假定西歐現代化模式是人類發展的普世典範。這一假定是説現代經濟發展是為了提高人民福祉,而西方模式是最佳或唯一模式。其實,提高人民福祉只是發展的結果而非發展的動力。**經濟學者、哲學家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設法提升發展目標,認為不應該只看物質生產與物質生活的改善,更應衡量人的能力(capability)成長,發展應是為了讓人得到實質上的自由。受此影響,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於1990年起,開始統計“人類發展指標”(human development index)。這一指標除了人均所得之外,還計入平均壽命與識字/就學率。這樣的修訂當然提高了西方發展模式的層次與理想性。然而,在歷史與現實中,現代經濟發展僅僅是源於提高人民福祉的動力嗎?
▍後發者視野
在當下,後發地區在形式上,確實會以追求現代經濟發展為當然目標。然而在歷史與現實中,後發地區在被西方殖民之前,都是在各自的傳統模式中發展,社會結構、文明程度、生產力水平各異。隨着西方列強以優勢力量強力向外擴張,19世紀末的西方已完成瓜分其他地區為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過程,而其他地區在經歷過這段屈辱的歷程、建立現代國家之後,開始追求經濟發展,主要動力是為了追求自身的生存與尊嚴。
**換言之,後發地區是在西方壓力下被迫追求現代化經濟發展,而不是為了所謂要提高人民福祉自主地追求現代化。**即使是最快速且最早成功實現現代化的模範後發者——日本,也是在美國黑船壓境迫使日本簽訂不平等條約之後,才走上加速改革推進現代化的道路。所有後發地區都是在走過這段屈辱的過程後,才認識到:唯有在實現現代化、發展經濟且有實力後,方能做地球村裏有尊嚴的村民。
各後發地區原本走在各自發展的道路上,發展程度也不一樣。到19世紀,大部分地區的生產力與自我組織能力顯著不如西方,而西方殖民統治則毫無例外地高度改變了當地的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在取得政治獨立後,當地社會必須重新自我組織,建立有效的現代化政治組織,以追求發展為目標,才能走上重生和現代化之路。但是重新全面改造社會談何容易,建立有效的政治組織更是困難重重。“二戰”後至今,只有極少數地區能夠成功追趕,縮小與西方的距離。
例如,**典型的殖民地經濟至今依舊普遍存在,大多數後發國家仍然依靠出口大宗商品(能源、礦產、農產品)為生,就如在殖民地時代一般。**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2016年出版的《大宗商品依賴度報告》,統計了各國大宗商品佔總出口值的比例,將該比例大於60%者定義為依賴國,比例大於80%者為強依賴國。在2015年,總共135個國家中,91個為依賴國,其中61個為強依賴國。同時,這些依賴國的出口商品類別少,依賴度越高,可能越貧窮,食物安全度越低,因為多數依賴國也是食物淨進口國。發展趨勢顯示依賴度仍在增加中。
**後發地區若尚未能工業化,僅能出口大宗商品是否是“必然的”現象?答案並不那麼簡單。**尚未工業化的後發地區,確實不能出口現代工業產品,而只可能出口農礦產品及手工業產品。然而,**它們在被殖民之前,經濟上可能是自給自足,或者低度商業化、生產多元化。將生產活動集中於少數類別的農礦產品,並且以出口為主,大多是殖民者強制給予該地區的國際經濟分工位置。從傳統的自給多元轉變為高度商業化、集中專業化、高度依賴出口,這種經濟模式的轉變並非“必然”。**指出這差別並非為了懷舊或表達義憤,在現實上走回頭路早已不是選項,但要真正理解後發地區的歷史與處境,不看到路徑依賴的面向,將無法掌握後發發展的真相。
“二戰”後西方學界建立起來的發展經濟學,一則假設西方模式為普世典範,現代化是人類必然道路,其他地區只是時候未到,只須學習追隨;再則依據其“科學中性”的研究取向,去政治化、去歷史化,不單忽視殖民的影響及南北經濟關係的制約作用,更假設後發者已成功重組政體,假設後發國家的政府必然以追求現代化及人民福祉最大化為目標,因此發展經濟學的工作只是提出中性的政策建議。這門學問從西方先發者的角度,假設了一個抽象普世的理性經濟世界:後發者只待學習跟上來。
相較於此,要真正理解後發地區的處境,推動發展並進而設想未來,必須先放棄西方現代經濟發展模式是“常規與必然”的假設,以後發者的視野,回到歷史現實,正視殖民遺產與南北關係的影響,面對自身政治社會組織重組的挑戰,才能開始理解自身,也才可能有效推動自身的現代經濟發展。
▍成功後發者的反思
後發者作為學習者,必須自覺地認識到學習雖屬必要,但仍要理解西方模式的文明特殊性及其侷限,參考其優劣點且注意對自身的適用性。再則,可進一步區分尚未成功以及已初步成功現代化的兩類後發者。
尚未成功的後發者,除了上述的考量之外,需要更好地瞭解自身,理解並學習較為成功的後發者的發展經驗,才能踏上現代化之路。
後發國家在初步達到工業化之後,較有餘裕進行反思。一方面,需要檢視自身現代化的狀態,要意識到自身是在既有的文化傳統基礎上學習西方現代化,實際上的現代化成果必會是一種混合的狀態——如亨廷頓所言,一個社會不可能隨意改變自身的文明與價值。另一方面,則需要參考目前顯現出來的發達國家的困局,思考如何避免重蹈覆轍,同時思考如何改善全球現代化的狀態與進程。
**人類社會走到21世紀時,比較有條件檢討數百年來居於主導地位的西方模式。因為至今已有一些後發國家達到初步工業化,其中包括體量特別巨大的中國,這些新興工業國家給全球經濟分佈帶來很大的變化。**發達國家佔全球所得的比例,從1820年工業革命即開始持續上升,但從1990年起這一比例首次開始下降——從大約六七成至今已降到低於50%。製造業的分配比例也呈現同樣巨大的變化,其中中國製造業佔全球的比例從1990年的3%升至近三成。這些非常具體的現實改變,才有可能使後發地區站穩腳跟,獲得尊嚴,也是後發者進行反思的堅實的物質基礎。
**近二三十年來,歐美發達國家陸續顯現出發展上的困局。**全球化快速推進,尤其是金融資本迅速擴展到全球各地,逐利全球,除了為後發地區帶來金融波動與危機外,也帶來了席捲全球的2008年金融危機。**金融化在發達國家內部造成資本逐利短期化、生產性投資減緩、製造業生產力停滯以及內部貧富分化越趨嚴重的趨勢,經濟上的分化則帶來政治上的民粹化。**與此同時,雖然全球流動的金融資本對全球秩序帶來風險,但在缺乏國際協調下卻難以因應。此外,科技雖持續快速發展,但是生產力進步卻趨緩,帶來的現實問題是失業增加與貧富分化。此次新冠疫情更是出乎意料地給發達國家帶來嚴峻的考驗。
**西方國家走向衰弱,也使得後發地區比較有條件以較為持平的角度來檢討西方現代化模式,較有條件看清楚這一模式的優劣處,更重要的是,應較能“歷史性”地看待西方模式。**西方國家的現代化模式不是人類“常規性”“必然或自然”,雖然它主導了世界幾百年,但是我們現在也目睹了這一模式開始走向衰落。這一模式也可能在未來經由修正而得到復興,但無論如何它都是立基於西方文明而具有內在有機生命——就像中國以往的朝代興衰一般。
▍歷史視野
**如果拉長人類的歷史來看,近數百年來西方資本主義模式實是一特殊案例。**西歐在羅馬帝國衰亡後並未如中國一般發展出大一統的帝國政治傳統,而是諸國持續競爭搶奪資源的模式。**英國在其中率先發展出一個高效的政治模式,即精英合謀向外爭奪資源的政治軍事體制,包括有效的財政及金融制度,並進而發展出民族國家範式。**這個高效的政體以逐利為目標,有效地擴張了對外掠奪的經濟模式,並且發展出資本主義制度,進而推動了工業革命,為人類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工業及物質文明的躍升。但這一文明模式的向外侵略性高,不斷征服其他地方,佔取為殖民地。這當然迫使其他地區必須追趕現代化,才能自強。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已清楚地指出,資本主義是一個人類前所未有的制度,它不斷帶來生產方式的革命,不斷地改變社會,並且市場競爭也迫使資本家必須不斷更新才能維續自身的地位,這是至今唯一一個不斷顛覆自己的制度。它的成功迫使其他國家也採取同樣制度,以免被消滅。至今資本主義已帶來驚人的生產力進步。只是如今科技進步與整體發展的矛盾日增,生產力進步的成果難以廣泛分享,不斷擴大貧富差距。
因此,西方模式宣稱具有“普世性”的説法面臨多方面的挑戰。西方模式的普世性必須在幾方面得到現實上的支持才能成立。一是適用性,即此模式可適用於其他地區,也就是其他地區能夠藉由複製此模式,成功地實現現代化經濟發展。事實並非如此,“二戰”結束以來,只有少數後發國家能夠縮短與西方的距離,這其中中國因體量龐大才得以使發達國家所佔比例開始下降。另一方面則是可延續性,這既包括西方本身是否能持續其繁榮的局面,也包括在現代工業化文明對生態的破壞之下,西方現代工業文明能否持續。目前西方開始衰退為前者的前景帶來顯著的不確定性,而近年來的氣候變化問題也對後者提出挑戰。
▍肯定、否定與非必然論
關於西方現代化發展模式“能否複製”的理論問題,依據其答案可分為肯定論、否定論、非必然論。肯定派包括主流新古典經濟學派,其認為後發者只須努力學習並完善市場制度,發展只是時間問題。肯定論也包括對馬克思理論的某種解釋,即依據辯證法認為資本主義殖民者終會在殖民地激發出資本主義的鏡像。肯定派理論可説都是自詡為放諸四海皆準的普世性理論。
否定論則包含依附理論及世界體系論等,這一類理論在左翼理論中較為強調西方對其他地區的掠奪剝削,認為新舊殖民關係都會導致後發地區難以發展;在強調該關係之不平等之時,否定論基本認定後發者將無力改變自身的命運。這部分理論雖未必完整且爭議紛紜,但由於與西方現實政治多有關聯,因而有廣泛影響,在此稍作討論。
20世紀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的戰後黃金時代告一段落。在後發地區,拉丁美洲的戰後起點雖高於其他地區,但是戰後前期其發展成績不佳,成長甚為有限,這樣的發展成績引發了依附理論與世界體系理論等。這些理論雖對西方資本主義體制提出嚴厲批判,但幾乎否定了當地能突破受制命運的可能性,認為除了脱離資本主義體系之外別無他途。既然後者的可能性不大,該理論就不太關注本地主觀能動性的因素。
當時出現的另一重要的現實發展是東亞的“經濟奇蹟”,與拉丁美洲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對於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同樣有着上述三種不同説法,在此且先來討論否定論。東亞的成績清楚地提供了依附理論的反證:依附理論認為後發者越依附發達者,則越不能發展。然而,東亞藉由高度參與國際市場,尤其是出口初級工業產品到發達國家市場,成功啓動了自身工業化的引擎,若依據該理論將貿易額佔GDP的比例當作所謂“依附”的指標,則東亞的依附帶來的不是發展停滯,而是快速增長。**依附理論者如何因應這一理論挑戰呢?他們大多認為東亞表面上GDP的成長,源於對環境與勞動力的剝削,缺乏生產力的進步。實際上也是以所謂的“普世價值”來否定後發者的發展成績。雖説隨後東亞經濟持續升級,並清楚地呈現出生產力不斷進步的現象,但他們多未改變意見。**近年來,在中國經濟顯著復興之後,他們除了延用這樣的批評之外,也以貶抑性的“國家資本主義”稱之:亦即在普世價值之外,再以左翼階級觀點來否定中國的發展成果。
依附理論主要是通過指陳西方的剝削,使得依附於西方的拉丁美洲無法發展,在這一理論説法中,“發展”仍然被當作一個可欲的目標,重點是要探討如何成功地發展,依附程度與發展成果是否成負相關,則是一個可被檢驗的説法。但是,在面對東亞及中國的成功發展之後,他們卻提出各種標準,來否定東亞及中國發展的價值,似乎顯現出這些理論流派最關切的重點是維繫對西方資本主義批判的立場,而不是後發者能否成功發展。
本文一再強調立論的“立場”之重要性,此例可説又是一個佐證。**西方左翼學者在戰後長期處於發達國家的國內邊緣位置,立場多以反對資本主義為第一優先,對於原先落後的東亞竟然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得以發展自身經濟,他們無法有同情的理解,也無法認同後發地區發展優先的立場。**同時,又牽涉出幾個所謂“普世價值”的議題——諸如環境保護、勞動力剝削、民族主義等——以此來否定後發者的發展成績。
**若脱離時空,這些目標看起來甚為正當,其國際主義精神也令人嚮往。但是,我們要首先看到時空與立場是更為關鍵的因素。**數百年前,西方發達國家率先形成資本主義體制並進而發展了先進生產力,其在環保與勞動保護上也走過歷史性長期演變的過程,而推動社會主義的力量更是伴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演變。換言之,西方“進步分子”提出的批判,特別是針對較成功的後發者的批評,其實意味着要求後發者在推動經濟發展時,要同時達成環保、勞動、階級等目標,並在後發者藉由民族主義動員人民共同發展經濟之時,否定民族主義的作用。這些理論不考慮時空因素,徑自以所謂高道德標準來否定後發者的發展成果,顯示出其“立場”是以自身反對資本主義為優先,而不顧及後發者的處境。
其次,這些説法也與當今國際的南北現實政治相配合。
**在政治現實中,近數十年來,隨着資本全球性的移動,西方工會既然難以要求限制資本的移動,即配合着上述左翼的論述,發展出以環保及勞動條件為約束性規範,來降低其他地區勞動力的吸引力。這顯示出勞工難以跨國集結的現實困境,致使西方勞工將後發地區勞工視為競爭者,而在現實中這些議題也與西方的帝國政策相聯結。即西方各國在與後發國家談判,要求其開放市場的同時,也提出環保與勞動標準要求,一則安撫國內勞工與左翼,再則可作為對應新興後發國家的彈性籌碼。這也涉及階級與國族問題的複雜性,即在歷史現實中,國族因素多優先於階級因素,勞工階級的跨國聯結甚為困難,但西方發達國家統治者在殖民時期,以種族主義及殖民利益來籠絡國內的下層階級卻是常例。**例如,英國19世紀大殖民者羅德斯即常以維持英國國內的安定來合理化他在非洲的殖民冒險計劃。**近年來西方發達國家民粹政治上升,恐怕也是因為如今難以用殖民利益安撫下層,只能訴諸種族主義與國族主義。**而西方進步左翼的論述則為中間政黨,如美國民主黨提供了支持性的説法。
當然,也有些為數不多的發達國家學者,如安士敦(Alice Amsden)與阿瑞吉 (Giovanni Arrighi)等,認識到後發地區只有依靠經濟發展才能有尊嚴,也只有當它們發展了經濟之後,才能自行設法解決貧窮、平等、環保等問題,因此真誠地期望後發地區能發展起來。他們的立場與價值的優先順序,顯現出跨越國族的國際主義精神,恰恰與上述的一般西方進步左翼方向相反,令人感佩。
不同於肯定論與否定論,本文認為(包含安士敦在內的)結構學派的部分理論可以延伸解釋為“非必然論”,即後發發展是有可能的,但不一定會發生,更不一定成功,這其中當地的主動因應實為關鍵因素,但也必須要有主客觀條件配合。
非必然論牽涉到後發發展“如何成功”的問題,引申出近數十年關於如何解釋東亞經濟奇蹟的爭議,即被稱為是state vs. market的爭議。主流經濟學派宣揚自由市場理論,認為必須遵循市場規律,政府必須儘量少干預市場,後發地區才能發展。結構學派則認為東亞的成功有賴於有效的國家干預,成功的因素包括政治高層有堅定意志支持發展,經濟建設部門的官僚體系有能力並具有鑲嵌自主性,能實行合宜與時俱進的產業政策,發展成果能較為平均地分享等。後發國家與地區的不同發展經驗背後,顯示出各自文化上的顯著不同,也呈現出各自條件的複雜組合——大家都是被迫地學習,而成功實為不易。
除了客觀因素之外,不同於肯定論與否定論,非必然論強調國家合宜政策的關鍵作用,將歷史的與本地主觀能動性的因素納入考量,因此較能解釋後發國家與地區不同的發展成果。
劍橋大學經濟學者張夏準的著作《踢開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指出西方國家,尤其是要追趕英國的後發國家如美法德等國,在開始發展的初期都有賴國家大力干預,來扶植幼稚的工業及建立相關制度等。只是如今這些西方國家早已發展,卻要求後發國家不要照做,其實就等同於已攀登者踢開梯子,不讓後來者跟進。**他建議後發者學習發達國家過去實際的行為,而不要理會現在的説法:即西方主流經濟學自由市場論的説法,也是近數十年來全球主導性的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由於後發者本來就缺乏完善的現代市場制度,自由放任只能維續既有的貧窮狀態,因此,要發展現代經濟,必須改革政治、社會與經濟制度,建立現代經濟體制,施行合宜的產業政策,這些艱難的工作特別需要國家集中力量而為之。結構學派的先驅A. Gerschenkron曾指出後發的難題:**經濟越落後,市場制度越不完善,就需要越加強力的市場制度替代品——國家干預。**新自由主義基於自由市場原則反對國家干預,西方左翼的否定論基於普世價值及階級論而批判成功後發經濟體的國家干預,若依循兩者都會使得後發者失去推動發展的制度基礎,無助於經濟發展。
如果將視野拉長,歷史性地審視現代經濟發展,就更加能夠理解非必然論其實合乎常情。如果我們不再將西方模式視為是常規性或自然,那就清楚其沒有必然性了。此外,西方左翼的否定論認為後發必然難以成功的説法,也早已有了重要的反證。以往之所以將西方模式視為常規性,自有其現實基礎,一方面是西方數百年來的優勢力量提供了物質性支持;另一方面也有理論支持,除了既有的西方現代化理論,也有左翼馬克思理論的經濟決定論及人類社會發展階段論,這些都是西方現代化鼎盛期的樂觀看法。歷史發展至今,西方模式面臨嚴峻挑戰,這正是我們重新審視“西方模式是常規性的”説法的良好時機。而一旦放棄這種既定説法,思考的空間也就能變得開闊起來。
▍多元現代化
探索人類發展的規律當然是一個重要的知識計劃,倡導歷史化的探索絕非否定發展規律的可能性。這是一個嚴肅的知識課題,需要我們持續探討。本文僅提出重新思考既有説法的必要性。
一、後發者自身文明不同於西方,檢視自身混合式的現代化成果實屬必要,必須歷史性地來看這一歷程,認識自身傳統,不應再將西方視為唯一典範,如此才能有效地反思並修正方向,掌握自身現代化道路,尋求永續發展之路。
二、如今西方逐漸走向衰落,這一歷史性變化正是提醒後發者不應,也不能再將西方視為天經地義的唯一模式,必須進一步審思西方模式的優劣點。在意識形態激烈的競爭中,面對肯定論、否定論與非必然論,後發者也必須明辨何者真正有助於自身發展。
同時,這也意味着後發者不僅需要自行摸索未來發展的道路,也應該擔起責任來共同探索多元現代化的可能道路。西方的現代化迫使全球隨之改變,但仍只是現代化的一種方案,只有當各地都能成功建立各自的現代化社會,才能構成“普遍性”現代化。
本文發表於《文化縱橫》2021年第4期,原標題為“反思工業文明與經濟發展——後發者的視野”。文章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特此編髮,供諸位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