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農民工“更名”,不如提高勞動者保障_風聞
石佳佳律师-律师-公众号:律界佳族-做有人文情怀的好律师2021-09-22 21:41
最近“人大代表建議倡導媒體不使用“農民工”等語言,深圳人社局回應”一事引起了人們的關注。據悉,有人大代表向深圳市人社局建議:“政府倡導各方媒體在宣傳上,不使用‘農民工’等歧視性語言,讓業者有尊嚴,並出台政策,提高從事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就業者政府主導評分積分體系權重。”深圳人社局的答覆為:“經核查,目前人民日報、新華社等中央主要媒體在報道中對‘農民工’羣體仍然使用‘農民工’表述。2019年12月4日國務院第73次常務會議通過的《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也採納了‘農民工’表述。對照相關法律法規、對標中央主要媒體報道,我市雖不能要求本地媒體不使用‘農民工’表述,但也將結合深圳實際,引導新聞媒體多使用‘來深建設者’表述,並指導督促本地媒體加大對來深建設者宣傳力度。”
對於此事,最大的爭議點在於“農民工”一詞是否有歧視性含義。嚴格來説,“農民工”一詞只是對這一羣體身份的客觀描述,百度百科對“農民工”一詞的定義為:“户籍地在鄉村,進入城區從事非農產業勞動6個月及以上,常住地在城區,以非農業收入為主要收入的勞動者”。可見這只是箇中性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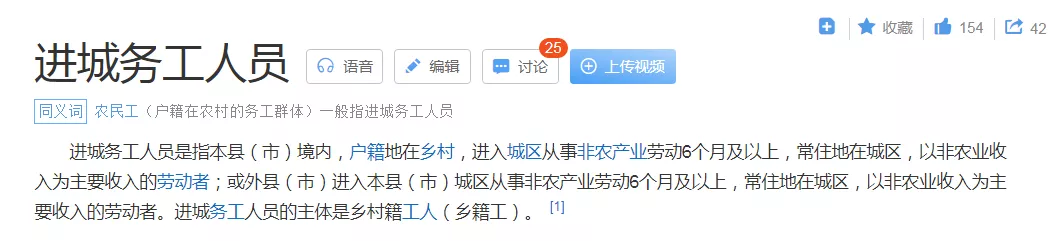
然而,一箇中性的詞彙,在使用上可能會因為被指代對象的實際狀況而產生超出這個詞語本身以外的含義。比如我國在歷史上曾被稱為“支那”,“支那”起源於印度。印度古代人稱中國為“chini”,據説是來自“秦”的音譯,中國從印度引進梵文佛經以後,要把佛經譯為漢文,於是高僧按照音譯把chini就翻譯成“支那”。由於在古代,我國長期處於世界領先的地位,因此“支那”一詞往往帶有幾分尊崇之意。到了清朝末年,反清革命志士為了與清政府劃清界限,也常以“支那人”自稱,民主革命先驅宋教仁還專門創辦了革命報刊《二十世紀之支那》。只是伴隨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敗給日本,日本以支那稱呼中國漸漸帶有了勝利者對失敗者的蔑視之意,國人感受到了這份侮辱,因此開始對“支那”一詞反感起來。1930年,國民政府訓示外交部∶今後凡載有“支那”二字的日本公文一律拒收。
從“支那”一詞內涵的演變可見,一箇中性詞,其是帶褒義還是貶義,與這個詞本身無關,而跟其指代的對象在社會中的實際地位有關。

提起農民工,我們首先會想到什麼?灰塵漫天的建築工地,混着汗漬粉塵的衣着,令人同情的討薪橫幅還是春運期間被大包小包壓彎了腰的五六十歲中老年人?總之,是弱小的、辛苦的、髒兮兮的、可憐的底層形象。他們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在繁華的大城市裏有着深刻的自卑,不僅生活環境相對惡劣,甚至工作內容也非常危險,並且老闆還往往不願意為他們買社保。這類弱勢羣體,在受着體面人的同情的同時,也受着無形的鄙夷。他們所從事的工地、外賣、煤礦、搬運、維修、流水線被世俗認為是沒出息的活。孩子,包括農民工自己的孩子,從小就被教育不要成為從事這些辛苦卑微行業的人,哪怕有些農民工的收入遠比在乾淨寬敞寫字樓裏996的白領們要高得多。
正由於“農民工”一詞藴含着新時代無產者們那麼多沉重、痛苦、麻木的經歷,所以在精英眼裏,在那些體面人眼裏,“農民工”已經成為卑賤的代名詞。他們害怕這個兼具了工人、農民雙重身份的字眼刺痛了他們眼中底層人的自尊,引起不滿,從而破壞了他們生活的安寧,便絞盡腦汁地去創造更温馨、更高尚的詞彙來粉飾農民工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不堪。可是無論給農民工們換上怎樣高雅的代名詞,他們還是那羣在老家種莊稼已經養不活自己而不得不來城市賣苦力的農民,還是在風吹日曬中揮汗如雨、滿身疲憊的工人,還是受了老闆欺負敢怒不敢言不知該怎麼維權的討薪人。
不給他們提高勞動保障,不給他們的子女提供更多的上學機會,不給他們的老家創造更多的希望,換再多的好聽的代名詞,最終的結果都是一樣地變成“歧視性”語言。畢竟童話代替不了現實,人間還是那個人間。
做有人文情懷的好律師,歡迎關注微信公眾號:家事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