鄰里噪音,日常地獄_風聞
直面派-直面派官方账号-讲述值得讲述的真实故事,直面生活、命运和内心2021-09-23 09:37


又一次,傅嶽被樓上“砰”一聲巨響吵醒了。他看了下時間,已經快要凌晨一點。白天裏那種眩暈、胸口發悶的感覺又回來了。他氣得呼吸急促,飛快起身衝進廚房,隨手抄起一把菜刀,決心上樓跟製造噪音的鄰居拼了。
剛出家門,傅嶽突然停下來,他想:“我是坐電梯上去呢?還是走沒有監控的樓梯?”十來秒後,隨着理智慢慢恢復,他開始為剛才“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衝動感到後怕,身體不受控制地發抖。
和樓上鄰居因為噪音發生衝突三個月以來,傅嶽曾無數次冒出過類似的危險念頭,這是離出事最近的一次。
傅嶽985高校畢業,工作幾年後,在蘇州攢錢付了首付,然後結婚、生子。在旁人眼中,他一向體面、情緒穩定,而讓他一反常態,出現文中最開始失控行為的源頭,是樓上住户不定時發出的噪音。
樓上100平的房子住了六口人,兩個老人,兩個青年,兩個小孩。傅嶽時常聽到小孩在地上跑跳,從晚上七八點持續到十一二點睡覺為止;大人發出鼓搗東西的聲音,像是在打掃衞生;老人的動靜則集中在早晨,買完菜做早飯的時候。
在長期噪音的侵擾下,傅嶽幾乎變成了另一個人。一天晚上,他一聽到樓上的“哐當”聲,站到牀上,對着頭頂的天花板一頓錘,手關節流的血順着手臂濺到牀單上,疼了好幾天。儘管那聲音並不大,但他已經習慣第一時間跌入厭惡、抓狂的情緒裏。

在樓上鄰居看來,傅嶽有點小題大做了,鄰居説:“你耳朵這麼敏感,肯定有問題,是不是對我家有什麼目的?”妻子也勸:”商品房多多少少會有點聲音。”
“小題大做”,受鄰里噪音困擾的人常被這樣指責。在偌大城市裏,馬路的車流聲、基建裝修的“轟鳴”聲、廣場舞音響、甚至空調外機運行的“嗡嗡”聲,都足以掩蓋這些微小、隱秘而持續的鄰里噪音。
事實上,鄰里噪音很常見。我國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大興房地產建設,完成了從“筒子樓”、“單元樓”到商品房的更迭。如今,城市樓房往往多而密,比如廣東城中村的一些握手樓,兩户窗的距離甚至不到半米。
老一輩人和街坊有多年的感情基礎,包容性和意願更強,但在那些新社區裏,陌生人從天南海北匯到一起,生活習慣的不同,會將樓上樓下迅速分化為不同陣營。即使搬家,也難以確保下一任鄰居就能合乎心意。
據2020年“全國生態環境信訪投訴舉報管理平台”數據顯示,全年羣眾舉報共44.1萬件,其中,噪音擾民問題佔比41.2%,僅次於大氣污染。
醫學顯示,長期接觸噪音會導致噪音焦慮,造成失眠、抑鬱和神經衰弱。不少人因此性格大變,和鄰居大打出手。裁判文書網上,與“噪音”有關的文書高達43240篇。
然而,這個羣體鮮少被關注,更缺乏救濟。

傅嶽多次上門溝通、給小孩送上水彩筆、遙控汽車,直到樓上覺得過意不去,兩人開始聊起教育、吐槽物業,慢慢有了鄰居的樣子。這個過程,他花了一年。
傅嶽調解完矛盾8個月後,中國的另一端,劉國強的故事走到尾聲。他和樓上長達3年的噪音拉鋸戰,最終以他被判了一年半結束。
劉國強是個年輕小夥,從2016年開始飽受樓上鄰居的噪音折磨,投訴、報警、調解……通通沒用。一些噪友在羣裏安利震樓器,劉國強花600多塊錢買了一個。賣家跟他説:“我保證你用幾天,樓上肯定不吵了!”
震樓器是一種震動馬達,使用者希望通過用其製造噪音,讓鄰居體驗到等量的痛苦,從而達到一種威懾平衡。在鄰里噪音的戰爭中,它常被視為最有效的反擊手段之一。
當晚,劉國強戴上耳塞就睡,把震樓器支在天花板上,開了一整晚。第二天,樓上果真收斂了許多,沒幾天就主動上門求和。看着之前一直挑釁的鄰居突然服軟,劉國強很滿意,很快停用了震樓器。
沒想到一個月後,樓上突然又鬧起了大動靜。有人分析,這是經典的“敵疲我擾”戰術,在對方放鬆戒備時突然反擊,會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劉國強每天上班都魂不守舍,滿心都想着怎麼對付樓上,經常劃拉手機屏幕,不停地刷着QQ羣友們和鄰居鬥智鬥勇的事蹟。他們的反擊提議越來越激進,甚至有人開始直播砸鄰居家門。
羣友們一波波對鄰居的言語討伐,給劉國強壯了膽。劉國強心想:忍了這麼久,是得給樓上點顏色看看了。他用502膠水堵了樓上的門,樓上也不甘示弱,從陽台往下潑水,“正好”灑在劉國強家晾的衣服上。局面越來越僵。
出事那天,樓上男人叫囂:“有本事今天你就把我打死!”換在以往,這事兒多半吵吵完就各回各家,繼續明爭暗鬥了。

但那天,劉國強不知道哪裏來的怒氣。他一把將鄰居抱起來,從半層樓梯上摔下,瞅着鄰居一動不動地躺在地上,撞破的頭往外汩汩冒血,劉國強慌了。
鄰居的傷勢比劉國強估計得嚴重,因為傷到了腦部,對方可能變成植物人。劉國強因此被法院判刑一年半。
在這場噪音戰爭中,所有人都輸了。
像劉國強這樣對噪音製造者實施激烈反擊的人,終究是少數。通常,人們在遇到鄰里噪音時,有兩條路徑,一是私了:通過物業、社區街道、鄰居溝通調解;二是求助公權力:報警、起訴。
鄰里噪音類型很廣,比如蹦跳或走動、開關門窗、敲擊和鋸東西、拖動桌椅和傢俱、電視樂器等發出的噪音,大多發生在上下樓層之間,難以界定和取證。現有法律,也多是圍繞交通、施工噪音施行。
我國住宅噪聲標準是白天不能超過55分貝,晚上低於45分貝。而一個28公斤的兒童從沙發上跳到地面,瞬時噪音就可能高達60分貝。
當這兩種努力都落空後,人們才會考慮反擊或搬家。然而房價高企,大部分人都不具備隨時搬家的能力。於是,如何合理反擊,在無休止的鬥智鬥勇中奪回短暫的安寧,就成了這個羣體做夢都在思考的問題。
傅嶽也曾加購過震樓器,那東西在他購物車裏靜靜躺了三個月,還是被他刪除了。傅嶽説,如果不是家人勸阻,他很可能會成為下一個劉國強。
2019年,傅嶽的噪音糾紛解決後,業餘時間開始運營“安靜之家”的公號和微信社羣。人對噪音的感知不同,別人很難和他們共情,甚至經常被指摘“矯情”、“敏感”。只有在抱團的社羣中,傅嶽和羣友才會擺脱現實世界中的那種異類感。
這些全國各地受噪音折磨的人,在互聯網上化成了一個個暱稱,大多跟“樓上”“噪音”“反擊”這些字眼有關。咒罵和幻想反擊,構成了羣裏的主要生態。

晚上六點多,周小琴下班回家,縮着脖子輕手輕腳地開門,比做賊還要小心翼翼。進了自己家後也不敢開燈,就靜靜地坐在沙發上玩手機,黑暗中,手機的微光照亮了她的臉。
周小琴面對的問題比傅嶽更棘手。傅嶽的樓上鄰居是無意識影響到別人,而周小琴的樓上晝夜不休地製造噪音,純是出於惡意報復。
剛搬進杭州新居的半年裏,周小琴從沒被噪音困擾,直到她家樓上鄰居懷疑水管是被周小琴家堵的。物業檢查後證明,水管堵了是因為樓上洗衣服時沒掏乾淨,在業主羣裏提了一嘴這事。興許是覺得沒有面子,自那之後,一場長達3年的報復開始了。
只要周小琴開燈,樓上的“交響樂”就吵鬧不停。跳繩、拖傢俱、馬桶沖水、往地上砸鐵球……“乒乒乓乓”的動靜能從晚上六點多持續到凌晨,不論周小琴躲到哪個房間,都不得安寧。
樓上是自由職業,吵鬧到凌晨四點是常事。周小琴求助於社區,社區只是打電話給對方口頭教育,沒有任何作用。
周小琴不是沒有努力過,送水果、發紅包、請吃飯,樓上鄰居每回剛接受禮物時會消停幾天,但很快又恢復原樣。
周小琴上門溝通,樓上把門開了一道小縫,説:“我什麼都不知道,以後別來我們家了。”周小琴再要説的時候,對方開始破口大罵:“誰讓你之前把我家水管堵了!”此時,距離堵水管的事情過去了兩年。
有一次,樓上鄰居砸完地板,兩人在路上遇到了,他看着周小琴得意地笑。周小琴盯着他,罵了一句髒話。樓上鄰居笑容凝住,轉身走了。當晚,鐵球砸地板的聲音變本加厲了。
那段時間,周小琴的丈夫晚上睡不好,白天開車上班時出了車禍,修車花了一萬多,不敢再上路。周小琴自己也整夜睡不着,頭髮大把掉,記憶力下降,上班經常遲到,屢次被領導約談。

丈夫不喜歡周小琴老提噪音的事,勸她把注意力放別的地方。周小琴逐漸意識到,自己的狀態不對勁,只要有一丁點聲音,整個人就會繃緊。她去醫院看病,確診是抑鬱症,每月吃藥花銷三四千。
距離周小琴1000公里外的張果在河北,同樣飽受噪音困擾。
張果備孕了一年多,去醫院光檢查費就花了小一萬。醫生説,夫妻倆生理上很健康,就是心理太焦慮了。
今年上半年,周小琴搬到同小區的羣租房後,生活恢復了寧靜。只是,噪音脱敏並非一蹴而就,她想起過去還是會哭。
她想過換房子,但第一套房的貸款至今都沒還完,只是偶爾約中介看看房,提前感受那種快樂。那些房子無一例外,都是頂樓。
和周小琴的隱忍不同,30歲的張果更相信以暴制暴。
疫情期間,張果待在家裏,天天聽着樓上小孩3D立體式環繞的聲音。她在業主羣和樓上協商,對方説:“誰家還沒點動靜了?以後你有了孩子也一樣。”
張果瞪大眼睛:我家孩子怎麼可能跟這種人一樣?她希望樓上鄰居在地上鋪些泡沫墊子,減少噪音,但鄰居就是不願意。張果找了好幾次社區居委會,後者都以有孩子為由不處理。
踹門是張果爸爸在另一個小區採取的措施,比張果好聲好氣央求和找居委會都有用。張果爸爸人高馬大,長得“很像黑社會”,好聲好氣和他樓上溝通過幾次,在樓上租户黑着臉表示“孩子本來就愛玩,這是我家你管不着”之後,他直接上樓踹門,踹走了好幾家帶孩子的租户,並跟房東放話:“以後再租給帶孩子的,來一家趕走一家。”
“我爸耳朵不好使了,但還是被逼到這份兒上。”張果也想衝上樓踹幾腳,但被丈夫拉住了。
張果丈夫有一家律師事務所,他知道,鄰里噪音糾紛,警察不一定會逮人,但上樓踹門,會。
總之,張果一年半的掙扎並沒有等來好結果。她決定搬家,最近在看一套獨棟的房子。
張果所在地房價均價一萬四五,換房尚有餘力。但傅嶽遇到的北京羣友則沒那麼幸運了。他們大多北漂多年,攢了很久首付,終於買了一套中小户型的房子,結果遇到了鄰里噪音問題。
2009年,傅嶽剛開始工作,聽到的最多的消息是哪裏的房子已經搶完。他曾目睹過用麻袋取錢去交首付款的人。有人告訴他,關於中國房價“這一切才剛剛開始。”在房價上漲的黃金時代,房子質量差一點,隔音不達標,只要能趕上買房都不重要。
傅嶽做過相關調查發現,鄰里噪音跟房價、地段、樓盤、小區高不高檔沒有直接關係。去年五月份,上海陸家嘴的幾個朋友也集中反映了遇到鄰里噪音問題,“你想啊,那兒的房價多少啊?”
那鄰里噪音跟什麼有關呢?跟人羣、行業、素質有關。外來人口多的城市,如北上廣深,鄰里噪音最嚴重,尤其是學區房,學區房鄰居經常能聽到小孩哭鬧、大人吵架的聲音,羣裏有個姑娘,聽樓上從一胎蹦到二胎,晚上永遠都是雞飛狗跳。

傅嶽們不是沒想過報警。當私下調解、投訴、溝通的渠道一一被堵死後,他們將所有希望傾注在了報警和起訴上。
張果報過三次警。第一次是在疫情期間,民警無法出警,只能幫張果打電話給樓上房東,讓他勸一下租客,情況照舊。
第二次報警,警察出警了,還是上一次那個警察,問她:“你不之前報過警嗎?怎麼又報?”張果嘆氣説:“問題不解決,只能再次報警。”警察上樓讓對方管一管孩子,轉身讓張果簽完字,走了。
最後一次是鄰居報的警。
那天早上,張果和樓上鄰居在電梯裏狹路相逢,張果瞪了她一眼,樓上見狀,小聲唸叨:“有毛病。”張果回嘴:“上樑不正下樑歪,擾民還有理了?”兩人的聲量一個比一個大,樓上開始用手指她,這恰好是張果最討厭的事情。張果怒火中燒,推了她一把。
對方馬上拿起電話報警,張果沒理她,翻了個白眼就自顧自上班去了,前腳剛到單位就被警察傳喚。噪音擾民的事,警察讓張果去法院起訴。
張果丈夫問了事務所裏的其他律師,説法基本都是:全國目前還沒有一例生活噪音勝訴的案件,法官是很難參考的,就算是勝訴了,也沒有實質性的懲罰,所以無解。
報警十幾次無果後,周小琴決定起訴。
她到法院現場諮詢,屏住呼吸,聽到的是這樣的話:“建議不要過來打官司,就算最後贏了,樓上還吵,你還是得報警。”
律師也不建議她打官司,“律師完全代理是八千塊錢,打官司花的錢可比打官司贏賠得的錢多。”
周小琴苦笑,給了律師五百塊錢諮詢費,離開了。
一位經手過類似案件的方律師告訴字母榜&直面派:“如果是鄰居的聲音太吵,處理會比較麻煩。一方面是取證困難,另一方面是訴訟結束,執行起來也有很大障礙。取證難以證明是哪一家發出的聲音,什麼時候發出的,是否超過分貝;執行上,如果碰到不講理的,就是不按照法院判決去做,執行法官也很難對他採取什麼措施,最嚴重的可能會構成“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但關於噪音,國內沒有這個先例,適用的可能性不大。”
像張果和周小琴那樣,一次次報警,在多方周旋中慢慢消耗掉希望的人,社羣裏一抓一大把。苦惱之下,有些羣友甚至提出要移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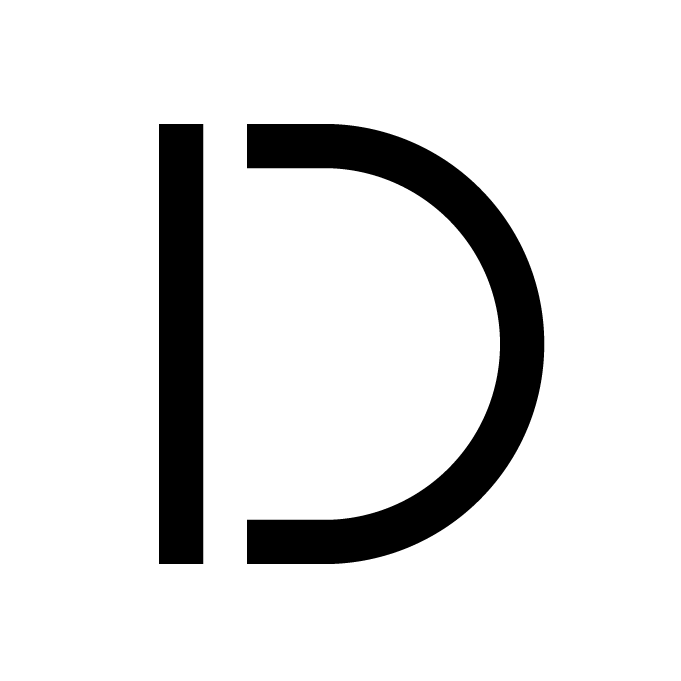
有些國家法律規定,樓層噪音是危害公共環境的行為。
以美國為例,他們官方督查組會在公寓樓一米處測聲,超過45分貝就會被禁止,哪怕是狗叫也不能超過3分鐘。一旦有人投訴,督查組就會帶着檢測儀器趕到現場測試分貝,違規超過3次的人,會被處以525美元~2625美元罰款,當場開罰單。
韓國在2014年實施了《共同住宅樓層間噪音標準規定》,明確了噪音類型:蹦跳或走動發生的噪音;開關門窗發出的噪音;敲擊和鋸東西發出的噪音;拖動桌椅和傢俱發出的噪音;健身器材等運動器械發出的噪音;電視、收音機、樂器等發出的噪音,除了下水道。
噪音標準是日間57分貝,夜間52分貝;對於1分鐘內持續噪音的標準為:日間43分貝,夜間38分貝。一週超過3次超標,就屬於違法範疇。

日本除《環境基本法》外,還有《輕犯罪法》,這是獨立於刑法之外的存在,專門約束那些道德層面上的行為,給予了警察更多的執法彈性。比如,插隊罪、尾隨罪、妨礙安靜罪,可能被處以1日以上30日以下的拘留,或1000日元以上1萬日元以下的罰款。
知乎上有個用户在日本遭遇了鄰里噪音糾紛。
他租的是日本普遍的木造房屋,隔音本就不好,但第一年沒有任何問題。第二年,樓上來了新住户,動靜明顯比第一年大很多,晚上還經常響起生命大和諧的聲音。他不堪其擾,打了日本110。
10分鐘後,到了三名警察,但樓上不開門,警察也沒辦法,留了他的聯繫方式隔天溝通,並説:“如果對方過後再製造噪音,你可以再次報警。”當晚,樓上安靜了。
第二天上午,警察跟他反饋,已經讓樓上到派出所説明情況,調查後會再聯繫他。下午,房東那邊也來電話,先是道歉,説:“樓上是剛搬過來的外地年輕人”,附近鄰居也受到他們影響,已經責令他當天搬家了,並表示之後會登門拜訪。傍晚,警察來電,調查情況和房東説的差不多,他們會對樓上住户保持關注,定期詢問那個人的工作情況和居住地址。末了提醒他,不要在這裏租太便宜的房子。
中國目前使用的《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是1997年施行的,對於鄰里噪音的類型、規定、處罰尚沒有明確的條款。
為數不多關於生活噪音的法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58條:製造噪聲干擾他人正常生活的,處警告;警告後不改正的,處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罰款。
傅嶽指出,中國參考國外的《噪音法》意義不大。
首先,國外地廣人稀,而中國的房子太密集了,住宅壓力不是一個量級。第二,隔音標準不一樣,中國住宅樓板標準厚度是80mm到120mm,日本過去是150mm,現在又調高到200mm。第三,國外法律是健全一些,但是執行起來也有很多問題,只是,比如日本的國民性,他們的文化裏,“管好自己,不影響別人”更有助噪音的溝通。
所以,各國的噪音法條並不具有普適性,還是需要中國自身加快鄰里噪音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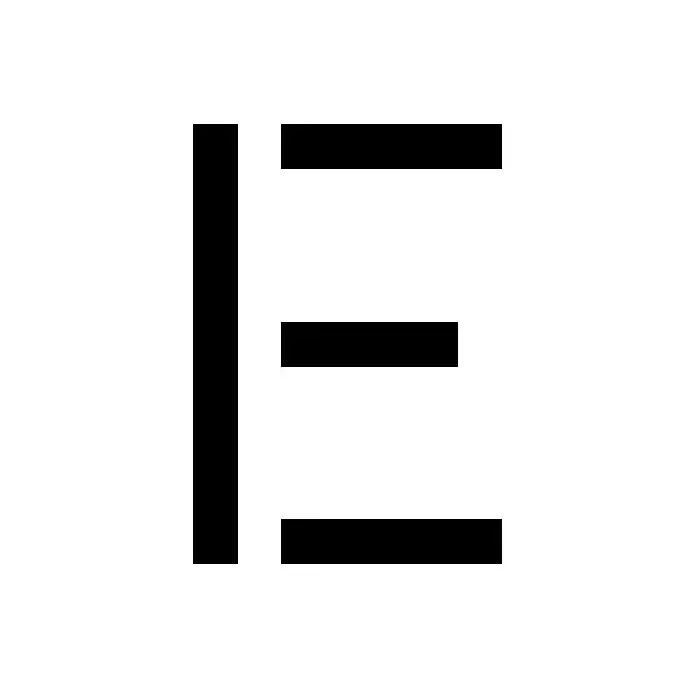
在95後李小雨的家鄉,鄰里噪音被一些傳統思想濃厚的居民認為是“聲煞”,是犯小人,需要專門的符文去解,很多人會在自家門口貼詛咒符。
李小雨和母親一起住在縣城的老房子裏。板樓太老了,沒有物業,隔音糟糕。樓上房東是一名老師,將房子租給了夜店混混,後者經常半夜開Party、喝酒打牌。李小雨跟房東協商了五個月都沒有結果。
有天晚上,李小雨站在一樓陽台窗户邊,窗子裝了鋼化紗窗,外面的人沒法看到裏面。她看到混混用非常恐怖的眼神盯着她們家,和旁邊的人比了一個抹脖子的動作,儘管她知道他們看不到她,但還是生生被嚇退了一步。
房東説:“你的死活關我什麼事兒?我不可能不租房子,除非你給我兩千塊。”李小雨去報警後,反而被樓上老師找的混混威脅,生了一場大病。
李小雨和母親張羅了一場法事,花了好幾萬塊錢。沒有效果。
李小雨崩潰了,給樓上老師發了短信,説要去學校大鬧一場,才把他約出來。“如果不處理,我就直播跳河。”很快,樓上老師就把房子賣了,新租户是一個安靜的大叔。
即使樓上混混已經搬走半年了,李小雨在路上看到跟樓上混混髮型相似的人,還是會下意識覺得那人會害她。“要是那人敢往我身邊靠,我絕對能立刻跳起來把刀掏出來!”
傅嶽遇到懷着6個月身孕,被樓上詛咒孩子是腦癱的女人;遇到有人貸款100萬換房;遇到有姑娘的父親間接因噪音的影響去世,設靈堂期間,樓上依然在跺腳報復;遇到有人寫下“我想像梵高一樣割去耳朵”的投稿。

這些人背後,都是一個因噪音,更確切地説,是因為鄰居的拒絕溝通而破碎的家庭。**他們在求助中的吶喊、沉淪,他人難以拯救,**像醫生面對絕症患者,只是偶爾治癒,常常幫助,總是安慰。
61歲的康爺爺是個老兵。3年前,他因為鄰里噪音,一閉上眼睛,就會想起在戰場上痛失戰友的畫面,炮火轟鳴和衝鋒號的聲音。他身上的彈孔早已被時間癒合,但戰爭遺留下來的PTSD還如影隨形。
老街坊都走了,每當樓上的小年輕夜裏打遊戲,“噼裏啪啦”的鍵盤敲擊聲傳到他耳中時,寂寞就尾隨而來。但他已經一把年紀,很多事情也不想搞明白了。
他不會上網,就將自己和噪音鬥爭的種種細節手寫下來,託女兒發給安靜之家,作為一種告別,然後把老房子賣給了一對做美髮的小夫妻。傅嶽也不知道最後他去了哪裏。
在看房期間,張果學會了自嘲,她在朋友圈發:樓上轟隆了一整天,體力槓槓的,下一屆鐵人三項沒樓上我不看。
去年,傅嶽遇到物業經理,經理曾經調解過他的矛盾。他問:“你樓上這兩天一直在投訴他樓上的噪音,你知道這事兒嗎?”傅嶽這才知道,原來樓上鄰居也開始跟他的樓上斡旋了。唯一不同的是,傅嶽的樓上有兩個小孩,而樓上的樓上是3個。
“安靜之家”社羣裏,人數變動是常事。不斷地有人進羣,為找到組織雀躍,也有人想重新開始,不再被噪音裹挾,他們和傅嶽道完感謝後默默退羣,刪除了所有聯繫方式。
羣聊依然熱火朝天,他們在討論什麼樣的音響反擊更加有效。這時,一個頂着孩子頭像的人連着發了3條消息,最後一條是,“我今天非要給她點顏色看看。”
(本文中劉國強、周小琴、李小雨、康爺爺、張果為化名)
【直面派】原文 -- 講述值得講述的真實故事,直面生活、命運和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