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無神論史》連載16——第五章 秦漢時代神人關係的新見_風聞
国际邪教研究-国际邪教研究官方账号-珍爱生命,愿天下无邪!2021-09-23 09:30
編者按:為宣傳科學無神論,從9月10日起,我們將連載李申的專著《中國無神論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縣人。1969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獲哲學博士學位;2000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轉任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現任中國無神論學會顧問、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中國反邪教協會副會長。
 第五章 秦漢時代神人關係的新見與對舊神祇觀念的否定
第五章 秦漢時代神人關係的新見與對舊神祇觀念的否定
一、天人感應思想的興起及其自身矛盾的暴露
秦漢以前的神人關係,就像傳統的君臣關係或君民關係。臣民要絕對服從君主的意志,君主可以隨意對待臣民。至於君主為什麼這樣而不是那樣對待他的臣民,臣民都是無權過問的。
社會的進步,使君主的隨意性得到了遏制。特別是春秋戰國時代,假如君主不能合理地對待他的臣民,很可能會遭到臣子的唾棄和民眾的反對因而遭受失敗。於是,君主應根據臣民的表現合理地對待臣民,成為一個時代意識。從周朝初年的“皇天無親,唯德是輔”開始,上天的意志表達,也就是他的賞罰,應有一套規則,就日益成為社會的共識。
 然而什麼是有德?所謂諸子、百家的認識就各有不同。老子、莊子主張清靜無為,墨子主張兼愛、非攻。他們的上天或上帝喜歡的德行,也就不同。至於上天如何得知人們德行的狀況,又如何表達自己的喜歡與厭惡,這些思想家們也沒有一個明確的説明。所以探測上天的意志,主要還只能遵守傳統的“天垂象,見吉凶”。而對天象的解釋,早就出現了重大分歧。
然而什麼是有德?所謂諸子、百家的認識就各有不同。老子、莊子主張清靜無為,墨子主張兼愛、非攻。他們的上天或上帝喜歡的德行,也就不同。至於上天如何得知人們德行的狀況,又如何表達自己的喜歡與厭惡,這些思想家們也沒有一個明確的説明。所以探測上天的意志,主要還只能遵守傳統的“天垂象,見吉凶”。而對天象的解釋,早就出現了重大分歧。
從戰國時代開始,許多以前不知的自然現象被人們發現。比如聲音共振。人們發現,彈奏這張琴的宮弦,另一琴的宮弦也會發聲。還有所謂“慈石”吸鐵。慈石,就是磁石。這些現象,都是物體在不接觸的情況下所發生的相互作用。人們把這種作用稱為“感應”。中國古人不認為物與物的相互感應是沒有物質往來的所謂“超距作用”,而認為使兩物發生感應的中介,是物質的氣。就像人到水邊感到涼爽是“水氣”的感應,到火旁感到熱是“火氣”的感應一樣。
這些現象的發現,使人們把眼光投向更多的此類現象。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地上的事物可以和天上的事物發生感應。比如“陽燧取火”。即金屬的凹面鏡可以在太陽底下使易燃的物品着火,這被認為是和太陽相感應的結果。還有所謂“方諸取水”。一個石制或金屬的用具,在明亮的月夜可以生出水來,這被認為是和月亮感應的結果。於是,人們就認為,天離人如此遙遠,也能發生感應,因此,物與物在不接觸情況下發生的感應,是不論距離遠近的。
天人可以感應的明確表達,首先見於《淮南子》。《淮南子·天文訓》在列舉了陽燧見日為火、方諸見月為水的例子以後説道:
人主之情,上通於天。故誅暴則多飄風,枉法令則多蟲螟,殺不辜則國赤地,令不收則多淫雨。(《淮南子·天文訓》)
 天人感應思想就這樣建立起來。並且認為,這樣的感應,是不論距離遠近,都可以發生的:“月盛衰於上,則螺蚌應於下,同氣相動,不可以為遠。”(《淮南子·説山訓》)
天人感應思想就這樣建立起來。並且認為,這樣的感應,是不論距離遠近,都可以發生的:“月盛衰於上,則螺蚌應於下,同氣相動,不可以為遠。”(《淮南子·説山訓》)
到董仲舒,就把從戰國以來所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感應思想,發展為全面的新的神學思想。
董仲舒認為,天,是和人同類的物。同類的物可以發生感應,所以天和人可以感應。人,主要是君主,如果幹了好事,天就會降下祥瑞,以示表揚;人如果幹了壞事,天也會降下災異,以示警誡。如果人能夠改正錯誤,天就會繼續保佑君主。如果不加改正,天就會繼續警告;還不改正,天就會讓他滅亡。好事壞事的標準,就看君主的行為,是否符合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五項原則。
這樣,藉助新發現的自然現象,董種舒建立了完整而系統的新的神人關係。好壞的標準有了,這就是儒家的仁義禮智信五項道德原則;全新的聯繫方式有了,這就是以氣作為中介而發生的相互感應。這時的上天,不再是一個隨意獎勵和懲罰的上天,而是遵守一定道德原則實行獎懲的上天。
董仲舒新的天人關係學説由於有新發現的自然現象做基礎,所以不僅得到了漢武帝的欣賞,而且被學者們普遍接受。董仲舒也被稱為當時的儒學宗主:“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漢書·五行志》)據現有史料,西漢時期被稱為“儒宗”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漢初的叔孫通,另一個就是董仲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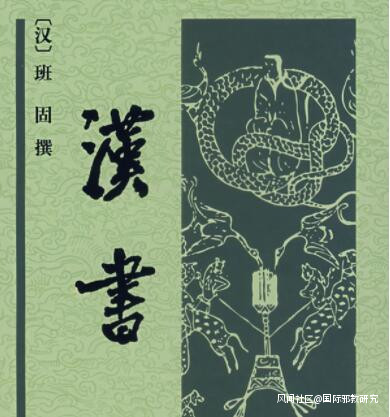 既然是儒者宗主,漢武帝又獨尊儒術,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思想就成為西漢朝廷上處理天人關係的指導思想。從董仲舒開始,儒者們就辛勤地觀察着天象,也包括所有的自然現象。如果發現異常,就推測其中的天意是什麼?推測,人,主要是君主,做錯或者做對了什麼事,從而建議君主發揚或者改正自己的做法。這些觀察的記錄,今天還能見到的,就是篇幅很長的《漢書·五行志》。所謂“五行志”,就是把天地間的一切事物分為金木水火土五類,觀察五類事物中的異常現象,推測其中體現的天意。
既然是儒者宗主,漢武帝又獨尊儒術,董仲舒的天人感應思想就成為西漢朝廷上處理天人關係的指導思想。從董仲舒開始,儒者們就辛勤地觀察着天象,也包括所有的自然現象。如果發現異常,就推測其中的天意是什麼?推測,人,主要是君主,做錯或者做對了什麼事,從而建議君主發揚或者改正自己的做法。這些觀察的記錄,今天還能見到的,就是篇幅很長的《漢書·五行志》。所謂“五行志”,就是把天地間的一切事物分為金木水火土五類,觀察五類事物中的異常現象,推測其中體現的天意。
這樣的推測天意,實際上形成了對君主行為的監督作用,是臣子約束君主行為、使之走向正道,也就是儒家之道的重要手段,對於防止政治腐敗,起到了重要作用。
然而就在天人感應學説被朝廷正式接納以後不久,就發生了問題。
有一天,遼東為劉邦建立的祖廟、劉邦墓上的祭殿,都發生了火災。董仲舒在家知道此事,就從中推測天意。剛寫了個初稿,被前來拜訪的主父偃看到了。主父偃偷走草稿,送到朝廷。皇帝讓臣子們討論。董仲舒的弟子呂步舒不知道是老師寫的,就説這份奏稿是非常愚蠢的推測。於是皇帝把董仲舒下獄,差一點判了死罪。從此以後,董仲舒再也不敢推測災異。
 然而董仲舒的思想影響已經成為共識。漢代朝廷上,每逢有異常的自然現象,從中推測天意,成了重要的政治-宗教活動。漢武帝死,漢昭帝繼承皇位。由於幼小,實際上是大臣霍光執政。元鳳三年正月,山東泰山和萊蕪山南鬧哄哄地好像有幾千人在吶喊。百姓們去查看,有一塊大石頭,四十八圍,一丈五尺高,自己立了起來,旁邊有數千只白烏鴉。昌邑縣有乾枯的社樹復活。國家的上林苑中,一棵斷枯的大柳樹也自己立起,有蟲子在樹葉上吃了一行“公孫病已立”的文字。董仲舒的弟子眭孟認為,這是將有普通百姓做天子。他建議應該到民間查訪賢人,禪讓帝位。霍光大怒,認為這是“妖言惑眾”,把眭孟處以死刑。
然而董仲舒的思想影響已經成為共識。漢代朝廷上,每逢有異常的自然現象,從中推測天意,成了重要的政治-宗教活動。漢武帝死,漢昭帝繼承皇位。由於幼小,實際上是大臣霍光執政。元鳳三年正月,山東泰山和萊蕪山南鬧哄哄地好像有幾千人在吶喊。百姓們去查看,有一塊大石頭,四十八圍,一丈五尺高,自己立了起來,旁邊有數千只白烏鴉。昌邑縣有乾枯的社樹復活。國家的上林苑中,一棵斷枯的大柳樹也自己立起,有蟲子在樹葉上吃了一行“公孫病已立”的文字。董仲舒的弟子眭孟認為,這是將有普通百姓做天子。他建議應該到民間查訪賢人,禪讓帝位。霍光大怒,認為這是“妖言惑眾”,把眭孟處以死刑。
然而五年以後,漢昭帝去世,漢宣帝果然是從民間找到的皇孫,宣帝就把眭孟的兒子封為郎官。
繼承董仲舒事業的,有夏侯始昌和他的侄子夏侯勝。漢昭帝剛剛去世的時候,霍光等人先是請漢武帝和李夫人的孫子昌邑王劉賀做皇帝。不久,他們發現這個昌邑王生活放蕩,不適宜做皇帝,謀劃選擇一個更好的皇子皇孫來做皇帝。這時候,夏侯勝曾攔住昌邑王的車駕,勸他要小心,説有人謀劃要推翻他。霍光懷疑是同謀的張安世泄露機密,但夏侯勝告訴他,《洪範傳》説,天氣久陰不晴,就是有人要謀劃推翻皇上。霍光聽説以後大驚,提拔了夏侯勝,並要求臣子們今後都要通曉一點儒經。
兩方面的事例,有效和無效,妖言和經術,並存在於漢代君臣的心目當中。
西漢末年,推測災異是否有效,是妖言還是經術?衝突更加尖鋭起來。
 現實中,西漢末年的政治,先是漢成帝時,太后王氏的兄弟王鳳當權。當時最善於推測天象的儒者谷永,每次推測天意,都説是批評皇帝:
現實中,西漢末年的政治,先是漢成帝時,太后王氏的兄弟王鳳當權。當時最善於推測天象的儒者谷永,每次推測天意,都説是批評皇帝:
永於經書泛為疏達,……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前後所上四十餘事,畧相反覆,専攻上身與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漢書·谷永傳》)
因此,所謂天意,就成了公開的、政治鬥爭的工具。
漢成帝死,漢哀帝出位。哀帝是元帝的侄子,祖母是漢元帝的妃子傅氏,母親丁氏。母以子貴,王氏的勢力暫時被壓了下去,傅氏、丁氏一度把持朝政。哀帝死,王家勢力又重新抬頭,但是也分成了不同的派別。王鳳的兄弟王音、王商各有自己的勢力。善言災異的谷永、還有杜鄴、杜欽等,對於同一天象,由於他們的政治立場不同,各自攀附一股政治勢力,所推測的天意也就各不相同。班固評論他們的態度和立場説道:
贊曰:孝成之世,委政外家。諸舅持權,重於丁、傅在孝哀時。故杜鄴敢譏丁、傅,而欽、永不敢言王氏,其勢然也。及欽欲挹損鳳權,而鄴附會音、商,永陳三七之戒,斯為忠焉。至其引申伯以阿鳳,隙平阿於車騎,指金火以求合,可謂諒不足而談有餘者。孔子稱友多聞,三人近之矣。(《漢書·谷永杜鄴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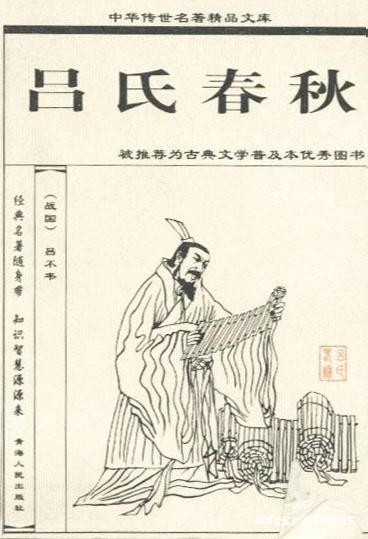 同樣的天象,不同的人從中推測出了不同的天意,那麼,天意到底是什麼?其中是否體現着天意,難免不使人生疑。
同樣的天象,不同的人從中推測出了不同的天意,那麼,天意到底是什麼?其中是否體現着天意,難免不使人生疑。
現實中如此,對於歷史上的天象事件,在西漢末年也產生了許多不同的意見。
所謂“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説的是董仲舒研究《春秋》一書的成果。
司馬遷《史記·天官書》説:“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説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六經,包括《春秋》。“紀異而説不書”,即記載了那些異常天象,比如日食,比如彗星、流星,還有六隻鳥兒倒退飛行等等。但是不説這些天象包含着什麼樣的天意。董仲舒的創新,就是一一補上“説”,即説出其中體現了什麼樣的天意,並和現實的事件一一對應,説明天意的真實和英明。
比如《春秋》記載的宋國同一月發生的兩件大事,一件是“隕石於宋五”,另一件是“六鷁退飛”。董仲舒認為,這是“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劉向同意董仲舒的意見。但是劉向的兒子劉歆則認為,這一年,歲星所在位置,正對着魯國的分野,所以魯國多喪事。隕石那一月,太陽的位置關係到齊國的分野,五顆隕石,象徵齊桓公死後五公子作亂。兩件事都發生在宋國,象徵宋襄公要稱霸,但六年後霸業就要衰落。還有一位重要的占星家京房,他作的《京氏易傳》,認為由於宋襄公“拒諫自強”,才導致了六鷁退飛。
 這樣,董仲舒以外的三個人,就有三種説法,究竟哪一種是正確的呢?而類似這樣地對春秋以來到漢代為止,歷史上數以百計的奇異天象和異常自然現象的評論,幾乎每一件都有重要分歧。《漢書·五行志》逐條列舉了他們的不同意見,這就表明,這些不同意見在當時,已經是眾所周知。那麼,這由董仲舒開創的天人感應學説,後人的見解與他是如此不同,這個學説還能贏得信任嗎!
這樣,董仲舒以外的三個人,就有三種説法,究竟哪一種是正確的呢?而類似這樣地對春秋以來到漢代為止,歷史上數以百計的奇異天象和異常自然現象的評論,幾乎每一件都有重要分歧。《漢書·五行志》逐條列舉了他們的不同意見,這就表明,這些不同意見在當時,已經是眾所周知。那麼,這由董仲舒開創的天人感應學説,後人的見解與他是如此不同,這個學説還能贏得信任嗎!
作《漢書》的班固,在記錄了當時著名的所謂“推陰陽、災異”的專家眭孟、夏侯勝、京房、翼奉、李尋等人的事蹟以後評論道: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貢猶雲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説時君著明者也。
察其所言,彷彿一端。假經説義,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強臣。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這是班固對他們命運的嘆息,也是對他們學説的批評。在班固看來,推測天意天道這件事,連孔門親傳的弟子們都難得聽聞,這些後學又是從何處得到的這些方法。他們“假經説義,依託象類”,各執一詞,不過是“億則屢中”,也就是子產當年批評占星家禆灶的“多言或中”。由此看來,班固對他們的説法、作法,幾乎是持完全否定的態度。
東漢初年的王充,曾師事班固的父親班彪,因此,和班固也當有交往。如果説班固從經學和事實的角度批評了天人感應學説不過是“億則屢中”,王充則從理論上徹底否定了天人學説的可信性。
二、王充對天人感應學説的批判
天人感應的思想基礎,是當時新發現的自然現象。因此,要從根本上否定天人感應,也必須從考察自然現象入手。
 王充考察了當時在天人感應學説中居重要地位的自然現象。比如日食、月食,雷電、水旱災害,蟲災等等。
王充考察了當時在天人感應學説中居重要地位的自然現象。比如日食、月食,雷電、水旱災害,蟲災等等。
天人感應認為,太陽是陽類,是君主的象徵。太陽被侵蝕,象徵着君主被那些不懷好意的臣子們所侵犯。因此,每逢日食,就要罷免那些威脅皇帝安全的臣子。首當其衝的,就是宰相、太尉之類的所謂“三公”。據衞宏的《漢舊儀》,西漢時期,就已經形成了罷免、甚至處死這些大臣的固定程序。而有明確記載的,就是有一次日食,漢宣帝藉故處死了司馬遷的外孫楊惲。王充考察了日食。他發現,“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日,月一食。”它們“食有常數,不在政治。”(《論衡·治期》)也就是説,不是人的行為不端引起上天的警告。
打雷,當時認為是上天的震怒。雷擊,是上天的懲罰。王充考察,雷,是一種火。遭雷擊的物體,常常起火,或者有燒焦的痕跡。而且雷聲雖大,也不過“震驚百里”,遠處的人就不知道。因此,雷電不是天怒,雷擊也不是上天的懲罰。至於水旱災害,他發現,氣候的變遷,有一定的規律:“水旱飢穰,有歲運也”,“天之暘雨,自有時也。”(《論衡·明雩》)因此水旱災害也不是上天的懲罰。
還有蟲災。王充考察發現,蟲災的的發生“必依温濕”;蟲子危害穀物,也“自有止期”,因此也是一種自然發生的現象,與政治和天意,都沒有關係。
王充的第二個方法,是揭露那些被認為是天人感應典型事件的內在矛盾。比如傳言説,鄒衍無罪而被下獄,他仰天長嘆,盛夏的五月天就下起了霜雪。王充説,如果説是因為他的冤情感動了上天,那麼,曾參無罪卻被懷疑殺人,太子伯奇被父親虐待直至放逐,他們為什麼就不能感動上天。因此,所謂鄒衍冤情感動上天的事,是虛言。
 關於蟲災,一種説法是,黑身紅頭的蟲成災,是武官腐敗,惹得上天憤怒;紅身黑頭的蟲成災,是文官腐敗。因此,只要處分相應官吏,蟲災就會消失。王充説,若是白身紅頭或者黃身黑頭或者身頭皆青的等等,又是哪種官吏腐敗呢!因此,這種説法,也是虛言。
關於蟲災,一種説法是,黑身紅頭的蟲成災,是武官腐敗,惹得上天憤怒;紅身黑頭的蟲成災,是文官腐敗。因此,只要處分相應官吏,蟲災就會消失。王充説,若是白身紅頭或者黃身黑頭或者身頭皆青的等等,又是哪種官吏腐敗呢!因此,這種説法,也是虛言。
類似的例子,可説是不勝枚舉。比如周武王渡河時起了大風,武王揮動戰戈,風就停息了;魯襄公激烈戰鬥到黃昏,他一揮戰戈,太陽就倒退了三舍;宋景公三句善言,火星就移動了三舍。甚至堯讓后羿射下太陽等等,都是不可相信的虛言。
從對事實的考察中,王充得出結論,天和人,是不可能發生感應的。其理由如下:
第一,物與物的相互感應,大物體能感動小物體,小物體不能感動大物體。比如天將要下雨,不少小動物都會有特殊反應,但是這些小動物的反應,卻不能感動上天降雨。人在天地之間,就像蝨子在人身上。人聽不到蝨子的鳴叫,上天也聽不到人的聲音。
第二,物與物感應的中介,是氣。氣,就是一種力。力的傳遞,受距離遠近的限制。就像火的熱、水的寒一樣。人離火近,就感到熱;離火遠,熱就衰減。離水近,會感到涼爽,離水遠,涼爽就衰減。一條大魚在水中翻騰,激起的水花,也不過幾丈遠。天非常高,人離天非常遠。人的氣要能感動上天,是不可能的。
王充得出結論:物與物之間,以氣相感的事,有些是存在的。有些也僅僅是“適逢偶會”,偶然巧合。至於涉及人事吉凶之類的感應,則都是適逢偶會,偶然巧合:
 月毀於天,螺消於淵。風從虎,雲從龍。同類通氣,性相感動。若夫物事相遭,吉凶同時,偶適相遇,非氣感也。(《論衡·偶會篇》)
月毀於天,螺消於淵。風從虎,雲從龍。同類通氣,性相感動。若夫物事相遭,吉凶同時,偶適相遇,非氣感也。(《論衡·偶會篇》)
像武王揮戈而風止,那是武王揮戈時恰巧風就停了。杞梁妻痛哭,正好城牆倒了,就説是她哭倒的。鄒衍嘆氣,正好碰上天下霜雪,就説是鄒衍的冤情感動了上天。如此等等,那些所謂應驗的事實,都不過是這種適逢偶會,並不是天人之間的相互感應。至於當時傳言,南陽卓公因為德行高尚,蝗蟲都不入他的縣境。王充説,這也是偶然巧合罷了。假如卓公能感動蝗蟲不入縣境,他能否感動蚊蠅不入他的家門呢?況且蝗蟲這樣的東西,它們聚集在野外,都不是平均鋪開的。沒入卓的縣境,不過是偶然巧遇罷了:
夫蝗之集於野,非能普博盡蔽地也,往往積聚多少有處。非所積之地,則盜蹠所居;所少之野,則伯夷所處也。集過有多少,不能盡蔽覆也。夫集地有多少,則其過縣有留去矣。多少不可以驗善惡,有無安可以明賢不肖也。蓋時蝗自過,不謂賢人界不入明矣。(《論衡·感虛篇》)
也就是説,蝗蟲不過境這種事情,並不能判斷出當地官吏的優劣。
至此為止,王充就完成了他對天人感應理論的考察和否定。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實踐上,王充對天人感應學説的批判,都是正確的,而且迄今為止,仍然有它的理論價值。但是當時的社會需要鬼神,天人感應理論是當時政治生活的神學油彩,也是當時政治生活的監察官。它是當時的政治生活所必須,所以,雖然到了東漢末年,王充的理論廣泛流傳,但是天人感應的思想,卻仍然是朝廷之上的統治思想。儒者們仍然辛勤地觀測着天象和各種各樣奇異的自然現象,從中推測那對當時有用的“天意”,以改進政治,以維護政權的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