別指望法國站隊_風聞
新潮沉思录-新潮沉思录官方账号-2021-09-25 07:48
文 | dlsdyc
2021年9月15日,美英澳三國宣佈成立所謂的AUKUS聯盟。該聯盟旨在加強聯盟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的力量投射,“維護該地區的穩定與繁榮”。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美國和英國將協助澳大利亞建立起一隻核動力潛艇部隊。雖然AUKUS沒有在任何地方提到我國,但考慮到現有的國際政治局勢,武裝澳大利亞劍指何方簡直不言自明。我國第一時間指出,該聯盟違背了核不擴散的基本精神,讓澳大利亞一個無核國家輕易獲得了武器級的濃縮核材料。
澳大利亞建造核潛艇是以撕毀和法國的900億澳元訂單作為代價。而法國一年的軍費也不到900億澳元。美英澳的這種做法無疑高度損害了法國的利益和麪子。自法國總統馬克龍以下,各路官員、前官員都紛紛發表評論,表示決不接受AUKUS聯盟的做法。法國直接召回了駐美國和澳大利亞的大使。當然,在與拜登通了電話之後,馬克龍又同意將把大使派了回去。一時之間,所謂的歐洲戰略自主再一次成為了眾人的笑話。從敍利亞到阿富汗再到AUKUS聯盟,大家不得不問,美國什麼時候會再打歐洲的臉呢。

是是非非潛艇門
時間拉回到2016年。隨着經濟實力的不斷提升,澳大利亞決定進一步拓展自己的海軍實力。作為無核國家,澳大利亞優先選擇了常規動力潛艇作為自己的發展方向。在法日德等多個國家的競標下,澳大利亞最終選擇了法國海軍集團作為製造商。原因有三。第一,法國的潛艇單價較低,長期的維護費用也更為廉價;第二,法國許諾大部分潛艇的安裝製造工作將在澳大利亞完成,這在為澳大利亞帶來工作崗位的同時,也可以彌補澳大利亞所欠缺的產業鏈;第三,法國的潛艇是以核動力為底本進行改造,澳大利亞顯然對積累相關技術充滿了濃厚興趣。

然而正如所有的西方大型工程和採購案一樣,中標的價格絕不是最終的價格。在吃下這筆訂單之後,法國海軍集團對於採購案的預算也不斷飆升,最終達到了900億澳元,超過了原來的一倍。單純價格的上漲不是問題的關鍵,畢竟缺乏相應技術的澳大利亞除了做冤大頭外也沒什麼更好的辦法。更糟糕的是,與法國的核電站建設如出一轍,法國的潛艇建造速度也十分堪憂。預先設定的時間表一拖再拖,以至於可能要在30年代澳大利亞才能獲得自己的潛艇。
聯繫到我國海軍的快速發展,澳大利亞顯然意識到,等到法國人交貨,可能國際局勢早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就在此時,打着“美國回來了”旗號的拜登政府出現了。在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的指導下,拜登政府實行了所謂的戰略收縮和區域協調機制。一方面從歐洲和中東抽身,另一方面在印太地區不斷組建各種區域聯盟遏制我國的影響力。前段時間被大肆吹捧的QUAD四方聯盟就是例證。
AUKUS聯盟不過是其中的最新一環。這一聯盟的直接目的就是對澳大利亞的海上力量進行再武裝。核潛艇技術就是本次交易的重中之重。

對於澳大利亞而言,美英的出現無疑為其改頭換面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澳大利亞船廠已經建設完畢,苦苦等不到法國人開工的情況下,打着瞌睡送枕頭的好事豈有放過之理。尤其是本來核潛艇就比常規潛艇更加適合在大洋地區進行作戰,澳大利亞毫不猶豫地投向了英美的懷抱。
從現在揭露的消息看,從2021年年初,美英澳就開始商量起所謂的核潛艇計劃。三國都十分清楚,法國一旦知曉此事,必然會從中作梗。一切計劃都只在三國內部進行秘密溝通和交流。表面上一切歌舞昇平,無事發生。
僅僅在事發兩週前,法國與澳大利亞還首次開啓了2+2部長級對話。雙方共同討論了對於印度太平洋地區情況的基本看法,尤其討論了所謂的航行自由以及我國在海洋領域積極進取的表現。此舉被認為是法澳之間展現對於印太問題的共同立場,也是法國積極參與印太事務的積極標誌。2016年法澳之間簽訂的常規潛艇訂單自然也是雙方關係的重要象徵。
僅僅兩個禮拜之後,法國人就從天堂滑落到了地獄。按照法國外交部的聲明,法國政府只比媒體提早幾個小時知道了此事。這一“背信棄義”的行為嚴重挫傷了法國人的尊嚴。一時之間,人們紛紛想起了阿爾斯通的前車之鑑。已經開啓競選週期的法國政壇,更是如同打了雞血一般批評三國的不義之舉。
在追求連任的巨大壓力下,馬克龍也直接指示召回駐美國和澳大利亞的大使。歐盟也第一時間支持法國的立場,稱美英澳的行為高度損害了歐洲盟國的信任和信心。一時之間,歐盟戰略自主的問題再一次進入人的眼簾。
然而,隨着拜登的一通電話,似乎一切又開始恢復平靜。在拜登公開許諾為法國在西非地區的軍事行動提供更多支持後,馬克龍決定中止召回大使的做法。法國的迅速服軟使得馬克龍一直高呼的戰略自主更加成為空中樓閣。歐洲國家的戰略自主似乎再一次陷入了雷聲大雨點小的局面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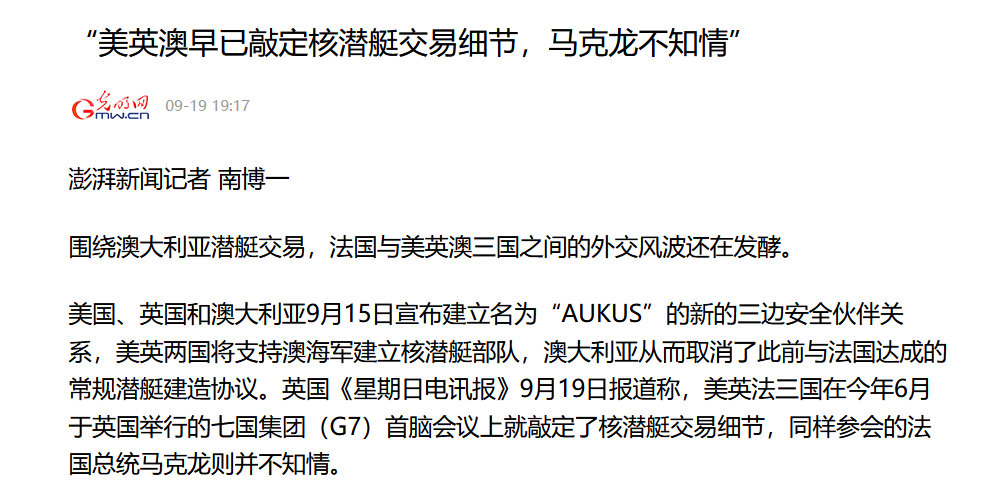
法國的戰略自主之路
歐盟戰略自主問題一直是個老生常談的話題。自歐盟建立起來,一直就有聲音表示歐洲需要建立自己獨立的戰略能力。法國人更是整個戰略自主話題的急先鋒。每次稍有風吹草動,法國人必然高高扛起戰略自主的旗幟。前幾年被馬克龍大力倡導的“歐洲軍”概念就是典型的表現。
法國的積極態度與中東歐國家形成了鮮明對比。波蘭等國家紛紛強調,“歐州軍”在屬性下與北約的部分性質高度重合,沒有必要建立所謂的“歐洲軍”,浪費額外的財政預算。它們的問題反而是,為何法國人如此熱衷於所謂的戰略自主呢?
對於二戰後的法國而言,雖然獲得了戰勝國的地位保住了自己的面子,但依舊抹殺不掉二戰中被德國佔領半壁江山的事實。恢復到二戰前法國的政治地位是法國人普遍關心的問題。作為與英國一樣的殖民體系大國,重新行使對於殖民地的統治是一種有效宣告法蘭西迴歸的方式。整個法國政治界敏鋭地意識到,在戰爭中瓜分了最多勝利果實的美蘇兩國一定不會輕易坐視英法恢復自己的戰前地位。因此,二戰結束後不久,法國就急不可耐地試圖恢復對於法屬印度支那地區的統治。
然而法屬印度支那戰爭、蘇伊士運河危機以及阿爾及利亞戰爭的失敗,直接摧毀了法國重鑄舊帝國的夢想。同樣麻煩的是,由於缺乏足夠的佈局,將前法國殖民地統合成為法共同體的嘗試也沒有成功。從曾經的殖民帝國退縮為歐洲地區國家,如何保持法國作為國際大國的地位,成為了法蘭西政界無法繞過的問題。
所幸的是,雖然喪失了殖民地這一工具,歐洲一體化的風潮為法國開啓了另一種可能性。法國人已然注意到,單純憑藉法國自身的體量不足以捍衞自身的全球影響力。雖然英國和法國同為歐洲國家,但英國更多將自身認知為歐洲大陸之外的國家。在德國、意大利戰敗的情況下,法國成為了歐洲大陸(不算蘇聯)戰後政治聲望最高的國家。**它需要以歐洲作為支點,強化自己的話語權。**代表,或者説主導歐洲聲音,成為了法國外交的重要導向。1959年的歐洲經濟共同體成為了這一思路的重要成果。
在戴高樂的領導下,以不損害法國國家利益為前提,法國成為了歐洲一體化的積極鼓吹者。與此同時,為了強調法國的特殊地位,戴高樂推行了“自由獨立的外交政策”。退出北大西洋公約與我國建交就是這一政策的重要表現。戴高樂試圖以這種方式在外交場合證明,法蘭西是一支可以進行獨立外交決策的力量。法國也並非是美蘇之間的附庸。至少,戴高樂認為,通過控制以法德為基礎的歐洲經濟共同體,法蘭西可以再次偉大起來。1968年的事件雖然導致戴高樂下台,但戴高樂主義卻深深浸透在法國的外交基調之中。對於法國而言,它也唯有憑藉歐洲這一平台,才能在某種程度上獲得與美蘇對等的地位。

冷戰的結束改變了遊戲規則,美國的一家獨大和法蘭西例外論的衰弱,使得法國人越來越將自己定義為一個接受美國領導的西方普通國家。但沒有改變法國以歐洲撬動全球影響力的基本思路。重新加入北約的法國,依舊將自己視為歐洲國家在政治上的代表者。法國的外交影響力也與歐洲深度綁定在一起。這是法國政治現實的結果,也是法蘭西戰後命運的寫照。唯有作為歐洲領袖的法國,才能將自己僅剩不多的全球影響力保存下來,維護自身的歷史尊嚴。
別指望法國站隊
法國對於自身影響力的敏感體現在許多方面。對法語的推崇就是一個典型的表現。在英國退歐之後,法國國內就一直有聲音要將法語作為歐盟的主要工作語言。對歐盟機構的設置也是基於這種敏感性。雖然將歐洲議會設置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增大了歐盟內部的行政運行成本,但卻成為法國對歐盟控制力的重要表現。甚至在2020年法國疫情依舊嚴重的情況下,法國就一直要求歐洲議會議員回斯特拉斯堡開會。
通過對於歐盟事務的一系列干涉,法國成為歐盟內部不可或缺的聲音。法國需要通過歐盟這一傳聲筒,説明法國對於世界其他地區的事務依舊可以保有相應的影響力。不過,法蘭西的倔強終究是一種舊時代的產物。對於法國全球影響力的幻夢正在走向終結。法國在潛艇問題上的迅速服軟來自法國外交政策的內在缺陷。它以歐洲聯合為基礎的方案存在兩個關鍵不足。
**第一,法國無法統合歐洲力量。**一方面,法國雖然在歐盟佔有較高比重的話語權,但法國並沒有成為歐盟的主導者和話事人。戴高樂被許多人批評的一點,就是他毫不猶疑的法蘭西霸權主張。他試圖成為“歐洲皇帝”的渴望如同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然而,隨着英國的加入和德國經濟實力的快速發展。法國不得不接受所謂的歐盟三駕馬車的運作方式。唯有英法德達成一致,才有可能將某種重大的歐洲決議推行下去。英國退歐之後的法德軸心依舊需要同樣的一致。

另一方面,歐盟的內部差異也破壞了法國推行其政策的能力。在歐盟東擴之前,南北歐的內部矛盾已經是歐盟內部令人頭疼的問題。在東擴之後,東西歐的對立進一步破壞了歐盟內部的凝聚力。歐盟全體一致的決策機制更是讓這個問題變得極為突出。任何一個國家,包括馬耳他這樣的微型國家,都可以阻止某項決策或者聲明。這使得歐洲難以作為一個統一的實體發出自己的聲音。
第二,今日歐洲本質上是一支附屬於美國秩序的國際力量。歐洲一體化一直讓很多歐洲人產生一種幻覺,即自己可以作為美國平起平坐的合作伙伴。不過,今日歐洲的國際地位是由美國主導的戰後國際秩序所保證的。馬克龍一直高呼北約已經“腦死亡”,但北約依舊為整個歐洲提供了許多安全保障。在北約的保護下,歐洲國家可以通過縮減自己的軍事開支,將相應的預算轉移到經濟發展和社會福利上去。特朗普政府的一個基本論點就是歐洲國家在讓美國承擔了不成比例的安全成本的同時,還利用它們的經濟優勢補貼歐洲公司,傷害美國企業和民眾的利益。
**除了安全問題外,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也為歐洲提供了所謂的價值觀同盟。**在美國領導下的西方陣營,可以通過強調自己價值觀的優越性,進一步壟斷和放大自己的話語權。對於第三世界的發展,歐洲國家往往與美國一樣,採用民主、人權、環保之類的理由進行打壓。歐盟想要徵收的碳排放税本質就是一種以環保為名義的新型貿易壁壘。通過實質上的貿易保護主義,歐洲可以有效保護自身產業鏈的位置,繼續佔據高附加值的產業。
不過,國際局勢的變化,對法國和歐盟產生了越來越不利的影響。全球經濟的不景氣,直接導致美國孤立主義的重新抬頭。特朗普政府的上台就是其中一例。歐洲人突然間發現自己再也不能“白嫖”美國。這極大地增加了歐洲的焦慮感。即便拜登宣稱美國回來了,但是從施政的實際結果看,美國也越來越缺乏維護歐洲利益的興趣。歐洲戰略自主的呼聲自然愈發高漲。

但問題是,對於絕大多數歐洲國家,且不論美國是否會允許,跳出美國所主導的國際秩序同時意味着將承擔高度不確定的風險。這意味着歐洲需要徹底重塑一整套國際政策主張。隨着新自由主義所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日益衰弱,歐洲一體化的動能也被消耗殆盡。這使得歐洲國家很難有更積極的動力促進歐洲內部的整合。這才是為何每次歐盟戰略自主討論都無疾而終的真正原因。
**歐洲國家不是不明白問題所在,問題是沒有人願意承擔帶頭承擔改變的風險。歐洲政治秩序的徹底變革,涉及到太多的國家利益和域外力量博弈。**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法國一邊迅速召回大使,一邊在電話之後就中止了召回。也難怪大家要日常辱法了。

今日的歐洲缺乏成為真正獨立政治力量的可能性。它必須在一定程度上依賴於美國發揮自己的影響力。阿富汗問題是這樣,敍利亞問題也是這樣,伊朗問題同樣是這樣。歐洲國家所能做的,只是儘可能調和美國行動對自己產生的消極結果。英國退歐後的“全球英國”政策更是這種關係最赤裸裸的表現。雖然鮑里斯本人是一個典型的現實主義者,但他意識到唯有始終強調英美特殊性下的價值觀同盟,才能最大限度保證英國的全球影響力。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説,現在仍然遠遠不到樂觀的看待老歐洲可以真正的開始反抗美國的秩序。英國可能並不想得罪中國,但在現有的框架下,它唯有繼續與美國站在一起,才能彰顯自己的話語權。法國雖然盡力顯得自己與美國平起平坐,但事實上仍然要追隨在美國的秩序框架之內。其他的歐洲國家也存在類似的情況。在美國日益強大的壓力下,每個西方國家都陷入這一結構性困境之中。不改變,意味它們依舊是美國主導西方秩序的附庸;改變,意味空前不確定的巨大風險。變與不變,這是每一個歐洲人心頭縈繞不去的問題。
所以,目前來説法國也好,歐洲也好,仍然不能指望他們下定決心真正的參與到挑戰美國秩序的隊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