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新:偷得浮生半日閒?_風聞
虎落平阳-2021-09-30 15:37
【多餘的話】這是執行主編杭州師範大學《語文新圃》的某一段心路歷程。寫作時間為2007年底,2010年雜誌由於某種原因“急流”而“勇退”矣!
偷得浮生半日閒?
金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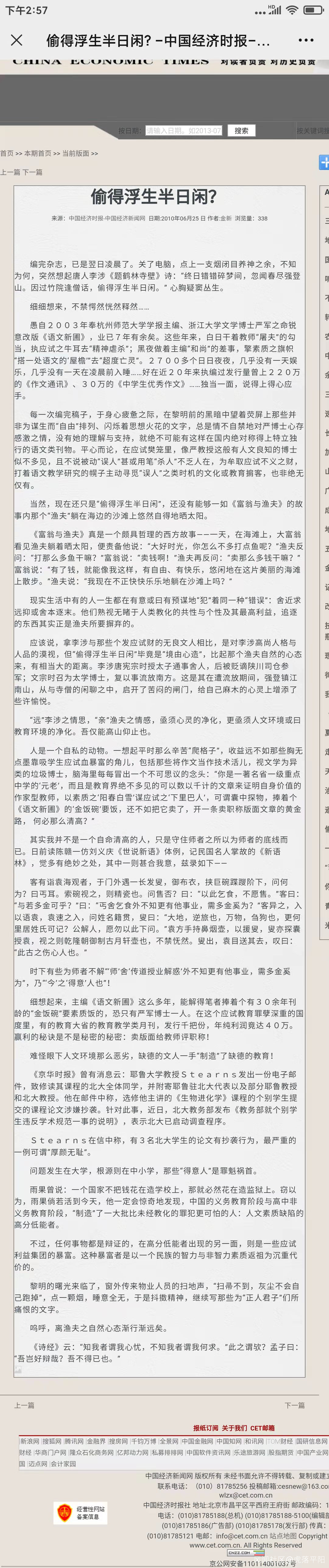
編完了《語文新圃》2008年第1期,已是2007年12月26日凌晨2點30分了。關了電腦,點上一顆煙閉目養神之餘,不知為何,突然想起唐人李涉《題鶴林寺壁》詩:“終日錯錯碎夢間,忽聞春盡強登山。因過竹院逢僧話,偷得浮生半日閒。” 心胸疑竇叢生。
細細想來,不禁愕然恍然釋然……
愚自2003年奉杭州師範大學學報主編、文學博士嚴軍之命鋭意改版《語文新圃》,爾來業已5年矣(2003年第2期—2008年第1期)。這5年來,白日干着教師“屠夫”的勾當,執應試之牛耳去“精神虐殺”;黑夜做着主編“和尚”的差事,擎素質之旗幟“搭一處語文的‘屋檐’”去“超度亡靈”。5年,1800多個日日夜夜,幾乎沒有一天娛樂,幾乎沒有一天在凌晨前入睡……,“三餘”兼顧,每月近8萬字的用稿量啊!對於一個門外漢,不啻天方夜譚。好在近20年來執編過發行量曾上220萬的《作文通訊》、30萬的《中學生優秀作文》……獨擋一面,説得上得心應手。
每一次編完稿子,於身心疲憊之際,在黎明前的黑暗中望着熒屏上那些並非為謀生而“自由”排列、閃爍着思想火花的文字,總是情不自禁地對嚴博士心存感激之情,沒有她的理解與支持,就絕不可能有這樣在國內絕對稱得上特立獨行的語文類刊物。而這60本雜誌又是我文字生涯裏的“佛龕”,讓我在應試屠戮的血光中,依稀看見莘莘學子輾轉倒在所謂文化人發明的文字垃圾中,深感觀應試罪孽世界一切之音的責任。憑心而論,在國家意志下的應試樊籠裏,像嚴教授這般有人文良知的博士似不多見,且不説被動“殺人”不乏人在,為牟取應試不義之財,打着語文教學研究的幌子主動尋覓“殺人”時機的文化或教育劊子手,也非絕無僅有。
當然,現在還只是“偷得浮生半日閒”,還沒有能夠一如《富翁與漁夫》的故事內那個“漁夫”躺在海邊的沙灘上悠然自得地曬太陽,還得抓緊完成由余秋雨任總主編我任主編的《新語文新天地》叢書(計18本,將在2008年5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繼續完成由我主編的《精彩閲讀》叢書(計16本,已於前年由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10本,尚餘6本還在寫作中,2008年2月交稿),完成了這些閃耀着素質華光與體現着人文理念的叢書後,我才可以有暫時享受“自然陽光”的“權利”與機會。
《富翁與漁夫》真是一個頗具哲理的西方故事。
一天,在海灘上,大富翁看見漁夫躺着曬太陽,便責備他説:
“大好時光,你怎麼不多打點魚呢?”
漁夫反問到:“打那麼多魚乾嘛?”
富翁説:“賣錢啊”
漁夫再反問:“賣那麼多錢幹嘛?”
富翁説:“有了錢,就能像我這樣,有自由,有快樂,悠閒地在這片美麗的海灘上散步。”
漁夫説:“我現在不正快快樂樂地躺在沙灘上嗎?”
現實生活中有的人一生都在有意或曰有預謀地“犯”着同一種“錯誤”:捨近求遠抑或捨本逐木。他們熟視無睹於人類教化的共性與個性及其最高利益,追逐的東西其實正是漁夫所要摒棄的。比如一些無良文人,披着形而上的人文外衣,在物慾的遊戲徵逐中,離人文本真的目標愈來愈遠。他們常常以為自己能擁有很多,事實上除了文化商人的手腕、沾滿應試鮮血的鈔票、一塊人文的遮羞布外,什麼都沒有,包括靈魂與良知。
應該説,拿李涉與那些個無良文人相比,是對李涉高尚人格與人品的漠視,但“偷得浮生半日閒”畢竟是“境由心造”,比起那個漁夫自然心態來,有相當大的距離。李涉唐憲宗時授太子通事舍人,後被貶謫陝川司倉參軍;文宗時召為太學博士,復以事流放南方。這是其在遭流放期間,強登鎮江南山,從與寺僧的閒聊之中,啓開了苦悶的閘門,給自己麻木的心靈上增添了些許愉悦。
“ 遠”李涉之情思,“親”漁夫之情感,亟需心靈的淨化,更亟需人文環境的淨化。吾僅能高山仰止也。
人是一個自私的動物。一想起平時那麼辛苦“爬格子”,收益遠不如那些胸無點墨靠吸學生應試血暴富的角兒,包括那些將作文當作技術活兒,視文學為異類的垃圾博士,腦海裏每每冒出一個不可思議的念頭:“你是學軍中學的‘元老’,而且是教育界絕不多見的可以數以千計的文章來證明自身價值的作家型教師,以素質之‘陽春白雪’謀應試之‘下里巴人’,可謂囊中探物,捧着個‘金飯碗’要飯,還不如把它賣了, 何必那麼清高?”
其實我並不是一個自命清高的人,只是守住師者之所以為師者的底線而已。日前讀陳贛一仿劉義慶《世説新語》體例,記民國名人掌故的《新語林》,覺多有絕妙之處,其中一則甚合我意,茲錄如下。
客有詣袁海觀者,於門外遇一長髮叟,御布衣,挾巨碗蹀躞階下,問何為?曰丐耳。索碗視之,則精瓷也。問售否曰:“以此乞食,不願售。“客曰:“與若多金可乎?“曰:“丐舍乞食外不知更有他事業,需多金奚為?“客異之,入以語袁,袁速之入,問姓名籍貫,叟曰:“大地,逆旅也,萬物,芻狗也,更何里居姓氏可記?公解人,願勿以此下問。“袁方手持鼻煙壺,以援叟,叟亦探囊授袁,視之則乾隆朝御製古月軒壺也,不禁憮然。叟出,袁目送其去,嘆曰:“此古之傷心人也。”
時下有些為師者不解“‘師’舍‘傳道授業解惑’外不知更有他事業,需多金奚為”,乃“‘今’之‘得意’人也”!
細想起來,主編《語文新圃》這五年,能解得筆者捧着個有30年刊齡的“金飯碗”要素質飯的,恐只有嚴軍博士一人。在這個教育罪孽深重的國度裏,有的教育大省的教育教學類月刊,發行千把份,年純利潤竟達40萬。贏利的秘訣是不是秘密的秘密:賣版面給教師評職稱!
難怪眼下人文環境那麼惡劣,缺德的文人一手“製造”了缺德的教育!
2007年12月25日和《京華時報》消息:
12月19日,耶魯大學教授Stearns發出一份電子郵件,致修讀其課程的北大全體同學,並附寄耶魯駐北大代表以及部分耶魯教授和北大教授。他在郵件中稱,選修他主講的《生物進化學》課程的個別學生提交的課程論文涉嫌抄襲。針對此事,近日,北大教務部發布《教務部就個別學生違反學術規範一事的説明》,表示北大已啓動調查程序。
Stearns在信中稱,有3名北大學生的論文有抄襲行為,情節最嚴重的一例可謂“厚顏無恥”。
問題發生在大學,根源則在中小學。那些“得意人”是罪魁禍首。
雨果曾説:一個國家不把錢花在造學校上,那就必然花在造監獄上。竊以為,雨果倘若活到今天,他一定會驚奇地發現,中國的義務教育階段與高中非義務教育階段,“製造”了一大批比未經教化的罪犯更可怕的人:人文素質缺陷的高分低能者。
不過,任何事物都是辯證的,在高分低能者出現的另一面,則是一些個應試利益集團的暴富。這種暴富者是以一個民族的智力與非智力素質返祖為沉重代價的。
黎明的曙光來臨了,窗外傳來物業人員的掃地聲,“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點一顆煙,睡意全無,於是抖擻精神,繼續寫那些為“正人君子”們所痛恨的文字。
嗚呼,離漁夫之自然心態漸行漸遠矣。
《詩經》雲:“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歟?孟子曰:“吾豈好辯哉?吾不得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