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恆丨地方院校還能再出鄭克魯這樣的大家嗎?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2021-10-05 20:45
陳恆|上海師範大學世界史系教授
時間轉瞬即逝,一眨眼,鄭克魯先生離開我們已經一年了。今天這個會議既是對先生的追思會,亦是先生的學術思想研討會,更是中國外國文學翻譯和研究界的一次盛會。大家看看出席會議的嘉賓名單,可以説是羣賢畢至。這是上海師範大學的榮耀,也是中國外國文學界的高光時刻。

鄭克魯先生
今天來賓很多,我儘量在簡短的時間內表達我的敬意。鄭先生一生著述4000萬字,不僅是法國文學翻譯的守望者,更是偉大的學者和教育家。一所地方師範大學,能有這樣的學術大師,放在今天學科評估的背景下,似乎是匪夷所思的;鄭克魯先生以一人之力,翻譯如此多法國文學作品,這在當代學術界是無法想象的;他在一所地方高校,幾十年如一日,培養了一代代致力於文化交流與文化批評的學者,這是令人難以企及的;他在中法文化交流、乃至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取得如此驕人成績,更可謂是空前絕後。基於以上四點原因,我願將鄭先生身上體現的這種成就與意外,稱為中國學術界的“鄭克魯現象”。如果這個命題成立的話,按着這個思路,我個人感覺有這樣幾個問題需要認真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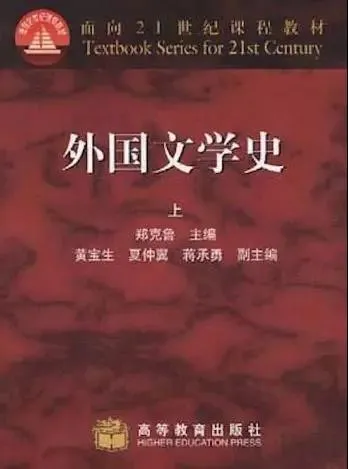
鄭克魯主編的高教版《外國文學史》
第一,我們需要什麼樣的高等教育?我個人感覺,可能在鄭先生之後,地方高校很難再出現像他這樣的翻譯家、學術家和教育家。但願我的感覺是錯誤的。我印象中,鄭先生1987年來到上師大直至去世,那時他47歲,正是一個人文學者富於創造力的階段,可以説把人生中最重要的、最好的學術年華都奉獻給了上師大。就其學術成就而言,按照今天教育部和大多數高校的治校思路,鄭先生早已被其他更好的學校高薪聘走。如果所有的學術精英都集中在雙一流高校,那地方大學、地方高等教育便越來越差,難道這是國家的幸事嗎?
第二個問題是今天我們需要什麼樣的文科?我們如何看待人文學術研究的意義?今天拿到的會議手冊,第一頁鄭先生的這句話給我觸動非常大:“生命就是你給世界留下了什麼”。這也讓我想到另外一句話,1936年浙江大學的竺可楨校長在開學典禮上的講話:第一,你來做什麼?第二,你畢業以後做什麼樣的人?鄭先生用實際行動回答了竺可楨校長的提問。教育就是讓人儘量成為全面的人、完善的人,多留給世界一點東西。而文科教育就是為學生提供人文批判思維、培育情感認知,讓學生不忘價值與美感,鄭先生的話就是他對價值的體悟。這是當下正在倡導的新文科教育需要認真思考的。
第三個問題就是我們今天如何看待域外文明?這是我們特別要關注的,因為異質文化永遠處於對流之中,唯其如此,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才能被其他文明不斷激活,從而不斷抓住發展和完善的機遇。任何文化若想弘揚自身的價值觀,都要正視人類所有的文明成就,都要借鑑其他民族的創造發明,都要與當代世界各國進行合作互動,而非將自我隔絕於世界,貶低乃至否認別人的成就。以開放的心態欣賞域外文明,以嚴謹的方法探討別人取得成就的內在機制與深層原因等等,這都是當代域外文化研究的使命,更是當代中國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
人總得有一點情懷,尤其人文領域的學者,學術界本應該為社會提供安身立命的精神食糧,現在也功利化了。像鄭先生這樣,幾十年甘於坐也樂於坐冷板凳的學者,幾十年精心翻譯法國文學、培養學生的學者,似乎不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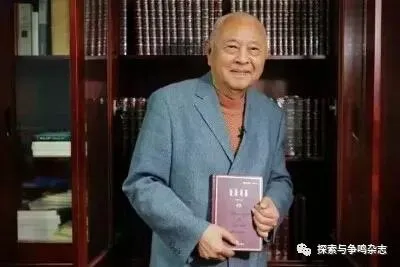
鄭先生低調豁達,他的性格是寬容的,從不與人相爭;他對待中西文化交流也是寬容的,在翻譯研究法國文學的同時,不忘回顧東方文學。人與人之間要包容,相互尊重、相互學習,文化之間是這樣,國與國之間也一樣。理想的社會既要講效率,也要講公平,更要講一點真善美。説到這裏,想到德國思想家雅斯貝爾斯説的一段話,願與大家分享:
關於人類當代狀況的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緊迫。當代狀況既是過去發展的結果,又顯示了未來的種種可能性。一方面,我們看到了衰落和毀滅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了真正的人的生活就要開始的可能性。但是,在這兩種互相矛盾的可能性之間,前景尚不分明。
老師們、同學們,讓我們一起努力為未來一切存在的可能性進行切實可行的工作。像鄭先生這樣,少説一些大話,多做一些實事,兢兢業業為世界做點什麼,爭取為世界留下點什麼。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