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爸爸朝鮮女兒,父女戰場分別70年,至今未能相見_風聞
熊猫儿-2021-10-06 16:03
大家好,我是羅伯特劉。
現在説到朝鮮,大家都當成貧窮、落後的代名詞。
殊不知,它也曾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輝煌過,繁榮程度不但遠超中國,也高於韓國,令人羨慕。
特別是到七十年代末,中國人均GDP僅有245元人民幣,朝鮮卻已高達600美元,且實現全民免費醫療、免費教育。
那時期的朝鮮,不僅物質生活豐富,文化也引領亞洲先鋒。電影《金姬和銀姬的命運》引入中國後,一下風靡各大城市,成了中國年度票房冠軍。
電影講述因朝韓戰爭而不幸分離的兩姐妹,她們分別在朝鮮、韓國長大後,天壤之別的命運。
中國解放軍第81師的副師長黃萬豐,也和戰友去看了這部電影,當片中主題曲《爸爸的祝福》響起時,他忍不住淚流滿面。
25年,那被強留在朝鮮的女兒,還好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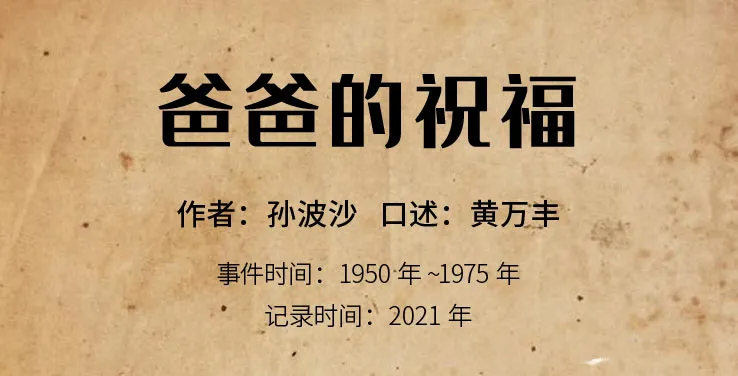
1975年,中國電影的票房冠軍,是從朝鮮引進的《金姬和銀姬的命運》。
一天,轉業到地方的通訊員來部隊看我,我時任解放軍第81師副師長。
晚飯後,我陪着在朝鮮戰場一起出生入死的通訊員,到部隊大禮堂看這部朝鮮電影。這在地方還一時看不到。
當影片的主題曲《爸爸的祝福》響起,通訊員已是淚流滿面。
他轉向同樣熱淚盈眶的我,説:“首長,這不就是那朝鮮女上尉唱的《祝福歌》嘛!”
我猛地想了起來,説:“是啊,她當時唱的歌,就是這個調調。”
我的心不由抽動了一下,一個小小的人兒出現在眼前,她該有28歲了,沒準已經結婚成家了呢。

那是1950年的冬天,我們第27軍秘密集結在朝鮮長津湖畔,開始抗美援朝第二次東線戰役。
這一年我才23歲,是第27軍81師243團1營1連的連長。
在零下40度的極寒中,我連作為預備隊之一,負責在長津湖以東警戒。
幾天後,傳來一條消息,長津湖東岸的美軍第7師17團,忘乎所以,竟站在鴨綠江邊朝中國方向撒起尿來,以侮辱我新中國。
婢養的,老天爺也不凍掉美國佬那雞巴玩意兒。
這個動作十分下流,戰士們聽後紛紛罵起來,説等戰場上逮到17團的人,一定讓他們喝自己的尿。
我提醒戰士們説,我們不能學美國佬那一套,我們要用戰鬥力和美國佬説話,打得他們心服口服。
戰場的預備隊往往有兩個結果,如果仗打順了的話,不需要放一槍一彈,上去打掃戰場即可。但若仗打不順,預備隊就成了敢死隊。
起先,我軍在新興裏方向安排了2個團的預備隊,除了我們243團,還有兄弟團242團。
11月27日,在冰天雪地裏已經隱蔽守候了6天的志願軍戰士,彷彿是從地下冒出來一樣,將在帳篷、睡袋裏的美軍打了個措手不及。四天後,美軍第7師全線撤退。
此時,242團作為預備隊第一梯隊加入了攻擊,可才戰鬥到12月1日的午夜,全團僅剩下不到2個連的戰鬥力,僅正連級以上幹部就犧牲了14人。
他們攻擊的正是美軍第7師的“北極熊團”,王牌中的王牌。我團奉命連夜急行軍,支援242團。
等我連趕到後浦時,“北極熊團”已經被徹底降伏了,除了我軍包圍圈外,其餘的不是被擊斃就是當了俘虜。
後來才知道,在圍殲“北極熊團”時,242團的第5連受命在附近的水門橋處,阻擊來援敵人,冰天雪地無法做工事,只能趴在雪坑裏,槍口一齊對準前方。
飢寒交迫中,一夜之間,全連100多人竟然化作了一座座晶瑩的冰雕,犧牲後的他們保持着完整的戰鬥隊形,每個人都手握武器,隨時準備射擊的姿勢……
全殲“北極熊團”的奇蹟和志願軍的突然襲擊,迫使整個東線的美軍嚇破了膽,扔下大量傷員、屍體於不顧,爭先恐後逃到了南部的後方。
我連也接到新任務,需要於12月2日夜跨過冰封的長津湖,朝西岸方向機動待命,隨時支援其他一線陣地。
當時志願軍戰術都是晝伏夜出,白天不敢動,怕美軍的飛機轟炸。
出發命令到達之前,我們1連的任務仍是警戒。敵人都投降了,還警戒什麼啊?我當即下令各排趕緊去打掃戰場。
看着隨處可見的美軍武器,我讓戰士丟掉手中步槍,統統換成美式M1自動步槍,它能一次連發8發子彈,比我們大多戰士手中的“單打一”步槍要強太多了。
除了換槍,我們只要吃的,大家早就餓壞了,餅乾當場就吃掉了,只剩下了一些肉罐頭帶走。
我吞了幾塊餅乾,剛噼裏啪啦打開了一支自動步槍槍栓,準備瞄準時,出發的命令也到了。
恰恰這時,朝鮮語聯絡員抱着一個朝鮮小女孩跑了過來。
我一問才知道,小女孩5歲,名叫嬌靜子,父母在昨天美軍的轟炸中雙雙身亡。
朝鮮語聯絡員遇見她時,她已經哭得沒有眼淚了。

我老家在膠東牟平,17歲參加八路軍,不知打過多少惡仗,最看不得老百姓遭殃,因為我自己也是窮苦人出身。
尤其是到了朝鮮戰場後,因為都是夜裏行軍,一路上,藉着暗淡朦朧的月光,隨處可見慘遭殺害的朝鮮人民的屍體。
有的房屋被炸塌了,燃燒未盡的木料屋架上閃着點點火星,飄着絲絲青煙,還有趴在母親身上哭泣的孩子。
他們穿着白色衣裙的母親已經死去,被炸飛的白色衣裙掛在樹梢上,白色的布條在寒風中抖動。
活着的老鄉用我們聽不懂的語言呼喊着,眼淚,血水,泥土一齊糊在臉上,每個人的臉上都不約而同展現着同一個表情,就是驚恐。
這些慘狀,刺激着每一個志願軍的心,大家低頭前行,不忍直視。軍務在身,軍情緊急,每個人都必須跟着隊伍急行,無法對那些哭泣的孩子伸出援手。
即便如此,只要沒有炮火,善良的朝鮮民眾一見到志願軍,還是搶着把藏在窖子裏救命用的土豆拿來讓我們吃。
每每這時,我就教育戰士們,不為別的,就是為這些和我們父母兄弟姊妹一樣的朝鮮老百姓,我們也得打敗橫行霸道的美國佬。
此刻眼前的小人兒,穿的破破爛爛,個頭還沒有椅背高。在這冰天雪地裏,要是放着不管,最多一夜,她必死無疑。
我看她眼角的淚水已經結冰了,可我不敢去動,因為一動,眼角的皮膚就會撕裂。

插畫師根據現場還原
我家鄉許多人闖過關東,我有這個禦寒的經驗,最有效的辦法是到目的地不準立刻休息,不停走動一陣保持血液循環;
二是“搓”,不管路上多累,到宿營地第一件事就用雪搓手腳。
特別是耳朵和嘴角、眼角結冰了不要去用手摸,讓它自然化掉,所以我們連隊過江後沒有一個凍亡和嚴重凍傷。
情況緊急,來不及多想,我讓炊事班長倒出一個竹筐,再用自己的棉被子將小女孩包裹好,挑起竹筐開始了急行軍。
竹筐挑孩子是我老家土法子,扁擔兩頭掛着筐子,一頭裝着物件,一頭坐着孩子,走得快還省勁。
這個叫嬌靜子的小女孩,個頭很小,此刻窩在竹筐裏,可以坐,也可以躺,活像個鳥窩裏的小鳥。
起初,竹筐裏的她還是警惕地看着我,不多一會兒,就打起了瞌睡來。
人小的時候覺格外多,但這是來回晃盪的竹筐,還有不時響起的槍聲,這也能睡得着,她該是多累啊。
不知為何,我心裏突然冒出個奇怪的想法,這次輪到我們去當敢死隊了,如果我犧牲了,嬌靜子就權算是我撿來的閨女吧。
我還沒結婚啊,她或許是我朝鮮戰場唯一的紀念了。

12月3日拂曉,連隊到達了長津湖西岸邊的宿營地。
見上級一時沒有命令,我叫上通訊員拆了我的棉被,給孩子趕身衣服,她身上的衣服實在太破了。也不知道她是怎麼在炮火中活下來的,命可真大。
通訊員的手果然又快又巧,快到傍晚,就給嬌靜子趕出了一身棉襖和棉褲。
朝鮮女人的傳統服飾是短褂長裙,不管男女,都愛穿素色的衣物。看着嬌靜子穿上這一身黃綠色的小衣褲,模樣簡直精神極了,我這棉被拆得真值!
零下幾十度行軍,衣服和棉被都是救命的東西,先救孩子的命要緊,我睡覺再想辦法吧。
雖然語言不同,但不知道為何,小人兒乖乖聽我擺佈,不哭不鬧的,我剛給她穿上了新棉衣時,南下的命令也到了。
我挑起嬌靜子,又開始了夜行軍,等趕到指定集結地時,前方1224高地方向已是槍聲大作。
預感到大戰即將來臨,我急忙將嬌靜子交給了炊事班長,像下戰鬥命令一樣叮囑炊事班長:“你丟了什麼,也不能把嬌靜子給我弄丟了,啊!”
炊事班長一個立正,大聲説:“是!”
隨即,我帶領1連跑步趕到了1224高地,等候命令。到黎明時分,接到防守高地的命令。
因為我們之前一直做預備隊,1連此時可謂兵強馬壯、彈藥充足,戰鬥開始時,僅用迫擊炮和重機槍火力,就將美軍死死擋在了高地前。
一時傷亡劇增的美軍,立即停止攻擊。天亮後,超過100架次的美機陸續抵達高地上空,重磅炸彈、凝固汽油彈、機關炮,輪番轟炸掃射後,陸地美軍向高地發起了攻擊。
戰鬥到中午,我連兩門迫擊炮打完了所有炮彈,3排陣地危在旦夕,我急命預備隊1排前去截擊。
1排有對親兄弟,同在一個班,哥哥陳本中是副班長,弟弟陳本華是班長。
兄弟倆都要求去最前沿阻擊點,哥哥找到了我,説自己不怕死,唯一的要求是留下弟弟作預備隊員,給陳家留個後。
可弟弟也找到我説,自己是班長,危險時刻哪能讓副班長先上,要麼一起到阻擊點,要麼副班長留下來。
副班長,哥哥;班長,弟弟。
見兄弟倆各執己見不肯讓步,而美軍也快接近了陣地,我只好同意兄弟倆都上前沿阻擊點。
極寒天氣的陣地上,戰鬥異常激烈,美軍拼命攻擊,我們在死命阻擊,沒過多久,班長陳本華不幸中彈,犧牲在了哥哥的面前。
陳本中強忍着悲痛,跳出戰壕,將弟弟的遺體拖到了身後的背坡處,將其雪葬後,又返回了前沿陣地。
只見回去的他壓上了一個彈夾後,突然叫罵着端起輕機槍,發瘋一般衝向了不遠處的美軍,這不要命的舉動,一下把進攻的小隊美軍嚇得撤下山腳。
看見這一幕後,我急忙派通訊員跑過來,命令陳本中撤到二線陣地。可一心想要為弟弟報仇的陳本中,怎麼也勸不下來。
不能給陳家斷後,大家都想護下這悲憤中的哥哥。

戰鬥持續到下午,美軍見久攻不下,急忙派英軍的加強坦克排前來救援。
在炮火的掩護下,我親自帶領1排2班衝出陣地,炸燬了公路上的幾輛榴彈炮牽引車,將敵軍的車隊堵在了公路橋以西。
見阻擊任務完成,我立即帶領2班撤回了高地上,一看少了個陳德生。
瞭望哨的通訊員一看,他正在橋頭陣地包紮傷口,眼見東面美軍的4輛坦克開了過來,陳德生抓着防坦克手榴彈從橋下迎了上去。
在這險象環生中,陳德生竟然接連炸癱了3輛坦克,第四輛坦克見狀掉頭逃走了。
見突圍和救援同時受挫,美軍又一次呼叫來20多架轟炸機,密集轟炸後,凝固汽油彈產生的巨大熱浪,將齊膝深的雪化成了污濁的水……
聞訊趕來的第81師孫端夫師長,從望遠鏡裏看到1224高地的慘狀後,心急如焚地對我們的團長説:“黃萬豐的1連,怕要報銷了!”
好在我早已改變了阻擊戰術,運動作戰一直堅持到下午4點多,美軍見天色已晚,夜間突圍將付出加倍的傷亡,主動停止攻擊。
放棄汽車徒步的美軍主力,十分狼狽狂奔起來。我一看美軍要跑,立即帶領戰士衝下了高地,四處射殺掉隊並拒絕投降的小股美軍。
而調頭返回救援的美軍敵機,見敵我雙方近距離混戰在一起,無法投彈,也只好又轉身去掩護前方。
這一戰,我們擊斃220名美軍,繳獲了20輛卡車和16門105榴彈炮,還有陳德生炸燬的那3輛坦克,以及美軍丟掉的罐頭和餅乾若干。
看到吃的,我才突然想起了嬌靜子,因為罐頭她之前已經吃過了,可容易消化的餅乾還沒有撈着吃。
我抓上餅乾,讓通訊員先帶上幾盒,趕緊先送去後方的炊事班。
以前我只是光棍一個,無牽無掛,如今有了嬌靜子,突然對活着有了不一樣的感覺。
通訊員剛離開,營裏的命令到了,我連集結後沿江鹹公路的右翼,去側擊逃跑的美軍。
我向來執行命令不打折扣,可這一次我沒有立即傳達命令,我得等陳德生呀。
剛剛打掃戰場沒有發現他,直覺告訴我,戰鬥經驗豐富的陳德生一定能活着回來。
陳德生是廣東江門人,有着廣東人特有的聰明勁,打仗十分機靈,我十分喜歡這名廣東兵,時常學着他的腔調,喊他“廣東仔”。
美國佬的坦克都讓他炸掉了,打掃戰場又沒見到他,這個廣東仔去了哪裏呢?

這時,給嬌靜子送餅乾的通訊員已經返回,又報告説,營裏來人催了,問我們何時出發。
看着陣地下還冒着煙的3輛坦克,我問通訊員,你不是説這坦克是廣東仔打掉嘛,廣東仔現在人呢?我活要見人,死要見屍。
通訊員沒辦法,只好帶上兩名戰士,去尋找陳德生。
我也趁着間隙趕回到了炊事班。這次戰鬥和以前的都不一樣,只要槍炮一停,我心裏總是擔心那個小人兒。
回到炊事班一看,沒想到在這震耳欲聾的槍炮聲中,吃過餅乾的嬌靜子,此時已經熟着了。
圓圓的小臉,彎彎的睫毛,嘟囔的小嘴,不知她的夢裏會有什麼。就是布娃娃也捨不得扔呀,更何況還是個活生生的人。
這一天的相處,估計炊事班長也喜歡得很,正利用先前剩下的一截棉被,在給嬌靜子縫小棉被呢。
我吃了幾口剛繳獲的罐頭,接過炊事班長的針線,縫好了最後幾針後,炊事班長遞上了他的旱煙袋,説讓我吸一口養養神。
我抽了幾口的煙,突然又想起了陳德生。因為此前陳德生説過,如果能活着回國,回家給我捎廣東最好的水煙抽。
突然,通訊員跑進來報告説:“連長,廣東仔回來了。”
我出門一看,陳德生正被兩名戰士架着,我只顧高興了,揮手就捅了他一拳説,“我就説嘛,你這個廣東仔一定能活着回來,你老家的水煙我還沒抽呢。”
陳德生一個趔趄,説:“連長,你輕點啊!”
這時我才知道,他渾身上下受了5處重傷。我趕緊讓兩名戰士將陳德生送到了團衞生隊,這才下達了轉移的命令。
開始迂迴追擊美軍後,我們都是夜裏行軍,白天宿營。只要不打仗,無論白天還是夜間,我都讓嬌靜子待在自己的身邊。
即便是行軍也自己挑着走,生怕將已經是孤兒的嬌靜子遺落在什麼地方找不到了。
而一旦參加戰鬥,我便將嬌靜子交給炊事班長,每次都像下戰鬥命令一樣,認真叮囑炊事班長:“你丟了什麼,也不能把嬌靜子給我弄丟了,啊!”
12月11日傍晚,我們追擊到了上通裏的側翼,再往南是一馬平川的平原地帶,無疑,這裏成了我們截擊美軍的最佳地點。
聽到前方鐵路一線激烈槍聲後,我急忙將挑着嬌靜子的扁擔交給了炊事班長,命令大家做好隨時出擊的準備。
不一會兒,通訊員就送來師長的命令,我帶着1連緊急前往阻擊陣地,只見前後左右吐着火舌的第二輛火車,已經跑出了火力射程。
這時,師裏的命令又到了,我們1連由預備隊變前衞,連夜朝咸興方向追擊。
我回到炊事班,挑起嬌靜子接着開始了急行軍。
這樣左肩換右肩走了約一個小時,我剛想放下擔子喘口氣,被噩夢驚醒的嬌靜子突然大聲哭喊起來:“阿媽妮,阿媽妮……”
炊事班長急忙跑過來,一邊哄着哭聲不斷的嬌靜子,一邊焦急地看着我。急行軍中孩子的哭聲,不僅影響軍心,甚至會引來敵機的轟炸。
我也一時不知如何是好,只能挑起扁擔原地轉了幾圈,沒想到,嬌靜子竟出奇地安靜下來。
看着我挑着扁擔不停地原地轉圈,炊事班長氣得就罵,都是這可惡的美國佬造的孽。
將近半個月的行軍中,嬌靜子早成了全連的中心人物。戰士們只要有空閒,第一件事就是來看這個不會説中國話的小人兒。
這聰明的小人兒卻學會了認人,全連幾十個爭相對她好的糙漢子,她就數和我最親。
也不管我打仗累不累,她已經習慣了我挑擔子,一旦換了別人,她就會哭鬧,我索性也堅持一個人來挑嬌靜子。
這可能就是上天安排的父女緣分吧。

按照我軍的追擊部署,我們第81師將沿公路進逼咸興,然後與其他部隊合圍美軍的後勤基地興南港。
但這之前,我們繳獲的罐頭已經快吃完了,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炊事班長只有把希望寄託在我們打勝仗上了。
12月14日夜裏,我連奉命攻擊咸興的美軍,臨出發前,炊事班長特地找到我説,千萬別忘了搞點吃的來。
第二天清晨,我帶着連隊回到始發地的隱蔽處時,炊事班長還以為我們打了勝仗,急忙問:“連長,打勝仗了吧,繳獲吃的了沒?”
我沒好氣地説:“繳獲個頭。”
炊事班長着急問:“怎麼了?”
“美國佬的火力太密了,靠不近也打不動。”見炊事班長明白了幾分,我又急忙問:“嬌靜子呢?”
炊事班長指了指遠處,説剛給她吃了兩勺牛肉罐頭,這才睡着了。
這是我們全連僅剩下的2個牛肉罐頭,是留給重傷員救命的。
炊事班長沒有辦法,只好用水煮罐頭熬湯,撐了一個白天,而到了夜裏,嬌靜子又餓得啼哭起來。
一個傷員掏出了自己僅有的小半瓶罐頭,炊事班長用開水泡成漿糊狀,給嬌靜子餵了幾口,嬌靜子這才止住了哭聲。
剩下的罐頭,嬌靜子又吃了2天。大人能扛餓,孩子不行,餓了就哭,我心裏着急,但又毫無辦法。
堅持到了12月18日,美軍開始了大規模撤退,我帶領戰士第一個衝進了咸興,一番搜索後,俘虜雖然沒有抓到,卻發現了一包美軍遺落的糖果。
心裏比抓俘虜還高興,抓了一把讓通訊員趕緊先送回炊事班。有了糖果,嬌靜子就不會哭鬧了。
我和戰士們每人也吃了幾塊糖果,繼續朝興南港方向追擊,等追到離港口不到3公里時,美軍的飛機和軍艦上的炮火,又形成了一個密不透風的火力圈,部隊只好再次停了下來。
這樣對峙到晚上,美軍的飛機轟炸停了下來,軍艦上的遠程炮火也出現了空檔,我一看機會來了,帶上3名體力最好的戰士摸進了火力圈去找吃的。
藉着炮火的光亮,我們摸到了美軍的一個後勤倉庫,裏面是成堆的罐頭,來不及細看,大夥各自背上一箱開始回撤。
我們前腳離開倉庫,後腳就遭遇了美軍巡邏隊,只能一路邊打邊撤,背後的罐頭箱叮噹作響,剛開始還重的很,越跑身上反而越輕快。
接應的戰士發現我們後,一羣人驚得目瞪口呆,趕緊圍上來查看情況,一個戰士嚇得大叫:“連長,你們傷成這個樣子還能跑啊!”
我回頭一看,3名戰士的後背和棉褲腿,無不是血淋淋的一片,再一瞅自己的後棉褲腿,也是一片猩紅。
原來,我們背的不是肉罐頭,而是一箱兩大桶的西紅柿汁罐頭,幾乎全叫美軍給擊穿了,所以才越跑越省勁。

插畫師根據現場還原
聞聲趕來的炊事班長,把每個桶都掏出來搖晃了大半天,才折出了大半桶西紅柿汁,再和上開水分給戰士們和嬌靜子吃。
看着血紅血紅的西紅柿汁,小人兒嚇壞了,小嘴緊閉,眼神裏透着抗拒。她一定是當成了鮮血,心裏害怕呢。
我一邊説着她聽不懂的話,一邊假裝放鬆享受地喝了一大口,見我喝完沒啥事,鬼機靈這才抿着小嘴兒,咕咚咕咚喝起來。
可吃完之後沒一會,大家覺得更餓了,那時候才反應過來,這酸酸甜甜的玩意開胃。
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西紅柿汁罐頭,也是第一次吃。美軍的後勤補給,那真是世界一流呀。
羨慕的同時,更感到難過。

12月25日拂曉,美軍炸燬後勤基地,燒燬了倉庫全部給養,順利撤離了興南港。
沒來得及撤退的平民痛苦地哀嚎着,低矮的茅屋在數秒內被夷為平地,大火和濃煙吞噬了這座平靜的海邊小城。
迎着還沒有消失的爆炸聲與硝煙,我帶領連隊又是第一個衝進了一片廢墟的興南港。
望着地獄一樣的場面,我不知道,又會出現有多少個“嬌靜子”,又有多少個“嬌靜子”連逃生的機會都沒有,就化作了灰燼。
這些日子,除了行軍打仗,我一刻都不離嬌靜子,因為我成了嬌靜子的依靠,嬌靜子也成了我的心上肉。
長津湖戰役結束後,部隊奉命去天氣比較暖和的咸興一帶休整,3個多月過後,又奉命參加了第五次戰役。
這個時候,我已經是235團1營的參謀長了。
第五次戰役不僅打得急、打得大,也打得遠,到了後期聚殲美軍不成,反倒成了緊急突圍。
在殘酷的突圍戰中,我依舊挑着嬌靜子行軍,一旦戰鬥就交給留在後方的炊事班,不僅我,全連都認定這是上天送給我的女兒。
歷經一個多月,我不僅以最少的傷亡帶回了部隊,嬌靜子也毫髮無損。
師部早知道我帶着嬌靜子行軍打戰的事,也沒有下達相關指示,讓我留下,還是繼續帶着走。
命令沒來之前,我們就這樣一路行軍,一路作伴。
1952年10月1日,這一天是國慶節,軍文工團恰好來我團慰問演出,第一個節目是手風琴伴唱《志願軍戰歌》:
雄赳赳,氣昂昂,橫渡鴨綠江……
這雄壯的歌聲一出,現場立即沸騰了,前幾排的戰士們紛紛站起來,忘情地打着節拍跟唱起來。
見戰士們擋住了視線,我急忙將嬌靜子扛在了自己的脖子上,拉着嬌靜子的小手也跟着哼唱起來。
這時,我在團警衞排當排長的老鄉,將我悄悄拉出了會場:“老夥計,我們死不了了!”
我一頭霧水,警衞排長壓低了聲音告訴我,他聽團首長説,我們27軍要換防回國了。
“命令很快就宣佈,注意保密。”警衞排長小聲説。
一聽説部隊要回國,我急忙返回現場,從通訊員身上接過嬌靜子。
我能帶着閨女回國了!這真是天大的喜事!
我趕緊帶着嬌靜子趕去了附近的集市,用自己不捨得花的津貼,給嬌靜子量做了一身新衣服。
回到駐地後,又託結束演出的文工團女戰士,給嬌靜子剪了發洗了澡,直到自己滿意為止。
我強壓住內心的欣喜,這種由內而外盪漾出的喜悦感染了周邊的人,小人兒也笑開了臉。
是呀,我不僅從戰場上活了下來,還多了個女兒,這真是天大的奇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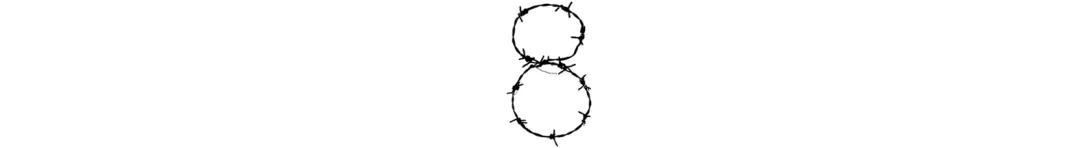
焦急地等到10月3日,回國的正式命令到了——傍晚部隊集結,4日拂曉前乘火車秘密回國。
就在大家都為這個命令興高采烈之際,一瓢冷水澆在我的頭上。
我是萬萬沒想到,師部在這時派人專門來轉告我:志願軍不能帶任何朝鮮人回國,嬌靜子必須留下。
此前,我帶着朝鮮孤兒行軍打仗的事兒,已經傳遍了81師,師首長們既沒有表揚,但也沒有批評。
我本以為師部已經默許了我們這對半路結緣的父女。
我一下急了,直接跑去找團政委,團政委説做不了主,我又找到師政治部主任。
我告訴主任,嬌靜子是個孤兒,我帶着她兩年了,出生入死,我能把仗打完就靠這個念想,她就是我閨女,我要帶嬌靜子回去過好日子,我捨不得她,她也離不開我!
政治部主任雖然深受感動,可志願軍總部有令在先,他只能開導我説,這不是一個嬌靜子的問題,這是國家與國家的政治問題。
再説,戰後朝鮮急待用人,嬌靜子應該為自己的祖國儘快消除戰爭創傷而貢獻力量,我們必須服從紀律。
道理我懂,可就這麼把嬌靜子拋下,我怎麼能甘心!
返回駐地的路上,也不知怎麼想的,我頓生一計,要被運回國的大炮都被炮兵仔細包裹好了,我把嬌靜子藏進帆布裹着的炮座裏,別人鐵定發現不了。
説幹就幹,我趕緊抱着嬌靜子去炮兵16團比劃了一番。
可那帆布包裹的炮座裏十分憋人,7歲的嬌靜子這兩年裏長大了不少,如果不能及時把她弄出來,可是會憋出人命的。
我想了想,這樣不成,小人兒的身體經不起折騰。
而且萬一讓檢查站的朝鮮人民軍查出來,這不是給志願軍丟人嘛,違反紀律的事我絕不能幹。
我揹着小人兒默然回到營地,已是傍晚時分。
路上我思來想去,都沒想到更好的辦法,到了跟前我再做什麼怕是來不及了,我打算先物色一個託付的人選。
我想起一名熟悉的朝鮮人民軍聯絡員女上尉,她戰前是文工團的隊長,丈夫犧牲,父母也在美機的轟炸中遇難,對志願軍非常友好。
我同她講了事情的前因後果,拜託她照顧嬌靜子,幫忙轉交給地方合適的好心人家收養。女上尉一聽,自然是同意的。
時間緊迫,我趕緊吩咐通訊員,讓炊事班長給嬌靜子開個小灶,炒上2個女上尉送給的雞蛋。
將近兩年的相處,小人兒已經很懂事了,她早已將我看作了自己的爸爸,常常一口一個“阿巴吉”地叫我。
開飯時,小人兒抬着那碗炒雞蛋,遞到我的跟前,一句“阿巴吉吃”,讓我緊繃的情緒失控了。
看到我哭了,小人彷彿意識到了什麼,一下子撲到了我的懷裏。
我收住淚,哄了好一會兒,她才又笑着吃起飯來。

我的反常也引起了通訊員和炊事班長的注意。除我之外,連隊裏跟嬌靜子感情最好的就屬他倆了。
倆人等嬌靜子入睡後,一起走進了我的房間。我乾脆將事情的前前後後告訴了他們,上級不準帶,炮座藏不下,只能把這小人兒留下了。
兩個大老爺們聽後,更是一籌莫展,三個人都眼睛濕潤了,我知道他們也捨不得,但是別無他法。
10月4日零時,我朝打好行裝的通訊員下達了命令:各連立即起牀,收拾行裝和武器,半個小時後出發火車站。
這時,睡夢中的嬌靜子忽然驚醒,突然喊着要找我:“阿巴吉!阿巴吉!”
我趕緊抱起嬌靜子,想先哄她入睡,人民軍女上尉聞聲趕了過來。她從我手裏接過了嬌靜子,邊拍邊輕聲哼起了當地的民謠:
睡吧睡吧寶貝,我可愛的寶貝
白頭山上有顆星,燦爛放光輝
星光閃閃守護着你,我可愛的寶貝……
嬌靜子慢慢平靜下來,雖然停止了哭聲,但小嘴兒仍夢囈般地嘟囔着。

插畫師根據現場還原
擔心嬌靜子醒來的女上尉,一邊示意我快走,一邊繼續哼着歌謠。
營裏的朝鮮語聯絡員告訴我們,這首十分動聽的民謠叫《祝福歌》。通訊員記下了民謠的歌詞,我趁機悄悄給嬌靜子留下了3個月的生活費。
10月4日拂曉前,我們秘密到了火車站。跟我預想的不同,火車站上只有極個別的人民軍內務部隊戰士在巡邏。
見我們是清一色的志願軍官兵,不但沒有什麼檢查程序,反而是一番熱烈的握手與擁抱。原來,嬌靜子完全可以順利地帶回國內……
我後悔得腸子都青了,不行,我要回去找嬌靜子!
“嗶嗶嗶”,火車出發的哨子聲響了,一下把我釘到了原地,我神魂顛倒地愣在站台上不知所措。
一名朝鮮人民軍軍官見狀,還以為我捨不得離開朝鮮,硬是和戰友將我連拉帶推擁上了火車。
這時,又傳來了一陣鐵錘敲擊鐵軌的刺耳聲。
我透過車窗發現,一名朝鮮阿瑪尼正用鐵錘用力擊打鐵軌,這是傳遞空襲警報的一種方式。
隨着阿媽妮“叮噹叮噹”的敲擊聲,背上一名和嬌靜子差不多大的孩子,也在張嘴哭喊着。
我們走後,這對母子和我的嬌靜子可如何是好啊?
看着眼前的景象,我站在火車廂門口哭得一塌糊塗。要知道,戰鬥中犧牲了那麼多的戰士,我都沒這樣哭過,可這一刻,我實在忍不住了。
我邊流淚邊對通訊員説,我們為什麼來抗美援朝啊,就是為了不讓我們的母親和孩子,像朝鮮的母親和孩子這樣受苦。
通訊員勸我説,當時我們來朝鮮戰場赴死都沒有流淚,如今要回國了,更不能流淚了。
我當時有個十分幼稚的擔心,如果美軍再打過了鴨綠江,這對母子和嬌靜子可如何是好呢。
通訊員説,營長你放心好了,再給美國佬10年,他們也打不過鴨綠江。
我説,那萬一呢。
通訊員道,如果美國佬再打,我就跟着你回來,就和美國佬他們幹。
這就是我和小小人兒嬌靜子在朝鮮戰場的故事。
電影《金姬和銀姬的命運》早已落幕,我和通訊員都深陷在《祝福歌》中,久久不能自拔。
算起來,嬌靜子已經28歲了,她結婚了嗎?做媽媽了嗎?還記得我這個中國阿巴吉嗎?
在朝鮮戰場流血犧牲,我們不後悔,這些年,我後悔的是,沒把那個小人兒帶回國啊!
我也可以忘記過去與敵人的仇恨,但讓我忘記犧牲的戰友以及嬌靜子,我怎麼做得到呀。
他們可是我一場場血戰,活下來的最後理由。

八十年代,黃萬豐副師長受邀訪問朝鮮,受到了金日成首相的親切接見。
整個行程,他滿腦子都是嬌靜子。私下先打聽,才知尋找嬌靜子要驚動朝鮮領導人,怕影響公務,話到嘴邊他又咽了回去。
這個遺憾延綿了他到一生,到80多歲,黃老依舊忘不了嬌靜子,依舊後悔沒把閨女給帶回來。
也許只有在戰場上廝殺過的人,才更能更加感同身受,那些在戰火中失去父母的孩子,他們是被歷史遺忘的戰爭受害者。
戰爭不成就英雄,只會留下孤兒寡母。
編輯:趙斯卡 羅伯特劉 / 插畫:徐六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