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學史導言(李申)_風聞
国际邪教研究-国际邪教研究官方账号-珍爱生命,愿天下无邪!2021-10-08 15:20
一、寫作緣起
我做博士論文的時候,導師任繼愈先生給我選定的題目是《中國古代哲學和自然科學》。當時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不久,百業在興。中國哲學研究領域,對於中國古代哲學和科學的關係,呼聲很高。不過我的論文對這個問題只講了一半。數年以後,我才有機會完成下一半,並於2002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合成一冊再版。當下一半將要完成的時候,又應席澤宗先生之邀,參加了由他主編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科學思想卷》(就是他多年來欲撰寫的“中國科學思想史”)的寫作。該書共七章,本來我僅擔任兩章。後來一位朋友因為出國,他擔任的兩章先後交給了我。最後,席澤宗先生在看過我撰寫的稿子以後,把他自己擔負的那一章也給了我。《中國古代哲學和自然科學》以及“中國科學思想史”的性質,使我不得不把中國古代科學的各個領域,至少是那些主要的領域,都從頭到尾摸了幾遍。據我觀察,在當今的世界上,還很少、甚至可以説沒有像我這樣做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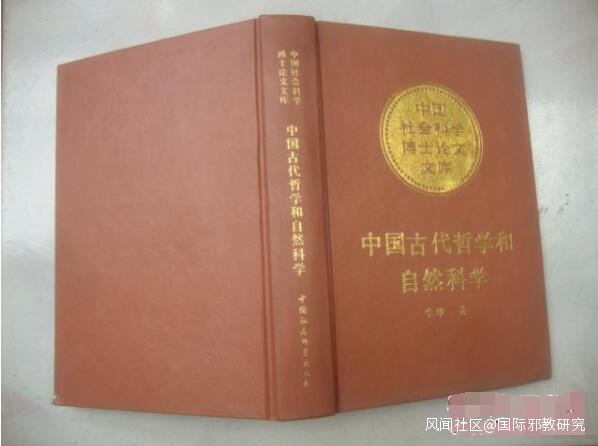 在做博士論文的時候,我不得不擱置起關於中國古代有沒有自然科學的爭論。但是到我寫作下一半的時候,就不能再對這個問題保持沉默。然而迄今為止,認為中國古代無科學的人士,似乎仍然是學術界的主流。幾部講述中國古代科學的書,也都必須加上“技術”二字。好像離開“技術”,中國古代就沒有多少、甚至完全沒有科學可言。雖然我不是專業的中國科學史研究者,而僅僅是客串而已,但是這件事對於我來説,仍然是始終難以釋懷。近二十年來,無空則已,只要有空,就想要寫一部純粹的“中國科學史”出來。
在做博士論文的時候,我不得不擱置起關於中國古代有沒有自然科學的爭論。但是到我寫作下一半的時候,就不能再對這個問題保持沉默。然而迄今為止,認為中國古代無科學的人士,似乎仍然是學術界的主流。幾部講述中國古代科學的書,也都必須加上“技術”二字。好像離開“技術”,中國古代就沒有多少、甚至完全沒有科學可言。雖然我不是專業的中國科學史研究者,而僅僅是客串而已,但是這件事對於我來説,仍然是始終難以釋懷。近二十年來,無空則已,只要有空,就想要寫一部純粹的“中國科學史”出來。
光陰荏苒,轉眼已入老年,不能再等了。於是拿起筆來,撰寫這部自認為應該寫的“中國科學史”。就在這個時候,我發現,在我之前,已經有一部《中國科學史綱》問世,而且是權威人士主編,專業人事撰寫的著作。然而心願早定,何況自古以來,同樣題材多部史書的情況早就存在,於是,也就不顧淺陋,來湊一次熱鬧。
二、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
要撰寫“中國科學史”,首先遇到的問題就是:中國古代有沒有科學?我的專業是中國哲學史,然而我這個專業,卻設置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畢業以後又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工作二十年。我所知道的是,自從上世紀初西方學術由嚴復等人正式傳入中國以來,關於中國古代有什麼、沒什麼,就不斷髮生爭論。研究哲學的認為,中國古代沒有哲學;研究宗教的認為,中國古代沒有宗教,中國古代是無宗教國。中國古代沒有科學,不過是用現代學術標準反觀中國傳統文化的結果之一罷了。中國古代,既無宗教,又無哲學,也沒有科學,那麼,中國古代還有什麼呢?按照嚴復的説法,中國古代就無“學”。在嚴復看來,所謂學,就是要通過大量的事實然後總結出結論來,才叫做學。中國古代,大家唯聖人之言是從,以聖人的是非為是非,根本就沒有人從大量事實出發去總結出什麼結論的事,這樣,説中國古代無學,也就可以理解了。
那麼,中國古代,都有些什麼呢?!
自從胡適寫出《中國哲學大綱》、馮友蘭寫出兩卷本的《中國哲學史》之後,中國古代無哲學的聲音就低沉下去了。前幾年又有人突然提起中國哲學的合法性問題,雖然曾經引起了一陣小波瀾,然而也僅僅是小波瀾而已。至少多數中國學人,不會再認真對待這個問題。在宗教問題上,任繼愈先生提出了“儒教是教説”。雖然起初二十年間贊同者只有三五人。但到今天,贊同這個判斷的,已經是一支龐大的隊伍。學界普遍承認中國古代有宗教,這個宗教就是儒教,只是個時間問題。
 記得在編寫《宗教大辭典》的時候,當時多數人不同意編進儒教。我的一個朋友説,你們讓李申先畫一個儒教出來嗎,然後大家再批評,看他畫的那個儒教是不是宗教。今天,我也想先畫一個“中國科學”出來,供學界批評:中國古代的這點東西,是不是科學?
記得在編寫《宗教大辭典》的時候,當時多數人不同意編進儒教。我的一個朋友説,你們讓李申先畫一個儒教出來嗎,然後大家再批評,看他畫的那個儒教是不是宗教。今天,我也想先畫一個“中國科學”出來,供學界批評:中國古代的這點東西,是不是科學?
不過在畫出中國古代科學麪貌之前,還是應該先談兩句我對“什麼是科學”的認識,或許對於讀者和作者自己,都有某些益處。
三、什麼是科學目前關於科學的定義,據説是數以百計。據筆者所知,處於兩個極端的,大約有兩種。一種認為,只有從一個或少數幾個基本原理出發,邏輯地推出一系列定理或判斷的知識系統,才是科學。甚至認為這些原理或者定理,都必須能夠用數學方式加以表示。其標本,就是歐幾里德的《幾何學》。依照這個標準,不僅中國古代沒有科學,即使在古希臘,符合這個標準的科學,大約也只有歐氏的幾何學。亞里士多德到托勒密的天文學,亞氏本人的《動物學》,都難以符合標準。因為直到現在,天文學和生物學的許多內容,還必須依靠經驗的觀察。其所含知識之間,也未必都能組成一個邏輯系統。
實際上,這樣嚴格的定義主要不是説古希臘如何如何,而是為了要説明,只有像近代以牛頓為代表的那樣的學,才是科學。其它的,都難以稱為科學,最多也就是經驗而已。經驗,僅僅是一些沒有系統的知識的堆集,因而未必正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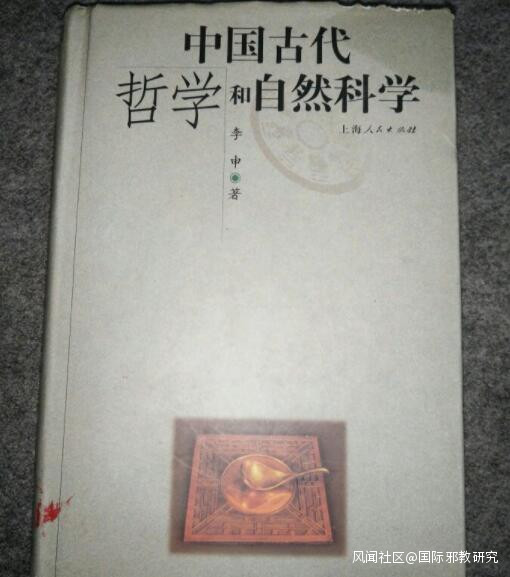 這樣的科學觀暗自包含着這樣的前提:科學所提供的知識都是正確的,而這些正確的知識之間都是有嚴密邏輯相聯結的。凡是不能用嚴密邏輯聯結的知識,很難保證是正確的。
這樣的科學觀暗自包含着這樣的前提:科學所提供的知識都是正確的,而這些正確的知識之間都是有嚴密邏輯相聯結的。凡是不能用嚴密邏輯聯結的知識,很難保證是正確的。
把這樣的科學觀打開缺口的,是以愛因斯坦為代表的新物理學。相對論和量子論的出現,使以牛頓為代表的物理學原理僅僅在宏觀情況下才是正確的,因而並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知識。與此相伴,歐氏幾何的真理性也打了折扣。在曲面條件下,兩點間並不是直線最近。這樣,被認為正確的科學知識,原來僅僅在一定範圍內才是正確的。新物理學曾經使不少傳統的物理學家驚惶失措,而伴隨着新物理學所帶來的新科學觀,給學術界所帶來的震動,並不亞於物理學本身。
牛頓科學並不是完全正確的,這就不由人不想起被牛頓科學所推翻的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物體只有被推才能運動,重物體比輕物體下落得快,太陽是繞着地球轉的,在當時人類的實踐範圍內,也都是正確的知識。甚至燃素論,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説是正確的,因為它至少説出了可燃物是因為含有可以燃燒的東西。因為直到現在,維生素的得名,也不過僅僅説出了其中含有可以維持生命的東西。
如果再往上推,則可以推到人類剛剛誕生的時期。這個東西是可以吃的,那種野獸是危險的,用木棒對付野獸要勝於徒手,用打碎的石頭的尖鋒挖掘比手好使。如此等等,就是人類最早的正確知識。這些知識,是科學的源頭。因此有人得出結論説,一切確切的知識,比如“花是紅的”,“草是綠的”等等,就是科學。這是另一極端的關於科學的定義。這樣的定義,也不能説是錯誤的,因為除了把“花是紅的”之類的知識歸入科學之外,還沒有其它更好的歸宿處。
這樣,我們就有了一個科學知識發展的序列,也是一部科學發展的歷史:從最簡單的確切知識到最複雜的知識系統。雖然正確的程度有區別,但在一定範圍內都是正確的知識,則沒有區別。至於知識系統化的程度,也是隨時代發展而發展。當人類剛剛脱離動物界的時候,其知識是否有什麼系統,是個不易回答的問題。但在我們視野可及的範圍內,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區間內,人類的知識,也都有了某種系統。只是系統化的程度有別,邏輯嚴密的程度有別而已。
用這樣的科學觀看待中國古代的知識狀況,我們完全有理由説,中國古代是有科學的。而本書,也就力求描述中國古代科學發展的歷史,揭示中國古人認識世界的曲折歷程。
四、“科學”概念和科學觀
“科學”在英文中是science,德語是wissenschaft,法文scientin,均來源於拉丁文scientia,詞根為scio,其本義是“知識”、“學問”。“科學”的希臘文是επιστήμη,從動詞επίσταμαι產生,本義為“知道”。但古代的這些知識、學問,從後人的眼光看來,未必就是正確的。甚至根本難以列入今天被稱為“科學”的知識的範疇。比如在印度,所謂知識,就是“吠陀”。對我們今天來説,吠陀只能歸入宗教或者神話傳説之類,但在古人的眼裏,這就是他們的知識,而且被認為是真理,最正確的知識。至於其它民族所説的知識,雖然未必都把今天看來不過是神話的東西包括在內,但並不區分是自然界的知識還是社會方面的知識,則是普遍現象。所以迄今為止,科學這個概念,在不少文字中,還是既指關於自然界的知識,也指關於人類社會領域的知識。而俄國或蘇聯所建立的科學院,就既包括了自然科學各個領域的研究所,也包括着社會科學或者被稱之為人文科學的研究所,至今仍然如此。我國的科學院,起初也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在一起的。二者的分離,是文化大革命以後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的事。
 科學這個概念演變的歷史,也是一部濃縮了的人類科學史。它説明,科學,作為知識或者學問,起初包含着各種各樣的知識,其中正確和錯誤並存,精華和糟粕共生。科學史,應該如實地描述科學的這個發展過程,展示人類認識世界的軌跡,以給後人經驗和教訓,榜樣和警示。
科學這個概念演變的歷史,也是一部濃縮了的人類科學史。它説明,科學,作為知識或者學問,起初包含着各種各樣的知識,其中正確和錯誤並存,精華和糟粕共生。科學史,應該如實地描述科學的這個發展過程,展示人類認識世界的軌跡,以給後人經驗和教訓,榜樣和警示。
相對論、量子論誕生一百多年以來,人們的科學觀念已經有了巨大的變化,已經不再把科學等於正確,看作真理的化身。人們知道,今天的科學成果,也可能包含着我們尚未覺察的錯誤,或者僅僅在一定範圍內才是正確的。因此不可認為我們已經窮盡了真理,而應該謙虛謹慎,兢兢業業,把人類認識世界的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然而在如何看待科學的歷史方面,卻仍然認為,古代,至少在中國古代,是沒有科學的。從理論上説,這是不徹底的現代科學觀。
這種科學觀的形成,在牛頓時代,或者在這個時代以後不久。在這個時代,基督教教會認為,他們自己掌握着絕對的真理,不僅上帝,而且教皇,也是沒有過錯的。因此,那些和基督教會認定的教條不一樣的學説,肯定是謬誤。在反對基督教的十八世紀法國唯物主義哲學家看來,恰恰相反,只有他們才發現了真理,那些傳教的和信教的,不是騙子,就是傻子。當哥白尼、伽利略到牛頓的科學發現被證明為真理、並且冠以“科學”稱號的時候,此前被基督教會認定的學説自然被視為非科學的,至少是夠不上科學的資格。而當人們把中國古代所掌握的知識和歐洲相比較的時候,發現中國古代所掌握的、以天文、數學為代表的知識,甚至還不如中世紀後期的基督教會。因此,接受了近代科學的人們,無論是歐洲人還是中國人,都認為中國古代無科學,也就不是什麼奇怪的事。雖然一百多年以前有位偉人就説過,我們今天的知識中所包含的謬誤可能比真理還要多。然而直到又過了一百多年,在相對論、量子論出來以後所誕生的所謂科學哲學家們,才共同達成了這樣一種共識:科學,是一個不斷變換着思維方式的人類的認識活動,這個活動的結果,儘管被人們所普遍接受,但並不都是正確的。至於要人們普遍認為科學是一個不斷發展的認識過程,就像人們普遍接受了地球是圓(球形)的,是圍繞太陽旋轉的那樣,就更加困難。
人們在考察“science”這個詞彙來源的時候,知道它源於拉丁語,而且在science出現以前,中世紀就有了同義的scientia。那麼,假如當時沒有scientia,也就是沒有科學這種東西,又如何能出現scientia這樣的詞彙和概念呢!我們只能説,當時的scientia和今天的science相比,許多知識是錯誤的,或者是粗糙的,應該拋棄。但應該承認,今天的科學,就是從當時的科學發展來的。
為了區別今天的科學和過去的科學,有人發明了“前科學”或“潛科學”這樣的概念。意思是説,過去雖然也有類似的知識,但夠不上科學的資格。就像胎兒還沒有人的資格一樣。當然,如果拿剛剛受精的卵和一個成人比較,其區別自然是明顯的。然而,如果把剛剛出生的嬰兒和一分鐘前母腹中的胎兒相比,相差有多大呢?假如因為難產而晚出生了一段時間,或者因為早產而早出生了一段時間,則“潛在的人”就成了“現實的人”,或者“現實的人”還是個“潛在的人”。至於科學和“潛科學”或“前科學”的區別,還決不像胎兒和嬰兒的區別這樣鮮明。而且“前科學”和“潛科學”既然都用了“科學”這個概念,就説明,它們也都是科學家族的成員。如同我們研究人體發育不能不研究胎兒一樣,我們研究科學的歷史,也不能丟掉近代以前的科學,包括中國的科學。如果僅僅認為牛頓開始的科學才是科學,而以前的不是,那麼,遲早有一天,牛頓科學也會被歸入“潛科學”或“前科學”一列。為了避免這種無用的、只能帶來混亂的概念遊戲,我們還是把以前的科學也叫做科學,並按歷史階段加以區別,就像我們把原始時代的社會也看做人類社會,而只是區別出社會的類型一樣。
五、“科學”一詞在中國
有人説,“科學”是外來語,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的啓蒙思想家福澤瑜吉首先把“science”譯成“科學”,後來被中國學者採用的。
如果是外來語,那就應該是science,就像今天的WTO、GDP一樣,或者像菩薩、坦克、吉普,用它們的音譯,也可以説是外來語。但是,科學這個詞,儘管是日本人用它來翻譯science,但日本人用的是漢語詞。因此,對於漢語,科學不是外來語。在古代漢語中,曾經不只一次地出現過“科學”這個詞。
就現有的文獻檢索,有的“科學”可能是“科舉”,因形近而誤。比如陳亮《送叔祖主筠州高要簿序》:“自科學之興,世之為士者往往困於一日之程文……”。有的版本則是科舉。而且從上下文看,科舉也比較合理。但是有些“科學”,則當時就是這樣的用法。
 見於文獻,最早使用“科學”這個詞彙的是唐代人。唐朝末年,羅袞在《倉部栢郎中墓誌銘》中説道:“近代科學之家,有栢氏倉部府君,諱宗回,字幾聖……”(《文苑英華》卷946)云云,其中所指的倉宗回,是個科舉落第者。文中説倉氏隨父學《開元禮》,考官考的是《尚書》,而他對《尚書》的理解,和當時認可的鄭玄注不同,因此落第。所以此處的科學,當是指科舉之學的學科而言。
見於文獻,最早使用“科學”這個詞彙的是唐代人。唐朝末年,羅袞在《倉部栢郎中墓誌銘》中説道:“近代科學之家,有栢氏倉部府君,諱宗回,字幾聖……”(《文苑英華》卷946)云云,其中所指的倉宗回,是個科舉落第者。文中説倉氏隨父學《開元禮》,考官考的是《尚書》,而他對《尚書》的理解,和當時認可的鄭玄注不同,因此落第。所以此處的科學,當是指科舉之學的學科而言。
宋代,薛季宣《答徐元德書》,説自己“早失義方之教,仕縁世蔭。以惰不為科學之習。居官無有治跡可以求知上官。心非不欲為眾所為,顧不能耳。”(《浪語集》巻二十五)其中的“科學”也未必就是科舉之誤。元代王惲《絳州重修夫子廟碑》把“科學”和“異端”並提:“朝夕孜孜,匪不磨勵。科學異端,簿書期會,愚者不及,淪於自棄。”(《秋澗集》卷五十二)張憲《悼博羅同知沒于軍》則感慨他的沒于軍陣的友人即使從事科學,又能如何:“已矣專科學,於今定若何。陣雲寒可掬,兵氣耿相磨……”(《玉笥集》卷八)這兩處用法,説是“科學”,都比“科舉”更為合理。
明代初年,禮部公堂上立石,刻着禮部官員的職責:“尚書、侍郎,掌禮樂儀章、郊廟祭祀、朝貢會同、賓客宴享、學校科學之政。”(《禮部志稿》卷八)朱元璋曾有指示,允許監生回到父親所在的地區參加“科學”考試。“近奉欽依,聽其依親原籍,亦得與考科學,亦固可待志士矣。”(同上,卷六九)據清代所編《續通典》卷22:“正嘉之間,文體日偷。楊慎極論其弊曰:太祖始制科學,詔舉子經義,無過三百字,不得浮詞異説。”則明代《禮部志稿》中所説的“科學”,很可能就是明朝初年朱元璋以及他的臣子們曾經用過的詞彙。因為朱元璋不可能 “始制” 科舉。而這個詞的意義,就是指科舉的分科之學。
今天有些學者喜歡談論古代整體思維,説古代的學問也是一個整體,並不分科。這種説法是錯誤的。至少在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先秦的典籍中,不僅學問在大的方面要分科。比如孔子把他的學生分為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四科。就在具體的領域,也是分科的。比如醫學,《周禮》中就分數科。愈接近現代,與今天自然科學相近或相同的學科,其分科更是日益明確和固定。宋朝政和年間,醫學“學生分三科,兼治五經內一經。方脈科,通習大小方脈。風產針科,通習針灸口齒咽喉眼目。痬科,通習瘡腫傷折金鏃書禁。三科學生,各習七書。”(宋章如愚《羣書考索後集》卷三十)清代初年,關於天文學,“禮部議,於官學生內,每旗選取十名,交欽天監,分科學習。有精通者,俟滿漢博士缺出補用。”(《欽定八旗通志》卷九十八)所以當乾隆開千叟宴的時候,在欽天監工作的、當時七十二歲的意大利人那永福作的千叟宴詩中寫道:“歐邏巴州西天西,意達里亞臣所棲。六城環以地中海,高墉架海橫天梯。人有醫治教道四科學,物有金剛珊瑚哆囉珠象犀。……”(《欽定千叟宴詩》卷二十五)在這裏,把西洋傳來的學問譯為“科學”,可以説是呼之欲出了。如果再細心查尋,則自乾隆以後,到清朝末年,中國人把西洋學問稱為“科學”的,很可能有早於日本人者。在這裏,重要的不是要和誰爭什麼發明權,而是要説明,科學,是中國固有的詞彙。
 然而,用科學翻譯science,卻並不十分恰當。更恰當的,應當是“格致”或其它詞彙。其重要原因是,“格致”,是人類不可或缺的認識活動;而“科學”,容易被認為是一個獨立存在的、成型且大體固定的知識體系。
然而,用科學翻譯science,卻並不十分恰當。更恰當的,應當是“格致”或其它詞彙。其重要原因是,“格致”,是人類不可或缺的認識活動;而“科學”,容易被認為是一個獨立存在的、成型且大體固定的知識體系。
六、中國古代的窮理和格致
英文Science的意思,就是中國古代所説的知識或者學問,那麼,用“知識”或“學問”去翻譯Science,豈不更加確切!?然而知識、學問,一般是指求知活動的結果。而當日本人、中國人於19世紀末開始接觸西方人的Science的時候,他們發現,Science指的不僅是求知的結果,還包含自覺去求知的活動。這種求知活動,有一套更加高明的方法,能獲得比較正確的結果,需要一個更加適當的詞彙去描述它。首先是日本人,後來是中國人,最初找到的詞彙,是古漢語中的“窮理”和“格致”或“格物”。明治初期的日本大學中,就有“窮理學”一科。
“窮理”出於《易傳》“窮理盡性而至於命”。翻譯成現代漢語,應當是“窮究物理盡知人性直到通曉天命”。説的是認識了所有的道理,或者徹底認識了那個理,也就是充分認識了自己的本性並且能充分發揮出來,就能夠通曉天命。在古人看來,這是認識的最高境界。當然,Science是不講什麼天命的,而窮理,也就是一項自覺而認真求知的事業,和Science接近。
 格致或格物,全稱是“格物致知”,出於《大學》:“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在這裏,格物致知,被認為是治國平天下的前提。從漢代以來,儒者們對“格物”的“格”字做出了不同的解釋,漢代鄭玄認為“格”就是“來”,宋代程頤認為“格”是“至”。清代顏元解釋為“手格猛獸”的“格”。意思都是接觸事物,以便認識事物的理。張載則解釋為“去”。説去掉心中之物,使心虛明純淨,才可以達到認識的極點。司馬光解釋為“扞格”的格,説是心能抵禦外物,才能認識真正的道。總之也是自覺的認識活動。元代一部醫學著作,名稱就叫《格致餘論》。清代有一部《格致鏡原》,主要也是講自然科學問題。明代末年,徐光啓為《幾何原本》所寫的序言中,也把利瑪竇帶來的天文數學等稱為“格物窮理”之學。也就是説,格致一詞,早就被中國人作為自覺接觸事物以獲得確切知識的概念。所以當中國人最初接觸Science的時候,更多地還是把Science譯為“格致”。
格致或格物,全稱是“格物致知”,出於《大學》:“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在這裏,格物致知,被認為是治國平天下的前提。從漢代以來,儒者們對“格物”的“格”字做出了不同的解釋,漢代鄭玄認為“格”就是“來”,宋代程頤認為“格”是“至”。清代顏元解釋為“手格猛獸”的“格”。意思都是接觸事物,以便認識事物的理。張載則解釋為“去”。説去掉心中之物,使心虛明純淨,才可以達到認識的極點。司馬光解釋為“扞格”的格,説是心能抵禦外物,才能認識真正的道。總之也是自覺的認識活動。元代一部醫學著作,名稱就叫《格致餘論》。清代有一部《格致鏡原》,主要也是講自然科學問題。明代末年,徐光啓為《幾何原本》所寫的序言中,也把利瑪竇帶來的天文數學等稱為“格物窮理”之學。也就是説,格致一詞,早就被中國人作為自覺接觸事物以獲得確切知識的概念。所以當中國人最初接觸Science的時候,更多地還是把Science譯為“格致”。
但是,“窮理”的目的是要儘性至命,“格致”或“格物”為的也是治國平天下。明代王陽明“格竹”失敗的故事,已經廣為流傳。與王陽明同時的湛若水作《格物通》一百卷,講的全是正心修身、敬天法祖的道德修養和治國理論。這些作法以及獲得的結果,都與Science的宗旨和方法相差甚遠。而且,當日本人或中國人使用“格物”、“格致”或“窮理”去對應Science的時候,起初僅僅指的是物理、化學等少數學科。直到二十世紀初中國開辦京師大學堂,其“格致”一科指的也還是物理、化學等少數在西方近代比較發達的學科,不能涵蓋Science所指的眾多學科。於是,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由康有為、嚴復、王國維等人借鑑日本學者的作法,把“科學”作為和Science對應的概念,以指稱人類自覺的求知活動以及求知的成果。
“科學”雖然僅僅是分科之學,但是這個詞彙表明,Science是一種“學”,也就是一種學問,符合Science指稱知識或學問的本義。什麼學?分科之學。雖然傳統曾經用過“科學”指稱分科之學,但現在,這種分科之學不僅僅是分科而已,還包括着採用新的方法和新的治學目的和治學態度。如同“經濟”這個古代詞彙被賦予了新的內容一樣,科學,隨着所指稱對象的變化,也在原來的基礎上又增加了新的內容。清代末年,取消科舉。新開辦的學堂,有數理化,醫農工商,也有文史政法,包括讀經諸科,被《清史稿》的作者們統稱為“科學”。只有“端飭品行”一項,不在科學之內。當時距離科學一詞的流行尚不很遠,這就是説,近代中國人接受科學作為Science對應詞的時候,其主要意義,也是分科之學。
 然而,在科學旗幟下的那些分科之學,不僅和“以聖賢是非為是非”的科舉分科之學有重大區別,就是和傳統的醫學、天文等學問的做法,也有重大不同。許多結論是新的,方法也是前所沒有的。拿這新的結論和方法與過去相比,就感到傳統的方法“不科學”了。古代沒有這些方法和結論,當然也就沒有科學。於是,和西方近代學者認為只有他們的結論才是正確的一樣,中國古代無科學的結論,也就順理成章了。於是,歷史被割斷了,科學,似乎是一種突然冒出來的、沒有歷史的學問。如果説有歷史,歷史也只能從哥白尼、伽利略等算起。
然而,在科學旗幟下的那些分科之學,不僅和“以聖賢是非為是非”的科舉分科之學有重大區別,就是和傳統的醫學、天文等學問的做法,也有重大不同。許多結論是新的,方法也是前所沒有的。拿這新的結論和方法與過去相比,就感到傳統的方法“不科學”了。古代沒有這些方法和結論,當然也就沒有科學。於是,和西方近代學者認為只有他們的結論才是正確的一樣,中國古代無科學的結論,也就順理成章了。於是,歷史被割斷了,科學,似乎是一種突然冒出來的、沒有歷史的學問。如果説有歷史,歷史也只能從哥白尼、伽利略等算起。
實際上,這裏説的“不科學”,主要是方法不精密,結論不準確而已。如果顧及到一點歷史,則古人那些自覺而認真的求知活動,也在不斷發展着求知的方法,修正他們的結論。而我們今天的方法和結論,不過也僅僅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認識水平而已。這樣的方法和結論,不僅不是認識的終結,而且和以前的方法和結論也有割不斷的聯繫。這樣認識,就不會把不準確、不精密説成是“不科學”。因此,認為中國古代無科學的觀點,也僅僅是一種把我們當代的科學和正確劃了等號的觀念在作怪罷了。
這裏的粗略考察表明,中國古代,不僅有“科學”這個詞,還有科學這樣的事。既然Science指的是學問和知識,豈有堂堂中國五千年文化,而沒有知識和學問之事的?!我們可以批評古人的方法太粗疏,有的甚至完全不正確;批評他們的結論許多太浮淺,有的甚至是錯誤。但要説那不是科學,則是説不通的。有人説,那是技術,是經驗。那麼,技術也好,經驗也好,在大的文化分類系統中,應該歸於哪一類呢?宗教?哲學?還是藝術?都歸不進去,還是歸入科學一類恰當一些。
 而且,把技術和科學完全對立起來,也是不恰當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情況是有的。然而低等動物僅僅會把獲得的知識變成本能,高等動物所獲得的許多知識就需要通過教育才能延續。當狒狒拿起石頭去砸碎硬果的時候,你很難説這裏沒有知的內容。一個有着五千年悠久文化傳統的民族,怎麼可能僅僅會做,而沒有知?!
而且,把技術和科學完全對立起來,也是不恰當的。“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情況是有的。然而低等動物僅僅會把獲得的知識變成本能,高等動物所獲得的許多知識就需要通過教育才能延續。當狒狒拿起石頭去砸碎硬果的時候,你很難説這裏沒有知的內容。一個有着五千年悠久文化傳統的民族,怎麼可能僅僅會做,而沒有知?!
在筆者看來,如果把科學定位於關於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狀況的知識,則技術就是關於人如何去做的知識。二者並沒有原則區別。雖然如此,本書還是儘量避免那些技術層面的東西,而僅僅把關於自然界的知識作為描述的對象。
七、中國科學史的起點和終點雖然有人主張,凡是確切的知識都是科學。但是我們只能説這是屬於科學領域的知識,卻不能説這是人類科學活動的開始。單是確切的知識,不單早期的人類具有,就是一些高級動物也有,而不僅是本能。然而這些知識,都是動物在謀生過程中,人類在他們的生產和生活實踐中所不自覺地獲得的,是謀生,或生產和生活活動的副產物。沒有這些知識,不僅人類,許多稍微高級一點的動物,也無法生存。這些知識的正確性,是促進人類把探討知識本身作為重要事業的前提。人和動物的區別,就是無論動物如何聰明,都不可能專門把獲取知識作為自己的一項事業。但是當人類意識到知識價值的時候,就會分出一些人來,專門,或主要從事知識的生產。直到今天,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幾乎都要謀求在確切知識、也就是科學知識的指導下進行,才覺得放心。科學知識的生產和應用狀況,已經成為一個國家富強與否和文明程度的標誌。因此,我們也只把自覺從事的以獲取知識為目的的活動稱為科學活動,並且把這個自覺獲得知識活動的始點作為科學的始點。
 自覺獲取知識的活動,在不同領域的表現是不一樣的。在天文學領域,樹起一根標杆去測量日影長短變化,甚至在未樹標杆之前,注意觀測日月星的出沒狀況並且記錄它們,這就是天文學的開始。在醫學領域,認真觀測疾病的狀況,自覺尋求治療的方法和藥物,就是醫學的開始。在農業領域,探討增產的方法,也應該是農業科學的開始。在數學領域,能夠從具體事物中抽象出數字並自覺探討數字之間的關係,也就是數學的開始。因此,像我國典籍《山海經》中記載日月出入的位置,《夏小正》中記載中星出沒的時間,甚至神農嘗百草的傳説,后稷教民稼穡,都應視為我國先民科學活動的開端。這些開端具體在什麼時代,當時是什麼樣的情況?今天已經很難知曉了,然而我們的先民很早就自覺地從事專門生產知識的活動,則是確定無疑的。這些活動的成果,以不同方式,記載在我們的古籍當中。這些記載,就是我們這部中國科學史的基本資料。
自覺獲取知識的活動,在不同領域的表現是不一樣的。在天文學領域,樹起一根標杆去測量日影長短變化,甚至在未樹標杆之前,注意觀測日月星的出沒狀況並且記錄它們,這就是天文學的開始。在醫學領域,認真觀測疾病的狀況,自覺尋求治療的方法和藥物,就是醫學的開始。在農業領域,探討增產的方法,也應該是農業科學的開始。在數學領域,能夠從具體事物中抽象出數字並自覺探討數字之間的關係,也就是數學的開始。因此,像我國典籍《山海經》中記載日月出入的位置,《夏小正》中記載中星出沒的時間,甚至神農嘗百草的傳説,后稷教民稼穡,都應視為我國先民科學活動的開端。這些開端具體在什麼時代,當時是什麼樣的情況?今天已經很難知曉了,然而我們的先民很早就自覺地從事專門生產知識的活動,則是確定無疑的。這些活動的成果,以不同方式,記載在我們的古籍當中。這些記載,就是我們這部中國科學史的基本資料。
科學是人類自覺認識世界、獲取知識的活動,和哲學、宗教都不一樣。哲學是一個個獨立的思想體系構成的世界,體系之間的界限,要遠大於體系之間的聯繫。宗教的世界裏,更是一個個獨立的“王國”。愈到後來,“王國”之間就不僅是界限,而且是排斥甚至敵對。科學則不是一個個獨立的思想體系,而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是人類為了更好的生活因而追求更多的知識、並且對知識不斷發展和改進的活動。這樣的活動,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必要組成部分。如果因為某些偉大人物的名字而使科學之間有所區別,那也不是獨立的體系,而是科學本身發展的階段,一個分支。哲學和宗教體系一個個都獨立於社會生活之上,人們也根據自己的狀況決定對它們的態度:需要,還是不需要?而未必就影響自己的生產和生活。但人們,無論是個人還是羣體,都不能離開科學,否則就要墮入愚昧和落後。因此,哲學體系在歷史上不斷變更,宗教體系也不斷更替,都有自己的誕生和滅亡。誕生的,將來也要滅亡。但科學,可以説有誕生,從人類自覺追求知識開始;卻不會有滅亡。因為人類存在一天,就需要知識,需要知識的更新。
但是對於中國科學來説,卻有自己的終點,這就是隨着西方近代科學的傳入,中國科學的支流逐漸融入人類科學的主流。具體在什麼時候,不易確定。各個領域也不一樣。在天文學領域,以清代國家採用湯若望等人所制訂的歷法為標誌,中國古代天文學就走到了盡頭,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其它領域,則要到鴉片戰爭以後,才逐漸退出了歷史舞台。也有的門類,比如中國醫學,仍然在盡着自己的使命。我們之所以説傳統醫學,也就是中醫也有終點,只是説它的理論已經不是在傳統的道路上繼續發展。進一步發展的道路,是融入近現代的世界醫學。
八、中國科學史的意義
單是為了一句“中國古代無科學”,就值得撰寫一部《中國科學史》。然而《中國科學史》的意義,決不僅僅是要滿足阿Q式的虛榮。重視自己的歷史,幾乎是任何民族的共性。一句“讀史使人聰明”,幾乎説盡了所有歷史著作的意義。歷史上,帝國主義征服一個民族,從思想上首先要做的,就是消滅那個民族的歷史意識。社會愈是發展,人們愈是想較多地知道自己的歷史。如今在我們中國,隱士、流氓,宦官、妓女,纏足、賭博,都有了自己的歷史著作。相比之下,為科學修史,當更為迫切和需要。
 雖然,為中國科學修史,而且是要修成一部純粹的、離開技術問題也能成立的科學史,這件事的難度,恐怕比我這個僅僅客串了一點中國科學史研究的作者所能想象的要複雜得多。然而在這裏,我也只能像寫作《中國儒教史》時候的心情一樣,以馬克思自勉的話自勉:
雖然,為中國科學修史,而且是要修成一部純粹的、離開技術問題也能成立的科學史,這件事的難度,恐怕比我這個僅僅客串了一點中國科學史研究的作者所能想象的要複雜得多。然而在這裏,我也只能像寫作《中國儒教史》時候的心情一樣,以馬克思自勉的話自勉:
這裏是地獄的入口處這裏必須禁絕一切猶豫。筆者希望,這本《中國科學史》之後,應有真正夠格的《中國科學史》出來。
九、中國科學史的寫法“中國科學史”的全稱應當是“中國自然科學史”,即中國人認識自然界事物的歷史。它的內容,是自然事件和自然物以及相互之間的關係。人與自然事件和自然物的關係,我們視之為技術,而一般不列入本書的範圍,除非不得不提及的情況下,也是為了尋求在這種關係中體現了什麼樣的人對於自然事件之間關係的認識。這是本書對於科學和技術關係的處理。當然,也不涉及社會科學問題。這不是作者本人不認為社會科學也是科學,而僅僅是為了適應目前多數人關於“科學”概念的積習而已。
一般説來,對自然物和自然的事件的認識,都是具體的認識。比如生物中那些個體的習性,非生物中的某些具體物的性質。然而第一,在取得了許多具體認識之後,人們不可能不把這些知識加以概括,得出更進一步的、具有普遍意義的結論來。即如花是紅的、草是綠的,也都不僅僅是具體的知識,而是概括的知識。一般説來,凡是知識,都是某種概括出來的共同本質。這是人類在自然的生命途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抽象能力。區別僅僅在於概括程度的高低,也就是知識所反映的實際範圍的大小。而當這種概括達到當時的最高點的時候,一般也就被列入哲學的範圍。不僅後人把這些知識列入哲學,即使當事人,也往往認為自己所得的知識是哲學。直到牛頓,仍然把自己那些物理學定律視為哲學結論。
從一個個具體的知識中歸納、概括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結論,其中不可避免地要進行從特殊到一般的推論行為。即使像花是紅的、草是綠的這樣的結論,也不可能是完全歸納的產物。而且實際上,花並不都是紅的,草也並不都是綠的。至於那些具有更高普遍意義的結論,其中不確定的、甚至一定是錯誤的內容,當更加嚴重。這就是人們常説的“靠思維甚至臆測來填補”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説,把這部分內容放入哲學,是正確的。然而,迄今為止的科學結論,又有幾項是完全歸納而不帶推理甚至臆測的內容呢!在這些內容上,本書的內容和哲學,會有一定的交叉。原因僅僅在於,科學和哲學,本就處於這樣的關係之中。
 從和自然物對立的意義上,人是認識者。所以我們的科學史,就是人認識自然界的歷史。從自然物的意義上説,人體、包括人體的特殊器官:大腦,也都是自然物。因此,對於人體包括大腦以及精神現象的種種問題,也不能不納入科學史的範圍。在這裏,我們還會碰到作為哲學核心的精神與物質的關係問題。然而,我們在這裏不討論諸如“心生種種法生”或者“存在就是被感知”一類純粹依賴思維產生的問題,而僅僅把範圍限定在我們認為是恰當的領域。
從和自然物對立的意義上,人是認識者。所以我們的科學史,就是人認識自然界的歷史。從自然物的意義上説,人體、包括人體的特殊器官:大腦,也都是自然物。因此,對於人體包括大腦以及精神現象的種種問題,也不能不納入科學史的範圍。在這裏,我們還會碰到作為哲學核心的精神與物質的關係問題。然而,我們在這裏不討論諸如“心生種種法生”或者“存在就是被感知”一類純粹依賴思維產生的問題,而僅僅把範圍限定在我們認為是恰當的領域。
人類的抽象、概括和推理能力,是發展認識的必要條件。沒有這樣的能力,也就沒有科學。然而,這個能力也是人類認識陷入錯誤的契機。有位名人説過,真理再向前一步,即使僅僅一小步,就會變成謬誤。當人類把自然物的能力向前推進以致遠遠超出它自身的能力的時候,自然力就成為超自然力,負載超自然力的對象,就成為人類最初的神。本書不討論神學問題,但是也必須説出當初人類在認識中如何把正確的知識由於推理的過度而成為錯誤,並且還把這類知識和其它知識放在一起而不加區別。並且想借此告訴人們,現在被稱為宗教的那些觀念,並不是人類純憑想象所建立起來的,雖然後來的宗教觀念確實許多是僅憑想象甚至是有意的謊言,但在最初,則主要是在認識過程中出現的錯誤。也就是説,神祇觀念,和科學是“同根”生出來的,但是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就像人類中的兄弟、朋友後來由於種種現實的原因而不可避免地成為仇敵一樣。
誇大自然物的力量創造出了神祇,誇大人的力量,就人是自然物這一點來説,乃是把人崇拜為神的開始。就人作為人而言,對人力量的誇大,就是產生巫術的温牀。巫術和科學的知識處於直接對立的地位,也直接危害着人類的身心健康,然而它也不是從人類認識過程之外產生的騙局,而是人類認識過程中的謬誤,與人類急切想掌握自然力的願望相關。中國古代,和其它民族一樣,也往往會把這類知識視為真理,和那些正確的知識放在一起。而我們的科學史,也不得不涉及這些內容。
當我們注意科學發展中,也就是人類認識世界的過程中那些謬誤的時候,我們看到,人類比動物高明多少,也就比動物荒唐多少。然而無論是聰明還是荒唐,不僅是後人的財富,也是後人的鏡子。這裏展示着人類求知過程的曲折,展示着求知道路的艱難。當我們今天讚頌古人的輝煌、或者慨嘆古人何以如此荒唐的時候,我們也當低頭看看自己。因為一句諺語説得好:“閣下,這説的正是您呢!”
 作者:李申
作者:李申
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縣人。1969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獲哲學博士學位;2000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轉任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現任中國無神論學會顧問、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中國反邪教協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