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力克丨德國式的“文明”“文化”思想戰,為什麼沒有出現在中國?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2021-10-12 21:24
高力克丨浙江大學社會學系教授
西方語境中的“文明”與“文化”
“文明”(civilization)與“文化”(culture)都屬於舶來的“和制漢語”,即來自古漢語的日本“漢字”詞語,被日語借用來翻譯歐洲現代詞語,又被重新引入現代漢語。
“文明”(civilization),指人類社會脱離野蠻的進步狀態。經過啓蒙運動的洗禮,“文明”被賦予社會進步的意涵,一般指人類脱離野蠻狀態而進化的一切物質、制度、精神成就,特指現代文明。德國社會學家埃利亞斯指出,“文明”這一概念涉及完全不同的東西:技術水準、禮儀規範、宗教思想、風俗習慣以及科學知識的發展等。它既可以指居住狀況或男女共同的生活方式,也可以指法律懲處或食品烹飪,幾乎每一件事都是以“文明”或“不文明”的方式進行的。文明“這一概念表現了西方國家的自我意識……它包括了西方社會自認為在最近兩三百年內所取得的一切成就,由於這些成就,他們超越了前人或同時代尚處‘原始’階段的人們”。它表達了“他們的技術水準,他們的禮儀規範,他們的科學知識和世界觀的發展等等”。
“文化”(culture),一般指人類的生活方式、精神活動及成就。16世紀以來,culture從“照料動植物的生長”之義,延伸為“人類發展的歷程”,其意主要指人類的思想、知識、精神、藝術等相關活動,亦在廣義和狹義上指一個民族、羣體或一個時期特殊的生活方式。在英語中,culture經歷了複雜的語義演變。“文化”語義的泛化,使其與“文明”之部分語義趨於重疊。人類學之父、英國人類學家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廣泛的民族學意義來説,乃是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和任何人作為一名社會成員而獲得的能力和習慣的複雜整體。”泰勒所謂的“文化”,是可以與“文明”互換的同義詞,包含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
19世紀法國歷史學家基佐在其《歐洲文明史》中以啓蒙的歷史觀闡釋“文明”概念:文明是人類普遍的人性與社會的發展,它是一種普遍的人類命運,是一切其他事實的歸宿和總結。“發展的概念是這個詞所包含的基本概念。”“文明由兩大事實組成:人類社會的發展及人自身的發展。一方面是政治和社會發展,另一方面是人內在的和道德的發展。”基佐的進步論文明史觀建基於普遍的人本的單數文明概念,這是啓蒙時代以來英法語境中主流的文明概念。另一方面,基佐的“文明”還是一個複數形式的概念,“歐洲文明”本身是一個具有地域性的歷史概念,它是歐洲各民族文明的集合體,經歷了由“古代文明”向“現代文明”的演進,並且因其文明進步而彰顯了不同於其他非歐洲民族文明的特性。法國歷史學家布羅代爾指出,1819年前後,“文明”一詞開始被用作複數形式。其新義是一個時期或一個羣體的集體生活所共有的各種特徵。單數形式的文明概念(一種典型的18世紀的概念),即與進步的信念相關而僅為某些特權民族或特權集團所擁有的文明概念,已逐漸式微。20世紀的文明概念某種程度上已擯棄了關於文明優劣的價值判斷。複數形式的“文明”(civilizations)是中性的描述性概念,其含義相當於泰勒的“文化”概念。
而在德國知識界,則發生了“文化”與“文明”的意識形態戰爭。啓蒙運動以後,英國和法國拜工業革命與民主革命“雙輪革命”之賜,成為現代“文明”進步的典範。19世紀初,德意志思想界則發生了由啓蒙主義向歷史主義的轉變。法國大革命走向恐怖階段後在德意志引起了巨大失望,並導致了對自然法學説的反思。對大革命意識形態的反動在拿破崙統治德意志之後進一步增強。這激發了德意志人的民族情感,並使得公眾思想中啓蒙價值與遭人憎恨的法國文化相等同。1806年,費希特在《對德意志民族的講演》中稱德意志人是一個不同於法國人等其他民族的原初的民族,從而以日耳曼中心的文化民族主義代替了赫爾德具有世界主義傾向的民族觀念。可見,歐洲的所謂“文明”與“文化”之爭,實為德國人對英法現代化優勢的競爭性反應。這與其説是英國人、法國人與德國人的論戰,毋寧説是具有民族悲情的德國人一方的挑戰。英法以“文明”自傲,德國則以“文化”自矜。德國知識分子以文化民族主義的“文化”話語抗衡英法啓蒙主義的“文明”話語,通過反思文化現代性而救正西方的社會現代性,這不僅表徵着德國與英法知識界的思想衝突,而且意味着文化現代性與社會現代性的現代性模式之爭。
“文化”與“文明”的區別性表述可能始於康德:“道德觀念屬於文化範疇”;“而這一思想的流行,只不過造就了那些追求名譽、追求表面的禮儀規範等所謂的德行,只不過推進了文明而已”。日本學者上山安敏則認為,“文化與文明的區別,眾所周知這是從尼采那裏繼承而來的,文化是社會創造活動時期,文明是理論的精密和物質的享受的時代,田園的靈魂和都市的智能分別與之相對應”。
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在《共同體與社會》中,將歐洲“文化”在現代衰變為“文明”,歸結為人類由“共同體”而向“社會”變遷的結果。他指出,共同體時代以家庭生活和家庭經濟為特色,社會時代則以商業和大城市生活為特色。大城市和社會的狀態從本質上説是人民的毀滅和死亡。“既然整個文化已經變成了社會的和國家的文明,那麼,在這種與之相似的形態下,文化本身也在走向沒落,除非它的分散的胚胎仍然具有生命力,除非共同體本質和思想重新得到滋養,並且在行將滅亡的文化之內悄悄地發展着新的文化。”滕尼斯並不否定和拒絕進步、啓蒙運動、自由和文明的價值,他也不贊同浪漫派用詩來美化過去的觀點,但他理解和讚賞這些幻想:由基督教和古代滋養的、主要是北歐的“文化”,越是不能反思到它的社會的基礎即共同體的基礎,在它的輝煌的、更為青春勃發的“文明”形態下,就將越發迅速而徹底地消耗殆盡。它越是過渡到離不開國家的中央調節的社會里,就越發迅速而徹底地筋疲力盡。滕氏對“文明”的批判,開啓了德國思想界揚北歐“文化”、抑西歐“文明”的思潮。
1918年,德國歷史學家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汲取尼采的懷疑精神,創立了其文化形態史學的歷史哲學。其“宿命的哲學”否認歷史的連續進步,把歷史視為一個“前文化”“文化”“文明”演變的過程,並把文明歸為一種文化的邏輯結果。“文明是文化的不可避免的歸宿……文明是一種發展了的人類所能作到的最表面和最人為的狀態。”從“文化”到“文明”的過渡,是羅馬人繼承希臘人的秘密。“希臘的心靈——羅馬的才智;這一對照就是文化與文明的區別素。”質言之,希臘“文化”是主人的、精神的、藝術的,而羅馬“文明”則是僕從的、實用的、非藝術的。在現代西方世界,“帝國主義就是沒有摻假的文明……文化人類的精力是向內的,文明人類的精力是向外的”。斯氏發展了滕尼斯揚“文化”抑“文明”的觀念。美國歷史學家伊格爾斯指出,從啓蒙的進步觀念到斯賓格勒的“在劫難逃”觀念的轉變,生活和思想在無可抗拒地走向科學化和技術化,只不過被孔多塞認為在人類解放中是絕對積極因素的理性和啓蒙,如今越來越成為對人文價值的威脅,在斯賓格勒看來,它們正好是生命和精神的反題。對於成千上萬處於困惑時代的有教養的德國中產階級來説,斯賓格勒的著作成了靈感的來源。
德國社會學家阿爾弗雷德·韋伯則進一步賦予這對概念以德國“文化”對抗英法“文明”的意識形態戰爭色彩。他指出:所謂文明,是指理智和實用的知識及控制自然的技術手段;所謂文化,則包含了規範原則和理念的諸種價值結構,是一種獨特的歷史存在和意識結構。現代社會的根本特徵不是永恆的穩定與單純的進步,而是穩定與危機、進步與倒退的辯證。現代性危機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文明壓倒了文化,人在物質文明的大潮中徹底喪失了作為類存在的自由本質,而淪為物的奴隸。人類應當揚文化而抑文明,只有表徵人之為人的規定性的文化,才能成就健全的現代人,從而拯救現代社會的危機。在他這裏,“文明”被窄化為理智化和技術化,“文化”則代表着精神性的人文價值。“文明”與“文化”的差異,亦相當於其兄馬克斯·韋伯所謂“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之別。
正如伊格爾斯所指出:“在德國的Kultur(文化)與盎格魯-撒克遜的Zivilisation(文明)之間展開的文化戰爭——那是德國精英們藉以確立他們對於德國民眾的統治權的一套意識形態——中,德國‘1814年觀念’與法國‘1789年觀念’迥然有異。作為西方民主觀念之基礎的啓蒙運動被認為膚淺不堪,它假定了一種抽象的人性和一種以普遍人權為預設的非歷史的倫理。歷史主義或者德國的歷史觀所堅持的是一種它所認為的歷史實在論,也即認定人沒有本性,而只有歷史。”埃利亞斯也強調,“文明”一詞的含義在英法兩國和德國區別極大。在英法,這一概念集中地表現了這兩個民族對於西方國家進步乃至人類進步所起作用的一種驕傲;而在德國,“文明”則是指那些有用的東西,僅指次一等的價值,即那些包括人的外表和生活的表面現象。在德語中,人們用“文化”而不是“文明”來表現自我,來表現那種對自身特點及成就感到的驕傲。㉑以上論述顯示,關於“文明”與“文化”內涵的討論,需要立足於相應的語境。而中國語境中的“文明—文化”論述與德國的思想差異,是一個需要探索而頗具意義的問題。
清末民初思想中的“文明”與“文化”
在中國,“文明”首先是一個現代問題。近代文明觀念的傳播是西學東漸的產物。晚清思想史經歷了一個從“天下”到“文明”的思想過程。傳統的“天下”觀是一種中國中心主義的中華文明觀,其與朝貢體系相伴隨的“華夷意識”,具有一種傲視一切外族的價值優越感。鴉片戰爭以後大清屢敗於西洋的堅船利炮,而深陷亡國滅種的危機之中。洋務派、維新派、新文化派為救亡圖存而向西方尋求富強之道,由器技而制度、倫理,逐漸發現了西洋“文明”的價值,並以文明為中國現代化的核心目標。
嚴復是晚清第一位認識現代文明之意義的啓蒙先知。甲午兵敗,嚴復面對“世變之亟”,痛切地認識到所謂中國禮儀之區而東西南北皆犬羊夷狄的“華夷之辨”的荒謬。他反思洋務運動“中體西用”式改革的失敗而向西方追尋富強的原因,發現了西方“自由為體,民主為用”的現代文明。在致梁啓超的信中,嚴復稱讚梁氏贈寄之《新民叢報》“為亞洲二十世紀文明運會之先聲”,並談及著譯之意義:“夫著譯之業,何一非以播文明思想於國民?”傳播文明思想於國民,是嚴復的啓蒙宗旨。嚴復信奉甑克思“蠻夷社會—宗法社會—國家社會”的社會進化論,以現代“國家”為文明之基本特徵,認為西方已進入國家社會,而中國尚滯留於宗法社會。他將“文明”定義為:“文明者,西人謂之Civilization……案其字乃與City市府或城邑之字,同原於辣丁之Civitas,所謂一邑之眾是已。可知西人所謂文明,無異言其羣之有法度,已成國家,為有官團體之眾。其人之動作云為必與如是之團體社會相宜,懷刑畏法,有敬重國家,扶翼同類之德心,必如此,而後乃稱為文明人也。”嚴復強調,“文明社會”與“初級社會”、文明與非文明的一大普遍差異,在於是否脱離宗法社會。“初級社會,大抵不離家族形質,而文明社會不然。”所謂文明,即由宗法而國家的社會進化。
在嚴復看來,文化的命運取決於文明。近代三百餘年,世界大通,為國家富強之大勢所趨。“通則曏者之禮俗宗教,凡起於一方,而非天下之公理,非人性所大同者,皆岌岌乎有不終日之勢矣……而非天下之公理,非人性所大同,其終去而不留者。”“天下之公理”和“人性所大同”,即具有普遍性的人類文明。各民族文化傳統的存廢,取決於其是否合乎公理與人性之“文明”。
嚴復反對洋務派的“中體西用”,亦反對激進的西化主義,而主張中西文明的融合:“然則今之教育,將盡去吾國之舊,以謀西人之新歟?曰:是又不然……不知是乃經百世聖哲所創垂,累朝變動所淘汰,設其去之,則其民之特性亡,而所謂新者從以不固,獨別擇之功,非曖姝囿習者之所能任耳。必將闊視遠想,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而後得之,其為事之難如此。”嚴復對護存文化傳統和民族特性的關切,揭示了文明變革中的文化認同問題。
另一位論述相關問題的重要人物是維新派領袖梁啓超。梁啓超戊戌以後流亡東瀛,受福澤諭吉及明治日本文明論思潮之影響,一改其早期重政治改革的“變法”主張,轉而關注文明和精神革命問題,“文明/野蠻”模式成為其思考中國問題的重要思維框架。他在《文野三界之別》中引用西方“蠻野之人”“半開之人”“文明之人”的文明等級論,並比附以“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之春秋三世説,將其歸為世界人民所公認的進化公理。梁啓超受福澤諭吉文明論的啓發,主張中國的文明化宜從精神入手。他在《國民十大元氣論》中主張:“今所稱識時務之俊傑,孰不曰泰西者文明之國也。欲進吾國,使與泰西各國相等,必先求進吾國之文明,使與泰西文明相等。此言誠當矣。雖然,文明者,有形質焉,有精神焉。求形質之文明易,求精神之文明難。精神既具,則形質自生。精神不存,則形質無附。然則真文明者,只有精神而已。”他強調:“求文明而從形質入,如行死港,處處遇窒礙,而更無他路可以別通,其勢必不能達其目的,至盡棄其前功而後已。求文明而從精神入,如導大川,一清其源,則千里直瀉,沛然莫之能御也。”
嚴復和梁啓超追慕的“文明”以英國為典範,體現出晚清啓蒙思潮具有濃厚的崇英色彩。而五四新文化領袖陳獨秀則熱烈地追求法蘭西文明。他在《青年雜誌》創刊號發表《法蘭西人與近世文明》,並翻譯賽諾伯的《現代文明史》第三章。陳獨秀指出:“文明雲者,異於矇昧未開化者之稱也……可稱曰‘近世文明’者,乃歐羅巴人之所獨有,即西洋文明也……而其先發主動者率為法蘭西人。”他強調,近代文明之三大精華是人權説、生物進化論和社會主義。“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蘭西人之賜。世界而無法蘭西,今日之黑暗不識仍居何等。”
在陳獨秀這一時期的《吾人最後之覺悟》中,“文明”與“文化”兩詞通用:“歐洲輸入之文化,與吾華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數百年來,吾國擾攘不安之象,其由此兩種文化相接觸相沖突者,蓋十居八九。凡經一次衝突,國民即受一次覺悟。”“自西洋文明輸入吾國,最初促吾人之覺悟者為學術,相形見絀,舉國所知矣;其次為政治,年來政象所證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殘之勢。繼今以往,國人所懷疑莫決者,當為倫理問題。”陳氏所用的廣義“文化”概念與“文明”相通,包含技術、政治、倫理等維度。五四運動以後,“新文化運動”一語開始流行,此時陳獨秀才開始改用狹義的文化概念,即“文化”特指精神活動。

關於清末民初“文明”與“文化”的概念運用,還可以魯迅、杜亞泉為例。魯迅留學東瀛時深受明治日本尼采熱的影響,對19世紀文明持批判態度。其《文化偏至論》中,“文明”與“文化”是兩個通用互換的概念:“意者文化常進於幽深,人心不安於固定,二十世紀之文明,當必沉邃莊嚴,至與十九世紀之文明異趣。”“第不知彼所謂文明者,將已立準則,慎施去取,指善美而可行諸中國之文明乎,抑成事舊章,鹹棄捐不顧,獨指西方文化而為言乎?物質也,眾數也,十九世紀末葉文明之一面或在茲,而論者不以為有當。蓋今所成就,無一不繩前時之遺蹟,則文明必日有其遷流,又或抗往代之大潮,則文明亦不能無偏至。”魯迅以19世紀西方文明之“物質”與“眾數”為“文化偏至”,其所謂“文化偏至”,亦即“文明偏至”。
杜亞泉論中西文明,既取“進步”的單數文明概念之義,又取中性的複數文明概念之義。他把文明歸為社會演化的趨勢,“社會大勢,既已日趨於文明,斷難強之復安於簡陋”。“吾國文明,尚在幼稚,而都市生活之趨勢,已露端倪。”他反對西化主義,而堅持中西調和的文明觀。文明有其普遍性與特殊性,“故吾人現今所宜致力者,當採世界文明之所同,而去其一二端之所獨,復以吾國性之所獨,融合乎世界之所同,毋徒持此模仿襲取者,慊然自足,誇耀其文明之進步也”。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引起杜亞泉對現代西方文明的深刻反思。他反對線性進步的文明觀,認為“西洋文明與吾國固有之文明,乃性質之異,而非程度之差;而吾國固有之文明,正足以救西洋文明之弊,濟西洋文明之窮者”。“至於今日,兩社會之交通,日益繁盛,兩文明互相接近,故抱合調和,為勢所必至。”在杜亞泉看來,文明以經濟與道德發達為目的。“於人類生活有最重要之關係者,一曰經濟,二曰道德……故既富加教,實為人類保持生活之大綱。文明之定義,本為生活之總稱,即合社會之經濟狀態與道德狀態而言之。經濟道德俱發達者為文明,經濟道德俱低劣者為不文明;經濟道德雖已發達,而現時有衰頹腐敗之象,或有破壞危險之憂者,皆為文明之病變……今日東西洋文明,皆現一種病的狀態,而缺點之補足,病處之治療,乃人類協同之事業。”杜亞泉的“東西文明”屬於中性的複數文明概念,而其“經濟道德俱發達者為文明”則承襲了基佐、福澤諭吉的進步文明概念,但並不以西方為文明典範。
五四以後的“文明”話語與“文化”話語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梁啓超從西方現代文明的廢墟上回望中國傳統,發生了深刻的思想轉變。他在《歐遊心影錄》中反思現代性的缺弊和民族主義的偏狹,轉而倡言世界主義和“中國人對於世界文明之大責任”。他主張“拿西洋的文明來擴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補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來成一種新文明”,“把自己的文化綜合起來,還拿別人的補助他,叫他起一種化合作用,成了一個新文化系統”。從《新民説》到《歐遊心影錄》,梁啓超的思想發生了從追尋現代文明的政治民族主義到反思現代性之文化民族主義的深刻轉變,但他並沒有擯棄啓蒙理想,其具有世界主義傾向的文化民族主義以調和中西的新文明為目標。不同於德國式以“文化”抗衡“文明”的反啓蒙的文化民族主義,梁氏所謂“文化”仍是“文明”的同義詞,並沒有揚“文化”而抑“文明”。
“五四”以後,中國思想界加速分化,“文明”與“文化”話語也由此呈現出新的特點。這一時期,激進派轉向馬克思主義,保守派則興起了一股“西方物質文明、東方精神文明”的思潮。“歐戰”暴露的西方文明的危機,使保守派對西方文明的崇信動搖,退回到洋務派“中體西用”的文化保守立場。康有為在民初鼓吹“物質救國論”和孔教運動,梁啓超在《歐遊心影錄》中批判西方科學主義與物質文明破產,張君勱在《人生觀》中為科學與人生觀劃界並讚譽宋明理學的精神價值。這種“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二元論,批評西方文明之物質與精神的衝突,強調“精神文明”高於“物質文明”,不乏反思“文明”和現代性批判的意涵。但以此心物二元論評判中西文明,“西方物質文明”與“中國精神文明”二分,導致中體西用論之反現代的保守傾向老調重彈。

這種保守的文明二元論引來胡適的批評:“今日最沒有根據而又最有毒害的妖言是譏貶西洋文明為唯物的(Materialistic),而尊崇東方文明為精神的(Spiritual)。這本是很老的見解,在今日卻有新興的氣象。從前東方民族受了西洋民族的壓迫,往往用這種見解來解嘲,來安慰自己。近幾年來,歐洲大戰的影響使一部分的西洋人對於近世科學的文化起一種厭倦的反感,所以我們時時聽見西洋學者有崇拜東方的精神文明的議論。這種議論,本來只是一時的病態的心理,卻正投合東方民族的誇大狂;東方的舊勢力就因此增加了不少的氣焰。”胡適反對“中國精神文明、西方物質文明”的二元論,堅持文明整體論,強調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不可分割,西方文明整體上優於中國文明。
胡適本人對“文明”與“文化”的定義雖有分殊,卻常將兩詞作近義詞使用。他在《我們對於西洋近代文明的態度》中指出:“第一,文明(Civilization)是一個民族應付他的環境的總成績。第二,文化(Culture)是一種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第三,凡一種文明的造成,必有兩個因子:一是物質的(Material),包括種種自然界的勢力與質料;一是精神的(Spiritual),包括一個民族的聰明才智、感情和理想。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運用自然界的質與力的作品;沒有一種文明是精神的,也沒有一種文明單是物質的。”認為文化是生活方式,屬於廣義的大文化概念,其意與“文明”相近。胡適1933年在芝加哥大學的英文演講《中國的文藝復興》,以中國文化之調整為主題。“中國的問題,無論初看起來怎樣錯綜複雜,其本質是文化(cultural)衝突與文化重新調整的問題,即在下述情形中如何造成一個令人滿意的文化調整的問題:一個古老的文明(civilization)已被強制性地納入了與西方新文明的經常而密切的接觸之中,而這一古老文明已明白顯示出它完全無力解決民族生存、經濟壓力、社會與政治的無序,以及思想界的混亂等緊迫問題。”在胡適這裏,“文化”與“文明”的意涵並無大的差異。
梁漱溟在1922年出版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對“文明”與“文化”作了説明:“文化與文明有別。所謂文明是我們在生活中的成績品——譬如中國所製造的器皿和中國的政治制度等都是中國文明的一部分。生活中呆實的製作品算是文明,生活上抽象的樣法是文化。不過文化與文明也可以説是一個東西的兩方面,如一種政治制度亦可説是一民族的製作品——文明,亦可以説一民族生活的樣法,——文化。”他強調:“文明的不同就是成績品的不同,而成績品之不同則由其用力之所在不同,換言之就是某一民族對於某方面成功的多少不同;至於文化的不同純乎是抽象樣法的,進一步説就是生活中解決問題方法之不同。”梁氏之文明與文化概念,與胡適相近,接近泰勒的文化概念。文明由文化(人生態度)決定。文明與文化是同一事物的兩面,生活的成就是文明,生活的樣法是文化。他將征服自然、科學、民主歸為西方文化的三大特色,這種大文化概念與“文明”意涵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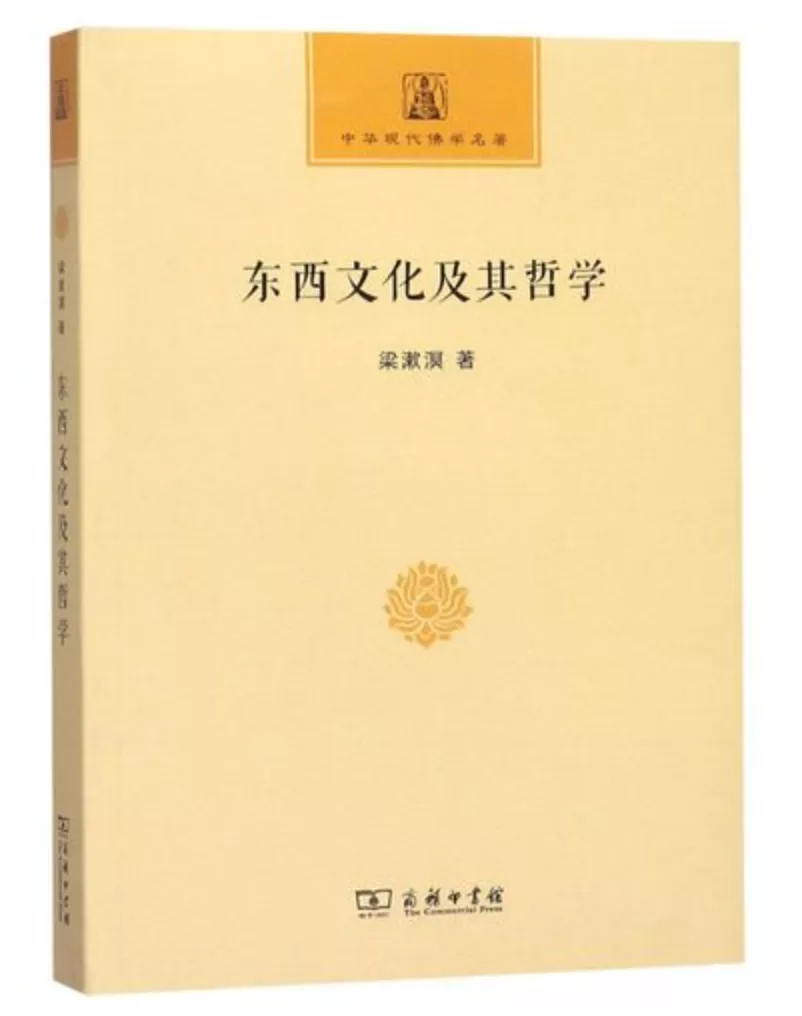
以留美學人為主的學衡派,對“文明”與“文化”語義之別亦並不介意。宗奉白璧德人文主義的吳宓在批評新文化運動時,經常“文明”與“文化”兩詞混用:“蓋吾國言新學者,於西洋文明之精要,鮮有貫通而徹悟者。苟虛心多讀書籍,深入幽探,則知西洋真正之文化與吾國之國粹,實多互相發明、互相裨益之處,甚可兼蓄並收,相得益彰。”關於新文化運動,吳宓指出:“今新文化運動,自譯其名為New Culture Movement,是以文化為Culture也。Matthew Arnold所作定義曰:文化者,古今思想言論之最精美者也……按此,則今欲造成中國之新文化,自當兼取中西文明之精華,而熔鑄之,貫通之……孔教、佛教、希臘羅馬之文章哲學及耶教之真義,首當着重研究,方為正道。”吳宓強調,“文化”二字其義渺茫而難以確定,有廣義狹義之分。這種與“文明”通用的“文化”,可能取自阿諾德狹義的精神性文化的概念。
抗戰時期著“貞元六書”的哲學家馮友蘭,倡言“新理學”,呼喚中國“舊邦新命”之文化復興。他強調,對西方的評判要分層次,區分“文明人”與“野蠻國”,文明是天然狀態的改變,與野蠻相對立。關於五四新文化運動,馮氏指出,民初人之談西洋文化者不明層次,“這班人高談西洋人之‘精神文明’……西洋人或者講自由,平等,博愛,或者有俠義精神,或者富於同情心。但西洋底國,則決不是這樣底……實則是國對於國之關係,尚在所謂天然狀態之中”。“在現在底世界中,人是文明底,而國是野蠻底。野蠻底國卻是文明底人所組織者。”馮氏認為,文化有其類型。“現在世界是工業化的世界。現世界的文明是工業文明。中國民族欲得自由平等,非工業化不可”,“我們中國文明,原來是農業文明”。“所謂西洋文化是代表工業文化之類型的,則其中分子,凡與工業文化有關者,都是相干的,其餘,都是不相干的。如果我們要學,則所要學者是工業化,不是西洋化。”馮友蘭的文明觀揭示了西方之文明與野蠻的“兩面神”。他以文明類型論區分西方文明與“現代文明”,強調西方文明是一種建基於工業化的“工業文明”類型,其與工業化無涉的因子並不具有普遍性。因而現代化是工業化,而不是西方化。這裏馮友蘭也並沒有區分“文明”與“文化”、“工業文明”與“工業文化”的概念。他以“工業文明”“現代化”等概念立論的文化類型論,在“全盤西化”與“本位文化”的論戰中獨樹一幟。
通過以上案例,可以看到,“五四”後中國思想領域並不是單純地經歷了一個從“文明論述”到“文化論述”的轉折。“文明”與“文化”兩種話語,在思想者的論述中出現了明顯的互滲與結合。
斯賓格勒與德國文化思想在中國
那麼,前述西方思想界的“文明”與“文化”之辨,是否在中國引起了迴響呢?耐人尋味的是,兩度留學德國的新儒家張君勱,似乎並未注意德國思想界的這一問題。在題為《歐洲文化之危機及中國新文化之趨向》的演講中,他也是“文化”與“文明”並用:“歐洲文化上已起一種危機是也。諸君在上海所見,租界秩序何等整齊!外人聲勢何等浩大!電燈何等光明!文明利器何等便人!何以歐洲人對於其文明起了反動?何以有所謂危機?”在《明日之中國文化》中,張君勱將“文明”與“文化”二詞混用,甚至以“文化”譯civilization:“我們翻閲現代歐美出版之書籍目錄,時常會看到一種新穎的書籍名稱,如《文化在試練中》(Civilization on Trial)……如《我們創化中的文化》(Our Emergent Civilization)。”“歐戰”告終,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宣告了歐洲文明的危機,其時張君勱正隨梁啓超遊歷戰後歐洲。但他在介紹斯氏西方文明危機論時,並沒有提及其揚“文化”抑“文明”的觀念:“斯本格勒的《歐洲之衰亡》,此書於第一次大戰後出版,轟動一時,後來有英譯本,名曰《西方的沒落》(Decline of the West),因其書名引人注意,而且把歐洲人崇拜的西方文化的沒落,用預言家的態度説出,更使人們觸目驚心……他看文化的立足點,就是將文化視同草木,有春夏秋冬四季的嬗遞變化:春天是含苞發芽之時,夏天是發展成長之時,秋天是成熟收穫之時,到了冬天,非沒落衰亡不可。”湯因比深受斯賓格勒影響的文化興衰論,亦頗受張君勱青睞。儘管如此,他並沒有強調斯湯二氏之揚“文化”抑“文明”的觀點。這可能是因為,作為一個政治上追求民主憲政的自由主義者,張君勱自然不會否定以英法為典範的“文明”的價值。張君勱思想中的自由主義底色,抵禦了德國浪漫主義和文化民族主義的反啓蒙觀點。張氏的“文化”概念是一箇中性的描述性的歷史概念,是與“文明”相通的包含物質、精神、制度的廣義文化概念。“文化為物,發之自內,由精神上之要求,見之於制度文章。”“文化有總根源,有條理,此後不可籠籠統統説西洋文化、東洋文化,應將西洋文化在物質上、精神上應採取者,一一列舉出來,中國文化上應保存者,亦一一列舉出來。”這種與“文明”同義的大文化概念,是當時中國知識界的一種普遍認識。
再如,留法學者李思純信奉斯賓格勒文化形態史學,但他亦並未區分“文明”與“文化”。他反對文化直線進化説,亦反對文化循環論,而倡言斯氏的文化興衰論。耐人尋味的是,他對基佐的進步論文明史觀與斯賓格勒反啓蒙的文化形態史學皆持文化興衰論的理解:“法國史家基梭(Ferancois Guizot,1787—1874)著《歐洲文明史》(Histoire de la civilization Europeenne),其書綜觀歐洲文化之發育滋長,實互相倚伏,互相影響。已滅之文化,偶遺蹟於將來而生新精神,將衰之文化,亦偶影響於他方而茁新事物,其轉徙承襲,不能外於生住異滅之理焉。”顯然,李氏將“文明”與“文化”視為同義詞。其文化興衰論源於斯賓格勒:“論文化之盛極必衰,衰極必亡,而持論最有力者,有德國現代哲學家斯賓格勒氏(Spingler)。斯氏有感於歐洲文化之趨於死途,常冥思默想而成一書曰《西土沉淪論》(Undergang der Abend land)。其書體大思精,證例繁富,歷引希臘羅馬及東方古國先代文明其發生滋長及衰敗滅亡之曩例,更輔以歷史學、社會學、生物學之觀察,最後斷定歐洲文化之現已趨於死亡……其書所論文化之生住異滅,信為確義。”這裏,李氏接受了斯賓格勒的文化興衰論,但並未襲取其批判英法自由主義而揚“文化”抑“文明”的德國式文化理論。作為巴黎大學畢業生,李思純的觀點亦反映了法德兩國之文明觀及思想語境的差異。
留法學人張申府也認為,無論在英法還是在德國,“文明”與“文化”的語義都是相近的。“英法人談這問題的,常常把civilization與culture兩字混而用之。”“本來,英法是以‘文明’自驕,而德是以‘文化’自異的。但現在,在兩方研究這個問題的,彼此所謂,外舉大體已經一致……德之kultur與英法之culture雖源同形類,但今後若相翻,則Civilization與kultur更相當。《牛津袖珍字典》中注kultur,謂為德國人所見之civilization,可謂甚是。”張申府指出:“‘文明’與‘文化’在中國雖都是新名詞(至少新意義),自也象在日本一樣,‘文明’要比‘文化’舊得多。‘文明’兩字久已入了普通話,即如‘文明新戲’‘文明大鼓’,‘很文明的’‘文明棍’之類。就這些常言道,似乎以‘文明’為culture之譯語,也沒有什麼不妥當。”“所以我意‘文明’與‘文化’,在中國文字語言中,只可看成差不多與‘算學’與‘數學’一樣,只是一物事之二名,或一學名一俗名。不必強為之區異。或則頂多説,文化是活動,文明是結果。”
社會學家吳景超(芝加哥大學社會學博士)則是當時少數知曉和關注A.韋伯的德國式文化觀的學者。他同意文化具有世界性與國別性,並引用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主任麥其維的觀點強調:含有世界性之文化為“文明”(Civilization),而含有國別性之文化為“文化”(Culture)。文化與文明的分別,即文明是“發明”出來的,而文化是“創造”出來的。發明的東西可以從一個民族傳播到另一個民族,而不失其特性;可以從這一代傳到那一代,而依然保存其用途。凡自然科學及物質的工具等,都屬於文明。而文化則是創造的,其為一個地方一個時代民族性的表現,只有在一定的時間與空間內才能保存其原有的意義。凡宗教、哲學、藝術等,都屬於文化。如美國“發明”的電燈即為“文明”之一種,其已傳播全球。但美國所“創造”的教育系統,只有在美國的環境中才可以發生作用。可見,全盤西化的理論是不能成立的。因此,在20世紀30年代“全盤西化”與“本位文化”的論戰中,吳景超主張文化折中:“我們在建設的過程中,不但要保存中國的優美文化,及採納西洋的優美文化,有時還要創造一種新的文化,來適應新的環境,或滿足新的要求。”
轉折還是“復調”:重思“五四”後思想中的“文明”與“文化”
通過上述分析,對於中國近代思潮中“文明”與“文化”問題,可以獲得新的認識。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在近代中國思想史上發掘了一個意義深刻的新的問題域。
在思想史上,“文化”與“文明”的對立是德國近代思想的獨特問題。其源於德國知識分子對普遍主義的、擴張性的法國文明的抵抗和對民族文化的深刻認同。外族侵凌、小邦林立、政治專制、經濟落後,構成了近代德意志的特殊歷史語境。18世紀法國啓蒙運動所推動的理性主義、普遍主義的現代“文明”,遭到德國哲學家赫爾德崇尚民族、歷史、文化之特殊性的浪漫主義的抵抗。在19世紀,這種德國啓蒙傳統被費希特反對拿破崙侵略的、以“文化”凝聚德意志的民族主義所強化。而隨着普法戰爭中普魯士戰勝法國和德意志帝國的崛起,民族主義成為統一德國的主流意識形態。在思想界,尼采反理性、反民主的權力意志哲學,開啓了德國反現代性的批判思潮。從費希特到滕尼斯、斯賓格勒,以德國“文化”反抗法國“文明”的思潮,是以反侵略的文化民族主義和反啓蒙運動的非理性主義批判思潮為思想背景的。這一德國特有的“文化”概念,雜糅了近代德國的民族主義、歷史主義、浪漫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等思潮。
而由於中德歷史語境的不同,中國思想界接受了“文化”概念的精神傳統及“認同”之義,但並未受到反現代的德國文化主義思潮顯著影響。中國雖然具有與德國相似的受欺凌的後發展國家的歷史語境,但包括德國派學人張君勱在內的中國知識人,並沒有被捲入這場德國“文化”反抗英法“文明”的意識形態戰爭,追尋文明與現代化仍是中國現代思想的核心主題。論及西學對中國思想界的影響,英法文明觀遠大於德國文化觀,中國文化民族主義亦未全面走向德國式的反啓蒙和反現代的保守思想。如果説德國思想的“文化—文明”之辨與洋務派的“體—用”之辨、“道—器”之辨異曲同工,“五四”後的文化民族主義則與晚清的“中體西用”論不可同日而語。無論是晚年梁啓超,還是新儒家梁漱溟、張君勱、牟宗三等,皆肯定現代民主政治,儘管同時他們對西方現代性有着深入的反思批判。正如亨廷頓所指出,19世紀德國思想家對“文明”與“文化”的區分從未被德國以外的思想界接受。
中國知識人對於中國文化復興的“文化的自覺”,並非始於“五四”。辛亥革命後,儒教隨帝制崩潰而解紐,新生的民國陷入空前的秩序危機與意義危機。晚清維新派鉅子憂慮中國文化的命運,紛紛轉向文化保守主義。康有為鼓吹“國魂”併發起孔教運動,梁啓超1912年發表《國性論》而倡言中華特性,嚴復1913年發表《思古談》《讀經當積極提倡》,大力推崇“國性”。民初形成了一股守護“國性”之文化認同的保守思潮。1918年梁濟在遺書《敬告世人書》中沉痛警告:國性不存,國將不國。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杜亞泉反思西方社會進化論和物質主義之流弊,並倡言“精神救國論”與東西文明之調和。這些都表徵着中國知識分子護存本土文化價值的“文化的自覺”。而論及對西方現代性的反思,早在20世紀初,魯迅就在《文化偏至論》中對西方現代性之“物質”和“眾數”有着深刻的批判。因而,中國思想界的“文化的自覺”並非始於梁啓超的《歐遊心影錄》,而是更早。而梁著獨特的思想史意義,在於一個啓蒙先知對西方現代性的反思和對中國文化價值的迴歸。一個曾經熱烈追慕西方現代文明的晚清維新領袖,在“歐戰”後迴歸中國文化的懷抱,這表徵着晚清以降西化思潮的衰落。“歐戰”以後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危機畢現,追慕歐化的知識界開始反思西方現代性的缺弊,並重新審視被蔑棄的中國文化傳統的價值,五四激進反傳統主義思潮盛極而衰,原本被歐化思潮所淹沒的護持中國傳統的文化民族主義思潮逐漸浮現。復興中華文化的“文化的自覺”與“文化”話語的流行,成為五四後新的思想文化景觀。
而由前文論述可知,在近代中國觀念史上,五四以後“文化”話語的興起並沒有取代近代主流思潮中的“文明”話語。作為一種“和制漢語”,“文化”在日本和中國本來是一個比“文明”晚出的概念。“文化”話語流行後,中國知識人大多對“文明”與“文化”二詞不加區分、混而用之,甚至熟稔德國思想的張君勱亦然。從概念到語義層面,“文化”都沒有代替“文明”,二者仍是同義詞或近義詞。與其説五四後“文化”話語取代“文明”話語而流行,毋寧説兩種話語呈現出語義互滲交融的趨勢。“文明”話語與“文化”話語的融合,同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現代文明與中國文化的融合趨勢一致。
五四以後,知識界的“文明”話語經歷了深刻的語義演變:其一,摒棄了西方中心論意識形態的單數文明概念(“文明”=“西方”),代之以中性的描述性的複數文明概念(“中國文明”與“西方文明”)。其二,認識到西方文明的現代性在於工業化,“現代文明”是“工業文明”,而不等於“西方文明”。其三,“文明”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並非西方的特權。“文明”與“野蠻”並不是西方文明與非西方文明的本質,而西方亦是一個文明與野蠻的“兩面神”(文明人與野蠻國)。這種兼具單數文明與複數文明、時代性與民族性認識的“文明”概念,表徵着中國人之文明觀的深刻變遷。
因此,在五四以後的現代中國思想圖景中,“文明”與“文化”並非消長更替,而是並行不悖、相互交融,它凸顯了中國現代化範疇內現代文明進步與中國文化復興的兩大主題。馮友蘭之“舊邦新命”“現代化不是西方化”的文明論,賀麟以新文化運動為儒學復興之契機的文化論,皆以中國的文明進步與文化復興為目標,表徵着現代中國思想家高度的“文明自覺”與“文化自覺”。中國的現代化是現代文明進步與中國文化復興的統一。清末民初,“文明”的追尋是中國近代思想的主旋律。五四以後知識界“文化”主題的浮現,形成了思想史上“文明”與“文化”的雙重變奏。如果説清末民初中國新思潮猶如一曲“文明”變革的主調,那麼,五四以後,隨着“文化”認同思潮的興起,“文明”的主調演變為“文明—文化”的復調,從而形成一曲“變革”與“認同”的協奏曲。而在這曲“文明”與“文化”的復調中,“文明”仍是第一主題,是中國“文化”轉型的方向,亦為中國現代化的總目標。
21世紀,轉型期的中國迎來了文明進步與文化復興的時代。梁治平指出,文明話語的興起是近年來國際政治中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也是中國思想理論方面最值得注意的一種發展。當代中國的文明話語分為兩種類型,即“大寫的文明論”與“複數的文明論”,這兩種文明論各有其合理功用:“複數的文明論”強調文明的多樣性、共生性和平等性,對內有助於凝聚認同,對外有利於溝通對話;“大寫的文明論”具有超越性、會通性和批判性,有利於文明的開放與提升。而所謂多樣性的“複數文明”,亦即近代思想史中常見的“文化”概念。當代中國思潮中“單數文明論”與“複數文明論”的辯證互補,延續了近代中國思想之文明進步與文化復興的雙重主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