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綜十八年,哇唧唧哇最初的夢想和最後的抵達_風聞
娱乐硬糖-娱乐硬糖官方账号-2021-10-17 07:33

作者|李春暉
2004年,直到《超級女聲》季軍張含韻將“酸酸甜甜就是我”唱到洗腦,很多人才剛醒過味兒來:這檔接受“任何喜歡唱歌的女性”報名的節目,將開啓一個全新的娛樂時代。這直接導致了2005年“超女”空前絕後的盛況,至今被反覆拿來回味。
但當2021年10月16日,《明日創作計劃》的“四強”站上舞台,他們大概率應該已不會想到“草根逆襲”這些18年前素人音綜的經典敍事。18年,已夠一個初生兒長到成年,一切已成約定俗成之物,彷彿一直就在那裏。

當年的超女都已作為“姐姐”回爐,舞台的主角從80後轉眼就到了00後,台下的我們不管是厚古薄今還是興嘆變遷,素人選拔型音綜仍然是時代情緒最不會説謊的鏡子。而在另一些人眼裏,這中間的變與不變更加鮮明,並與他們自己的人生交織。
從2004年成立的天娛,到2017年成立的哇唧唧哇,有一些人貫穿始終。比如哇唧唧哇聯合創始人,原天娛傳媒副總裁、2009年“快女”總導演馬昊;從“11快女”“13快男”一直跟到了“明日5”的視覺導演劉子夏;在《燃燒吧少年》後又連做了五季“明日”的音樂導演陳詩、內容策劃導演李嶽成……

馬昊
“變化越來越快。1983年跟1985年的人差不太多,但現在你會發現2000年和2002年的人很不一樣,因為互聯網的速度迭代得更快。但相同的是對音樂的熱愛,他們需要音樂,也相信音樂。所以你永遠能找到那個他。”馬昊説。為了適應這種迅速的變化,哇唧原有的節目板塊今年升級為哇唧製作,除了眾所周知的“明日”系列,更多不同形式的節目已經出現在他們的日程上。
就像是一場夢,醒了很久還是很感動。從那一年到這一年,素人登上舞台,一個每個人可以平等做夢的舞台,如今還存在嗎?
去到現場
2005年的夏天是屬於“超女”的。五個賽區,十五萬人報名,媒體爭相報道各地排隊報名的盛景。人們彷彿一夜之間被告知還可以有個“明星夢”,不少人可以説出身邊人報名參賽的故事,或者自己就許下過這樣的宏願。
當年的超女快男海選視頻,是硬糖君至今最愛的音綜環節。爆笑,又有點感動。後來不許大搞公開海選了,絕對是此類節目最大的遺憾。
馬昊很早就投入到海選工作裏。第一次見07“快男”陳楚生,是後來《我是歌手》的洪濤在酒吧裏聽到陳楚生唱歌后向馬昊舉薦的。馬昊並沒有覺得很吸引,“整個人看起來很疲憊”。但當他坐下來開始彈吉他開始唱,“我的心馬上被他抓住了”。
《明日創作計劃》的“四強”莊主恆剛走進面試間的時候,馬昊再次忍不住想,“趕緊走”。其貌不揚,又害羞到話也講不清楚,“這怎麼上電視”。但當他拿起吉他唱自己寫的《海海》,馬昊立刻明白,“他心中有詩”。

不是為了故事性非要欲揚先抑,回想下當年海選視頻裏的李宇春、張靚穎,我們仍不免感慨這中間神奇的化學反應。
美食紀錄片喜歡錶現真正的大廚如何去山野裏尋找最佳食材,其實對於內容公司也是一樣。**不同於市面上多數同類節目都在使用選角公司,從天娛到哇唧唧哇,從“快男”“快女”到“燃少”再到“明日”系列,哇唧哇唧製作都是導演組自己選角,**公司建立了一套覆蓋18歲以上年輕人的選角渠道。
去當地見本人是必須的。畢竟現在的技術鬼斧神工,別説美顏、連視頻都可以修。每個選手都要被拍出一套“證件照”級別的錄影,打光、角度,皆有統一標準。
他們在民間還有自己的“線人”。哇唧在各個學校建立了特派員制度,那些喜歡音樂、喜歡“明日”系列的少年人成為了深入每所中學、大學的選角志願者。自己畢業了,又推薦學弟學妹來繼續這項選角事業。
因此,如果説當年《超女》類似於一種時代的媒介賦權,《明日創作計劃》則是讓現在的年輕人獲得更大的主體性。

一個相當值得玩味的現象,相較於傳統的成團節目,原創音樂節目裏的選手,地方性越來越突出,素人素得可怕,也素得可愛。
在參加《明日創作計劃》之前,蔣先貴從未離開過六盤水。我們都學過一個詞叫“夜郎自大”,戰國時期,這裏就是夜郎國地。在2021年城市商業魅力排行榜中,貴州六盤水獲評為“五線城市”。

這曾是一座貧瘠的邊城,又是一個新興的移民城市,五方雜處,異質交融。它還沒有像北上廣那樣被城市文明高度改造和同質化,甚至還保留着90年代“海馬歌舞廳”味兒的歌廳。
但與此同時,這裏的年輕人有互聯網,他們可以看到整個外面的世界。而當一個五彩斑斕的世界是存在於想象中並似乎觸手可及,正是它最迷人的時候。唯有此時,才能寫出“你去找宇宙飛船,我去引開保安”。即便最終是破碎的“可這裏沒有宇宙飛船,所以我們也到不了月亮”。
“小鎮青年”,曾被視為內容產品的重點傾銷對象,卻很容易被忽略他們本身的勃發創造力——尚未被規訓出一條筆直的人生道路,同時又能透過互聯網獲得平等的知識與見識,新工具讓個人獨立創作成為可能。當這樣東西南北的青年齊聚《明日創作計劃》,那些默默生長、野蠻生長的孩子第一次被世界看見。
音綜的破壞性與長期主義
真正成為爆款的音綜、真正被人記住名字的歌手,他們必然帶有一定的破壞性。超出人們的預期,其製作者也不能掌控走勢——所有人都只能去忠實地反映這個時代、這羣少年。
超女快男時代在2005年塑造的第一位樂壇明星李宇春,在當時挑戰了傳統的性別意識並以清新的颱風令萬千觀眾傾倒。而其製造的最後一位音樂明星——“13快男”冠軍華晨宇,則以“火星人”著稱,自我沉浸、如痴如狂,正適應了一羣年輕人的自我意識覺醒。觀念的變化往往是落後於現實的,需要一些標誌性人物與事件,將那些潛滋暗長的情緒以鮮明的形象在大眾意識中確立下來。
2017年開始的“明日”系列,除了“為熱愛音樂的素人提供舞台”這個主旨沒變,每年都在換模式。因為每年年輕人的音樂喜好都在變,時代的脈搏也在變。比如去年的“樂團季”,本來哇唧製作並沒想做樂隊的,但疫情之下一個人太孤獨了,每個選手都説想大家一起玩音樂。於是做了樂隊,節目也就此成就。

而在見到今年這些少年之前,哇唧製作最初的企劃是“民謠季”,摩拳擦掌要“重新定義中國民謠”。但少年們才不準備被定義,也不想去定義誰,他們就是愛音樂,玩音樂,玩各種元素的音樂,如果説有什麼共性,就是普遍愛復古。那得了,再次從善如流,就這樣變成了“創作季”。
“真的就像中醫把脈一樣,你得自己去感受那個東西。我覺得去年做樂隊就是最好的年份,今年做創作就是最好的年份。因為疫情過了第二年的時候,很多人在疫情期間有大量蓬勃的創作,年輕人想發聲了。”馬昊説。
但錄完第一場海選,整個節目組還在找感覺。他們是創作型選手,沒有一上來就能抓人的長相。多數是純素人,自然也沒太多“前情提要”“貴圈親友”可供傳播。“我當時很焦慮,都心悸了。但我一直的習慣就是去一線,既然我不瞭解,我就去問好了。”於是,馬昊讓每個選手都交上來一個PPT,主題就是他們的“審美”——喜歡穿什麼衣服,喜歡看什麼書,喜歡看什麼電影,喜歡聽什麼音樂。
“**你會發現這一輩的小朋友他們會看很老的東西。**他們的書單跟電影單,都是以前的東西。可能在他們的概念裏,那些東西是帶着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去寫或者拍的。他們比我們想象中更具有對社會的思考,看很多文藝的電影、哲學的書。”哇唧製作內容導演李嶽成説,為了跟上選手的步伐,他們會和選手看一樣的電影、一樣的書。而一旦年輕人覺得“原來你懂”,溝通也就建立起來了。
一公的歌曲都是龍丹妮和選手一個一個談定的,其實定歌不是重點,還是在“看人”。從李宇春到華晨宇再到毛不易,亦或是今天的蔣先貴、7Z,在整個行業引入日韓模式流水線化的生產藝人“標準件”之時,哇唧唧哇的藝人長相、外形總是風格迥異,音樂風格更千差萬別。如果有什麼一以貫之的東西,大概就是從龍丹妮到每一位編導都掛在嘴邊的那個詞——獨立人格。
甚至連舞台效果都是圍繞“獨立人格”展開的。視覺導演劉子夏也深知內娛舞台,觀眾更偏愛黑科技和新奇特。但因為“明日”系列的重點始終是“人”,所以並未做太多包裝,而是將整個舞台留給他們本人。“比如蔣先貴,因為他喜歡花,我們就把花放到舞台上;他喜歡穿復古的服裝,他就穿復古的服裝;他喜歡那種復古的氛圍,我們就把燈光、屏幕做成這樣的氛圍,讓他自己去表達就好了。這是“明日”的舞台跟其他舞台不太一樣的地方。”
獨立人格也構成了哇唧系節目和藝人與同行的最大不同——原創的音樂、獨特的面貌、自成一派的言行舉止。或許正因為整個產業流水線統一包裝出太多精製品,才讓哇唧製作更有了獨特的吸引力和競爭力。

但尋找和尊重獨立人格也是一件磨人的事。“明日”某種意義上就像個音樂的“野生動物保護區”,選手宿舍每年都會發生“逃跑事件”。就在接受硬糖採訪的前一天,導演組發現大家都起牀了,只有一個選手還在賴牀。靠近一看,人早跑了,牀上放的是一頂假髮。
“滿世界找了一天,因為封閉創作他也沒有手機,最後在很遠的一個便利店找到了,在那裏想怎麼寫歌呢。”導演組無奈道。好在,他們已經積累了豐富的破案經驗。
黃金時代,回得去嗎
**市場這一輪調整後,如何把秀粉轉化為音樂粉,是擺在所有業內人面前的難題。**在這方面,哇唧唧哇算是有成功經驗的——毛不易絕不是典型的音樂明星,卻是互聯網音綜時代誕生的第一位全民型歌手,並至今保持這一紀錄。

預測素人選拔音綜的冠軍仍然是一件困難的事,即便是對於其締造者來説。2017年的《明日之子》是哇唧唧哇成立後的第一檔節目,很早時,馬昊就興奮的告訴所有人自己找到一個寶貝,就是毛不易,當時節目組都沒人信。
貌不驚人、曾經做過實習護士、上來前兩首歌還頗有諧星風範,當時看不出毛不易的“星相”,不算沒眼光。而所謂“雕琢”,是統一的美輪美奐,還是各自的千奇百怪?哇唧唧哇信奉的是“放大和提純”。
“**我們只做放大和提純,放大他身上的才華,放大他身上的閃光點,然後把他的才華和閃光點去提純,其實哇唧就是在做這件事情。**你把他改造成別人,何必呢?他身上最珍貴的東西就沒了。”馬昊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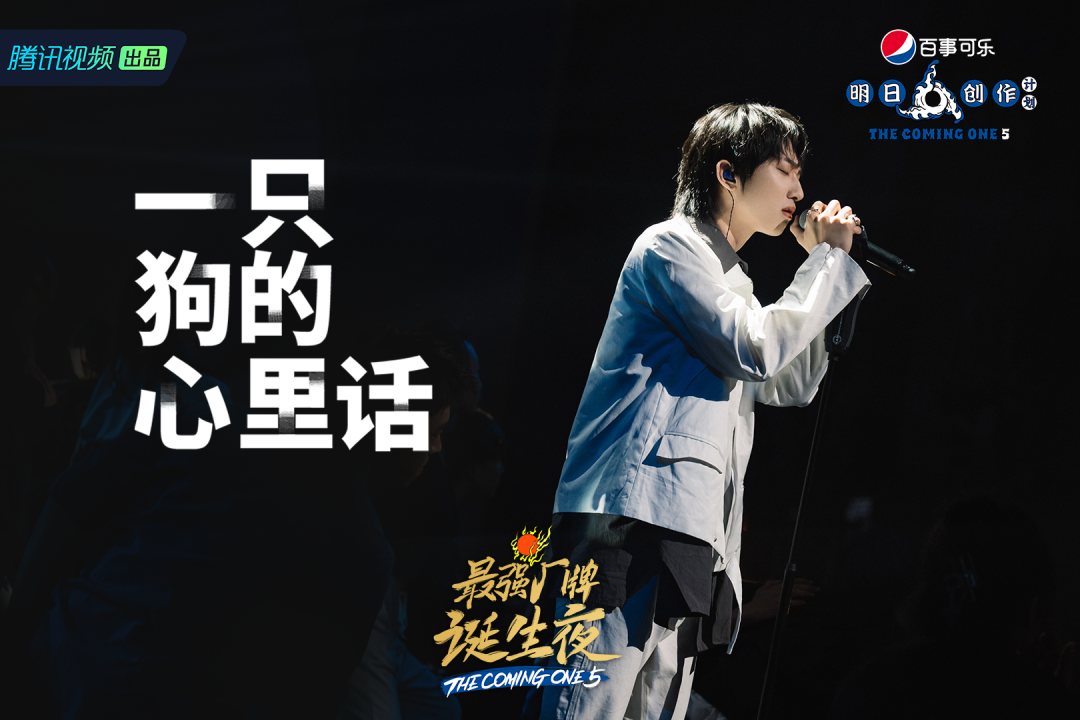
我們懷念音樂或明星的黃金時代,有時其實是在懷念那些“真人”。那些“超女”還能真情實感地扯頭花,明星還敢偶爾“佔用公共資源”自我表達的日子。大家都變成絕美的明星AI了,還有啥意思?
“今年我們希望,首先做個人吧。你要把人做出來,因為在這個時代如果人沒有出來,歌很難。但是歌出來也很重要,歌怎麼才能出來?就是人歌合一,毛不易之所以出來,他是人歌合一的。”馬昊説。
唱《消愁》的毛不易是人歌合一的,唱《戀人與玫瑰花》的蔣先貴是人歌合一的,唱《海海》的莊主恆的人歌合一的。他們的音樂、視覺、言行舉止都自成一派,又別具一格。
如果説毛不易的成功在於人歌合一,並對準了某種社會情緒。哇唧唧哇能夠成功推出毛不易就在於全產業鏈,從原材料選角到節目製作,再到後期的音樂開發,都可一手包辦。節目還沒播,整個企劃團隊就已經來了,保證了節目內外產品調性的一致。不至於像一些音綜,沒“售後”,出道即巔峯。
**我們反覆感慨缺少新人、新歌,事實上,就以哇唧唧哇一家,今年就已經就推出125首新歌,產能是三大音樂公司的三倍有餘。**但這就是一個不會誕生巨星、連全民型明星都很難出現的時代。一些人會説是現在的藝人不行,當然我們知道還可以用各種媒介理論來解釋,馬昊覺得做音綜一年比一年更難,但仍預測“明年音樂節目會有一個很大的井噴”。

因為覺得《明日創作計劃》的開局不算火爆,節目組搞了個動員會讓大家説説想法。蔣先貴説,“創作的意義,創作為什麼要有意義呢?我沒有別的事可以做,我就是創作。”
電視音綜最氾濫的那幾年,導師總問“你的夢想是什麼”,久了被引為笑談。但“夢想”還被認為很重要,還敢於做夢、並可宣之於口的時代,總讓人有點懷念。
有次在長沙吃宵夜,一位導演朋友問馬昊,“你的夢想是什麼。”馬昊脱口而出,“我的夢想是照亮別人的夢想。”
“可能我們70後從小受的教育,就是你要為這個世界做點什麼,總想做點有意義的事。當我特別累特別想放棄的時候,就會出現一個毛不易、出現一個蔣先貴。你會發現你不努力,你對不起他。他這麼有才華,你得讓他被看見。”
更年輕的哇唧製作導演們不肯使用“使命感”這樣的詞。但發現一個個素人、為他們搭建舞台,就彷彿去呵護一個“野生選手保護區”,你卻並無法預料他們將得到怎樣的結果。這本身就“很有趣”,也是“一個很大的成功”。

今天的我們,是否還會被音綜裏別人的夢想照亮?可以確信的是,每代年輕人仍會從這裏得到他們這個時代的音樂人,不管那在別人眼裏看來是什麼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