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擊碎了“美國夢”的男人——羅伊·鮑邁斯特_風聞
返朴-返朴官方账号-关注返朴(ID:fanpu2019),阅读更多!2021-11-04 10:14
提到心理學家,大眾能説出的名字不過是弗洛伊德、榮格,或是斯金納、馬斯洛,對他們的生平、成就大概也所知甚少;而對仍然在世、學術生涯尚在壯年的心理學家,瞭解得就更少了。
對其他學科而言,不瞭解科學家的生平,並不妨礙公眾去理解和應用他們的研究成果。但心理學卻有所不同——心理學家研究的很多問題本就是每個人在生活中都會遇到、思考的問題,因此,瞭解心理學家的一些學術歷程,對我們看待問題的方式也許有所啓發。
撰文 | 向睿洋(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心理學碩士)
他是當今最負盛名的社會心理學家之一。
他是著名的“自我控制力量模型”的提出者,巧妙地將自控力比作肌肉,使用後會損耗,鍛鍊後可增強。
他將“歸屬需要”看作人的基本心理需要,這篇發表在1995年的論文被引用了多達18000次,是引用量最多的心理學論文之一。
最重要的是,他擊碎了“美國夢”,挑戰了全美國對提升自尊的盲目信仰,挑戰了在各領域只鼓勵、誇獎而不懲罰、批評甚至不比較的社會規範。
而如今,他又站在了社會心理學界諸多爭議的風口浪尖。
他就是——羅伊·鮑邁斯特(Roy Baumeister)。
 Roy Baumeister(1953~)
Roy Baumeister(1953~)
一個服從的叛逆者
◆ ◆ ◆
羅伊於1953年出生於美國俄亥俄州。他的父親,魯迪,曾在二戰期間為納粹德國服役,參加東區戰事並且被俘,在蘇聯的戰俘營住過幾個月。後來,魯迪移民到美國,成為一家石油公司的中層經理。他十分易怒,有着極右的保守的政治傾向,信奉權威與服從,有強烈的控制慾,凡事都要按照他的方式來。
羅伊在父親極為嚴格的管束下長大。他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但生活中卻沒有什麼快樂。父親認為孩子不應該參加體育活動,也不該參加舞會或party。但在父親看重的方面,他一定要是最好的。父親甚至希望他是班上個子最高、長得最好看的。
家庭灌輸給羅伊一整套生活方式和看待世界的模式。孩提時期的羅伊相信父母告訴他的一切。但隨着年齡的增長,他漸漸發現,父母的某些看法是有問題的,他內心裏出現了反叛的聲音。究竟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對的、錯的觀念是從哪裏來的?這些問題讓他迷惑不解。一開始他求助於宗教,遍覽聖經,但仍然沒有找到答案。
羅伊的本科是在普林斯頓大學主修數學,期間,他參加了一個到海德堡大學的交換項目,在那裏他選修了哲學,並第一次讀到了弗洛伊德的作品。這為他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羅伊發現,心理學可以讓他更接近“人的觀念從何而來”以及“人待人處事的規則”的答案。
於是,等交換結束回到美國,羅伊向父親提出想轉修心理學。父親對此不屑一顧,全然反對,“學這些沒用的東西只會浪費了你的聰明才智!”
後來,父親發現自己公司裏的心理學顧問的工資竟然比自己還高,才勉強同意了讓羅伊轉修心理學。他一定沒想到自己的兒子之後會成為一位鼎鼎有名的心理學家。
他也一定沒想到,羅伊在學了心理學以後首先想做的事,就是分析自己的父親。不過羅伊開始理解他的父親,畢竟魯迪17歲就參軍了,沒有正常的青少年期來發展社交,軍旅生活讓他變得冷酷,一個德國家庭長子的身份也讓他習慣於做一個發號施令者。
他擊碎了“美國夢”
人本主義思潮興起於20世紀50年代。創始人卡爾·羅傑斯(Carl Rogers)宣稱人性本善,孩子們應該被養育在一個“無條件積極關注”的環境下,遠離各種限制,以充分發揮他們的潛能。
人本主義思潮之所以能夠興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正好與“美國夢”相契合——每個人都是好的,每個人都需要自由,以實現最好的自己。
隨之而來的就是歷時幾十年的、轟轟烈烈的“自尊運動”——在馬斯洛(Abraham Maslow)將自尊需求列為僅次於自我實現的第二高層次的需求之後,1969年,一本名叫《自尊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Self-Esteem by Branden, Nathaniel)的書出版,列舉了心理學研究的各種發現,提出:高自尊——也就是自我感覺良好——對人有各種積極的作用。此後,社會各界都全心全意地相信,高自尊對人各方面都有所助益,能促進人的思維能力,讓人有更好的情緒,總之百利而無一害。所以,應該把提升自尊作為第一要務。
在學校裏,為了提升學生的自尊,不應批評、懲罰學生,不應進行排名,老師應該變着法地鼓勵學生,甚至考試分數都應該能多給就多給,還經常讓學生給自己寫信誇自己,要讓每一個學生都認為自己是最棒的,是獨一無二的。
甚至對罪犯,也應該採取鼓勵為主的方式來對待,癮君子如果能戒毒一段時間也應該對其進行獎勵。法官都認為“應該用愛和關懷來幫助他們重新獲得自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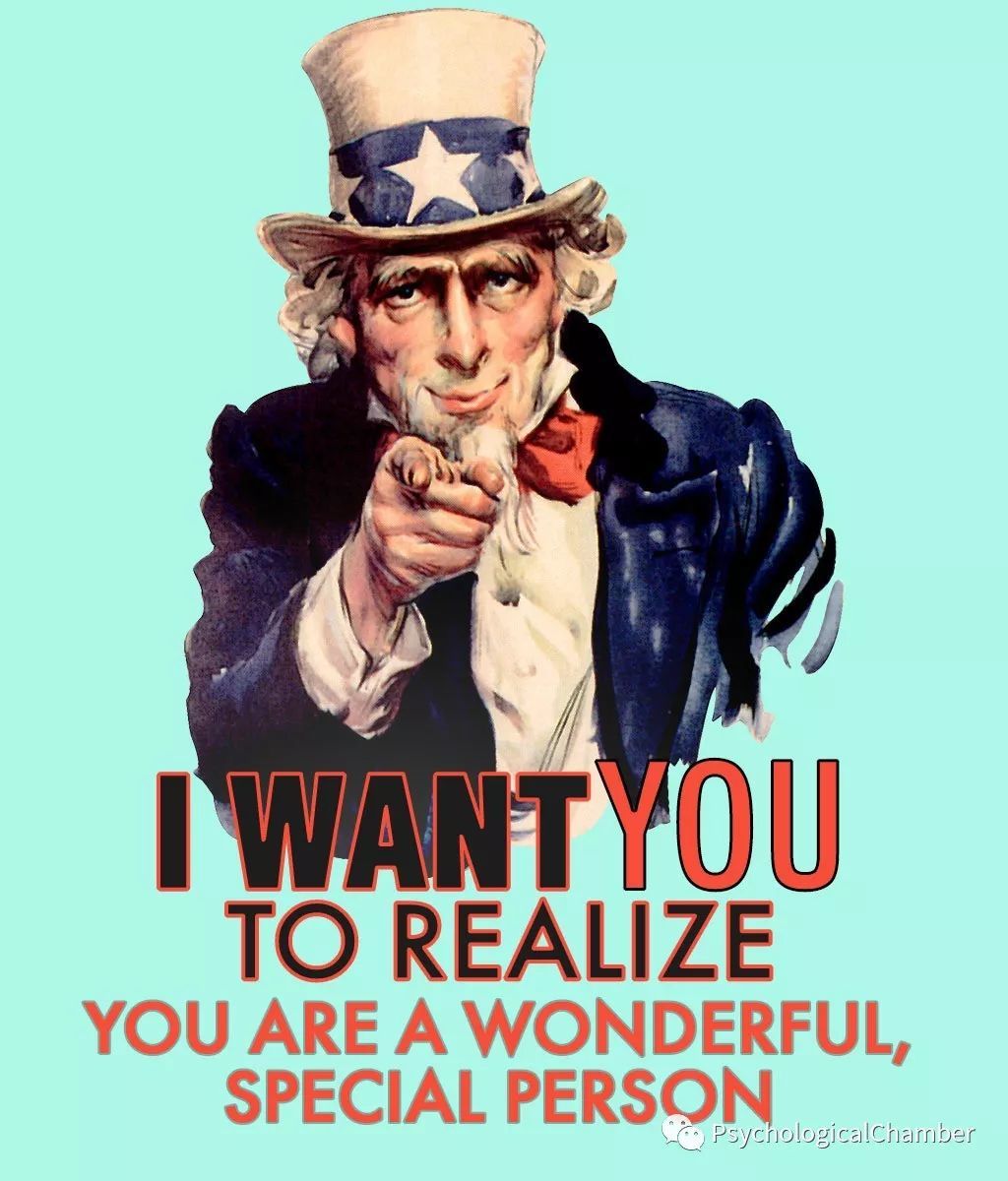 正在學習心理學的羅伊也相信高自尊的積極作用。部分原因可能是回想自己的童年,他對自己沒能參加體育、社交活動來獲得更高的自尊感到耿耿於懷。但他對《自尊心理學》有些失望,因為這本書裏更多的是故事,讀起來很有意思,但科學的證據並不充分。因此,他將高自尊者和低自尊者的差異作為自己的本科畢業論文題目,試圖用自己的研究證明高自尊的積極作用,並從此開始了對自尊的研究。
正在學習心理學的羅伊也相信高自尊的積極作用。部分原因可能是回想自己的童年,他對自己沒能參加體育、社交活動來獲得更高的自尊感到耿耿於懷。但他對《自尊心理學》有些失望,因為這本書裏更多的是故事,讀起來很有意思,但科學的證據並不充分。因此,他將高自尊者和低自尊者的差異作為自己的本科畢業論文題目,試圖用自己的研究證明高自尊的積極作用,並從此開始了對自尊的研究。
然而漸漸地,羅伊對“自尊運動”越來越不滿,因為高自尊的作用被越來越誇大,他覺得就像“高自尊的人掙了更多的錢,交了更多的税,所以研究結果偏向他們”。讓他最終和“自尊運動”徹底決裂的時刻,是人們開始普遍認為低自尊會導致暴力行為。但是根據自己的研究,羅伊知道低自尊者通常都是害羞、自我懷疑的,他們不想當出頭鳥,總是別人叫他們做什麼就做什麼,這些聽起來和暴力、攻擊性沒有一點關係。
羅伊想要看一看,究竟是哪項研究表明了低自尊會導致暴力行為。但當他查文獻的時候,他發現每一篇做出這一論斷的文章總是在引用別人的文章,但查來查去,竟沒有一篇原始的研究,沒有任何真正的證據。
震驚之餘,羅伊開始仔細研究這個問題。他發現,攻擊性高的並不是低自尊者,而往往是一些高自尊者,或者説是“虛假高自尊”或自戀者,當他們的自尊受到威脅時,就會表現出高的攻擊性[1]。
這一“離經叛道”的發現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自尊運動”的擁護者羣起而攻之。面對他們的張牙舞爪,羅伊毫不慌張,反手就開始對以往所有的自尊研究進行整理總結。他認為自我報告式的自尊測量並不可靠,而對他認為可靠的研究進行梳理後,他發現,高自尊和人們堅信的很多積極效果之間並沒有明顯的因果關係,高自尊不會讓人在多數任務中表現更好,也不會讓孩子更少地抽煙、酗酒。高自尊和好的學業成績之間確實有很強的相關,但卻並不是因為自尊更高讓學生取得了更好的成績,而是相反,取得好成績提高了學生的自尊[2]。
而對於那些有問題的高自尊者,羅伊用“自戀”來描述他們——一個健康的高自尊者,比如愛因斯坦,在別人説他愚蠢的時候,不會因此生氣;但是一個自戀者認為他們理應被別人崇拜,時刻都想要感覺高人一等,在別人不認可他們時,他們可能會因此而失去控制。
自戀可以被看作是一種對自尊的成癮。羅伊用自己的研究,將矛頭直接指向了“自尊運動”——那種靠“提升自尊”建立起來的假大空的自尊,難道不更像是自戀嗎?
1950年時,10個美國青少年中只有1個會認為自己是“一個很重要的人”,但是到1990年,這個數字變成了8個。“美國夢”的實質是個人奮鬥,要靠奮鬥讓自己感覺自己很好;但“自尊運動”卻忽視了奮鬥,只讓人沉迷在空無的自我感覺良好之中。通過羅伊的研究,美國人終於認識到了這個問題。
離經叛道的基礎
擊碎“美國夢”是羅伊“離經叛道”特質的一個集中體現。他始終扮演着“局外人”的角色,當別人都認同一件事時,他卻偏要來質疑它。在女性地位越來越高,女權主義越來越興盛之時,羅伊卻站出來(儘管他自己其實支持女權),指出總體來説男性的地位不比女性高,因為雖然社會上層男性更多,但底層同樣也是男性佔多數。心理學研究越來越關注弱勢羣體,羅伊卻對過多地從外界尋找原因(貧窮、上癮等等)感到不滿,“我有時候覺得我們心理學家的工作就是在幫人找藉口”。
羅伊的這種“離經叛道”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被他的家庭所塑造的。他的成長曆程充斥着服從與反叛兩股激流的碰撞。他的父親就是一個“局外人”:作為一個右翼分子,魯迪不斷反對流行的左翼觀點。羅伊多少會受父親的影響。更重要的是,父親要求羅伊對他完全服從,羅伊雖然表面上不反抗,但反叛的衝動不斷在心中鬱積,直到有一天他徹底脱離父親。
但羅伊並沒有成為第二個魯迪。他的“離經叛道”被心理學的科學訓練武裝了起來,他的反叛完全建立在實證的基礎上。他是一個絕對“不站隊”的人,甚至連大選他都不去投票——他堅信自己不應該有立場,才能避免各種偏見,對所有觀點持開放態度,只用數據説話。
羅伊的第二個心理學思維武器是“辯證地看問題”。他拒絕簡單的“對”或“錯”的陳述,在他眼裏,凡事都是一種權衡,而不是非黑即白,正如不良行為可能是出於良好的目的,不下對錯的定論,才能更好地看清背後的真相。例如“自尊運動”,並不是羅傑斯、馬斯洛錯了,而是對高自尊的過度追捧會導致自戀的問題。
這就是羅伊“離經叛道”的基礎。他看不慣主流的觀點被當作“對的觀點”,但他也不是與主流觀點完全相反,他只是用數據説話,深入研究這些主流觀點究竟合理在何處,不合理在何處。
當反叛者被當作權威
最近幾年,羅伊成為社會心理學界備受爭議的人物。這些爭議不是因為他“離經叛道”地提出了什麼政治不正確的言論,卻是因為——這個一直以來的反叛者似乎成為了權威。
自2011年起,心理學,尤其是社會心理學,開始了一輪研究實踐的自我反省。大量之前的研究結果被發現並不可靠,很多研究不能被成功重複。在審查過去研究成果的可靠性時,風靡一時的“自我損耗效應”首當其衝。
“自我損耗”(ego depletion)的現象由羅伊與其夫人(同為社會心理學家的)戴安妮·泰斯(Dianne Tice)共同發現,並提出“自我控制力量模型”對其加以解釋。據説某一天晚上,羅伊和戴安妮在家裏烤了一爐曲奇餅乾,突然就想出了這個idea。“自我損耗”的經典研究範式就是,在一個瀰漫着烤曲奇香味的房間裏,桌上放着一盒巧克力曲奇和一盒胡蘿蔔,一半被試被要求吃胡蘿蔔,而另一半被試吃曲奇;前一半被試吃完胡蘿蔔後,在解一個無解的迷宮遊戲時,堅持的時間會更短,因為抑制想吃曲奇的衝動消耗了他們的自控力[3]。
 “救命!這盤蛋糕在引誘我!”
“救命!這盤蛋糕在引誘我!”
在這項研究發表後的十幾年裏,產生了幾百項基於“自我損耗”的研究。且不説“自控力資源有限”是不是對“自我損耗”最好的解釋,至少“意志力任務會損耗自我調節能力”這個效應應該是存在無疑的。然而,2016年的一項大型重複研究卻並沒有重複出“自我損耗效應”[4]。
羅伊對這項重複研究的方法提出了諸多批評,其中重要的一點是認為,該研究所使用的引發“自我損耗”的方法未能奏效。有反對者寫了一封公開郵件,要求羅伊提供一個最有效的引發方法,以進行進一步的重複驗證,這時羅伊被激怒了:“你的名聲不好,我不想和你合作”[5]。
目前,學界對“自我損耗效應”是否存在還沒有一個定論。
不只是不斷反駁對自己研究的批評,羅伊也表達了他對社會心理學研究實踐總的看法。社會心理學研究正在發生一個很大的轉向:要求有更多的被試數量,以使結果更可靠,避免巧合性的顯著結果或誇大研究的效應;並強調研究過程、數據的公開透明和重複研究的重要性。
但羅伊對此有不同的意見[6]。對於重複研究,羅伊發表了極具爭議的言論。他認為從事心理學研究需要天賦,在他自己的實驗室裏,有天賦的學生總能重複出他的研究成果,那些不能成功重複的,一定是能力存在什麼問題。對於現在很多失敗了的重複研究,他也認為是進行重複研究的研究者對研究缺少某些必要的瞭解。
而對被試數量問題,他的觀點也同樣富有爭議性。他説在他還是個學生的時候,常規的研究方式是想一個好的研究問題,只需要招募10名被試就能取得顯著結果;如果不能顯著,就説明提出的問題還不夠好,要招募20名被試是在浪費寶貴的被試資源。現在一個實驗動輒要招募成百上千的被試,那麼很微弱的效應也能取得顯著的結果,雖然結果可靠,但這些效應並沒有什麼意義,將會使社會心理學變成一個“嚴謹但無聊”的學科。羅伊認為,想出好的研究問題本來就是心理學研究者必備的天賦,現在堆被試數量的方式將會讓心理學研究越來越沒有技術含量,成為體力勞動。
羅伊的這些觀點看起來都像是一個精英主義權威的諸多牢騷,一個保守的老派研究者對新研究實踐的反動。那個曾經的離經叛道者,真的成為了他曾經不斷反叛的權威了嗎?
每一個科學家總是相信自己的數據是最好的,羅伊也無法擺脱人的這種天性。堅持自己的觀點,在有足夠的證據駁倒自己之前絕不輕易妥協,本來也是科學家的傲骨。尤其是當自己的一項研究成果或一種研究實踐已歷經多年,要被徹底推翻,肯定會有強烈的牴觸。
或許,可以換個角度看,現在新的研究實踐已經成為了主流觀點,大勢所趨,羅伊所做的不過是和以前一樣,提出他對新的主流觀點的質疑。
如今,羅伊已經68歲了,他的學術生涯從來不乏爭議。反叛者也好,權威也罷,他始終勇於質疑主流觀點,只相信數據;始終辯證思考,儘量不站隊;也始終堅持自己,絕不輕易妥協。
這就是社會心理學家羅伊·鮑邁斯特。
本文編譯並補寫自 https://medium.com/matter/the-man-who-destroyed-americas-ego-94d214257b5
參考文獻
[1] Baumeister, R. F., Smart, L., & Boden, J. M. (1996). Relation of threatened egotism to violence and aggression: The dark side of high self-esteem. Psychological review, 103(1), 5-33
[2] Baumeister, R. F., Campbell, J. D., Krueger, J. I., & Vohs, K. D. (2003). Does high self-esteem cause better performance, interpersonal success, happiness, or healthier lifestyl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4(1), 1-44.
[3] Baumeister, R., Bratslavsky, E., Muraven, M., & Tice, D. (1998). Ego depletion: Is the active self a limited resour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5), 1252-1265.
[4] Hagger, M. S., Chatzisarantis, N. L., Alberts, H., Anggono, C. O., Batailler, C., Birt, A. R., … & Calvillo, D. P. (2016). A multilab preregistered replication of the ego-depletion effect.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4), 546-573.
[5] https://replicationindex.com/2016/04/18/is-replicability-report-ego-depletionreplicability-report-of-165-ego-depletion-articles/
[6] Baumeister, R. (2016). Charting the future of social psychology on stormy seas: Winners, losers, and recommenda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66, 153-158.
本文經授權轉載自微信公眾號“PsychologicalChamber”,有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