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青的外交之路(二) | 新中國女總領事走馬上任_風聞
外交官说事儿-外交官说事儿官方账号-让更多人了解有血、有肉、有情怀的中国外交官2021-11-08 11:56
作者簡介
朱青,1924年生於上海,早年就讀於滬江大學,1942年參加新四軍,1946年擔任過陳毅軍長的翻譯。上海解放後,曾任陳毅市長、潘漢年副市長的秘書。1953年進入外交部,曾任外交部第二亞洲司副司長。1981年被任命為中國駐日內瓦總領事。1994年11月22日,於北京病逝。

日內瓦是一座迷人的城市。它位於瑞士的西南端,南面和法國接壤,憑着幾十條通道,它和法國之間保持着密切的聯繫。由於聯合國的歐洲總部和很多專門機構設在這裏,日內瓦給人的感覺是一個相當國際化的城市,不論走到哪裏,總能看見各種膚色和身着各種服飾的人徜徉其間。
當地的日內瓦人就更有意思了,他們如果要去首都伯爾尼,就説:“我要去瑞士。”當然,這一方面是因為日內瓦州本身就具有相當的獨立性,另一方面也因為在他們的感覺裏這裏似乎更多地屬於國際社會。
新上任的總領事要向日內瓦州長遞交由本國政府總理簽署的委任書,州長、州政委員還要正式接見。我接到州政府禮賓司通知接見的日期後,着實準備了一番。我寫了儀式上的致辭,根據當地的習慣做法,還要有一段法文的開場白。我請教了領館中法語説得最好的領事,錄了音,認認真真地反覆背誦了那段開場白。
此外,還要講究一下穿着,我選了一件暗紅色的旗袍,外加一件黑色錦緞上綴有彩色菊花的外套,配了一雙黑色尖頭的高跟鞋。一切就緒後,自己覺得萬無一失了,誰知一來到州政府前,馬上就被將了一軍。我發現自己犯了一個不大不小的“錯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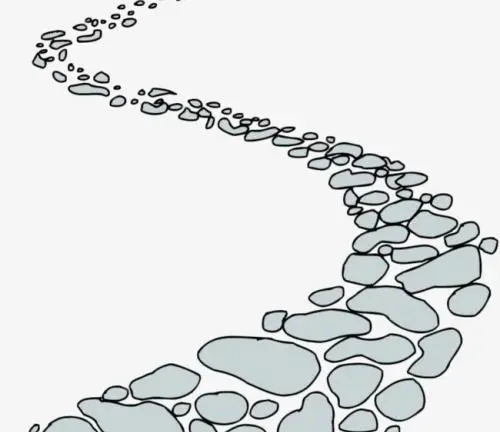
原來州政府坐落在一個大斜坡的頂端,而這條從我腳下向上延伸的斜坡完全是用鵝卵石鋪就的。據説,從前人們都是騎馬上去的,不難想象,馬蹄敲擊在鵝卵石的路面上,聲音必定清脆悦耳。可是現在要穿着高跟鞋走上去,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沒辦法,我不得不挽着同去的領事的胳膊向上走,儘管心裏並不十分願意,也只有如此了。

一進州政廳,禮賓司長就走過來低聲問我説:“你能不能稍講幾句法語?”這一問,正中我的下懷,我胸有成竹地告訴他説:“沒問題啦!”會見州政府官員的時候,我把已經背誦得相當流利的那段法語講了出來,會見的氣氛一下子就變得輕鬆起來。
接着,我作了簡短的致辭。我説:“在我任內,希望能在州政府的支持和幫助之下,努力促進中瑞關係的發展……”我還把萊蒙湖比作西湖,引用了蘇軾“濃妝豔抹總相宜”的詩句來形容它的美麗。
在州長作了簡短致辭後,我同各位州政委員自由交談起來。
上任拜會結束後,禮賓司長送我出門,我們一路並肩而行時,他對我説了兩件事:
一是糾正我剛才的一個説法。他説:“你説的萊蒙湖應該叫作日內瓦湖”;另一件事是開玩笑地提醒我,總領館應該請州政委員們吃中國飯。對於他所説的第一點,我實在不敢苟同,因為萊蒙湖橫跨三個州,怎麼好被日內瓦一個州“獨有”了呢?至於他説到的第二件事,我當然是“樂於從命”的。

1987年,朱青在中國駐瑞士大使館門前
在我任期內,因為兩國關係發展很好,所以我們和官方之間以友好交往為主,其他政治方面的交涉,基本上是關於“兩個中國”的問題。瑞士是西歐國家中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並且注重發展兩國間的友好關係,所以有些問題一經交涉,他們總是儘量考慮我們的要求。
一次,台灣一個民間樂團到瑞士演出,節目單上印着“中華民國”的字樣,我們將此事向州政府禮賓司提出後,他們就要求台灣演出團把這些不合適的字樣塗掉。
有時,台灣方面也有人來出席在日內瓦舉行的一些會議,當然,他們只能以個人身份或民間團體的名義參加。但是在掛旗方面常常會出現難以處理的局面。碰到這種情況,瑞士方面有時就索性在所有代表的面前都掛上一面瑞士國旗,以避免出現“兩個中國”的問題。

日內瓦是一個長年累月會議不斷的城市。聯合國歐洲總部和其他各種常設機構的會議加在一起,據説一年要開3萬多次,比紐約聯合國總部更勝一籌。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每年各主管部門派去日內瓦參加各種政府間和非政府組織會議的代表團越來越多,加上各路人馬途經此地,所以總領館另一項重要的日常工作就是迎來送往。
從日內瓦路過的也還有外國的代表團。如在我上任後不久,1982年1月3日,根據國內指示,我接待了西哈努克親王夫婦一行幾十人。

西哈努克親王夫婦
西哈努克親王1970年3月在國外訪問時,柬國內的陰謀家發動了政變。其後,越南又在1978年底入侵了柬埔寨。親王雖身在異國,但一直關注柬國內的形勢。柬人民經過三年多的艱苦奮鬥,形勢越來越好。就在這個時刻,親王自巴黎經日內瓦去了北京。親王深得旅法柬僑的愛戴,不少柬僑隨着親王自巴黎一直送到日內瓦。
我們在小宴會廳裏設了主賓桌,然後又在大廳裏設桌招待親王夫婦的隨行者。親王夫婦,温文爾雅,氣度不凡。他們會講法語,英語也十分嫺熟。當我講話時他們總是笑容可掬,微側着頭,認真地聽。我除了在小宴會廳裏與親王夫婦交談外,也去了大廳向其他柬方客人一一敬酒致意。對此親王夫婦特別高興,舉杯來到我座位面前,祝酒致謝!莫尼克公主更是向我擁抱、“貼面頰”。説實話,這個“洋”規矩在來到歐洲之前,我還沒有領受過。

聯繫留學生解決他們的困難也是總領館的一項日常工作。有一名留學生,來自湖南的農民之家,因外語水平稍差,尤其不善口語,所以處在洋學生中間常常感到手足無措,見人更是不抬頭、不打招呼,學生們因此都譏諷他為“怪人”。
每當他來到總領館,總是為此傷心哭泣,覺得自己很對不起父老鄉親。他説:“我知道老鄉們養大一口豬要付出多少辛勞,他們不知道要出口多少頭豬換回外匯,才能供我出國留學。可是我現在什麼也沒有學到手,真是無顏見鄉親。”我告訴他有什麼想不開的事儘管來找總領館,鼓勵他要自信。同事還專門指派了一位和他同專業的留學生,在語言、交往和生活方面多予關照。不久,他的境況有了很大改變,不僅學會了與洋學生相處,各科成績也上升很快。

總領館在當地是中國政府的派駐機構,所以在日內瓦發生有關中國人的涉外事件,瑞士方面都要來找我們解決。
一天,州政府禮賓司通知總領館説,有一些中國人未辦簽證就要入境,現在在機場等候,要我們趕快前去處理。我馬上派了一位領事趕赴機場,一問才知道原來是一批出國的勞務民工,因為他們中間沒有一個懂外語,所以見飛機停了,就以為到了目的地,跟着其他乘客下了飛機。
這下,總領館就忙開了,又是向民工瞭解情況,又是向當局做出解釋,同時還要和國內有關方面進行必要的聯絡,一直忙到把農民工送走。

住在日內瓦的中國僑民,主要是在聯合國機構工作的國際職員,他們文化知識水平較高,收入頗豐,其他僑民一般也都很安分守法。但是有時個別的也有一些違法事件。曾經有一個在國內某機關任職的副科級幹部,為了出國放棄了“鐵飯碗”,挽起袖子學炒菜,在親戚家開的飯館裏當了一名“黑工”。
這家飯館每天要到午夜12時才“打烊”,然後還要打掃衞生,收拾殘局,第二天清晨又要去遠地採購當天所需的食品。沒過多久,這位“副科長”就受不了了,於是開始磨洋工。終於,當老闆的親戚無法容忍這位“懶工”,便向當局告發他是非法居留做工的。
當我們知道他即將被驅逐出境時,去找了有關方面瞭解情況,看看是否能用體面一點的方式出境,而不是被“驅逐”,尤其是希望媒介不要渲染。但是瑞士的法令是嚴格的,對這位“副科長”的處理,我們實在也是無能為力。
1984年春,我在同朋友們的依依惜別中離開了日內瓦,到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之一的伯爾尼任職。所幸的是,後來我又多次到過日內瓦,重新回到朋友中間再敍友情。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