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瑋:駁“崖山之後無中國”説_風聞
今天敲钟人不来-2021-11-09 13:56
作者:羅瑋
來源:《歷史評論》2021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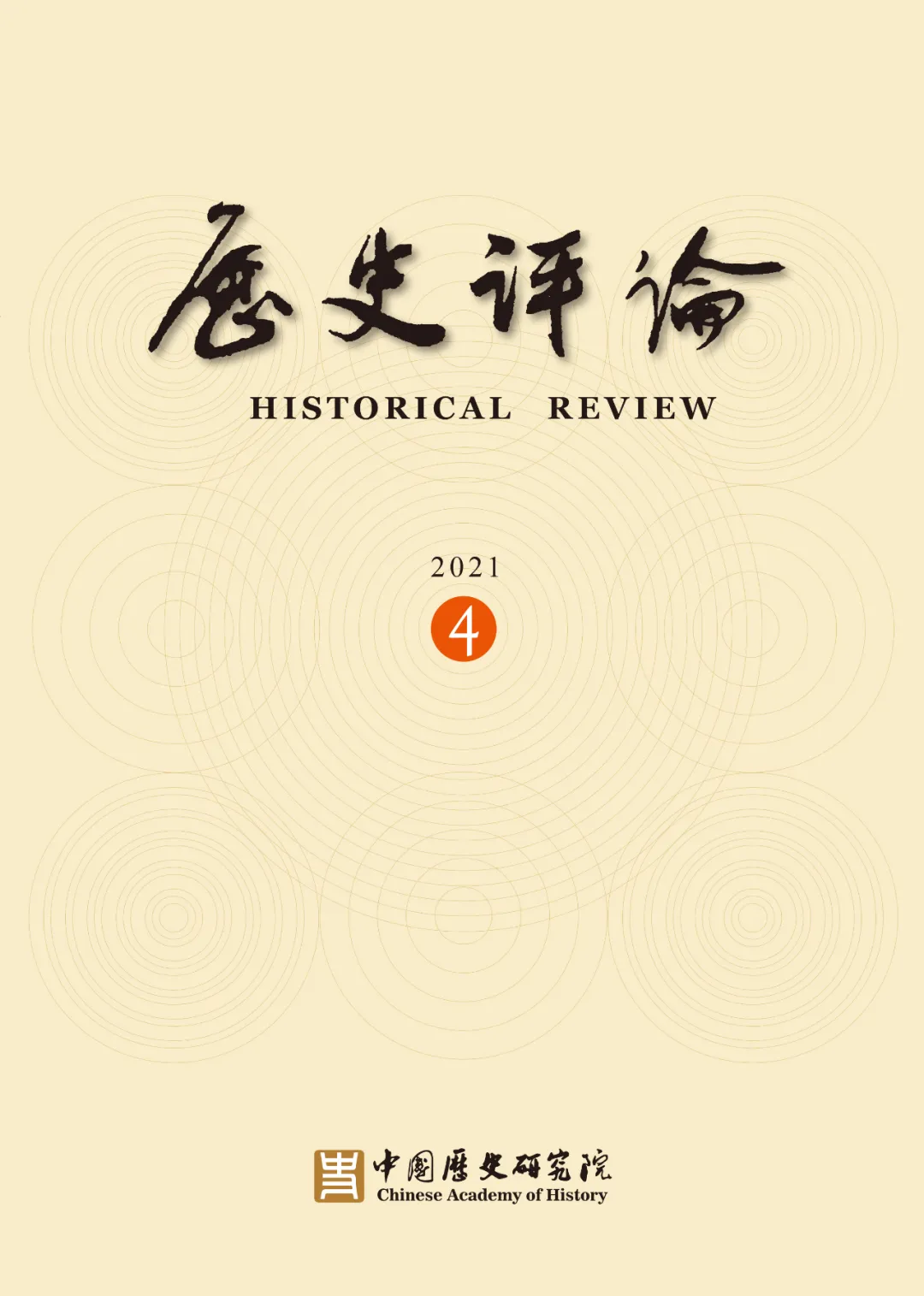
“元清非中國論”本質上是為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提供輿論支撐而臆造出來的説辭。二戰後進一步衍生出“崖山之後無中國”的提法,不僅流行於日本通俗文學領域,還在網絡興起後傳入國內,被重新包裝後廣泛流播,目的是矇蔽不熟悉歷史的網民。
一直以來,“元朝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王朝”是不刊之論。然而近些年,社會上逐漸出現了“元朝不是中國王朝”的論調,認為“崖山之後無中國”。這種錯誤觀點雖遠談不上是主流,但藉着網絡流傳很廣。因此有必要加以澄清,予以批駁,以正視聽。
一般認為,“崖山之後無中國”一語直接來源於日本作家田中芳樹於1997年出版的一部講述崖山之戰的歷史小説《海嘯》。“崖山之後無中國”作為主題語赫然置於該書首頁,表面上是在營造歷史悲劇情緒,實際是進行某種潛移默化的政治立場灌輸。而網絡上流傳的蠱惑性網文也常直接引用《海嘯》,經過層層煽動性鋪陳,最後拋出自己的觀點:“唐宋在日本。”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其實,網上一些討論已注意到田中的思想來源於20世紀日本東洋史中右翼歷史學家的“元清非中國論”(又稱“滿蒙非中國論”),但多語焉未詳。東洋史是日本明治維新後產生的以中國歷史為核心的泛亞洲史研究,在日本歷史學科中佔非常重要的地位。日本東洋史的興起與明治維新後日本對周邊國家的擴張和殖民活動關係緊密,它的誕生不是一個“純學術”事件,而是為當時日本政治服務的。因此,跟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步入學界的學者不同,戰前的東洋史學界與日本政治牽涉很深。其中,鼓吹“元清非中國論”者主要有三位:內藤湖南、矢野仁一和宮崎市定。
內藤湖南(1866—1934)是“京都學派”主要奠基者,有“近代日本漢學第一人”之譽。他在中國史的宏觀理論方面有兩大觀點:一是空間維度的“中國文化中心移動説”;二是時間維度的“唐宋變革論”。其中“中國文化中心移動説”的政治意味最強,與“元清非中國論”淵源頗深。
1894年,內藤湖南以《地勢臆説》為題,第一次表述了“中國文化中心移動説”的基本觀點,後又在《支那論》《新支那論》(他稱中國為“支那”)中將其系統化,認為中國古代文化中心是按照“洛陽→長安→燕京(和江南)”路線移動的。但僅僅概括這一現象並非其主要目的,更重要的是引出為日本政治服務的中國“中毒”、“解毒”或“恢復年輕”理論。內藤臆稱中國文化中心形成後,自身文化積澱日久,產生種種衰頹的症狀,形成“中毒”;周邊地區新生的、強壯的勢力反作用於“中毒”的中心文化,使之獲得新的生命活力,即所謂“解毒”或“恢復年輕”。
很顯然,內藤這套理論是為了解釋中國歷史上農耕定居的漢族與北方民族的互動現象,把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看作對中國“解毒”。在敍述技巧上,內藤可謂頗具“匠心”。他刻意將中國狹隘化為漢族政權,再把漢族與蒙古、滿洲在敍述上隔離開來,把中國與遼、金、元、清等中國北方民族建立的王朝隔離開來。這就是“元清非中國論”的淵源。在曲解中國真實歷史的基礎上,內藤特別強調“外來民族的侵入”是維繫中國歷史悠久的原因,是中國人民“非常幸福的事”。反觀當時明治維新後日本國力日盛,咄咄逼人,而晚清中國日益孱弱的局勢,內藤的用心已十分明顯了。
相較於“以古喻今”,內藤對其學説的現實目的直言不諱。1894年,內藤在《日本的天職與學者》中即已道明,中國文明之中心,“今又將有大移動,識者實早已瞭解其間要領,此乃日本將接受大使命之際也”。當內藤看到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等粵籍人士主導的維新、革命活動風起雲湧時,他又提出,中國文化中心已轉移到廣東,“在對中國文化的接受上決不晚於廣東等地的日本,今天將成為東洋文化的中心,這對中國文化來説,是一股新的勢力,已毋庸置疑”。他進一步引申説,“日本與中國在政治上成了一個統一的國家的話,文化中心移至日本”,“將日本的先進文化移動到中國,促進已經處在衰老垂死狀態的、產生自身‘中毒’徵兆的中國實行‘革新’”。在此邏輯下,內藤赤裸裸地鼓吹對中國的軍事入侵,妄稱“日本的力量介入中國促使其革新,還算是中國自發的革新,而最快的捷徑是從軍事上加以統一”。
由上可知,在將中華民族內部曾入主中原的北方遊牧民族與日本等同,將洛陽、長安、北京、江南、廣東等中國地域與日本類比的錯誤前提上,內藤湖南的“中國文化中心移動説”,不僅為日本對中國領土的覬覦提供“合法性”基礎,也為日本右翼的“元清非中國論”開啓惡端。
內藤的另一大發明“唐宋變革論”,認為中國從宋代進入“近世”,比西方早了四五百年,過早的成熟也就意味着過早的衰落,因此需要外界力量的“解毒”和“革新”。這同樣是為侵略目的服務的。此外,內藤還提出過中國“領土過大論”和“國防不必要論”,都是赤裸裸的侵略理論。
內藤之後,日本國際關係史學家矢野仁一(1872—1970)在1923年出版了成名作《近代支那論》,其中《支那無國境論》《支那非國論》兩篇文章,叫囂“滿、蒙、藏本來就不屬於中國領土”的論調,堅稱“中國不等於清朝”,直接拋出“元清非中國論”,為日本軍國主義集團鳴鑼。
第三位代表性學者是“京都學派”第二代領軍人物宮崎市定(1901—1995)。同他老師內藤一樣,宮崎涉獵中國歷史領域甚廣,並構造了一個龐大的體系。但與內藤湖南不同,宮崎市定更注重考察漢族與北方遊牧民族互動如何影響中國歷史。
高喊“歷史學家必須和他們所處的時代共呼吸”的宮崎市定於1925年應徵入伍,經過一段時間的軍訓後,轉為預備役。1932年“一·二八”事變爆發之後,他被派往上海,成為侵華日軍的一分子。宮崎市定也承認自己“與(日本)軍隊緣分匪淺,而是捲入很深的關係當中”。
日本侵華期間,宮崎市定推出多部所謂中國史著作。如《東洋的樸素主義民族與文明主義社會》(1940)、《日出之國與日暮之處》(1943)及《支那、南洋關係史》(1944),為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合法性”製造“歷史依據”。此外,宮崎與眾多右翼學者一起參與了日本軍部支持下的多部反動歷史書籍的撰寫,如《支那政治史》(1941)、《異民族統治支那史》(1944)、《大東亞史概説》(未出版)等,竭盡全力為近代以來日本的對外擴張政策提供“歷史依據”。
《東洋的樸素主義民族與文明主義社會》是宮崎第一部史學專著,是對“元清非中國論”的再一次推動,也為日本侵華作了一次有力的輿論鼓譟。該書將中國歷史上漢族與北方遊牧民族的緊密互動現象,置入“樸素主義”與“文明主義”的二元對立框架。在他的話語體系中,“樸素”是褒義的,“文明”是貶義的。如同以往日本右翼學者的話術一樣,宮崎仍將漢族政權等同於“中國”,窄化“中國”的意涵,並將漢族建立的政權與遊牧民族政權隔離、對立開來。該書認為,中國這個“文明主義”的社會,每逢發展到飽和點,就要趨於頹廢。在具有“樸素主義”的遊牧民族侵入並建立了他們的統治以後,才能使其重新振作起來。但契丹、女真、蒙古和滿洲統治了中國以後,卻又不免因“文明化”而趨於衰落。由此可見,宮崎將內藤湖南的“中國文明的中毒與解毒説”進行了更為精緻的理論包裝。
在該書中,我們可以經常見到宮崎提及日本。如書中《宋人所見日本》一節,對歷史的零星記載隨意誇大發揮,宣稱“最能理解日本人特點的莫過於宋人”;“宋人對日本的感情自然也很親善”;“日宋之間的親睦邦交一直繼續到宋亡以後……向日本請求援兵以復興宋室的計劃,似亦並非止於風傳”。由宮崎對宋朝與日本關係“捕風捉影”式的高度評價,再聯想到元朝取代南宋後隨即對日本發動的幾次征伐,那麼日本文人學者的“崖山之後無中國”也就呼之欲出了。
宮崎還不忘從浩瀚史籍中找出一些孤立的文字,拼湊起來進行比附,如他借滿人入關建立清朝之例,宣稱“日本和滿洲在樸素主義的訓練上一脈相通之處,即在於語言雖然不通,但系以心傳心,互相瞭解。誠所謂好漢識好漢”。真是為了達到政治目的,不惜對歷史細節進行毫無根據的臆想與虛構。
當清朝無法逃出從“素樸”走向“文明”進而滅亡的“歷史週期律”,那麼代替清朝的是誰呢?中國的未來又將如何?宮崎在此書最後一節《東洋史上的新局面》中,直白露骨地展現其真實意圖。該節認為,日本也是具有“樸素主義”的民族,並且,日本的“樸素主義”是掌握了科學的新的樸素主義,具有“發展性”,因此日本如果對中國的統治一旦建立,就決不會再蹈契丹、滿洲和蒙古等北方民族的覆轍。宮崎市定進一步提出,日本不僅應當統治中國,還要承擔“建設東亞新秩序”這個“重任”。如此,在對中國歷史的歪曲與解構基礎上,宮崎最終把着眼點放在論證日本對華侵略的“合理化”、“合法化”上。
由上可見,“元清非中國論”本質上是為了對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提供輿論支撐而臆造出來的説辭。二戰後進一步衍生出“崖山之後無中國”的提法,不僅流行於日本通俗文學領域,還在網絡興起後傳入國內,被重新包裝後廣泛流播,目的是矇蔽不熟悉歷史的網民。對此,今人不可不慎。
點評:對待一個大的學術思潮或流派,需要嚴肅關注其背後深刻的歷史背景。本期發表的有關日本東洋史學的文章對此作出了一些努力,或可使我們對這一學派有更全面、更清晰的認識,而不至於“蔽於一曲”。需要指出的是,日本的對華侵略戰爭雖然失敗,但東洋史學的謬誤並未得到徹底清算,在冷戰背景下,它的一些觀點和方法成為西方漢學的思想資源,並衍生出“內亞性”、“新清史”等概念和學術流派。對此,我們應予以充分關注。
作者單位:中國歷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