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無神論史》連載43——唐末儒者關於上天功能的討論_風聞
国际邪教研究-国际邪教研究官方账号-珍爱生命,愿天下无邪!2021-11-14 22:05
**編者按:**為宣傳科學無神論,從9月10日起,我們將連載李申的專著《中國無神論史》。李申,1946年4月出生,河南孟津縣人。1969年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原子物理系;1986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世界宗教研究系,獲哲學博士學位;2000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儒教研究室主任。2002年轉任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現任中國無神論學會顧問、國際儒學聯合會顧問、中國反邪教協會副會長。

第九章 隋唐五代時期的無神論思想
九、唐末儒者關於上天功能的討論
唐代以前,儒者們關於日月星究竟是石?還是什麼別的東西?曾進行過長期的爭論。唐代初年,孔穎達作《左傳正義》,認為這是個説不清的問題。後來,天文學家李淳風作《隋書·天文志》,仍然重複古老的見解,説日月星都是所謂“陰陽之精”。所以在“日月星是什麼”,“它們為什麼會發光”等問題上,隋唐時代沒有取得多少進展,但是對於它們所附着的天,唐代的認識卻有着根本的進步。那就是他們根據《毛詩》,認為天是一個“元氣廣大”的存在物,所以稱為“昊天”。這個見解,被《開元禮》所繼承,並且成為關於“上天是什麼”的法定解釋。
唐代末年,在對天的這樣的概念的基礎上,韓愈、柳宗元等人展開了天人關係的討論。

事情起源於韓愈的一段牢騷。韓愈説,現在的人們,有了疾苦,向天呼籲,認為不應讓殘民者昌,佑民者亡。韓愈説,這是不知天的緣故。比如果實朽壞就會生蟲,人體有病也會生瘡癰。人,就是元氣陰陽所生的蟲子和瘡癰。他們墾田鑿井,開渠築城,是元氣陰陽的罪人。假如能減少甚至消滅這些“蟲子”和“瘡癰”,天地一定是高興的。
在這裏,韓愈所説的天,就是元氣陰陽。
柳宗元在《天説》中引用了韓愈的話,認為韓愈大概是“有激而為是”。柳宗元認為,“上而玄者世謂之天,下而黃者世謂之地,混然而中處者世謂之元氣,寒而暑者世謂之陰陽。”雖然物體大,但上天和果實瘡癰草木,性質是一樣的:
天地,大果蓏也;元氣,大癰痔也。陰陽,大草木也。
這樣的天,怎麼能夠賞功罰過呢?柳宗元的結論是:
功者自功,禍者自禍。慾望其賞罰者大謬;呼而怨,慾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謬矣。子而信子之義以遊其內。生而死爾,烏置存亡得喪於果蓏癬痔草木也。(柳宗元《天説》)

也就是説,這樣的天地,不會報復人,也不會賞功罰過。人們在危難的時候呼天怨天,希望天地以仁愛之心可憐自己,就更加荒謬。所以人們不要把自己的吉凶禍福、得失存亡寄託於這個像果實、瘡癬、草木一樣的東西上。
柳宗元的《天説》被他的密友劉禹錫得知,劉禹錫認為,柳宗元的《天説》也是“有激而云”,“非所以盡天人之際”(《天論上》),所以他作了《天論》,以求把這個問題弄個明白。
劉禹錫把講天人關係的分為兩家。一家是傳統的天人感應説。這種説法認為,人的災禍都是由於有罪而天降懲罰,幸福都是由於行善所得上天表彰。危難時向天呼籲天能聽到,有所要求向天祈禱天會給予答覆,好像有個什麼東西在確確實實地主宰着人的命運。另一家是“自然之説”。這種説法認為,天與人根本不同。雷霆震殺樹木人畜,並不是它們有什麼罪過;春天香花和毒草一起生長,天不選擇其中的善惡。盜蹠和莊蹻橫行天下,孔子、顏回一生窮困,這説明沒有什麼主宰者。劉禹錫認為,這兩種説法都沒有窮盡天人關係,並因而提出了自己的“天人交相勝”説: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動物之尤者也。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餘曰:天與人交相勝耳。(《天論上》)
天與人之所以交相勝,是因為天道和人道不同:
天之道在生殖,其用在強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天論上》)
比如説,天暖使萬物生長,天寒使草木凋謝,水火各有自己的作用,木料堅實但不如金屬鋒利,年青的壯健,年老的遲鈍,強者做君長,弱者被奴役。這一切,都是天的作用。至於春種秋收,防災除害,開礦冶金,崇尚賢才,獎勵功勞,制訂行為準則,擯斥腐敗奸邪。這一切,都是人的作用。所謂交相勝,是説這兩種作用的此消彼長。
劉禹錫把天道與人道此消彼長的情況分為三種:第一種是政治清明,人道正常發揮。這個時代,是非標準統一,行為有共同的法則。循規蹈距的會得到賞賜,胡作非為的要受到懲罰。這是人道勝過天道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人們就會認為,天道和人事不相干。第二種是政治原則受到局部的破壞,受賞的並不全是良善,被罰的也不都是惡人。用詭詐也可能得到幸福,靠僥倖就能夠免除災禍。這是人道駁雜不純的時代。在這個時代,關於天人關係的説法也各種各樣。第三種情況,政治極端混亂,是非顛倒,善惡錯位。受賞的都是奸佞,挨罰的也全是正直。在這個時代,如果還要説什麼天道人事不相干,就會理屈詞窮。劉禹錫由此得出結論説:

故曰:天之所能者,生萬物也;人之所能者,治萬物也。法大行,則其人曰:天何預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則其人曰:道竟何為邪!任天而已。法小弛,則天人之論駁焉。今以一己之窮通,而欲質天之有無,惑矣。(《天論上》)
所謂“一己之窮通”,是批評韓愈、柳宗元二人,都是從個人的遭遇出發,“有激而云”,來討論天的有無,這樣是不會得出正確結論的。
在劉禹錫看來,天的所能,就是寒暑往來,日月交替,風雨旱澇,萬物生死,與社會的治亂沒有關係。而人的吉凶禍福,是產生於社會治亂。在社會政治清明時,好人有好報,人們很清楚地知道,吉凶禍福是由於自己的作為,是社會對自己的合理報答。反之,若是天下大亂,則是非顛倒,報答乖舛。按劉禹錫的結論來看,報答無論合理與否,它都是社會的報答,而不是天的報應。天沒有使天下大治的能力,也沒有能力把社會搞亂,因而也不應對人的吉凶禍福負責。因此,企圖從人的禍福報答是否正常來討論天道的有無,這本身就是錯誤的。
劉禹錫説,比如在旅途中,強有力者可以先喝到泉水,這就是天勝。在城市或村莊裏,住華麗的房子,吃精美的飲食,就一定是聖人和賢者,這就是人勝。因此,天人交相勝,就是天理和人理交替取勝。在劉禹錫這裏,天理,就是自然界的混亂的無秩序狀態,這個狀態遵循着弱肉強食的原則。人理,就是社會的等級尊卑秩序及其一系列倫理道德規範。劉禹錫認為,在這交相勝中,人理務求戰勝天理,而天理卻並不追求戰勝人理。
《天論》下篇,劉禹錫為自己的主張做了結。他認為,世界上的事物儘管千差萬別,但道理只有一個。因此,由小可以推大,由近可以及遠。人為“倮蟲之長,為智最大”,假若“能執人理”,就能使人理勝於天理。反之,若是紀綱敗壞,天理就要取勝。決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天。他最後的結論是:天不預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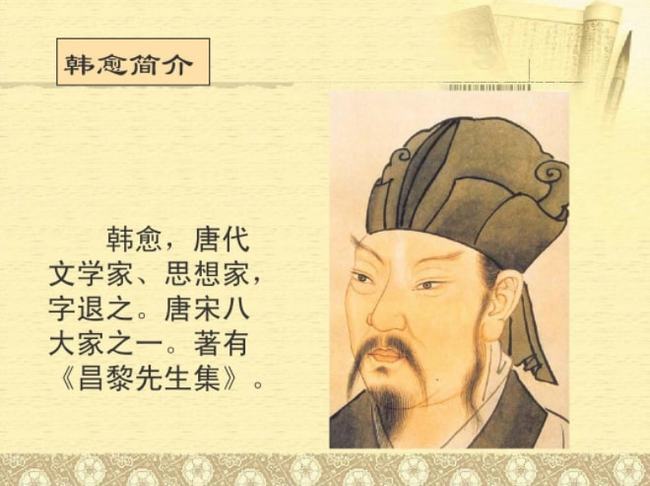
當柳宗元看到他的文章以後,覺得和自己的意見並沒有什麼差別。但不贊成劉禹錫説的“天恆為惡,人恆為善”,認為這是“過德乎人,過罪於天”(柳宗元《答劉禹錫〈天論〉書》)
劉禹錫把亂歸於天理,把治歸於人理,柳宗元不能同意,其別的儒者更加不能接受。宋人在《天説》的解題中就説,假如説天不能賞善罰惡,還怎麼進行道德教化?而且,依劉禹錫所説,上帝的作用就是敗壞人世的秩序!這不僅是摘掉了上帝頭上的光環,並且還換上了荊棘做的冠冕,因而更加不能被其他儒者所接受。
從認識發展的角度看問題,劉禹錫認為天理代表着混亂,而人理或人治代表着秩序,並且人類力求戰勝混亂,建立秩序,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是一種少見的對人與自然關係史的深刻觀察。認為人們只把自己不認識或無能為力的情況歸於天命,也是對宗教起源的一種深刻説明。因此,劉禹錫的《天論》,不僅在中國無神論思想的歷史上,而且在中國一般社會思想發展史上,都應有自己重要的地位。
韓愈、柳宗元和劉禹錫對天人關係的討論,最重要的歷史作用,就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否定了漢代董仲舒以後的天人感應觀念。柳、劉作為否定者,其論斷越出了儒教所能接受的範圍。後人不能接受他們的結論,但將在他們已經開闢過的土地上耕耘,從天人感應和天人不相預這平行四邊形的兩條邊之間,找到一條合力的對角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