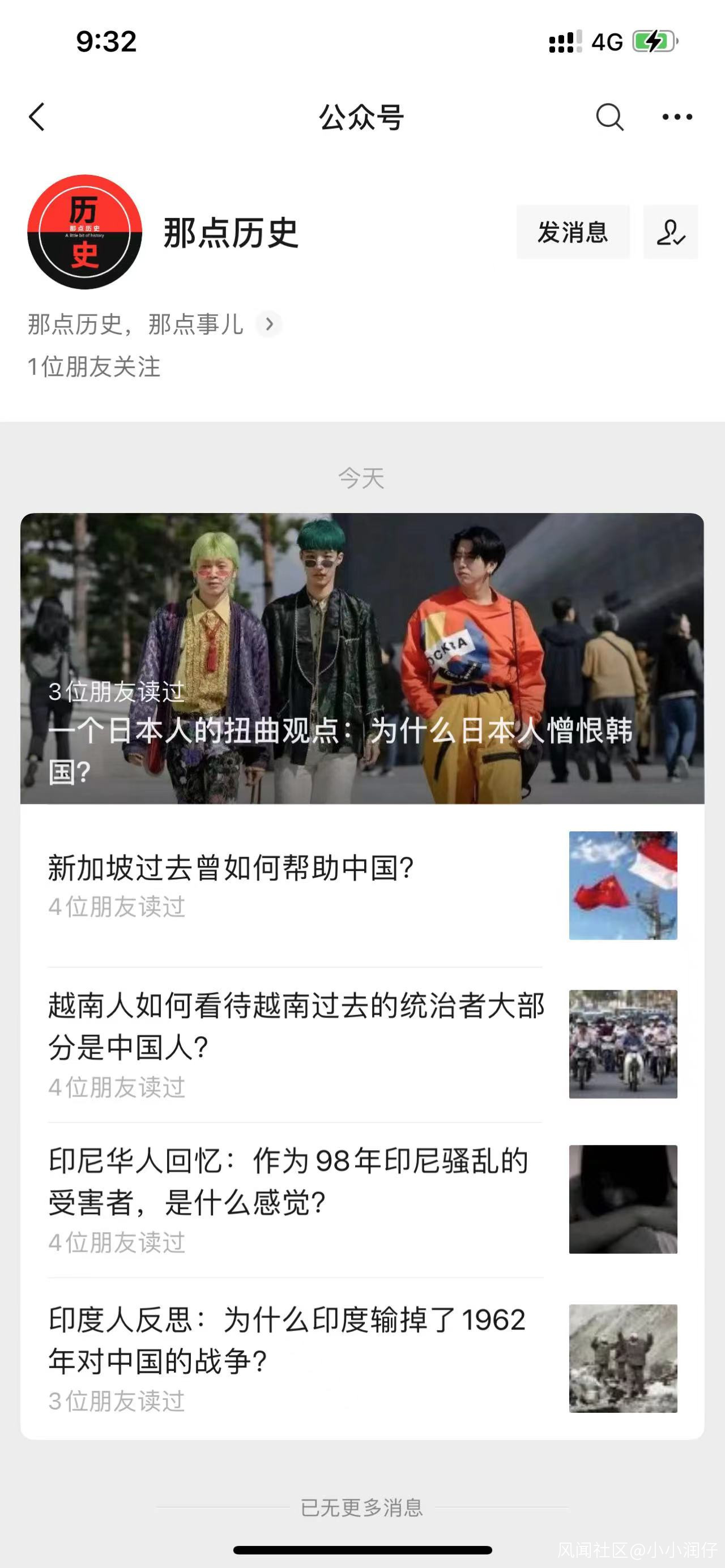印尼華人回憶:作為98年印尼騷亂的受害者,是什麼感覺?_風聞
小小润仔-微信公众号:外国那点事 欢迎关注!2021-11-15 21:39
作為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亞騷亂的受害者是什麼感覺?
What was it like to be a victim of the May 1998 riots in Indonesia?

1. Fiona Liausvia
沒有查詢到該網民的背景信息
騷亂髮生時,我大約8歲。我家住在雅加達郊區,但暴徒經過我們的地區,洗劫了他們能找到的所有商店和超市。這是我根據我的經驗可以告訴你的。
雅加達郊區
凌晨兩點左右,媽媽把我和弟弟叫醒,讓我們收拾衣服。我把我的聖經裝在一個小箱子裏,就這樣。我們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但我們跟着她走了。我媽媽帶我們到我們家後面的花園,那是位於山上的。我們爬到了那裏,我媽媽讓我們留在那裏躲起來。我還依稀記得她當時説的話。
“如果暴徒來襲擊我們, 你帶着你的弟弟, 爬上那堵牆, 躲在那裏.”
“如果我碰巧被人強姦,被人襲擊,你就帶着你的弟弟,去爬那堵牆。”
“如果有人問你國籍,你就説你是印尼人,不是中國人。”
“戴上這個帽子,把臉藏起來。”
她就下去了。
我們當時住在一個住宅區,那裏的人大部分是印尼土著。那天晚上大家都沒睡好。我父親拿出他的打鳥獵槍,那晚我們都知道了,幾乎所有的鄰居都有打鳥獵槍。
我為我們的鄰居同胞感到驕傲,甚至到現在。住房區的所有男人都帶着他們的任何武器出去,站在我們住房區的門前。他們威脅説,如果暴徒決定進入我們的住宅區,他們就開槍。
當天我們沒有發生任何事情,多虧了我們住宅區所有勇敢的父親。所以我們安全下來,在家裏呆了一天。
在我的印象中,我所在的地區是這樣的。
我們在家裏呆了幾天,然後我們聽到了關於我們朋友的消息。一家被突襲商店是屬於我們的一箇中印混血朋友的。之後他們就搬到了新加坡,並決定再也不回印尼了。是的,我們的一些朋友在他們的房子被突襲後搬出了這個國家。這對他們來説是一個創傷性的經歷。
其中一家超市被燒燬,因為老闆拒絕打開大門。
另一家超市大開大門。暴徒來了,拿走了所有的東西,然後離開了超市。
雅加達
騷亂髮生時,我奶奶住在雅加達的親戚家。她聽説暴動的消息後,擔心地病倒了。當時雅加達非常危險,但我父親把車開到城裏,把母親送回了我們家。因為她病得很重,站不起來,所以我們從鎮上送她回來後就直接送她去醫院。聽媽媽説,我父親開車穿過暴亂的人羣,他們對我父親的車進行了敲打。有人看到有人從超市搬電視出來走在路上。但後來,他還是成功通過了,並把我奶奶帶回來了。
結局
這是我的故事,從我的角度來看,我必須承認,我從來沒有把暴徒看作是想趕走印尼華人的土著印尼人的代表,他們可能是那些’從暴亂中獲益’的人。他們可能是一些人’利用’暴亂的情況下進行突襲和搶劫……並使事情變得更糟。我不認為他們襲擊商店或超市是基於種族的原因,因為被燒燬的超市屬於印尼土著,而被遺漏的超市屬於印尼華人。我們的鄰居由99%的印尼土著和1%的印尼華人組成,但我們還是一起出來保護我們的家人。
有傳言説,暴民可能是有人故意製造的,但也許在暴動的情況下,暴民也可能是自然形成的?我到現在還完全不知道,但我知道,這不是印尼土著與印尼華人那麼簡單。
2. Jonathan Yang
户外和動物愛好者;2016年至今行政營銷
Outdoor and animal enthusiast; Administration Marketing 2016–present
這是我母親懷我時的故事。
那時候我家裏很窮,我媽懷我的時候也一直在工作,走街串巷賣一盤餅,我爸用豬皮做了一種油炸的小吃,騎着一輛破舊的自行車在城裏賣。
後來發生了騷亂,我母親不能工作,父親只能按客户的要求出去送單。那個月他們的錢很緊張,因為他們不能好好幹活。更糟糕的是,母親突然跪在地上,忍受着肚子的疼痛,父親在外面送單,母親沒有手機,因為手機很貴,電話費就更不用説了,所以她無法聯繫父親。幸運的是,我母親的一個忠實客户,一個非常善良的中年婦女(阿姨)正在他們家做客,她馬上叫了一輛人力車把我母親送到醫院。
另一個不好的地方是,最近的醫院是,需要30分鐘的路程,是一家非常、非常昂貴的醫院,可以稱得上是當時的富人專用醫院之一,它叫Atma Jaya醫院。阿姨在電話亭裏跟我爸爸聯繫,他嚇了一跳,當他想衝過去的時候,又發生了暴動,逼着他回家。
媽媽把我平安地生下來了,但我是早產兒,醫生説要把我放在保温箱裏,要等兩個星期。幾天後,騷亂開始平息,我父親馬上去醫院看望。現在又出現了另一個問題,醫院的費用非常高,以我父母當時的收入,他們至少要工作10年,這大約是3000萬印尼盾(當時的匯率是2600美元吧),要知道,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數目。我的父母拼命的向親朋好友借錢,也沒有人理睬,甚至連自己的姐姐和哥哥,他們連借一點錢買一盒牛奶都拒絕。幸好,好心的阿姨設法説服她的朋友借給我父母一筆錢,足夠支付所有剩餘的賬單。
在保温箱的一天結束後,母親準備用出租車帶我回家,因為父親有急事,而好心的阿姨又很忙,父親擔心會有不好的事情發生,就給了她一些額外的錢,結果真的騷亂又發生了,原本路上沒有人,突然熱鬧起來,人們試圖搶劫商店、房子、搶劫華人。出租車司機馬上停下車,讓我媽下車,他怕他們發現他的車內有華人,會受到牽連。我媽媽正在哀求,但司機轉為憤怒,我媽媽抽泣着,不情願地從車裏走出來。
她慢慢地走着,想從公園裏溜走,突然有人叫她,我媽嚇壞了,她以為自己被發現了,原來叫她的是一個華人,我媽很高興,聽完我媽的故事,那個人説要帶她回醫院,因為帶我媽回她家很危險。我媽媽在醫院裏躲了一個星期,護士很善良,她是以前照顧我媽媽的人,她給我媽媽提供了食物和幾條温暖的毯子,讓我媽媽在大廳裏睡覺,因為有很多病人和暴亂中的傷員,她不能自私。
一個星期後,情況平靜下來了,我爸爸不能去接她了,因為他也在接一個難民,突然在他附近發生了騷亂。母親沒有叫出租車,而是用Ojek(類似於出租車,但用的是摩托車),為了掩蓋她白皙發黃的皮膚,她用寬鬆的大外套、長袖襯衫和口罩包住腿。不幸的是,又一次發生了暴動,但這次的地點離醫院很遠,我媽不能回去,司機想走另一條路,但被暴動分子堵住了。
第二次,司機讓我媽從車上下來,她照做了。忽然,其中一個暴徒看到我媽媽可疑,大喊 “華人!",人們開始追趕她,我媽媽扔掉自己的東西,抱着我拼命地跑,她找到一個空的崗亭,躲在裏面,她能聽到他們大聲地談論 “她在哪裏?",“找到她!讓我們強姦她!”
突然有人注意到我媽在崗亭裏面,是一個棕色皮膚的老太太,我媽和老太太互相對視,她怕老太太把自己的位置告訴暴徒。“喂,你,你有沒有看到一個華人女人從這裏經過?“騷亂者粗魯的問老太太,“我沒看到這裏有華人 “,老太太笑着搖了搖頭。騷亂者開始從這裏散去。
她把目光轉向我媽,低聲説:“跟着我,他們走了”。我媽媽疑惑的看着她,“如果你不想死,那就跟着我”,老太太催促我媽媽。我母親意識到,如果她想害她,那就可以在一開始就害她,所以她跟着她進了一個小巷子裏的小房子。裏面有一個老人,應該是老太太的丈夫,出乎意料的是,這對老夫妻對我媽很好,最後她在他們那裏避難了兩天。那個小房子裏只住了2個人,他們的孩子已經有了自己的家庭。
老人説要送我媽媽回家,還帶了一車雞。我媽跳上後面的車,和雞混在一起,而我則被老太太抱在車前。在他們到達目的地後,附近有很多暴徒在守衞,他們是由其他華人花錢僱來守衞的,他們中的很多人拿着砍刀和武士刀,有的甚至還準備了雞尾酒炸彈(不知道那個華人是誰,花了多少錢租來的這些暴徒)。
我母親感謝他們,説總有一天會報答他們。那對夫婦只説 “在這混亂的日子裏,互相幫助是天經地義的事,不必太在意”。
在我9歲那年,我們家事業有成後,母親帶着我們一家人又去找那對老夫妻,但當我們走進那對老夫妻居住的地方時,已經被毀壞,換了一家店面。直到現在有時我媽還會説起那對老夫妻。
3. Jessica Lim
2018年至今,Sociolla公司產品經理;S.Kom信息技術和Oracle數據庫專業,比努斯大學,2012年畢業;住在印度尼西亞
Product Manager at Sociolla 2018–present; S.Kom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Oracle Database, Binus University Graduated 2012; Lives in Indonesia
我當時7歲,我弟弟5歲。我們住在機場附近,但為時已晚,無法逃脱。我的父親試圖把我和弟弟送到我們的親戚那裏去,去坤甸。但我們逃不掉,因為去機場的路都被封了,所以我們只能呆在家裏。
我們的家位於 “土著"住宅區附近。幸運的是,他們都是好人。包括我父親在內的所有男人都帶着兩把砍刀守在我們家門口。我從所有的人和收音機裏聽到,暴徒已經在我們的住宅門前了。
我媽媽給我穿了三層衣服,因為當他們想搶我們的衣服時,我們下面還有一些衣服。我們穿着衣服和鞋子睡覺,當他們來的時候,我們必須做好逃跑的準備。父親每天早上總是一邊聽廣播一邊磨着砍刀,每天晚上守着大門。
直到那一天,我都不記得日期了。他們是在羅摩衍那樓完成屠殺後來的。這是一個市場,他們把華人鎖在裏面,並燒燬了所有的建築。沒多久他們就會到我們這裏來。
3天后,騷亂平息了。但我們仍在為一切做好準備。這對我們的父母來説是一個創傷,即使是現在。他們總是建議我小心土著,不要和他們做朋友,他們生活在恐懼中。
當我23歲的時候,他們告訴我,在暴動前7天,我父親幾乎不能下班回家,因為所有的路都被封鎖了。然後他們去了市場,拿走了所有能給我們吃的東西,因為我們不能出去。在市場裏,大家像瘋了一樣。那時候,我什麼都不懂。我只知道父母為了保護我們的安全,沒睡好覺。尤其是我,因為我是個女孩,騷亂者喜歡強姦所有的女人。我仍然記得那天的情景。
4. Diaz Flamberge
住在印度尼西亞
Lives in Indonesia
那時我8歲,不在雅加達,我住在廖內。
我記得那個時候,是下午3點左右在學校。我坐在靠近窗户的地方(我的教室在二樓),有時候上課無聊的時候就會往外面看。那天晚上,我看到大約有5-8個人跑到學校後面的街上。那條街上的居民大多是華人。這些人拿着砍刀跑到某個房子裏,用它砸房子。喊叫聲很多,我看到他們把那家人拉出來。我對着老師大叫,讓她知道我看到的情況。當她來到窗邊的那一刻,她命令我們所有人拉下窗簾,聚集在黑板附近。我們可以聽到尖叫聲,大部分女生都捂住了耳朵。
老師走了,可能是告訴別人和校長去了。老師回來後,命令我們收拾東西,因為父母要來接我們。我記得爸爸叫我走快一點,就跑到車上(我們那輛藍色的老皮卡)。我從來沒有見過他開得那麼快。我們跑過了紅綠燈,當我們經過回家的路時。我看到人們到處跑,大喊大叫。
在家裏,我們把自己封鎖起來。我們家的柵欄是用木頭做的,所以暴徒來的時候不會有什麼阻礙。從那天開始,我們從不開燈,只靠蠟燭。所以從外面看,主人不在家。
我們真的很感謝我們的鄰居們,他們大多是穆斯林,他們非常合作。他們照顧了所有住在那裏的華人。暴徒們從來沒有來過我們的街道,也沒有洗劫過任何房子。他們要求我們所有的人把在屋外祈禱的東西都拿下來,比如香爐或鏡子。如果暴徒真的來了,他們會説我們是他們的親戚。
我和我的兄弟姐妹被禁止外出,宵禁時間是下午6點。我們也不允許看報紙和看電視。媽媽在家裏儲備了大米、方便麪、雞蛋、肉類、水。我記得我的遊戲室有好多箱子,我可以玩爬山。也是在一天之內,我們有那麼多的電話,第二天就完全沒有聲音了。
等我長大了,懂事了,我問媽媽那天發生了什麼。她説雅加達發生了暴動,其他省也發生了幾起。大規模的強姦和殺人。她還説,我在香港的叔叔讓我們逃亡,住在香港,我爸爸的生意夥伴也是這麼説的,讓我們都搬到新加坡去,他會幫忙解決住房和工作。但我父母都拒絕了,因為,第一我們沒有錢,第二我父親不能離開工作,第三即使能離開,生活費也很貴,我們也活不了多久。所以結論是我們把一切都交給命運。
現在古斯-杜爾總統之後,情況肯定會有所改善。但我仍無法在中學獲得獎學金或參加科學競賽,或者我必須支付額外的現金來更新身份證,護照和駕駛執照。
5. Mellisa Tjee
廚師;東英吉利大學語言與跨文化交流專業碩士,2012年畢業;2011年至今在聯合王國的生活
Chef; M.A in Language and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 Graduated 2012; Lives in The United Kingdom 2011–present
沒有多少人知道,騷亂不僅發生在雅加達。騷亂髮生時,我在梭羅,我的城市因騷亂者搶劫和燒燬建築物而被燒燬。他們留下了破壞的痕跡。我們看到了他們的到來。
我和我的家人都在家看新聞並保持警惕。我們被告知要小心,因為暴徒正朝我們的方向走來,但我們希望它不會來找我們。
我記得我們附近的電影院被燒了,我們躲在裏面,同時聽到一小羣暴徒經過我們的街道。我們的一些員工(也許是假裝成他們中的一員)告訴這些人,裏面沒有人,沒有東西留給他們。幸運的是,這些人相信了這個謊言,走了,但在向我們的窗户扔了一些石頭之後。
那天晚上,我們在黑暗中睡覺,因為我們相信暴亂者會回來。我不記得發生了什麼事,但我問過我的姐妹們,她們説那天我們在天亮前第一時間得到了家教老師的幫助,搭上了車,逃到附近的醫院去避難。按理説,沒有人類會襲擊醫院,醫院本來就是一個安全的地方。
第二天,又發生了一場騷亂。附近的幾家工廠被燒燬。在醫院裏面我們就能聞到它的味道,很恐怖。我父親接到了 “朋友"的電話,他被告知需要做好逃跑的準備,因為暴徒要來醫院了。
醫生和護士是我們的英雄。他們沒有逃跑,而是在外面設置了人肉路障,確保這些動物不會打擾裏面的人。要知道,不僅是我們這些難民,醫院裏還有老人、病人和剛出生的嬰兒。
記得那天下午,媽媽把我帶到一個房間裏,把護照給了我。她告訴我,要儘量和姐姐、弟弟在一起,如果和父母走散了,就逃到新加坡去。她把現金塞進我的口袋,還讓我穿幾層衣服,以防這些暴徒也是強姦犯。
這真是令人作嘔。
幸運的是,這些暴徒沒有去醫院攻擊,也許是因為他們認為反正也沒什麼好搶的。也可能那個時候蘇哈托已經決定下台了。我也不知道,我也問過自己,但這對我來説已經不重要了。
但重要的是,當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已經是悲劇發生後近20年的事了,但從來沒有進行過適當的調查。關於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誰要為謀殺、強姦和破壞負責?
什麼都沒有。
6. Anonymous
匿名,沒有查詢到該網民的背景信息
那時候我還只有4歲。我什麼都不記得了,但我聽我父母和他們的朋友們講述了那件事。我的家庭並沒有受到什麼影響,只是我爸爸不得不關門幾個星期而已。
我爸爸當時有很多朋友,其中有一個是印尼本地的高級士兵。軍官給我們派了(我想)5個士兵,全副武裝,步槍。我們的建築羣很安全,非常安全。鄰居們很高興,給我們送來了米、食品、水和其他種類的雜貨。
鄰居們設立了siskamling(環境安全系統),這是一個安全問題的公共工作,基本上你必須在特定的時間內自願在建築羣周圍巡邏。我姐姐告訴我,她還記得發生的事情,她給我們的鄰居送了一杯咖啡。
我們的鄰居大多是印尼華人,我們住在雅加達一個昂貴的建築羣裏。那些印尼土著幾乎就要到我們的小區來殺我們。然而,我們全家都為我們的安全祈禱,感謝上帝沒有發生任何事情。
他們看到了發生在我們小區外面的事情,一羣人帶着電視、鋼琴、冰箱,最讓我們毛骨悚然的是,這些人很瘦小,卻能帶這麼重的東西。我們很確定,這些人是從附近的教堂偷來的鋼琴。
我母親帶着為她工作了幾年的印尼本地司機,現在他已經為我們工作了21年,在幾個士兵的陪同下,去超市買菜。大街上空無一人,但她看見到處都是血,乾巴巴的血。我很驚訝,有些超市還在營業,大概是暴動後幾個星期,人們才可以安全出門。
過了幾個星期,有些人勇敢地走出家門,之後越來越多的人出門,雅加達又變得擁擠起來。
買張機票,飛到新加坡,非常昂貴。聽説有人把寶馬賣了,只賣了2500元,我不清楚,就為了飛去新加坡或香港。房產很便宜,印尼盾價格大幅下降。現在,那些印尼本土人因為印尼盾價格跌成那樣,就怪我們華人。總之,問題是如何安全地開車去蘇卡諾哈達機場安全。
騷亂分子可能會攔車砸車,你就死定了。
我還聽過很多故事,一個父親殺了自己的家人,然後自殺,就是因為不想讓那些印尼土著殺了自己的家人。
還有一個故事,一對母子要呆在頂樓,鎖上門。騷亂者讓他們開門,否則就燒房子。他們因為火燒而死,他們死得很有尊嚴。
還有一個故事,那些印尼土著強姦了一個5歲的印尼華人女孩。然後,其中一個家庭成員,一箇中國女孩沒有被強姦。他們告訴她,他們沒有強姦她,因為他們已經滿足於強姦其他女孩,而且因為她很醜。
我現在永久居住在加拿大。上次我們聊到暴動,其中一個人,告訴我們,那些暴動者已經攻破了她的房子,準備強姦她,她的姐妹們,把她們全部殺死。她的爸爸卻把狗放了出來,只有兩隻狗,但暴亂者卻走了,因為狗是哈拉姆。在穆斯林,如果狗的唾液接觸到你的身體,你要洗好幾遍,他們怕髒。
有的人逃到香港,結果幾年後,因為找不到工作,做不了生意什麼的,把他的錢都賠光了。要想從印尼搬出去不是那麼容易的,如果可以,我們早就搬出去了。
有些印尼華人很幸運,在美國獲得了難民身份。他們在翻譯的陪同下,做了一個演講之類的事情。出乎意料的是,很多印尼土著都在罵他們,説 “你們是這個國家的叛徒”,“你們只是以暴動為藉口移居美國”,“狡猾的華人"等等。
有時候,我很想知道這些騷亂者的腦子裏到底裝的是什麼。
沒有調查,印尼警察沒有動手,我們也無能為力。
我真的為受害者感到難過。如果可以的話,我願意保護他們,甚至為他們而死。我看了其他的答案,我想流淚。
7. Aditya Januarius
2018年至今市場總監;2015年畢業於墨丘布阿納大學;住在雅加達
Marketing Supervisor 2018–present; S.Ds from Mercubuana University Graduated 2015; Lives in Jakarta
我自己和我的整個大家庭和親戚都從那次事件中倖免於難,但我住在芝萊杜,那裏的土著對華人很有侵略性,我還記得我的朋友很少有逃到其他城市或國家的,而我的家人沒有機會逃出來,因為我們在其他國家沒有親戚。但上帝為我的家人制定了不同的計劃。我家附近的人完全保護了我的家人和附近的人的安全。
我記得我爸爸和他的學徒每天晚上都會和其他人一起在街區裏走來走去,以保證街區的安全,因為我的街區離Ramayana Ciledug很近(現在已經被燒成灰燼,重建為Plaza Ciledug),而且離雅加達外環路(Rawa Buaya)也很近,這讓我的家人更難逃離。
但是,再次感謝我的鄰居們,他們非常友好,我們作為孩子從來沒有被教恨土著,甚至對我們的隔壁朋友。
但同樣的,如果你問我那天有多可怕……完全在我的腦海裏烙下的印象。我記得我媽媽顫抖着和我爸爸帶着砍刀還有其他男人一起出去保護我們的街區。
我媽媽的女傭(我們用女傭,因為我媽媽是一個裁縫,需要有人照顧我的小弟弟,他大約2歲)把我和弟弟緊緊地抱在卧室裏,而我媽媽準備了滿滿一箱子的證書,一些珠寶和一些現金。
我還記得我打電話給學校(我的天主教學校是Sang Timur Ciledug),其中一個修女告訴我不要去學校,因為他們關閉了大門,只對該地區的土著家庭開放。
我和我的親戚朋友失去了幾天的聯繫,因為我爸爸告訴我不要給別人打電話,因為電話意味着一個信號,接收電話的房子是一個華人。
我甚至記得,當我在回家的路上,特別是在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時候,人們會用眼光來評判我,所以我生了幾天的悶氣。
8. Joe Lee
教師;在比努斯大學學習;住在雅加達
Teacher; Studied at Binus University; Lives in Jakarta
一切都是從下午開始的,大概在2、3點鐘左右,我家門前平時熙熙攘攘的馬路突然變成了單向的(本來是雙向的馬路),當時我們家已經做好了準備。我媽媽儲備了很多食物和水,我們把房子鎖好、設好路障後,就躲在閣樓裏。
當時一片混亂。我記得火焰在我家對面燃燒。人們尖叫着求救,掠奪,像瘋狗一樣到處亂跑。
我只記得有人在砸我們的門,試圖強行進入,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和隔壁的土著説:“這個華人很好!沒必要殺他們!“我現在已經在地下6英尺了。
第二天,我們都不能出去,食物都很匱乏。有故事説,有的人一天煮一包方便麪,供一家人吃。我家由於我媽之前大肆購物,才免於那種情況。
後果是毀滅性的。印尼盾價值跳樓,所有物價飛漲,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這些所謂的 “內陸人"在做檢查站,把過往的華人分門別類,如果發現一個,就去割斷他們的喉嚨,或者我不知道,我不敢想象。
我不明白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也不明白為什麼情況會從一些學生的死亡發展到這種種族滅絕。但我知道一件事:如果這種情況再次發生,我們的國家將陷入 “真正的印尼人"和 “華人"之間的全面內戰。
現在情況確實好轉了。我們可以自由地表達我們的信仰(雖然我是一個基督教徒,但我擁抱我的傳統,我仍然會偶爾去拜祭我的祖先),我們在很多方面都得到了更多的自由,比如政治。
我記得人們説這是因為他們認為 “華人佔據了我們的經濟”,“內陸人應該照顧我們的經濟,而不是這些異教徒的華人”,但他們似乎忘記了一個事實:那時,由於蘇哈托的新秩序,我們不能做太多事情。
你看,那時候我們被壓抑得很厲害。普通話被認為是非法的,中文學校被取締,中國新年幾乎被禁止,等等。
沒有什麼可做的,我們能自由做的就是在經濟上,成為一個商人。由於我們的天性,我們茁壯成長,我們繁榮昌盛,你們可能都知道,我們大多數人都很有天賦,有很好的商業技能。高賣低買是我們的血液,我的爺爺奶奶常説。正是由於父母給我們的那種嚴酷的教育,我們才學會了比誰都要努力工作,我差不多感覺到了過去那些捱打的好處,因為現在我長大了。
現在,大多數的土著都不是那麼仇視我們,但還是有一些盲目的沙文主義者仍然仇視我們,甚至教他們的孩子仇視華人。我記得在我上初中的時候,有一些孩子就因為我是華人而躲避我。我仍然看到人們因為我們在經濟上的主導地位而憎恨我們(記住,這是由新秩序給我們帶來的麻煩造成的),甚至試圖和我們玩宗教遊戲,告訴華人是異教徒。
只是可悲的是,有些人為了自己的利益,拒絕思考,只願意被一些所謂的宗教領袖洗腦。現在,宗教法西斯主義與種族主義結合在一起,在這裏醖釀得熱火朝天。我只希望98年的暴亂不會再發生。畢竟,我們華人已經不是那個 “華人"了。認為僅僅因為我們是少數派,我們就可以被推來推去,這是不公平的。
9. Anonymous
匿名,沒有查詢到該網民的背景信息
我真的很害怕,事發時是在晚上,我父母的倉庫是受害者。人們聚集在大門前,想把它推倒。
幸運的是,我爸爸很快就叫辦公室的人(好心人)把電關了,所以最後衝進來的暴徒,看不到裏面的東西。他們只拿走了涼鞋,手機,和一些不值錢的東西。
同一天晚上,在我住的房屋,我們建立了一個路障來保護自己。沒有警察,沒有軍隊,沒有政府的支持,這是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我們選擇了自己的武器,比如棒球棒,高爾夫球杆,棍子,任何能阻止暴徒的東西。
他們終於來了,一直在外面等待的暴徒開始了戰爭。我們緊閉大門,從裏面對暴徒進行打擊,沒有傷亡,只有受傷的暴徒。現在,這才是最瘋狂的部分,暴徒向我們要錢去醫院?你相信嗎?
我們不能忘卻。
============================
想看更多精彩內容,請關注公眾號:那點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