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生窮困,沒有一首原創歌曲,卻無數次拒絕「名利雙收」的機會_風聞
哎呀音乐-哎呀音乐官方账号-一直想学习一门乐器,却不知从何开始?来!我教你呀2021-11-19 14:13
多年後趙已然接受採訪時,慢悠悠點上一根煙,激動的跟記者説:“我他媽的是個天生的戲子,在舞台上的一切都不用人教。”
這句話沒有任何吹牛逼和扯謊的成分,後來人們評價他的時候,有人説趙已然吉他不行,有人説趙已然唱功欠佳,但絕對沒有一個人説趙已然不會表演。
表演是他最大的拿手好戲,在三里屯的河酒吧,或是五道口的開心樂園、愚公移山、麻雀瓦舍…在任何一個毫不起眼的舞台上,這個蓬頭垢面的奇怪老頭拿起了琴,平日沒個正形的臉上霎時凝結了一層數九嚴霜,歌聲一起,情緒流水般肆泄。苦難以一種悄然的形式,住在他的歌聲裏。
台上人動情,台下人唏噓。
《再回首》
於是,這個“一生沒有一首原唱作品的”搖滾歌者趙已然,憑藉“鮮明的性格和亂七八糟的經歷本身”,給翻唱的歌曲賦予了反哺意義,從而讓歌曲多了故事性,久而久之成了“風格”,他“趙老大”的名號,也因此越叫越響亮。
「沒一首原創歌曲卻被稱作傳奇」,這是趙已然常常受到噓聲的最大原因。趙已然是個“沒活明白”的人,身上有太多矛盾,時代和個人性格的問題在他身上作祟,把他弄得傷痕累累。
記者採訪他,他一開始便煞有介事地説:我回顧這人生的50年,能想到的詞語,只有美好一個,一切都是美好的,那些苦難也是美好的。
然後在採訪的結尾,他不禁眺向遠方忍淚。這個時候我們才意識到,原來人們最着急掩飾的,反而是最不堪的秘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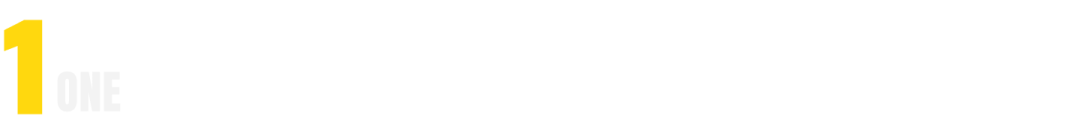
走上搖滾之路
生在解放運動盛行的60年代,生在饑荒遍佈的寧夏小縣城,自由、反叛、生機勃勃,這些詞語刻在趙已然的性格里野蠻生長着,因此給他一支麥克風,他就能表達,能嘶吼着靈魂唱歌。
趙已然從小學三、四年級就開始登台表演歌舞,11歲時精通拉二胡,很快就隨着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在各地巡迴演出。
時代的弊端也附着在這一代人身上:特別理想主義,特別嚮往自由。
類似於西方的嬉皮士,自由,放蕩,無政府主義,音樂作為玩樂的形式,就是他們生命的全部。
1977年,國家高考恢復,隨後第三年,趙已然考上了陝西師範大學化學系,選擇與音樂不相干的理科之原因,無人得知,大概是想再物資匱乏的年代留一條後路。如他所想,畢業之後被分到了銀川化肥廠的教育科上班,有了份穩定的工作。
可趙已然沒法忍受踏實枯燥的社畜生活,早在上學期間,他就自學打鼓,開始在學校內外演出、賺外快,跟着朋友走穴;畢業後更是屁股挨不着辦公椅,跑出去和本地的一幫大師們在銀川組了個樂隊辦舞會、辦吉他班。
化肥廠的工作很快就沒幹了,趙已然又回到大學時的走穴生活,賺着一筆一筆的小錢,活一天是一天,期待着出頭之日。
東方紅劇院在新華街上,劇院門口還有個茶館,被稱為好幾代流氓的總部。東方紅劇院對面是銀川劇院,是寧夏秦腔劇團的舞台,也是趙已然的家。
到了晚上,趙已然會和郝建寧等一大幫子人組成樂隊伴舞。但大家都不願意讓他打鼓,因為他總是動不動就把人家的鼓皮打爛,不好買也不好配。
每當趙已然披頭散髮穿着拖鞋奇形怪狀的在街上走着,流氓們就會高喊:鼓王,幹撒起那?
趙已然露出無賴的笑容,説他才不是鼓王,他弟弟才是,他是文人顏峻。
趙已然有個弟弟叫趙牧陽,比趙已然小四歲,也擅長打鼓。87年的時候被音樂人常寬從西安帶到了北京,一年後加入了東方歌舞團。
1989年,趙已然呆在銀川的音樂之路毫無進展,他打算去北京碰碰運氣,彼時,在北京的趙牧陽已經是北京搖滾圈的名人,人稱“西北鼓王”。
趙牧陽那時和常寬等人組了支樂隊,叫“寶貝兄弟”,一夥兒總在東方歌舞團排練,旁邊就是撥着吉他熱場的崔健。趙牧陽看到哥哥趙已然來了,開玩笑説:哥你拿把琴跟我們一塊兒玩嘛!
趙已然愛玩愛熱鬧,提着把吉他就上了,沒想到後來越玩越嗨,還成了“寶貝兄弟”的吉他手,這算是趙已然第一次在樂隊裏找到了個穩當的定位。
但趙已然多叛逆,多理想化啊。十月份的時候,趙已然看青藝小劇場演出:蔚華加入的“呼吸”是馬禾打鼓,常寬的“寶貝兄弟”是牧陽打鼓,還有老五哥、劉君利的“白天使”,以及“眼鏡蛇”等六七個樂隊。
趙已然説:我操,這還了得?
於是,趙已然把吉他撂了,從那個時候開始正兒八經地做一個鼓手。
當時他已經26歲了。
“我知道如果不是小時候就開始學的話,想達到一個高度特別難。鼓呢,我拿上就會打,但我想趕上別人的水平。”
趙已然做事風馳電掣,沒幾天就組了個樂隊叫“紅色部隊”,陳勁擔吉他主唱,他打鼓。
這支樂隊籍籍無名,兩首歌有點水花,一是魔巖挑樂隊拼盤,在《中國火Ⅰ》收錄了他們的作品《累》,“太陽在天上放着光輝,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另一首在陳勁的專輯《紅頭繩裏》裏,叫《逼上梁山》。
紅色部隊沒幾年就解散了,因為沒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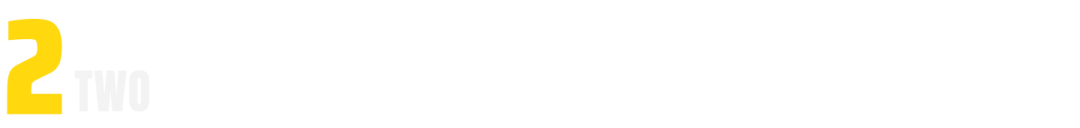
被稱為趙老大的那些年
俗話説的好,錢不是萬能的,但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沒錢做不了音樂,排練場沒地兒租,設備也買不起。
於是1991年,趙已然南下去了深圳,又幹起了走穴的活兒。
在中國南方,趙已然第一次感到人與人精神之間的那種差異,被眼前商業文明社會深深震撼。
“我到那是為了掙錢,但那裏的環境對我來説太不合適了,沒有精神生活,沒什麼朋友,就是喝酒”。
精神空虛,就在物品上找寄託,趙已然酗酒的毛病癒發嚴重,經常喝到神志不清在大街上躺着,恍惚間跟混混打起架來。
深圳賺不到錢,這時「紅色部隊」的前樂手給趙已然打電話,説可以來閩南試試——這個地方太可笑了,一天能掙一千。
趙已然聽完嗤笑一聲,不信。
對方説:“你來把,帶幾個人,路費我出,如果來了不喜歡這裏就當玩一趟。”
趙已然去了,對方並沒有騙他。
“這個地方太瘋狂了,我去的不是最好的場子,但樂隊每天每人能掙七八百。要是哪天掙了三五百,他們就生氣,説今天不好”。
趙已然有個名號叫“趙老大”,這也是從閩南開始的。
閩南給了他足夠大的舞台,來給他捧場的人絡繹不絕,名聲就這樣唱出來了。
趙已然最喜歡朋友,最喜歡江湖義氣,那幾年,全國各地包括上海、安徽、淮南、淮北、四川、內蒙等等,絡繹不絕一茬接一茬到那裏淘金的樂手們都去“投靠”他。
趙已然幫他們湊樂隊,湊歌手,湊齊了帶他們去找老闆,老闆看上了就開始駐場唱歌。
這樣,老大的名聲出去了,全國各地更多的的人開始投奔他。有些樂手在那等機會一等等幾個月,都靠他養着。
1990年代初,全國掀起了考試風:各地的歌手樂手需要通過考試才能上崗在酒吧唱歌。閩南也不例外,當地四條街大概三百個樂隊,上千個歌手,把禮堂塞得滿滿的。
而趙已然的那場考試,按現在流行的説法,就是把跨年開成了個人演唱會:本來禮堂裏只有前面一排文化局的人,考着考着,發現禮堂人越來越多,直到擠滿,窗户外也站滿了人。
趙已然一首歌結束,掌聲雷動。
結束後,文化局局長走到台上跟趙老大握手,激動地説:感謝你給我們石獅鎮帶來了文化!回憶起來,趙老大説:“笑死了!”
那年,趙已然掙了一百多萬,中間給母親寄過一萬,一年後回北京時身上剩幾萬,給兄弟買了些禮物,其餘的在那裏全部花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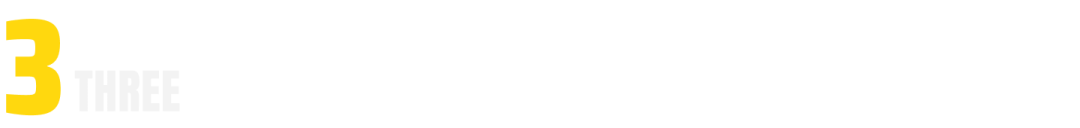
純粹的歌者
在閩南混得不錯,但1993年,趙已然又回了北京。
“你問我為什麼回?我該回來了,我呆夠了!”你説這人任性不任性?一次又一次地,把稍微穩定的生活打碎。
沒想到一回來,發現一切變樣了,一起混的朋友們都飛黃騰達,“有的還成天皇巨星了”。
樂隊們玩的東西變了,人們交流的方式變了,
面對這個商業社會,趙已然的第一反應是不適。「當時我還有一些選擇,可以跟着朋友們去掙錢」,但偏執和精神潔癖,還是讓他「莊嚴地選擇了地下」。
1998年春天,他搬去了偏遠的清河,“那地方沒人,安靜,一點點錢就夠我活了”,在那裏,他有了唱歌的衝動。
他湊了套鼓就開始練,每天都打。有一天,他躺在牀上,不知道怎麼回事,突然想起來80年代蘇芮的一首老歌《跟着感覺走》,從前覺得挺俗,現在反到覺得積極,當時趙已然手裏沒有吉他,找隔壁小女孩借了吉他,唱了一遍,覺得特別興奮。
那時候是半夜,他揹着這把吉他走了一個小時的路,打到了車——清河太偏了,直接奔一朋友家,把這歌唱給他聽,這個朋友也興奮壞了。後來他還唱給房東和周圍的孩子們,“他們聽得都特別高興”。
又找到那種純真的感覺了,清貧的日子裏,趙已然再次獲得幸福。
純粹的音樂人其實特別像孩子,有時的執拗讓人發恨,有時候的純真可愛又讓人無可奈何。

專訪截圖
2000年前後,趙已然和一羣人一起生活在北京東邊的農村。幾年的時間裏,寧夏人、山東人,外地的搖滾樂手在那裏出沒,説起來,那地方就叫“院子”,落魄音樂人的歇腳地,像是一個破落的公社。

2001年,北京三里屯南街開了家“河酒吧”,由來自蘭州的民謠樂隊野孩子創立。喜歡民謠的都知道,這裏是中國早期“LIVEHOUSE”的雛形,是中國當代民謠的「母親河」。
野孩子樂隊、萬曉利、小河、王娟、左小祖咒、舌頭樂隊、廢墟樂隊等音樂人常常這兒演出,音樂、啤酒與愛,是河酒吧的主題,那裏就像一個小小的烏托邦。

民謠歌手張瑋瑋回憶曾經在河酒吧度過的美好歲月説,“我那陣子看什麼東西都像隔着一層熱空氣,就是青春的那種巔峯狀態,覺得一切都太美了。”
趙已然後來也成了這個酒吧的常客。不過奇怪的是,他從來沒以歌手的身份出現在酒吧過,“我一直是鼓手啊,唱歌是我的愛好,是私人行為。”
又來了,這該死的特立獨行和執拗。
只有等酒吧客人都走了,只剩朋友的時候,酒過三巡的趙已然才開始唱歌,有一批人,專門等到12點後來,就為了聽他唱歌。
趙已然另一個買醉的地方則是“兩個好朋友”酒吧,12點後,他和樂手朋友一起上台,一般都喝醉了,他閉着眼睛打鼓——舞台上燈光刺眼,也看不清楚下面的情況,打了半天,睜眼使勁一看下面已經沒人了,都走了。
“我打得出神入化,根本什麼都不管”。
“我覺得那時候出來的音樂才是真正的音樂,全是本能嘛!不加理性,不加雕琢,沒時間把理性的東西強加到音樂中”。
這是趙已然一直奉行的理念:純粹無理性的音樂。
要問他不醉能演出嗎,老大説,肯定能。但「本能」是趙老大的關鍵詞。他認為靠本能出來的東西才是真正的藝術。
“我作為鼓手,同一個東西處理的方式和別人不一樣,一般來説,其他鼓手處理的80%到90%都一樣,就那麼個套路,打得順就完了。一般是這樣,我不是。”
趙已然一生只出了一張專輯,專輯的誕生也很奇妙:是朋友趁他表演時在後面偷偷用電腦錄下來的。
開始他還沒有名字。直到有一天,趙已然在河酒吧聽歌,無意間聽到隔壁桌有人問有人問張瑋瑋趙老大怎麼樣,張瑋瑋喊:“那是我們的大哥,那個人啊,就沒活過1988年!“
趙已然一聽,覺得真是啊,他真的沒活過那一年。
“這二十年,我的生活那麼流離,我所有的情感、我的方式、我的世界觀價值觀都一直在那邊(過去)呢,當時因為後來我在拒絕,我拒絕吸收任何知識,拒絕動腦子,拒絕學任何科技的東西。我把高等數學、四年化學本科都學完了,可到現在洗衣機、空調的説明書我看不懂。”
現在的世界比起1988年左右,大變了。
“我在城市裏能不能生存,也可以。我呆在這裏,是因為這裏的藝術,人才,環境,我喜歡。但現在我越來越看不到聽不到我想聽想看的——我甚至找不到我喜歡的音樂。”
1993年,趙已然剛從閩南迴北京、找不到去去處的時候,去朋友開的電器廠當了幾個月看門員,那時他天天打電話問朋友哪有搖滾演出,天天去看,但是以一種局外人的身份。
看了一個月,他沒看到一個好鼓手。他就跟朋友説我要搬走,繼續做樂手做音樂,接着,他就搬到了清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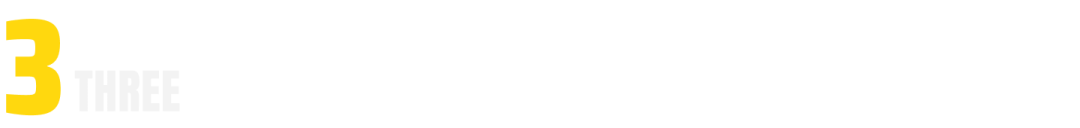
趙已然一生有很多機會獲得所謂的名利雙收,前提是放下那些執念的話。
有不少唱片商找過他,不知道是因為要求做商業化的歌曲惹怒了趙已然還是如何,「都被我罵走了」。

那張《活在1988》本來被趙已然藏起來了,不願意發表,“醜死了!我一直壓着,後來壓不住了,我圈裏人身邊的朋友都有了。”
野孩子的主唱小索説,那些西北的朋友們去他家喝酒,喝醉了放什麼音樂都不聽,就聽趙老大的。
張佺勸趙老大:雖然各方面條件不具備,但既然都錄下來了,別人也願意聽,不妨拿出來賣吧。
趙已然終於點了頭,為了那次演出,他還寫了一段自我簡介“活在1988”——朋友讓他寫,他不知道怎麼介紹自己,就寫了上面這麼一段話,印在海報上,於是有了趙已然最有名的那段自我簡介:
我本該是一名化學教師,陰差陽錯,不幸做了鼓手。十多年來,不求上進,碌碌無為,混跡於狹小的地下音樂王國,沉迷於越來越糊塗越來越荒唐的卡通境地,信以為真地在有限的幾位朋友面前義正辭嚴、斬釘截鐵地鼓吹着“垮到極處”的寄生蟲哲學。從沒有過工作,後以借錢為生。
後來,我慢慢變成了一個人。只有一雙拖鞋、一隻牙刷,住在了農村,且越搬越遠。
再後來,我笑得有些難看了,因為我越來越沒錢。以至於常常被迫求告家人,艱難度日。
有一天,我終於發現,磕不動了,再也垮不下去了。我頭天讓酒喝醉,吐了;第二天一早,酒還沒醒,咣嘰,又讓茶給喝吐了。
那一天,我發現,我的臉特別難看,太難看了。我終於知道,我太不漂亮了。
我一生熱愛漂亮女人,痴情於不敢面對、不敢褻瀆的漂亮女人,然而我自己卻從沒漂亮過,從沒漂亮過一次。
我也知道了,在我所追求的自由中,我沒有自由過一次。
於是,我終於倒下了。
於是,在深夜裏,在不要錢的燦爛陽光下,在只有神或鬼才能看得見的微笑或悲痛中,我想起了那些曾經會唱的歌。
於是今天,被逼無奈,我端正了思想,換了身份,不做鼓手,稍不情願地自覺有些滑稽般地坐在了這裏,懷着年輕時代的美好夢想,準備唱歌。

“從前我們搞搖滾樂,條件極其艱苦,餓着肚子在做,我們那些人覺得自己在做一種革命工作,有意無意中的,把自己設定成這麼一個位置。”
他們不懂外語,不懂搖滾樂在外國發展成什麼樣子,單純地把它跟自由、公正、直言、反叛這些詞彙聯繫起來。
“誰知道這個東西最後還他媽能掙錢了”,十多年後趙已然回過神來,搖着頭自嘲。
趙已然年輕時給自己寫過未來規劃:我要在52歲之前出三張唱片,寫一本書,然後到學校當化學老師去。
誰料到最後連第一個都沒有做到。
**“我試過改變自己的生活方式,改變想法,可是已經太晚啦!我都50多歲啦。”**為時已晚,只能就這樣了。
想起一則趙已然兒時的小故事,關於他的名字。
趙已然一直覺得自己的真名趙牧牛很土,所以他沒告訴過任何人,自己給自己取了「已然」。
父親是個藝術家,摸着他的腦袋問:誰給你取的。
趙已然説是自己,父親聽完皺了眉。
“你知道這名字什麼意思嗎?這名字不好,已然已然,意思是,就這樣了。”
生命無常
謹以此文追念趙老大
(完)
文中圖片來自網絡
封面出處:《醉鄉民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