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金堯 | 歷史學是否已到重提“宏大敍事”的時刻?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2021-11-23 21:58
俞金堯 | 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最近,媒體上熱烈討論關於“文科生太多”的問題。這其實是很一般化的説法。文科生在中國太多了嗎?那要看具體情況。有些專業的文科生可能還不夠,比如國家要實現治理能力現代化,就很需要政府管理方面的人才,這方面的人才恐怕還不夠。歷史學也是這樣,有的方面,如中國史、近代史都很強,但世界史可能相對弱一些。世界史裏也有區別,如美國史研究隊伍兵強馬壯,研究西班牙史、葡萄牙史的則相對缺乏。而當前史學領域最突出的問題之一,就是做宏大敍事的人很少。
現在有個趨勢是大家喜歡做微觀的、具體問題的研究,在後現代主義盛行的背景之下講宏大敍事,似乎不合時宜。但實際上宏大敍事很重要。一方面,宏大敍事是人類的一種內在需求,大到國家、民族、人類,小到個人和家族,我們需要知道它們是怎麼發展演變的。所謂宏大敍事就是人類對於歷史發展脈絡的整體把握,這是人的一種內在需求,自古就有,而不是到近代以後才出現。比如,在歐洲,基督教信仰主導的時代就有基督教的宏大敍事,教會人士根據《聖經》把歷史敍述出來。文藝復興、啓蒙運動以後,就有了現代性的宏大敍事。另一方面,宏大敍事還包含時代的需要,每一個時代都需要有它自己的宏大敍事,我們這個時代也應該有適合時代的宏大敍事。所以,宏大敍事的必要性是不能否認的。當然,我們能不能構建出一個得到廣泛認可的宏大敍事,那是另外一回事。
圍繞中國史和世界史,長期以來歷史學家一直在思考它們的關係。這裏可能涉及一些概念:什麼是世界史?什麼是外國史?世界史是不是對應着外國史?如果不把概念搞清楚,當講到“世界史”的時候,人們心目中的世界史其實就是外國史,而不是真正的、人類整體意義上的“世界史”,那就很難説到一起去。人們使用同一個名詞討論問題,但各自所指的內涵不同,那就討論不清楚。我認為,真正的世界史一定是要用宏觀的視野來敍事,它不能侷限於外國歷史上一些具體問題的研究,也不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曆史的集合,它一定是一個在歷史哲學基礎之上構建起來的關於人類歷史的體系。它不是中國史,不是外國史,也不是中外歷史的集合,它就是世界史,是一個以宏大敍事為特徵的歷史體系。

宏大敍事具有時代性,不同的時代對宏大敍事會有不同的需求。我們所處的是一個“大變局”的時代,世界格局正在發生變遷,從中國的角度來説,這個變遷所帶來的影響尤其明顯,從某種程度上説,主要是中國的崛起推動了世界格局的變遷。這個變局大到什麼程度?相關問題仍可深入討論。但當前的世界正在發生重大變化,無疑是一個客觀的事實。大變局為歷史學進行新的宏大敍事創造了條件,也提出了新的問題:原來的世界格局是什麼樣的?它存在了多久?它的基礎是什麼?世界格局的變遷需要經歷多長時間?當前大變局的歷史背景和發展趨勢如何?世界歷史上發生過多少大變局?這些變局對今天有什麼啓示?未來形成的新的世界格局,是由變遷中的現實所決定的,還是開放而不確定的?等等。這些事關時代變遷的問題,都與世界歷史有關,而且也只有在宏大的歷史進程中才能進行合理的解讀。例如,要全面認識“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就不僅僅要了解當代的變遷,還需要認識歷史,至少需要回顧一個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進程,才能看清正在變遷中的世界格局的樣貌和特徵,以及正在發生的變遷的實質。實際上,當今的世界格局是在過去五個世紀左右的時間裏形成和發展而來的,其所涉及的世界歷史,就是一部世界近代和現代史。歷史學對現實問題的回應,可以使現實問題產生時間縱深感,可以避免國際問題研究扁平化。關於“大變局”的歷史研究,既回應了時代的需要,也必定是一種宏大敍事。歷史學應當並且可以為社會科學研究作出獨特的貢獻。
當然,由於理解不同,“時代”也可以是多面向的。我們既可以把現時代理解為大變局時代,也可以把這個時代理解為全球化新時代或世界體系發展的新階段。已經有學者在研究這些方面的宏大敍事,葛兆光教授就講到要做“從中國出發的全球史”。再如,“大分流”也引起了廣泛的討論。“大分流”是指東西方歷史過程在一定時間產生的一個根本性差別,這個主題夠大,現在對它的討論也很熱烈。如李伯重教授新近的一篇文章,講到世界貿易從古代到近代經歷了四個階段,他研究的就是一個與世界體系和“大分流”關係密切的大問題,具有宏大敍事的特徵。
不過,當前的宏大敍事還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是理論闡述不夠,有時甚至是有意識地撇開理論。我們看到,一些歷史主題的過程敍述得很清晰,比如世界不斷全球化的過程、交流不斷擴大的過程,世界體系形成的過程,大分流的過程,等等,但往往就事論事,缺少理論支撐,而理論對於宏大敍事是很重要的。舉例而言,關於大分流的討論,學者似多不願使用資本主義概念,或不願意強調資本主義的作用。其實,資本主義這個概念很重要,如果在構建近代以來的宏大敍事時不使用或不強調資本主義,很多歷史的敍述恐怕會不夠深刻。這個問題的根源就是在弗蘭克的《白銀資本》和彭慕蘭的《大分流》那裏。弗蘭克明確提出不要使用資本主義這個詞,要放棄這個“死結”。彭慕蘭雖然沒有否認資本主義,但他沒有把資本主義當作一種具有根本意義的東西,來區別於歐洲的封建經濟、亞洲的小生產經濟。他突出英國的煤炭開採和擁有殖民地在大分流中的作用,而把大分流的時間節點放在1800年,似乎在此之前,歐洲與中國在經濟社會發展水平上沒有差別,甚至中國的發展似乎還更好一些。問題在於,光講大分流、全球化的過程,強調一些具體的原因,而不強調資本主義發展所起的推動作用,難道大分流和全球化都是自然發生的歷史過程?這些歷史發展過程背後的動力機制在哪裏?英國之所以擁有大量殖民地,難道不是與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相關?英國埋藏豐富的煤炭資源已有幾千萬年曆史,英國人也早就用煤炭做燃料,但只有到工業化時期,英國才大量開採煤炭,這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需要。所以,“大分流”難道不是歐洲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的結果?如果説,資本主義的發展造成了18、19世紀歐洲與中國的明顯差別,那麼,這樣的分流不是在16、17世紀就已經在事實上發生了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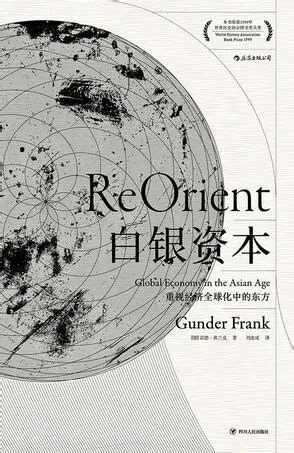
再如我們研究全球市場,研究早期世界市場的形成,如果離開了資本主義,就根本沒有辦法理解。近代早期世界市場的一個基本內容是各地之間的貿易往來。但是我在研究過程中發現,這些貿易關係其實基本上是單向的:歐洲商人到中國、日本、印度,是單向的;商品從亞洲各地運送到歐洲,是單向的;勞動力方面,是歐洲人把黑奴從非洲販運到美洲;然後,還是歐洲人把白銀從美洲運到中國,再從中國購買商品運回歐洲。也就是説,在這樣一個全球市場體系中,所有的市場信息都控制在歐洲人手裏。我們知道,在市場經濟裏,誰掌握了信息,誰就掌握了市場,就能壟斷價格、掌握貿易規則。這樣一個單向的貿易體系對中國人很不利。那個時候有多少中國商人出國去做生意,尤其是到歐洲或美洲去做生意?除了個別人因為傳教的需要到歐洲以外, 19世紀以前幾乎沒有中國人去歐洲經商。所以,儘管我們都認為近代早期中國經濟在發展,有人還把當時的中國比喻為亞洲經濟快車的“火車頭”,但我們發現,那些拿着三等車廂座位票的歐洲人卻跑到火車頭,成為駕駛這趟快車的司機。就是説,是歐洲人主導了世界經濟。對此如何解釋?光看經濟數據,近代早期中國的經濟似乎還是比較有優勢的。但這些數據可能會掩蓋實質性的內容,例如經濟的類型。從近代早期的情況來看,中國是以發達的小生產經濟、高度“內卷化”的經濟,參與到全球經濟體系中去的。而當時歐洲的經濟則是處在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即商業資本主義。這是兩種不同的經濟形態。當不同的經濟形態還原為數字以後,我們只能看到數字上的差別,而看不到經濟類型的不同。事實上,我們不僅要認識到近代早期世界貿易和交往越來越密切的過程,看到中國在當時全球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更要看到這個經濟體系本質上是西方人主導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這是事情的關鍵,而這個核心的問題,僅僅靠數字是很難認識到的。可以用這樣一個比喻:一邊是十五歲的少年,一邊是五十歲的中年漢,比力氣後者更強壯,但假以時日,少年一定會勝過壯年。近代早期歐洲經濟與中國經濟的差別正與此類似。
同樣,僅僅看到各地之間交往的表象,也容易忽視問題的本質。比如鄭和下西洋與歐洲人開闢新航路可以對照。表面看,我們可以從鄭和七次下西洋的壯舉中獲得某種自豪感。但觀察航海背後的動力,不難看到,開闢新航路和地理大發現的背景,仍然是歐洲資本主義的興起和發展,這是鄭和下西洋所不具備的,這也可以解釋中國人為什麼沒能建立起世界體系。日本學者杉山正明寫的一些書,認為蒙古征服把歐亞大陸連在一起,這樣的交往似乎成了15、16世紀世界交往的前奏。但這種聯繫與新航路開闢、新大陸發現以後的世界聯繫,存在本質的不同。不能用貌似的聯繫來掩蓋本質差別。所以,如果我們抽去了資本主義這個概念,用其他種種具體的因素去解釋近代以來的世界歷史,那是不容易搞清楚的。我們或許可以瞭解到大分流、全球化等歷史過程及其細節,但是我們不知道這些過程的背景,不知道引起這些歷史進程的根本原因,認識就不能深入。正如現在説世界處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是一個重要的指標,但問題不是僅僅靠GDP就可以説清楚的。
回到“大變局”這個主題。關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最初正式文件裏其實是表達為“數個世紀以來”“近代以來”,時間限定上基本就是指15、16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後來説“百年未有”,那就明確限定為過去百年左右的時間。但是,不管是一百年還是幾百年未有的變局,我們需要知道原來的這個“局”是什麼?如果搞不清楚那個存在了幾個世紀的格局是什麼樣的,不知道我們面臨的是一個怎樣的變局,那麼,我們恐怕很難把握新的局勢。我認為,原來的世界格局是由西方主導、由資本主義發展支撐的,現在我們所看到發生變遷的就是這個“局”。所以,理解當代就需要一個宏大的歷史敍事,而構建宏大敍事需要一個很好的理論體系。對於過去五個世紀的世界歷史的闡述,資本主義這個概念就非常適用。當然,對此也需要動態看待,不能簡單地用19世紀的資本主義概念來理解全球化時代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一直在發展,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資本主義表現出不同的形式,這個話題同樣也涉及宏大敍事。
總之,人類需要宏大敍事,每一個時代需要有適合時代的宏大敍事,而歷史學家有責任為這個時代提供適應時代需要的宏大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