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勇安 | 走向國際的中國世界史與新文科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2021-11-26 21:23
張勇安 | 上海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讓整個世界放慢了步伐,人員往來、商品貿易、物流交通等跨區域、跨境的流動都一度被迫全面或部分地中斷。現實物質世界的變化無疑給學術研究帶來諸多困擾,不可否認,“慢生活”必然放緩歷史知識生產的節奏。但在邁阿密大學歷史學教授瑪麗·林德曼(Mary Lindemann)看來,在經歷劇變之時,“或許我們也應該抓住良機來反思如何進行歷史研究(the doing of history),尤其是思考慢下來給研究、寫作和教學能夠帶來什麼益處”。毫無疑問,全球歷史學家獲得了一個對歷史學研究、寫作與教學進行“精耕細作”的契機,而中國的世界史學界,面對新文科建設熱潮則有了更多期許,那就是如何進一步拓展與國際學術界共情共建共融的可能,思考世界史研究如何更好地與國際學術界對話交流。
跨國語境與國族本位的互動
歷史知識生產正隨着其推廣者的大眾化和需求的普及化而變得更加多元,如呈現形式各有側重、內容選擇參差不齊、需求導向左右供應等,這些狀況顯然同“新文科”建設主張的學術引領背道而馳。歷史知識生產的形式、內容和導向,都對位於“知識金字塔”塔尖的歷史學家/研究者的知識生產的能力、層級、水準提出了更多更高的要求,因為這些知識的流佈與傳承最終決定着國民的整體素養,甚至是國家的綜合實力。
於歷史學家而言,究其一生的研究,無疑都是探尋“那個高貴的夢想”——求“真”,進而通過“真”來傳遞世間的“善”和“美”,換言之,正是通過智識的學習而實現其德育和美育的功能。因此,不難發現,歷史學作為馬克思眼中“唯一的一門科學”,歷經數千年,從原初的宏大敍事模式,到精細化的研究領域的分野,再到因受到哲學、文學、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的影響而遭遇的諸如語言學轉向、空間轉向(Spatial Turn)、文化轉向、情感轉向、圖像轉向、物質轉向(Material Turn)等不同解釋範式,不可否認,這些求變求新之舉對於歷史研究、教學和寫作均產生了強烈衝擊,但是,尚無法打破學者之間的地理隔絕與國籍障礙,也難以推動不同國家的歷史學家圍繞共同議題展開深層次的有效對話與交流。
2006年12月,《美國曆史評論》刊出“跨國史”對話專欄,有來自不同領域/學科的6位跨國史研究實踐者參加,旨在探討跨國史作為一種方法的廣泛的可能性和特殊性。事實上,跨國史不再是新事物,但它似乎確實是一種連續被表徵為比較史、國際史、世界史和全球史的方法的“最新化身”。誠然,這些方法之間存在重要區別,但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希望打破民族國家或單一民族國家作為分析的範疇,尤其是要避開西方曾經以種族中心主義為特徵的歷史寫作。不僅如此,跨國史研究還將進一步推動國際學界對“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關注,來自“全球南方”的研究者們有望以平等身份與來自“全球北方”的研究者平等對話,甚至翻身做學術研究的“主人”。南非約翰內斯堡金山大學非洲文化教授伊莎貝爾·霍夫邁爾(Isabel Hofmeyr)就指出,“跨國史”為理解全球南方複雜的聯繫、網絡和參與者開闢了更廣泛的分析的可能性。跨國方法的關鍵主張是對運動、流動和流通的核心關注,在其看來,歷史過程不僅是在不同地方進行的,而且是在不同的地點、場所和地區之間的運動中構建起來的。這些主張和認識無疑為不同國家的世界史研究在更大範圍和更多元主題上的推進提供了良機,同時契合了當下新文科建設對跨越傳統研究路徑和解釋模式的必然要求。
中國的世界史研究者不僅要關注到這些新的研究趨向,更需要多多地參與這些史學的實踐過程。近代以來,中國國勢的衰敗不僅是國家經濟、軍力、政治等物質和技術層面的頓挫,更為關鍵的則體現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全面退化。西方強盛的話語和學術霸權桎梏了中國學術,使其不能更好地服務於我們對世界的正確認知,更無法影響世界事務的進程。正因如此,跨國史研究可以考慮真正將中國納入考查的範圍,“以我為主”推動國際學術界打破“東方vs.西方” “殖民vs.帝國” “中心vs.外圍”等認識世界、觀察世界、理解世界的“二分法”。因為這些根深蒂固的研究路徑常常內嵌於我們研究的預設之中,主導着對於歷史文獻的解讀、利用與書寫。儘管我們要竭力突破這種學術上的“西方中心主義”或“以例外論為特徵的國家範式”,卻可能正在接近或已經跨入西方學者發明的另一個“帝國地理學”的框架之中。因此,中國學者有理由更加積極而主動地“在中國發現歷史”的同時,注重能動地利用跨國史等研究方法,發現中國歷史的“世界意義”“全球價值”“國際主義”“跨國影響”。
與此同時,中國的世界史學者有必要也有能力來推動國際學術界跨國史研究的“亞洲轉向”和“中國轉向”。受限於各種主客觀條件,國際學術界的跨國史研究甚至全球史研究還總是把跨國或全球視為“遙遠的背景”或簡單的陪襯。近年來,隨着中國學術界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與合作的深化,國際學術界的研究者正在悄悄發生變化,如英國惠康基金會資助重大國際合作項目,其研究主題越來越重視亞洲地區、社會主義國家以及中國在國際/全球衞生史上的角色和作用。劍橋大學白玫(Mary Brazelton)新近的研究就是這方面的嘗試,她試圖通過20世紀中國參與全球衞生事務的四個重大事件來揭示:與醫學史流行的敍述相反,整個 20 世紀,中國和中國歷史參與者在這一領域發揮了關鍵作用。儘管如此,我們仍有理由警惕,這些研究能否真正地規避其慣性的殖民史學和後殖民史學的路徑依賴。
從學理意義上講,中國不僅是中國人之中國,在更多意義上是世界/全球/國際/跨國之中國。中國在區域、全球視閾中的角色和作用,必須置於“開放”語境中才可以更好地理解。我們注意到,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開始嘗試推進這一領域的研究,葛兆光先生《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等一系列著作,試圖從周邊的反應來觀察“歷史中國”;沈志華教授近年努力推動的中國與周邊國家關係研究,雖主要着力於冷戰時期雙邊關係,但帶動了越來越多的年輕學者加入,不斷拓展冷戰國際史的研究;徐國琦教授已經出版的《中國人與美國人:一部共有的歷史》《亞洲和第一次世界大戰:一部共有的歷史》,加上正在寫作中的一部,合為“共有的歷史”三部曲,同樣是將中國置於中美關係、中國與世界互動、中國與全球互融中來理解“中國意義”的成功實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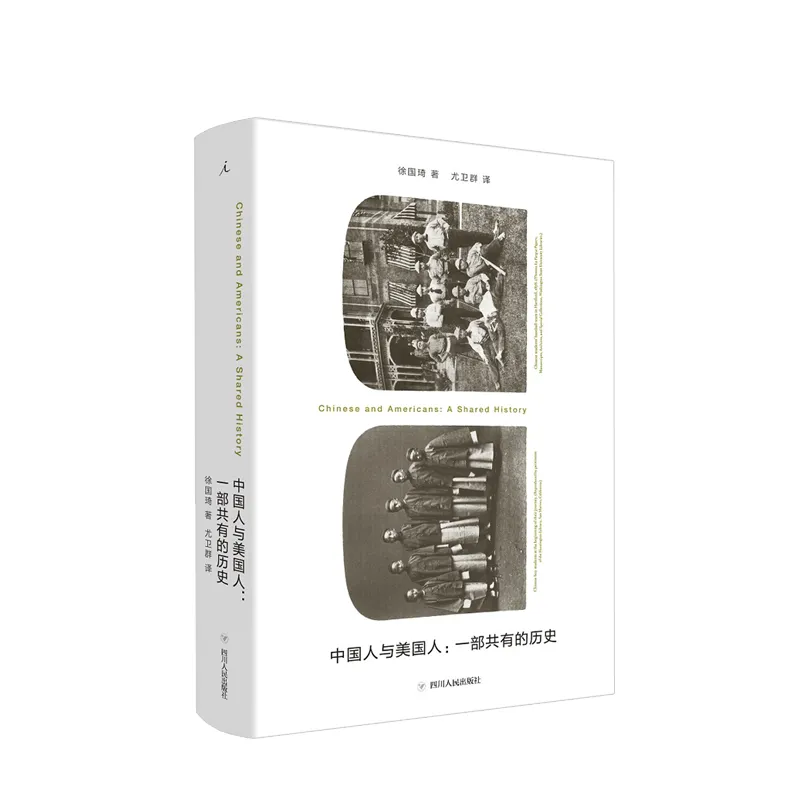
國際對話與學術中國建設
對於中國學術界而言,必須思考如何向世界展現一個真實而立體的中國。若能將“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昇華為學術表達,構建出“四個自信”的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通過與國際學術界的學術碰撞、交流與對話,推進國際學界共商共建共享的“學術人類命運共同體”,必將增進世界各國之間的理解與戰略互信,共同貢獻於全人類的福祉。對此,中國的世界史研究者大有可為。
現在,中國世界史領域的重要學術期刊/集刊正越來越多地從譯介西方史學的著述轉向首發國際學者的最新著述,尤其是新近創辦的重要學術集刊,非常注重跨學科的交流對話,強調多國學者圍繞同一主題展開討論,設置專刊推進國內外學者的學術對話和交流。國家社科基金中華學術外譯項目更是大力支持中國學術著作的譯介工作,通過遴選重要的學術著作(儘管目前仍多侷限於中國問題相關的選題),譯介為外國語言,極大地推動了國際學術界對中國學術的認識與理解。中國歷史研究院等單位創辦了多份外文學術期刊,直接向國際學術界推介中國史學成果,如《中國近代史研究》(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世界歷史研究》(World History Studies)等。中國學術界的主動而為,正在推動中外學術的深度、有質量的交流與對話。
與此同時,雖然因為全球經濟下行的壓力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中國研究和中國歷史研究的教席崗位有一定減少,但國際學術界對中國研究的關注和熱情並沒有減弱,尤其是近年來,國際學術機構和學者越來越強調同中國學術界開展交流與合作,更加註重吸收中國學者參與相關的學術活動和學術平台建設。如重要的國際學術期刊越來越注重刊發中國學者或者是涉及中國問題的學術成果,甚至定期或不定期地組織以中國學者為主的專刊或專欄。這既離不開華裔學者的推動,又同中國學者學術素養的國際化密切相關。比如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Diplomatic History、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等雜誌刊發中國學者的論文,美國長島大學夏亞峯教授、羅文大學王晴佳教授就貢獻良多。重要的國際學術會議甚至冷門絕學如國際埃及學大會也越來越多地願意邀請中國學者參會,中國學者的聲音可以被更多的國外同行聽到。
不僅如此,還有更多的中國學者應邀擔任國際重要學術組織或機構的執行委員會委員,擔任國際著名史學期刊的編委、同行評審人,尤其是在新興交叉學科的期刊中,中國學者的影響力日益提升。中國學者正在積極作為、深度參與國際學術,這些現象正體現了新文科所倡導的發展趨向,即國內外學術界更為有效地展開對話。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國內外學術界的機制性合作正日趨多元。如2012年中國美國史研究會與美國歷史學家協會(OAH)達成雙向交流合作機制,深化了雙邊學術交流互動;英國惠康基金會資助的“共享未來:中英醫學人文項目”,自2016年以來每年從中國高校選派3~6名研究生赴英國思克萊德大學和曼徹斯特大學攻讀科學、技術和醫學史“雙碩士項目”,英國高校則每年從全球遴選3名青年研究員到上海大學、復旦大學或上海社會科學院從事為期一年的訪問研究。這些制度性的建設正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其對於推動相關領域學術研究、加強國際學術對話進而建設學術中國的價值和意義不言而喻。
當然,這些工作目前仍有深化的空間,對話的效果還有待評估,重大課題的聯合研究、長期跟蹤研究尚顯不足,應邀擔任國際重要學術組織職務、國際重要學術期刊主編的中國學者人數還相對有限。特別是對於“提煉標識性概念,打造易於為國際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範疇、新表述,引導國際學術界展開研究和討論”,還有許多工作要做。但必須強調的是,強化國際學術對話應該而且能夠成為世界史學科乃至學術中國建設的重要方向。
中國學術如何進一步走向世界
新文科建設為世界史學術研究、寫作和教學提供新的發展機遇,但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道長且艱,時不我待。政策的制定者、執行者、實踐者需要更加務實地練好“內功”。作為天然具有“國際範”的世界史學科,需要在同國際學術界的不斷對話和碰撞中,生髮出具有生命力的學術火花,進而形成燎原之勢,真正構建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世界史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以下三方面工作尤其值得重視:
第一,重視制度建設,加快打造高水準、多層次、國際化的學科體系和學術平台。積極對接國際學術前沿,瞄準國際社會發展大勢和國家戰略需求,積極謀劃和設置更加適應學術發展、社會需求、國家戰略的學科方向和研究領域,而不應受限於現行的學科體系或框架。在學位設置上,更加關注“學術市場”的發展需求和崗位,按需定製。儘管近來國家層面已經在不同渠道推出“交叉學科”,但這種過渡性措施尚不足以銜接新文科發展的需求。必須通過學科的解壓甚至重組,才能盤活更多學術和市場資源,培養更多適應未來學科要求的領軍人物,才有望形成引領國際學術發展新方向的中國學派。而作為系科設置調整和新興學科領域擴張的配套工程,需要更加積極支持創辦高水準國際化的多語種的學術期刊,創設學術議題,引領學術討論,培育學術話語的影響力;還應適時創設國際學術研究協會等,搭建國際性學術網絡。通過這些機制性制度性的建設,中國學術走向世界才可能由設想變成現實。
第二,強化對全職國際化師資隊伍建設的支持力度和政策傾斜。儘管越來越多的海外高校選擇在中國創辦校區/分校或推進聯合辦學,但其培養多侷限於“通識”教育層次,而缺少成規模的研究型人才培養體系,若轉型為中國高校又缺少政策支持,故這一渠道的國際師資隊伍建設雖然成效顯著,但缺少歸化的長效機制。國內高校近年來幾乎都把國際化戰略作為學校發展的重要引擎,積極推進師資、科研、人才培養的國際化,但速度和成效卻不盡如人意,尤其是師資國際化多體現為“海歸”師資數量的增加和長期出國人員比例的提升,而真正的“洋教授”卻存在着數量不多和質量不高的問題,成熟的國際與國內師資“一體化融合式聯建團隊”更不多見。因此,有必要通過調整永居或歸化政策、提供同等國民待遇、加強校園多元文化建設等方式和渠道,支持國際化師資引進和建設,真正聚天下英才而用之。以此而論,世界史、外國語言文學等高度國際化的學科或可先行嘗試。
第三,堅持立德樹人,拓展國際化人才培養新渠道。誰贏得了青年,誰就贏得了未來。高校教育作為育人的主渠道之一,只有贏得青年,才能立於不敗之地。這裏的青年一代不僅包括中國青年學生,中國高校還應放眼世界,將全球優秀青年作為育人對象。高校需要推進中國學生與國際學生的融合式培養,這是國際通行的教育模式,而在我們這裏尚未普遍推行。目前我們對國際學生多是單獨管理和單獨培養,實際上難以實現優勢資源的互補共贏,只有打通招生關、培養關、管理關等,實現融合培養,才能真正提升國際學生培養的質量和水平。與此同時,還需要整合優質的教育資源,推進國際視野、中國特色、當地元素三結合的課程體系、研究領域、學科方向建設;培養具有全球視野、瞭解中國特色,又能夠適應其本國/本土需求的創新性卓越人才,讓這些國際“學術青年”成為中國學派、中國學術網絡的重要傳承者、宣傳者、傳播者、拓展者。
總之,只有練好“內功”,才能真正對世界發揮正向效能,更好地展現中國學術的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