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進程中的“聯想”們_風聞
新潮沉思录-新潮沉思录官方账号-2021-11-29 21:41
文 | 新華門的卡夫卡
本文是筆者針對前幾天本號劉老師討論張傑明一文,聯想到最近又引起廣泛討論的聯想集團的問題,又聯想到更普遍性的長期以來在我國廣泛存在的中間層套利的問題,從這個角度討論下現象背後的歷史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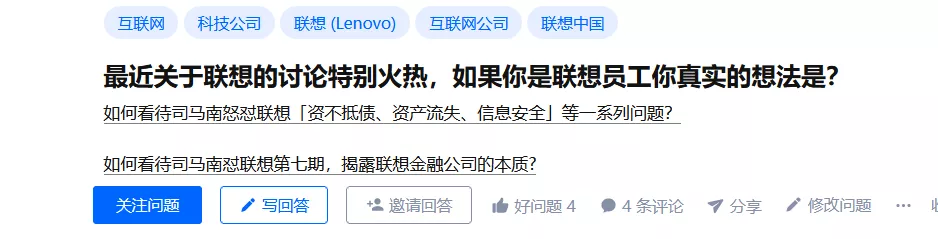
信息差導致委託-代理關係的極致情況
一直以來,筆者有個慣熟於運用的中國社會和中國行政治理分析工具,就是周黎安和周雪光所構建的“行政發包制”。而行政發包制本身,就是我們在不完全信息的情形下決策這個約束條件下產生的向現實妥協的唯一解。
筆者小時候讀一些調查報告、社會深度調查時,時常會想一個問題:明明應該這樣,為什麼決策者指向了那樣;明明A是對的,只要稍微去了解一下就可以否定B方案,可為什麼會選B?後來我才發現,實際上真實的活動過程遠比調查所呈現的更為複雜。
前幾天筆者和一個朋友討論秦漢政制、隋唐政制之間的變化,就發現其實從小政府到大政府之間的更替,不僅僅是西方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的演進規律,我國古典時期的國家政制,也表現出這樣的特點。
秦統一天下後實際上還沒有真正建立起穩固的國家體系便為農民起義所傾覆,漢初確立了黃老之治、休養生息的基本方針,到文景之治後漢代開始了政府職能與職權不斷擴張的歷史進程,黃老之治逐漸為儒皮法骨所取代。而在內裏的,就是有效治理和集中統一之間深刻矛盾。調節這對矛盾的關鍵點,在於信息差,以及為縮小信息差所投入的資源。
對比漢初,黃老之術治國的源起,恐怕和秦國法制過度使用民力進而導致的民間疲敝有深刻關聯。更進一步的追溯,是戰國以降數百年的天下征戰,早已使得天下間生靈塗炭而百姓疲憊不堪。秦國以十年時間征伐天下、一統中國,從古代的治理尺度來看,仍然屬於極快的進度。這使得秦統天下的進程快於社會秩序和社會意識的形成,最終強而有力的秦國以其法制兼併天下,嚴酷的秦法制在六國滅亡後,由推動國家開拓、兼併的動力變成了導致社會秩序崩潰、國家滅亡的本質原因。

無論是陳勝吳廣起義,還是其他地方的揭竿而起,根本上是秦制的存在已經變成了國家機器對百姓民力的過度役使、殘酷壓榨和嚴重浪費。
漢初修正秦代政治,轉移黃老之術修養民力,但這是不得不為之,並非是統治者不渴望“赫赫武功”。及至漢武帝,無為而治迅速轉向有為,而最後,固然北擊匈奴、鑿空西域,但也落得“海內虛耗”的結果。以至昭、宣時期不得不再度轉向休養民力。而這樣的故事在中國歷史中一再上演。其核心則與農業手工業社會的技術條件和“黃宗羲定律”深刻綁定,即一切面向社會的剩餘產品索取,在前現代化的治理手段和治理能力下,通過轉嫁,必定會演變成向貧下中農的橫徵暴斂。
因為社會的“正義裁決者”不掌握信息。所謂“皇權不下縣”,“官無封建而吏有封建”,所描述的就是這樣的情形。因為信息傳遞的成本和邊際,使得古代的中華帝國,其等級官僚制和理性只存在於縣級以上層級,而往下,自然是古典的封建社會。
從20世紀的最後一個十年,到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我們與歷史上的情況當然不同。但相同的地方在於,由於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政策,搶佔有利戰略機遇窗口期的外部約束,導致必須由各地方各顯神通、充分放權,才能最有效率的利用要素、發展經濟。於是上層為避免信息差,通過分權和放權,乾脆的將決策層級更大幅度的下移,**這就導致了實質性的“諸侯經濟”,以及與這一經濟現象所交織的、經濟權力的中層板結。**考慮到我國並不是一個聯邦制國家,但“諸侯”之間的獨立性和差異性,甚至大於許多聯邦制國家,這種中央-地方關係是在單一制國家中,一種推演到極致的“委託-代理”關係。
中間層的無風險套利
八九月份的時候,筆者還曾討論過關於“雙控限電”的情形。從現在來看,國家能源局的確是要控制高能耗行業的,但之所以出了岔子,一個因素是上半年廣東、江蘇、福建等外貿大省和陝西、寧夏、青海、新疆、雲南等能源大省過度上馬高能耗項目,超出了國家能源局的掌握;而另一個因素,則是由於內蒙古嚴查煤炭市場的結構性腐敗,導致煤炭的“計劃外”市場整體消失,每年實際產量減少了約5億噸煤炭。

無論是2009年的關停小煤窯,還是2011年的減少煤礦50%,亦或者是進入新時代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質上也未觸及煤炭生產供給領域的放任式結構,這種“計劃與計劃外並存”的市場結構,導致決策者嚴重的信息不足。當開始認真倒查,落實制度後,計劃外市場直接消失,這自然導致了能源供給的嚴重不足。
其實這幾年,類似內蒙古在煤炭領域“倒查20年”的情況比比皆是,總書記對內蒙古煤炭領域的問題是這樣説,“當共產黨的官,當人民的公僕,拿着國家資源去搞行賄受賄、去搞權錢交易,這個賬總是要算的”。再就如陝西的秦嶺北麓違建,當清算來臨之時,同樣是倒查15年。這樣的案例一再發生,這表明,雖然説對違紀違法的查糾,多數情況下會區分更早之前和“十八大以來”,但對某些結構性問題,則就不是輕易放手了。其所指向的,大抵就是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對中間層持續分權放權後,中間層肆意進行的“無風險套利”。
無風險套利是一個金融市場的名詞,它是一種利用金融工具獲得無風險收益的方法。因為在金融市場中,定價的參照是風險,即風險越高、利息越高。最開始無風險套利多是基於外匯市場的,把資金投資於外匯中,規定遠期匯率,取得外匯的存款收益後按既定的匯率將外匯換回本幣,從而獲得高於國內存款利率的收益。也就是套利的同時進行保值,鎖定了匯率,這就稱為無風險套利。
例如:我國年利率為7%,美國為10%,一年期美元長期匯率比即期匯率低4%時,可以10%利率借入美元,經外匯市場兑換為人民幣,投資於我國,同時賣出遠期人民幣,則可無風險淨賺1%的差額。後來,凡是存在無風險獲得利潤的結構,即稱為無風險套利。譬如説,某些企業以LPR利率獲得貸款,然後將自有資金以市場利率(高於LPR利率)拆借給自己的供銷夥伴企業,這裏實際上就是利用政策優勢在進行無風險套利。
筆者之所以借用“無風險套利”這個概念,來描述九十年代末期以來的經濟和金融活動中的亂象,大抵也是因為,許多這時期富起來的一代人,實際上既非“勤勞致富”,也不是“冒了風險進而獲得風險收益”,更和互聯網發家這代人的技術獲利和依靠資本集中快速放大不同,他們的成功,大抵都是“無風險套利”,也就是我們過去在談論改革和改制中所説的“原罪”。
這其中,當然也包括類似這幾天輿論場所關注的“聯想”。實際上聯想的改制,是上世紀末到新時代前,這近20年間國企改制的一個典型案例,是一個代表。聯想的所有制變化過程,實際上很多年前就已經不是秘密了,他是通過內部管理人團隊對公司的實際掌握,利用九十年代期間的“改制”、“股改”的流行風潮,以及直接上級對股權等概念的不熟悉,一步步將八十年代流行的“利潤分配權利”(是廠長負責制邏輯下的產物)包裝和替代為職工股份,又通過縮小“職工”的概念範疇,將職工的範圍縮小為聯想的管理層,最後再引入外部的“幫手”,引入“社會資本”購買聯想股份,而後倒手分發給管理層等人。

一通操作下來,中科院股份和員工股份被稀釋了,管理層反倒持有42.5%的股份,成了大股東,壓倒了國有資本和員工持股。整個過程自然是充分玩溜了“信息差”,對上層來説,起初的“職工持股”怎麼看怎麼像是姓“公”的,再加上還有中科院的持股,批准機關估計是怎麼也沒想到持股的職工就只是一個“羊頭”。
另一個案例,則是張明傑案發的過程,根據檢方指控:2009年7月,哈爾濱產權交易中心發佈有關原種場整體產權轉讓公告,公佈標的底價為6160萬人民幣,且轉讓不包含國有土地使用權(3.5億就是指這塊地)。之後東江公司提出受讓申請,擬合同階段,張明傑在轉讓合同中加入有關國有土地使用權轉讓的內容。8月,在其主持下,東江公司、原種場及其上級主管單位舉行產權轉讓簽字儀式,儀式上的張明傑矇蔽原種場及其上級主管單位有關人員在已被加入包含國有土地使用權轉讓內容的“轉讓合同”上簽字。
這樣就完成了利用職務之便,以6160萬轉讓國企並且把市場價值3.5億的國有土地白送給了私人公司。還有就是6160萬按規定應由轉讓方(原種場及其上級主管單位)負責發放職工安置款,但操作中由東江公司實際發放,結果11467218.50元人民幣沒給。
從本質上説,聯想與內蒙古的煤炭企業,與陝西的秦嶺北麓違建別墅,甚至與罪犯張明傑,是具有相同之處的。這個相同之處,就是利用上層不掌握實際決策所需要的信息,有時明知不對卻只能放任,下層雖然受害但只要還能忍受就無所作為,中間層全部被收買、被壓制或乾脆是一丘之貉,在這種情形下進行的肆意妄為。幾個案例之間所不同的是,有些考慮一下外部觀感,儘量包裝的漂亮一點,比如聯想;有的則“悄悄地進村,打槍的不要”以瞞天過海,比如內蒙的煤炭企業,秦嶺的別墅批文;還有的則乾脆大大咧咧,吃相難看到極致,“反正你奈我何”,“笑罵由你,好官我自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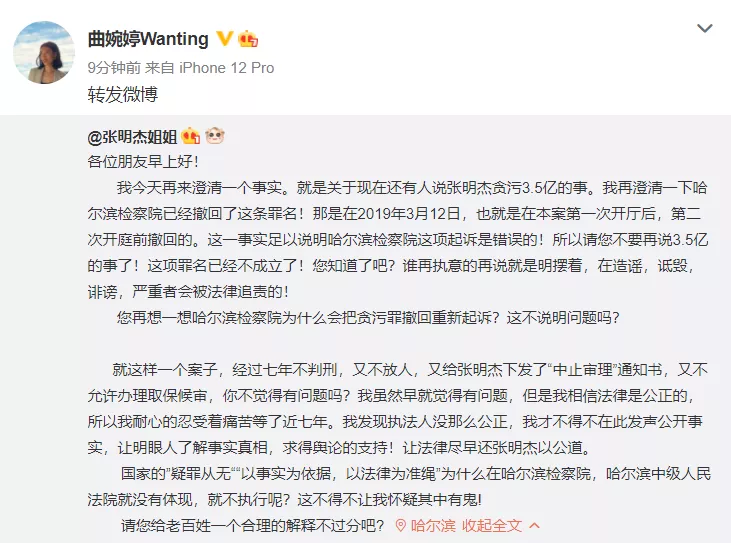
這些“地頭蛇”之所以如此任性,因為有效信息“被我截留了”,而且出於穩定、大局和其他的考量,在當時的情形下不會對他進行認真查糾。由於信息傳遞的極高成本,使得自建國以來,**我國行政體制的運行,一直在控制—放權中反覆橫跳,所謂的“一放就亂、一放就死”,大抵就是這樣。**決策權力可以上收,但信息無法有效上收,因此一旦決策上移,不但會導致臃腫、低效,甚至還會養肥“條”的部門中上傳下達的部門。而一旦決策權力下移,又由於存在信息差,這裏就存在類似於金融市場的無風險套利那樣的結構性套利空間。
新技術的契機
中國政制一直以來是“條塊結合”的,即如果將國家政制視作一棟巨型宏偉建築,一棟史上空前、古今中外所無法相比的巨大建築的話,那麼這棟建築是靠直達頂層的承重架(垂直的“條”)和因地制宜、充分尊重具體構造構型的承重牆(分級管理的“塊”)組合而成的。更進一步深究,如財政、發改、工商、工信等部門和各級黨委的工作部門,都是完全統屬於本機黨委政府的機構,而如公安等部門則既要服從本級的領導,也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向上級彙報,而税務、海關等則由中央完全垂直;在省界內,則有環保、質檢、國土等部門屬於省內垂直,公安等部門在市界內垂直。如此縈繞而龐雜的關係,構築起了中國政制的大廈。
在過去,由於各級政府權力運行的有界性,使得“各守本分”成為一種官場潛規則,理論上上級對下級的臨時打斷幾乎很難發生,這也就是上文所提及的“無風險套利”的來源。這種有界的根本性邏輯,是各級政權獲取信息的成本,必須控制在一個限度之內,那麼具體分配到每件事務上的投入,就變得有限了。但現在,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有界性”出現了被打破的契機。
當然,對信息的要求,也同樣需要畫出邊界線,但決策的底線在哪裏明確,獲取信息的邊界如何劃分,則可能還需要更深一步的明確與探索。這也是目前治理中亟需關注的問題。
下篇,筆者想來探討信息技術的進步與直接税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