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爾都塞 | 怎麼“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_風聞
保马-保马官方账号-2021-12-08 12:50
編者按
《怎麼辦?》是保存在法國當代出版紀念研究所“阿爾都塞資料庫”中的一份95頁的文稿,是作者寫於1978年的一部未完成的長篇作品,共四章。原書由G.M.戈什加林整理,法國大學出版社2018年出版。《怎麼辦?》中文版收入陳越主編的“阿爾都塞著作集”,2022年將由西北大學出版社“精神譯叢”出版。保馬今天推送的是該書的第一章,原標題為《“怎麼辦?”中的“怎麼”》。
這是一部奇特的作品,是一部政治與哲學、實踐與理論深刻結合的作品。在法國和歐洲共產主義運動出現危機的時刻,阿爾都塞向他的同志和讀者重新提出了列寧的老問題:怎麼辦?實際上,作者生前就出版了《二十二大》(1977)和《不能在共產黨內繼續下去的事情》(1978)兩個小冊子,並留下了另一部長篇文稿《黑母牛》(寫於1976年,已整理出版,中譯本吳子楓譯,商務印書館即出),對這個問題提供了一名共產黨員的回答。
但作者並不滿足於以政論形式談論這個問題。在《怎麼辦?》中,阿爾都塞以對他公開承認的理論先驅葛蘭西進行激烈批評的方式,對政治實踐的問題從思想史深度作出理論的回答。第一章從怎樣在政治現實中“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切入,論述什麼才是真正的歷史具體。由此引出第二章《安東尼奧·葛蘭西的絕對經驗主義》中對葛蘭西的批判,指出了葛蘭西從“絕對歷史主義”的困境出發,導致其領導權理論的混亂和缺失。第三章《葛蘭西還是馬基雅維利?》則回到馬基雅維利複雜而深刻的思想,在那裏去尋找理解和批判葛蘭西理論的力量。在未完成的第四章《葛蘭西、歐洲共產主義和階級專政》中,阿爾都塞回到政治實踐語境,指出葛蘭西將階級鬥爭簡化為領導權鬥爭、將“佔領國家”簡化為“佔領市民社會”的理論遺產在“歐洲共產主義”實踐中的影響。
然而,這部作品在其寫成四十多年後的發表,讓我們發現更為奇特甚至驚人的地方,與其説是借對當時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的思考來批判葛蘭西的理論遺產,或者借理論批評來思考政治實踐的難題,不如説,它預言式地批判了“西方左派”在未來——即在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全球性困境。
感謝三位譯者對保馬的支持。

怎麼“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
文 | 阿爾都塞
譯 | 陳越、王寧泊、張靖松
怎麼辦?
列寧的老問題,開創了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與實踐。對一個懂得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共產黨人來説,這是一個不同尋常的問題。
這是一個政治問題。
怎麼樣有利於引導和組織工人和民眾的階級鬥爭,使之戰勝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
這個簡單問句裏的所有詞都要掂量一下。
怎麼樣才有利於引導和組織工人和民眾的階級鬥爭?我們看到,引導或政治路線先於組織,這肯定了政治路線對於黨和黨的建設、[對於]根據政治路線建立的黨的組織的優先性。
怎麼樣才有利於引導和組織工人和民眾的階級鬥爭?我們看到,引導(路線)和組織(黨)依賴於工人和民眾的階級鬥爭。
因而黨是政治路線的工具,而政治路線本身就是對當前工人和民眾的階級鬥爭的表達,也就是説,是對——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趨勢相對抗的——這種鬥爭的趨勢的表達。
那麼,一切都依賴於對工人和民眾的階級鬥爭——在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對抗中——的當前趨勢的“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 [1],因而依賴於對這種對抗作具體分析,這種對抗同時把資產階級構成為統治和剝削的階級,又把工人階級構成為被統治和被剝削的階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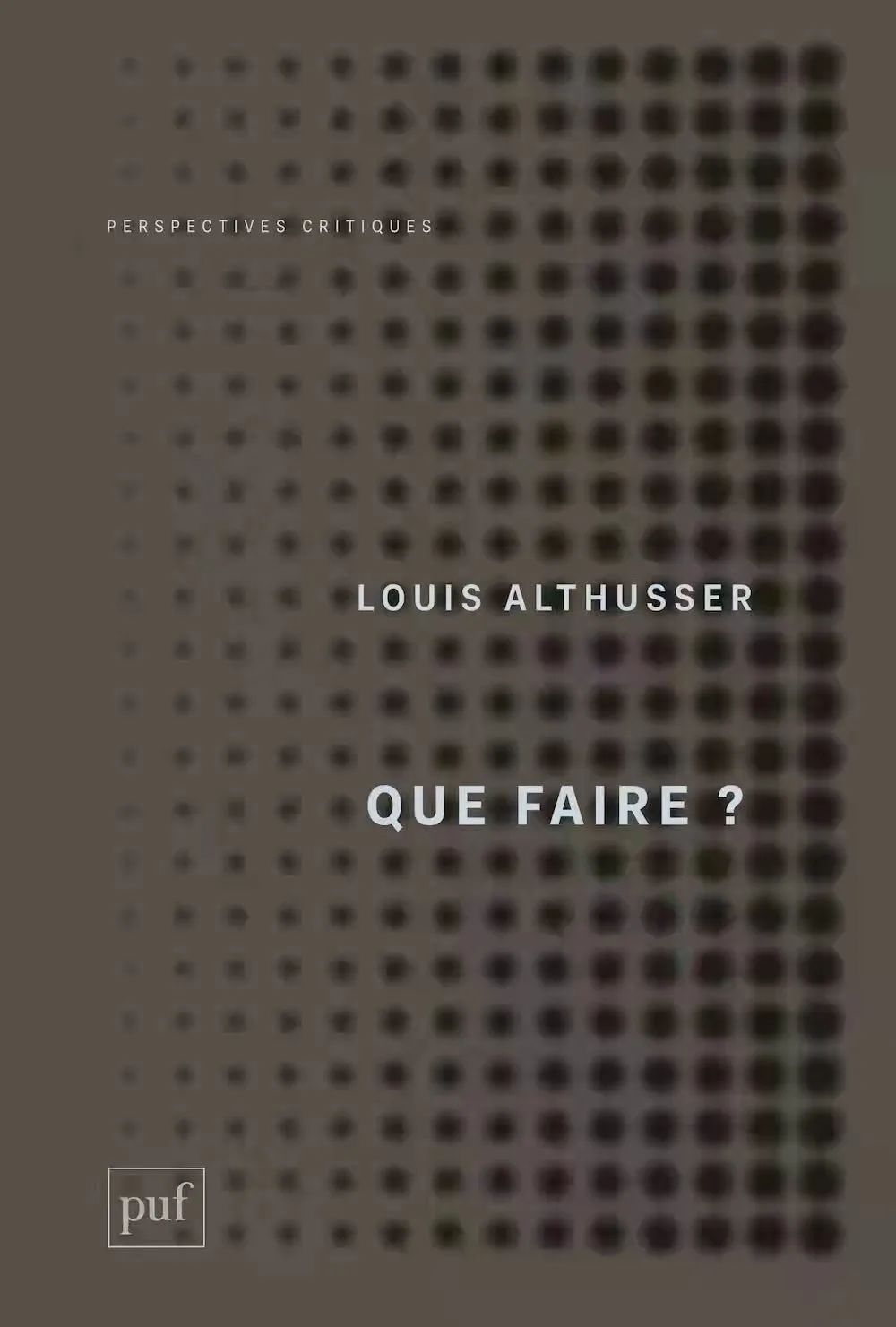
《怎麼辦?》法文版
如果説,馬克思——至少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言——的確維護了矛盾對於對立面,也就是階級鬥爭對於各階級的優先性的論點,因而也就是階級對抗對於各階級的優先性的論點[2],那麼因此正是這種對抗本身應當成為“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的對象。
否則我們就陷入了“庸俗社會學”,否則我們就會一方面分析資產階級,另一方面分析工人階級,相信自己最終能夠把兩者分開來認識。這就好比我們相信通過“分析”各球隊的陣容,而不是通過分析它們的對決,就能認識一場足球賽。沒有對決,世上就沒有什麼足球隊。
而且當我們説矛盾對於對立面的優先性,階級鬥爭對於各階級的優先性,這時我們只是在陳述一個抽象原則。因為,必須在現場,在“具體”中,去看看這種對抗歷史地獲得了怎樣的形式,這種對抗給它所構成的各階級賦予了怎樣的歷史形式,直至其細節。為了理解這些原則的意義和豐產性,我們就不可避免要“實地(sur le terrain)”去對事情進行分析,直至其最小的細節。
我們如何能夠做到這樣的“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比如説,知道一個冶金業、石化工業、“家庭”或產業化農業的勞動者,一個鐵路員工,一個銀行業、社會保險業的職員等等在生活、勞動、被剝削的條件[3]的細節方面所發生的事情?
有些人相信,只要向那些有關的人發出號召就夠了,只要要求他們:向我們講述你們的生活、你們的勞動、你們受到的剝削,等等。例如《人道報星期日雜誌》(L’Humanité Dimanche)[4]就是這麼做的,它號召所有有關的讀者向他們講述“貧困”[5]。於是報社收到數量可觀的來信,説句題外話,它們都在總編的辦公室裏睡覺呢[6]。很好。勞動者在寫作,他們説了很多有趣的、聞所未聞的、令人震驚的事情。這可以是一種用於具體分析的素材。但不是一種具體分析。
有些人相信,不要準備,只要實地去詢問勞動者就夠了。要麼向他們提出問題——但我們知道,自發的問題並非自發,它們都逃不出提問者頭腦中已有“觀念”的圈套——而勞動者説出他們想説的事情;要麼設法讓他們講述,儘可能少干預:但這種情況下,勞動者還是説出他們想説的事情,而且,就算他們説出了自己知道的一切,有件事情可以肯定:他們知道得總是比他們自以為知道的多得多(或者少得多)。這多得多的,他們説不出來,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知道。這少得多的,則被他們自以為知道的事情所掩蓋[7]。這種“採訪”同樣可能是一種用來具體分析的素材。但不是一種具體分析。
我們不能不去實地,去開始認真傾聽勞動者——但我們也不能不為這種相遇作準備。重要的不是為建立“良好的溝通”(屬於由“人際關係”所製造的那一類溝通)作心理的準備:重要的是某種理論的和政治的準備。正因為這一點,我們可以説,一種具體分析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或對認識的條件的政治意識——完全是同一件事情。唯一不同的是對象的規模。
列寧説過:不僅是為了自己認識自己,並且為了把自己構成為一個自覺/有意識的[8]階級(也就是説,要有一個能夠引導、統一和組織其鬥爭的黨),工人階級應當最大程度地考慮在自身之外、在資產階級方面發生的事情。它不能滿足於知道在自己身上發生的事情,從而滿足於自己認識自己;它也應當去看到和理解在另一方面發生的事情。重要的不是單純的好奇心,重要的是同時把握對抗的兩個項,以便能夠將對抗作為構成這兩個項的東西來把握,將階級鬥爭作為把各階級劃分為各階級、從而構成各階級的東西來把握。否則,工人階級就會始終被限足在自己受剝削的境地,沒有前途的反抗與烏托邦的夢想並存,並且在這種禁閉狀態中,屈從於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一切壓制和操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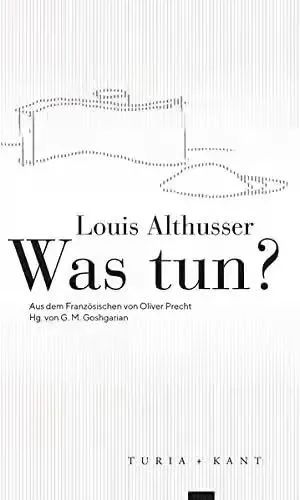
《怎麼辦?》德文譯本
為了最終能夠把握這種對抗,為了最終能夠理解這種把各階級劃分為各階級的階級鬥爭的機制,單靠“自覺/自我意識”[9]是不夠的。意大利電視台最近在阿爾法·羅密歐工人的勞動場所詢問了他們[10]。這是一些勞動者的先鋒,有高度的覺悟/意識[11]。我們看到了他們所做的一切,他們也説出了他們所知道的一切。這是獨立車間的一些工人,他們在阿爾法·羅密歐龐大的生產勞動過程中佔據了一個單獨的位置。儘管他們在車間中、在勞動中是孤立的,但最終還是能夠對他們工廠的生產過程的結構和機制——不僅對他們自己工廠中的勞動過程,而且對在外部形成的分包的存在,甚至對阿爾法·羅密歐的經濟和財務政策,對它的投資、它的市場,等等——形成某種觀念。極為罕見的是,他們甚至還達到了某種意識,意識到這個體系對他們自己產生的後果,對他們自身的勞動條件、對他們受到的剝削、對這種剝削與他們自身的勞動力再生產條件(他們的住房、他們的家庭、妻子、子女、學校、社會保障、出行、他們的汽車,等等)之間的關係所產生的後果。更加令人驚訝的是,在某種程度上,他們甚至還理解了他們的孤立與他們的無知(在這種狀態中,壟斷企業阿爾法·羅密歐用它的政策,直至幷包括它的勞動組織和分工,來掌握工人)是他們被剝削的條件的組成部分;因為這種孤立與無知是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形式之一,目的是要防止他們獲得正確的集體意識,因而防止他們的請願行動或政治行動取得功效。
因此,他們在自身“獲得意識(prise de conscience)”[12]方面已經走得很遠了——而我特別要強調的是,就此而言,這屬於“意識”的一種例外情況,離開意大利“冶金工(métallos)”[13]鬥爭的背景是難以理解的。他們多年來大大超出了傳統工會請願(捍衞工資水平,反對加快節奏,等等)的框架,以便干預勞動過程的組織及其對工人的控制,甚至干預僱傭他們的托拉斯的投資政策。我們在法國遠遠看不到這樣的例子。
但同樣就是這些勞動者,他們顯示瞭如此非凡的分析能力,卻在一個不可逾越的困難上“絆住了”。儘管他們知道在他們的工廠和托拉斯中發生的事情,但對於在菲亞特[14]那裏,因此也就是在同一生產部門中實際發生的事情,他們卻沒有任何類似的觀念,而對於國民生產的其它部門——冶金業、紡織業、石化工業、礦業、農業、運輸業、銷售托拉斯和金融托拉斯等等——中發生的事情,絕對沒有任何觀念。然而,如果人們對阿爾法·羅密歐不單在汽車生產和汽車市場中,而且在冶金業、在紡織業、在塑料工業、在石化工業、在橡膠製造業中的地位沒有一個儘可能完整的觀念,就絕對不可能對於是什麼決定着阿爾法·羅密歐中發生的事情形成一個觀念——那些工業直接影響到汽車生產,因為它們為後者提供成品,以及製造車輛的原材料。如果人們不理解汽車生產在經濟生產全體中,也就是説在現有各部門全體中所佔據的確定位置,他們就絕對不可能理解是什麼決定着汽車生產在整個國民生產中的存在和重要性。若要理解這種位置本身,除非人們的確願意一方面考慮資本在尋求利潤率最大化時的競爭,這種競爭解釋了資本在汽車部門(而非其它部門)中的投資,另一方面考慮這種投資在資產階級經濟戰略全體中的地位,而這和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是分不開的。
聽起來也許令人驚訝,但有研究表明,小汽車,這種以往是為富人的好奇心和奢侈欲提供的對象,它的大量(de masse)生產,因而也就是價格較低的、為大眾(pour les masses)——也就是為勞動者——提供的各種汽車的生產,由美國福特公司有意識開創的大量生產,是與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舊戰略的全面改寫相聯繫的。
過去,工廠主在其工廠周圍建造工人住房。這不僅對於礦業(礦工宿舍[les corons])而且對於冶金業和紡織業(工人新村[les cités ouvrières])來説,都是常見的做法。這種解決辦法自有其好處:工人沒有通勤(=損失時間)的需求,他們能夠在早上精神飽滿地來到勞動崗位。工廠主在當地有他自己的商店、他的教堂、本堂神父和學校。他可以通過勞動和出售食品衣物,對他的員工進行雙倍的剝削。他尤其可以就近監視他的員工,並通過勞動方面的剝削,通過消費方面的依賴和紅利,也通過他的本堂神父和學校老師,任意支配他們。
但這種在同一場所的雙重集中——勞動過程方面的集中和勞動力及其再生產的維持方面的集中——也有嚴重的弊端。首先是只有在對住房建設等進行投資的條件下,才能增加勞動力。工廠主碰到了這第一重限制。而他尤其是碰到了第二重限制,即這種雙重集中增進了勞動者之間的交流,並使他們在鬥爭中獲得了可怕的力量。
馬克思[15]曾強調工人在生產過程中的集中對於階級利益的“覺醒(prise de conscience)”[21]和集體鬥爭的組織所發揮的作用。當勞動過程中的集中被居住的集中所疊加,當勞動場所與居住場所實際上成了一回事,當僅僅這個工廠的勞動者又被聚集在同一居住區,可以想象這種雙重集中對於“覺醒”和鬥爭會造成怎樣的爆炸性後果。如果説,在工人鬥爭的歷史上,礦工長期以來都充當了先鋒,其次是碼頭工人和冶金業勞動者,再次是紡織業勞動者,那麼這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在這一威脅到其剝削的安全保障的嚴重危險面前,資產階級改變了戰略。它放棄了在工廠周圍建設“工人新村”的老做法,它放棄了自己從中獲取的一切好處,採用了另一種方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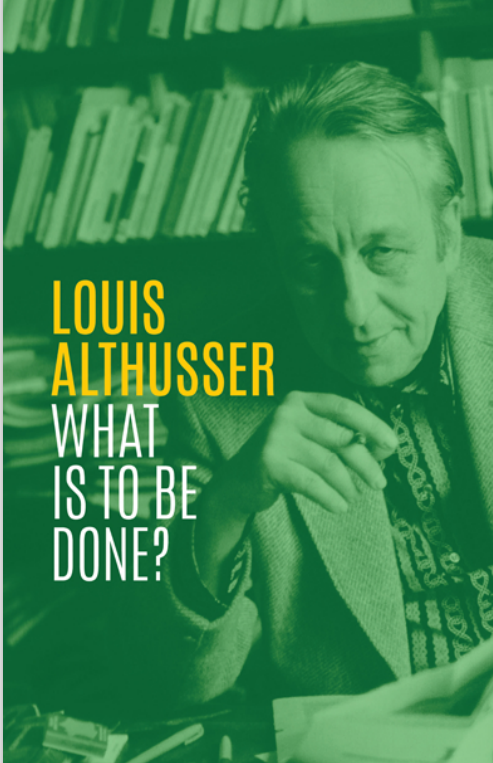
《怎麼辦?》英文譯本
需要越來越多的勞動者,而為了僱傭他們,就不能依賴用工人新村、礦工宿舍或其它方式來安置他們的“城市規劃”。需要能夠僱傭居住在任何地方的任何勞動者,即使有距離,即使很遙遠,遠到隨心所欲;也需要能夠“玩弄(jouer)”市場的波動,在一個部門增加或減少勞動人手,或者將其轉入另一部門。勞動人手的“流動性”對於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發展,對於它在資本的投資及其轉移方面的“遊戲(jeu)”來説,都已成為絕對的條件之一。需要資本最終完全從它侷限於在工廠周圍建設工人新村這種固定資本投資的舊桎梏中解放出來。服從於尋求(平均利潤率基礎上的)利潤最大化的資本的流動性,使勞動人手的流動性成為必要,實際上,也就是使勞動人手從必須靠近工廠的居住場所解放出來成為必要。顯然——其理由與第一個理由並無二致(因為當資產階級的目標就是從作為階級鬥爭的剝削中獲取利潤的最大化時,它同時也應當確保其剝削的社會與政治保障的最大化)——顯然,為了抵抗誕生於雙重集中的工人的鬥爭,需要把勞動者最大限度地分散開來。他們只要通過勞動過程的集中被聚集在一起就已經足夠了:不需要再把他們額外地聚集在工廠周圍的工人新村裏!
這些不是想象中的變動,而是事實;我並沒有憑着揣測其意圖來隨便指控資產階級。我們有許多文本、文告,以及由資產階級自己的專家撰寫的研究成果,表明該階級完全意識到自身在工人住房政策方面“轉向”的階級特性:它意識到這種“轉向”所要預防的危險,以及它期待這種轉向帶來的後果。
當然,這種在工人居住方面的“轉向”,把住房的選擇權完全交給工人(隨你住哪裏,我不想知道),同時,也把工人甩給由一整套複雜的、看似偶然的進程構成的邏輯——其中,伴隨着最厚顏無恥的政治(奧斯曼摧毀了巴黎市中心的工人居住區,以開闢寬大的交通幹道,而1848年以後的槍炮正是藉此得以“創造奇蹟”[17]),城市地租起了主導的作用——這有助於把大批工人趕到郊區,而郊區的耕地逐漸被侵佔。金融資本、城市地租和政治共同導致了新的資本主義城市規劃中居住區階級特性的更新。被驅趕到遠郊的工人儘可能住了下來,而當人們覺察到,被集中在生產中的工人還是太危險,便試圖“改變他們的精神”,更直截了當地説,就是通過讓他們對財產感興趣,通過讓他們購買在郊區的小房子和小花園,誘使他們遠離階級鬥爭。這就是獨立房屋政策,它被毫不掩飾地明確構想出來,被公開地表明為工人階級非政治化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做了業主的工人,所有時光都被用於打理房子和花園,遠離所有“咖啡館”[18],再加上長期貸款和小家庭的束縛——你還能為資本主義夢見什麼更好的保證!
現在我們回到汽車的話題。資產階級在勞動力方面政策上的這次大轉型,是由開創了汽車大量生產的福特公司明確而有意識地構想出來的。在這個大轉型中,汽車成為一種為大眾——也就是為勞動者——提供的產品,成為一種必不可少的手段,以便讓工人——他們可以住在任何地方,因而大部分時間都遠離工廠,如果被第一個工廠解僱了,沒準離下一個工廠更遠,以此類推——能夠從住房自己開車到工廠門口,能夠精神飽滿地出現在那裏,幾乎就像住在跟前一樣。有一些為富人生產的工廠(藍旗亞、法拉利[19]),或者像阿爾法·羅密歐,它們在生產普遍高於普通工人經濟能力的小汽車方面更專業一點(而且自南方阿爾法[20]之後,連這種情況也不再有了),這並不意味着什麼:那種小汽車也同樣為其他勞動者、職員、管理人員等等——他們住得同樣遠離自己工作的企業——效勞。重要的是,法拉利、藍旗亞和阿爾法·羅密歐,本身是在菲亞特及其同類(通用汽車、福特、雪鐵龍、WM,等等)的基礎上存在的,也就是在一個龐大的、植根於全世界的帝國主義企業的基礎上存在的;而這些企業的汽車櫃枱幾乎是專門用來銷售那些被大量(en masse)生產、供大眾(de masse)消費的小汽車,也就是工人通常能夠購買的那些大眾型小汽車。
汽車是調動勞動力——也就是把勞動力[作為]被剝削的勞動來維持和交付使用——的手段的組成部分,完全就像特別用於把商品運送到市場,“使商品變成為商品”(馬克思[xxi])的運輸手段——今天仍被一些人經常無視的這個現實,不能由“技術進步”或“生產率的發展”來説明,而要由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在戰略上發生一種驚人逆轉的歷史來説明——這一點,阿爾法·羅密歐最有覺悟/意識的工人也無法知曉。他們不僅無法跳出自己企業的界限(儘管他們非常瞭解自己企業的結構和機制),他們也不僅無法充分了解在菲亞特那裏發生的事情(後者在世界範圍內的投資和多種生產的戰略超出了他們的視野),他們不僅無法知曉在意大利國民生產其它部門中發生的事情,而且,他們顯然意識不到在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框架內,汽車的大量生產在資本主義針對勞動力的戰略轉型中,已經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
這就是在意大利電視台那部非同尋常的電視片裏發生的和沒有發生的事情。在那裏,阿爾法·羅密歐的工人們講述他們的勞動、他們受到的剝削、他們的資本主義企業、這個企業的生產過程和投資政策的那些機制,以及它在工廠中進行階級鬥爭的方式,而後者激起了工人的階級鬥爭的異常猛烈的反擊。
發生的事情就是我們所看到和聽到的。在電視裏,我們看到工人在勞動,我們聽到他們説出自己知道的事情、自己在鬥爭中已經意識到了的事情。他們所説的事情令人驚愕:他們最終靠自己,也就是説,在自己的工會鬥爭中,獲得了這樣的意識、這樣的知識,證明他們像工廠裏最好的管理人員和工程師一樣知道底細,至少在某些方面知道得還更多。
但是我們只看到自己所看到的,並且看不深入:看到一個人在勞動,這是個極其聰明能幹的人,僅此而已。我們也只聽到他們所説的事情、他們最終知道的事情。只缺剩餘的部分(le reste)……剩餘的部分,也就是支配着與工人的階級鬥爭相對抗的、就其全體而言的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具體形式和具體手段的整套全體的體系,它導致了這個簡單的事實,這個事實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像一切“不言而喻的”事情一樣,又是令人費解的:那麼為什麼整個汽車生產都有賴於汽車的大量生產,也就是為大眾提供的生產?因而為什麼勞動者有了汽車,也就是有了對汽車的需求?你也許認為,他們買車是為了享樂,或者是為了禮拜天和家人去兜風、去看朋友?為什麼為工人生產汽車?這個統領一切的簡單問題,阿爾法·羅密歐的工人沒有提出來。他們不可能提出來。

最近整理出版的幾部阿爾都塞著作
因為,工人們在其崗位上的勞動,甚或勞動過程,甚或公司的投資政策,甚或公司在工廠中進行階級鬥爭的政治手段——並非通過對這些事情加以觀察乃至分析,就能讓我們最終得出一些理論原則,以便從其核心及各種表現形式上,理解把各階級劃分為各階級的階級鬥爭的根本對抗。要做到這一點,必須求助於馬克思主義理論:它是唯一曾經考慮和重視這個難題、並且——以每天被實踐檢驗的形式——實際而具體地解決這個難題的理論。因此,沒有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最起碼的掌握就不能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這種掌握,對於理解事情在什麼樣的全體的體系中發生,乃是必不可少的。然而,今天這個體系甚至包括了世界資本市場和跨國公司,以及它們根據最低報酬的勞動人手、根據尋求和獲得原材料的資源、根據其價格的波動、根據某個國家令人擔憂或放心的“政治局勢”等等來轉移投資的“政策”。為了理解某個工人在某個部門參與的某個勞動過程所佔據的位置,就需要——至少是粗線條地——理解這個體系的機制。
但同樣是這種掌握,對於最終能夠當面正確地“聽”一個工人講述他的生活和勞動,是必不可少的,同樣是必不可少的。因為要能夠聽,這個聽的人就應當知道什麼問題可以提什麼問題不可以提;他應當知道如何把勞動者所説的事情同勞動者本人——關於全體過程對其自身狀況所造成的後果方面——所不知道的事情聯繫起來;他最終並且尤其應當通過這種聯繫,準備學習他不知道但勞動者知道的事情;儘管勞動者並不知道自己知道這些事情,卻還是説了出來——通過歪打正着、拐彎抹角的方式,甚至通過他們的遺漏和沉默。
勞動者知道得比他自以為知道的更多或者更少,這個問題揭示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深深懂得並已向我們吐露出來的一個現實:意識形態的後果。生活、勞動、被剝削、鬥爭、勞動力再生產的種種條件,不是人們——就像觀察火車站發生的事情那樣——可以觀察到的赤裸裸的事情。即使按馬克思的説法[22],大工業的機器把勞動者歸結到機器本身的附屬品的狀態,人們也不是“機器動物”[23]。他們不如説是“意識形態動物”[24]。他們對自己、對他們的勞動、對世界都抱有我們所謂的“觀念”。
而這些觀念確乎可以按照人們經驗的偶然性,以分散的次序,出現在人們頭腦中,最終,它們總是重新聚集在觀念的一些全體的體系中;後者雖然缺乏完全的內在一致,卻也具有某種一致性,而我們就稱之為意識形態[25]。最終,它們總是重新聚集在這些意識形態中,因為它們先前已經被聚集在意識形態中了,因為 “經驗的偶然性”通常只是意識形態——為了把自己強加於社會中的個人——所採取的形式。這些意識形態不是個人的“觀念”的總和,而是一些“體系”,或剛性,或柔性,通常兼而有之。這些意識形態不是純粹而簡單的“觀念”(沒有什麼東西能以這種形式存在),而由於它們總是與實踐有關,由於它們總是激勵着某種實踐的判斷與態度的體系,所以必須要在它們的身體(corps)、[身體]的活動[26]中——因而也要在那些實體(corps)[27]中——理解它們。
是的,意識形態有一些實體,它們來源於這些實體,完全就像它們有賴於一些身體[28]。這些實體是一些“機構”,主要是國家及其不同的意識形態機器(法律體系,學校體系,政治體系,工會體系,宗教、家庭、醫療、信息、文化體系,等等)。在這些意識形態領域的全體中,在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與被統治的意識形態之間,上演着一場殘暴的意識形態階級鬥爭。
所有這一切,看似讓我們遠遠離開勞動者,其實把我們直接帶回到他身邊。因為他是那些複雜的意識形態直至在他的身體裏相互對決的場所,而那些意識形態的對抗“自然而然地”向他隱藏了起來。國家及其整個一般意識形態體系,還有資本家及其整個內部使用的意識形態體系,總是向勞動者提出一些“觀念”,讓他能夠在這些“觀念”裏承認自己。這些“觀念”有關作為勞動價格的工資、有關社會地位的提高、有關分享利潤、有關任務的自由分攤、有關經濟(生產)與政治之間的不同、有關他若想成為好的一家之主就應當深信不疑的道德標準、有關可以確保他孩子前程的學校——如果不是由教會給孩子們行洗禮、講授教理、告訴他們(就像告訴他)永生乃是今世苦難的回報。由各種體系構成的這個給人以強烈感受的體系,既不是形式的,也不是可形式化的(馬克思主義與“系統論”毫無共同之處,後者如今代表了帝國主義意識形態階級鬥爭的先鋒理論意識形態);它有足夠的威懾力,有時也有足夠用於補償的誘惑,讓工人忘記自己只是機器的附屬品,也就是説,是資本家剝削的對象。但工人同樣可以看到他身處的真實狀況(condition)[xxix],而且只要他們稍微反抗一下,只要他的反抗稍微受到有組織的鬥爭的啓示,他就會產生另一些觀念:它們把原先的觀念當作一些騙局來揭露,它們向他講述階級鬥爭的現實,講述聯合起來改變其勞動條件(conditions)、改變不斷造成那些條件的這個社會的必要性。
我的説法是極其圖式化的。短短几行文字又能怎樣呢?不過這些文字也足以讓人感到,講述自己勞動和生活條件的勞動者,不是像一個昆蟲學家在講述這些事情,而是像這樣一個人——他要麼或多或少地服從於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為了回應他明確的擔憂而產生的具體形式,要麼或多或少地從這些形式中被解放出來,並通過這種解放得以或多或少地意識到同樣這些勞動的和被剝削的條件,連同這些條件在他的勞動力再生產中的所有延續。這樣一來,人們就能理解這句大概仍然是謎一般的話:同一個勞動者能夠知道得比他自以為知道的更多,同樣——因為這種情況也出現了——也能夠知道得比他自以為知道的更少。而悖論在於,並不總是在他最“有意識”的時候,他自動地就會知道得比他自以為知道的更多。因為那時他可能像是被他所達到的“意識”的初級真理所矇蔽:這可以在一些戰士[30]那裏看到,在他們那裏,最基本的意識成了某種絕對知識,使他們看不到整個兒一部分自身的狀況,尤其是他們的同志們的狀況。這些人把自我意識當成知識,他們的自我意識也阻礙了他們的知識。相反,一些並不以擁有任何特殊“意識”自居的勞動者——哪怕這是因為他們不屬於任何工會或任何政治組織——有時候他們實際知道得比他們認為自己知道的多得多。這些人不把自我意識當成知識,他們的意識也不會自動地阻礙他們的知識。一種嚴謹的具體分析應當關心這些差異和悖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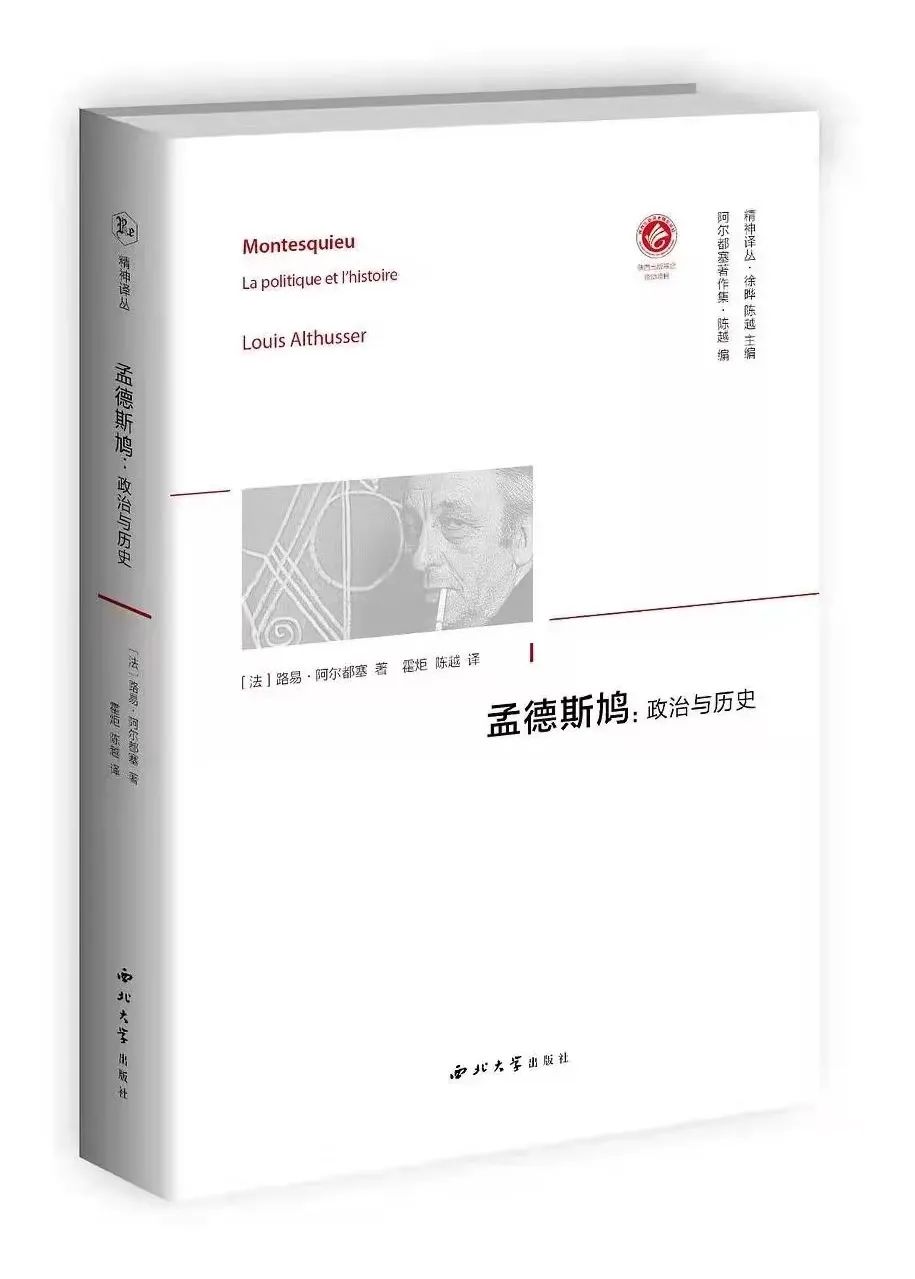


中文版“阿爾都塞著作集”已出品種
這些悖論不單在天性方面[31]令人好奇,它們也在政治方面意義重大。因為,正是基於這[些]悖論,羣眾對於各階級的優先性,以及羣眾和各階級對於階級鬥爭組織——對於工會和黨——的優先性,才在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得到確立。[32]這絕不是要陷入對羣眾的崇拜,而是要極其關心工人的意識程度,同時知道他們的意識程度(更不用説還有知識程度)並不一定與他們自以為已經達到的程度(因而與他們的自我意識)相一致。通過羣眾對於各階級的優先性、羣眾和各階級對於工會和黨的優先性,馬克思主義傳統還打算説出許多別的事情,但就我們佔據的這個要點而言,它以聰明人自然能聽懂的那種提醒的形式,指出了一個簡單的事實:勞動者並沒有逃離意識形態鬥爭,因而並沒有逃離佔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的統治;而任何形式的工會意識或政治意識都總是冒着把自己當成完善的真理的危險,除非它承認有些並沒有被組織起來因而按道理也更沒有意識的工人,在沉默中,比起那些代表他們[33]説話而且説得有點太快的人,能夠知道得多得多。
我們現在可以着手研究那個最令人生畏的問題,那個在“怎麼辦?”中的“怎麼”裏面包含的問題。但在這個問題之前,還有另一個問題,同樣令人生畏,它就包含在提問的行為(le fait de l’interrogation)本身當中。
因為人們可以合理地問自己:“怎麼辦?”這個政治問題是向誰提出的、它究竟會向誰提出。既然這是個政治問題,我們會很容易回答説,它是向這樣一些人提出的——他們已經知道什麼是政治、什麼是政治行動,因而他們有了某種政治意識,能夠在一定的情況下,自己給自己提出“怎麼辦?”的問題。這些人應該已經是一些或多或少精通組織和鬥爭的戰士,他們應該有足夠的意識去理解階級鬥爭對工人階級而言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上,比如説,工人階級不能再繼續依靠他們舊的組織、舊的路線和舊的實踐了。在這種條件下,如同列寧在1903年,他們就會給自己這個問題:“怎麼辦?”。作為(或多或少)意識到工人階級鬥爭組織的歷史困境或危機的戰士,他們就會給自己提出這個問題。而列寧在當時能夠做的事情,無非是傾聽他們的問題,重新考慮它,給予它最大程度的鮮明、力量和公開性,不過,他也有(對於他們的)優勢,能夠對他們的問題提供一些具體的回答:必須建立一個新的組織,而且它的形成同時要圍繞着一份報紙,後者充當了把仍然是分散的現有各革命“團體”統一起來的手段;它應當與工人運動、與農民運動保持某種關係;它應當領導某種統一的—民眾的階級鬥爭,以反對封建的—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及其工具——沙皇制度;而在這場將是長期處於秘密狀態的鬥爭中,黨應當以某種方式(非常嚴格的民主集中制)組織起來,具有一個“職業革命家”的重要核心,等等。
因此,在這個假設裏,要有一個領袖,他要重新考慮一些已經有意識的戰士給他們自己提出的這個問題,並且在被當前的客觀要求推向深入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基礎上,在現有階級鬥爭的客觀條件和所謂“主觀”條件(現有組織的程度和形式,它們具體實現並衡量着羣眾與戰士的“意識”)的基礎上,對“怎麼辦?”的問題,給予非常精確的、具體的回答。這些回答相互構成了同時包括理論原則、引導、組織和行動的一整套體系(為了“長期”[34]鬥爭),以及相應的口號(為了當前的行動)。
我強調這一點。我們可以明確承認一個對“怎麼辦?”的問題在理論上和政治上負責任的馬克思主義的回答,只要我們注意一個事實,就是這個回答必須具有這樣的維度:一個——就工人階級鬥爭的“長期”性而言的——未來的維度,它是那個公開提出問題的人所要重新考慮的。這個未來的維度,就是我們所説的關於“戰略”或“政治路線”的回答,同時也是關於——在鬥爭中實現這一“路線”所必需的——理論的、組織的、意識形態的和實踐的手段的回答。這就像對法國而言,法國人民聯盟(l’union du peuple de France)[35]的路線,要靠左翼聯盟(l’union de la gauche)[36]和應當與之相適應的各種手段充當紐帶[37]。
然而,這個馬克思主義的回答要想成為負責任的,除了關於“長期”性,也就是關於戰略和“路線”的回答之外,還包括對於當前行動的回答,説到底,我們也可以稱之為“口號”。當然,這些在當前或不遠的未來應用的“口號”,並不構成與戰略性回答完全不同的一類回答:因為與之相反,我們只能在戰略性回答的基礎上,也就是根據“長期鬥爭”——這種鬥爭應當儘可能考慮到客觀局勢諸要素的全體,考慮到在這些要素的對抗中佔統治地位的趨勢——來設想這些“口號”,從而表述它們,從而向黨的(或工會的)戰士提出它們。
例如,像(由喬治·馬歇在其報告中引用的)“反對扣押”[38]這樣的口號的確是一個當前的口號,但作為口號,它也從屬於在人民羣眾反對帝國主義剝削的鬥爭中捍衞他們的利益、統一他們的行動這一階級戰略的“長期路線”:它在自身水平上,腳踏實地,“一步一步,一磚一石”(喬治·馬歇),通過在當前捍衞法國工人、移民勞工、卑微的養老金領取者以及其他“窮人”的利益,為幫助他們在實現“民主變革”和進一步實現社會主義的鬥爭中聯合起來的戰略目標作好準備。
同樣,像“呼籲洛林冶金業工人為鋼鐵工業國有化而鬥爭”[39]——在那裏,國家由於“浪費”[40]丟掉了幾十億——這樣的口號,是一個既在當前又在不遠的未來應用的口號。它顯然也從屬於在整個生產部門中捍衞一大批勞動者利益的“長期路線”,以便為——這裏仍須“一步一步”——在勞動者具有一些明確戰略目標的鬥爭中把他們統一起來做好準備,也就是為民眾聯盟(或法國人民聯盟)作好準備。對後者而言,“左翼聯盟是紐帶”[41](喬治·馬歇)。
從形式上看,這個口號完全正確,但我們可以考慮它是否具備應用上的“客觀”條件。“主觀”條件(勞動者不惜一切代價保住他們工作的願望,工會和黨的願望)當然是具備的。但客觀條件——不僅“戰略路線”,而且由此產生的任何“口號”,都應當考慮這些條件——卻不能不説是一個難題。不僅因為3月19日獲得勝利的[42]資產階級在它本身固有的長期戰略中一定沒有讓鋼鐵工業國有化的“意圖”。而且因為無論是哪個階級執政,只要這個階級真想讓鋼鐵工業國有化,它就會遇到來自國際競爭的巨大現實困難;這種競爭能夠基於其設備(也就是其技術生產率)的狀態、工資的狀態,説到底,就是鋼鐵工業資本家想要在冶金生產的法國市場(因為國外市場已經被日本和其它國家的廉價生產所佔據)獲得的利潤率的狀態,以比法國生產價格低30%到50%的價格,把冶金產品投放到法國市場。
因為如果他們得不到這種利潤率——目前在冶金工業比在法國其它生產部門要低——他們就會想要放棄鋼鐵生產,並且,儘管這麼做有很大困難,也會想要讓他們的固定資本轉產(實際上,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他們不能讓礦山轉產!甚至也不能讓高爐轉產),另謀生產領域,或者很簡單,就像他們常做的那樣,讓國家替自己付錢。而每當一家公司或者——更不必説——一個資本主義生產部門讓國家替自己“付錢”時,總是通過國家貸款,也就是通過税收,會有那麼多錢(幾百億新法郎)在從生產性勞動者全體那裏——因而首先是從工人階級而不是從資本家階級那裏——攫取的剩餘價值中被提前抽走。

阿爾都塞在高師門口
這個例子證明,從“長期戰略路線”裏“提取”某些當前的口號,有時是比較容易的,甚至是很容易的:例如“反對扣押”“捍衞勞動者的購買力”“為擴大民主而鬥爭”(比例代表制,捍衞並擴大工會權利,承認企業中的政治權利),在一切可能的形式下,在一切具體的鬥爭中,實現與勞苦農民、與城市小資產階級、與知識分子的團結,等等。但是相反,當這些口號得以實現的客觀條件本身直接取決於“政治路線”本身沒有認真為之承擔責任的一些條件時,從本身正確的“戰略路線”中直接“提取”某些口號,常常是困難的,甚至是非常困難的。當政治路線沒有承擔責任——就是説,既沒有認識到這些條件的存在,也沒有對它們作具體分析——時,相信一個口號(哪怕是從這個形式上正確的政治路線中“提取”出來的)將會奇蹟般地代替“政治路線”發揮作用,是一種幻象。因此説到底,即便一個口號是從形式上正確的路線中提取出來的,它也可能是錯誤的。
顯然這是一種極端情況,這時工會的或黨的領導遠離實際,高高在上,以含糊不清的“理論”的名義,滿足於應用這種“理論”,沒有從事“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的工作,或者半途而廢。這就是法共等許多共產黨目前的情形。
近些年來,法共就這樣居高臨下地“決定”具體的現實應當是什麼,不作真正認真的、深入的具體分析,而是滿足於把一種“理論”的真理應用到“具體”的可見的、因而也是表面的簡單現象上。這種“理論”要麼是人為的,要麼是部分任意的,要麼是不準確或不充分的——儘管局部是真實的——這種“理論”之所以被採納,是由於它的“政治路線”在理論上的合法化。
我要説的是所謂國家壟斷資本主義(CME)理論[43]。黨相信,把一種像這樣構成的理論“應用”到可見的“具體”之上,就可以得到對上述“具體”的真正的認識。黨的官員或其他共產黨員就是這樣從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理論出發,寫出了大量所謂的“具體分析”,要麼關於“法國社會各階級”,要麼關於“需求”,要麼關於大學,要麼關於科學(“科學技術革命”),或者關於文化,等等。這些文章具有一些真實性,但並不是真正的理論研究:論證這一點——人人都知道或猜到這一點——易如反掌。這些文章可以羅列很長的清單,而如果説書籍報刊發行中心(CDLP)[44]處境維艱,那麼這些平庸作品在那裏銷路慘淡大概也不無理由:它們吸引不了任何嚴肅的讀者,只能待在地下室裏。
與其它例子相比,這一公然的失敗尤其清楚地證明此路不通:這就是把一種理論簡單地應用到具體之上。我説的不只是一種錯誤的或在原則上被誤解的理論,而是一種一般意義的理論,包括一種真實的理論。如果你掌握了這種假定是真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如果你決定把它應用到具體之上,並期待這樣的“應用”生產出關於具體本身的真理,你可能要永遠期待下去了。因為這套應用操作的前提,意味着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本身得出了一種完全錯誤的觀念。
如果你把一種預先存在的理論應用到具體之上,以便認識這個具體,你就不可避免地要假定,理論在其自身中——哪怕只是萌芽狀態,但無論如何都是原則上——已經包含了你裝作從理論的應用中期待的關於具體的真理。而如果你接受了這個立場,如果你把它普遍化,那就假定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在其自身中事先以理論形式佔有了能夠以“具體”的形式出現在世間的一切東西的真理。我不是在這裏作詭辯家式的批評,我説的是事情本來的樣子,而且在原則上,整個這套步驟是很簡單的(儘管它往往表現出極其複雜的形式,這正好掩蓋了它的欺騙性)。如果馬克思主義理論事先成為關於一切具體的真理,也就是關於一切具體情況的真理,也就是關於歷史上可能產生的、新的和無法預料的一切東西的真理(而我們已經為無法預料的、無法想象的東西付出了二十年!),這意味着它不是一個“具有科學性”或“操作性”的理論(不管用什麼詞),而是一種絕對哲學,它知道一切,絕對事先就知道了一切——按照亞里士多德的一個很好地表達了自身本意的提法——它是那種“關於最初和最終的原則的科學”[45]。
如果我們真的願意考慮兩件事情,上述這種奢望的荒謬性立刻就一目瞭然了。首先,所謂“具體”,作為人們經歷着的、在其中做出反應——反抗或忍受,行動或順從——的東西,始終在變化,而且絕不會再出現第二次。這是一條基本真理,不只是研究變化的歷史學家——即便他們要用某些強大的穩定性來解釋這種變化——而且就連普通人也足夠了解它。同一個太陽在每天早上升起,物體總是以同樣的方式墜落,血液總是(除非有病理學障礙)按照同樣的迴路循環,等等。但在社會生活中,包括在歷史停滯的大型帝國的強大穩定性中,總是有什麼事情永遠在變化。不管怎麼説,如果我們可以討論某些生產方式的停滯——這種生產方式原模原樣地再生產自身,幾乎沒有變化——和由此產生的那些社會,那麼至少,很顯然,在我們所熟悉的社會——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一切都永遠在變化。
不僅是某種技術發明改變了某種生產的物質基礎(例如,運輸業從蒸汽機到電能和化學能——噴氣式飛機和火箭),或創造了新的基礎(石油及其無數衍生品取代了煤炭及其衍生品;電子元件創造了一種全新的通訊形式,並通過計算機提供了在異常複雜的情況下精細組織生產過程、預測產品流通銷售的手段)。而且首先是這裏生產的再生產形式總是“擴大的”(資本主義總是在自身危機中發現重新獲得新的活力的手段——看看1929年的危機吧——包括藉助戰爭,這是解除帝國主義的一些最嚴重危機的典型形式)。而這些擴大的再生產形式絕不是一些技術形式——這樣的話我們就不能理解其擴大的必要性——而歸根到底,它們是帝國主義時代國內和世界資產階級用以反對國內工人階級和剛剛從政治壓迫中解放出來的世界各國人民的一些階級鬥爭的形式。
因此,具體不僅是變化着的東西(至少在我們的社會中),而且是高速地、越來越快地變化着的東西。我們的時代是速度的時代,這是出於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的必要性:讓資本儘可能快地流通,以便榨取儘可能多的剩餘價值;把一些部分的資本的流通時間降到最低限度,以便使剩餘價值相應地增多;加快勞動過程中的節奏,以便榨取儘可能多的剩餘價值;在投入到機器的資本上面實現剩餘價值的最大化,因為競爭者總會把價錢更便宜或生產率更高的新機器投放到市場,所以要在不得不更換舊機器之前把它們使用徹底,等等。我們時代的速度甚至已經成為一個文學主題或哀歌的主題,歸根到底,它不是取決於汽車(在高速公路上是被限速的)、飛機或火箭,而是取決於資本的擴大再生產在循環上的這種加速,它與通過資本家的階級鬥爭實現的剝削的增長是一回事——它為工人反對加快節奏、反對勞動分工和組織、反對勞動力迅速消耗的鬥爭賦予了全部意義,而工人的鬥爭是被直接捲入這一獨自運行的進程中來的。
因此如果一切都在變化,如果具體就是變化着的東西,那麼很明顯,一種理論想要在其自身中事先掌握關於變化着的和將要變化的東西的一切真理,這個奢望的確是迷亂和荒謬的。此外,如果具體就是變化着的東西,那麼人們僅僅“看到”其變化的東西就並不是構成變化的原因。在同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錯誤觀念進行的鬥爭中,這個提醒具有頭等的重要性。因為有些馬克思主義者會説:好吧,馬克思主義理論不能奢望事先掌握關於其對象的真理,因為其對象本質上是“歷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不能事先認識它;馬克思主義理論只有通過自身服從於其對象的歷史性,通過自身作為理論而獲得一種歷史性,才能認識它。這種歷史性不僅使馬克思主義理論不會因為它想要事先成為其對象的絕對真理的奢望而背叛其對象,而且還能通過預防這種危險而真正理解其對象。這樣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只能通過讓自身獲得其對象的預防性——歷史性,才能預防這種危險。這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解釋為歷史主義理論,把馬克思主義解釋為“絕對歷史主義”——與之聯繫在一起的便是葛蘭西這個名字[46]。
註釋:向上滑動閲覽
[1] 弗拉基米爾·列寧,《共產主義》,見《列寧全集》(Œuvres),法譯本,巴黎/莫斯科,社會出版社/進步出版社(Éditions sociales/Éditions du Progrès),1956年起,第31卷,第168頁。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引用了這一提法,見《毛澤東選集》(Œuvres choisies)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6年,第361頁。——原編者注
列寧在《共產主義》中關於“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的論述,見《列寧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8頁。毛澤東在《矛盾論》中的引用見《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12頁。——譯註
[2] 路易·阿爾都塞,《答約翰·劉易斯》(Réponse à John Lewis),巴黎,馬斯佩羅出版社(Maspero),“理論叢書”,1973年,第28頁以下。——原編者注
“馬克思列寧主義告訴我們完全不同的事情:階級鬥爭(新概念)是歷史的原動力(新概念),它驅動、 ‘推動’歷史向前進,並完成革命。這個論點極其重要:因為它把階級鬥爭擺在第一位。……在《共產黨宣言》的論點[譯按:即“階級鬥爭是歷史的原動力”,這是阿爾都塞借用馬克思在《法蘭西階級鬥爭》中關於“革命是歷史的原動力(moteur,《馬克思恩格斯全集》譯為“火車頭”)”的説法,對《共產黨宣言》基本論點的提煉]中,出現在第一位的再也不只是被剝削階級等等,而是階級鬥爭。的確應該看到,這個論點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決定性的。因為它在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間劃出一條根本的分界線……”隨後也提到足球隊的例子。見阿爾都塞,《自我批評論文集》,杜章智、沈起予譯,台北,1990年,第60頁以下。譯文有修改。——譯註
[3] 複數的conditions,本書譯為“條件”,dans ces conditions也按習慣譯為“在這種條件下”;單數的condition除列舉某種“條件”外,一般譯為“狀況”。——譯註
[4] 由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機關報《人道報》(L’Humanité)主辦的週刊。——譯註
[5] “跟我們説説你的生活”;“我們想收集你們的意見,懇請你們參與到一項廣泛的調查中,讓有關你們日常生活、苦難、鬥爭和希望的真理顯露出來”;“行動、真理、希望:《人道報星期日雜誌》用一百個問題獲取30000份答覆。讓我們有所認識”,《人道報星期日雜誌》,1977年1月5—11日,第49期,封面和第27頁。“四周內……數十萬共產黨員將走訪他們的鄰人,建議他們在‘今日苦難與希望記事本’中描述自己的生活。重要的是,這是由法國人自己實現的一種大型測試……”“讓真理顯露,讓不公退去,喬治·馬歇(Georges Marchais)表示”,《人道報》,1977年1月7日第4頁。參見路易·阿爾都塞197[7]年2月8日致埃萊娜·裏特曼(H.Rytmann)的信,《致埃萊娜的信,1947-1980》(Lettres à Hélàne,1947-1980),奧利維耶·科爾佩(O.Corpet)編,巴黎,格拉塞/當代出版紀念研究所(Grasset/IMEC),2011年,第679-680頁。——原編者注
[6] “《人道報》每天都在傳播從苦難與希望記事本上收集到的這些證詞。”“關於一個民族生活和希望的無可比擬的證詞”,《人道報》,1977年2月14日,第1頁。這場“苦難與希望”活動在整個1977年及稍後一些時間繼續進行。——原編者注
[7] 阿爾都塞手寫的批註,位於頁邊:“重要的不是提問,而是高聲讓人反思:人們(在交談中)發現了他們不知道自己知道的事情”。見第82頁。——原編者注
[8] consciente,本書一般譯為“有意識的”,個別地方考慮語義和漢語習慣,需要優先譯為“自覺的”、“有覺悟的”,則採用“自覺/有意識的”“有覺悟/意識的”等表述形式,以便讀者在上下文中將二者聯繫起來理解。——譯註
[9] conscience de soi,本書一般譯為“自我意識”,個別地方考慮語義和漢語習慣,需要優先譯為“自覺”,則採用“自覺/自我意識”的表述形式。參見上一條註釋。——譯註
[10] 可能是指紀錄片《工廠勞動筆記:工廠裏的生活》(《Appinti sul lavoro di fabbrica: una vita in fabbrica》),由RAI 2[意大利廣播電視公司電視二台]的“編年史”節目組在阿爾法·羅密歐的阿雷塞-波泰洛(Arese-Portello)生產地攝製,於1977年12月28日首次播出。——原編者注
阿爾法·羅密歐(Alfa Romeo)是意大利轎車和跑車製造商,創建於1910年,總部設在米蘭。現為菲亞特集團旗下公司。——譯註
[11] conscience,本書一般譯為“意識”,個別地方考慮語義和漢語習慣,需要優先譯為“覺悟”,則採用“覺悟/意識”的表述形式。——譯註
[12] 《喬治·馬歇:沿着二十二大的道路前進》(«Georges Marchais: avancer sur la voie du ⅩⅩⅡe Congrès»),《人道報》,1978年4月28日,第7頁。——原編者注
«prise de conscience» 直譯為“獲得意識”(同時承接上文“獲得正確的集體意識”),下文則意譯為“覺醒”。這個説法出自馬歇的報告。喬治·馬歇(Georges Marchais),1972—1994年任法國共產黨總書記。——譯註
[13] 作者使用了métallurgiste(冶金工人)一詞的俗語縮寫,所以加引號。——譯註
[14] 出自意大利都靈汽車製造廠(Fabbrica Italiana Automobili Torino)的縮寫Fiat。菲亞特集團現為意大利汽車等製造業以及工程技術領域的壟斷巨頭。在作者寫作本書之後的1986年,阿爾法·羅密歐公司被菲亞特集團收購。——譯註
[15] 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摩西·赫斯(M.Hess)、約瑟夫·魏德邁爾(J.Weydemeyer)],《德意志意識形態》,M.呂貝爾、L.埃弗拉爾和L.讓諾韋譯,見《文集》,M.呂貝爾主編,第三卷:《哲學》,巴黎,伽利瑪出版社,“七星文庫”,1982年,第1120—1123頁;《共產黨宣言》,M.呂貝爾和L.埃弗拉爾譯,見《文集》,第一卷:《經濟學》,一,巴黎,伽利瑪出版社,“七星文庫”,1963年,第170頁以下。
[16] 上文譯為“獲得意識”,下同。——譯註
[17] 指拿破崙三世時代的官員喬治–歐仁·奧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1809—1891)在任塞納區行政長官期間(1853—1870年)主持的巴黎改建規劃。該規劃旨在緩解城市迅速發展與其滯後的功能結構之間的矛盾,其核心是城市幹道網和其他基礎設施建設。這次改建奠定了巴黎的現代城市格局,同時也引發了巴黎人口從市中心向郊區的大規模遷移,並形成貧富階層的地理分割。在1848年以前的多次人民起義中,巴黎原本狹窄蜿蜒的中世紀街道為起義者進行街壘戰和游擊戰提供了便利,而改建後的寬闊街道則使政府軍可以輕而易舉地運輸部隊和部署火力。——譯註
[18] 打引號的“咖啡館”,蓋指議論政治的集合場所。——譯註
[19] Lancia和Ferrari,意大利豪華轎車生產商,均為菲亞特集團旗下公司。——譯註
[20] Alfa-sud,阿爾法·羅密歐於1972年在南方設立的新廠,裝配旗下首款專為與德國和日本車競爭的小型車。——譯註
[21] 卡爾·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剩餘價值理論》(Theorien über den Mehrwert),《全集》(Werke),第26卷,第二部分,柏林,迪茨出版社,1974年,第246頁。——原編者注
[22] 《共產黨宣言》,前引,第168頁,參見路易·阿爾都塞,《亞眠答辯》(1975),見《立場》(Positions),第2版,巴黎,社會出版社,“Essentiel”叢書,1982年,第181頁。——原編者注
“工人變成了機器的單純的附屬品……”,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279頁,前引。參見陳越編《哲學與政治:阿爾都塞讀本》,第215頁。——譯註
[23] 參見路易·阿爾都塞,《在哲學中成為馬克思主義者》(Être marxiste en philosophie,1976),G.M.戈什加林(G.M.Goshgarian)編,巴黎,法國大學出版社(Puf),“批判前景”叢書(Perspectives critiques),2015年,第89頁。——原編者注
這一説法出自笛卡爾:“如果有那麼一些機器,其部件的外形跟猴子或某種無理性動物一模一樣,我們是根本無法知道它們的本性與這些動物有什麼不同的”。見笛卡爾《談談方法》,王太慶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第44—45頁。——譯註
[24] 路易·阿爾都塞,《馬克思主義理論與共產黨》(Théorie marxiste et Parti communiste,1966—1967年,未刊稿),當代出版紀念研究所(Imec),阿爾都塞資料庫,Alt2.A07—01.10,第87頁;《論再生產》(Sur la reproduction,1969年),雅克·比岱(J.Bidet)編,巴黎,法國大學出版社(Puf),“今日馬克思:交鋒”叢書(Actuel Marx:Confrontations),2011年第2版,第120頁註釋9、295頁;《寫給非哲學家的哲學入門》(Initiation à la philosophie pour les non-philosophers,1977年),G.M.戈什加林(G.M.Goshgarian)編,巴黎,法國大學出版社(Puf),“批判前景”叢書(Perspectives critiques),2014年,第228、384頁;《哲學與馬克思主義:與費爾南達·納瓦羅對話錄》(«Philosophie et marxisme. Entretiens avec Fernanda Navarro(1984—1987)»,見《論哲學》(Sur la philosophie),巴黎,伽利馬/NRF,“無限”叢書(L’Infini),1994年,第70頁。——原編者注
如:“我還可以對此作進一步的發揮,在一系列著名的定義再加上一個補充的、意識形態的定義,我要説:人天生是一種意識形態動物。”見阿爾都塞《論再生產》,吳子楓譯,西北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188頁,註釋4。——譯註
[25] 注意這裏和下面“意識形態”的原文都是複數形式(idéologies),即上文所説的“觀念的一些全體的體系(des systèmes d’ensemble d’idées)。——譯註
[26] 手寫添加文字難以解讀。阿爾都塞可能是想寫“必須要在實體的活動中——因而也要在身體中——理解它們”。——原編者注
[27] 法文corps一詞兼有“實體”(“團體”)和“身體”的意思,文中故意使用了這種歧義,並用斜體(中譯本用黑體)加以區分。——譯註
[28] 米歇爾·福柯(M.Foucault)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但用的是不同的理論語言,這是由於他直到現在都避免提出國家的難題,因而也包括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難題,也包括意識形態的難題。——阿爾都塞注
[29] 關於“條件”和下文“狀況”的譯法,見前注。——譯註
[30] militants,指政黨和工會中的活動分子。——譯註
[31] 這裏的形容詞naturelles也可譯為“在自然方面(的)”。——譯註
[32] 路易·阿爾都塞,1967年10月25日致羅伯託·費爾南德斯·雷塔瑪爾(Roberto Fernndez Retamar)的信,《美洲之家》(Casa de las Americas),1993年1—3月,第190期,第60頁以下。——原編者注
羅伯託·費爾南德斯·雷塔瑪爾(1930—2019),古巴著名詩人、文學批評家和政治活動家,也是古巴重要文化機構“美洲之家”及其同名雜誌的負責人。——譯註
[33] 原文en leur non系誤植,當為en leur nom(以他們的名義,代表他們)。——譯註
[34] «longue durée»,這個短語在歷史學中以“長時段”的譯法著稱。——譯註
[35] 法國共產黨在1974年前後宣傳的提法。黨的二十二大(1976年)規定法國人民聯盟是“一切金融壟斷勢力受害者[……]的民眾大聯合,反對統治國家並使它窒息的狹隘等級,擁護在實現民主改革的過程中給這個等級以嚴厲打擊的民主變革”。《喬治·馬歇:沿着二十二大的道路前進》一文,前引,第9頁。參見路易·阿爾都塞,《黑母牛:想象的訪談(二十二大的不滿)》[Les Vaches noires :interview imaginaire(le malaise du XXII Congrès),1976年],G.M.戈什加林編,巴黎,法國大學出版社,“批判前景”叢書,2016年,第449頁。——原編者注
[36] 法國共產黨、社會黨和左翼激進派運動組成的競選同盟,它們於1972年達成了一個“共同施政綱領”。——原編者注
[37] 注意cimentée(譯為“[靠……]充當紐帶”)的原意為“被水泥粘合”。——譯註
[38] 下面兩段中引號內的詞句,系引用馬歇1978年4月27日在法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所作報告中回顧的黨的一些口號,有的引文不夠準確。《喬治·馬歇:沿着二十二大的道路前進》一文,前引。——原編者注
[39] 上同,第10頁。——原編者注
洛林,法國東部大區。——譯註
[40] 阿爾都塞在這個地方做了一個加註記號,卻沒有提供註釋。——原編者注
[41] 注意ciment(譯為“紐帶”)的原意為“水泥”。——譯註
[42] 1978年3月19日,由於1977年9月22日突如其來的左翼聯盟解體,右翼在第二輪國民議會選舉中奪取了意外勝利,獲得約51%的有效選票。——原編者注
[43] 國家壟斷資本主義(capitalisme monopoliste d’État)理論是法共在1967年十八大上採納的。從1969年開始,阿爾都塞在一系列文本中對其做出了批判,其中大部分仍未出版。參見路易·阿爾都塞,《黑母牛:想象的訪談》,前引,第391頁以下;《二十二大》(XXIIᵉ Congrés),巴黎,馬斯佩羅出版社,“理論”叢書,1977年,第21頁以下;《不能在法國共產黨內繼續下去的事情》(Ce qui ne peut plus durer dans le Parti communiste français),巴黎,馬斯佩羅出版社,“理論”叢書,1978年,第92頁以下。——原編者注
[44] 書籍報刊發行中心(Centre de diffusion du livre et de la presse),負責銷售、發行與法共有關的各出版社產品的機構。——原編者注
[45] 大概出自《形而上學》(Métaphysique)981.b.28—29。——原編者注
« science des principes premiers et derniers »,更有可能是阿爾都塞使用的法譯本(甚或他本人)對亞里士多德《形而上學》第一卷982 b 7—10中“ἐπιστήμην… τῶν πρώτων ἀρχῶν καὶ αἰτιῶν”(可譯為“關於首要的原理和原因的科學”)提法的翻譯。“最初和最終的”這個阿爾都塞喜歡的悖論性的表達可以更準確地説明亞里士多德説的“首要的”意思,也與他接下來説的“因為善,即終極因,也是原因之一”相符合。——譯註
[46] “實踐哲學是絕對‘歷史主義’,是思想的絕對世界化和此岸性,是歷史的絕對人道主義”,《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