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了太多濕地公園,但這樣的長蕩湖太少……_風聞
猫盟CFCA-猫盟CFCA官方账号-民间野生猫科动物保护联盟2021-12-14 22:36
青峯説,寫這篇文章的初衷,是想致敬大好對水南村十餘年紮實的觀察和記錄。
長蕩湖是一片湖泊型濕地,青峯在不同的季節造訪,與許多自由美麗的鳥類邂逅,它們在這裏覓食、遊戲、互毆、休憩……
認識更多的物種讓他獲得成就感,而用一顆摯愛自然的心,和一雙善於發現美的眼睛,看到世界本來的樣子,這種感受更讓人着迷。
可是長蕩湖也沒躲過成為公園的宿命,當那裏慢慢填滿人工改造的痕跡,白鸛還會來嗎?
《瓦爾登湖》是本家喻户曉的書,中學時我就嘗試讀過,那時我驚豔於書中大自然的恬靜與優美,嚮往那份寂寞和釋然,也詫異於作者頻頻流露出的對技術和發展的仇視。
事隔經年,資本日趨成為了普世的標準,大自然早已淪為自然資源。碳匯、消耗與供給、共同的健康、生態金融,氣候政治……
再讀《瓦爾登湖》,雖能讀出更多認知的狹隘與宗教的矇昧,但依舊引人反思:保護非得有利可圖嗎?衡量價值只能有一個標準嗎?
保護大自然,僅僅出自天性的憐憫,僅僅因為大自然很美,不行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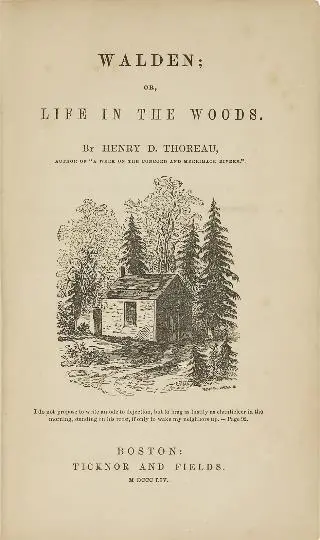
1854年初版《瓦爾登湖》 圖源網絡
我簡單去網上搜了搜瓦爾登湖的具體位置,但這感覺就像是尋找名人故居或是某種小吃的發源地,充斥着無法考證的傳聞和後人蹭熱度式的再創造。
就當它只是個存在於心靈之中的概念吧,或者更可能的情況是,它就是那種很常見的湖泊型的濕地。
有了一些自然觀察的基礎後,發覺書中的那些自然事物確實也不難找見,我身邊就有一個這樣的湖——長蕩湖。

夕陽西下時分的長蕩湖 ©dodo
夏
夏末的長蕩湖碧波盪漾,藻類不正常的爆發讓整個水體呈現一種詭異的質感,像倒入了粘稠綠色染料的染缸,從湖上吹來的褥熱的風夾着一陣一陣的腥臭。

長蕩湖,夕陽下的黑天鵝 ©青峯
湖邊颱風灌溉過的曠野上,野草瘋長到半人多高,只趟過一小段,運動鞋裏就會掉落無數的草籽。
一點小小的騷動都會導致草裏蚱蜢像浪潮一樣四散跳開,而每隔50米就出現一隻的棕背伯勞,也從側面説明這裏的食物供給十分充足。
靠近湖水的岸邊上的草被黃牛啃出些許空地,無數惱人的蚊蠅圍着這些巨獸的鼻孔、眼睛、耳朵和它們剛剛排泄的糞便,幾十只白鷺和牛背鷺也圍着這幾隻牛不停地啄食這些肥美的昆蟲。
有幾隻牛實在不堪其擾,乾脆下水躲躲,巨大的身軀沒入水中,湧起的水浪把無數細碎的浮萍和水葫蘆掛在岸邊的高草上,滴滴答答的,還衝出了一隻幼年中華鱉開始腐敗的屍體。
幾隻鷺乾脆站立在水牛光滑的脊背上,弄得我還得和身邊的女兒解釋:“牛背鷺是那種脖子有點黃的鷺,不是站在牛背上的鷺……”

牛背鷺和白鷺,脖子有棕黃色的是牛背鷺 ©湯曉梅
遠處被湖水隔開的陸地上,兩棵大樹受到了中白鷺的青睞,它們站滿了每一根樹枝,縮着脖子靜立不動,利用樹蔭的廕庇熬過這酷暑之下漫長的正午。
路邊平整過的農田成了喜鵲的聚會廣場,足足300只喜鵲起起落落嘰嘰喳喳。沿着田埂走一會,一隻大白鷺在魚塘邊發呆,長長的脖子彷彿佔去了一大半的體重。
幾隻沒見過的形似鳽(yán)鳥類的大鳥在半水生動草叢裏來來回回地起降,我照着圖鑑對了半天,才發現它們是夜鷺的亞成體……

大白鷺對着水面發呆,或者應該説是觀察水裏的動靜 ©阿惠
驅車開上大路,綠化帶的柳樹上停着兩隻黑卷尾,下面草皮上白鷺大搖大擺完全無視往來的車流,上空不時劃過一隻一隻的須浮鷗.
隨着車輛往前數量不停地在增加,當數到100只的時候我意識到今天趕上了須浮鷗遷徙的大軍,它們似乎着意選擇沿着水的線路飛,或三五成羣,或是20只的大羣,一輪一輪沒有停歇。
我迎着它們行走,看見了一處蟹塘,塘邊停着好多休息的須浮鷗,還有幾隻白翅浮鷗,不時有幾隻飛起來懸停在塘上叼起金色的蟹苗快速吞下,給我都看餓了。

須浮鷗 ©林森
這一帶還有好幾種翠鳥,但我至今都沒找到。
那是我對長蕩湖的初印象,後來,我逐漸意識到,大湖裏鳥少,環境要素更為複雜的灘塗和草地裏鳥才多。
秋
今年的秋天來得特別晚,明明都十月份了,天還是熱,不過好歹沒那麼多雨水了。
長蕩湖周邊的水產養殖業歷史悠久,於是有了很多閒置荒棄的水塘,它們總能給觀鳥愛好者帶來意外的驚喜。

各種鴴在淺水中覓食 ©阿惠
一個寺廟外面就有這樣一個水塘,我們稱其為“魔術塘”,一段時間不下雨之後,塘裏的水逐漸乾涸,露出大半的塘底淤泥,於是不知道從哪一天開始,這裏突然冒出了很多種鴴鷸。
我把魔術塘由近及遠分為三個區域,濕潤淤泥為主的灘塗區,泥水交融的潛水區和地勢最低的深水區,鴴鷸們按照腿的長短分別佔據着各自的生態位和平共處着。

長嘴鷸、澤鷸、黑翅長腳鷸“共處一室” ©萬古一刀
黑翅長腳鷸可以走到水最深的區域去,青腳鷸也可以,但是水要碰着肚子了。
黑腹濱鷸、黑尾塍鷸和中杓鷸喜歡呆在淺水區,水塘的淤泥還是太黏膩,我好幾次看見它們的長彎嘴插進泥裏吭哧吭哧拔不出來,特別社死。
金眶鴴和環頸鴴則喜歡呆在灘塗區,活力無限地跑來跑去。

黑尾塍鷸 ©大衞

環頸鴴更喜歡灘塗地帶 ©阿惠
魔術塘就像是迷你版的南匯濕地,然而這裏還不是唯一的驚喜,普門寺山下有更大的一片濕地,那裏水也淺,而且草長得更高,於是成為了夜鷺蒼鷺池鷺們的樂園,但是這天我居然在這裏遇見了4只白琵鷺。
白琵鷺比大白鷺略大,嘴巴長直末端扁平,像是一把鏟子,它們在水裏會一邊溜達一邊把嘴伸進水裏左右搖擺探食水中的蝦蟹等甲殼類動物。
後來這裏又來了一隻更為罕見的黑臉琵鷺,可惜這次我沒能找見。

黑臉琵鷺 ©阿惠
我似乎擁有伯勞雷達,每次來長蕩湖最起碼能見到十隻棕背伯勞,但那天我意外發現一隻灰色的,是隻楔尾伯勞,只可惜剛剛想拍就被邊上的棕背伯勞打跑了……

楔尾伯勞緊緊握住線纜,穩穩當當地站在上面 ©豬籠草
再來長蕩湖,目標就不是鴴鷸了,而是秋遷的紅腳隼。
紅腳隼又名阿穆爾隼,小型猛禽,以昆蟲和小型爬行動物為食,在我國東北及西伯利亞地區繁殖,每年秋天開始遷徙,於非洲越冬,是遷徙距離最長的猛禽之一。
光臨長蕩湖的只是小小的一羣,但卻並不難找,路邊的電線上落着的都是,雌鳥雄鳥長得完全不一樣。

紅腳隼們佔領了電線和電線杆子 ©阿惠
它們不停地飛上飛下,是在捕食,我看見其中一隻抓住了一隻螽斯,站在柵欄上美美地大快朵頤。
長蕩湖邊大片的無人管理的雜草養育了數量龐大的昆蟲,這應該是吸引這一小羣紅腳隼的原因。這一天我一共數到118只紅腳隼,我的第一個百猛日。
時值猛禽秋遷的尾聲,除去紅腳隼也有零星的其他猛禽,半空中一隻燕隼在毆打一隻普通鵟,一隻鵲鷂同樣在高草上盤旋,據説有人在對岸的湖面上見到了一隻鶚。

燕隼 ©阿惠
我在今年的2月份買了第一架望遠鏡(到目前也是唯一一架…),400多塊的森林人,那時候我只認識喜鵲、珠頸斑鳩、烏鶇和白頭鵯四種鳥,如今我觀察到過的鳥種數量已經來到了186種。
加新固然讓人欣喜,但最讓我欲罷不能的是身處大自然當中時候的感受。
當我站在曠野之中,隨着時間一秒一秒的延伸,聽覺和視覺似乎都在逐漸變得敏鋭,微風過耳,草木窸疏,大自然呢喃着想要向我訴説些什麼,大腦清晰得彷彿能記住視網膜傳來的每一幀畫面,稍有不同就能立刻感知到。
水杉的枝條逆風而動,眼睛立馬追過去,是一隻樹鷚。
一團火苗從一個灌木閃爍到另一個灌木,然後不見了,彷彿是幻覺,我堅持不懈地等了好久,哈,是隻北紅尾鴝,寒流也把它們從北方帶過來了。
餘光掃過田埂,好像有個不同尋常的突起,倒車回去,是隻昂首挺胸的雄性環頸雉。

北紅尾鴝 ©萬古一刀
觀察野生動物是心靈與大自然的交流,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放下偏見、利益、價值觀,不再是透過你的過往去觀察,而是直面世界本來的樣子。
寫這一篇的初衷是想致敬大好老師對於水南村的觀察和記錄,然而下筆之後才覺得無比蒼白,十餘年紮實的觀察產生的差距果然不是初學者堆堆辭藻就能撫平的(關於水南村,可戳:來到北京的大鴇,能不能等到水南村的春天?)。
夜老師也經常提到歐洲良好的自然觀察氛圍,一個普通人持續十年對家裏穀倉紫翅椋鳥繁殖的觀察記錄,最終成為了氣候變化的實證。
因熱愛而堅守,在世事濁流中不放棄那一點微不足道的自我,是最温暖的英雄主義。

一羣反嘴鷸掠過湖面 ©阿惠
冬
一次斷崖式的大降温宣告了秋天的終結,從北方飄來的不僅僅是冷空氣,還有大批的候鳥。
我聽説有一隻東方白鸛興許是被寒潮吹得和同伴走散了,落在了長蕩湖,我決定去找找看。
沒想到剛到湖邊就看見了一隻猛禽,一隻比鴿子略大的鳥在高草上空,前後交叉式地揮動翅膀保持懸停,維持不住了再上下扇動飛起來一些,白色的身體,黑色的翅邊沿,紅寶石一樣的眼眸,那是一隻黑翅鳶。
猛禽身上那優美但致命的魅力永遠令人神往,這一點和貓科動物很像~

黑翅鳶 ©阿惠
貼着湖向前開,出現了一處施工現場,似乎是要挖出一片魚塘?
總之為了施工把水排幹卻無意中使這裏成為了類似濕地灘塗的景觀,這種類型的濕地曾經遍佈中國的東部,表面荒蕪的泥沼實際上藴藏着數量驚人的蠕蟲和貝類,是涉禽們的優質棲息地。
儘管看起來黑乎乎的,但淤泥豐富的營養支持了藻類的繁盛,再加上屍體沉入淤泥不易分解,濕地灘塗的碳匯能力甚至大於森林。

這樣的灘塗,是涉禽喜歡的地方 ©青峯
而如今這類濕地大部分已經被開發了,有的是圍墾,有的植樹造林,還有更暴殄天物的被改造成了沙灘。
所以即使是這種臨時形成的灘塗也十分珍貴,水鳥們紛紛在這裏聚集,臨近黃昏鳥兒們都在休息,這些長脖子水鳥休息時候都是把頭反弓到翅膀下面,遠看有點點像烤鴨……
三隻反嘴鷸站在淺水處,水更深的地方一處凸出的泥地上大約20只短嘴豆雁在睡覺。

反嘴鷸 ©大衞
更遠處的斷垣下面,大羣蒼鷺在水裏排成一列,我嘗試去數一下,數到300只的時候,一隻巨大到無法忽視的大鳥進入瞭望遠鏡的視野——
真的很大,像車流裏突然出現一輛坦克那樣顯眼,紅腿,白身,黑翅——東方白鸛,居然這麼快就找到了……
東方白鸛是國家一級保護動物,2012年的數據顯示全球野生種羣大約只有3000只。它們喜好的棲息地是平原沼澤,捕食魚類、蛙類和小型齧齒類。
顯然,南方的水田很適合它們,因此捕殺和農藥的濫用很可能是它們致危的主要因素。
大概是嫌周圍的蒼鷺太吵,白鸛抽出了巨大的喙,昂起頭,一下子鸛立鷺羣,展開寬大的翅膀滑翔去了稍遠一些的水域。

白琵鷺與東方白鸛 ©阿惠
再多的書本知識都無法代替親眼所見的震撼,而只要見過一次,你就再也無法對它們的消亡無動於衷。
我一直待到夕陽西沉,歐亞大陸週而復始地準備遁入暗影,低垂下地平線的恆星從負角度艱難地把輻射丟在這片灘塗上,鮮紅的淺水、藍黑色的深水,赭紅的濕泥,金色水窪,斑斑駁駁,像教堂彩色玻璃窗灑在大理石地面上的投影,這景象多美呀!
初冬的江南似乎更加符合秋天的定義,草木枯敗,梧桐落葉,烏桕紅了,銀杏黃了,雁陣驚寒,一隊豆雁排成人字“嘎嘎嘎”地從頭頂掠過,仔細看裏面還混了一隻鴻雁。
蘆葦和荻高高地立在水畔,隨風搖曳,白茫茫的一大片,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那旮瘩看鴨子。

一隊豆雁,裏邊混了一隻鴻雁 ©阿惠

蘆葦和荻隨風搖曳 ©dodo
我拖着漂亮太太想去更近的地方拍拍鴨子,結果驚飛了兩隻藏在草裏的鵪鶉,然後我們發現褲子和鞋上掛滿了蒼耳的種子,我們一邊摘一邊往對方身上扔,根本停不下來,一直玩到天黑,結果鴨子也沒看成……
隨着年歲漸長,好多興趣都無法再帶給我愉悦,唯有大自然帶來的快樂永不枯竭。

褲腿上掛了好多蒼耳 ©青峯
前幾天我又去了長蕩湖一趟,魔術塘裏來了三隻鶴鷸,但是水塘可能要被利用起來了,水位繼續增高的話不知道以後鴴鷸們還會不會來。
近千隻白鷺從遠處地平線上騰起,像礁石海岸上被狂風捲起的泡沫。電線杆上兩隻喜鵲在騷擾一隻紅隼。高草地裏小鵐、葦鵐、紅頸鵐和黃喉鵐嘰嘰喳喳跳個不休。
每次都能見到的那隻白尾鷂也在,只是它心儀的高草地的面積又縮小了,挖掘機將土地翻開、平整,不知道要建設什麼。

白尾鷂 ©阿惠
一個稍大的湖裏,無數骨頂雞在遊弋,路過的情侶看着它們説:“好多野鴨子啊。”
我望遠鏡瞄了好一會,也不算錯,是有很多鴨子,斑嘴鴨、綠頭鴨、綠翅鴨、紅頭潛鴨、白眼潛鴨、鳳頭潛鴨、赤膀鴨、琵嘴鴨、羅紋鴨、針尾鴨、赤頸鴨…… 裏面還混着幾隻鳳頭鸊鷉。

好多鴨子!©曼巴
更遠地方還有幾抹潔白,那是過來越冬的小天鵝,它們像寒霜的十字架一樣升空,降落,在水面滑行,留下的長長水紋一直漣漪到湖岸。
任何語言去形容這份優雅都是匱乏的,只能歎服大自然的美學造詣。
西路灘塗那裏的施工穩步進行,水徹底幹了,白鸛走了,雁也走了,只剩下幾隻白鷺和蒼鷺。一隻戴勝居然沒發現我,在近處的枯草裏尋覓着蟲子。
濕地公園是個令我恐懼的詞,這裏明明不需要建設就已經這麼美了。
覆蓋上水泥,清理掉野草,疏浚了河道,種上觀賞花卉,房車露營,燒烤大會,遊艇俱樂部,煙火晚會,那的確會是一個短期創收很好公園,但肯定和濕地沒什麼關係了。
我想也許明年,白鸛應該不會來了吧。

水面上齊刷刷一羣小天鵝 ©阿惠
我無意中又找到一處水淺的塘子,水網密佈的江南就是這點好,夾縫中也不缺驚喜,13只小天鵝和30多隻灰雁在塘裏睡覺。
我斜倚在堤岸上,整片區域只有我一個人,多麼醉人的孤寂啊,我索性坐下來,鞋子放在淤泥上,望遠鏡也不需要了,相機也丟開,這一刻沒有工作,沒有屋頂,沒有憂愁,我的靈魂和大自然獨處。
湖堤的石塊上,斑駁得遺留着一叢一叢的淡水貽貝的屍體,夏季豐水期它們的幼苗在這些石縫裏着牀生長,冬季水位下降它們便只剩下了這碳酸鈣質的空殼,無機質的世界自有它的規律,但沒有憐憫。
這些軟體動物能夠收集水中游離的碳酸鈣形成保護殼,這種死後不會輕易分解的殼固定了大量的碳,它們對於環境穩定非常重要,也一度十分興盛。

淡水貽貝遺留下來的殼 ©青峯
它們留下的萬億計的遺體甚至定義了一整個地質年代——雜色頁岩、紅色砂岩和含有大量雙殼類遺體的灰巖共同組成的三疊紀。
那也是恐龍剛剛興起的時代,漫長的地質年代見證了無數物種的興亡,而人類卻一直到工業革命開啓後才意識到物種是會滅絕的。
人生苦短,一百年對於我們這個物種已經太過漫長,漫長到可以輕易遺忘身邊生機勃勃的江河、隨處可見的走獸和曾經繁盛的飛羽。
然而6000年的人類文明也只不過是地層中薄薄的一層沙礫,即便是隕石也沒有讓恐龍瞬間全部滅絕,大滅絕是以千年萬年計的,身在其中的我們很像蜉蝣之於四季。

鳥或許是飛上藍天的恐龍 ©青峯
一隊普通鸕鷀在夕陽頭上寫出一個一字,一隻孤單的白琵鷺像叼着一把湯勺一樣越飛越高。
候鳥帶來四季的輪轉,這些從白堊紀飛來的巨獸彷彿也稍來了遠古的訊息,我愴然地看着它們,感受洪荒的時間長河呼嘯着貫穿着身體。

普通鸕鷀 ©dodo
45億年的漫長地質年代裏只發生過5次的大滅絕事件,我們趕上了第六次,或者説是我們親手締造了這次大滅絕。
一個物種過於強勢導致環境波動並引發大滅絕,這並不是第一次,但卻是地球誕生至今唯一一次。這個物種試圖通過自我約束,親手阻止它的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