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年困難時期”科學家鮑健餓得吃餵牛的飼料,並且目擊了自己“發小”的爺爺的死狀_風聞
guan_16375531041471-2021-12-15 20:51

鮑健(見上圖),1956年生,安徽阜陽市潁上縣人,先後擔任過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中科院安徽光學精密機械研究所和“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研究員和博士生導師,他的生平,大家可參閲“中科大”的官網的這個網頁:http://dsxt.ustc.edu.cn/zj_js.asp?zzid=3987。他在雜誌式叢書《老照片》的第九十六輯上發表了一篇回憶“三年困難時期”自己的經歷和見聞的文章,現將那篇文章的主要內容摘錄在下面:
【農場憶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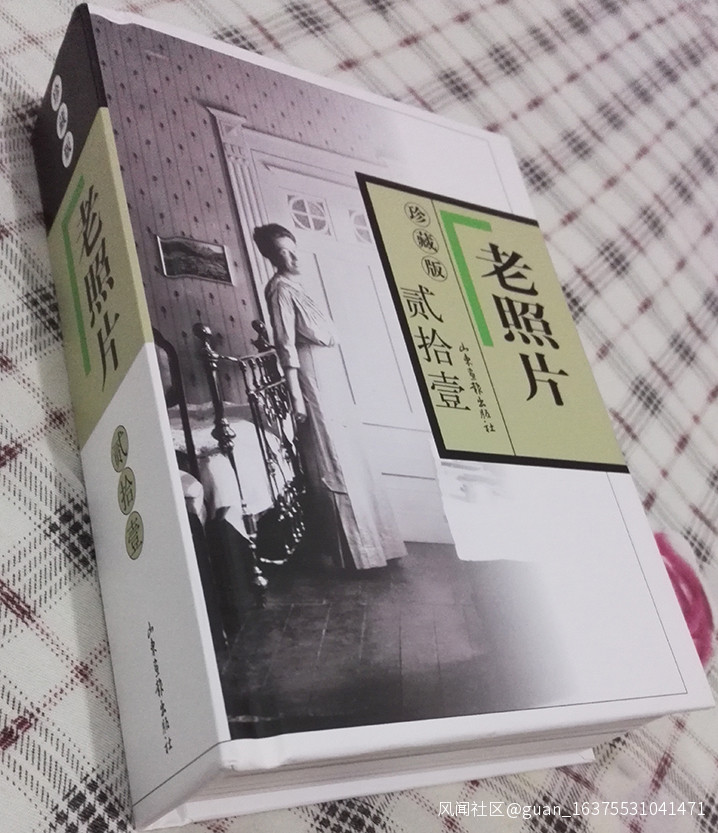
我買的是《老照片》的“合訂本”(珍藏版)的第二十一卷

右邊那一面是第96輯的封面,這一叢書是“山東畫報出版社”出版的。
**摘要:**右派陳叔叔負責飼養牲口,……我經常去牲口房裏玩,餵牛除了草以外,還要添加些精飼料,把豆餅打碎放入牲口槽,牛都會挑着豆餅吃。聞着豆餅的香味,陳叔叔經常順手丟給我一塊,那豆餅是榨油剩下的渣滓,經壓榨後非常緊緻,一小塊在嘴裏越嚼越多,只有充分軟化後才能下嚥。沒人的時候陳叔叔自己也吃,……一天中午,在英子家的院子裏,一簾草蓆蓋着一具屍首,英子説是她爹爹(合肥方言指爺爺)餓死了,那時是困難時期,城裏人還有基本口糧保證,雖然吃不飽但不會餓死,最可憐的是農村人,沒有任何保障,尤其是許多老年人,……由於那時候餓死人很尋常,許多家庭都有人“營養性死亡”,所以英子爺爺餓死了也沒人去哭,那幾年大家都有點麻木了。
去年父親遭遇車禍不幸去世,在整理老人遺物時發現一張拍攝於1962年2月的老照片,看着這張泛黃的舊照片,我的視線模糊了,思緒彷彿又回到1960年,那個不堪回首的“困難時期”,那也是我童年記憶的“起點”……
嘎噠、嘎噠—— 一個四五歲穿着揹帶褲的小男孩拉着小鴨子玩具在路上走着,那就是我。我隨母親從潁上農村來到合肥,投奔幾年前已經來合肥工作的父親,一家人總算團聚了(他父親當時在合肥市的市委黨校工作,此文的結尾寫明瞭這一點。——樓主附註)。媽媽雖然只是小學畢業,但在那個年代已經算不錯的了,所以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在安徽紡織總廠當上了一名紡織女工,工作是三班倒,非常的辛苦。我還有個不到一歲的弟弟,媽媽上班以後,為了照看我和弟弟,姥姥也從農村老家過來。姥姥對我很好,弟弟還不會走路,成天坐在小推車裏。姥姥經常摟着我,教我唱童謠,還問志遠啊(我小時候曾用名:鮑志遠),將來娶媳婦要找個什麼樣的啊,要臉白的,要好看的,要燙頭的(指燙髮),我那時太小,還不明白什麼意思,只聽懂了“燙頭”,以為是指洗頭,就大聲喊我不要“燙頭的”我要“涼的”。我們住的地方叫陳老崗,就是現在的“和平廣場”東邊那一片(樓主附註:《老照片》刊登此文時刪掉了這半句作者對自己當年的住房的位置的描述,但作者的博客刊登此文時是有這半句的:http://baojianc1.blog.163.com/blog/static/24123200320149168488974/),住的房子是簡陋的平房,沒有吊頂,朝上看就可以看到尖尖的屋頂。遇上下雨天,能聽見雨點打在屋頂的聲音,時間稍久就會有漏雨,開始是慢慢的滴,然後就會越來越大,越來越急,就得用臉盆來接。我最高興的事就是打着雨傘站在雨地裏,聽着雨點打在傘面上啪嗒、啪嗒的聲音,從雨傘下邊朝上望去,就像我自己的小房子。1960年,那是三年困難時期最難熬的一年。自打我記事時,飢餓就是生活的主旋律,**我甚至以為生活就是這樣的吧,吃不飽是理所當然的,天天吃飽飯反而不正常,也是不可能的。**每次路過食堂時,總是被做飯的香味所吸引。可能是肚裏油水少,就是覺得餓得快,剛吃過飯很快又餓了。媽媽上夜班會帶回來一個饅頭,那是廠裏給夜班工人發的“夜宵”,媽媽捨不得吃帶回來給我。白麪饅頭很難得,可得小心,到“安全”的地方再吃,如果在大街上“毫無防備”地吃,極有可能會被周圍的“饑民”敏捷地搶走。
**農村老家不斷有人過來,帶來那邊餓死人的消息。**父親覺得應該把這一情況報告給上級,就實名寫信寄往北京。可沒想到,不久北京方面就把父親的信轉回安徽省處理。處理過程頗具戲劇性,省裏成立了調查組去潁上老家那邊“調查”,當地政府先給村裏邊每家發一袋糧食,然後調查組再進村“調查”。看到家家都有糧食,調查組認定這是一起右派分子猖狂向党進攻的“嚴重事件”,必須嚴肅處理。很快,父親就被定為右派(右傾)分子,**開除公職(留用察看)送勞改農場改造。那時侯右派分子太多,正規的勞改農場已經人滿為患,安排不過來,為此合肥一些大單位就自辦勞改農場,把父親送到合肥市文化局農場改造。**那一段時間,父親的心情很不好,記得父親去農場的那天早晨,我要跟着去,父親狠狠地訓斥了我,讓我別跟着,我感到十分委屈,就在家門口哭,那天早晨有些薄霧,太陽紅紅的,日光裏,父親的背影隱約拖着淡淡的影子,越走越遠直到看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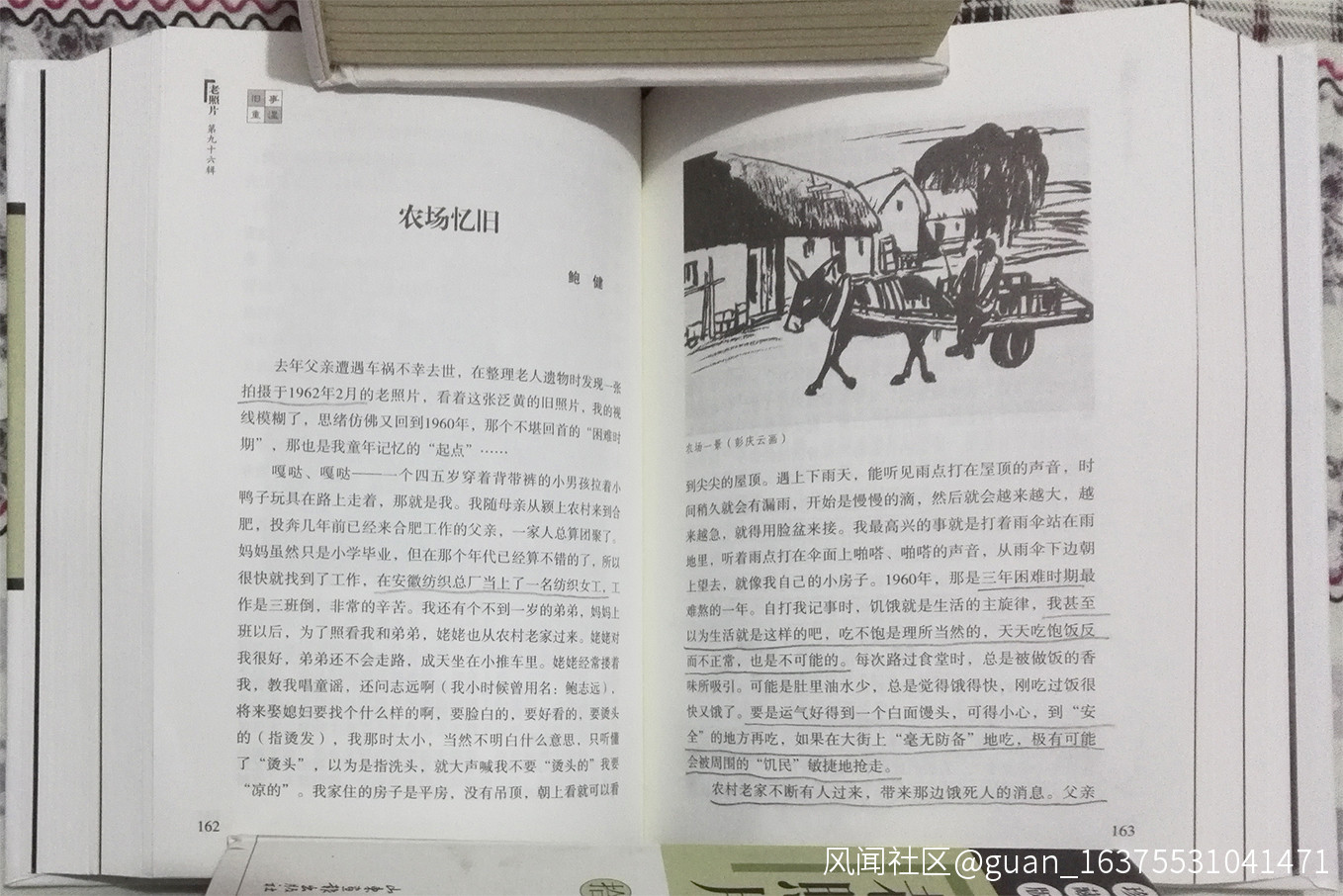
爸爸被開除公職去農場後,我們家住的房子也被收回,媽媽只好搬到紡織廠的集體宿舍去住。媽媽是紡織女工,工作三班倒非常辛苦,根本無暇照顧我們兄弟倆,剛一歲的弟弟隨姥姥回農村老家,而我去了爸爸所在的文化局農場,時間是1961年的早春。文化局農場也就剛開辦不久,在合肥郊外一個叫張窪的地方(雖然現在那裏已經是樓宇林立了,但50多年前還是荒村僻野),徵了幾十間草房,上級給了兩百多隻鴨子、兩頭毛驢和一頭水牛,購買了農具等生產資料。由於是文化局辦的農場,在那裏勞動改造的右派主要是來自文化局系統內不同單位的人員,有作家、演員、幹部等等,大概有二十多人樣子,農場場長是個轉業軍人,這些右派就由他來監督管理。
農場裏就我一個小孩,每天最期待的就是吃飯時間,還沒到開飯時間就去伙房裏張望,有時右派大廚會給個冷飯糰子,那滋味甜絲絲的,好吃極了。碰上運氣好,在田邊水溝裏捉到個小螃蟹啥的,我就拿到伙房的灶膛裏去烤着吃。
牲口房有兩間,一間牛舍,住着農場的一頭水牛,那個牛總是在吃,吃草時在吃,不吃草時嘴仍在嚼個不停。另一間住着兩頭毛驢,毛驢是棕灰色的,嘴巴上有一圈白毛,看着很滑稽,盯着看總感覺它們好像在笑我。
右派陳叔叔負責飼養牲口,他去放牛時我經常跟着去,老牛揪着地裏的青草發出呼呼的聲音,我躍躍欲試,想試試騎牛是什麼感覺,陳叔叔把我抱起來放到牛背上,哇好高啊,騎在牛背上的感覺比我想像的要高,可能是我太矮小的緣故吧。我經常去牲口房裏玩,餵牛除了草以外,還要添加些精飼料,把豆餅打碎放入牲口槽,牛都會挑着豆餅吃。聞着豆餅的香味,陳叔叔經常順手丟給我一塊,那豆餅是榨油剩下的渣滓,經壓榨後非常緊緻,一小塊在嘴裏越嚼越多,只有充分軟化後才能下嚥。沒人的時候陳叔叔自己也吃,可時間長了還是被人發現給舉報了,右派分子不好好改造,還偷吃牛飼料。為此場長開會把陳叔叔批判了一通,並讓其做了檢討才算了事。
農場離周圍的村莊很近,農場只有我一個小孩,我只能去找村裏的孩子玩,可村裏的孩子嫌我小,不願理我。只有一個叫英子的小女孩,英子大我一歲,她倒不嫌我,於是我們兩個經常在一起玩,看那些男孩子割草、放牛、打鬧。
**一天中午,在英子家院子裏,一簾草蓆蓋着具屍首,英子説是她爹爹(合肥方言指爺爺)餓死了,那時是困難時期,城裏人還有基本的口糧保證,雖然吃不飽但不會餓死,最可憐的是農村人,沒有任何保障,尤其是許多老年人,**拒絕進食,寧願餓死把糧食省給兒孫。由於那時候餓死人很尋常,許多家庭都有人“營養性死亡”****,所以英子爺爺餓死了也沒人去哭,那幾年大家都有點麻木了。回到家裏我還在想英子爺爺餓死的事,我就問爸爸,人死了是怎麼回事,什麼時候還能活過來嗎?爸爸説人死了就什麼都沒了,永遠也不會活過來了。那是我第一次對死亡有了恐懼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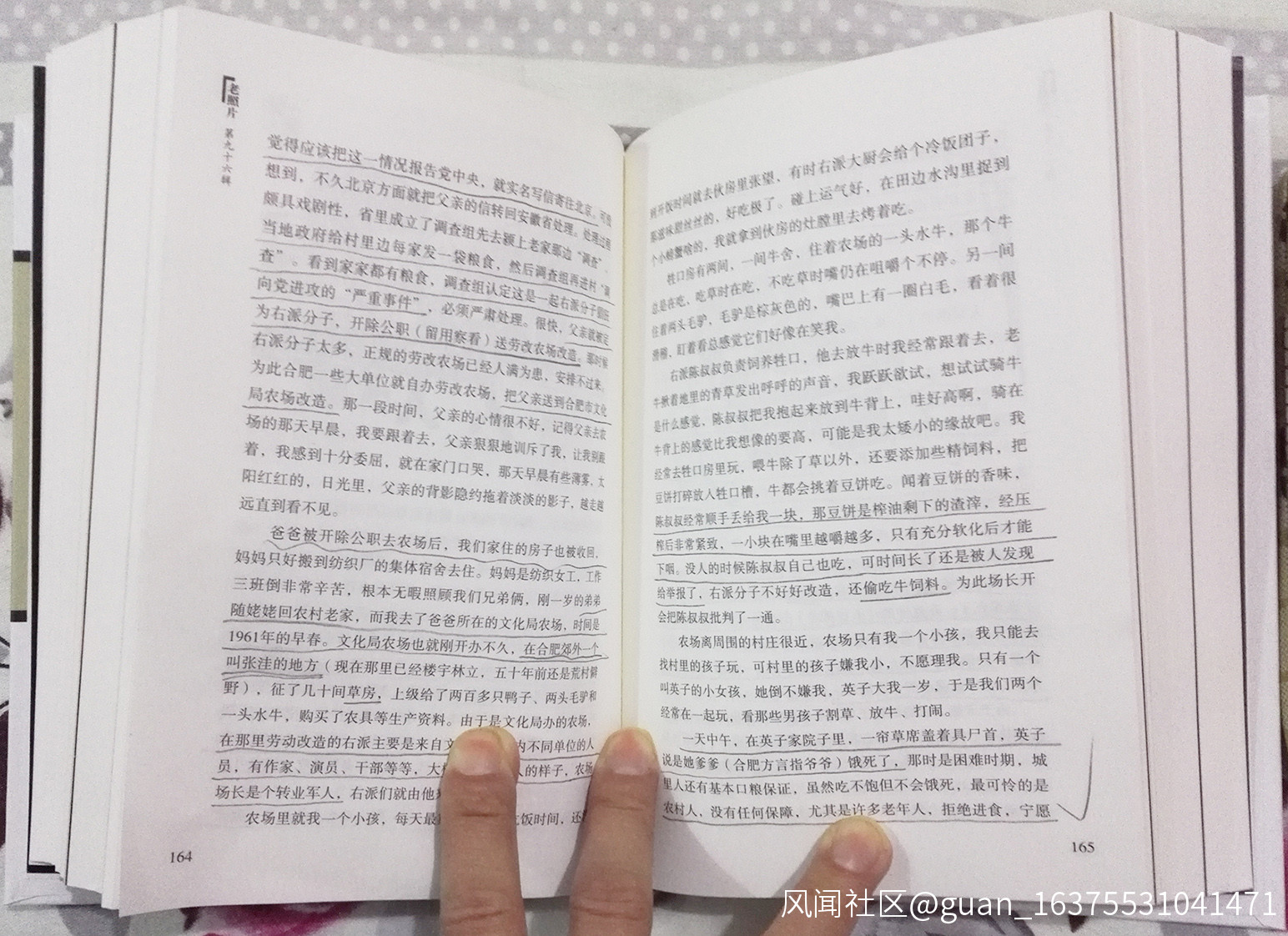
天漸漸熱了,蟲子也多起來。中午大人們都在午休,小孩精神頭大,我仍然在大樹下面的陰涼地玩,不知是誰把揚穀子的柳條簸箕放在太陽下曬,我把它拖到樹蔭下面,我坐在中間雙手把着兩邊左右搖晃。樹邊的田裏,蟲子把農作物啃的就剩光桿了,在太陽的暴曬下,蟲子也找陰涼,紛紛朝樹蔭那裏爬,我那個搖晃的“船”成了“絞肉機”。那幾年又叫“三年自然災害”,其實,我並沒有看到什麼洪水、乾旱,倒是蟲子不是一般的多,那是相當地多啊。前兩年上級號召“消滅四害”,對於四害之一的麻雀,人民羣眾發揮聰明才智,採用槍、彈弓、網等進行獵殺,晚上用手電筒照着掏麻雀窩。組織大批民眾敲鑼鼓、敲臉盆,驚嚇麻雀讓它們無法覓食和落腳,很多麻雀飛着飛着就掉下來累死了。在這樣的“人民戰爭”打擊下,不光是麻雀,別的鳥兒也被殃及池魚,鳥兒數量大大減少。那時候農藥、化肥使用並不普遍,種田基本靠天,鳥兒是蟲子的天敵,一旦鳥兒數量減少,蟲子數量必然大大增加。
由於天熱,農場的鴨子每天早晨從鴨棚趕出來時,總有幾隻被熱死、踩死的,因而右派們每天都能沾點葷腥,那兩百隻鴨子很快就被吃光了。……(略)
……(略)雖然農場裏的右派們是來勞動改造的,但終究是“公家”的人,即使吃不飽,但絕不會餓死,但周邊的老百姓不一樣,他們沒有任何保障。春荒時候,老百姓餓的實在受不了,就把家裏值點錢的物件拿到農場,找右派們換點山芋什麼的充飢。我家的一把大茶壺就是那時換來的,茶壺上面有“和合二仙”的圖案,兩個神仙,一個舉着個荷葉,另一個雙手拿着盒蓋,揭開的盒子裏好像有蝙蝠飛出來。……後來文革“破四舊”時,那把壺被認定為“四舊”,被紅衞兵抄走砸掉了。那時候人們還沒有收藏意識,如果那把壺今天還在,讓專家鑑定一下,極有可能是件“老”東西呢。
……(中略)
農場有個儲藏室,存放着糧食和一些“貴重”物品,儲藏室的鑰匙在場長手裏,要去拿東西就得找場長拿鑰匙。一天早晨,聽到外邊吵吵嚷嚷的,我出去一看,儲藏室的牆不知被誰打了個口子,説是昨天夜裏進來賊了,把儲藏室裏兩百多隻鴨肫偷走了,農場裏兩百多隻鴨子被右派們吃了,而鴨肫曬乾後穿成串保留起來了。那時侯的鴨肫就像現在的燕翅鮑魚,屬於“高檔食品”,兩百多個鴨肫價值兩百多塊錢呢。報案後,在等待警察過程中,我看到我家的餅乾桶就在牆壁破洞邊上,父親為防止我把餅乾一下子吃完,就把餅乾桶寄放在農場儲藏室裏,過一段時間就拿幾塊給我。我看到自家的餅乾桶後就試圖去拿,還沒走到破洞跟前就被呵斥不準去拿,我不明白為什麼自己的東西都不能去拿,大人們説要保護好現場,等警察來調查。警察終於來了,經過仔細現場勘查取證,警察給出的調查結果出乎意料:偷盜現場是偽造的,應該是農場內部有人監守自盜。正當大家感到詫異的時候,有人發現場長不見了,實際上那兩百多個鴨肫就是場長拿回老家給私吞了(後來經過清點,農場收穫的黃豆也短缺了不少)。看到右派們一個個平反離去,場長預感到農場也快要關門了,如果最後清查資產,這些個窟窿怎麼填呢,於是他就搞出這樣一出鬧劇來(此文前面的段落説了這位場長是一名轉業軍人,是上級派來專門監督和管理右派的。——樓主批註)。哪知道人民警察火眼金睛,場長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見事情敗露只好溜之大吉。大家趕緊向上級領導報告了情況,上級指示由我父親和**楊經理(定右派前,是合肥“長江劇院”經理,所以大家還是習慣地叫他楊經理)**接替場長負責農場日常工作。
到了1962年的春天,農場裏只剩下各“職能部門”(例如:伙房、財務、管理員、飼養員等)的十餘名右派(也已全部平反)還在留守。上級指示農場關閉,由我父親和楊經理負責清理農場資產,把生產工具和牲口就地賣掉,準備返回合肥。那天早晨,公社的人來拉農具,牽牛和那頭毛驢,……中午吃完午飯後,大夥把行李裝上架子車,我是小孩當然坐車啦,毛驢沒有了,大家就倆人一組輪流拉車。……

到了合肥城已是傍晚時分,大家提議先去照個相,於是來到三牌樓附近的東風照相館,……於是就留下了這張珍貴的照片。照片中最後一排最右邊戴毛帽子的就是我父親,照片中唯一的小男孩就是我,抱着我的靠中間的那位是楊經理,挨着他的是他夫人和女兒,楊經理夫人和女兒並不在農場,她們是聽到我們返城消息來迎接我們,並參加合影的。……
回到合肥,一家人終於又團聚了。父親被暫時安排在**長江劇院(合肥市越劇團)**工作,楊經理也官復原職了。半年後,父親回到原來的工作單位合肥市委黨校工作,完成了一個輪迴。再轉過年來,1963年春暖花開時,我上學啦……

1962年5月。我和父親去農場時,姥姥把弟弟帶到鄉下去了,我們從農場返回合肥後,姥姥又把弟弟送回來了,為了讓姥姥回去能有個念想,媽媽、姥姥、我和弟弟照了這張“準全家福”,因為父親當時正在外地學習、培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