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野模之南語:枕着一片黑色田野_風聞
人间后视镜-人间后视镜官方账号-我保证,故事与你有关。2021-12-16 10:27

她確實是個鄉村野模,但她又不像。視頻和照片中的她更像是一個真正的模特,特地跑到鄉村來拍攝。這讓她在一系列的TA中特別出挑,但是,又缺少了“鄉村野模”這個標籤必須提供的那種對立和割裂——人們想看的是“很像但不是”,唯有如此才能構成刺激,才好投入感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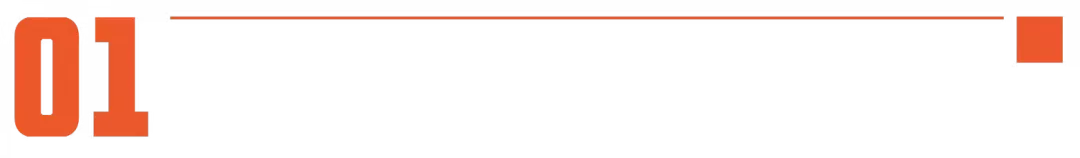
誰是之南語?
回答這個問題本可以很簡單:“鄉村野模”。你知道的,就是短視頻中經常見到的那種,田間山頭,忽然顯現一個踏着貓步的身影,男女莫辨,配着節奏激昂的音樂,一步步舞着剪刀腿,叉着腰仰着頭,高傲地走過來了,好似走在巴黎時裝週的T台上,定點,轉身,給你一個冷漠的目光。
然後你注意到衝突。這不是巴黎,甚至連一個小舞台都不是。這就是中國最普通的鄉村裏,最普通的一角,比如,一條泥土路。你擔心TA尖尖的十公分的鞋跟,會不會插進土裏拔不出來,扭傷那瘦骨伶仃的腳踝?還好沒有,TA走得穩穩當當,十分自信。你在凝視,你發現TA身上的衣服,形態誇張,顏色也鮮豔,但質料顯然非常粗糙,再定睛觀瞧,那甚至不是什麼質料,而是麻袋皮,塑料袋,菜葉子……這些鄉村裏隨處可見的東西,被TA煞有介事,又苦心經營地製造了,披掛在身上頭上。於是,你驚豔了,感慨了,悲憫了。還沒等更多的想法跟上來,你的手指習慣性地一撥,下一個視頻蹦出了出來,TA不見了。
這些TA,所謂“鄉村野模”,在近幾年的短視頻平台上出現了很多,將之南語也列進去,很方便,也很合理。但是,她似乎有些什麼地方不太一樣。
比如她的樣子。她的臉不漂亮,但很好記。略寬的臉頰線條分明,鼻樑挺直,高顴骨,堅毅的下頜角和下巴。眼瞼細長,濃眉,豐厚的嘴唇。她通常是沒什麼表情,很沉着的樣子,偶爾一笑,眼睛眯起來,露出酒窩,就羞澀了,顯出她23歲的年紀。身材無可挑剔,身高174,平直的寬肩,細腰窄胯長腿。她的貓步,表情和颱風,都是自學的,又好像渾然天成。總之,就是一個職業模特的樣子。
還有她的服裝以及拍出來的視頻。服裝有些是她自己設計製作的,有些是粉絲寄來的,都是她來搭配,很新穎,不帶一絲土氣。視頻和照片是表姐拍的,表姐大她七歲,兩人從小一起長大。表姐以前在鎮上的婚紗影樓工作,現在自己寫網文小説。表姐審美不錯,拍攝修片水準都很高。

這些全加起來,就成了她的“不太一樣”。她確實是個鄉村野模,但她又不像。視頻和照片中的她更像是一個真正的模特,特地跑到鄉村來拍攝。這讓她在一系列的TA中特別出挑,但是,又缺少了“鄉村野模”這個標籤必須提供的那種對立和割裂——人們想看的是“很像但不是”,唯有如此才能構成刺激,才好投入感想。她太像了,她簡直就是。
不過,這也不是什麼要緊的事。如同“之南語”這個名字。名字不是她的,甚至都不是她自己起的。這個ID本來屬於表姐,為紀念一段感情經歷而起,其義已不可考。拍攝和發佈這些視頻之前,她連個賬號都沒有,於是直接拿來用。後來紅了,去大城市參加活動,接受採訪,也就之南語了下去。
2021年的9月,中國貴州威寧縣雪山鎮,之南語在樹下坐着。一頂草帽遮住了她的眼睛,午後陽光漫漫,這是農閒時節,沒有什麼活兒要幹。遠處傳來各種動物的聲音,豬,羊,還有鳥叫,嘈雜又安靜。樹林裏後面的地裏有牛,兩條狗趴在她的腳邊。她就那麼坐着,坐在藍色板凳上,穿着一條黑褲子,白色球鞋,太陽鏡拿在手裏沒有戴,紫色長袖T恤的背上有一隻很小的翅膀,偶爾她説句話,露出很白的牙齒,低頭看地的時候又顯得憂鬱。
她坐在那裏,就像一個地地道道的本地姑娘,也像一個見過大世面的人,回到故鄉,暫時棲息在此地。除了之南語,她還有另一個名字,她自己的名字,跟古代的一個妃子同名,名字裏有一隻會飛的鳥。現在用兩個名字呼喚她,她都會答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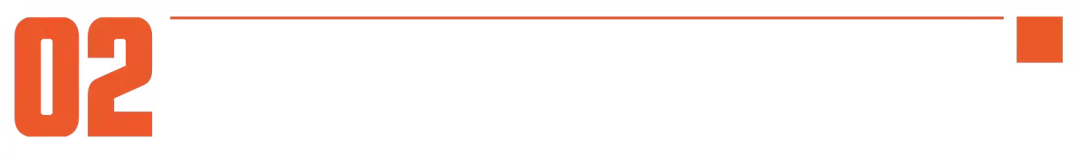
整個九月無新事,除了導演。
導演是拍紀錄片的文青,千里迢迢從北京,先飛,又坐了車,帶着人馬,浩浩蕩蕩地過來。這樣的紀錄片,之南語拍過不少。但她還是認真,把導演此前的作品找出來看了,看完覺得這可能是個能聊聊的人。在父母開的小賣部門口,她看見了導演,遠看挺魁梧一個人,四肢閒散地放着,透着老實,她就走過去,走過去才發現,導演已經架起機器,把她的走過去拍下來了。
導演也做了功課。他從一大堆短視頻博主裏挑出了之南語,研究了一番,決定來拍她。彼此雖是如此認真,但怎麼拍還是暫時沒頭緒。兩個人,還有各自的夥伴,每天吃了飯就各處走走拍拍,大量地聊。之南語説自己,內心懶散,目光呆滯,哪裏一坐就是大半天。此地能説話的人恐怕也就表姐一個,但從小一起,話再多也沒了,來了導演,大家都有點活潑。

先領導演去看常用的拍攝地,一所破房子,舅奶奶就在這房裏去世。表姐覺得恐怖,但之南語覺得美。她扮上,給導演走了一段台步:別緻的不對稱短款皮夾克,草帽(自稱雷鋒帽),紅色抽帶運動褲,運動鞋。導演拍了,倆人一起覺得,也都是別人拍過的。你想要真實的我,之南語説,我可以根據你的想法去做回我自己。這話有點玄,又被她撤了回來:“廣告片我也看過不少,我覺得你這樣拍有點不妥”。

然後回家。之南語家裏一對父母,四個孩子,她行二,但她不住家,出來跟表姐單過,住在爺爺奶奶家旁邊。房是普通村房,土牆,土柱,灰撲撲的煙囱,藍布罩着桌子和鐵架子的椅子,牀單也是藍,這就有點文藝氣,加上之南語和表姐,還有了閨閣氣,像大學畢業來城市闖蕩的年輕姑娘在城鄉結合部租下的房間。房間裏的東西都是別人送的,牀單,草帽,畫,書,包,高跟鞋,化妝品,娃娃是妹妹打籃球贏的,之南語很少買東西。她跟導演聊起《樹先生》,説自己就是樹先生,又自卑又驕傲,好面子,一無是處。還虛偽,虛偽在心裏想要什麼,人家送過來了,嘴上還是説着不要,因為害羞。平台上曾有人給她發私信:你是國際名模嗎,你在大山裏拍照有沒有蚊子?她回四個字:鄉村野模。也有商務邀請來詢價的,她回:隨便你們,看着給。然後就沒有了。還有個什麼地方邀請她去,要給她發一個“網紅獎”。她説不來了,我不值得擁有這樣一個獎。
那都是她還“紅”的時候發生的。那段時間她去過一些大城市,如果要形容,她説,那些地方就是星巴克的味道。現在這種事情也少,她的粉絲就停在某個數字不大動了,目前在快手,這個數字是7.8萬。她每週更新幾條,類似自説自話,收入還是靠硬照平模——店家寄衣服來,她穿上拍好,照片發回去,每月能有幾千塊,在這裏生活夠了。

在這房子裏,每天醒來,之南語和表姐倆人分頭在自己房間裏坐着,劃手機,看書,看電影,寫東西,縫衣服,久久無話。之前種玉米,土豆,挖地,現在農閒,手上的繭子已經褪了。有了拍視頻的想法,出去拍一條,回來繼續坐着。吃飯的時候,表姐去給爺爺奶奶做飯,之南語自己吃。晚上十點後之南語運動,跑步練功,讓自己還有柔韌度和好的肌肉線條。沒什麼不良嗜好,不玩遊戲也不社交,她説,爺爺奶奶老了,連個説話的人都沒有。雖然在家很頹廢,但對他們是個陪伴。沒法走出去,只有不停看電影看書,提高審美,用行動觀察世界。

聊了兩天,導演去拍之南語拍視頻。她説,這是你讓我拍的。她化妝,藍黑眼影上揚,眉腳下垂,戴上橙色絲絨耳環,綠色蕾絲裙用剪刀剪開,露出腿,海軍藍抹胸,軟底舞鞋。拍完卸妝,頭髮梳成兩個小辮子,用香皂搓臉,然後在塑料鏡子裏用卸妝紙擦去臉上的顏色,她看上去稚氣極了。此時大家很熟了,話題逐漸私密,她告訴導演,談過戀愛,但沒有愛情故事,你要聽,我可以給你編。前幾天有個人私信問她有沒有男朋友,要跟她一起隱居,一起打獵,她説你帶着財產來就可以了。她還説如果再談戀愛,除了那個人,不想見他的父母朋友和身邊所有人,不想相處,不想結婚,因為她沒有辦法愛屋及烏。
她再一次提起樹先生,説自己性格像。以前被拍,都是拍成“追夢的鄉村野模”,你想要真實的我嗎?這一次她要求導演:用你自己交換我自己。
她嚴肅起來了。講了一個拍攝創意,是她自己拍自己,以眼睛為中心,從內心世界出發,一身衣服從頭穿到尾。因為她又努力又頹廢,所以視頻用一個奇特的物件貫穿,首尾呼應,這代表了再普通的人也有自己的追求,不會一輩子都庸俗下去。前幾天她有害羞的,矜持的一面,不自然,拍出來沒有濃烈的情感,就沒有意義。“你拍的東西,我能想到,表姐能想到,大家都能想到”。她想要息息相關的感覺,“看到任何東西都會想到我”。
然後問導演:“你對我是什麼評價?”問完忽然警覺,羞澀地捂着嘴笑,笑着笑着倒在牀上,把臉埋在鋪蓋裏,不起來了。
她還有一個拍攝創意,拍她半夜睡不着的狀態。夜裏她關着燈,只有頭露在被子外面,她一動不動,想事情。她希望用幻想的方式拍,找一塊綠色的地,很多布料堆在她的赤身上,然後她去摸一塊自己喜歡的布。
第二天,她把最邋遢的自己穿給導演看:紅色絨帽頂上帶個球球,黑色棒球上衣,大嘴猴睡褲,解放鞋,半穿軍大衣,手藏在袖子裏。她説小時候有次父母吵架,吵得很兇,她穿的就是這身。是個記憶。
跟之南語一起待了六天,導演走了。最終拍成的紀錄片裏,有一個段落是之南語的創意:她的高跟鞋踩在鄉間路上,一張時尚雜誌撕下來的冊頁飄過來,被她踏在腳底。離開一個月後,導演給之南語寄了一份禮物:一行禪師的《佛陀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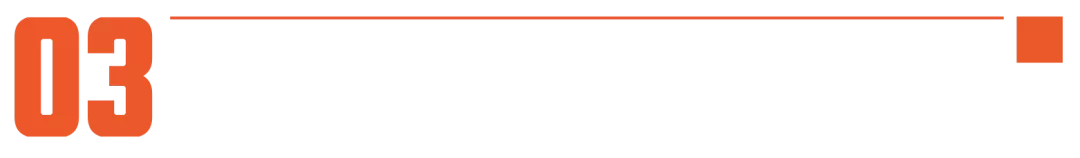
小時候之南語害羞、懦弱,還自卑。自卑一是因為窮,上到初中才有一雙正常的鞋子穿;二是因為長得高,課間操時站在最後面,被男生嘲笑。
小學的時候她成績好,全校前幾名,可是到初三,就不行了。
初中之南語住校,快畢業那年的一天,宿舍裏其它女生吵鬧,被宿管阿姨訓斥,要求寫檢查,她爭辯説,自己沒有吵,還是被要求寫檢查,於是在檢查裏寫“我沒錯”。學校找了家長,她依然堅持自己沒錯。老師沒有見過這樣的學生,將她驅逐,不許她再住校。之南語家在鄉下,沒了宿舍住,只能轉學。爸爸給她在新學校附近租了間民房,民房附近是工地,到了晚上,有工地上的男人來敲門,用手電筒晃她的窗户,偷她晾在外面的衣服。那樣的夜晚,她只能縮在牀上,跟同住的女孩抱在一起,抵禦恐懼。
高中的時候,之南語開始叛逆。不是高調的,成羣打夥的叛逆,那其實是找尋同伴,互相取暖,也發泄,是有療愈效果的。她的叛逆是靜悄悄地在自己世界裏叛逆:漂染頭髮,塗指甲,作非主流打扮;讀郭敬明,青春疼痛文學;看頹廢的電影,聽頹廢的歌,《妹妹揹着洋娃娃》《紅嫁衣》《黑色星期五》之類。

漸漸地,話越來越少,一開始連超市都不敢去,害怕和別人説話。時間久了之後,變成了不想説話,和大多數人沒有共同的話題,又覺得別人的話題無聊。
到了高三,學習成績太差,又不能不學,臨近高考,之南語逛街看到了一個舞蹈室,轉了進去。舞蹈室的老師想多收一個學生就多一份錢,也無所謂。於是她拿自己的生活費去學了兩個月。學上,之南語才發現自己特別喜歡現代舞,看到一個自己喜歡的舞蹈,會想哭,好像是自己內心憋着的一股勁,但被別人跳了出來自己不會跳,便難受,心很痛。
她要求學現代舞,可舞蹈室老師不教這個,他讓之南語跟着一個男生去跳他的劇目,之南語不願意,老師就放棄她,全然不管,一直到藝考結束。藝考的舞蹈是之南語自己着摸索學的,朱潔靜的《等待》。既不會基本功,也不懂現代舞,她就純粹按着自己的理解來,跳得張牙舞爪。藝考她隨便報了兩個專業,空乘和舞蹈表演。分數下來,空乘的分數挺高,本科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她又堅持了自我,選擇了舞蹈,所以就去讀了個專科。
大學學費12580,爸爸給了五千,剩下貸款。生活費是管同學借的。剛入學,12人一個宿舍,本專業的女孩在宿舍裏污言穢語,大吵大鬧,她轉身出去找老師,換了一個宿舍,跟其他專業的同學住。於是大學裏她也經常是一個人,睡覺,練功,跳舞,沒有什麼故事,同學們都挺喜歡她,因為她很安靜。
舞蹈表演專業包含很多舞種,現代舞也在其中,學現代舞的那段時間她很認真,老師也喜歡她,畢業匯演的時候讓她開場,跳了一個現代舞節目,她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一個心願,一直感激那老師。
舞蹈表演的畢業生,大多數都去做了老師。之南語不想去。她認為自己肯定是一個責任性很強的人,但知識能力不足以撐起一個孩子的前途,怕誤人子弟。當一個好的舞者,她覺得自己在這方面天賦又不夠。在學校時有人問她怎麼不去當模特,她有點動心。畢業後沒有什麼出路,她就想,做模特也行,於是自己摸索着學,學了之後發現,自己有點天賦。
那段時間,之南語給一個服裝店做平面模特,拍藝術照,拍了一段時間,她認為那個工作配不上自己,趕上表姐也對當時的工作厭倦,兩人就一起回了家。之後,她開始做自己的模特,學習設計衣服,剪裁,製作。
把腦袋裏想的東西把拍成自己想要的東西,是表姐的主意,放到網上,也是表姐的主意,那時候,之南語只是覺得這些還挺有趣,但什麼都不懂。


之南語在威寧上初中,威寧有個草海碼頭,據説有黑頸鶴。但她從來沒有看見過。
症狀應該早就出現了。初三搬到民房裏,她跟一個朋友一起住,一直到高中,每天兩人形影不離,逛街,剪頭髮,買衣服,各種好玩的事都在一起做,兩個人都談了戀愛之後,約會也互相跟着去。後來,倆人一起喜歡上那些頹廢的東西,一起聽歌看電影,之後害怕,晚上抱在一起睡,她們租的房子是一個很暗很潮濕的小房間。
她開始越來越不愛説話,不想動,孤僻,陷入深深的黑暗。那時候大家不懂什麼抑鬱症,只覺得是年少輕狂,叛逆。她去過醫院檢查,醫生給她一張問卷,她看了,不想答,她知道自己答完是個什麼診斷,她害怕。

最嚴重的時候,走在媽媽後面,她會忽然想把她掐死。看到很可憐的人,會想,為什麼要把自己過成這樣?然後憤怒,想把那人從懸崖上推下去。這些念頭可能持續四五秒,非常強烈,不受控制。醫生給過她藥,特別嚴重的時候她會吃,不嚴重,就靠自己扛,好在時間也不長,最多一個月就慢慢好起來,只是反反覆覆。
朋友依舊是個活潑的人,她喜歡快樂,喜歡和有趣的人在一起玩,上到高二,就有點排斥之南語的沉默,開始去找別人玩,兩個人鬧過一陣矛盾,還是互相離不開,於是又複合,繼續每天形影不離,像是一場愛情的演練。
忽然有一天,朋友不見了。再出現時,她剪掉了留了很久的長髮,然後也莫名其妙地不再説話。之南語不以為然,即使不説話,兩人在一起也有交流,只是不像以前。
草海有個廟,廟的旁邊是森林,朋友就在那個森林裏切破了手腕。然後跑了回來,沒死成。這樣陸陸續續地發生了很多次,跳河、吃藥,都有,都沒死成。後來就退學了,然後又回學校復讀,老師上着課的時候,她忽然哈哈大笑。那之後,開始吃藥。藥裏含激素,朋友本來是個很高、很瘦、很漂亮的女孩,吃藥後變成了一個大胖子。停掉藥,她又漂亮回去,胖了又瘦好幾次,她沒能上成大學。

18歲生日的那天,之南語去了草海旁邊的六盤水,她爬到水礦醫院的頂樓,想在那一天結束自己的生命。當真正想跳下去的時候,她是昏昏然的,一片麻木,聽着耳邊的風,手裏還握着手機。這時候手機震動了一下,她回過神來,下了樓,買了火車票,懶懶散散地回家去。短信就是那個朋友發來的,她準備好了生日蛋糕等着她回來。
前年,之南語給這個朋友介紹了一個男朋友,一個長得不好看,但很老實的男生。她想着可以有個人去保護她。他們在一起之後,朋友的病慢慢地好了,現在停了藥,兩人打算明年結婚。
十八歲生日那天的事之南語沒告訴過朋友。她沒告訴過任何人。她也覺得當時就是年少輕狂。她想抑鬱不是什麼嚴重的病,自己能扛過去,她也早已經習慣了自己扛過去。

從小之南語視力就不好。家裏人以為是近視,到了初三帶她去配眼鏡,但戴着眼鏡她也看不清楚。到了高一高二,眼睛開始痛,痛得死去活來,有一週徹底失明,沒有光感,生活無法自理。後來慢慢恢復,視野還是像被一層霧罩着,那時候,她真的害怕了,去華西醫院檢查,醫生説,是先天性的角膜病變,兩隻眼都有,如果正常的眼睛是透明的玻璃,她的玻璃上就有很多污點。要治療,只能做手術,用激光把上面的病菌刮掉,但治了之後會不斷復發,所以沒有徹底失明之前不建議做手術,吃藥、輸液、複查也都沒有意義。醫生告訴她,視力下降到0.1之後再來醫院。
醫生還説,這個病程多長誰也不知道,有的人可能要到四五十歲才失明,有的人可能一輩子都不會失明,如果到失明的程度,就只能換角膜。
家裏的兄弟姐妹都挺健康,只有之南語是這樣。眼病經常復發,感冒後,哭過後,或者到了某個季節,都會劇痛。痛過了那幾天,也會好。平常看書看電影,她也不覺得模糊,因為她不知道清楚是什麼樣子。她只去過一次電影院。眼病復發的時候她不會告訴父母,不想讓他們那麼緊張,説了,爸爸會心情不好,媽媽會帶着她去搞迷信算命。但這對她來説就是一件很小很小的事情。這個她也早已習慣了。
之南語養了兩條狗,其中一條是盲的。她還記得收養它之後,它的眼睛先是充血,然後變成了白色。她送它去鎮上的寵物醫院打針,它還很歡快地滿街跑,差點被車撞上,她滿街地追它,好不容易追上,帶了它回來,養到現在。它一直很活潑,經常出去招惹別家的母狗。她説,眼盲一點兒也沒耽誤它談戀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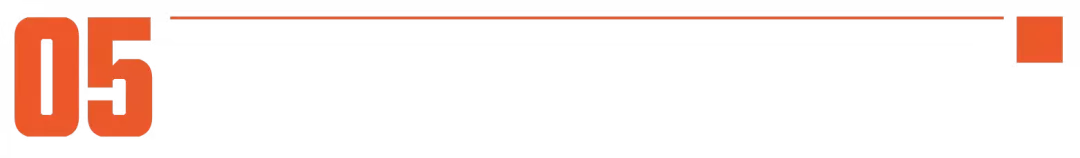
十月底,之南語買了件旗袍,想在自家閣樓上拍個有點詭異氣氛的視頻,但是買來才發現,她有點長胖了,旗袍穿不下。她把旗袍給媽媽穿,表姐掌機,跟媽媽一起拍了幾張合影。
媽媽穿着旗袍,説冷。有張照片上她套上了之南語的軍大衣。之南語穿白色的吊帶,長裙,化了妝。媽媽不覺得好看,説她塗的口紅像吃了死耗子,鬼一樣。在之南語的家鄉,這些都是非常不正當的,很醜的,他們喜歡的照片就是端端正正面對相機,直直地站着。
照片上,母女倆有非常相似的頓挫的輪廓。之南語把照片發到微博上,配文是“我和我媽媽”。
幾天前,家裏停電,奶奶家點了一支蠟燭,之南語捧着一本書在燭光下讀,表姐在旁邊打毛線,爺爺奶奶坐着聊天,她忽然有一種感覺,好像回到了小時候。2021年快過完了,這是一年來她能想到的温馨的瞬間。
“小時候很喜歡一隻雞,家裏來了客人,雞被殺掉吃了,我一直哭,爸爸打了我一頓。從此以後,就再沒什麼喜歡的東西。”她説她活到現在,一點也不叛逆,一直很乖順。
時裝,短視頻,網紅,之南語現在在做的事情,家裏人都知道,也支持,但談不上理解不理解。實際上她自己又能理解多少呢。別人關不關注她,她認為對她來説沒有多大的影響。以前在平台上過一次熱搜,那段時間關注很多,別人告訴她,趕快到處去評論,露臉,去吸粉,認真經營一下,可能會有一百多萬粉絲。她覺得這些話“好商業”。“你要從內心真正喜歡我之後,再來關注,這個是我想要的。我不是什麼超模,我就在鄉村幹這個事情,我沒有你想象的那麼好。你喜歡我做我自己,你來關注我,我很開心,我不希望你來關注我之後,再來教我怎麼做事。”

對之南語影響比較大的人,她説,是張國榮。高中的時候聽他的歌,看他的電影,痴迷於他的病態美——“當然他不是病態的,但當時在我看來就是一種病態美。無論心情好壞,我把他當作自己精神上的慰藉。我的很多事情沒有辦法向別人説,像我生的這些病,向家人説,向朋友説,他們都不理解。沒有人陪伴我的時候,張國榮陪伴我。”
因為喜歡張國榮,她懷疑過自己是不是“藝術病幻想症”,後來發現不是。
她現在感覺自己越活越普通。
有那麼一天,她去田裏放牛,把牛趕到地裏,感覺一切都是那麼美好。“牛在吃草,天空很藍,我在大自然裏自由自在,身心都是放鬆的,很多詞在內心讚揚自己”。過了幾分鐘,牛跑了,她趕快去追,牛跑得很遠,她追上去,趕回來,筋疲力盡,特別煩燥。“我當時覺得自己不過是個普通人,也因為這些事情浮躁不堪,還把自己抬得這麼高,就會悔恨自己前幾分鐘的讚美。我不過很平凡,很平凡,很平凡的一個幹農活的莊稼人而已”。

“鄉村野模”的視頻,之南語有些時候想放棄,但是想到放棄,又會感覺痛苦。“放棄不是因為我不火,是我覺得對這個東西有疲倦感了。”可是不做這些事情更痛苦。她喜歡創作帶來的成就感,要徹底放棄它,需要找到其他的創作方式。她讀劉震雲,讀渡邊淳一,看賈樟柯,晚上睡不着,她想寫故事,想得天馬行空,恨不能馬上出版;早上起來,要麼沒有慾望去寫,要麼寫過好幾次都失敗,一開始寫父母,後來又寫農村戀愛,校園戀愛,都沒寫成功,失敗了就全部刪掉,自己都不再看,“內心多半時候悲涼到極致”。
之南語在雪山鎮,她的家鄉,她還走不開。她想着這個地方可能還有很多沒有發現的東西,等把它們用盡了,再去其他的地方去發現更好的東西。
表姐説,她願意拿着20塊錢去徒步旅行,吃不飽穿不暖也沒關係。“可能有些人對流浪的定義是追求自己,”之南語説,“真正的自由是把自己內心緊繃着的東西放下。”她也想去流浪,第一,沒有錢只能流浪,第二詩和遠方什麼的,總要去遠方看一看。“我很窮,我是一個靠精神維持生存的人,所以想用更多的東西充實自己,現在看到的都是書裏和電影裏,想要真切地感受這些還是得出去,即是要待下來也是晚年。我想象自己揹着白色的翅膀,還是要飛的,還是希望被別人看到。我消失的那一瞬間是要被記錄的。”
她説她和表姐都是活在自己世界裏的人。表姐説,你是個光滑的圓潤的石子,遊在大海中。
之南語曾寫過一首詩,叫《一邊,一邊》,詩是這樣的:
“我走過麥田
穿過樹林
拔下耳機
一邊聽歌
一邊聽風”
她解釋着“一邊一邊”的雙重涵義,一層是時間上的重疊,一層是物理上的分裂。她一邊説,表姐一邊笑,“誰管你一邊兩邊的!沒有人在乎你的一邊一邊。”那次之後,她就沒有再寫了。
作者:葉三
編輯:簡杉
人間後視鏡工作室出品,點擊關注更多精彩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