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風華|基於共同人身所有權的家庭,今天是否還是一種命運共同體?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2021-12-20 21:54
李風華|湖南師範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何以為家?在這個紛繁變化的世界中,與家庭有關的各種問題往往迅速成為輿論熱點,背後所折射的權利義務問題則表明,家庭的邊界一直在變動。而準確把握當代家庭的本質,是構建一般社會理論並理解各種與家庭有關的社會變化的前提。
家庭是個體來到這個世界上所首先要面對的羣己關係,也是絕大多數人終其一生都需要打交道的實踐領域。從政治哲學的角度來看,對家庭的理解是認識羣己領域的一個起步,同時也是把握個體與社會、國家之間關係的一個重要環節。理解家庭,不只是認識家庭本身,也是用以補足從個體到整個世界的政治與社會圖景。
筆者嘗試從人身所有權的角度去理解家庭,將它定義為一個基於共同人身所有權的命運共同體。在這個基礎上,婚姻、離婚、死亡都涉及個體的自我所有權和家庭的共同人身所有權之間的關係。
家庭:一種基於共同人身所有權的命運共同體
家庭首先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共同體與社會相對立,指參與者主觀上能夠感覺到共同屬性的社會組織,它有可能是一支軍隊、一個教區、一個班級、一個車間,等等。從形式上看,共同體與我們通常所稱的組織或羣體是一回事,不過共同體更強調羣體的歸屬感。
家庭無疑是一種共同體,即韋伯所謂“最為省事”的共同體的類型。但家庭並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共同體,而是一種命運共同體。命運共同體不同於通常的組織或羣體。阿馬蒂亞·森認為身份是多樣的,而且可以選擇。“一個人的公民身份、居住地、籍貫、性別、階級、政治立場、職業、工作狀況、飲食習慣、所愛好的運動、音樂鑑賞水平、對社會事業的投入,等等,使我們歸屬於各個不同羣體。每個人同時屬於這許多個羣體,而其中任何一種歸屬都賦予她一種具體的身份。沒有一種能夠被視為該人唯一的身份,或者一種單一的成員劃分。”儘管每個人都有多種身份,但絕大多數身份並不能與家庭身份相提並論。“我”與某個人組成一個俱樂部,深感高山流水,知音難得,甚至願意同年同月同日死。這在生活中當然有。但是這種“我”與知音的命運共同追求,只是個案,並不具有普遍性。尤其重要的是,雖然“我”與知音對於共同命運的追求是合法的,但“我”與知音所構成的共同體並未得到法律意義上的共同人身所有權的確認,並不足以構成一種命運共同體。也就是説,“我”和“我”的知音僅僅是在個人自由的意義上實現了共同的命運,但在政治上並未獲得實質上的集體權利。企業是另一種類型的共同體,它在某種程度上也具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未來。但是企業也不足以稱之為命運共同體,每個人可以自由地進入企業,同時也可以自由地退出企業。人們在企業中並不必然藴含着共同歷史和共同生活的命運。同理,教區、鄰里等社會組織,也是如此。總之,在當代人類的所有組織中,能夠稱得上命運共同體的並不多。國家是一種命運共同體。全人類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仍然停留在應然層面,其在政治權利和義務上的現實性是非常薄弱的。家庭可以當之無愧地構成一種命運共同體,不僅在過去有着非常久遠的歷史,而且在可見的未來仍然有其牢不可破的地位。
那麼,如何從政治哲學的角度去理解家庭這個特殊而又最常見的命運共同體呢?筆者認為,基於上一節的認識,應當從人身所有權的角度去把握。在家庭內部,“我”在一定程度上直接擁有了對方的身體,具有了部分的人身所有權,而對方也相應地擁有“我”的身體。這種相互的人身所有權是家庭構成命運共同體的基本依據,因此可以説,家庭是一種基於共同人身所有權的命運共同體。具體而言,可以從如下幾個角度去理解。
第一,對子代而言,家庭並非一種自願的選擇,這種非自願性構成命運共同體的初始條件。當代意義上的家庭是兩位成年異性共同自願的組合,如果僅僅停留在自願這個層面,那麼,家庭似乎與其他社會組織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看上去,它類似於一種俱樂部,但僅僅侷限於兩個異性(這裏我們暫不考慮同性婚姻、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等制度)。兩個人可以自由地結婚,也可以自由地離婚。但是,作為一個完整的典型意義上的家庭,是不可能將子女排除在外的。而且,正是由於子女的存在,才決定了家庭問題的特殊性。
當夫妻有了孩子,這帶來了與前述“自願”完全不同的權利問題。父母固然是自願結婚並且自願生育的,但是他們並不能自願決定孩子的所有特徵。而對於孩子而言,這在權利上是一個完全嶄新的問題,因為他來到這個世界上,根本不包含任何的自由意志。他不能自由地選擇是否來到這個世界上,他不能自由地選擇自己所處的國度,同理,他也不能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父母。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上,對於他本人而言,並非自願,由於這種非自願的出生行為,他就被賦予了一個嶄新的身份——家庭成員。僅僅由於這一事實,就足以將家庭與社會領域中絕大多數組織區別開來。一般地説,社會領域所通行的原則應當是自由。但是,我們能夠對家庭內部成員賦予徹底的自由嗎?比如説,新生兒的父母有權利拒絕撫育孩子嗎?
很顯然,至少在當代,父母撫育孩子已經不僅僅是一種權利,而且必須是一種義務(意味着孩子對父母的人身具有權利)。因為如果我們賦予了父母自由解散家庭的權利,孩子就很有可能會在飢餓寒冷之中死去。當然,也許會有人認為,父母對孩子的愛將足以避免這種糟糕的情形。但是如果政治哲學淪落到訴諸“愛”等情感因素的時候,這説明政治哲學自身無力解決問題,它必須承認這樣一種邏輯上的困境:數千萬乃至上億的新生兒出生,但現存的成年人卻可以完全有權不顧這些人的死活,聽憑其受凍捱餓而死。要克服這個困難,政治哲學就必須通過權利義務來介入新生兒的生存處境,而不是聽之任之。父母沒有權利來決定是否撫養這個孩子,同理,孩子也不能自由地決定(假設他在有了一定的意識和能力之後,比如 6 歲以後 18 歲以前)是否脱離家庭。父母與孩子之間這種非自願的權利義務關係,決定了家庭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作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家庭有着與其他組織截然不同的權利義務結構。其他組織的成員結構及其相應的權利義務安排,本質上是人為的,是成員們自由意志的體現與表達。然而,家庭的結構卻是被自然的生育結構先天決定的。在每一個家庭的內部,人們的命運彼此息息相關。而跳出了單個的家庭,每個人的命運卻相差極大。因此,家庭成員之間的權利義務關係更為緊密,一方對另一方的人身、財產擁有權利,實施這權利時往往並不需要另一方的同意。這顯然有別於絕大多數羣己領域中的人際權利結構,後者往往通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消極自由。
第二,家庭是一個內部實施共產主義的集體經濟單位。在小農經濟中,家庭既是一個共同的生產單位,也是一個共同的消費單位。有學者認為,工業社會里,“家庭已經從一個生產性的單位轉變為一個消費性的單位” 。這種看法是錯誤的,它將家務勞動排除在生產勞動之外,僅僅只是因為家務勞動沒有獲得市場交易的收入。一個人為其他家庭提供家政服務,這是一種可以獲得報酬的公認的勞動,而這個人為自己家庭提供家政服務,難道就不能視為一種勞動嗎?這種看法之所以錯誤,在於將生產理解為一種狹義的商品生產。確實,傳統的小農藴含着要比當代家庭更為豐富的經濟與社會含義,但是當商品生產被排除在當代家庭範圍之外後,家庭作為一個比較純粹的養育勞動和家務勞動的場所,才日益凸顯出本質性的內在權利結構。
馬克斯·韋伯將共產主義確定為家族的一個基本特徵,其中家族作為一個重要的生產與消費組織而存在。而當工業化來臨後,家族解體為家庭和企業。為家庭掙取收入的勞動往往發生在家庭之外,比如企業組織。但我們可以看到,共產主義因素並未因此消失,相反,當代法律更加強調了家庭內部的共產主義因素,最突出的一點就是家庭的財產共有。在家庭裏面,一個人的收入很自然地成為另一個人(通常是配偶)的共同收入,這在其他組織中是無法想象的。甚至可以説,家庭共產主義是當代世界各種制度中最為普遍的一種制度,它超越了政治制度和宗教觀念上的差異和對立。那麼,有必要追問:這種家庭共產主義的權利基礎是什麼?
第三,家庭共同人身所有權是家庭共產主義的基礎,而不是相反。兩個人通過婚姻創造了一個新的家庭,同時也創造了家庭的共同財產。共同財產既可能來自婚後兩人各自的勞動,同時也可能來自婚前財產的收益,還有可能來自個人的自願贈與和投入。不管共同財產依據什麼樣的方式產生,其內在的依據是家庭中的共同人身所有權。所謂共同,指的是作為整體的家庭,而不是兩個人獨立貢獻的加總。比如,我們不能因為其中一個人對於家庭財產的貢獻特別大,在離婚時財產分割上對該人給予更為有利的分配(如果雙方自願不平等分配,這是可以的)。
第四,家庭的共同人身所有權並沒有抹殺個體的自我所有權,而是兩者互相嵌置,互相限制,形成一種多級人身所有權。家庭的共同人身所有權是相對的,存在着一定的限度,其限度就來自個體的自我所有權。絕對的共同人身所有權意味着:配偶中的一方可以限制另一個人的行動,同時也受到對方的對等限制;一方可以任何處置對方的身體以及與身體有關的活動和資產,比如施加暴力,強制某種行為,對方也擁有同樣的權利;一方有權知悉對方所有的信息,自己也同樣沒有任何隱私和自主空間。相對的家庭共同人身所有權則有別於此,其中每個人對配偶的行為有一定的約束,比如反對婚外性關係,使用另一方的勞動收入和財產收益,等等。但是個體可以拒絕家庭中的暴力,對於自己反對且不知情的配偶的債務可以拒絕承擔,同時也有一定權利保持自己的隱私或個人空間。
家庭暴力問題值得單獨解釋一下。假如家庭中的人際關係與家庭之外的人際關係完全一致,那麼,根本就不需要反家庭暴力的專門立法,因為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刑法等法律就已經足以應對家庭中的暴力問題。但之所以反家庭暴力需要專門立法,這不僅僅是因為家庭中暴力現象比較常見,而且它藴含了這樣一個前提,即由於家庭中的成員彼此擁有人身所有權,因此一定程度上的人身攻擊是法律所允許的。換句話説,家庭的共同人身所有權規定了家庭相處之道的區間範圍——在彬彬有禮的消極自由主義人際關係與觸及法律的家庭暴力之間。在這個範圍內,家庭成員大可以相愛相殺,不管是愛得如膠似漆,還是恨得死去活來,都屬於人們的自行選擇。
家庭中的個人仍然擁有本人的自我所有權,這種自我所有權並未被婚姻所擊碎,但或多或少受到了限制和削弱。很難在家庭的共同人身所有權與家庭中個體的自我所有權之間劃出明確的界限,不同的國家、不同的家庭中,這種界限的具體位置又是不同的。有的家庭,夫妻各自管理各自的收入,僅僅在共同支出時才進行商量;也有的家庭所有的收入歸其中一人支配,另一人僅僅得到零用錢。有的家庭中,不僅無法容忍婚外性關係,甚至異性交往也加以嚴重限制,但也有家庭對於婚外性關係更為寬容。這也意味着,家庭中的自我所有權與共同人身所有權是相互嵌置的,共同人身所有權的範圍受到兩個自我所有權的主體的共同約定,同時共同人身所有權在限制了個體的自我所有權的同時,又通過個體的行動表現出來。一個具有獨立意志的個體行動,既是其自我所有權的權利表示,往往同時又代表了其家庭的共同人身所有權,向家庭所有成員負責。這種共同人身所有權與自我所有權相互嵌置的情形,是家庭幸福的源泉,也是各種家庭矛盾的根源。
結婚、離婚與死亡
結婚、離婚和死亡是家庭產生或者解體的重大事件。在這裏,我們探討結婚、離婚和死亡等事件所藴含的共同人身所有權問題。
結婚是獨立的兩個個體之間的自由結合,意味着一個新家庭的誕生。從人身所有權的角度來看,它意味着兩個人決定共同讓渡自己的人身所有權,從而形成一種集體性的共同人身所有權。這裏需要闡明三個問題 :
第一,婚姻的實質並不是愛情,而是對各自身體及其財產的相互佔有。愛情可能是許多人走入婚姻的原因,但愛情並不是婚姻的依據。婚姻意味着兩個人彼此承認,對方對於自己的人身擁有某種程度的所有權,可以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這顯然不是愛情所能夠涵蓋的。康德將婚姻視為配偶雙方對性器官的相互佔有,其邏輯是:每個人都有性衝動。一個人想使用另一個異性的性器官並進而佔有後者的身體,其唯一合乎道德的做法就是讓對方也同樣有權使用自己的性器官以及自己的身體。由於身體是自我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這也意味着雙方都承認對方對於自己的人身所有權。而婚姻意味着兩個人彼此可以長期擁有對方整個人,這其中包含對對方身體的所有權。康德的理論觸及了婚姻的實質,但由於過於重視貞節觀念,並且在性問題上喋喋不休,因此被當代許多論者不屑。如果我們將康德的論述擴展至一般意義上的人身所有權問題,就不難看出康德的洞見與不足:洞見在於,婚姻即相互佔有;不足在於,忽略了家庭的共同人身所有權中更為重要的內容是財產,家庭中新生的孩子對於家庭成員的人身及其相應的財產也擁有類似的權利。
第二,為什麼人身所有權是可以讓渡的。美國《獨立宣言》宣稱:“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渡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但徹底的自由至上主義者則堅持,如果禁止讓渡某些權利,事實上意味着消滅了這些權利,説明了自我所有權並不存在,這才是真正對個人生命與自由權的侵犯。其結論應當是,任何法律不得禁止或者限制個人出售他所擁有的事物,每個人都有權把自己的人身權利商品化,出售給他人,包括愛情、道德責任、尊嚴,只要個人是自願的,他可以賣身為奴,甚至獻出生命。討論人身所有權的可讓渡性的文獻通常所舉的議題是勞動法、拘禁等問題。但是,結婚就是一例更為典型的人身權的讓渡,男女雙方都放棄了自己的部分人身權利,從而組建起一個共同人身所有權的命運共同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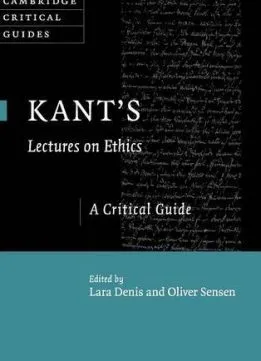
第三,讓渡的結果是集體人身所有權,而不是股份制人身所有權。在勞動力市場中,當“我”將自己在 8 小時之內的人身所有權交給企業,“我”所獲得的是一份工資。至少從形式上看,這是一種平等交換的讓渡。然而對於婚姻而言,這種人身所有權的讓渡與勞動力市場中的讓渡存在區別,婚姻中雙方讓渡給一個新的實體——家庭。借用蘇力用合夥比喻婚姻的説法,家庭是一個不可分割的共同人身所有權,它類似於一種公共產品,而不是股份制的人身所有權。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每個人在家庭中的權利本質上是對等的,也是同一的。
如果説結婚就是彼此讓渡人身所有權而形成共同人身所有權,那麼離婚就是這種共同人身所有權的解體,每個人都恢復原初的自我所有權。與此同時,雙方將共同財產進行分割。從權利角度來看,離婚的核心內容不是感情的對錯,而是財產的分割。一般情況下,現行的權利實踐是平等分割,有孩子則將孩子的撫養考慮進來。孩子的人身所有權歸誰?這確實是離婚所帶來的比較特殊的人身所有權問題。根據中國婚姻法的實踐,孩子與親生父母彼此仍然擁有一定的權利,這可以理解為一種代際共同人身所有權的繼續。
這裏有兩個問題值得單獨拿出來:一個是“婚外性關係”,一個是不平等的人力投資。一些學者反對法律介入婚外性關係。“人們的生活空間,在一個自由的社會 , 會大於在一個不自由的社會。把處置婚外性關係(它是發生在有道德選擇能力的成年人當中的自願行為)的權力交給警察和國家,無疑是每一個人自由生活空間的縮小。”確實,在當前的中國法律實踐中,配偶一方對於另一方的婚外性關係並不具有提起訴訟的權利,但在家庭財產分割的時候,有無過錯已經普遍成為財產分割的一個依據。這事實上説明,前面康德所述配偶雙方彼此對於性器官的權利(亦即貞操),一定程度上獲得了保護。20 世紀末,有學者聲稱:“據説正在起草中的《婚姻家庭法》就擬創造‘配偶權’的法律概念,規定夫妻雙方有互相忠誠的義務,一方對另一方不忠,被侵害的一方可以根據‘配偶權’所賦予的權利要求法律保護 , 或者説要求法律對對方進行制裁。理由是通過這樣的規定來防止輕率離婚,以減少由離婚而產生的社會問題,維護婚姻家庭的法律秩序。這樣的建議,最好不要成為法律。因為它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常識, 即有些領域,是不能靠法律治理的,感情就是這樣的領域。‘配偶權’可能增加離婚的難度,但是它能夠解決夫妻雙方的感情問題嗎?用‘配偶權’維持沒有感情的婚姻 , 是否具有道德合理性?”現實的法律實踐已經確證了這樣一種配偶權的存在,雖然並沒有這樣的定名。離婚中過錯方在分割財產方面的失利,其實已經證明,配偶雙方彼此擁有人身所有權,這種權利的受損方可以主張賠償並得到法律支持。

所謂不平等的人力投資指的是這樣一種情形:婚姻存續期間,家庭對於配偶中的一方進行了較長時期的人力投資。比如女方工作所獲得的收入相當一部分用於資助男方攻讀博士學位,而男方在獲得博士學位後提出離婚。此時如果僅僅平分財產,顯然對於女方不利。在筆者的閲讀經歷中,美國和中國都有判處男方賠償女方的案例。這些判決事實上支持了女方對於男方的人身所有權以及該人身所有權所藴含的人力資本投資。
死亡也是婚姻和家庭解體的一種方式,而且是終極方式。除了意外或者完全個人自主決定生死的情形,死亡本身有時也涉及共同人身所有權的實踐。比如當患者已經喪失意識,無力決定自己的生死時,通常由其家屬來決定是否繼續治療。一般而言,這種共同人身所有權的行使應當劣後於個人的自我所有權。個體的自我意見在各種治療方案的選擇中佔據優先地位。但有時,為避免個人的決定未必符合其利益,我們往往又允許家庭成員基於共同人身所有權的意見優先於個人自主意志。比如患者因為不堪痛苦,要求安樂死或者放棄治療,而家屬卻要求繼續治療;或者有時患者渴望治療,而家屬由於預算負擔而放棄治療。種種情形説明,個人的自我所有權與家庭的共同人身所有權之間存在着互相嵌置,而不是簡單的誰先誰後的問題。
死亡並不意味着共同人身所有權的驟然消失。一般而言,配偶一方死亡意味着共同人身所有權不復存在,但人身所有權並不只是一種完全依附於身體的權利,它還投射到依附於該人身的財產以及人格等權利。在現行的法律實踐之下,生者仍然擁有對於逝者的人身所有權。比如可以接受遺產,可以決定逝者屍體的處置方式。逝者擁有的知識產權在其身後 50 年內仍然有效,這意味着生者對於逝者的人身所有權仍然可以踐行。而為逝者的名譽權而提起訴訟,並不限於 50 年,比如有關狼牙山五壯士的名譽權訴訟。總之,由於逝者的人格、財產權利等方面的主張,也必須通過生者來爭取,因此死亡實質上加強了生者對於逝者的人身所有權。
家庭的過去和未來
上述對於家庭的人身所有權的解釋是基於當前中國的主流法律實踐,這種人身所有權的狀態具有當下的合理性,它不同於歷史上的家庭人身所有權,也肯定不是未來的最終狀態。事實上,與家庭有關的各種人身權利一直在變化。歸根結底,在個人與家庭之間的人身所有權的結構變化,是一個受制於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歷史進程。在具體的表現形式上,家庭的人身所有權體現為國家法律的相關規定,因此,家庭人身所有權的變遷,直接表現為相關法律規定的變遷。
在最早的原始社會,個人生活在氏族和部落之中。隨着私有制的誕生和階級的分化,原始社會的部落解體,個體主要是生活在家庭(或者家族)之中,而其安全保護則由國家來承擔。發展到當代,傳統的家族已經湮沒,基本上不具有法律上的地位。家庭成為個體最重要的身份,而國家則構成另一種個體不可迴避的共同體。在家庭與國家之間,存在着各種各樣的社會組織,但是隻有家庭與國家才能夠稱得上命運共同體。值得注意的是,國家能夠決定家庭的人身所有權的安排——當然,從終極的意義上看,國家也是所有個人在有關家庭等人身所有權問題上所表達出來的集體人身所有權。
早期的國家可能對於家庭內部所有的事務都一概不理,賦予家長以絕對的權威,家長可以決定內部成員的生死。秦漢時期,家長若殺死自己的子女或奴僕,他人是無權過問的。但反過來,子女或奴僕殺死家長,這顯然不容於法律。這説明,此時並不存在前文所述的家庭共產主義,家庭成員各自的人身權利並不對等。家庭類似於一種首領制度的等級制羣體。隨着人權觀念的演進,家庭內部的不平等程度有所減輕,如家長對於成員的生殺大權被國家所剝奪,但不平等的人身權利仍然是傳統家庭的基本格局。中國的傳統社會中,男性可以一妻多妾,妻與妾之間的權利是不平等的。在財產方面的處置權則基本上由男性家長所把持,女性成員則只能有一點點私房錢,並只能在少數事情比如家務方面具有一定的權利。此外,還要看到,男性家長去世之後,對女性配偶構成了一個特殊的問題。家族甚至可以限制乃至剝奪寡婦在家庭財產和事務方面的權利。
進入現代社會之後,傳統的家族逐漸解體。家庭共產主義逐漸取得了如本文所述的基本形式,家庭成員實現了大體上對等的共同人身所有權。當然,這個過程並非直線的直接實現婦女解放運動所期望的婚姻自由。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魯迅所提出來的,娜拉出走以後,怎麼辦?事實上,雖然結婚自由、離婚自由被寫進了婚姻法,但由於收入差距的擴大與階級的分化,女性尤其是貧窮女性往往受到不平等的對待。與此同時,法律實踐中對於家庭的保護,亦即對於家庭共同人身所有權的承認,反而要比以前更多,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國家對於家庭養育孩子、贍養老人的税務減免。

現代福利國家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國家介入原來由家庭共同承擔的權利與義務,比如義務教育、養老等問題。換句話説,孩子不僅僅是一個家庭的孩子,同時也是全社會的孩子;老人不僅僅是一個家庭的老人,同時也是全社會的老人,社會承認國家整體對於孩子和老人的人身所有權。在這裏,國家共同人身所有權得以凸顯。此外,家庭的人身所有權還受到國家層面的制約。過去幾十年裏,中國家庭的生育權受到國家層面的限制,這説明國家共同人身所有權的強有力存在。當然,國家共同人身所有權並不是今天才有的,歷史上婚配權和生育權也曾受到國家的強力干預,比如中國歷史上許多王朝建政之初為鼓勵生育而強制婦女婚配。這説明,家庭在生育問題上的人身所有權從來就不是一種天賦的自然權利,它是國家所賦予的權利。某種具體的權利存在與否,取決於當時形式上作為共同人身所有權的國家意志。
一個突出的現象是,當代社會中,離婚日趨普遍。黑格爾這樣看待婚姻:“婚姻就其概念説是不能離異的”,但由於婚姻含有感覺,因此存在離異的可能性,而立法則應當儘量使這一離異可能性難以實現。當代社會離婚現象的普遍性説明了婚姻或愛情的脆弱性。但是,這並不是家庭的脆弱性,因為家庭仍然以單親的情形繼續存在。

馬克思主義的終極目標是共產主義社會,那裏不存在私有制,因此也同樣不存在家庭。許多人唱着各式各樣的家庭頌歌,就是因為家庭共產主義是冷冰冰的市場經濟中一個温暖的庇護所。從社會變遷的角度來看,家庭共產主義也是階級再生產的一個環節。當財富分化程度日益加劇、階級躍遷日益困難的時候,一個人的出身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未來的命運。“無產者的一切家庭聯繫越是由於大工業的發展而被破壞,他們的子女越是由於這種發展而被變成單純的商品和勞動工具,資產階級關於家庭和教育、關於父母和子女的親密關係的空話就越是令人作嘔。”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對這種家庭頌歌持以批判態度,就是因為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歌頌家庭的背後,是無產階級無力成家或者無產階級家庭成為一種被剝削對象的殘酷現實。當代許多國家通過房產税、遺產税等手段來限制鉅額財產的代際傳承,這在諾奇克看來,是對個體的自我所有權的侵犯。但這恰恰證明,在個體、家庭乃至所有社會事務中,國家這個全社會人民的共同人身所有權的主體,是所有權利的來源。只有國家消滅,家庭才有可能消滅。當兩者都不復存在的時候,我們才有可能真正實現這樣一個聯合體:“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