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野:澳大利亞想與中國和好嗎?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袁野】
在自吹和譴責了國會山暴亂一番後,特朗普結束了自己的總統生涯,留給世界的卻是一地雞毛,他的那些“跟班小弟”們也開始慌了,帶頭大哥走了,我們該怎麼辦?
澳大利亞就是其中之一。“五眼聯盟”裏,澳大利亞大概是最死心塌地的了,和中國交惡,則是莫里森政府“表忠心”的結果。特朗普拂拂衣袖走了,莫里森是不是要緊急掉頭,而這個頭該怎麼掉,中國又會買賬嗎?
中澳關係為何會走到今天這一步?
全世界的學者和研究機構,只要是在正經進行分析判斷,不是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那種拿錢辦事的,都得出了一個共識性的結論:和美國一樣,澳大利亞還沒學會適應一個崛起了的中國。
例如,前澳洲駐華大使芮捷鋭(Geoff Raby)在其新書《中國的大戰略和澳大利亞在全球新秩序中的未來》中強調,堪培拉的外交和戰略政策必須建立在“對中國不可阻擋的崛起如何深刻改變世界秩序的嶄新理解”的基礎上。他説,澳大利亞需要用高超的技巧來駕馭一個新的“有界多極秩序”。
全球學者開給堪培拉的“藥方”也是一樣的:既要“應對”中國,也要與其合作。換言之,就是需要保持平衡,在競合之間走鋼絲。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戰略研究榮譽退休教授休•懷特就寫道:
“莫里森認為他可以與北京方面達成協議。但要管理與這個地區大國的關係,就必須做出艱難的選擇和妥協……中國是一個我們必須學會與之合作的國家,不僅因為在未來的幾年乃至幾十年裏,沒有哪個國家能提供與中國同樣的出口機會。”
“我們必須做出妥協,在一些問題上讓步,以便在其他問題上取得進展。有時情況不會很好,但當你與大國打交道時,這就是國際政治的運作方式。”
“現實情況是,國際關係像任何其他類型的關係一樣,總是需要大量的妥協和讓步……這是我們作為一個主權國家必須做的,在一個我們不能事事隨心所欲的世界裏,我們要盡我們所能取得最好的結果。”
墨爾本大學亞洲研究所研究員梅麗莎•康利•泰勒説得更直接:
“當我聽到有人説澳大利亞別無選擇、只能與中國對抗時,我想起了新加坡駐華大使比拉哈里•考西坎的話:‘我曾經問過一名越南高級官員,河內領導層的變動對中越關係意味着什麼。他回答説,每一位越南領導人都必須與中國和睦相處、並勇敢地面對中國,如果你不能同時做到這兩點,你就不配當領導人。’”
“不幸的是,目前澳大利亞只做到了一半。”泰勒評論道。
法裏德•扎卡里亞博士在澳大利亞羅伊研究所的2020年度演講中也是這麼建議的。這位哈佛博士擁有一大堆頭銜:《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大西洋月刊》特約編輯、《紐約時報》多本暢銷書的作者、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主持人,這絕對是西方主流輿論的代表了。他建議: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澳大利亞如何在保持其獨立性的同時,繼續確保與中國的貿易?……我認為,在某些方面,最好的樣板是新加坡。李光耀曾對我説,他最驕傲的一件事是他能夠維持新加坡獨立的事實。從某種意義上説,它被視為一個親美國家,但從來不是一個反華國家,沒有被中國認為是敵人。”
遠在紐約的扎卡里亞可能是真的對西太平洋的情況不太瞭解,不然他不會建議讓澳大利亞“屈尊”學習新加坡。他也許是忘了、也許壓根就沒意識到,新加坡能夠做到這一點,首先是因為他沒有堪培拉的那種對中國的種族和意識形態優越感。
走鋼絲需要高超的政治技巧和手腕,但澳大利亞決策者目前還沒有到討論能力問題的程度,他們還停留在上一步:我願不願意走鋼絲?我想不想在抗衡中國的時候維持起碼的合作?
答案很明顯:我不!

被種族主義困擾的澳大利亞外交
2019年,前新加坡外交官、駐聯合國大使馬凱碩(Kishore Mahbubani)提出了這樣一個問題:人們在做地緣政治判斷時,靠的僅僅是冷靜理性的分析嗎?如果情緒影響了我們的判斷,我們對此意識得到嗎?還是説它是在潛意識層面裏起作用?如果誠實地回答這些問題,就必須承認:非理性因素總會發揮某種作用。
馬凱碩是正確的。“中國不是高加索人種的國家,這本就是地緣政治競爭的一個因素,而且它或許也能解釋為什麼西方國家在情感上對中國崛起反應如此激烈。”
作為離中國最近的西方國家,澳大利亞的反應也是最激烈的,這並非巧合。“幸運之邦”對中國人的敵意比其建國的歷史還要古老,從19世紀的“黃禍論”開始,這個國家就在堅持不懈地妖魔化中國,冷戰時代這種妖魔化更是變本加厲,相較之下近幾十年的和睦反倒像是插曲。
幾年前,當中澳兩國的關係開始緊張時,澳大利亞迪肯大學國際關係學者潘成鑫就總結道,“澳大利亞與中國的緊密經濟聯繫未能動搖其歷史思維方式,這或許並不令人意外”。他補充説,如果有什麼區別的話,“地緣經濟上的鄰近似乎加劇了這種焦慮”。
悉尼大學美國研究中心的現代歷史學教授詹姆斯•柯倫也在2020年12月的一場演講中説,早在1893年,“澳大利亞殖民地傑出的知識分子”查爾斯•亨利•皮爾森就寫道,中國是西方戰略優勢的最大潛在威脅,“澳大利亞同胞,那些生活在分隔白人和有色人種的邊界上的人,將會是第一個敲響警鐘的人,是第一個採取措施保衞西方文明的人。”柯倫教授説,在澳大利亞的國家戰略心理中,“過去的幽靈”有一種反覆出現的趨勢,這有助於“更好地理解為什麼衝動有時會壓倒澳大利亞外交務實、理性的強大傳統”。

新南威爾士大學的中國歷史教授路易絲•愛德華茲(中文名李木蘭)更深入地闡釋了這一點。在澳大利亞世界中國研究中心的2020年度演講中,這位曾翻譯過《紅樓夢》的教授直言痛陳,中澳關係之所以走到今天這一步,歸根結底是因為澳大利亞人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
“澳大利亞與亞洲的關係正困在一台倒退的時光機裏——我們的主流媒體、政客、公務員、文藝界和大學的的領導人都存在一個錯誤的觀點:澳大利亞人是白人,他們的祖先來自利物浦、利默里克(愛爾蘭城市)或是倫敦。很明顯,他們無法真正看到這個國家的人口在語言、宗教、膚色和階級上的全景。”
“澳大利亞的亞太觀同樣讓人沮喪。我們是五眼聯盟的成員——美國、英國、加拿大、新西蘭和澳大利亞。但澳大利亞的眼睛卻受困於戰後的眼病——通常説這是‘斜視’。我們知道這種眼病,因為澳洲的許多高層在領導我們時一隻眼睛盯着英國,一隻眼睛盯着美國……而伴隨着這些眼睛的嘴呢?它們似乎只會説一種腔調,並且只説英語。而耳朵則有些聽力問題,儘管有很多先進的助聽設備。”
愛德華茲直言不諱地表示:
“我認為,澳洲人們還不適應自己比亞洲人更虛弱、更貧窮、更沒有影響力——尤其是與中國人相比。我認為在管理澳大利亞政策和敍事的關鍵機構中存在着種族問題。許多澳大利亞領導人依舊幻想着自己在將專業知識和更好的原材料居高臨下地交到心懷感激的北方(指亞洲)‘發展中國家’的人們手中。”
“世界的變化比澳大利亞領導人能夠理解的似乎還要快……我們所處的時代已經變了,即便我們的國家依然被白人東方主義者‘紆尊降貴地施捨窮人和棕色人種,指導他們’的幻想所主導……不知為何,今天的澳洲還是有很多身居要職的人以為澳大利亞不僅向亞洲提供了礦產資源,還提供了優越的知識和技術。是時候有人該告訴他們開張視聽,好好向亞洲學習了。”
“我擔心,我們現在的這批領導人正在削弱我們的中等強國的地位——每次我們的領導人開口説話,我們都在變成一個更小、更令人厭惡的國家。我們針對的是誰?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一個正在崛起的軍事強國,以及我們最大的客户。幹得好,貿易國。”
“我們現任領導人的視野被一層東方主義的面紗所籠罩,它受困於過時的種族主義和文化等級制度。而中國的崛起意味着我們需要非常、非常、非常清楚地看到這個國家。掀開東方主義的面紗,揭開‘竹簾’——我們目前似乎正竭盡全力閉目塞聽——可能會使五眼更有效地工作。”
愛德華茲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國與亞洲的女性和性別研究,但卻比很多國際關係學者更能直擊澳大利亞外交的要害。如果不是要退休了的話,恐怕她也無法如此仗義執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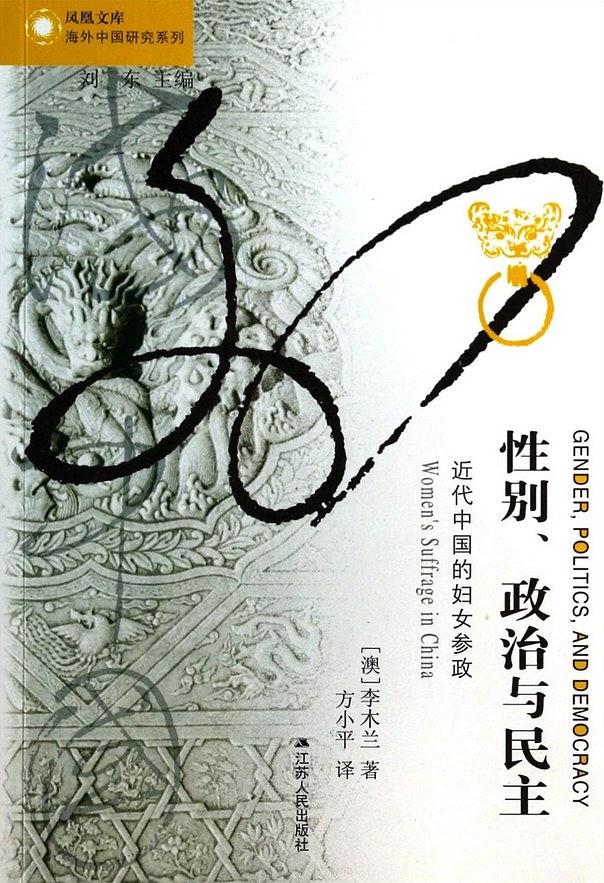
李木蘭的作品
很多人正想要“新冷戰”
愛德華茲和柯倫等人的批評是否“過火”,是否“冤枉”了莫里森?其實他們還多少有些“為尊者諱”呢。2019年5月莫里森意外贏得大選、正在歡天喜地之時,《對話》(The Conversation)新聞網就一不小心暴露了總理的另一面:虔誠到不行的教徒。在勝選時,這位總理第一時間感謝了“神蹟”。
“莫里森的五旬節派基督教信仰(Pentecostal Christian faith)是理解他政治生活的核心”,《對話》報道稱。該教派是20世紀初出現在美國的新教教派的一支,“它強調個人與上帝的直接聯繫為那些得救的人所專有,這導致了一種相當二元的世界觀:有得救的和被詛咒的,有正義的和邪惡的,有虔誠的和邪惡的。”
“在五旬節派的這種排外觀點中,耶穌是唯一的救贖之路。只有那些被耶穌拯救的人才有希望在天堂獲得永生。在最好的情況下,它能使人謙遜;最壞的情況是自命不凡和傲慢自大。只有重生的基督徒才能得到救贖,穆斯林、猶太人、佛教徒、印度教徒、無神論者和非重生的基督徒都註定要在地獄的折磨中度過永恆的時光。”《對話》稱。
這種信仰有助於解釋莫里森為何敢於不顧一切地對抗中國。從現實主義的視角看,這位總理的蠻幹勁頭幾近不可理喻,但從一位教徒的角度出發,就不難理解了:莫里森似乎認為自己已經被上帝選中,正引導着澳大利亞走向應許之地,這足以讓他在水面行走、使死人復生,化一切不可能為可能!

在澳大利亞2019年即將舉行大選的背景下,莫里森開通微信公眾號。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有這麼一位“受困於過時的種族主義和文化等級制度”的總理,盤踞在大位上的頭腦和智囊們自然也就將澳大利亞歷史中最陰暗的沉渣統統“發揚光大”了。理智的、至少有健全知識的外交官和中國問題專家們靠邊站了,ASPI這樣的反華軍事遊説團體和口無遮攔的反華後座議員們大行其道,中澳貿易的衝擊波絲毫影響不到他們,他們對中國的真實情況也是一無所知。堪培拉也許真的想不通,面對高貴的“英語民族”的怒火,中國人為何不僅不驚恐萬狀,竟然還敢反擊?
當然,也不能將澳大利亞的蠻行全部歸因於種族主義和愚蠢傲慢,畢竟就算是再無腦的人,也不可能相信所有關於中國的謠言。從“中國滲透”、“中國威脅”到“中國出口禁令”,無非是為兩個目的服務的:首先,轉移人們對澳大利亞社會日益加劇的不平等的憤怒;其次,爭取澳朝野對美國亞太戰略的無條件支持。今年早些時候,《澳大利亞金融評論》的安德魯•克拉克就指出,莫里森身邊的一些人認為,他可以在下屆聯邦選舉中使用“中國牌”作為他的王牌。
至於另外一些人,包括澳大利亞一些最知名的戰略分析師,則早就迫不及待地宣稱“冷戰2.0”已經開打了。在與捉摸不定的恐怖主義進行了近20年的鬥爭之後,他們無比渴望像冷戰時代那樣,再次樹起一個實實在在、清楚明確的意識形態對手。對澳大利亞、乃至對整個西方來説,“冷戰”意味着美好的舊時光:對手最終分崩離析,柏林牆倒塌了,西方領導人們喜氣洋洋地在聖誕節宣佈勝利。這些難道不比小心翼翼地走鋼絲更吸引人嗎?
至少堪培拉目前似乎真的是這麼認為的。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