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姆·萊博維奇:美國當初為什麼積極組建聯合國?背後有盤大棋
【文/山姆·萊博維奇,翻譯/觀察者網 馬力】
對於大多數美國人來説,美國擁有全球軍事霸權這一簡單明瞭的事實也許從未有一刻進入過他們的腦海:那些部署在海外的軍事基地和在海外發動的戰爭距離他們的日常生活過於遙遠,而在軍中服役的士兵們則與大多數美國人碎片化的社會生活幾乎沒有交集。
可是當人們偶爾想起美國軍隊時,他們對自己軍隊的評價還是相當高的。在歷次問卷調查中,美國軍隊都展現了最受信賴的國家機構的形象。甚至在各政府部門經歷各種開支削減之後,美國不斷擴張的國防預算仍然保持了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
人們對美國政治充滿抱怨和質疑,但他們對美國軍隊卻是極為滿意的。這支軍隊不但是全世界最為強大的,而且也是全世界最為昂貴的:美國的軍事開支超過了排在後面10個國家的總和。

美國為何會成為世界警察?
歷史學者史蒂芬·沃特海姆(Stephen Wertheim)在其2020年10月出版的《明日世界:美國全球霸權的誕生》(Tomorrow, the World: The Birth of U.S. Global Supremacy)一書中。對美國社會的上述心態給出了自己的解釋。
他在書中聚焦於二戰時期最為關鍵的幾年,為我們回顧了與戰後世界秩序形成有關的一段極為重要甚至顯得頗有些瘋狂的歷史。史蒂芬·沃特海姆在書中介紹了多位相互之間關係密切的政府決策者和學者為他們心中日益成形的“美國世紀”描繪藍圖的過程,讀者可以從閲讀這本書得出結論:那些美國決策者和學者們早在二戰時期,就已經產生“美國應取得全球軍事主導權”的想法了。
這對美國來説的確是一個很重大的歷史轉變——當納粹德國1940年佔領法國時,美國的陸軍規模僅僅名列全球第19位,甚至還不如當時的荷蘭陸軍。在介紹美國決意以軍事手段重塑世界秩序(為了達成此目的,美國甚至還發起成立了聯合國,這是有些違反直覺的)的這段歷史時,史蒂芬·沃特海姆對美國在上世紀40年代的外交政策,進行了頗有些“修正主義”色彩的解讀,他的觀點有助於我們以全新的視角審視當今的諸多國際問題。
《明日世界:美國全球霸權的誕生》一書為我們介紹了美國地緣政治專家們在世界秩序問題上的深入思考和不斷演進的各種觀點,並且很清晰地介紹了美國外交政策開始轉變的時間和具體過程。圍繞美國戰後外交政策的演化發展這一主題,該書介紹的許多具體細節都會令讀者感到耳目一新,甚至與人們所熟知的情況是完全相反的。
這本書重點介紹了法國於1940年6月被納粹德國佔領之後的一段歷史,當時頗具影響力的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已經在着手為納粹德國佔領整個歐洲之後美國的國家前途進行謀劃了。這段歷史的具體細節如下:
在珍珠港事件發生之前,美國國務院撤銷了負責戰後戰略規劃的委員會,這時美國外交關係協會開始走出來為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確定邊界。最初,該協會的一些成員認為美國可能在歐洲陷落後龜縮在一個“四分之一個地球”大小的區域裏面,即北至加拿大、南至拉丁美洲北部的一個便於軍事防禦的區域。但很快他們就意識到,美國的一切經濟活動很可能被鎖定在這一區域裏面。當某個地緣政治集團實現對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主導時,美國在全球的貿易活動將面臨被切斷的風險。他們擔心,“四分之一個地球”對美國來説也許太小了,不利於美國人維持較為滿意的生活水平。
因此,該協會的一些人士開始把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邊界擴大到整個西半球(主要包括南北美洲、東太平洋、部分大西洋、部分北冰洋以及部分南極洲——觀察者網注),但隨後他們意識到這個範圍還是有些侷促,對美國來説不具有可持續性,這一地區無法做到在經濟上獨立運轉。美國南部和拉美地區需要向外出口農產品,而美國北部地區需要出口工業製成品。因此,西半球這一勢力範圍無法為美國提供一個真正獨立運轉的經濟基地,這樣美國就無法與被納粹德國主導的歐洲展開競爭;把太平洋地區也納入進來的確可以為美國北部地區的工業製成品出口找到市場,而且可以為美國提供黃麻纖維、橡膠和錫等資源,但是把太平洋地區納入進來之後,為美國勢力範圍之內的農產品找到出口市場的壓力就更大了;這樣一來,把英國也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就是唯一的解決方案了,英國當時是全球一個主要的農產品進口國。
史蒂芬·沃特海姆在書中寫道:“經過數月的研究,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戰略規劃專家們發現,如果納粹德國能夠在戰後實現對歐洲的長期穩定佔領,那麼美國就必須把世界上其他幾乎所有地區都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才行”。就好像一個正處於發育期試穿不同尺碼服裝的孩子,美國也試着為自己的勢力範圍規劃了不同的邊界,那些戰略規劃專家們最後發現,也許只有20世紀初形成的帝國主義世界體系那樣大的勢力範圍才能讓美國感到舒適。
在外交政策層面上來説,美國戰略規劃專家們得出的上述結論實施起來其實很簡單。時任《紐約時報》記者、美國外交關係協會會員漢森·鮑德温(Hanson Baldwin)曾這樣總結道:“這要求美國實現對全世界的主導,而且要有大英帝國在旁邊給予長期密切的配合”。
然而問題在於,美國民眾並不會輕易接受這一外交政策:美國須與英國結為緊密聯盟,美國須承受全球軍事擴張所帶來的成本,而且把全世界都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是頗具帝國主義色彩的做法。當時一位參與外交政策討論的人士指出:“就盎格魯—美利堅人的性格來説,在這一外交政策上獲得他們的合作幾乎是不可能的,除非政府能夠獲得某個強有力的組織的支持”。
這其中的問題在於,美英兩國必須做到在扮演世界警察角色的同時,還能夠避免被貼上帝國主義標籤。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戰略規劃專家們最初並沒有把創建國際組織的方案納入考慮,他們覺得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那樣的組織其宗旨含混不清且過於理想化,並沒有發揮很大作用。可是在1942年,也就是美國外交關係協會中的諸位專家被美國國務院納入重新啓動的戰後戰略規劃機構的那一年,他們發現創建某種新型國際組織的確有其好處:他們意識到創建聯合國這樣一個國際組織,在説服美國公眾接受美國外交政策轉向這一問題上,是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
與此前的國際聯盟不同,聯合國能夠通過由英、美、中、蘇四大國(以及稍後加入的法國)所主導的安全理事會(Security Council)來集中行使“警察”權力。的確,聯合國裏面還有聯合國大會(General Assembly)這一機構,不過按照羅斯福政府時期副國務卿薩姆納·威爾斯(Sumner Welles)的説法,聯大隻是“一個用來對那些小國表示慰藉的小禮物”。
在1943年1月舉行的一場長達2小時的聽證會上,薩姆納·威爾斯向羅斯福總統保證,美國加入聯合國並不會對這位總統塑造戰後世界秩序的工作構成干擾,由四大國組成的安理會將在戰後世界秩序中扮演關鍵決策者的角色(需要指出的是,由於四大國負責在聯合國做出重大決策,羅斯福總統甚至認為並不需要為聯合國設置一個永久性的總部,他認為聯大可以一年召開一次,以便讓那些小國發發牢騷)。
自那以後,組建聯合國的工作進行得相對比較順利,至少在策劃發起成立聯合國的那些戰略家們看來是如此。1944年,在秘密召開的敦巴頓橡樹園會議上,四大國敲定了新組建的聯合國的一些具體細節。1945年,在舊金山舉行的一場公開會議上,世界上其他國家也加入了就成立聯合國進行的對話。來自發展中國家和非政府組織的代表要求進行一系列重大改變:他們希望聯合國能夠對經濟和社會問題給予更多關注;他們對四大國否決權這一設置的必要性提出了質疑;他們還希望推動聯合國就人權問題發表聲明。
不過,四大國還是為自己保留了否決權,以避免舊金山會議上提出的對聯合國憲章進行修改的各種方案獲得通過。四大國的外交部長們在時任美國國務卿小愛德華·斯特蒂紐斯(Edward Stettinius Jr)的家裏,召開了會議並就一些重要議題達成了共識。雖然四大國為了維護聯合國“自由主義堡壘”的聲譽在一些重要問題上作出了妥協,但聯合國這個新的國際組織絕不可能對大國維護自身地緣政治利益的單邊行為造成干擾。如果美國想在某地部署軍事力量,他可以把此事交予聯合國通過並藉此使自己的軍事行動合法化,而聯合國絕不會對美國的單邊軍事行動造成任何實質性阻礙。史蒂芬·沃特海姆在書中把這一安排戲稱為“工具性國際主義”(instrumental internationalism)。甚至連美國國會中那些保守的民族主義者對此也是欣然接受的,這一點並不奇怪。

美國昆西治國理政研究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明日世界:美國全球霸權的誕生》一書作者史蒂芬·沃特海姆
不但在國會里,聯合國在美國社會上也收穫了廣泛的支持。美國國務院特地為此策劃了大規模公關行動(包括散發數百萬份宣傳冊、舉辦數百場演講會和記者會),目的就在於讓美國公眾相信,聯合國是維護世界和平的最佳方案和終極希望所在。美國為實現成為世界警察的目標打造了一個勢力均衡的新體系,而這個新體系被成功地包裝成了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的勝利果實。
史蒂芬·沃特海姆在書中對聯合國崛起過程的傳統歷史敍事,進行了令人頗感耳目一新的修正。英國首相丘吉爾和羅斯福總統1941年共同發表的《大西洋憲章》(the Atlantic Charter)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人們通常認為,《大西洋憲章》是美國為打造二戰後以聯合國和自由人權價值觀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所邁出的第一步。然而史蒂芬·沃特海姆卻認為,情況並非如此。丘吉爾首相在起草憲章時曾提出要建立一個“有效的國際組織”,但羅斯福總統卻堅持主張應該把這句話刪掉,他認為“重建一個像國際聯盟那樣的組織是毫無意義的”。事實上,《大西洋憲章》既不意味着威爾遜主義的復活,也沒有為《世界人權宣言》奠定基礎。史蒂芬·沃特海姆指出,《大西洋憲章》其實是美國戰後戰略規劃的早期成果,是盎格魯-美利堅時代到來前的序曲。
就這樣,史蒂芬·沃特海姆推翻了人們對歷史的一個錯誤認識——20世紀40年代是美國從孤立主義走向國際主義的轉折點(a simple shift from isolationism to internationalism)。事實上,在那一時期,最為激烈的美國外交政策辯論並非在高尚的國際主義和保守的孤立主義兩派之間展開,而是在各種不同版本的“國際主義”之間進行的。在二戰期間,被摒棄的孤立主義的本質,其實是一種較為剋制的國際主義,它主張擴大貿易、建立國際組織、制定國際法、限制用軍事手段解決國際糾紛等等。當這種不帶有干涉主義色彩的國際主義主張被打上“自私”、“閉關自守”和“孤立主義”的標籤之後,那些認為美國應掌握軍事霸權的人,便為自己的主張打上了“國際主義”的標籤。這時聯合國的價值便凸顯出來了。自那以後,輿論風向便偏向了帶有軍事色彩的“國際主義”一邊。你是願意做一個“自私的孤立主義者”還是願意做一個“關心世界事務的國際主義者”呢?
史蒂芬·沃特海姆這本書很顯然對我們這個時代具有重要價值。在後冷戰時代裏,人類歷史的發展道路已經被無休無止的戰爭、金融危機、地緣政治緊張關係以及當下蔓延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徹底劫持了。極右翼民粹主義者強烈反對全球化進程,中間勢力希望世界回到“自由國際主義”狀態,而左翼進步派則希望美國能放棄帝國主義道路,我們今天的國際體系以及美國在這一體系中的角色正再一次面臨重大變數。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應排除美國推行一套全新的、能夠獲得新的政治聯合勢力支持的外交政策的可能性。
史蒂芬·沃特海姆的研究工作事關如何重塑美國今天所面臨的這個時代,作為昆西治國理政研究院(the 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這家新成立的智庫的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他的理念與該智庫“推動美國外交政策從無休止戰爭向積極外交轉型”(move foreign policy away from endless war and toward vigorous diplomacy)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昆西治國理政研究院由科赫基金會(Koch Foundation)和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執掌的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共同出資成立,旨在“抓住一代人才有一次的機會把美國進步派和保守派中有相似立場的人匯聚在一起為美國外交政策指明一條理性、良善的道路”。《明日世界:美國全球霸權的誕生》一書所揭示的歷史細節讓我們意識到,美國社會所秉持的那種“作為送給全世界的禮物,軍事霸權體現了美國無私的利他主義精神”的觀念是多麼荒謬。
瞭解歷史可以幫助我們釐清當前美國外交政策的來龍去脈,而且還可以為我們制定新的外交政策提供思想線索;不過做到這兩點還不夠,我們還應當搞清楚,該如何讓我們希望推行的那些新的外交政策真正發揮政治效力。史蒂芬·沃特海姆的這本書為我們講述了一個理念如何獲得接受的故事——一種外交政策理念不但獲得了合理化解釋,而且還被每個美國人視為理所當然的常識。
令人遺憾的是,雖然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但這本書並沒有就今天我們該如何操作提供太多指導。在上世紀40年代,美國公眾還沒有參與重大政策問題的討論(民主、共和兩黨曾達成君子協定,不在1944年大選中觸及聯合國問題)。雖然智庫更接近權力階層,但在當時的美國,還沒有大量分析人士對民意調查進行研究。其實,真正關鍵的是政治精英們對美國民意的揣測。到了1945年,他們已經很確定,如果把軍事霸權用“自由國際主義”加以包裝,美國民眾就一定會接受。
在書的末尾,史蒂芬·沃特海姆轉而對美國當下的情況進行了分析,把1945年的精英共識和21世紀美國外交政策精英們的自鳴得意進行了明確的區分。他這樣做並不難理解,解構美國政治文化正是他寫作這本書的目的所在。在他看來,在國會里圍繞國防預算具體數字發生的爭吵是無足輕重的,龐大的軍費開支本身就已經説明美國政治精英們對掌握軍事霸權是怎樣的態度了;此外,與政治精英們自認為可以公開支持或反對什麼相比,美國民眾對冷戰冒險主義的看法也已顯得不是那麼重要。就這樣,美國政治精英在軍事霸權問題上的深度共識,已經使人們無法再就外交政策問題進行真正意義上的討論了。
這就是今日美國的現實。那些希望在外交政策領域實現民主決策的人,也許應該把自己與美國社會的態度更緊密地捆綁在一起。例如,四分之三的美國人都希望美國能從阿富汗和伊拉克撤軍,這個民意説明了什麼?史蒂芬·沃特海姆最近在英國《衞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這説明美國在海外的軍事行動已經在國內激起了強大的反對聲音,美國官方共識已經暴露了自己的弱點,這對那些希望美國外交政策走上進步道路並轉而更加關注氣候變化和全球不平等問題的人們來説是一個機會之窗”。
我希望他的判斷是正確的。不過我們並不能排除“四分之三”這個高比例也許與阿富汗和伊拉克這兩場沒有結果、沒有盡頭的災難性戰爭本身有關。也許當下美國社會對海外軍事冒險主義的厭倦心理,並不意味着一個劃時代的轉變,而僅僅是人們對戰爭失敗的一種情緒表達。其實這種情況曾多次出現(如越戰時期),一旦情況變化,美國社會就又會重新團結在戰旗之下(如第一次海灣戰爭時期)。
而且,即便“四分之三”這個數字反映了美國社會對軍國主義的深刻厭惡,我們也無法明確做出“美國將奉行更具國際主義色彩外交政策”的判斷。其實,我們有理由認為,這個數字反映了美國民眾對世界事務的一種“自私”的抗拒,因為同一項調查發現,75%的美國受訪者認為“美國應優先解決國內問題而不是國際問題”。我們該如何理解這一調查結果呢?這要看優先解決的到底是什麼樣的“國內問題”以及問題以什麼形式表現出來。不過,這應該無助於氣候變化等真正的全球性問題的解決。
若要在美國打造新的政治聯合勢力,我們就必須搞清楚美國民眾為何一直以來願意忍受美國政府抓住軍事霸權不放的政策。無論這個政策多麼體現精英主導,無論上世紀40年代那些精英向美國公眾如何欺騙性兜售其軍事擴張政策,美國社會並沒有表現出很強烈的抵制態度。史蒂芬·沃特海姆在書中暗示,這其實是因為那些戰略規劃專家對美國人內心深處的某種自我認知進行了利用。他寫道:“美國是世界上最為傑出的國家——這是美國人對自己國家的一種無需證明的公理性的認識,是他們內心國家認同的一部分,所以並不僅僅是美國人支持政府的外交政策或國家戰略那麼簡單”。這一觀點是非常有見地的,但史蒂芬·沃特海姆並沒有在書中把這個問題展開討論。
在20世紀40年代美國精英的話語體系中,他們為了對奪取軍事霸權戰略進行合理化解釋找到了三個具有不同來源的論據。雖然我們還不能斷定這三個論據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獲得了美國民眾的接受,但是由於其中每一個論據都有其政策上的意義,對它們在美國政治文化中的地位進行分析還是非常必要的,對於那些希望搞清楚美國當時為何沒有走上進步外交政策道路以及今天是否可能走上這條道路的人們來説,進行這樣的分析是尤其有價值的。
第一個論據來自人們普遍持有的一種觀念,即“強者有義務幫助那些不那麼走運的人”。上世紀40年代的美國很顯然已經是一個超級大國,許多美國人認為自己的國家對全世界擔負有某種責任。傳媒大亨亨利·盧斯(Henry Luce)和副總統亨利·華萊士(Henry Wallace)在戰後世界秩序問題上出現了很明顯的分歧,亨利·華萊士認為應構建一個全球化的人民的世紀(a globalist People’s Century),而亨利·盧斯卻主張建設一個資本主義的美國世紀(capitalist vision of an American Century)。不過,他們二人都認為美國對未來世界秩序的形成負有責任。亨利·盧斯指出:“無論從美國自身利益的角度來説還是從歷史的角度來説,美國都對身處其中的這個世界負有責任”。而亨利·華萊士認為:“就像一個18歲的男孩無法避免成長為一個成年男子一樣,美國也無法擺脱自己身上的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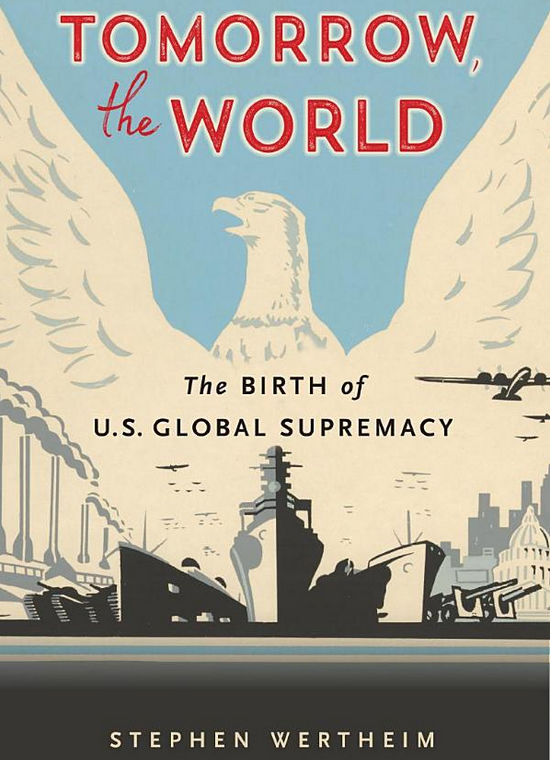
史蒂芬·沃特海姆所著《明日世界:美國全球霸權的誕生》(Tomorrow,the World:The Birth of US Global Supremacy)一書封面
這其中真正體現技巧的一點在於如何把履行美國肩上的責任與打造強大軍事力量進行掛鈎,德國慕尼黑髮生的反抗獨裁者事件,為這種掛鈎提供了很好的助力。曾負責向美國公眾推銷聯合國的助理國務卿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Archibald MacLeish),在上世紀30年代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哲學思想,他指出:“自由主義者應該有強壯的肌肉作為支撐,這樣才能履行與邪惡抗衡的義務”。阿奇博爾德·麥克利什認為持反戰思想的作家們是缺乏責任感的,並就此與文學界的同僚們分道揚鑣。
就這樣,和平主義者成了弱勢羣體,而那些行動派在社會上佔據了顯赫位置,美國通往軍事霸權的道路變得越來越平坦了。美國民眾很感謝軍隊所做出的貢獻,他們認為美國軍隊是奉獻、責任和無私利他精神的踐行者。對於今天那些希望美國能走上進步外交政策道路的人們來説,沒有必要對“美國對世界負有責任”這種觀念進行批判,他們更應該解決的難題在於如何讓“履行美國對世界的責任”與“打造強大軍事力量”這兩者實現脱鈎,他們應該積極提出這樣一種觀點:美國對世界的責任不應僅僅表現為強制力的使用,還應表現在對全人類公共利益的投資上。
這就涉及美國精英上世紀40年代對軍事霸權戰略進行合理化解釋的第二個論據了。此前西方有一種家長式的觀念,認為“文明”國家對自己的殖民地負有義務,而美國精英們內心也有這樣一種責任感,這種責任感可以被視為上述家長式義務觀念的一種發展,其發展歷程包括殖民美洲大陸時期以及對加勒比海地區和太平洋一些地區實現佔領的距離我們較近的時期,即橫跨盎格魯-美利堅民族四處擴張佔領的整個歷史時期。
一些歷史學家認為,20世紀40年代是美國“不受約束的擴張主義”歷史的一部分,史蒂芬·沃特海姆對此觀點是持批判態度的。在他看來,20世紀40年代是美國曆史的一個斷裂期,美國開始致力於在世界上尋求至高地位,美國不僅開始在“遠離歐洲對手的被殖民地區”尋求這種地位,而且也開始在與“全球主要對手的較量”中尋求這種地位;然而此前的美國並非如此,對軍事主導權的渴望並不是美利堅的民族基因。
史蒂芬·沃特海姆試圖闡明這樣一種觀點:我們有必要意識到,美國軍事霸權戰略的制定者所具有的那種全球抱負在某種意義上來説並不是與生俱來的,而是後來才產生的。然而,由於史蒂芬·沃特海姆是從那些以歐洲為中心的地緣戰略專家的視角來寫作的,他難免忽視一點:殖民主義對理解世界歷史以及理解美國自身在世界上的角色都具有重要意義。畢竟,史蒂芬·沃特海姆自己也曾表示,種族主義視角曾經在“白人的負擔”這個問題上讓各殖民主義國家擁有了共同話題,它在上世紀40年代也彌合了盎格魯-美利堅民族獲取世界主導地位的各種不同方案之間的分歧。
我們還無法判斷這種種族主義觀點在美國能向下滲透到哪一社會階層。一些人會好奇,在一個種族地位不平等的世界上,美國的地緣政治霸權到底有沒有讓那些身處社會底層的美國白人獲得一絲“心理優勢”呢?美國非洲裔社會學家、歷史學家、作家威廉·愛德華·伯格哈特·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就曾對吉姆·克勞(美國劇作家托馬斯·賴斯於1828年創作的劇目中一個黑人角色的名字,後來逐漸演變成了一個貶抑黑人的名稱和黑人遭受種族隔離的代名詞;此後人們用“吉姆·克勞法”泛指美國南部各州針對非洲裔美國人以及其他少數族裔為實行種族隔離制度而制定的各項法律,用“吉姆·克勞主義”指代美國統治階級對黑人實行種族隔離和歧視的一整套政策和措施——觀察者網注)時代白人在美國社會的角色進行過分析。今天,那些白人民粹主義者要顛覆當今的世界秩序,他們希望能增強美國的自主權。他們有時也會批評美國在國外的軍事幹預行動,但他們從未要求美國放棄軍事霸權。就他們所提出的恢復白人崇高地位的訴求來説,我們還看不出他們對改變既有世界秩序有何幫助。
如果要把不同版本的“責任”概念串聯在一起,我們需要看一看對軍事霸權戰略進行合理化解釋的最後一個論據:掌握霸權對美國經濟有利。在那些被零和思維佔據頭腦的戰略家們看來,這其中的道理非常簡單。“長電報”作者、美國冷戰戰略的主要制定者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曾指出:“美國所擁有的財富佔全世界的50%,但我們的人口僅佔全世界的6.3%……在未來10年裏,我們的根本任務在於為美國與世界建立一種互動關係模式,美國能夠在這一關係裏維持當前的不對稱優勢,而且還能確保這一不對稱優勢不會導致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受到損害”。實現這一目的的手段之一是美國須擁有強大武力;手段之二便是通過實施戰略性的對外援助項目把美國與他國之間的不平等狀況合法化,美國的對外援助項目有助於阻止一些人過於激進地推動全球財富的再分配進程。
我們並不知道到底有多少美國人(無論有意還是無意)希望保持美國與世界其他國家之間的不對稱優勢以維持自己在世界上的經濟地位。而且,美國軍事霸權在戰後黃金髮展時期對普通美國民眾經濟狀況的影響到底有多大並不是一個很容易回答的問題。在當下這個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貧困率不斷攀升的時代,僅僅2020年5月至今,就已經有800多萬美國人因新冠肺炎疫情陷入了貧困。很顯然,普通美國人的經濟狀況正在變得越來越差。美國精英階層正在大量囤積資源(不妨瞭解一下美國對產油國的軍售情況),那些資源更好的用處其實是被投入到大範圍經濟改革中去。此刻進步派人士應站出來發出聲音:不斷擴張的國防預算正在使情況日益惡化。
當精英們意圖推動美國掌握軍事霸權時,他們能夠利用上述論據中的某一點或全部三點為自己的主張提供支持。史蒂芬·沃特海姆從沒有説過自己的這本書可以被視為一部美國草根政治發展史,這本書也的確無法為我們描繪美國政治在更加宏大的社會圖景裏面的發展狀況,那樣做是極端困難的。我們無法確定這三點論據當時在多大程度上深入了美國民眾的內心,也無法判斷它們當時在美國社會上的影響力如何,而對於這三點論據被接受的程度及其社會影響力隨時間推移是如何變化的,我們更是無法給出答案。
如果我們希望進步外交政策真正在美國獲得推行,我們就必須想辦法讓其獲得美國民眾的支持。只是以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為論據對海外軍事行動進行簡單的批判是不夠的,解決氣候變化和全球不平等問題的國際努力並不會因此就自動獲得合理性。而且那樣做反而會給那些希望對孤立主義大加批判的人們以口實,那些人會藉此重新宣揚美國在世界上扮演不可替代角色的陳舊論調。
也許,重新構建“美國責任論”的話語體系能夠為我們開闢一條新路。在這一新的話語體系中,我們不會再把“領導地位”、“軍事霸權”這樣一些元素添加進去。美國若就此推行一套負責任的全新的外交政策,我們便能夠把資源重新分配到諸如全球減貧、氣候變化、人類衞生健康事業等真正需要那些資源的領域中去。屆時美國國內的人們也將獲得足夠的資源來應對貧困、失業、疾病等那些對他們來説真正的威脅。到那時,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把新的利益攸關方納入進來是非常重要的。“美國責任論”中的“責任”不但意味着集體決策(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同時也意味着位高者應以高尚的道德去履行自己的義務(noblesse oblige)。
當然,制定這樣一個目標對我們來説的確顯得有些過於野心勃勃了。不過好消息在於,美國的國防預算規模十分龐大,美國統治階級的未税收入也數額驚人。推行一套負責任的外交政策需要資金作為支撐,同時也需要有人為此作出犧牲。對政治冷感的美國民眾對軍隊卻十分推崇,這一事實提醒我們:美國人並不會拒絕對那些“耗資巨大且資金並非來自全民而是不公平地取自某一羣體”的事業給予支持。正如史蒂芬·沃特海姆對20世紀40年代美國曆史的描述所揭示的那樣,一切就看你如何向公眾推銷自己的理念。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20年10月19日美國《波士頓評論》網站)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