託卡馬克之冠:你可能不知道日本做了多少“努力”,才拉來原子能機構“背書”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託卡馬克之冠】
雖然福島核事故中產生的核廢水已經不是第一次流入大海了,但是作為日本政府正式做出的官方決策,把核廢水排入大海一事依舊給人以極大的震撼——儘管隨着福島核危機的日益拖延,所有人都已經一再調低對日本政府處理此類事件的責任預期,但日本政府不負責任的程度還是超出了大眾的想象。
原子能機構表態成“令箭”
最近有些人援引日本外務省的通稿,高強度復讀關於“氚無害”“低放射”“可以喝”等日方文宣話術,甚至還有人碰瓷國內核電站,聲稱二者排放都一樣云云,企圖通過指東打西轉移視線的方式來為日本的決策災難開脱洗白。從這個角度上説,日本外務省的公關經費也算是沒有白花。
如果日本的核廢水真像他們聲稱的那樣低輻射可以喝,那他們為什麼不直接喝掉呢?需知日本的城市居民生活用水也是有缺口的,既然能喝那為什麼不直接給日本居民喝呢?
1965年蘇聯用原子彈在哈薩克斯坦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州炸了一個水庫出來,輻射消散後,為了證實水庫安全可用,時任蘇聯原子能部部長斯拉夫斯基跳進水庫游泳以示安全。

資料圖來源:mediadrumworld.com
2010年美國發生墨西哥灣漏油事件,佛羅里達海灘一度因此關閉。在漏油被清理乾淨,水下漏油點被控制住之後,海灘重新開放,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帶着自己的女兒在佛羅里達游泳以示安全。
蘇聯人搞得,美國人搞得,你日本人説的比蘇聯人和美國人加起來都好聽,那你為什麼不喝?
估計日本人,尤其是日本政府內心也清楚,任何技術都必須要由人來實施,人是事故處理的首要因素,當人本身不靠譜的時候,討論技術就沒有意義。
此事發生之後,在事關全球公共治理的問題上日本的政府信用已經事實上破產,然而現在的問題是,日本為什麼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做出如此決策?它的決策依據是什麼?或者説,它的底氣何在?
無非兩條:一是美國政府的袒護,二是國際組織的背書。
前者很好理解,美國政府對自身及盟友在事關全球公共治理的問題上予以袒護是一個公開的國際政治現象,這甚至談不上是什麼秘密。其在這一過程中的雙重標準是明確而不加掩飾的,甚至被袒護方自己都不諱言這一點。
比如眼下日本方面就在反覆強調其行為獲得了美方的認可,其沾沾自喜的嘴臉彷彿是拿到了尚方寶劍,獲得了免死金牌;而由於洋流原因,美國實際上是日本排放核廢水的主要受害方,但美國方面居然對日本這種極其不負責任的行為表示“感謝”,這種沆瀣一氣的表態委實不堪入目。
而後者就非常值得玩味了,此次事件中,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有關表態成為日本文宣通稿、日本媒體以及國內某些人拿來當令箭使的諸多雞毛中最大的一根,在他們嘴裏,有關敍述甚至演變成了“聯合國允許日本排放核廢水”。

雖甚荒謬,但國際原子能機構沒有對日本極其不負責任的行為施加足夠的壓力,其出台的有關聲明至少在純粹理論層面認可了日本排放核廢水的可行性,這也是事實。
為何如此?
就此問題,我陳述一些基本事實。
日本積極介入國際組織
二戰結束後,與在國際場合中對美國的俯首帖耳和唯唯諾諾不同,日本在國際組織中的擴張和佈局是非常激進、非常有侵略性的。
由於主權結構受限,日本極其重視擴大自身在國際組織中的影響力,其中最主要的手段,就是通過JPO項目,向聯合國的諸多國際組織輸送工作人員,通過人事組織關係來影響、介入乃至操控國際組織的一般政治實踐。
JPO項目的全稱為初級專業人員項目(Junior Professional Officer program),它的前身是1954年由荷蘭政府與聯合國糧農業組織創立助理專家項目(Associate Experts),當時雙方約定,由荷蘭政府提供費用和派遣人員至聯合國糧農組織工作。
由於該項目同時滿足了聯合國的人力需求和國家對具有豐富國際工作實務經驗的人員培養需求,因而大受歡迎,聯合國的其它組織也陸續開展此類項目,與聯合國有密切關聯但並不從屬於聯合國的一些國際間組織——例如亞洲開發銀行——也有類似項目。
聯合國每年招收數百名JPO項目人員,由聯合國JPO服務中心負責管理,這些人員會根據計劃被分派至聯合國各個組織提供服務,其中的一部分人員會成為聯合國組織的正式職員,並參與到聯合國日常事務的管理和決策中。
招收JPO人員的聯合國組織主要有聯合國秘書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開發計劃署、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人口基金會、聯合國難民署、聯合國大學、國際勞工組織、世衞組織、糧農組織、國際移民組織、國際經合組織、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工業發展組織、國際電信聯盟,當然,還有國際原子能機構。
日本從1974年開始參與JPO項目,經過幾十年的努力和鉅額資金投入,成功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人員灌輸機制。日本安倍內閣於2015年發佈了《2015年日本復興戰略》,其中明確劃定了到2025年,要確保聯合國的各個國際組織中,日本籍正式職員的人數從目前的800人達到1000人的目標。
日本向聯合國的各個國際組織輸送了大量人員,這些人員中的相當一部分正在或者曾經在聯合國的國際組織中擔任關鍵職位。例如:
分管聯合國財政工作的副秘書長高須幸雄,
分管聯合國新聞、裁軍、人道主義事務的副秘書長明石康,
分管宣傳工作的副秘書長法眼健作,
分管人道主義工作的副秘書長大島賢三,
分管裁軍工作的副秘書長阿部信泰,
分管裁軍工作的副秘書長田中信明,
分管新聞工作的副秘書長赤坂清隆,
國際能源署總幹事田中伸男,
聯合國難民署高級專員緒方貞子,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松浦晃一郎,
國家海洋法法庭庭長柳井俊二,
國際海事機構事務局長關水康司,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區域合作司司張西本伴子,
中日韓三國合作秘書處秘書長巖谷滋雄,
聯合國糧食計劃署亞洲局局長忍足謙朗,
世界銀行獨立監察小組主席渡邊惠美,
世界銀行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執行副總裁本田桂子,
還有最關鍵的,在福島核危機期間擔任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的天野之彌。

國際原子能機構前總幹事天野之彌,已於2019年因病去世,享年72歲。(資料圖/原子能機構官網)
他們都是日本通過JPO項目派遣到聯合國工作並留用的人員。
這些人員,再加上日本通過其它途徑,例如聯合國常規工作人員招聘流程、聯合國志願者派遣計劃、學術及研究機構派遣人員等向聯合國派遣的工作人員,日本在聯合國及聯合國的國際組織中間搭建起了非常龐大的人際關係網絡。
僅僅在2018年,日本在聯合國各級別國際組織中的職員人數就達到了P2級別75人、P3級別252人、P4級別276人、P5處長級別160人、D1副局級59人、D2司級15人、高級官員10人。
在聯合國的諸多部門中,日本職員的數量非常龐大。比如:聯合國秘書處日本職員數量高達91人,位列世界第一;聯合國兒童基金會中日本職員數量為77人,同樣位列世界第一;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日本職員人數71人,還是位列世界第一;聯合國難民署日本職員58人,聯合國糧食計劃署日本職員39人。
而這些人員中至少一半以上是日本經由JPO項目輸送進聯合國的。例如:兒童基金會的77名日本職員中有60人是通過JPO進入聯合國的;開發計劃署的71名日本職員中有43人是通過JPO進入聯合國的;難民署的58人中有49人是通過JPO進入聯合國的。
從2003年開始,聯合國每年新招收的日本籍正式職員中,有JPO經歷的人佔比就長期維持在70%以上,某些年份甚至超過80%,其中來自學術機構或者研究機構的人員比例較高,長期在一半以上。
而這其中不乏高官,例如兒童基金會中4名日本高級幹部中3名是JPO人員,開發計劃署中9名日本高級幹部中6名是JPO人員。
日本通過JPO項目向聯合國輸送的人員如此之多,以至於在部分其它國籍的聯合國工作人員中,JPO被半開玩笑地稱呼為日本人行動(Japanese people operation)。
除了人事工作外,資金也是日本介入聯合國的國際組織一般政治實踐的重要途徑。
日本向聯合國的國際組織投入外交資金,屬於“政府改革開發援助”項目的部分工作內容。日本“政府改革開發援助項目”分雙邊類和多邊類,其中多邊類就大量投入到聯合國及聯合國的國際組織相關工作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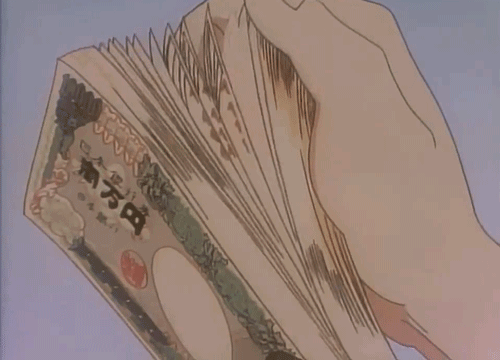
日本在聯合國所需資金的負擔比例在2000年達到頂峯(20%),後來由於日本自身的財政問題而逐漸下滑至不足10%。為了應對因資金投入不足而導致話語權下降的問題,日本於2015年重新修訂了《開發協力綱要》,開始引入民間資金投入到多邊類政府改革開發援助項目中。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為了向聯合國的國際組織派遣工作人員(例如前面提到的JPO所需資金)而投入的資金並未隨着日本負擔聯合國所需資金的減少而減少,反而通過調整外交資金的總體構成而逆勢上漲,其漲幅之高令人印象深刻。
具體有多高呢?簡單來説就是從2014年到2018年翻了一番還多,從11億日元上漲至23億日元,這在日本政府的總體外交預算和負擔的聯合國資金日漸減少的大背景下是非常可觀的。
另外,日本外務省國際機構人事中心還積極同參與JPO項目的聯合國國際組織建立對口關係,它與43個國際組織簽署了JPO協議,位列世界第三。其政府多部門聯合網羅並輸送人才,甚至還設立了專門的相關培訓項目和考試科目。
除了人員和資金,日本還通過積極爭取聯合國的國際組織在日本落户來獲取影響力。諸如聯合國大學、糧食計劃署、知識產權組織、世衞組織等都在日本設立了事務所或者中心。
結語
在福島核危機中起到微妙作用的國際原子能機構裏,日本籍職員的佔比並不算高,但在福島核危機的10年曆程中,有8年其總幹事一直是日本人天野之彌。
另外,美國在參與JPO項目時,其熱衷於向國際原子能機構定向派遣JPO人員,美國籍職員、美國籍幹部、有JPO經歷的美國籍職員這三項,在國際原子能機構中的佔比穩居世界第一,這對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決策形成過程和具體事務處理形成了極其深遠的影響。國際原子能機構在當代的歷次區域核危機中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密切配合,乃至於表現出某種程度的“橡皮圖章”特徵,即與此有一定關聯。
客觀而言,日本和美國在這些國際組織中所擁有的不成比例的人事結構,這事實上提高了這些國家在這些國際組織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加強了其設置議題和控制議程的能力,客觀上形成了對國際事務中一般政治實踐的塑造能力,這本質上是一種制度性的強權。

我不是質疑國際原子能機構或其它聯合國的國際組織在國際事務中的客觀和公正;事實上,在日本和美國能夠對國際原子能機構施加如此巨大的影響力的大環境下,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有關聲明依舊能夠咬住純粹理論可能不鬆口,而沒有在許可具體實施上開綠燈,這已經證明了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相關工作人員具有相當的職業操守和科學精神,他們知道自己手中之筆的如山分量,對每一個措辭都字斟句酌,慎之又慎,力求穩健。我從中看到了國際原子能機構工作人員持守人類公理正義的良知和外界政治壓力之間的搏鬥與抗爭,對此,我表示欽佩。
但如果某些人企圖以此論述國際原子能機構在福島核危機中的具體作為純潔無瑕如白蓮花,乃至於企圖進一步論述國際原子能機構給日本的非法排污行為提供了不可辯駁的政治合法性,那就不光是“瞎了眼”,恐怕還“黑了心”。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