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昕:俄羅斯經營“近鄰”的新規則,彷彿喊出了“再見帝國”

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副主任張昕參加觀學院活動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張昕】
在開始講座前,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關注這個地區,或者説肯定不是所有人都會關注這個地區。
大家看左邊這四幅圖,如果不看旁邊的註釋,能否判斷出分別代表着2020年發生的哪些事件,或者説在所謂的“後蘇聯空間”或歐亞空間內部發生了一些引發媒體關注的事件?
左上角是白俄羅斯,如果懂俄語的話,還能看出橫幅標語的訴求是什麼。右上角是顯示的是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之間圍繞納卡地區的衝突升級,左下角是吉爾吉斯斯坦因為選舉爭議引發的民眾騷亂,最後過於“熱情”的示威者還衝擊了議會大樓。右下角代表的是烏克蘭或者説東歐的重組。這些事件不能説全都是在去年特定發生的,其中一些仍然在持續進展中。

如果我們的眼光只聚焦在去年一年的話,在所謂的大歐亞地區或者“後蘇聯空間”內,至少有這些被各界廣泛關注的政治事件。可以毫不誇張地説,2020年對於俄羅斯周邊地區來説,是一個非常動盪的年景。以此作為由頭,我們可以回顧一下當代俄羅斯對於自己周圍的空間,是怎麼來認知的,用什麼方式來處理自己與周圍空間的關係。2020年俄羅斯周邊地區出現的這些衝突動盪,有多少是跟俄羅斯或者前蘇聯的傳統歷史政治結構有關,還有多少則會對未來俄羅斯經營自己周邊地區將產生直接的政治或政策影響。
我想特別強調一點的是,雖然這次的話題中完全沒有中國,但是如果在座的各位稍微敏感一點的話,就會發現這其中跟中國相似或結構性類似的地方很多,能找到的映照之處很多,希望今天的討論也可以給大家提供一些思考問題的思路。
1991年蘇聯解體對於當代的俄羅斯來講衝擊巨大,其中與今天主題相關的、最重要的兩個衝擊:一是地緣政治意義上的霸權地位喪失,原來美蘇兩極對抗的地位非常迅速地消失。二是蘇聯作為一個遼闊的多民族帝國,幾乎一夜之間崩潰。而事實上,這兩個過程至今還沒有完全結束,仍以不同方式在影響並塑造着當代俄羅斯如何處理、回應“我是誰”、”我跟周圍這些地區以及地區中的人羣是什麼關係”等問題。對俄羅斯的自我認知、自我定位、自我界定跟周邊空間、人羣的關係,上述兩個過程並未終結。
在俄語中,“近鄰”這個詞用的比較多,意思比較接近中文裏面的“周邊”。這些近鄰在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空間想象中扮演什麼角色?大概有點類似費孝通先生講的中國傳統社會的差序格局:俄羅斯的政治空間想象差不多也是一圈一圈的戰略圈。第一個圈層就是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第二個圈層就是“後蘇聯空間”內其餘的這些國家,這就基本構成了俄羅斯傳統意義中近鄰的核心地位。其中的重要內涵有很多,很大程度上限定或約束了對俄羅斯而言如何回答“我們是誰”這一基本問題。比如説烏克蘭,歷史上俄羅斯知識分子早就問過,沒有烏克蘭,俄羅斯是什麼?
近些年,俄羅斯自身對這個空間的表述也在不斷演變,從“後蘇聯”到越來越多地演變成各種意義上的“大歐亞”,雖然只是表達文字上的差別,但背後有着更深刻的政治和政策內涵。
具體到政策層面,1991年以後一直到現在,出現了一系列由俄羅斯主導推動的、可以稱為“經營周邊”有組織、制度化的嘗試,比如現在很少聽到的“獨聯體”,在經濟層面,之前有比較雛形的歐亞經濟社區、關税同盟,現在已提升到歐亞經濟聯盟,還有雙邊組織俄白聯盟等,在安全領域有集體安全條約組織,諸如此類的行動,都是俄羅斯在一體化融合方面所做的努力。

2014年2月,烏克蘭兩萬名反政府示威者在首都基輔獨立廣場上與警方發生激烈衝突。圖自歐新社
這裏面的一個“高光”事件就是從2013年開始的烏克蘭政治危機和2014年克里米亞的“迴歸”。當然,“迴歸”可能需要打個引號,因為對不同立場的人來説,“迴歸”的表達可能有很不一樣的含義,需要用不同的方式來界定。
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就是以克里米亞事件為核心來理解俄羅斯對“近鄰”地區的基本認知和態度的變化。順便也推薦大家,如果對烏克蘭和克里米亞感興趣的話,可以去細讀一下普京在2014年3月18日俄羅斯政府迎接克里米亞和塞瓦斯托波爾重回俄羅斯聯邦的官方儀式上的長篇演講。我個人認為,這是2000年以後俄語世界裏面最重要的一個政治文本,藴含着非常豐富的內涵。
在我的小文章裏,以普京這個演講為主要文本,我總結了當時俄羅斯認知自己與近鄰關係的一組基本原則。
第一個,俄羅斯把自己定位在為一個俄語文明為代表的一個文明共同體的中心,這個共同體是所謂的“俄羅斯世界”,俄羅斯自我定位是這個世界的核心和保護者。這個文明世界的地理範圍和包括的人羣特徵是有很大爭議的。
第二個,很重要的一點是,在俄羅斯看來,當時西方世界已經明顯處於道德崩潰時代,俄羅斯要跟西方慢慢脱離開,甚至不僅是脱離,還要反過來代表歐洲文明。現在的歐洲無法代表歐洲文明,歐洲文明的核心價值觀在“第三羅馬”、在俄羅斯才能得到更好的保護。按照這樣的看法,崇尚文化多元性的“白左”徹底摒棄了歐洲文明的根基,所以未來俄羅斯會以歐洲文明保護者的身份來拯救歐洲。
第三點,其實跟第一點有很大關聯性,認可將武力作為維護俄羅斯海外同胞利益的一個合理手段。這裏又有一個微妙之處:誰是我的俄羅斯海外同胞。如果用一個簡單的比照,大家看春晚時會注意到主持人報一連串賀詞,海外僑胞、港澳台等等,這是中國式的來界定誰是我們的同胞的一個差序表達。
俄羅斯也面臨着類似的問題,誰是我的海外同胞,誰會列入我認為可以用武力來保護合理利益的羣體,這是有爭議的。
最後一點,有着深刻含義的是,歷史正義和人民意志高於任何成文法,所以俄羅斯有充分的道義情感、以及更強的歷史正義性來讓克里米亞重歸俄羅斯。
這一事件在當時的衝擊力是非常巨大的,尤其西方政策界、戰略界甚至一致認為克里米亞事件是破壞了二戰以後整個國際秩序的一個性質極其惡劣、負面影響極其深遠的事件。

2014年3月18日,塞瓦斯托波爾,克里米亞民眾通過電視觀看普京演講。
回到“後蘇聯空間”這個話題,我覺得2020年這一輪俄羅斯周邊地區動盪,發生了一些變化。這裏我推薦俄羅斯智庫卡內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寧的一篇文章,他是一位相當有影響力戰略評論人士。特列寧先生的一些觀察與界定,和我自己對俄羅斯的看法有不少重合。在2020年這一系列近鄰事件中,俄羅斯的反應其實是相當防禦性的。尤其是歐美媒體、智庫按2014年的那套行為標準來想象俄羅斯應該有更加全面、極端的反應,但實際的俄羅斯反應非常有限。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納卡衝突,在“後蘇聯空間”裏面,亞美尼亞總體上是跟俄羅斯利益關切最大、重合度最高、走得最近的。但衝突發生後,俄羅斯一直沒有做任何直接表態,普京甚至説我們之間有條約,但條約只覆蓋發生在亞美尼亞領土上的衝突。換言之,當時的納卡衝突沒有發生在亞美尼亞領土上,所以俄羅斯沒有條約義務向亞美尼亞提供保護。後期俄羅斯雖然派出了維和部隊,但實際上是一個很晚的防禦性措施。
那麼俄羅斯付出的代價是什麼?也就是這裏講的最後一條,客觀上承認並接受土耳其在這一地區重新進入的現實,也就是第三方重新進入“後蘇聯空間”的現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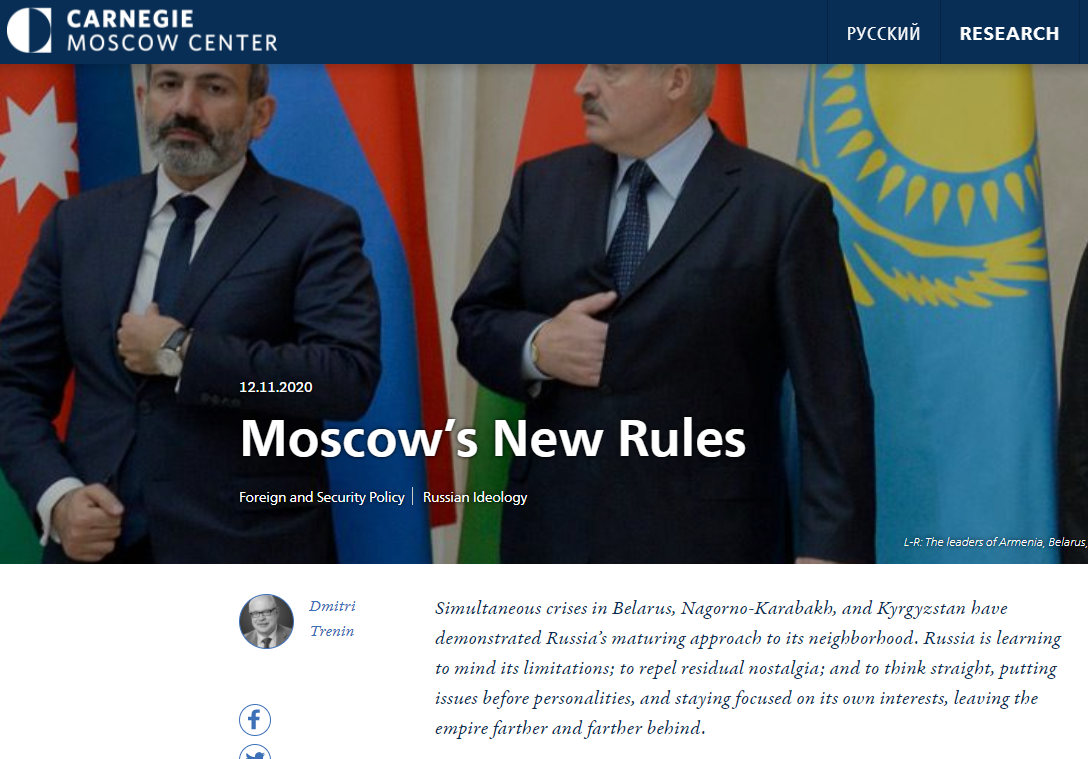
由此,特列寧先生總結了幾個特徵。他認為,經過2020年這一系列事件,某種程度上俄羅斯似乎間接喊出了“再見帝國”這個口號,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不再以維護一個龐大的帝國體系作為外交政策的一個核心。就像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所説“美國第一”,這邊則是“俄羅斯第一”。如果需要自身付出太多的代價來持續給一個所謂的前帝國體系裏面的國家或人羣補血的話,俄羅斯可能已經不願意承擔這些額外的風險跟責任了。某種程度上可以認為“前蘇聯”這個概念已經不復存在。
第二,與近鄰之間的國與國的雙邊關係當然要發展,但這種發展會更多地超越雙方領導人之間的氣質相投,領導人個人層面這些東西越來越不重要。大家可以回憶一下,在白俄羅斯這一輪國內動盪中,俄羅斯是以什麼方式來發揮自己的影響力的。
第三,就是在雙邊關係中可以做出承諾義務,但有上限。而且要再加一條,這是我的表達,這樣的承諾義務必須對等,雖然不一定對稱。
最後,不管是基於意願或非意願,接受第三方進入俄羅斯傳統的近鄰空間。除了土耳其這一最典型的例子之外,又不得不提中國。其實這幾年,俄羅斯對於中國在中亞、北極等地區活動的態度,總體上是越來越寬鬆開放的,尤其是2013、14年以後。相比之下,起初俄方的戒心和阻擊還是比較明顯的。
當然,是不是就像特列寧先生所説的,俄羅斯從此就是進入了一個“再見帝國”的階段,現在可能還是一個初期階段,後續發展仍有待進一步觀察。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裏,謝謝大家。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