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鋭:馬克思主義視域下的儒家民本思想——以嵇文甫為中心的探討
【文/王鋭】
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自誕生之日始,就有兩個十分明顯的特徵:
首先,注重論述近代以來中國的經濟生產方式變遷與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生產方式方式變遷,在此基礎上動態的分析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基本狀況,中國革命運動的動力、路線、目標與基本力量,通過研究歷史的方式為當下的革命活動確立一個清晰且客觀的時空座標;
其次,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分析框架、秉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立場,在大量佔有史料的基礎上,對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傳統進行新的評價,挖掘中國歷史進程當中因具有“人民性”與“革命性”而值得闡揚的政治與文化傳統,剖析帶有明顯的落後特徵,長期作為壓迫廣大民眾的政治、經濟與意識形態因素,把歷史主義與階級分析結合起來,將中國歷史的演進圖景與基本特徵呈現於世人面前。[①]
論及中國古代的政治傳統,不能不重視儒家的民本思想。[②]《尚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隨着漢代以來儒學被統治集團奉為官學,民本思想在中國古代影響深遠。它既是歷代政權彰顯自身政治合法性的基本要素,又是一些儒生藉以批判政治與社會弊病的理論武器。[③]
近代以來,隨着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在清末民初的政治文獻中常稱為“民權”)傳入中國,不少人或是出於宣傳上的便利,或是為了提升民族自信,或是希望將中國傳統與域外新知相結合,常從中國曆代典籍之中尋找與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相似的因素,進而“論證”民主思想中國自古已有,只是由於各種歷史原因隱而不彰,晚近與西洋學説相遇,實為將古典精義發揚光大的絕佳機會。在這之中,先秦時期孔孟的言説與明清之際顧炎武、黃宗羲等人的論著,經常被人們作為例證反覆宣揚。
關於前者,如孫中山在著名的《三民主義》裏通過列舉孔子與孟子的隻言片語,宣稱“由此可見,中國人對於民權的見解,二千多年以前已經早想到了”。“依我看來,中國進化比較歐美還要在先,民權的議論在幾千年以前老早就有了”。[④]關於後者,在晚清民國知識界極具影響力的梁啓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認為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的確含有民主主義的精神”,並強調以他為代表的這批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在戊戌年間讀了這些著作之後,“覺得句句都饜心切理,因此從事於推翻幾千年舊政體的猛烈活動”,晚清以來的思想變革堪稱“殘明遺獻思想之復活”。[⑤]
由此可見,**能否澄清儒家民本思想的本來面目,能否剖析民本思想產生的社會歷史根源,能否揭示先秦和明清之際相關政治言説的具體訴求,對於在思想層面普及名副其實的民主理論而言至為重要。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進程中亟需解決的理論課題。**對此,作為對先秦學術與宋明儒學深有研究,在民國學界具有一定影響力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史家嵇文甫(1895—1963)在那一時期的一系列關於儒學的論著尤其值得關注。
嵇文甫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之後,接受組織委派赴蘇聯留學,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系統學習馬列主義,因此具有紮實的理論功底。在他的學術論著中,時常體現出對時代思潮與學術熱點關注,其中就有有不少內容是對中國古代“民本”思想的辨析。以他的論述為核心,兼及其他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家、旁涉各種時代思潮,或可具體的呈現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如何在近代變局之下辨析中國古代政治傳統。

嵇文甫(1895—1963)
一、辨析先秦民本思想的時代特徵
新文化運動以降,隨着馬克思主義史學進入中國,一些早期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開始運用歷史唯物主義來分析中國傳統思想。如在《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一文裏,李大釗認為:“凡一時代,經濟上若發生了變動,思想上也必發生變動”。因此,儒家思想“是適應中國二千餘年來未曾變動的農業經濟組織反映出來的產物,因它是中國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層構造,因為經濟上有它的基礎”。[⑥]
作為具有一定舊學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嵇文甫很自然的也會注意到這個領域。1924年,在一篇名為《人的問題》的文章裏,他強調:“人不是個懸空的,抽象的,慢無着落的東西;他與他的社會、國家、周圍的一切情狀,都是息息相關的。我們不能除去一切社會關係,找出一個‘一空依傍’的‘人’。也不應該離去當前應做的事,籠籠統統的去故紙堆中撿出個做人的標準”。[⑦]他的這番話,無疑讓人想起馬克思那段更為著名的話:“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⑧]可見嵇文甫在分析歷史與現實問題的方式上已經基本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即將人以及人的思想置於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審視,着重分析各種意識形態之所以產生的政治支配形式、社會矛盾與經濟根源,即“我們不是從人們所説的、所設想的、所想象的東西出發,也不是從口頭説的、思考出來的、設想出來的、想象出來的人出發,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還可以描繪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反響的發展”。[⑨]在分析中國儒家民本思想的過程中,嵇文甫就是本着這樣的方法論來進行的。
大革命失敗之後,為了探討中國社會性質與革命動力問題,左翼知識界興起了關於中國社會性質與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希望由此準確把握中國社會的基本性質、為尋找革命的基本力量、制定革命路線提供歷史的參考。

《覺醒年代》中的魯迅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嵇文甫自然堅信歷史唯物主義在歷史研究當中的指導意義,強調認識具體歷史時期的經濟基礎與生產關係的重要性。在發表於1929年的《週末社會之蜕變與儒法兩家思想上的鬥爭》一文裏,嵇文甫認為:“一種學派或一個時代的思潮,都有社會經濟的背景。所以我們要治思想史,必先要研究經濟史。要用經濟史觀來治思想史,整理出來的結果才比較正確”。[⑩]而從社會形態上來説,周朝是封建社會,而“封建社會的基礎,是建築在貴族土地私有權上。當時的平民沒有土地,天子壟斷了土地而隨意分封,平民只是做耕守土地的農奴。所謂井田制度,就是那個時代土地分配的方法”。[11]
而總體上看,儒家思想便誕生於這樣的經濟基礎之上,孔子所謂的“吾從周”,就是對春秋末期出現的頗為劇烈的社會轉型深表不滿,希望在政治與經濟體制上回到西周時候的樣貌。孟子的“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也可以從這個角度來理解。因此,嵇文甫指出:“儒家代表貴族,主張貴族是特殊階級,不與民爭利;階級的懸殊,儒家認為是應該的”。[12]只有把握了這個特徵,才能從歷史的角度來分析先秦儒學的政治思想,包括其中體現出強烈批判色彩的主張,因為一種學説是否帶有批判性,不能只看他對於現狀的抨擊是否猛烈,更要看到它是從怎樣的階級立場出發來進行批判,它所描繪的理想的政治與社會狀態是怎樣的。在這一點上,嵇文甫指出:
儒家的政治原則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把“家”看得很重。但是這個“家”,乃宗法社會貴族之大家。當時的一國,不過幾個貴族之家耳。儒家把貴族之家看得很重要,能齊家就能治國平天下。這也是儒家擁護貴族政治的思想。[13]
具備了這樣的認識基礎,就可以較為系統的分析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了。馬克思説,考察社會變革時必須正視“人們藉以意識到這個衝突併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簡言之,意識形態的形式”[14]但是在中國社會史論戰當中,參與者多聚焦於歷代的社會經濟狀況,而對作為上層建築重要組成部分的意識形態問題缺少較為深入的辨析,這樣難以有效回應新文化運動以來在思想界、學術界具有較大影響的各種迴護中國傳統的論調,不易於在此基礎上建立完整的馬列主義文化領導權。
或是有感於此,1932年,嵇文甫出版了《先秦諸子政治社會思想述要》一書,針對中國社會史論戰當中“有些治中國社會史的,因為對於思想史缺乏充分的素養,所以每遇到思想史上的問題,總有些生吞活剝強作解人的情況”,嵇文甫強調“思想雖然是生活的反映,雖然是以一定物質條件為基礎的上層建築,但從生活到思想,從下層到上層,是一個複雜的過程,並不是才明彼即曉此的”,[15]因此需要在熟悉特定歷史時期的政治與經濟狀況前提下,仔細分疏各派的思想言説,將其內在邏輯與本質特徵明白揭示出來,既不簡單套用理論公式,也不將思想抽離出其所產生的歷史環境。
在書中分析儒家思想的部分,嵇文甫認為《左傳》裏的“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堪稱儒家理想中的政治圖景,即“庶民自從事於生產、貴族自從事於禮儀。老老實實,在有典有則的社會秩序中,過其安靜和睦的生活,也可以算是仁而有禮了”。[16]因此,孔子對於時局的批評,主要還是針對新興的統治集團破壞了這樣“温情脈脈”的禮制,衝擊着過去行之有效的等級與名分。當然,在這一過程中,不但舊日的貴族遭受了嚴重的打擊,廣大普通民眾也飽受戰亂與紛爭之苦。
在這個意義上,以孔子之道傳人自居的孟子充分繼承了孔子的政治立場。孟子呼籲統治者應“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對當時諸侯國之間不斷擴大戰爭規模深表不滿,作為批判時局的一部分,孟子非常關注民生疾苦,呼籲“仁政”應能夠保障一般民眾的基本生活,實現“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孟子·梁惠王上》)的社會景象,強調要“保民而王”。
這些言説,無論是批判戰國時期的兼併與殺伐,還是作為一種政治傳統影響於後世儒生,都是具有一定正面意義的。但嵇文甫要強調的是,如果認為孟子主張重視民生就將其主張與現代意義上的民主等而觀之,無疑是錯誤的。儘管孟子説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章句下》),又説過“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這樣的話,但結合先秦儒家的總體特徵,應該認識到:
孟子重民,是很明顯了。可是這就可以算民權思想麼?恐怕靠不住。孟子無論怎樣尊重民意,無論怎樣反對暴君,但是他始終沒有想到讓民眾自己支配政權。他所理想的社會,仍然是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寶塔式組織的封建社會;他的政治哲學,仍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德化主義……治人是“君子”們的專業,一般勞力的“野人”是不容參與政權的。一方是治者,一方是被治者,這樣的等級社會,與民權政治絕不相容。民權與君權,不是程度上的差別,乃是性質上的差別。君無論仁暴,而君只是君。尊重民意,體恤民隱,固是做聖君的必要條件,可是民權政治總還説不上。孟子稱當時人君為“人牧”,又拿“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牧之者”去比地方官受君之百姓而治之。可見人君無論怎樣愛民,亦不過如牧人之愛其牛羊而已。[17]
在這裏,要想進一步理解作為馬克思主義者的嵇文甫的這些觀點,必須把握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對於民主的論述。恩格斯認為:“社會的經濟進步一旦把擺脱封建桎梏和通過消除封建不平等來確立權力平等的要求提上日程,這種要求就必定迅速地擴大其範圍”。因此,“無產階級抓住了資產階級所説的話,指出:平等應當不僅僅是表面的,不僅僅在國家的領域中實行,它還應該是實際的,還應當在社會的、經濟的領域中實行”。[18]
列寧在革命鬥爭中繼承了這一觀點,指出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下,所謂民主“實質上始終是少數人的即只是有產階級的、只是富人的民主制度”。而“由於資本主義剝削制度的條件,現代的僱傭奴隸被貧困壓得喘不過氣,結果都‘無暇過問民主’,‘無暇過問政治’,大多數居民在通常的平靜的局勢下都被排斥在社會政治生活之外”。[19]所以説,要想實現名副其實的民主,“着重於實際保證那些曾受資壓迫和剝削的勞動羣眾能實際參與國家管理,實際使用最好的集會場所、最好的印刷所和最大的紙庫來教育那些被資本主義弄得愚昧無知的人們”,[20]所以必須廢除私有制,讓廣大長期處於被壓迫的人們能夠充分參與到政治與經濟生活中,在經濟平等的基礎上獲取實實在在的政治權力。
馬列主義經典作家的這些觀點,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期間已經較為普遍的在中國傳播開來了。如陳獨秀在《談政治》、李大釗在《Bolshevism主義的勝利》等流傳極廣的文章中皆有所介紹。嵇文甫對於民主政治的理解,基本上也是建立在這樣的理論之上的。因此他着眼於考察先秦時期民本思想話語裏,廣大普通民眾在社會生產關係中處於怎樣的位置,是否具有真正管理與支配政權的權力,還是隻作為被關懷對象,使統治者能夠通過施以小惠來換取其服從,讓其更有主動性的為統治者創造經濟財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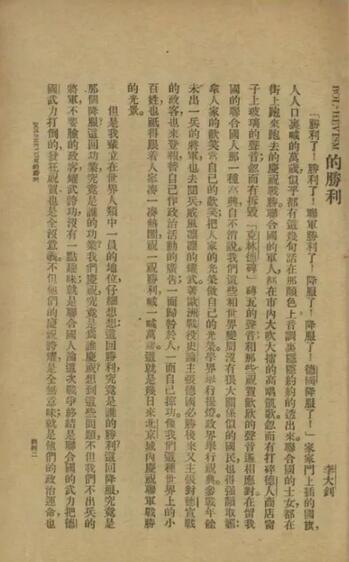
李大釗發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號的《Bolshevism的勝利》
基於此,在一份關於先秦諸子的講義裏,他提醒人們:“我們始終不要忘掉,儒家無論孔、孟、荀都主張王道政治。而所謂王道政治,既不是民主政治,也不是君主獨裁製下的官僚政治,而實在就是理想化了的貴族政治。這種政治的社會背景,是自然經濟,是宗法社會”。[21]及至晚年,他依然強調:“孟子學説中很富有人民性,所以清末搞民主運動的往往拿他做旗幟,很起了些宣傳鼓動的作用。但是如果真以為孟子主張民主政治,那就錯誤了。因為孟子只是反對暴君,而想望仁君,他並沒有主張,也不可能主張,變君主為民主,從政治制度上加以變革”。[22]
除此之外,嵇文甫還注意到孟子十分強調士人的操守。但他未像多數論者那樣表彰孟子的相關言説,認為這有助於培養具有高尚人格的士大夫,而是由此出發看到孟子的重要思考前提就是認為一般民眾比士人更為低等,因此後者稱為“治人”者實屬天經地義: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他(孟子)把“民”和“士”對立起來,“民”是受物質支配的,而“士”卻不受物質支配;行於“民”裏邊的是一種理法,行於“士”裏邊的卻另有一種理法。“以唯心論待己,以唯物論待人”;“以超人哲學待己,以唯物哲學待人”;我們的“亞聖”或者也是這種意思罷?然而,“士”於是乎高立於民眾之上了。[23]
近代以來,為了彰顯先秦儒家與現代民主思想之間的相似性,除了極力表彰孟子的“民貴君輕”之義,還把孟子對於士人政治地位的闡揚解讀成其政治思想中對抗“君權”的因素。特別是近代知識分子羣體大多脱胎於士階層,因此孟子的這些言説更有利於他們拿來論證自己政治與經濟地位(或曰“特權”)。但在嵇文甫的分析框架裏,孟子對於士人地位的論述是基於對民眾政治地位更低一等的論述前提之下的。從民眾的視角出發,士人與君主都是統治集團的成員,他們之間的權力分配與利益糾葛,只是統治集團內部的紛爭而已,與名副其實的民權並沒什麼關係。這同樣是辨析中國儒家民本思想時必須要注意到的問題。
二、揭示明清之際民本言説背後的士紳立場
在近代中國,明清之際的歷史、文化與思想是一個引起各派政治與文化力量持續關注的話題,形成了各種各樣的觀點。[24]特別是明清之際的著名儒者,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顏元等人的學説,自從清代前期考據學興起之後,就廣受關注,對他們的不同評價,既體現出不同學派之間的論爭,又往往超出學術的範疇,與人們對世變的思考結合了起來。在晚清民初思想界,這幾位大儒或是被詮釋成帶有革命性與現代性的思想先驅,或是成為西潮衝擊下固守傳統價值者所時常抬出的文化符號,或是被描繪成中國本土的民主思想先驅。特別是最後一點,幾乎成為晚清自新文化運動以降不同思想流派之間的共識,其中的差別只在於用什麼樣具體的民主理論來套到顧、黃、王、顏身上。包括一些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由於認為明清之際中國社會結構與生產關係發生了巨大而變化,因此這種變化在思想文化上的體現就是顧炎武與黃宗羲等人的民本思想中具有樸素的民主主義因素。可以説,在民國學界,能否對明清之際的歷史與思想提出具有原創性的見解,關係到能否在中國歷史研究領域建立真正的權威。
長期參與當時思想界與學術界各種論爭的嵇文甫自然十分了解這一點,因此他撰寫許多關於明清之際思想與學術的論著。不過與以上所列舉的那些觀點不同,嵇文甫根據他對於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學術的認識,對明清之際的民本思想進行了頗為詳實的辨析。在撰寫於1931年的《十七世紀中國思想史概論》一書中,他承認:“明末清初是中國地主階級自救運動很緊張的時代,是經世致用思想極興盛的時代。當時那班大師各本其對於中國社會中歷史的認識,提出自己政治改革的方案。其審時度勢,深思遠覽,所以為中國地主階級定久安長治的大計者,實非一般淺智短見的陋儒所能想象得到”。[25]

顧炎武像
但關鍵在於,表彰這些先賢在中國思想史演進脈絡中的傑出地位是一回事,認為其思想主張能夠和現代民主理論接榫又是一回事。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中的《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諸篇,批判君主權力過於膨脹,強調君主之間的關係應以道義為準則,反對大臣對君主的“愚忠”,建議在制度設計中提高宰相的政治地位,使之成為官吏之長,讓相權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君權的制約,創建具有穩定性與實效性的律令體系,在地方上將以士人為主體的學校改造成議政機構,藉此來伸張士紳階層的權力。嵇文甫指出,這些主張固然頗有見地,但究其實,“近代民權政治的原則‘民有,民治,民享’。‘民有’,‘民治’,梨洲都還説不到,只有‘民享’,總算慨乎其言之了。這種思想,我以為只可稱為‘重民思想’,徑稱為‘民權思想’似乎還不大妥當”,因為其主張“總沒有想到民眾自己支配政權”。[26]
關於如何分析某一歷史時期的思想,馬克思與恩格斯指出:“每一個企圖取代舊統治階級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説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就是説,這在觀念上的表達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27]這段話的引申之義就是,在研究思想史時,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前提下,不能毫無辨別的輕信各種思想與主張,而是要將其與言説者、宣傳者的真實的政治與經濟地位結合起來,考察言説者與宣傳者如何通過這些表面上帶有普遍性意涵的思想與言説來表達自己真實的訴求,進而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辨析這些訴求體現着怎樣的社會關係,象徵着怎樣的歷史趨勢。
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嵇文甫在研究黃宗羲等人的民本思想時正是踐行這樣的方法論。在《明夷待訪錄》中,黃宗羲對於君主權力過於膨脹之危害有着極為闢透的分析,認為這不但容易導致政治體系紊亂,而且違背了古人重視“公”的政治倫理,因此他建議在未來的制度設計中抬高相權與地方士紳的權力。對此,嵇文甫指出,不能像晚清民初的不少人那樣,將黃宗羲的這些主張視作是一種超出歷史語境、具有普遍意義的“反抗君權”,而是應該注意到,“這種傾向表示什麼意義呢?作這種主張的是站在什麼立場上説話呢?我以為丞相是士大夫的領袖,丞相政治是一種士大夫政治,也就是一種變相的貴族政治,這正是當時地主階級意識的表現”。[28]
他一針見血的指出: 然而我們必須知道,梨洲的學校是士大夫集團,他是要以士大夫集團的力量監督政府的。士大夫是代表地主利益的知識分子。由士大夫掌握的政治,終歸是勞心者統治勞力者的政治……在這樣的等級社會中,會有民權政治之可言嗎?不管梨洲説得多麼漂亮,他總是沒有超越了士大夫統治的理想。丞相是士大夫,學校中所教養的也都是士大夫。他以為只要把政權公開給士大夫,不由君主及其左右近習恣意妄為,政治就清明瞭。這隻可謂之紳權政治,而不可謂之民權政治。紳權政治是由貴族政治脱化而來,當時諸大師都抱此理想,而梨洲所言最帶急進色彩,可算是當時紳權論的左翼。但是無論怎樣左,也沒有左到民權主義。[29]
不管士紳集團如何批判君主權力過於膨脹,但自宋代以來,士紳的經濟基礎主要建立在對土地的佔有與對佃農的剝削之上。就此而言,士紳集團固然與皇權會有一定的衝突,但在支配土地、控制主要經濟與文化資源、役使大多數民眾這一點上,紳權與皇權的利益一致性遠大於分歧。[30]因此,嵇文甫的這個觀點,不但有助於全面把握明清之際民本思想的內涵,而且還有助於認識到近代借黃宗羲之名來宣傳“民主政治”的一些本質屬性。
前文談到,梁啓超回憶早年從事政治活動,經常借黃宗羲的論著來普及自己的政治主張。早在戊戌之前,西方近代資產階級議會體制傳入中國,不少中國士人覺得應效仿其法,以收“通上下之情”之效。關於議員資格,按照王爾敏的研究,時人“大致趨於上下院之制,而上院則以宗室勳戚及各部卿相為議員,構成貴介議院。下院則用下級官吏與練事之紳商為議員,取其老成碩德,才識卓異,以構成清流議院。”[31]戊戌變法期間,在湖南參與新政的梁啓超,認為政治上的變革,當務之急應“復古議,採西法,重鄉權”,踐行類似於地方自治的舉措。他認為當時中國一般民眾嚴重缺乏政治能力,所以“必先使其民之秀者,日習以公事,然後舉而措之裕如也。”而所謂“民之秀者”,非地方鄉紳莫屬。因此欲興民權,先興紳權,“紳權固當務之急矣。”[32]
在這樣的背景下,黃宗羲的相關主張自然很容易讓提倡改革的人士作為思想資源與宣傳工具。“他(黃宗羲)主張加重宰相的職權,而造成一種虛君制;又主張以學校監督行政。這都是他的苦心孤詣,欲以濟君主專制之窮。倘若他的理想竟能實現,或者會成一種紳權政治”。[33]“相權也罷,士權也罷,都只能算作紳權,而不能叫民權”。[34]由嵇文甫的這一觀點出發,則更能看清從明清之際到晚清,中國的士紳階層對於伸張自身權力之訴求的連續性,以及如何將這種訴求不斷的學理化、普遍化,同時也可洞悉這樣的訴求與名副其實的大眾民主之間的根本性差別。
與之相似,在《日知錄》的討論歷代制度變遷的部分,以及《生員論》、《郡縣論》等文章中,顧炎武基於民本的立場,也提出了他自己對於政治問題的主張。他認為在廣土眾民的環境下,由中央派遣官吏治理地方,在行政上會帶來諸多不便,由於官吏不熟悉本地情狀,往往需要藉助長期生活在地方,具有“地頭蛇”色彩的胥吏的幫助,這就給了後者假借政治權力來欺壓百姓、中飽私囊的機會。為了讓民眾不受彼輩的侵擾,顧炎武認為要在郡縣體制下注入先秦時期的封建因素,即在一定範圍內允許地方官員世襲,這樣由於他們與本地的興衰命運與共,並且十分熟悉當地的政治與經濟狀況,因此就可以發揮更大的主動性來治理地方,不但能夠庇護民眾,而且還能組織力量,禦寇自衞。顧炎武的這些設想,在晚清也被一些主張改革的人士視為地方自治理論的先驅,藉此來削減皇權對地方的支配。但嵇文甫通過徵引顧炎武《裴村記》中所説的“予嘗歷覽山東、河北,自兵興以來,州縣之能不至於殘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盡恃乎其長吏”,[35]指出:
他(顧炎武)的意思只是要充實地方上的自衞力量……為防止“不虞之變”起見,只有採取封建遺意,使地方權力強大,足以自衞,即所謂“寓封建之意於郡縣之中”,這正是當時地主階級所需要的一種自救方策。但亭林鞏固地主階級統治的方策猶不止此。他不僅要加強地方官的權力,並且要加強豪家大姓的權力。他很明瞭當時政權是建築在豪家大姓之上,他很明瞭豪家大姓是當時國家的柱石。[36]
因此,在分析顧炎武的政治思想時,不應忽視他所寄希望於改變政治現狀的那個羣體的基本特徵。在中國歷史流變中,豪族大姓具有怎樣的特點,其經濟支配方式對於社會有何影響,這從歷代儒者反覆抨擊“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的現象,以及反覆強調“抑兼併”、“恤貧民”的呼聲中,或從歷代農民起義不斷打出“均貧富”的口號中,或可窺見一二。遠的不説,在顧炎武生活的時代,晚明官僚豪紳集團變本加厲的佔有土地、壓榨剝削農民,讓許多自耕農變為地主階級的佃户,就是導致明末農民起義的重要原因。[37]如果説民本思想在覆蓋面上應儘可能的兼顧到更多的人,那麼顧炎武的這些主張,反而使民本思想中“民”的範圍大為縮減。
總之,嵇文甫強調,顧炎武“當創鉅痛深之後,深感社會失去中堅組織的危險,故重守令,重氏族,皆所以救其弊。他最卓絕的地方,在認識社會勢力,不僅注意政治的表面,而知道抓住其社會基礎。此之謂‘識治本’,‘達治體’。為東方式老封建帝國的君主策治安者,大概沒有比這再深切的了”。[38]這一觀點,無疑有助於洞徹顧炎武政治思想的主要是為哪個社會力量吶喊的,而不會將一些對於現代政治的期許投射到古人的思想上面。
三、餘論
值得注意的是,在1930、40年代的學術界,除了嵇文甫,其他馬克思主義史家也對中國儒家民本思想有所關注。比如在《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呂振羽認為孔子的思想“最符合‘士’的要求,所以自始便取得這一階層的熱烈歡迎與擁護。因而孔丘便以這一階層為基礎去策動其政治活動”。[39]秉承此志,孟子雖然同情民眾的疾苦,批判戰國君主的殺伐,但究其實,“他解釋‘臣’對於‘君’的忠實程度,是以‘君’對‘臣’的信託與知遇如何以為轉移,這是完全沒有原則性的,在本質上仍是絕對主義。後來儒家主張無原則的對君主個人盡忠,孟軻的這幾句話是有影響的”。因此,認為孟子思想具有民權特徵,“可以説是對孟軻的絕大誤會”。[40]
與呂振羽較為負面的評價不同,曾翻譯過《資本論》、對馬克思主義原典十分熟悉的侯外廬在《中國古代思想學説史》中則從與西方早期歷史的對比出發,認為戰國時期象徵着古典的“城市國家”日趨崩解,氏族單位日漸消失,新興的社會階級開始成為歷史舞台的主角。類似於亞里士多德所倡導的市民與貴族屬於天生的“政治動物”,孟子的民本思想本質在於擴大政治參與面,讓新興的“國人自由民”能夠成為統治集團的一份子,以挽救日趨腐敗沒落的貴族政治。[41]
而在著名的《十批判書》裏,身處抗戰時期大後方意識形態鬥爭氛圍裏的郭沫若為了證明孔子與墨子之間,前者在當時具有“革命性”,後者則為“保守派”,他強調作為民本思想核心要素的孔子的“仁”觀念是一種“由己及人的人道主義”,從歷史進程來看“這種所謂仁道,很顯然的是順應着奴隸解放的潮流的。這也就是人的發現。每一個人要把自己當成人,也要把別人當成人,然後自己才能成為人”。[42]對於《論語》裏飽受質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郭沫若則強調此處的“可”應為“能夠”之意,這段話放在歷史語境裏理解,應為“人民在奴隸制時代沒有受教育的機會,故對於普通的事都只能照樣做而不能明其所以然,高級的事理自不用説了”。[43]因此,孔子這段話是在對歷史現象做一個描述,並非在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張。
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在《中國通史簡編》這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通史編撰的代表之作裏,范文瀾認為分析包括民本思想在內的先秦儒家思想,必須從社會形態變革的角度出發認識到士階層的兩重性:“士處在社會中間階層,看不起老農、老圃,當然不願吃苦勞動。但在貴族階層裏,又沒有士的地位,很少有機會取得大官。因此他們憎惡世卿把持,要求登進賢才”。[44]因此,先秦儒家政治思想裏固然有批判的一面,但本質上都在主張“人民應該服從統治者”。必須承認,這些研究在具體觀點上並不完全一致,這一方面與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理論不同理解有關係,另一方面也和他們根據各自掌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對中國歷史與中國社會的不同剖析息息相關,更體現出了他們對當時現實的政治鬥爭形勢的不同分析。從今天的角度看,這些差異性反而表明了早期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內部繁榮而多元的面貌,以及不同學者基於不同的時代考量,對中國歷史展開頗具各自學術特色的研究。
與以上那些觀點相比,嵇文甫在這個問題上的研究無疑顯得更為細緻且全面,堪稱那個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史家裏,能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立場出發,對中國傳統思想有較為精深且持久研究的代表。在發表於1934年的《中國歷史上層有過民權思想麼?》一文裏,他將前文談到的那些觀點用精簡的方式敍述了一遍,並強調:“舊日的中國,長期停留在半自然經濟小商品經濟的社會中,人民大都過着簡單的散漫的農業生活。他們只希望聖明天子,並沒有意思去自己支配政權。他們有時候受不住壓迫了,則發而為無組織的羣眾暴動。暴動幸而成功,則舊朝變而為新朝,卻不是君權變而為民權。中國歷史上,只有‘弔民伐罪’的‘義兵’,而沒有真正的平民革命;只有浪漫的無治思想,而沒有切實可行的民治主張”。[45]
這一結論雖然被後來不少的中國思想史研究進一步論證,但嵇文甫對於中國儒家民本思想的辨析,值得注意的地方在於他由具體歷史時期的政治與經濟結構入手,深入分析各種政治批判主張的基本立場、所指的現象、分析的邏輯、解決的方案,而拒絕僅從那些主張的“批判性”表面看起來是否激烈判定其高下,尤其是他十分關注那些思想主張所設計的理想藍圖裏,哪一個階級或羣體最能受益,與此同時是否有意或無意遮蔽了其他更具普遍性的社會經濟矛盾。在他的分析框架裏,貫徹着歷史唯物主義把“抽象的人轉到現實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須把這些人作為在歷史中行動的人去考察”的特徵[46],在研究範式上超越了對中國傳統形式主義的肯定或否定。這既體現了嵇文甫對於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熟練掌握,又顯示了他對於時代學術與文化思潮的高度敏感性,在研究過程中不斷與不同觀點展開對話,使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史學更為“接地氣”。
此外,嵇文甫強調:“知道思想是生活的反映,是羣眾的產物,而具有階級性,則思想與社會的關係密切,思想隨着社會的轉變而轉變,當可洞悉無疑。因為所謂社會轉變,就是羣眾生活的轉變,就是階級關係的轉變,而這種轉變自然會反映到思想上去的”。[47]他對於中國古民本思想的解析,則用具體的例子向人們展示了馬克思者應該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思想。具體言之,對於中國傳統,必須根據歷史唯物主義方法論進行歷史的分析,揭示它在歷史中產生的政治與經濟背景,分析它在歷史進程中起到的正面或負面作用,以及這些思想在現實生活中代表了哪些羣體或階級的利益,並根據之前與之後的歷史發展狀況,綜合評估這些思想的歷史意義。而非脱離具體的歷史背景,用後見之明賦予這些思想超出其本來面目與所產生的歷史階段的正面價值或負面批評。這一點尤具學術與現實啓示。
最後,作為一名革命者,嵇文甫研究歷史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告訴世人社會發展的規律與剖析具體時代社會諸要素的方法,進而促進革命理論的傳播,讓世人能夠運用相似的方法來分析當下的社會狀況,形成正確的政治路線與良好的鬥爭策略,這也是革命戰爭年代裏大多數馬克思主義史家的共同特徵。如果説在嵇文甫生活的年代,儒家民本思想容易讓人混淆其與名副其實的民主政治之間的本質差別,那麼對於今天而言,面對後冷戰時代全球霸權意識形態話語裏的資本主義民主理論,也需要繼承嵇文甫對於中國儒家民本思想的辨析的方法與範式來進行一番剖析,尤其要注意到在表面上無比華美的詞彙背後,其所藴含着的對於階級狀況、經濟基礎、實際支配格局的基本假設。
如被視為資本主義政治理論家裏代表人物之一的熊彼特就聲稱,資本主義的民主政治“並無意味也不能意味人民真正在統治——就‘人民’和‘統治’兩詞的任何明顯意義而言——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機會接受或拒絕將來要統治他們的人的機會”。就此而言,“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政治”。[48]在這個過程中,廣大民眾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只是在投票之時就早已被“政治家”安排好的政治格局進行形式主義的投票而已。對於這樣政治體制及其意識形態話語,在今天同樣需要進行當年嵇文甫式的辨析,這樣才能更好的思考未來的制度建設問題,樹立堅實的制度自信與文化自信。
【本文原標題為《馬克思主義視域下的儒家民本思想——以嵇文甫為中心的探討》,刊於《福建論壇》2021年第2期。】
參考文獻:
[①]關於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總體特徵與流變,參見胡逢祥等著:《中國近現代史學思潮與流派(1840—1949)》,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版,第751—924、第1077—1257頁。
[②]如果將民本思想視為儒家傳統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話,那麼在中國歷史流變中,只有春秋戰國和明清之際這兩個時期民本思想顯得尤為突出,即一方面提倡民本思想的言説層出不窮,另一方面對當時的政治與文化產生了一定的影響,明清之際的民本思想更是被公認為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一個高峯。而在其他時期,基本上只是有不同的羣體在強調要實踐源自先秦儒學的民本思想。魏晉之際與晚唐時期,也有一些類似於民本思想的對君主制度的強烈批判,但那些言説主要是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而與儒學關係並不那麼緊密。因此,本文論述的重點就聚焦於春秋戰國(即先秦)與明清之際兩個時期。
[③]關於中國儒家民本思想流變,參見金耀基:《中國民本思想史》,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④]孫中山:《三民主義》,載《孫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62、263頁。
[⑤]梁啓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載朱維錚校注:《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46、123頁。
[⑥]李大釗:《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載《李大釗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5、187頁。
[⑦]嵇文甫:《做人問題》,載《嵇文甫文集》上冊,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頁。
[⑧]馬克思:《關於費爾巴哈》,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5頁。
[⑨]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52頁。
[⑩]嵇文甫:《週末社會之蜕變與儒法兩家思想上的鬥爭》,載《嵇文甫文集》上冊,第51頁。
[11]嵇文甫:《週末社會之蜕變與儒法兩家思想上的鬥爭》,載《嵇文甫文集》上冊,第42頁。
[12]嵇文甫:《週末社會之蜕變與儒法兩家思想上的鬥爭》,載《嵇文甫文集》上冊,第45頁。
[13]嵇文甫:《週末社會之蜕變與儒法兩家思想上的鬥爭》,載《嵇文甫文集》上冊,第47頁。
[14]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頁。
[15]嵇文甫:《先秦諸子政治社會思想述要》,,載《嵇文甫文集》上冊,第144頁。
[16]嵇文甫:《先秦諸子政治社會思想述要》,,載《嵇文甫文集》上冊,第151頁。
[17]嵇文甫:《先秦諸子政治社會思想述要》,,載《嵇文甫文集》上冊,第187頁。
[18]恩格斯:《反杜林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1—112頁。
[19]列寧:《國家與革命》,載《列寧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頁。
[20]列寧:《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文獻》,載《列寧選集》第3卷,第724頁。
[21]嵇文甫:《先秦諸子與古代社會(講義)》,載《嵇文甫文集》上冊,第304—305頁。
[22]嵇文甫:《春秋戰國思想史話》,載《嵇文甫文集》下冊,第213頁。
[23]嵇文甫:《先秦諸子政治社會思想述要》,載《嵇文甫文集》上冊,第192頁。
[24]關於這一問題,參見秦燕春:《清末民初的晚明想象》,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25]嵇文甫:《十七世紀中國思想史概論》,載《嵇文甫文集》上冊,第89頁。
[26]嵇文甫:《十七世紀中國思想史概論》,載《嵇文甫文集》上冊,第91頁。
[27]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節選)》,載《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180頁。
[28]嵇文甫:《十七世紀中國思想史概論》,載《嵇文甫文集》上冊,第98頁。
[29]嵇文甫:《十七世紀中國思想史概論》,載《嵇文甫文集》上冊,第100頁。後來溝口雄三用更為詳實的材料,進一步論證的嵇文甫的這個觀點。參見溝口雄三著,龔潁等譯:《所謂東林派士人的思想》,載《中國歷史的脈動》,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1—189頁。
[30]關於這個問題,參見費孝通、吳晗等著:《皇權與紳權》,北京:三聯書店2013年版。
[31]王爾敏:《晚清士大夫對於近代民主政治的認識》,載《晚清政治思想史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13頁。
[32]梁啓超:《論湖南應辦之事》,載吳江等點校:《飲冰室文集點校》第1集,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96、97頁。
[33]嵇文甫:《中國歷史上曾有過民權思想麼?》,載《嵇文甫文集》上冊,第472頁。
[34]嵇文甫:《<黃梨洲文集>序言》,載《嵇文甫文集》下冊,第256頁。
[35]顧炎武:《裴村記》,載劉永翔校點:《亭林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9頁。
[36]嵇文甫:《十七世紀中國思想史概論》,載《嵇文甫文集》上冊,第105頁。當然,類似的主張並非從顧炎武才出現,宋代以來已經有不少關於“富民”、“豪民”為國家基礎的論調,並反對儒家政治傳統裏的“均貧富”主張。參見葉坦:《富國富民論——立足於宋代的考察》,北京: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85—92頁。林文勳:《保富論:一種充分體現時代特徵的嶄新經濟思想》,載《唐宋社會變革論綱》,北京:人民出版社303—327頁。
[37]袁良義:《明末農民戰爭(修訂本)》,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版,第16—24頁。
[38]嵇文甫:《十七世紀中國思想史概論》,載《嵇文甫文集》上冊,第106頁。
[39]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81頁。
[40]呂振羽:《中國政治思想史》上冊,第174頁。
[41]侯外廬:《中國古代思想學説史》,載張豈之主編:《侯外廬著作與思想研究》,長春:長春出版社2016年版,第184—185頁。
[42]郭沫若:《十批判書》,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9頁。
[43]郭沫若:《十批判書》,第76頁。
[44]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上冊,北京: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129、143頁。
[45]嵇文甫:《中國歷史上曾有過民權思想麼?》,載《嵇文甫文集》上冊,第474頁。
[46]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6頁。
[47]嵇文甫:《先秦諸子與古代社會(講義)》,載《嵇文甫文集》上冊,第277頁。
[48]熊彼特著,吳良健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年版,第41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