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楓:喀布爾和AUKUS之後,美國沒有回來,法國回來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晨楓】
在喀布爾時刻之後,歐盟需要自己軍隊的呼聲再次高漲起來。8月底,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相當於歐盟外交部長)博雷利在接受法新社採訪時表示,阿富汗的混亂撤離為歐盟敲響了警鐘,歐洲需要發展獨立於美國的軍事能力。在9月2日舉行的歐盟成員國外長非正式會議上,他重申了這一觀點,並敦促歐盟建立自己的5000人的快反部隊。
法國總統馬克龍上任後就一直呼籲建立“真正的歐洲軍隊”,還批評北約已經“腦死亡”。在2018年紀念一戰結束100週年的時候,馬克龍提出建立獨立的歐洲聯軍,以應對俄中美,還得到默克爾的支持。
對此首先表示反對的當然是北約。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認為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歐盟軍隊是在“建立平行機構和重複的指揮機構”,這種“重複的努力”會損害各方合作的能力。北約歡迎歐洲在防務領域做出更多努力,但這種努力永遠無法取代北約。斯托爾滕貝格並不隱晦地指出,需要做的是確保歐洲和北美團結在一起,而北約80%的防務開支來自非歐盟成員國,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土耳其、挪威、冰島等。“任何削弱北美和歐洲之間紐帶的企圖不僅會削弱北約,還將分裂歐洲。”
喀布爾時刻之後,歐洲對美國陷入了深重的信任危機,這是西貢時刻之後從來未有的。
歐洲軍團:誰也不願意交出指揮權
歐盟是歐洲團結的產物。二戰後,在戴高樂和阿登納的領導下,法德之間達成歷史性的和解。以此為基礎,法國、西德、意大利、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在1952年結成歐洲煤鋼共同體,這六個國家後來成為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核心六國”,歐盟則是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政治架構。但歐盟是歐洲的政治經濟存在,不具有軍事力量。
戴高樂時代的法國就力主歐洲獨立,包括由“核心六國”組成的獨立軍事力量,但直到1987年,密特朗與科爾達成協議,建立法德旅(Franco-German Brigade),第一支“歐洲軍”才建立。法德旅在2009年組建完畢,由一名法國將軍指揮,旅部設在德國巴登-符騰堡的繆爾海姆。2009年,一個德國營移防法國的斯特拉斯堡,這是二戰結束以後第一次有德軍在法國駐紮。2014年,法國從德國撤回1000人,此後法德各在對方留一個500人的部隊。總兵力還是4000人(一説6000人)。
法德旅下轄法國的第3驃騎兵團、第1步兵團、德國的第291輕步兵營、第292輕步兵營、第295炮兵營、第550裝甲工兵連,另有一個法德混成後勤營。這是一個機械化步兵旅,配屬有兩個連的PzH2000自行榴彈炮和一個連的M270火箭炮。
法德旅還在繼續運作,但不大成功。德國軍人裏法語並不普及,法國軍人裏德語更不普及。作為北約成員,兩國軍人倒是都能用英語溝通,英語也是北約的工作語言,但作為歐洲獨立的軍事象徵,法德旅又沒有英美人員的參加,用英語作為工作語言就彆扭了。不過沒有英國的歐盟繼續用英語作為工作語言,這點彆扭也就忍了。問題是法德旅主要是一個政治存在,並不是有效的作戰單位。
但歐洲軍的夢想還在繼續。1992年,歐洲軍團(Eurocorp)司令部在法國斯特拉斯堡組建,1993年開始運作。歐洲軍團的核心部隊(也是唯一真正下屬的部隊)就是法德旅,另有一個指揮支援旅。值得注意的是,歐洲軍團的指揮權屬於成員國,不隸屬於歐盟或者北約,不是歐盟的共同安全與防衞政策(CSDP)的一部分,也不是CSDP下屬的永久性結構合作(PESCO)的一部分,但可以應歐盟、北約、聯合國、歐安會的要求而出動。

歐洲軍團是歐洲的一個跨國軍事組織,其共有約一千名士兵,駐紮於法國斯特拉斯堡。(圖源:維基百科)
歐洲軍團的成員國有比利時、法國、德國、盧森堡、西班牙,夥伴國家有希臘、意大利、波蘭、羅馬尼亞、土耳其,奧地利、加拿大、芬蘭曾經是夥伴國家,現在退出了。2004年的斯特拉斯堡條約規定,只要現成員批准,任何歐盟成員都可申請加入,成為成員國。
歐洲軍團受共同委員會指揮,委員會由成員國組成。成員國和夥伴國在需要時貢獻作戰部隊。在理論上,法國第1裝甲師、德國第10裝甲師、比利時第1中型旅、西班牙第1機械化師、盧森堡一個偵察連都可劃歸歐洲軍團指揮,峯值兵力可達60000人。不過這些部隊在平時都歸各國指揮,只有在戰時移交指揮權後才劃歸歐洲軍團指揮。在吸取了法德旅的教訓後,歐洲軍團用英語作為工作語言。
歐洲軍團倒是參加過實戰的,如波黑維和、科索沃維和、阿富汗ISAF治安戰、北約快反值班部隊、馬裏維和等。
歐洲還有歐洲憲兵(European Gendarmerie Force,簡稱EGF)、歐洲海上力量(European Maritime Force,簡稱EMF)等跨國軍事和準軍事力量。EGF相當於武警,EMF相當於海上警衞隊,與歐洲軍團一樣,EGF、EMF都不屬於歐盟或者CSDP架構,但可“應邀”提供協助。
還有更多的歐洲軍的構架。2010年,薩科齊和卡梅隆簽訂蘭開斯特宮協議,規定成立共同聯合遠征軍(CJEF),包括地面、海上、空中和後勤力量,但這也同樣不是常備軍,只是能夠迅速召集的遠征軍。同樣,CJEF只隸屬於英法和未來加入的成員國,不屬於歐盟或者北約。
德國與荷蘭在2016年組建了第414坦克營,有100名荷蘭軍人和300名德國軍人組成。説起來,這是德國兵員不足和荷蘭坦克不足的產物。這比法德旅的運作要平順的多,一是因為規模小,層級低,容易打造凝聚力;二是因為沒有語言障礙,荷蘭語和德語足夠接近,雙方可以直接溝通。這倒是常備軍。
這些歐洲聯合但不屬於歐盟或者北約的軍事架構是很奇怪的,但對歐洲人來説並不奇怪。歷史上歐洲君王經常只有少量親兵,內戰外戰的時候需要邀集貴族支持。君王得到自帶親兵的貴族加盟後,才能組成真正可以打仗的大軍。英國國王是這樣,歐洲國王也是一樣,只是邀集的不只是本國貴族,還有外國的國王、王子(日耳曼諸侯中常見的封號,在國際關係中地位比國王低,但擁有一樣的實權,尤其是軍權和財權)。在這個意義上,歐盟有點像歷史上架空的虛權君王,還不容易得到諸侯勤王。
歐盟有下屬的歐洲防務局,統籌歐洲防務和推進防務合作,但沒有實權。歐盟有CSDP的政策架構,下設PESCO等防務機制,但一大堆眼花繚亂的名目都是紙老虎,沒牙齒的。現代歐洲與歷史歐洲其實沒有太大的不同,諸侯抓緊自己的軍權、財權,放棄鑄幣權而改用歐元已經是天大的犧牲了,要求連軍權也放棄,那真是A Bridge Too Far了。博雷爾要求的5000人歐洲快反部隊是現成的,法德旅、第414坦克營、CJEF都可以成為基幹部隊,但誰都不願把指揮權交給歐盟。

歐洲防禦局,成立於2004年,總部設在布魯塞爾,歐防局的使命是支持歐盟成員國提升軍事實力,以滿足歐洲安全與防務政策的需要(圖源:歐防局官方網站)
歐洲軍到底是用來幹什麼的?
歐洲軍定位的錯亂,這是最大的問題。
歐洲利益不總與美國一致,這沒有疑問。歐洲需要自己的獨立軍事力量來保衞自己的利益,這就不那麼確定了。如果説保衞歐洲利益指維護歐洲的主權和領土完整,這實際上不是歐洲軍的任務,歐洲軍也完成不了這個任務,這是北約的任務。説白了,歐洲已經沒有能力保衞自己了,只有通過北約架構依靠美國才能保衞歐洲。
但如果保衞歐洲利益指維護歐洲的域外利益,要是歐洲利益與美國一致,歐洲反正是搭便車,維持現狀足矣。要是歐洲利益與美國不一致,這倒是需要獨立的歐洲軍事力量了,不同的歐洲跨國軍事力量也正是以此原則打造的。問題是,任何軍事力量的第一使命永遠是保家衞國(歐盟可以看成一個超級國家),然後才談得上保衞海外利益。即使是美軍也是一樣。美國由於地理紅利,本土受到的威脅水平很低,海外軍事存在的第一目的依然是確保任何戰爭的主戰場在海外,不使戰火波及美國。如果歐洲軍的第一任務是海外干涉,存在的理由就很蒼白了。
另一個問題是:如果歐州軍的主要使命是用於與美國利益不一致的海外干涉,還不只是美國放手而聽任歐洲填補空缺的情況,這對美國利益就是侵蝕,最終必然侵蝕美歐防務合作的政治基礎。
把歐盟變成有牙老虎也會使得歐洲一山二虎,另一隻老虎自然就是美國。歐盟這隻老虎和美國這隻老虎如何在歐洲共存,這是歐洲不願去想的問題。這與經濟、文化、科技競爭不同,那是兩隻老牛在同一片草地上吃草。
在技術上,歐洲軍的軍事指揮權也是敏感的問題。即使歐洲軍的成員國願意移交,各國還同時負有北約義務。同一支部隊聽命於不同的指揮鏈是軍事上的大忌,但要求成員國在軍隊建設上搞雙份,一份對北約負責,另一份對歐洲軍負責,這是不可承受的軍費負擔,也根本過不了民意關。
遠征軍也不只是各國貢獻裝甲師的問題,需要完整的空中力量、海運力量、情報指揮等支援保障體系,歐洲根本不具備這樣的能力。從前南斯拉夫戰爭到利比亞戰爭到敍利亞戰爭,歐洲一次又一次尷尬地發現,離開美軍作戰體系的保障,歐洲幾乎無法獨立發動一場現代戰爭。在喀布爾機場,歐洲軍隊也完全被動,美軍主動“站好最後一班崗”已經對歐洲盟軍很照顧了,美軍撤離後,歐洲盟軍獨立地繼續留在機場,撤出更多的人,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
但建立完整的歐洲作戰體系大大超過了歐洲的負擔能力,實際上也超過了歐洲現在的軍事技術水平。比如説,在隱身戰鬥機、預警機、戰略運輸機、戰略轟炸機、偵察衞星、軍事通信衞星、導航衞星、航母、盾艦、兩棲戰艦、核潛艇等方面,歐洲或者是空白,或者存在嚴重不足,而且在可預見的將來缺乏填空補缺的計劃。購買美國裝備不僅有錢的問題,還有使用上的限制,不可能以此成為真正獨立的軍事力量。
歐洲軍的根本癥結在於歐洲的政治野心與經濟、科技現實脱節。如果現在還是歐洲列強的時代,根本就沒有歐洲軍的問題,既不會有歐盟存在,也不會有北約存在。英法德會繼續爭霸,但只要有需要,各家都有能力自行派遣遠征軍,遍及全球的殖民帝國和歷次戰爭就是這樣打下來的。
今天,歐洲還自我感覺良好,自認為是世界的一極,但戰略思維與戰略資源嚴重脱節,政治野心與政治決心嚴重脱節,計劃和宏圖制定了一大堆,但既缺乏政治決心,又缺乏具體的執行力。只要有必要,美國有能力甩開歐洲單幹,這是因為美國有這個本錢。但是歐洲沒有。在心比天高力比紙薄這一點上,歐洲與印度很相像,但這是另一個話題。
歐洲軍也很難得到新歐洲的支持。必須説,歐洲軍事獨立是老歐洲的想法,新歐洲可是一心指望美軍保衞他們的。冷戰後的北約東擴使得老歐洲不再面對蘇軍入侵的威脅,新歐洲一方面成為老歐洲的緩衝區,另一方面以激烈反俄反共作為投名狀,任何可能導致美軍淡出歐洲的想法對他們都是致命的。
歐盟的主題是歐洲團結,歐洲團結的目的是達到歐洲獨立,但軍事上不獨立還不是歐洲獨立的最大難題,歐洲在這個科技正在主導生產力的時代,面臨科技上也失去獨立的問題。這是釜底抽薪的大問題。如果不能解決,未來的歐洲不是能不能獨立的問題,連富庶都難保持。
第一次工業革命由蒸汽機帶動,第二次工業革命由內燃機和電氣化帶動,都是在歐洲啓動的,造就了歐洲的繁榮,歐洲至今仍然在吃紅利。第三次工業革命由電子化和計算機化帶動,美國是領導者,歐洲落後了。第四次工業革命以人工智能、機器人、自動化、數字化為特點,主戰場在中美之間,幾乎沒有歐洲什麼事。歐洲很明白:靠普拉達、拉菲甚至法拉利、勞力士是沒法保持歐洲的繁榮的,旅遊更是在往後看。但再工業化是美國和歐洲都在掙扎的問題,歐洲的問題更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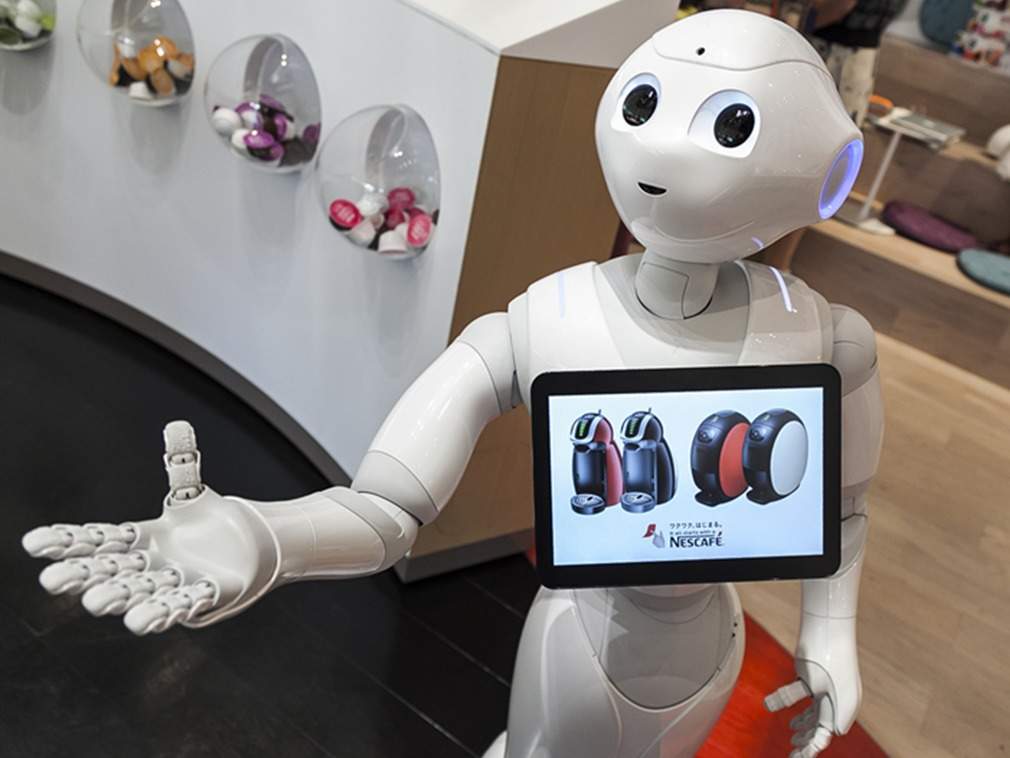
人工智能被視為是繼電力和互聯網之後對人類社會產生顛覆式影響的技術,早就是“兵家必爭之地”(圖源:VCG)
喀布爾時刻是個歷史性的時刻。在阿富汗戰爭開始的時候,美國處於冷戰後的巔峯,正在享受“歷史的終結”。這沒有歐洲多少事,但畢竟美國是“我們村的老大”,歐洲跟着沾光。這也是章家敦出版《中國即將崩潰》的時候。
美國是在噩夢中度過阿富汗戰爭這20年的,歐洲則是在夢遊中度過這20年的。喀布爾時刻把歐洲拉回現實:歐洲不能指望美國保護自己的利益。在犧牲美國利益和犧牲歐洲利益之間,美國會毫不猶豫地犧牲歐洲利益,連事先招呼和事後安撫都沒有的。歐洲更沒法獨立保衞自己的利益。
歐洲怎麼辦?老實説,除了繼續呼籲,歐洲上下並不存在更大的政治決心。各種共同防務機制還將繼續紙老虎下去,直到下一個喀布爾時刻。斯托爾滕貝格對歐洲軍的反對點中了要害:歐洲無法負擔這樣的平行架構,歐洲也不可能在美國佔絕對多數的股份公司裏有更大的發言權。
直到AUKUS時刻
法國的大單潛艇生意“被盜”,這樣規格和性質的毀約是史無前例的。法國也毀過約,出售給俄羅斯的兩艘“西北風”級兩棲攻擊艦在克里米亞事件後毀約了,最後轉售給埃及。但俄羅斯並非盟國,克里米亞迴歸俄羅斯在西方被認為是侵略和非法侵佔,所以這樣毀約是“合理”甚至“正義”的。澳大利亞不同,這是“具有共同價值和利益”的盟國,這樣卑劣的毀約就太背信棄義了。現在還不清楚法國毀如何索賠,澳大利亞是否會賴賠,未來澳大利亞的商業信譽會如何受到損害,但這是另外一個話題了。
馬克龍在康沃爾G7上與拜登勾肩搭背,以為很親密,法國軍艦與核潛艇還到南海巡航,但美英澳在那時已經秘密形成核潛艇共識了,法國被徹底當猴耍了。法國很憤怒,召回了駐美國大使,這還是1778年以來第一次。法國也召回了駐澳大利亞的大使,已經談了3年的歐盟-澳大利亞自由貿易協議可能要黃,法國還取消了法英國防部長會談。
法國不是失去理智,而是醒來發現自己在美國盟國體系裏的真實地位,也被迫重新評價法國的真正利益和威脅所在。馬克龍本來就是屬於“輕戴高樂主義”,現在有可能重拾戴高樂主義的旗幟,強力推動歐洲戰略獨立,而且是以歐盟為平台而不是法國單幹的戰略獨立,一方面為法國贏回榮譽和歐洲領導權,另一方面也凝聚日益四分五裂的法國民意和族羣。沒有什麼被外侮更能凝聚一個驕傲的民族的了。
歐洲戰略獨立需要有牙齒,需要在歐洲主導的政治架構之下。歐洲戰略自主首先要擔負起歐洲防衞主力的重任,而不只是歐洲自主的海外干預,現有的歐洲軍團與歐盟的尷尬關係是不能成事的。博雷利的5000人歐洲快反部隊也只是歐洲指揮下用於海外干預的準軍事歐洲憲兵力量,也談不上是歐洲戰略獨立的軍事中堅。歐洲戰略獨立的關鍵在於擺脱歐洲安全對美國的依賴,美國的背信棄義和英國的背後捅刀不僅是針對法國的,也是針對整個歐洲的。
法國不代表整個歐洲,但法國是法德軸心的傳統政治極,法德軸心則是歐盟的核心,比利時、荷蘭、意大利、西班牙都還是外圍,新歐洲只是“附件”。二戰嚴重削弱了法國,但法國依然是歐洲事務中舉足輕重的。北約起始於英法之間的敦刻爾克條約;歐盟起始於法德主導的歐洲煤鋼聯盟;歐元是在法國的政治領導和德國馬克的信譽下聯手推動的;歐洲先進製造的最亮點空客更是法國領導的。
法國也擁有歐洲唯一完整的軍事科技和製造體系,英國軍工體系已經成為美國附件了,德國軍工則是不完整的。法國軍事技術足夠先進,問題在於國內需求不足以支持可持續的發展。法國軍工需要空客化,不僅是“為歐洲的軍工”,更是“歐洲人的軍工”。軍工不是商貿,直接與地緣戰略和政治取向相關,只有重建歐洲戰略獨立,才有“歐洲人的軍工”的可能性。法國軍工必須放棄拘泥於全自主的傳統觀念,走出碎片化的眾多雙邊和多邊合作,走向可持久的泛歐洲合作,徹底解決可持續發展和規模經濟的問題,並以軍事裝備的歐洲化引導歐洲戰略獨立的實質化。法國軍工的空客化也可成為歐洲先進製造的起飛線。
由於法國經濟的相對滑落,德國不再單純是歐洲的經濟發動機了,在法德軸心中的政治發言權大有提高,尤其在2008年經濟危機期間。但德國的政治興趣大多集中在歐洲內部事務,最多延伸到歐洲與俄羅斯的關係。出於對自身歷史的敏感性,德國一般避免對國際安全事務做出過於強勢的表態。
近年來,中國成為歐洲政客中的政治話題,尤其在德國。得到美國的支持還是德國政客很看重的。但中國話題的性質不同,主要是經濟的,而不是政治和軍事的。在當前的德國大選中,中國話題始終熱不起來,很説明問題。在經濟上,中國製造正在紮實提升層次,已經侵蝕德國製造了。德國製造的精華在於機械的精密度和可靠性,但中國製造的機械質量在迅速提升,代表未來的數字化技術則是德國無法比拼的。
這樣的彎道超車很使德國憂心,不僅出口市場被擠佔,國內的基本盤都有可能不保。但在軍事上,再怎麼牽強附會,中國也對歐洲沒有軍事威脅,這個文章沒法做。在政治上,無非是“共同價值”那一套,在香港、新疆事務上鬧妖是一回事,提高到軍事層面就是完全不同的問題了。
德國政客可能通過歐盟平台在務虛的層面上高調挑戰中國,但在務實的德國政府層面上,還是相當謹言慎行的。默克爾時代結束了,但默克爾並不是因為執政失敗而離去,而是因為從政已久、身心疲憊了。16年總理當下來,功勞沒人數,過錯人人記,這是正常的。人們產生“默克爾疲勞”,她對黨內和友黨的控制日趨減弱,這也是正常的。但這與2020年特朗普被選下去,或者2016年希拉里落選,是完全不同的,那是選民拒絕現有政治路線的延續。

德國總理默克爾12月30日向德國民眾發表了她任期內最後一次新年致辭。她總結稱,在新冠疫情的影響下,2020年是她執政以來“最艱難的一年”。(圖源:路透社)
如果默克爾不執意離開政界,這次大選會遇到強勁阻力,但很可能依然是最強勁的候選人。這正好説明德國公眾並不急於在政治上大轉向,並不介意某種形式的“沒有默克爾的默克爾主義”。默克爾也不是從“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開始的,新的德國總理並非不可能在上台初期有譁眾取寵的動作,以積攢政治資本,但現實是最教做人的,不久就會回到穩健路線。當然,這樣的預判很快就要揭曉,只有時間才能證明是否正確。
如果正確,這意味着德國將不介意法國主導歐洲戰略獨立的議題,巴黎-柏林軸心而不是布魯塞爾才是決定歐盟基本政治方向的。在特朗普時代,德國吃過美國貿易戰的苦頭,德國最關心的歐洲經濟戰略獨立最終需要歐洲政治軍事戰略獨立為後盾,德國不可能在依靠美國保護的情況下贏得貿易戰中的對等地位。因此,歐洲戰略獨立的基點並不是針對誰,而是獨立於美國主導。
AUKUS涉及防止核擴散,間接地也涉及導彈技術控制。據傳協議也包括向澳大利亞轉移“戰斧”巡航導彈,由於核潛艇的性質和作戰使用特點,這大概率不只是傳言。澳大利亞核潛艇和“戰斧”巡航導彈對歐洲不是威脅,但打開的潘多拉之盒對歐洲是巨大的威脅。在歐洲的門檻上,不乏急於跨過核門檻和導彈門檻的國家。美國為了對抗中國,不顧歐洲安全,前有退出為歐洲安全量身訂造的“中導條約”,現有澳大利亞核潛艇和“戰斧”巡航導彈,歐洲很難不考慮美國對歐洲安全利益的漠視。
歐盟和法國一樣,也被當猴耍了。歐盟剛對中國梗起脖子,在中歐投資保護協議、新疆、香港、印太戰略等問題上積極配合美國,就被美國在事關歐洲安全的重大問題上直接無視,很難不感到寒心。9月20日,歐盟各國外長在聯大會議間隙舉行閉門會議,就AUKUS展開討論。會議結束後,博雷利表示,歐盟各國外長“明確表達了與法國團結一致”的立場。
在更加廣泛的層面上,拜登在推動美日澳印半導體供應鏈,沒有歐洲什麼事。歐盟也開始推動《歐洲芯片法》,將歐盟的半導體研究、設計和測試能力聯繫起來,由歐盟與各國協調投資,實現半導體自給自足,最終建立先進的歐洲芯片生態,不僅確保供應鏈安全,也將催生為突破性的歐洲技術開發市場。這不是商業行為,只能放在歐洲戰略獨立的大框架下理解。歐盟推遲了原定於9月29日與美國舉行的首屆“貿易和技術理事會”的籌備工作。歐洲議會國際貿易委員會主席、德國議員蘭格9月21日表示,歐盟與澳大利亞之間也“出現了信任問題”,雙方自由貿易協定談判預計將被推遲。
拜登的“美國回來了”很使得歐洲一些人、國家和組織感到鼓舞,急於抓住美國這根大槓桿,實現各種小利益。但AUKUS揭示了美國對盟國劃分為三六九等,“一人為大家,大家為一人”的盟國關係成了“大家為一人,但一人只為自己,會拉上有些人,其他人只是利用而已”。拜登的虛偽可能是美國的歷史性失策,比特朗普蠻橫的功利還要富有傷害性。
歐洲重建戰略獨立需要從政治決心、軍事技術、經濟資源、民意所有方面同步推進,歐洲一直缺乏這樣的勇氣和齊心,喀布爾時刻證明了美國無視歐洲十分焦慮的難民和恐怖主義威脅,AUKUS證明了美國無視事關歐洲生存的核擴散和導彈擴散威脅,歐洲戰略獨立或許得到了意外的動力。

法國總統馬克龍(資料圖)
在戴高樂時代,法國就努力推動歐洲戰略獨立,但在蘇聯入侵的威脅之下被看成無理取鬧,法國只有單幹,很無趣也很無助,最後在薩科齊時代“回到北約”。在後冷戰時代,法國試圖通過歐洲旅這樣的措施再次推動歐洲戰略獨立,但俄羅斯已經不成威脅,歐洲處在歷史上最安全的時代,還有北約罩着,歐洲戰略獨立師出無名。喀布爾時刻之後,歐洲戰略獨立師出有一點名了,但還是不足;AUKUS可能是關鍵的臨門一腳,歐洲戰略獨立總算師出有名了。
都説危機是危險和機遇並存,這是法國的機遇,更是法國領導歐洲的機遇。幸好英國脱歐了,否則還礙事。不斷有人猜測,法國會不會怒而再次退出北約軍事一體化體制,這也太小看法國了。馬克龍可能在心裏悄悄吼了一嗓子:“法國回來了”!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