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亮:“網絡舉報”的辯證法
【文/餘亮】
當下互聯網上流行的“挖墳”和“舉報”行為,常常掀起輿情風雨,但也應該開啓我們對政治和輿論的新思考。
2020年2月發生的“227”肖戰事件,由各種飯圈舉報、亂戰構成,至今未休,幾乎與新冠疫情同歲。至於某某導演有辱華言論、某某品牌發佈辱華廣告,某某教師在課堂散步反動言論,某某動畫片對兒童成長不利……一個個舉報明滅交替,事主過去的不良言行被挖出,互聯網有記憶,新賬舊賬一起算,似乎沒人躲得了。
對此,有人開心,有人恐懼。如果我們沒有過分的潔癖,也可以把這一切看做一種全過程民主在互聯網時代的曲折發展。
最近一起引起較大反響的輿論事件是“劉先生”對歌手宋冬野的舉報——劉先生反對五年前涉毒的藝人近期開演唱會,導致演唱會被主辦方取消。
在我的調查當中,普通網民多數支持長期封禁涉毒藝人。而一批知識分子媒體人則撰寫文章,以法治的名義批判舉報行為,將之視為告密,甚至視為文革。這其中的“雙標”色彩一眼可知——不合自己意見的舉報就是文革,就是烏合之眾,合意的舉報就被看作英雄,無視自身也經常參與舉報以及挖掘對立陣營人物的黑歷史。
但是,這些指責當中也有啓發的部分,比如宋冬野被罰三年禁演到期之後,是否應該根據舉報繼續被禁,這對我們的法治到底有什麼啓示?
可惜,一些“公共知識分子”繼續在固有的範式和過去的意識中思考,辯經很完美,卻錯過了啓迪。今天的互聯網舉報和過去不同,對法治、網治、人民民主都提出了新課題。

首先要把舉報看作一種信息和意志的傳達渠道,背後是信息權力結構的大變局。
過去一批精英媒體人無比強調輿論監督,那是因為在紙媒和門户時代,輿論仍然是傳媒精英可以掌握的“第四權力”。PC互聯網主要釋放了自由主義者的聲音能量,移動互聯網卻釋放出更多元也更不均衡的聲音能量。
國家支持建立的各種合法舉報渠道與大型互聯網社交平台和自媒體耦合共振,提升了人民監督的權力,然而這是一把雙刃劍。公知大V曾經嚐到雙刃劍的甜頭,現在嚐到了另一面。舉報是各種民意博弈的極化表現,包含積極與消極的成分,只放大其中一面,無助於認識理解。
以小粉紅現象為例,我在一篇論文裏初步談到事關愛國主義的舉報現象特徵(《小粉紅的大變局:中國青年思潮十年劇變》)。在政治維度上,這是一種過去被美國夢壓抑的愛國主義能量,如今通過互聯網,突破過去公知大V圍剿,得以與中國復興呼應的辦法。
例如,在大學裏,學生面對崇洋媚外教師形成的知識霸權,無法在課堂或者校內解決,就可能通過舉報來對抗。一如學生舉報教師性騷擾,得以釋放的不止是愛國主義,各種正負能量都在逐鹿。
第二,各種互聯網人羣與能量重整,必然摩擦不斷。
過去因為市場經濟而日益離散化的羣眾,現在又通過各種平台交流技術和二次元空間重新組織,尤其Z世代青年人,作為網絡原住民,深具互聯網和二次元脈搏。當別人責怪他們喜歡貼標籤、容易符號化而缺少現實經驗的同時,要想到,互聯網尤其算法的特徵不就是無窮的進行標籤化和符號化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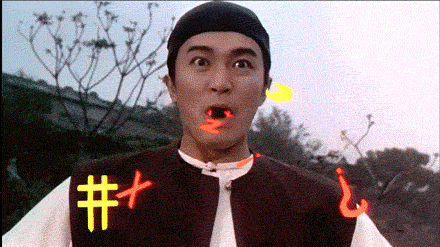
第三,“挖墳”“舉報”等行為是新的互聯網人格中的一環。
人們不喜歡的飯圈生態,就是互聯網組織形態的必然階段,這種“散户”抱團取暖或出征的狀況,中美兩大國莫不如此。
飯圈化的日常生活,伴隨着一種矛盾的“正確觀”:一方面要求公眾人物三觀正,一方面對自家愛豆網開一面。一方面網上衝浪無所不知,一方面又追求圈地自萌,不被打攪。這包含了一種“消極自由”態度,然而消極自由帶來的永遠不是開放,而是執迷、脆弱和內卷,塑造出的心性難以適應不同圈子的差異,難以體會不同語境的低語。
後現代人類,沉浸於虛擬空間,較少具有直接行動能力和機會,體魄越來越文明,精神越來越“規範”——一如“三觀黨”的出現,脾氣可能越來越脆弱或暴躁——一如抑鬱症的流行。因此不滿的時候,他們更習慣於選擇一條文明而憤怒的抗爭渠道——舉報。看似激烈的飯圈化舉報行動,卻具有“守法”特徵,即積極走正式渠道向各個主管方投訴舉報,善於利用人數和合法程序潮水般地打擊對手,從而體現為一種合法的“暴力”。
不得不承認,相比直接的黑客攻擊行為,機器水軍行為,甚至線下約架暴力行為,當下的“舉報”更少野性和率性,變文明瞭,也變狂躁或抑鬱了。很多互相舉報的陣營裏都會湧現出拿抑鬱症説事的人。暴力變得虛擬化,比如“人肉搜索”。即便以民族主義面目出現的年輕小粉紅,也少不了受此影響,然而因為偉大歷史鬥爭沒有終結,他們仍然承載了一息超越日常飯圈生活的氣概。
這就是舉報的二象性:一面是合法的“民主”過程,一面是虛擬空間“暴力”鬥爭過程。各方都在使用,各方都會喊冤。需要做的不是置身事外的坐而論道、品頭論足,而是要堅持從羣眾中來,到羣眾中去,倚重羣眾自我教育的力量進行引導、互相砥礪,善用這股能量。
例如,如何看待宋冬野被舉報,一些學院派從現有司法角度闡釋,有其道理,比如強調要以法律為準繩,不可隨意加重處罰,不可一味隨民意搖擺,戒毒人員在入學、就業、享受社會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視等等,但是卻忽視了中國的法治脈搏節奏,也沒有看到中國特色的“人民壓力政治”一面。
我向各行各業羣眾請教,他們有接觸吸毒者的醫生、法警、法考生、影視行業從業者、公共關係工作者以及各類行業人士。觀點總結起來有三點:
一是一線人員對吸毒惡果的嚴重程度認知遠超知識分子。
醫生直言吸毒讓人變成另一種生物。影視從業者指出西方世界荒謬的大麻合法化對國內演藝圈的影響,擔憂演藝圈成為毒品通道,且公眾人物的態度會給青年造成嚴重不良示範。人民羣眾的不滿不僅是針對宋冬野,而是對各種資本娛樂圈亂象不滿的集中反應。他們認為宋冬野缺少反省,不適合再作為公眾人物露面,從事幕後工作則沒有問題。
二是討論法治要放在具體的歷史和社會條件下看待,不能空談法條,要有自己的底線思維和法哲學。
中國人對毒品危害的感受遠超西方。有人盲目崇拜西方社會對吸毒藝人的“寬容”,這不僅不符合事實,也無視西方世界尤其美國每年大量人口死於毒品的恐怖狀況,這種“與國際接軌”思維是荒謬的。

宋冬野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吸毒“其實沒那麼嚴重,還是可以改正的”
有一線法警認為我們目前法律對演藝圈吸毒的懲處還不夠,法律有滯後性,需要靠民意來彌補。近期中宣部發布《關於開展文娛領域綜合治理工作的通知》,集中治理流量至上、飯圈亂象、違法失德等現象,與民意相呼應,也彌補了法律的滯後性。
第三,民眾走合法渠道舉報本身沒有問題,關鍵是處理舉報的有關方面要有魄力和決斷,既要呼應人民聲音,又不能縱容誹謗式舉報。還有危機管理人士認為,取消演唱會不是官方的決定,而是主辦方根據自身利益和各方訴求而作出的風險最小的決定,這是多方博弈的結果,而非一個簡單的法治問題。
互聯網舉報不是非黑即白的事物,而是我們發展過程中的一個辯證環節。趨利避害積極穩妥的加以利用,這正是發展和落實“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結合”的新時代課題。
(本文為《環球時報》10月27日約稿,限於篇幅,發表時有較大刪改,本文為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