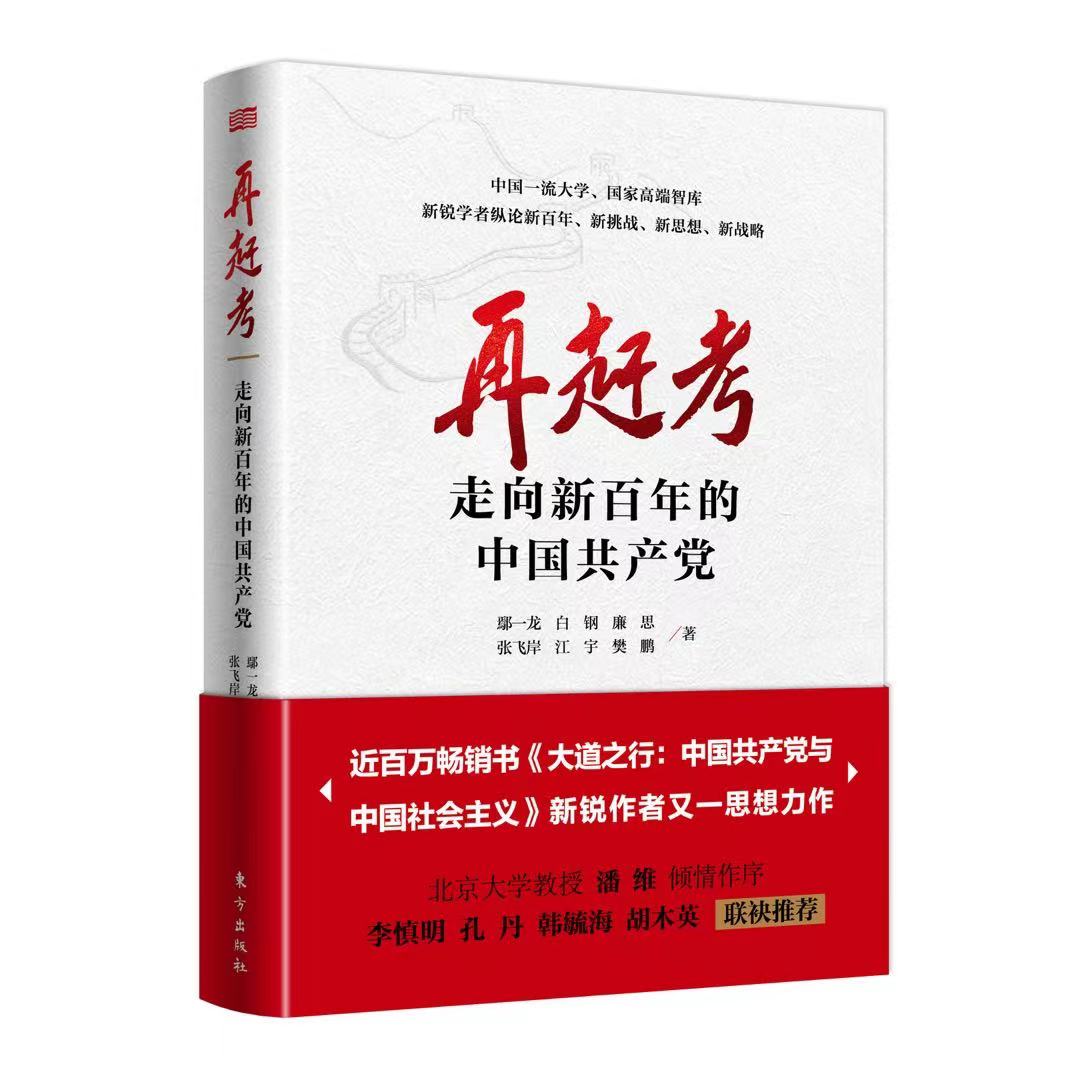鄢一龍|中共面臨的一道考題:如何避免資本撐破社會主義帳篷?
【文/ 鄢一龍】
社會主義將資本作為手段,以實現自身的目標。同樣,資本也可能將社會主義視為宿主,如同在沙漠中借主人帳篷取暖的駱駝,一點點擠入帳篷,並希望有朝一日,把主人趕跑,自己獨佔這個帳篷。
這個比喻並非危言聳聽。資本這隻駱駝已經不是原先那個可愛的寵物了,它已經成長為龐然大物,資本的體量與其能夠影響的經濟規模都與改革開放初期不可同日而語。
資本增殖的方式也越來越體現出其腐朽性、壟斷性的一面,這種變化還在與日俱增,使人不禁追問:資本要走向何方,這對社會主義意味着什麼?
就其本性而言,資本不會滿足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限定的結構,它正努力掙脱加在其身上的社會主義束縛,日益要求成為不受束縛的,既自主、自在又自為的力量。
(一)底層侵蝕:新基礎結構的私有制
底層結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互聯網時代經濟活動的基礎結構不再是公有制了。土地、交通、電力等基礎設施主要是工業時代的基礎結構,而平台經濟是互聯網時代最重要的經濟命脈,構成了其他經濟活動的基礎設施與共用的生產資料,平台經濟是由私人資本絕對掌控的。互聯網平台的用户規模、經濟體量都達到了宏觀經濟的規模。
例如,2019年,線上綜合購物平台天貓“雙十一”一天的成交額為2684億元,超過了海南省一年的消費品零售總額(2018年為1717億元)。這種類型的互聯網企業已經不能用傳統的大型企業加以看待,而是具有“準公地”特徵。
同時,互聯網平台具有其他經濟活動基礎設施的自然壟斷、外部性以及以平台租為收益的特徵。
互聯網企業前期大量“燒錢”,就是為了搭建平台。互聯網平台傾向於自然壟斷,是由於它的價值取決於使用者的數量,平台的用户規模越大,平台的價值越大。

競爭對手之間一定會不斷壓低價格來吸引更多的使用者,導致平台前期不但完全免費,還給用户大量的補貼,而小企業根本“燒不起錢”,最終佔據市場的是少數巨頭,它們發現聯合比競爭更有利,會進一步推進市場壟斷。
這和地方政府通過“三通一平”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然後再招商引資的方式是一致的,但是規模要大得多。平台和基礎設施一樣投資週期長,前期投入大。
二者的不同之處在於:基礎設施具有外部性,所以只有給企業壟斷經營權的時候,企業才願意投資;而平台的收益是外部性的內部化,企業前期“燒錢”,後期如果成功站穩腳跟,幾乎會一勞永逸,能夠獲得巨大的回報。
平台收入並非傳統企業的利潤,而是平台租與平台税。平台租是壟斷租金,是用户使用平台進行經營、交易活動付給互聯網平台的租金,由於平台是自然壟斷的,這種租金也是壟斷租金。
由於法律框架和強制性機構執行的市場交易保障機制,被技術手段所替代,平台的收益還包括平台税,這也使它的利潤率遠高於傳統企業。
(二)中層分化:貧富分化與階層對立激化
如同隕石要受到地心引力作用的影響,社會分化趨勢也受到私人資本的“地心引力”,在一個螺旋運動中日趨嚴重。
我國已經是一個收入差距很大的國家。我國居民收入基尼係數,長期超過國際警戒線,2008年最高達到0.491,隨後有所下降,到2019年降到0.465,但這主要是地區差距和城鄉收入差距縮小造成的,資本和勞動差距擴大的結構性矛盾並未改變。
根據《2021年胡潤全球富豪榜》,中國身家超10億美元的富豪有1058位,比美國多696位,居世界第一。考慮到我國GDP按照匯率計算仍然只相當於美國的70%左右,這一數據是很令人驚訝的。
與此同時,我國還有“6億人每個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1]。初次分配中的勞動報酬佔GDP比重下降的趨勢並未得到根本遏制。研究表明中國的勞動者報酬比重比美國低十幾個百分點,比德國、日本也都低好幾個百分點。[2]
更嚴峻的不是收入差距問題,而是財富差距問題。資本與經濟虛擬化、新技術、全球化的結合空前放大了財富差距。
21世紀以來,全球都經歷了金融深化過程,金融資產總量與GDP的比率,以及全球外匯交易量與全球貿易量的比率不斷提高。與全球虛擬經濟的海量交易活動相比,實體經濟規模壓根就不在一個數量級上,大量羣體就是靠收割金融財富積累了巨大財富。
過去幾十年,中國城市房產等資產快速升值,而窮人非現金資產很少,難以分享資產升值收益,富人則集聚了大量財富,使社會財富差距快速拉大。
隨着技術進步,經濟形態也發生了鉅變,從工業、大工業到平台經濟、注意力經濟、智能經濟,使財富向市場競爭頭部贏家集中的速度越來越快,規模越來越大。互聯網平台在短短几年間集聚的財富,超過傳統企業上百年積累的財富。
隨着貧富差距拉大,人們的生存空間被擠壓、上升通道收窄。年輕人對於“努力工作就能成功”的説法越來越不認同。精英階層一句不經意的“當我們忙着做各種青年策劃時,青年們正在睡覺”都會引爆網絡輿情。
“996福報論”、強制加班等屢屢衝上熱搜,不斷遭遇網絡羣嘲。“打工人”“內卷”“躺平”等網絡新梗熱度不減,背後折射的正是不同羣體階層意識的撕裂。
智能時代的到來進一步加劇了階層的對立與衝突。資本主義社會初期,資本家手裏飛舞的鞭子,已經進化成一個看不見的系統。其中最大的悖論是勞動者自主性的空前解放與資本對於勞動的空前控制並行。以外賣騎手(網約配送員)為例:
一方面,騎手不在特定組織中生活,不受傳統科層制的紀律約束,上線就等於上班,下線就等於下班,工作時間高度自主(調查發現,時間靈活是吸引騎手的最重要原因,60.4%的騎手對此最看重)。[3]

冒雨送外賣的騎手,圖自新華網。
另一方面,這種自主性是以空前的缺乏勞動保護與精準控制為代價的。平台能夠通過大數據、算法和精細激勵體系對騎手進行精準控制與激勵,騎手們通過競爭來獲得更多的收入,最終都會演變成平台提高激勵門檻的“內卷競爭”,而任何“數字控制與騎手自主性的較量總會以數字控制獲勝而結束”[4]。
與傳統的階級對立是人與人對立不同,騎手面對的是一個數字系統,不但資本家是看不見的,連那些代表資本家進行壓榨的管理人員、體制、規章都隱身了,有的只是完全理性、“公正”、精確的技術。據推算,2019年,外賣騎手已經高達1300多萬人,[5]這已經是一個龐大的數字“打工人”羣體。
“被困在算法裏”是他們在智能時代的生存困境,也可能是整個“打工人”階層在智能時代共同的生存困境。
如果任由算法邏輯發展下去,未來社會也許會進一步撕裂。今天運用在外賣騎手身上的算法控制,從邏輯上完全可以用在各行各業。不論是公司白領、工廠藍領、教師還是公務員,這些“打工人”階層可能都還沒意識到,算法才是巔峯級別的關鍵績效指標(KPI)管理。
目前已經把“打工人”折磨得生無可戀的KPI還只是人工算法,而只有智能算法才能精細地衡量工作績效,才能精準地激勵個體,才能精確地實現組織目標。
(三)上層突破:資本對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的滲透
不論是資本的總規模,還是資產持有者數量,我國私營企業主階層都是龐大的。今日中國,經濟和社會意義上的私營企業主階層,還不能轉化為政治意義上的資產階級,或者用馬克思的術語説,中國的私營企業主階層還是自在的,而不是自為的[6]。但是體量龐大的資本日益表現出擺脱束縛、向上層建築滲透的需求。
資本就其本性而言,只有構建出與其相適應的上層建築,才能夠獲得自我確證。就其本質而言,黨員幹部的腐敗,就是社會上支配許多事物的資本邏輯向政治權力滲透的結果。
黨員幹部不是生活在真空裏,而是生活在商品交換的汪洋大海中,資本的那種難以抗拒的購買力量,可以説無所不在。在政治生活場域,他們能夠遵循政治邏輯,但一遇到現實生活問題,許多人往往接受資本邏輯的擺佈,因此出現了很多“兩面人”:人前是政治面孔,私下是商業面孔。
2013年,遼寧發生的新中國成立以來最為嚴重的全國人大代表賄選案,就是資本邏輯向政治體制滲透,衝擊、瓦解黨的執政底線的一個突出例子。
賄選案中的45名全國人大代表(2016年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宣佈其當選無效),大部分都是大大小小的私營企業主,如果任由這個邏輯演進下去,就變成誰有錢誰就能掌握政權。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旗幟鮮明地指出:“決不能把商品交換那一套搬到黨內政治生活和工作中來。”
參考文獻:
[1] 《“6億人月入1000元”,國家統計局首次解釋》,中國青年報客户端2020年6月15日。
[2] 參見李揚、張曉晶等:《中國國家資產負債表2020》,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20年版,第19頁。
[3] 參見美團研究院:《從數字生活到數字社會》,中國發展出版社2020年版,第69頁。
[4] 陳龍:《“數字控制”下的勞動秩序——外賣騎手的勞動控制研究》,《社會學研 究》2020年第6期。
[5] 參見美團研究院:《從數字生活到數字社會》,中國發展出版社2020年版,第68頁。
[6] 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指出,僅僅是大批工人的共同經濟地位和他們與資本家的共同利害關係,形成一個“自在階級”;只有在衝突中,為自己的利益並團結起來,才能成為一個有意識的“自為階級”。這裏用這個概念來解釋在社會主義國家中只是作為社會階層存在的私營企業主階層與完成其經濟、政治、意識形態和階級身份建構的資產階級之間的差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