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美國國內越亂,越要提防中美關係迅速惡化
【採訪/觀察者網 陶立烽】
美國國內越亂,我們越要提防中美關係的迅速惡化
觀察者網:鄭教授您好,感謝您接受觀網的採訪。第一個問題和您最近的新書《大變局中的機遇》有關。我們最高領導層在2017年提出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概念,那您覺得大變局現在具體體現在哪些方面?另外,現在的新冠疫情對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又有哪些影響?
**鄭永年:**這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如果是看中美關係的話,在奧巴馬後期已經開始了,到特朗普掌權的時候爆發出來,現在拜登時期還在延伸着。
對於這個大變局,我想很多人心裏還是沒有準備好。因為從80年代開始,從美國里根革命、英國撒切爾革命那時候開始了一波全球化,而且這一波全球化比以前的全球化的廣度、深度、力度都要強。哈佛教授、經濟學家達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把它稱為“超級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這波全球化持續了將近40年,所以大家的心理已經適應這波全球化了。對現在這一個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家還是心理準備不足,不管是中國人還是美國人。
撒切爾夫人與里根(圖自美國新聞網站“政客”)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影響我們的各個方面,從中美貿易開始,現在影響到中美的科技、經濟、人文、社會、國防、軍事、地緣政治方方面面。甚至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也受到了影響,比如我們前段時間東北缺電,再比如英國的油荒,這些都和大變局有關係。就是因為之前的超級全球化,現在已經變成有限全球化,甚至有人稱之為逆全球化。
我們如果不看大變局的話,很難理解身邊發生的一些事情,也很難理解國家地區之間的關係變化。因為中美關係的變化,我們和歐盟、日本、印度的關係都在變化,我們處理香港問題(的態度)在變化,兩岸關係在變化。
所以總體上看,我們對這一波變化還是沒有太深刻的理解。大家都是比較膚淺地看待中美關係,中美關係實際上在非常深刻的變化,中美從建交到現在,現在的中美關係,無論是G2G的關係(政府跟政府之間),還是P2P(人民跟人民之間的關係),都不如從前。你看看美國的民調調查,美國90%多的人都對中國有負面看法,你再看看80年代的時候,中國改革開放的時候,鄧小平7次登上美國《時代》雜誌。
新冠疫情是另外一個因素。即使沒有新冠疫情,中美關係也是會變。
對於這個大變局,我們最高領導2017年就有這個預判,因為他和奧巴馬有那麼長時間的談話和討論。作為兩國領袖,他們對中美關係心裏是有底的。只不過當時雙方領導人都還是比較理性的,但是當特朗普這一個局外人上來,他就把所有的矛盾都暴露出來了。
以前我們老是説“發展是硬道理”,發展過程中會有問題,但是問題需要在發展過程中來解決,如果不發展,所有的問題都是問題。實際上中美關係也一樣,大家在交往在發展,問題肯定會有,但還是可以得到解決,可現在交往很少,那麼這個問題就變得更嚴重。
有一點大家必須看到,中美關係實際上是美國內政的一個反映。國際關係其實很簡單,就是三句話: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戰爭是政治的另外一種形式;所有的政治都是地方政治。如果理解這些話,就能理解中美關係。
中美關係的背景是美國的內政延伸,因為全球化影響了美國的社會,美國的中產階級人數萎縮,從七八十年代的70%一直萎縮到現在的50%左右,這一情況反過來又影響中美關係。

2011年10月,示威者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和芝加哥聯儲銀行外聚集,響應“佔領華爾街”運動(圖自新華網)
中美關係能不能得到改善?當然兩國的交往、尤其是兩國的領袖交往很重要,但是從根本來説還是取決於美國內政,美國的經濟結構失衡能不能調整?美國的財富分配、收入分配能不能做得好?我們當然不喜歡特朗普,特朗普就只提倡“美國優先”,但是希望他們真正能做到“美國優先”,把美國的問題搞定。美國自己的問題搞定了,中美關係就有穩定的基礎,美國問題搞不定,中美關係會越來越壞。
最近美國的一個共和黨眾議員(麥迪遜·考特恩,Madison Cawthorn)説如果共和黨執政,就要沒收所有中國在美資產。這就是民粹主義崛起的反映。作為中國人一定要意識到,美國現在對華政策越來越具有法西斯主義色彩。如果拜登真的能穩定美國國內形勢,能穩定發展,對中美關係是好的。美國國內越亂,我們越要提防中美關係的迅速惡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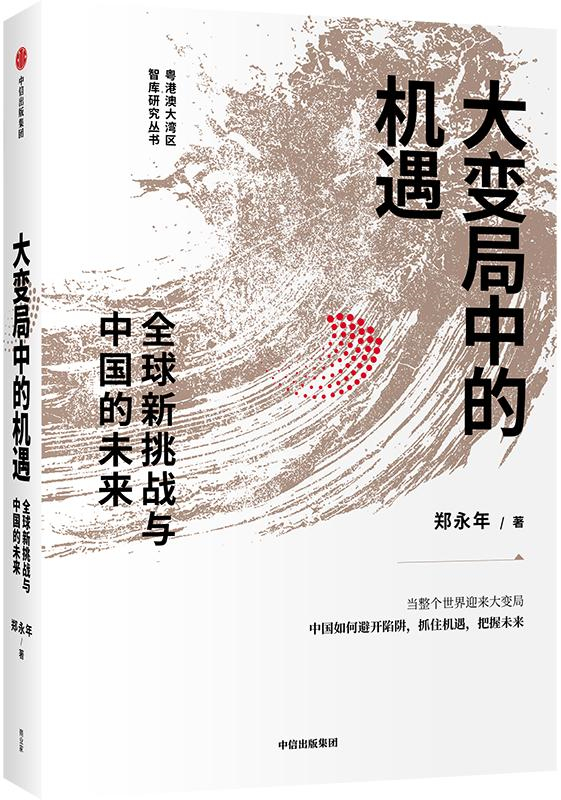
鄭永年新作《大變局中的機遇》,中信出版社粵港澳大灣區智庫研究叢書
中美確實有制度之爭,但不是民主/專制二元對立
觀察者網:所以在您看來,這次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它的根源是美國國內政治經濟情況的變化?大變局中是否存在中美製度競爭的因素?
**鄭永年:**拜登説中國跟美國是制度之爭,説什麼美國是“民主”的,中國是“專制”的。這當然這是錯誤的,但它確實是有制度的根源。
美國從上一波全球化裏賺了很多錢,但是利益沒有分配好,社會越來越分化。美國以前是一箇中產社會(middle class society),現在變成富豪社會(plutocracy)。80年代以來,在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主導下,美國太過於資本主導,政府對資本沒有任何的干預,完全變成以前的放任自由主義。所以造成了這樣一個結果。
而中國也深度參與了全球化,為什麼我們卻沒有發生像美國那種情況?就是因為政府跟市場之間的關係處理得好。
我們的經濟也是深度全球化,雖然收入差異也是蠻大的,尤其是跟改革開放以前比較起來,但是為什麼我們社會是穩定的?因為我們的中產階層在慢慢壯大,儘管比例還小;我們還通過扶貧,尤其是精準扶貧,過去40年使8億多人脱離絕對貧困。

記錄內地脱貧成就的香港TVB紀錄片《無窮之路》片段
所以對於政府和市場關係的處理,我們和美國不一樣。
美國的制度因為沒有能力處理和資本的關係,使得資本獨大。華爾街自己造成的危機,還要用普通納税人的錢來救。所以美國的民粹主義,從美國老百姓的角度來説也是容易理解的,資本出了那麼多的問題,你還來割韭菜?把中產割到了貧困。
所以中國政府現在做的就是要防止這些問題,比如最近的反壟斷,對一些過大的民營企業進行整頓,這些非常有預見性,我們不能重複美國走過的道路。
所以,“美國民主、中國專制”的二元對立是錯誤的,用政府和資本的關係,才能説得清楚什麼叫制度之爭。我們現在確實是制度之爭,但不是美國所定義的制度之爭。
如何實現共同富裕?上不封頂,保底,做大中產階層
觀察者網:説到貧富差距,現在我們國內也非常關注這一問題,尤其是宣佈全面小康之後就一直強調共同富裕,所以要實現共同富裕,您覺得有哪些比較可行的路徑?中央也提出的三次分配具體應該怎麼做?
**鄭永年:**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當今的世界基本上是三類國家。
絕大部分國家是第一類,還處於貧困狀態,低度發展或者説不發達。
我們過去40年使8億人脱貧,並且還在發展中,但世界上大部分國家仍然面臨貧困。非洲撒哈拉以南大部分國家還是很貧困,亞洲的很多經濟體中,經過亞洲97/98金融危機以後一直沒有從危機的影響中走出來,後來又受07/08金融危機的影響,還有拉丁美洲、東歐絕大部分國家,這是一大類。第二類國家,像美國英國,它發展了,但是貧富不均。第三類是共同富裕的經濟體,比如北歐那些小的福利社會,但這類少之又少。
所以我們在做的共同富裕,就是要解決一個世界性的問題。我們在擺脱絕對貧困問題上做得很出色,現在是時候解決共同富裕問題了。
現在大家都在講三次分配,但我個人覺得我們現在的爭論有點不正常。
我們現在説一次分配講效率,二次分配講公平,三次分配作為補充。很多人説這個説法是厲以寧先生提出來的,我想厲以寧先生也不至於提出這種説法,西方也沒有這個説法,實際上也不符合事實。對三次分配的認知非常重要,如果認知不清楚,永遠實現不了共同富裕。
我個人的觀點,一次分配一定要講效率,但一次分配如果不能做到基本公平的話,之後怎麼做也不能公平。一次分配就是就業。一個人要富裕,要生活,要可持續發展的話,首先要通過就業,如果不就業,無論福利再好,第三次分配救濟再多,你永遠是個窮光蛋,能活下來就不錯了。
所以我們為什麼強調勞動致富?勞動致富就是一次分配,你必須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而不能等國家或等待人家的救濟。為什麼那麼多國家把中小微企業放到頭等大事,就是因為就業問題。西方國家包括美國這樣典型的資本主義國家為什麼要反壟斷呢?就是為了讓中小型企業能發展起來,促進更多人的就業。
同樣,二次分配不能只講公平而不講發展和效率。如果二次分配光講公平,那就只有福利社會了,還怎麼理解凱恩斯主義這種促進經濟發展的財税政策?所以二次分配不僅要講公平,也要講發展,也要講效率。
那麼三次分配呢?我們現在社交媒體無限制地放大三次分配,這是錯的。我覺得要真正實現公平的話,就鼓勵人家去賺錢,賺得越多越好。賺來的錢你要回歸社會,進行三次分配。像美國歐洲都有一整套的制度來促成三次分配。
三次分配,不能説讓阿里巴巴出幾千億,騰訊出幾千億,這好像搶東西了,使得企業家有害怕心理。你得有一套好的制度規則,使得他們有動機為社會做好事情,我所在的港中大(深圳)好多樓都是香港人捐贈的,然後掛一個名,這也挺好。
那用什麼方法實現共同富裕,我認為有三點:
首先,上不封頂。要鼓勵人家去賺錢,賺得越多越好,但是要他們迴歸社會,必須有一套制度性的東西,而不是“運動式”地叫人家去捐款。
第二,保底。社會底層要保護起來,就要把養老、醫療、教育、公共住房的底線兜住,它不僅是保護社會底層,還是保護中產階級的基礎。我們比較一下德國跟美國,德國和美國都有民粹主義因素,都有極右極左,為什麼德國沒有像美國那樣的“華爾街運動”?就是因為德國的社會保障,就是保底保得好。
我感覺中國的中產階層有點像美國了。房子那麼貴,買了房子成為房奴了,小孩要上學了就成了孩奴,家人如果生一個大病,説不定要傾家蕩產。
我們現在正在做社會保底,這個方向是對的,比如提出“房住不炒”,這是非常正確的。所以我這本書裏也提出了軟基建,軟基建就是這些社會制度建設。
第三,做大做強中產。中產階層不是通過分配形成的,中產還是通過發展促成的。中國的中產現在是4億,比例還是低,只佔30%左右。所以十四五也把做大做強中產階級提出來了。
我們讓8億人口脱貧,成就很大,下一步一方面還要防止這些人返貧,另外在脱離絕對貧困的基礎上,如何使這些人跨入到中產階層,這是我們所要做的。如果我們有六七億的中產,我們會有多強大啊?
中產階層是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基礎,我們一直説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三駕馬車,出口、投資、消費。出口的話,當然我們會繼續出口,但要拉動那麼大的經濟體,至少不會像90年代那樣大比例。投資方面,我們高鐵也有了,高速公路也有了,港口航空港都建設得差不多了,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樣投資。
現在就需要刺激消費。在任何社會,富人階層永遠是過度消費,窮人階層永遠是消費不足的,所以消費社會就是中產社會,我們真的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內需社會也要求我們把中產做大。所以要實現共同富裕,就是這三個層面,上不封頂,保底,做大中產階層。
中美之間的競爭要看誰比誰更開放
觀察者網:您在書中也提到了,美國不管誰當政,中國在這方面不能有任何幻想。我們現在也講要“丟掉幻想,準備鬥爭”, 中國在和美國的鬥爭中,該遵循什麼樣的原則、以什麼樣的態度,使兩國關係處於“鬥而不破”的狀態?
**鄭永年:**我覺得還是一句話,就是中國人説的“義”和“利”。
特朗普追求利益能理解,但是你要有“義”,這個“義”是對你自己的也是對對方的。
所以我覺得要理性,特朗普追求美國利益,不顧一切搞全面脱鈎,結果傷人一千自損八百。生產鏈、供應鏈是經濟規律,不是政治可以左右的。
從特朗普到拜登,他們是想再工業化,要把生產線拉回美國,拉得回去嗎?拉不回去。他們不讓中國人賺錢,希望轉移到越南那些東南亞國家,但是你看看轉移得出去嗎?因為利益是掛鈎的,全球化狀態下已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像政治人物所設想的那麼簡單。所以説要有理性。
對中國也是一樣,我覺得我們的領導層還是非常理性的。之前特朗普一直搞脱鈎退羣,但中國還是在強調全球化,繼續推進全球化。我們這幾年跟東盟確定了RCEP,和歐洲確定了中歐投資協議,儘管現在碰到一些困難,但簽署就表明了是我們的意志、我們的方向,我們是互利的,另外我們現在也提出了要加入CPTPP。

2020年11月15日,15國簽署RCEP(圖自新華網)
我提出過一個“單邊開放”概念,很多人批評我,但是實際上中國正在進行單邊開放,當美國把中國企業趕走的時候,中國不僅沒有對等地把美國企業從中國領土上趕走,還鼓勵他們來。
中美之間的競爭並不是看誰更封閉,而是要看誰更開放,最後的贏家就是更開放的國家。幾千年的歷史都可以證明這一點。
觀察者網:您曾提醒過中國要避免陷入“明朝陷阱”,無論內外遇到多大的困難,也要堅持改革開放,不要讓發展的道路中斷。未來阻斷中國改革開放的因素,可能會有哪些?中國的政治制度是否具有這樣的韌性,來有效應對開放過程中出現的意外?
**鄭永年:**我覺得中國的現代化如果要再次被中斷,就是封閉。明朝在鄭和下西洋以後就閉關鎖國了,不過因為國家大,它可以通過內循環來支撐很長時間,但最後也衰落了,因為和人家脱鈎了,不知道外面世界怎麼發展的。
中國未來能不能成為真正的大國,就看能不能繼續開放。在開放後肯定會有改革的,至少不會落後。倒不是説某一種技術肯定是中國先發明,但別人有一些創造我們是能夠知道的。開放政策下,我們也通過不同的東西制度競爭,產生新的制度。開放是可以強國的。
但開放並不是説毫無原則的開放,很多地方都是對等開放,RCEP是對等的,中歐協定的也是對等的。但是有些符合我們國家利益的地方,美國歐洲越封閉我們就要越開放。
規則就是生產力
觀察者網:之前我們開放可能要向外面換資金、換技術,您在書中也提到了,第三次開放可能要用這個市場來換規則,您覺得在國際競爭中規則的制定權有多重要?
**鄭永年:**我一直強調,規則就是生產力,規則太重要了。
聯合國、WTO、WHO其實都是規則。這幾年美國歐洲罵我們的,其實都是規則問題。美國説我們沒遵守WTO規則、WHO規則,沒遵守海上航行自由等等。
為什麼説用市場換規則?我舉一個例子,歐洲有大的互聯網公司嗎?沒有,都在中國和美國。但他們有規則,歐洲人善於把市場轉換成規則。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單一市場,但我們的互聯網一點規則都沒有,我們出了門要麼是美國規則,要麼是歐盟規則,我們的規則只能在國內自己玩玩。所以説我們的互聯網公司之間的關係都像土豆,都是一個個封閉起來的,互不相關,互不排斥,就是量巨大而沒有規則,所以我們大而不強。汽車也是這樣的例子。
我們之後要高質量發展,高質量發展技術創新是很重要,但是我們規則講得太少,我們勤勞而不致富,歐洲人懶惰而致富,其中一條就是規則,要用腦袋賺錢,那就用規則,我們是用雙手雙腳賺錢的,很辛苦,我也希望我們的老百姓“懶惰”一點,但是能富裕起來。
觀察者網:您一直強調中國在這個過程中要掌握規則制定權和話語權。但美國也不會輕易放棄已經掌握的對國際秩序的主導權,那麼在這個過程中如何尋找到一條“共贏”之路?還是説只能是東風壓倒西風,或者西風壓倒東風?
**鄭永年:**我覺得不會的。當然了,中美之間競爭不可避免,下一步中美之爭也是規則之爭。
但中國不能學美國那套。美國是把自己的規則假裝成普世規則強加到人家身上,尤其是一些政治規則上。
中國不會那樣。中國的改革是在開放下推動的,80年代我們把外資請進來後,主要是遵循外資的規則,90年代我們加入WTO,和世界接軌,所謂接軌,就是修改我們的法律法規政策體系來符合國際規範,所以我們的規則好多就是世界的規則。現在我們對世界規則通過接軌,做一點補充。比如我們的一帶一路、金磚、亞投行,但這些也不是中國一方的,而是大家倡議式的,就是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國是一個包容性的文明,而不是排他性的文明。
當然,競爭不排斥合作,沒有競爭哪有合作。
現在中國有一點主動的,中國有了“一帶一路”,歐美也紛紛提出他們的“一帶一路”,但這是好事情。選擇多了,大家就比誰做得好,這就是規則之爭。我們就不怕,為什麼?假如西方還是用以前的那種用意識形態的,有很多附加條件的方法來搞他們的“一帶一路”,那他們就根本搞不通。二戰以後歐美國家就是這樣的,對非洲對拉美國家投資,都要附加上所謂的多黨制、民主自由,那些所謂的西方價值觀,有一個成功過嗎?沒有。中國是不干預政策,追求共同發展,其實還有很多當地國家讚賞我們這種方式,沒附加條件,這有什麼不好的。

2019年4月27日,第二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在北京雁棲湖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圓桌峯會,共40個國家和國際組織的領導人出席
觀察者網:您提出過一箇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模式,它優於西方政經制度安排的地方在哪裏?與西方給中國貼上的“國家資本主義”標籤有何不同?
**鄭永年:**當然不一樣了。首先我們講事實,不要講意識形態,要説西方是國家資本主義,但你去看我們的國有企業,你去看國有資本有多少?
劉鶴副總理在之前講中國的民營企業,提出56789:中國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90%以上的就是市場主體。怎麼能説是國家資本主義?但同時中國也不是英美這種資本私人的經濟體,中國也有國有資本,所以我説中國是一個非常理想的混合經濟。我寫了一本書叫《制內市場》,中國幾千年都是三層資本,三層市場,有國有資本、民營資本,還有中間國有資本跟民營資本互動的領域。
以前亞里士多德説古希臘政體,民主也不好,專制也不好,混合政體最好。實際經濟上也是這樣,以前計劃經濟不靈,華爾街主導的模式也不好,現在這樣的混合資本最好。中國過去40年經歷了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最近幾年在經歷新冠危機,就應對得比較順利,馬上從危機中走出來了,尤其是8億人口脱貧,西方都很難想象,這就是靠政府跟市場兩條腿走路的力量,比起西方這一條腿走路的,我們兩條腿走路就非常穩了,穩了才能走得遠。
當然西方自身實際上也在變化,從80年代到現在他們一直主張新自由主義,但這次新冠疫情以後,拜登又有點走向凱恩斯主義,他們自己也在變化。西方一直在研究資本主義的變種。英美完全是新自由主義;德國叫社會市場;我們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際上和德國的模式有點類似。所以這些東西不是互相攻擊就能理解,西方現在主要是理解不了我們。
當然現在的經濟學家都是西方培養出的經濟學家,都是西方的教科書,我們還沒有能解釋中國經濟的教科書。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