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揚:文明問題是個歷史問題還是現實問題?
按:最近,中國出版界的百年老店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文揚的最新力作《文明的邏輯——中西文明的博弈與未來》。這是繼2017年世紀文景出版的《人民共和國》和2019年底中華書局出版的《天下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之後,作者圍繞中國獨特性和中華文明獨特性展開的系列論述的一個最新努力成果。
《文明的邏輯》一書從“文明問題作為一箇中國問題”這樣一個去西方中心立場的問題意識談起,希望通過出版該書將這個議題推向中國思想界。在新書發行之際,觀察者網專訪本書作者、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文揚,與讀者們分享他的心得和感想。
專訪分上下篇,本文為上篇。下篇我們將發在觀察員,歡迎大家點擊查看更多精彩內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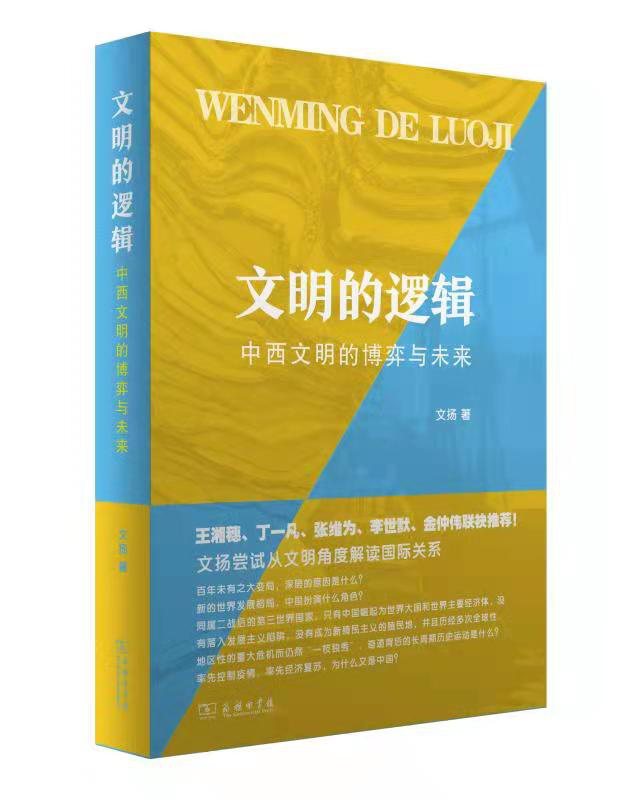
《文明的邏輯》,文揚著,商務印書館
觀察者網:近些年來,您發表了很多篇關於文明問題的文章,又在兩年時間裏連續寫出了《天下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一書和現在的這本《文明的邏輯——中西文明的博弈與未來》,合計共有50多萬字。去年下半年觀察者網還推出了您主講的《文揚論文明》40集音頻課。您為什麼如此關注文明問題?文明問題在您看來到底是個歷史問題還是現實問題?
**文揚:**文明這個概念本身就是一個同時包含了空間和時間兩個維度的概念,比如説提到“中華文明”,必然是既在空間上指一個幾乎覆蓋了整個歐亞東部地區的巨大社會,又在時間上指在這個社會里發生的一個歷經了數千年綿延不絕的歷史演變過程,就是人們常説的中華文明5000年。因此文明這個概念不能在歷史和現實之間進行簡單的劃分,而研究文明問題其實就是研究這個巨大的時空體,並通過深入解讀歷史更深刻地理解現實並預測未來。
打個比方,若將人類歷史比作一條奔流的大河,今天的人們看到在河面上有各種不同的運動,如浪花的起落、漂浮物的流動,還有眾多行駛的船舶;這些河面上的運動當然各有其當下的運動原因和規律,但並不是問題的全部,它們在當下的每一個運動,無不同時受到整個河流巨大的水體在給定的地勢環境下發生的整體運動的支配。在我看來,研究文明問題,就好比是研究河流水體的整體運動,包括水體的起源和擴大、水體的流速和流量變化、與其他河流水體之間的匯合或分流等等綜合問題,然後將研究結論作為理論基礎應用於分析現實問題,對當下河面上的各種運動現象給出更好的、更深刻和全面的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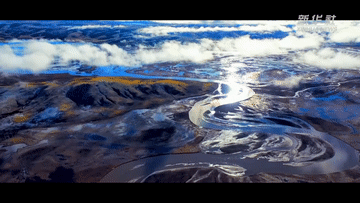
將文明理論應用於國際關係問題研究,作為一個學術傳統,在國際上早已有之。當代最為著名的,是美國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提出的“文明衝突論”,就是將整個世界劃分為不同文明的勢力範圍,用世界上“七八個不同文明”的劃分取代冷戰時期的“三個集團”或“三個世界”的劃分,通過研究這些文明之間的互動關係解釋現實中的國際熱點事件。
亨廷頓的這項研究,就很像是上面的那個比喻。冷戰結束後,按照意識形態劃分世界的分析方法不再適用,就像是河面上原本頗有規律的各種運動開始顯得雜亂無章,不再有統一的解釋框架。於是亨廷頓提醒人們,還是要關注深層的水體運動,因為這種運動才是更為持久和穩定的,更具有決定性的,也是更可以預測的,據此可以在複雜多變的河面運動中發現新的規律。
費爾南·布羅代爾給文明一詞下的定義之一是:“經過一系列經濟、一系列社會,仍堅持生存下來,同時幾乎只是一點一滴地才改變方向者,就是文明。”即是説,經濟和社會都是一個接着一個頻繁變遷的,國家和民族也都會在兼併融合過程中消失,只有文明,才是一種持久和穩定的存在。
這就意味着,應用文明理論解釋世界的重大變局,與其説是一種另類,一種區別於以主權國家或國家集團為基本單位的國際關係常規研究路徑的非常規研究路徑,毋寧説是一種每當世界局勢發生鉅變、當時流行的國際關係理論難以適用時,就會再次召喚人們重新關注的一種更為普遍化的研究路徑,一種以持久和穩定的文明勢力範圍為基本單位的研究路徑。
在我看來,當前這個以中國快速崛起、美西方快速衰落、國際政治和經濟格局快速重組為主要特徵的世界局勢,又是一次歷史性的時代鉅變。伴隨着當前現實的急劇改變,那些似是而非、牽強附會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理論正在成批地被淘汰;於是,與30年前冷戰結束後“文明衝突論”應運而生的情況類似,新一輪的文明理論研究又要復興了。
我在三年前開始發表關於文明問題的系列文章,實際上也是在時代浪潮的衝擊下應運而生的產物。最近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發表文章説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過時了,現在到了用“共同發展”與“全球性的正義”來代替的時候了。在我看來,他其實並沒有完全明白文明問題的含義,也沒有讀懂文明理論在關注什麼,而且犯了用“應然”代替“實然”的錯誤。可以説,由於人類歷史異常複雜和厚重,文明理論將處於永無止境的上下求索過程中,並不存在過時不過時的問題。
觀察者網:在《文明的邏輯》這本新書中,您開篇便提出了“文明問題作為一箇中國問題”這個命題,為什麼提出這個命題?該命題的確切含義是什麼?提出該命題的現實意義是什麼?
**文揚:**首先要建立一個基本的認知,即當今世界到底存在幾個可以分辨的文明?或者説整個世界可以劃分為幾個不同文明的勢力範圍?亨廷頓在他1996年出版《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這本書時,提出了一個説法,叫“七八個主要文明”,這個説法是怎麼來的呢?
按照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的研究,整個人類文明史上共出現過21個文明。第一代的文明社會有六個,即古代埃及、蘇美爾、米諾斯、瑪雅、安第斯、古代中國社會。以第一代中斷的文明為母體,先後出現了赫梯、敍利亞、巴比倫、希臘、伊朗、阿拉伯、印度、尤卡坦、墨西哥等十幾個第二代文明。以第二代中斷的文明為母體,又先後形成了五個第三代文明,即現存的中華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東正教文明和西方文明[ 〔英〕阿諾德·湯因比著,〔英〕D·C·薩默維爾編,郭小凌等譯:《歷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所以,如果湯因比仍然在世,他不會説“七八個主要文明”,只會堅定地認為只有五個。

阿諾德·湯因比(資料圖)
按美國歷史學家卡羅爾·奎格利的劃分,存世的文明也是五個。他在1961年《文明的演變:歷史分析導論》中認為,歷史上大的文明先後出現過16個:在西方,從克里特文明產生了古典文明,而後者又產生東正教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三大文明,這一點與湯因比的觀點一樣;但是在東方,他認為從華夏文明中產生出了中華文明和日本文明。他沒有將印度文明視為一個單獨的文明。另一位美國歷史學家馬修·梅爾科(Matthew Melko)也認為日本文明是一個單獨的文明,而不認為東正教文明是一個單獨的文明;他在1969年的《文明的本質》一書中總共列舉了12種文明,其中有7種是已消失的文明,即美索不達米亞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古希臘羅馬文明、拜占庭文明、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其中五種延續至今,即中華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和西方文明。
拉脱維亞裔美國政治學家阿達·博茲曼(Adda B Bozeman)的觀點與湯因比類似,她認為在進入現代世界之前,只有五種文明: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中國文明、拜占庭文明和伊斯蘭文明;在這個分法中,沒有了單獨的日本文明,並用拜占庭文明取代了湯因比所説的東正教文明。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一些分法,例如以色列社會學傢什穆埃爾·艾森施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認為猶太文明單獨構成一個文明,所以應該是六種主要文明[ (英)尼爾·弗格森著,曾賢明、唐穎華譯:《文明》,中信出版社2012年]。
由此可見,“七八個主要文明”,是關於目前存世的文明數量的籠統説法,在普遍公認的五個主要文明之外,又將日本文化和猶太文化可否被視為不同文明以及非洲文化可否單獨構成一個文明的問題含糊地包括了進來。
確定了歷史上出現過的所有文明以及當今存世的幾大文明之後,人們就會發現一個問題,即中華文明的獨一無二之處。在《文明的邏輯》這本書中,我是這樣歸納的:
第一,無論研究哪個時期或哪一代的人類文明,中華文明必定是其中之一;第二,無論把同一時期的文明分成哪幾個,中華文明必定是其中之一;第三,無論在歷史上總 計分辨出哪些出現過的文明,中華文明必定是其中之一。而且,中華文明是唯一具有這個“永在性”的文明,其他文明都不是。其他文明要麼早早中斷了,例如古埃及、古蘇美爾、古希臘羅馬等;要麼只在較晚的時期才出現,例如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等;要麼難以確認是否可以單獨列為一個文明,例如日本文明、猶太文明等,甚至包括印度文明。
觀察者網:這個命題對於流行的以西方文明為中心的文明論是不是一個顛覆呢?
文揚:“文明問題作為一箇中國問題”這個命題,首先就是建立在中華文明這個獨一無二的“永在性”之上的。眾所周知,由於西方輿論界對西方文明的大力渲染,“文明問題作為一個西方問題”曾長期以來被當作不言自明之理,一些以“文明史”或“文明”冠名的著作甚至只涉及西方某一時期的歷史故事及各項文明成就,其他則視而不見或隻字不提。例如1962年英國國家美術館主理、作家肯尼斯·克拉克撰寫的《文明》一書,內容講的是自羅馬帝國滅亡以來,歐洲在繪畫、雕刻、建築、文學和音樂等藝術形式上的發展,用作者自己的話説,就是“以黑暗時代至今的西歐人民的生活變遷為插圖實證對文明本質的闡釋”。此書以及於1969 年改編的 BBC同名彩色紀錄片,書名和片名都是 Civilization,名詞單數,後面沒有s,其含義就是:説到文明,不過就是這些內容了——在視覺形象上,就是盧瓦爾河城堡、佛羅倫薩的宮殿、西斯廷教堂、凡爾賽,其主人翁就是米開朗琪羅、達·芬奇、丟勒、特納和德拉克洛瓦。整個敍事裏沒有歐洲、北美以外的文明,也沒有基督教以前的文明。言外之意就是,除了他所展示出來的這些東西,其他都是化外之物。
在今天的世界,這種西方式的傲慢已經不被人接受了,隨着越來越多的考古成果,以及古DNA技術對於早期人類遷徙和分佈狀況的揭示,人類文明史的整體面貌慢慢浮現了出來。與那些真正決定了人類文明演變進程、影響了演變方向的重大事件相比,個別地區在個別時期的個別藝術成就,並沒有多大的重要性和代表性。美國歷史學家威爾·杜蘭特關於人類文明有過一個説法:“文明是增進文化創造的社會秩序。它包含了四大因素:經濟的供應、政治的組織、倫理的傳統及對知識與藝術的追求。”[ 威爾·杜蘭特,阿里爾·杜蘭特著,台灣幼獅文化譯《文明的故事》(全11卷),天地出版社2018年10月]按照這個定義,文明在知識和藝術方面的表現只是文明問題的多個側面之一。2018 年 BBC又製作了《文明》系列片新版,時間敍事變成了主題敍事,涉及六個大洲31個國家,原名 Civilization 加上了 s,成了複數形式,展示的內容改為了“文明們”。但這也只是在原來完全偏狹的立場上進行了一定程度的去西方中心的努力,仍然不是對文明問題的一個正確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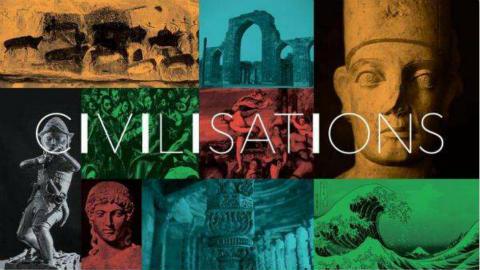
BBC紀錄片《文明》(資料圖)
當然,“文明問題作為一箇中國問題”並不是作為“文明問題作為一個西方問題”這個預設立場的反命題提出來的。從根本上説,這個命題是基於對於人類文明歷史的更為完整的認識和理解而提出來的。既然已經認識到,中華文明無論在歷史上所有出現過的文明的比較中,還是在當今存世的各主要文明的比較中,都具有不可忽視的獨特性;既然已經理解到,歷經數千年未曾中斷的中華文明必定藴含了某種對於人類文明至關重要的要素;那麼,以中華文明為主要研究對象來分析文明問題,甚或以中華文明的連續性為基準來分析其它各文明中斷和覆滅的原因,就是理所當然的。
圍繞中華文明的連續性而展開的問題,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系列,其中包括:中華文明保持連續性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其他原生文明未能延續下來的主要原因是什麼?如果其他幾大原生文明都無一例外亡於蠻族入侵,為什麼中華文明能夠在歷次蠻族入侵的衝擊下生存下來?在蠻族文化屢屢被中華文明反向同化的情況下,文明的維新是如何發生的?在中華文明之外,第一代原生文明先後亡於蠻族入侵之後,第二代文明又是如何重新誕生的?毀滅了原生文明的蠻族,自身又是如何創造出新文明的?蠻族社會創造出的新文明在近代與中華文明相遇後,又導致了什麼結果?等等。
在我看來,所有上述問題都需要以“文明問題作為一箇中國問題”這個命題為中心展開,而沿着西方中心論的文明研究路徑則不可能展開這些問題,因為正如我在《文明的邏輯》一書中論述的,西方文明正是作為蠻族所創造的新文明而問世的,其起源也正是古代文明的毀滅者。在我看來,圍繞中華文明的連續性而展開的問題由於涉及文明存續和滅亡的關鍵因素,所以才是文明研究領域內的核心問題,而那些以歐洲文藝復興之後的藝術發展為主線所展開的文明圖景,雖然賞心悦目,也精彩紛呈,但卻不是文明問題的核心和關鍵,只能作為人類文明的一個局部和側面。這就是我提出“文明問題作為一箇中國問題”這個命題的主要原因。
定居與遊居之劃分的意義何在?
觀察者網:《天下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一書出版之後,引起了一些討論,特別是關於定居與遊居、秩序主義與運動主義這幾個概念,有些讀者感到不太好理解。例如用定居農耕來為中華文明的特性做概括,似乎意味着其他幾大文明都不適用這個概念,那麼就應該歸為遊居文明,這個劃分或多或少與人們的一般認知有差異。因為根據人們從歷史讀物上的瞭解,在古代的地中海世界和古代印度都很早就有了定居城市和農耕村落,即使是西歐,中世紀以後也似乎都是定居的,特別是當代世界,全球各地的不同社會都是定居社會,如何理解其他文明大都是遊居文明這個理論概括呢?
**文揚:**2019年我在觀察者網上發表了“70年對話5000年”系列文章,那時就首次提出定居文明與遊居文明這個二分法,並將遊居文明又分為了遊牧、遊獵、遊商、遊盜幾種類型,後來又在《天下中華》和今年這本《文明的邏輯》兩本書和《文揚論文明》音頻課中進行了詳細闡釋。但是對於很多讀者,初次接觸這個二分法還是會有一些不理解。
首先需要説明的是,當使用“定居”和“遊居”來對不同文明進行概括,指的是這些文明在整個文明史的尺度上看的一個總的性質。舉個例子,比如概括兩個人的不同人生,説一個人是“流浪者”的一生,另一個人是“坐地户”的一生,意思就是前者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四處流浪,後者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未離開過本地;而這兩個概括,對於前者並不排除他在大部分流浪時間的間隔期也會長住在一個地方一段時間,對於後者也不排除他在待在家鄉的大部分時間的間隔期也會出去四處走一走。但是如果從兩個人各自完整一生的對比來看,“流浪者”的一生與“坐地户”的一生就是截然不同的兩種人生,兩個人的人生經驗和感悟,各自的性格、氣質、舉止甚至相貌,都會有顯著差別。若“流浪者”的流浪生涯主要是打家劫舍、殺人越貨、霸佔他人家園,那就更是如此了。
將中華文明概括為定居文明,將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概括為遊居文明,指的就是各自在其完整的文明歷史上的一個總的狀態。在中華文明方面,從5000年的尺度上和這個文明的主體部分來看,都是連續定居在以中原地區為中心的一個近乎圓形的地理範圍內的。而今天所説的西方文明則完全不同,這個文明實際上是在舊文明的廢墟上重新滋生出來的一個第三代文明,而它的起源、生長和壯大無不伴隨着整個社會的大規模遷徙和入侵,所對應的重大歷史事件分別就是公元5世紀前後的蠻族入侵羅馬帝國、11-13世紀的“十字軍東侵”和15世紀之後的大航海和新世界大殖民。在這個文明從誕生至今的整個文明歷史上,這三次大遷徙就是它的主線,被利奧波德·蘭克概括為“三次深呼吸”,這也是它區別於中華文明從來沒有整體上離開過原居地這個定居歷史的最顯著之處。就像是兩個不同的人生一樣,前者自出生到青年到壯年,每個階段都在四處遷徙和入侵,後者則一生中沒有離開過原居地,到了兩人相遇時,必然是處處不一樣,相互視為非我族類。

十字軍東侵(資料圖)
東正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也都與此類似。東正教文明與西方文明同屬從古希臘-古羅馬文明廢墟中滋生出的新一代文明,後者在地理上轉向西北部,前者則轉向了東北部;自公元7世紀伊斯蘭文明崛起之後,在這個新興文明的擠壓之下,東正教文明向北擴展到了東歐、俄羅斯和西伯利亞,而這個地區自古以來就是眾多草原遊居民族錯居雜處、相互殺戮的野蠻世界。在從16世紀開始的4個世紀中,通過這個文明中最強有力的俄羅斯人對此前幾個世紀裏韃靼人領土擴張的反攻,俄羅斯的疆域以平均每日增加130平方公里或者每年一個愛沙尼亞國土的速度向外擴張,最終佔據了2200多萬平方公里的廣闊土地。在這個擴張過程中,整個社會也是有很大一部分人口長期處於不斷遷徙的遊居狀態。伊斯蘭文明同樣是在一場民族大遷徙過程中誕生的,這個文明公元7世紀從阿拉伯半島起源,隨後伴隨着一股向東方和北方的移民浪潮而迅速興起,其遷徙規模堪比公元5世紀日耳曼蠻族入侵羅馬各省。此後歷經倭馬亞王朝、阿巴斯王朝、塞爾柱帝國直到奧斯曼帝國的多次大規模擴張,把伊斯蘭社會版圖伸展到了覆蓋北非、西亞、南亞和中亞的一個廣闊地區。在這個地區內,連接歐亞非三大洲的商路四通八達,包括航海活動在內的遠程貿易、宗教活動和軍事遠征是常態;由於整個社會以廣泛的奴隸制為基礎,而穆斯林人羣則懷抱着“遷徙圓滿”“不再返回”的信條,加之在廣闊的沙漠地區缺乏轉入定居社會的自然條件,很大一部分人口同樣也長期處於不固定在家園土地上的遊居狀態。
即使是印度文明也與中華文明有根本差別,由於其社會長期四分五裂,頻頻遭受外族入侵,缺少較長時間的統一和連續的大一統建設,所以儘管存在很大的定居社會,但也不具有類似於中華社會這種定居文明的特點,即連續的、大規模的、多元一體的定居農耕生產生活方式和社會構成。
所以可以説,除了中華文明,佔據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區的其他幾大文明都不是在連續的、大規模的定居農耕歷史中形成的,都在文明出現之後的很長時期內仍然延續着史前人類遊居採獵生產生活方式;從中國人的角度看,都是不同蠻族各自歷史的繼續。因為關於蠻族的定義正是由最早發育出社會複雜性和成熟文字系統的定居社會給出的,從連續的定居農耕社會的角度看,居無定所、長期遷徙的遊居社會,無論是騎馬民族還是海上民族,都是蠻族。古代中國人將這類社會統稱為“行國”,屬於“夷狄”,區別於中國“華夏”這樣的“居國”。
觀察者網:有些讀者注意到,您使用的是“遊居”這個詞,而不是人們通常使用的“遊牧”這個詞,為什麼做了這樣一個區別呢?這個區別的意義是什麼呢?
**文揚:**關於定居文明與遊居文明這個劃分,其由來是這樣的:問題的起點在於Nomad這個英文詞。Nomad, Nomadism, Nomadic這些詞據説大約在明代就進入中國了,那時的中國人根據自己的歷史經驗,毫不猶豫地將它們翻譯為“遊牧”、“遊牧的”,此後一直未曾進行過修正。
現在看來,這個翻譯實際上干擾了中文讀者對人類文明歷史的正確認知,因為Nomad這個詞本來的定義是指所有“沒有固定居住地的人羣社團”,並不專指遊牧社會。在史前社會,所有的採獵者社會都是Nomadic,在定居社會出現之後,除了遊牧人羣,那些沿貿易路線遊走的馬匹商隊、駱駝商隊或船舶商隊,也都是Nomadic,甚至那些過着流浪生活的吉卜賽手藝人等,也用這個詞來描述,所以Nomad應該相對於漢語的“定居”翻譯為“遊居”。
在人類學和考古學意義上,定居(Sedentism或Sedentariness)一詞的定義,可以指一種狀態,即“在一個地方長時間羣體居住的生活方式”;也可指一個過程,即“從遊居社會向永久留在一個地方的生活方式的轉變過渡”。在英文裏,相關概念有Sedentary Settlements, Sedentarization, Fixed Habitat, Sedentary Lifestyle等。而Nomad這個詞就是與這個概念相對的那個概念。確切説,遊牧這種生產生活方式,僅是畜牧生活的一種形態,正如日本學者杉山正明所説的,“特別是指隨着牲口追逐水草生長的足跡而將整個家搬來搬去的形態”。
因此,遊居並不等同於遊牧,在英文中,與Nomadic概念相關的有Hunter-gatherers, Pastoral Nomads, Tinker, Trader Nomads等,遊牧社會只是遊居社會中的一種。根據這番考證,我就使用了“遊居”這個漢語詞與“定居”相對,作為對於不同文明特性的概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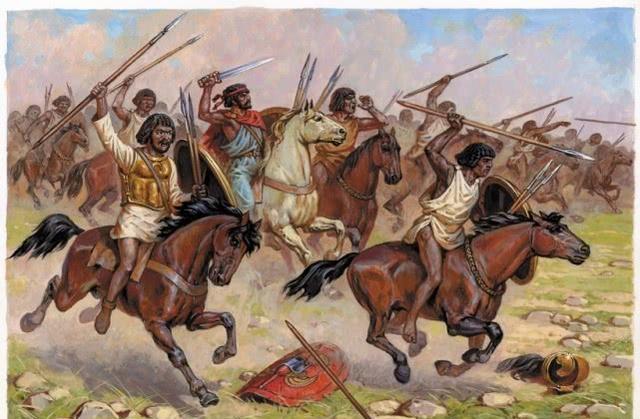
遊牧社會(資料圖)
從心理學上講,一個人對自身的認識往往是在與“他者”的對比過程中逐步深化的。文明之間的對比也是一樣,對於中華文明,只有把視野放開,充分理解其他文明的移動和遷徙性質,才能充分明白自身的定居性質。日本麗澤大學教授松元建一在2002年寫過一篇《解説——關於“定居”與“移動”》的文章,文中説,他是在北非撒哈拉沙漠旅行時突然發生“頓悟”的。
當時的他第一次意識到,在廣大的阿拉伯世界,非定居的四處遷徙生活形態才是一般的生活方式,而相比之下,日本人這個以“在一個地方努力”為通俗道德的民族,其實反而是一種特殊。於是他建議,在關於“何謂日本”的問題上,在還原為“島國”和“水稻”這兩個要素之外,應該再加上第三個要素“定居”[ (日)杉山正明著,黃美蓉譯《遊牧民的世界史》,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2014年1月,P264]。
他的這個認識過程,顯然也有助於中國人對於自身文明的深入理解,日本文化不過是中華文明的一個分支,如果用同樣的還原法歸納中華文明,去掉“島國”這個特性,不過也就是“農耕”和“定居”。
反過來,從阿拉伯世界的角度往外看也會得出它的“他者”觀察。被湯因比譽為“歷代最卓越的歷史學家、伊斯蘭教最偉大的歷史哲學家”的伊本·赫勒敦在他的名著《歷史緒論》中,也是用定居和遊居作為人類社會一個最基本的也是永恆的二元劃分。他將定居者稱為“城鎮人”,所有城鎮人都是沙漠這個“文明的蓄水池”養育出來的,是作為原始的遊居者社會的延續。在他看來,城鎮人離開了遊居社會後就因為生活舒適而變得腐敗,感染了壞品質,而沙漠中的遊居者則“比定居居民更好,因為他們更靠近最初的土地,更能遠離那些已經污染了定居居民心靈的邪惡習慣”[ (突尼斯)伊本·赫勒敦著,李振中譯《歷史緒論》,寧夏人民出版社2014年12月,P154]。
不僅阿拉伯人的世界觀是這樣,歐亞大草原上的人也是一樣,位於中國北方那些自黃帝以來即伴隨着中國歷史全過程的草原民族,在看待分佈在他們南方廣闊土地上的各民族時,眼中的“他者”們最大的特性是什麼呢?區別於他們自身的最大不同之處是什麼呢?不過也就是“農耕”和“定居”。
(未完待續,點擊查看下篇)
圖書鏈接:http://product.dangdang.com/29317638.html
https://item.jd.com/10039153698103.html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59561187986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