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德瑞:為何古代中國在制度上,有着驚人的穩定性?
【文/白德瑞】
在其主編的《官僚制與政治發展》(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一書的導論部分,政治學家約瑟夫•拉波蘭巴拉(Joseph LaPolambara)強調,最低層級的行政人員在塑造大眾對政府與國家的態度方面往往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他認為,不管那些處於行政官僚等級頂層的官員們是如何對各種價值觀,以及國家權威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有效影響加以描述,對社會大眾最直接的決定性影響,通常是由那些處於行政官僚等級最底層的行政人員所做出來的。
儘管拉波蘭巴拉的上述觀察主要針對的是社會大眾在感知國家政權正當性時那些行政工作人員給前者所造成的影響,但這一結論也同樣可以被用來描述各種行政機構與行政資源的可利用性及其在地方上的運用。
無論那些關於仁慈家長式統治與仁政的理念是如何被清朝的官員們加以鼓吹,並藉助宣講聖諭的活動而在帝國全境內傳播,對於絕大多數的皇帝子民而言,官府便意味着縣衙當中的那些書吏和差役。畢竟,縣衙的吏役們與當地社區的接觸最為直接,也最為頻繁。當地百姓只有在極少數的情況下才能見到知縣本人,而他們與知縣進行當面交流的機會更是少之又少。
從這個意義上講,帝國政府並非抽象美德的貯藏室與從高處向下輻射其影響力的道德權威,而是體現為衙門吏役這些知縣的爪牙,他們負責徵收賦税、緝捕人犯、遞送傳票、對田宅交易進行登記、張貼官府告示及在鄉村地區進行各種調查。
另一方面,衙門吏役的金錢利益和生計利益,與地方行政實踐的那種非正式特徵結合在了一起,再加上對吏役們的各種具體行為缺乏正式法令規定從外部加以控制,結果導致一些社會大眾在與這些國家在地方上的代理人打交道時,存在着對自己與衙門吏役相熟這一優勢及自己所具有的個人影響力加以利用的大量空間。正是這種可能性讓清代的官員們感到為之不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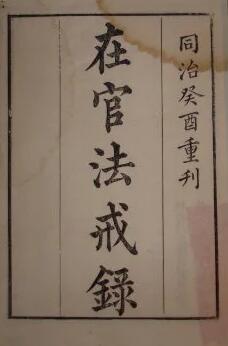
《在官法戒錄》刊本
雖然清朝的官員們經常斥責上述情形將會顛覆家長式教諭的影響並破壞公德,但是此類言辭的潛台詞則是那樣做將會導致朝廷權威面臨被稀釋的危險。當代的學者們通常會對上述相互作用的方式予以承認,但是也往往會將它描述為不僅削弱了國家對基層社會的滲透,而且還阻礙了國家與社會之關係在中國帝制晚期的充分理性化。
上述這兩種推測都有可能是正確的。但更重要的一點是,清代吏役們的那些非正式做法,使縣衙的行政活動變得不像是彰顯皇權的臂膀(不論縣衙的行政活動對當地百姓們是仁慈的,還是對社會大眾構成了擾害,抑或對其漠不關心),而更像是一個不同的人們在其中進行議價交換的區域。這一區域將那些非正式的私下交易與吏役們作為國家在地方上的代理人所承擔的各種正式功能結合在了一起。
在本書的前面幾章當中,我們已經看到此類交涉的許多例子,例如某人得到被招募進縣衙承充吏役的機會,由差役們擔任包税人,以及衙門吏役與地方社區之間的各種合作關係。除此之外,我們還可以將一些行政服務也歸入此類,例如向商人、牙人、戲班、妓院與鴉片煙館頒發執照或許可,對各種交易進行不實登記以規避繳納税款,又或者利用自己與在衙門當中工作的某些吏役的個人聯繫,使自己可以得到有利對待或內部消息。
在諸如此類的領域當中,清代縣衙的行政活動,為當地民眾提供了一種可被用來追求其各種個人利益的資源。這種資源的可獲得性,則取決於地方衙門吏役自身的各種經濟利益、他們對行政手段的控制,以及他們工作於其中的那一制度的法外運行特點。當然,在地方衙門吏役工作於其中的那一制度裏面,有着相當多的權力濫用空間。
但是正如我在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此類濫用手中權力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受制於地方衙門吏役自身希望這份生計能夠保持長期穩定的需要,同時還被當地各種關於怎樣才算一樁公平交易的觀念所約束。就此而論,衙門吏役乃是一個在當地的各種權力、權威與影響力之間遊走的特殊利益羣體。他們也是那個由彼此既衝突又聯合的衙門吏役、知縣與地方士紳所構成的三角模式當中的重要參與者之一。
首先,在維持所在縣域內各項行政事務穩定運行這一點上,衙門吏役與知縣的利益顯然是一致的。如果説知縣之所以期望行政事務能夠穩定運行,乃是為了增進國家的利益與基於自身仕途的考慮的話,那麼對那些希望保住自己手中飯碗的吏役們來説,維持行政事務穩定運行同樣也非常重要。這種共同的利益,使得非正式行政實踐所藉助的各種手段成了知縣們與吏役們之間的一種妥協。
然而,儘管知縣與吏役們之間經常相互合作,但他們的關係在某些方面天然存在衝突。例如,吏役們在承辦訴訟案件過程中的經濟利益,便經常會與知縣希望儘量減少待審案件的數量的想法相沖突。在這個例子當中,與其他領域中的情形相似,對各種行政資源進行控制並加以利用的問題,乃是雙方之間產生矛盾的最主要根源。
我們業已在本書前面部分討論過的許多例子當中看到,當新上任的巴縣知縣試圖通過改變一些慣例性做法來加強自己對衙門內部事務運作的控制時,吏役們能夠對知縣的這種努力進行抵制。為了在此類衝突中強化自己的主導,知縣們有許多種手段可以動用,其中最常用的是體罰這種赤裸裸的強制性權力。知縣們為了減輕對吏役的依賴,還經常會自己出錢僱用長隨與幕友,而這些人可以在專業技能方面與吏役們形成某種抗衡。不過在這個領域當中,最為重要的資源與支持力量,乃是知縣與當地士紳們之間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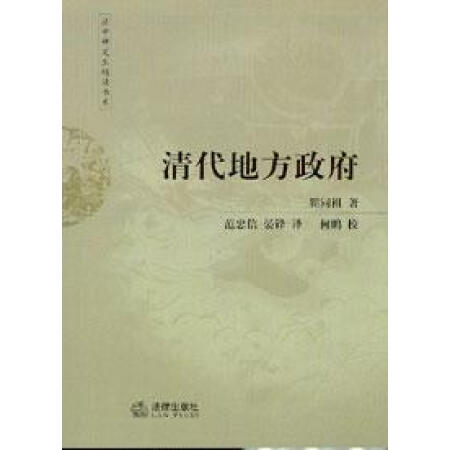
《清代地方政府》書影
在地方層面的所有政治關係當中,知縣們與當地士紳領袖們之間的關係在學術界被分析得最為透徹,以至於這種關係有時被描述成相當於地方權力及其影響之全部。此種看法在某種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沒有當地社區領袖們的配合,一名知縣要想管理好其治境內數以十萬計的民眾,根本就希望渺茫。
因此,衙門吏役被形容為知縣的爪牙,而士紳領袖們則經常被稱作知縣的耳目。這種以人體感覺器官進行比喻的説法非常形象和貼切,因為如果説爪牙可被視作執行知縣意志的工具的話,那麼耳目這一説法,則意味着一種認為士紳領袖們所起到的作用遠非純粹只是工具性的共同看法。
這種關係當中的合作,乃是植根於知縣們與士紳領袖們共享的儒家正統價值觀及建立在那些理念之上的權威結構。正如許多學者已經指出的那樣,這種存在於社會政治等級結構,以及該結構的那些意識形態基礎當中的相互投入,使得清政府能夠以一種在現代早期的歐洲不可能實現的方式,來與地方精英們分享權威。在社會出身、教育背景、志趣愛好及那些被明確加以表達的價值觀方面,相較於其與所在社區當中的其他羣體(包括衙門吏役在內)而言,知縣們與士紳們彼此之間有着更多的共同之處。
儘管知縣們與當地士紳領袖們在許多方面都很相似,但他們各自的利益及在追求這些利益的過程中所使用的手段卻並不總是一致的。如果説士紳領袖們對地方事務的介入經常被看成是給予縣衙以支持協助的一種重要來源,那麼這種介入同樣也經常會被知縣們及其上級官員認為是對官府事務的橫加干預與多管閒事。
這在19世紀後半葉尤其如此。當時,士紳中的積極分子開始填補正在逐漸走向衰弱的清朝中央政府在地方管理上的各種空隙,並對各種可用的新資源與正在不斷變化的時局加以利用。他們所做的這一切,乃是為了提升自己在地方事務當中的影響力。在此過程中,衙門吏役再次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從衙門吏役的行為及其金錢利益會對地方士紳們的權威造成妨礙或顛覆這一層意義上講,這兩個羣體之間的關係天然是彼此對立的。在這種衝突當中,社區領袖們經常利用衙門吏役的很多做法嚴格來講屬於非法這一點來大做文章,將這些做法説成是在魚肉鄉里。衙門吏役那種人盡皆知的貪腐形象,因此被士紳領袖們用來反襯他們自身被公認具有的道德魅力與那些無私動機。

影視劇中奸官猾吏的形象
正如諸如三費局之類的紳局在四川的設立那樣,此種策略有時不僅被這些士紳領袖們利用來作為捍衞自身在當地的社會地位的一種手段,而且還被他們利用來作為在此類半官方機構之中擴大自身對行政事務之影響力的一種有效工具。
雖然清代地方政治經濟體制的上述方面尚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但顯而易見的是,地方士紳與衙門吏役之間的互動,並非像以往所描繪的那樣總是彼此敵視。真實的情況是,社區領袖與衙門吏役之間的相互合作,無疑經常會被他們用來獲取各種狹隘的利益,或者被用來強化他們當中某些人的強制性權力。不過,倘若因此便認為當時的情況總是這樣,則就屬於無根據的臆斷。
正如本書前面討論過的當地社區領袖為遭到同班其他差役指控的巴縣衙門糧班領役範榮開脱的例子所展示的那樣,當地社區領袖們與衙門吏役的個人聯繫和接觸,有助於保護當地社會各種廣泛的利益,例如讓那些為害地方的盜匪能被官府迅速緝捕歸案,隱瞞當地社區賴以為生的製售私鹽或鴉片的行為而讓其不被知縣所知曉,又或者使差役們向當地民眾所收取的規費保持在某種慣例性限度範圍之內。
尤其是對那些自己手頭擁有的資源不多、處於精英階層底端的人們來説,他們與衙門吏役的直接接觸與合作,常常被其作為加強自身在當地的影響力及實現自己各種預期目的的最有效手段。在此類情形當中,有着最直接的決定性影響力之人並非知縣,而是衙門裏面那些高級別的書吏和差役。
因此,當地的士紳們在這種三角關係當中處於一個扮演着多重角色的特殊位置,他們在與知縣周旋時強調自己身為正統觀念之捍衞者的傳統角色,同時又在與地方衙門的吏役們進行非正式的磋商,以規避正式制度的種種束縛。
對於衙門吏役們來説,與地方上那些有影響力的個人培養非正式的聯繫,同樣也是大有裨益。正因如此,在本書前面幾章當中,我們不僅看到巴縣境內的一些社區領袖站出來聲援那些遭其同事指控行為不當的書吏或差役,而且還看到他們試圖將自己中意的人選安排到吏役隊伍當中的那些重要位置之上。
這些例子只代表了那些因吏役內部發生爭端而使得此類事情引起知縣注意的情形。那些沒有引發爭議並因此未被記錄下來的衙門吏役與社區領袖進行日常合作的例子,如今我們已無法看到。
雖然本書所描述的各類互動與交易之確切性質在某種程度上系巴縣所獨有,但是我想説這些關係的運作機制在清帝國全境則是類似的。不過,為了揭示這些運作機制,我們必須注意避免那種將西方的歷史經驗套用到中國頭上的傾向。易言之,不要預設在清代的國家與社會之間存在着一條涇渭分明的界線。
相反,我們需要超越正式制度與法律規定的那些邊界,不是把清代縣衙看作被嵌入在地方社區之中的一個其內部離散的機構(地方社區內部同樣也是離散的),而是將清代縣衙視為各種資源和做法(包括正式的與非正式的、物質性的與象徵性的資源和做法)匯聚於此的一處場所,對於當時操持不同營生方式的各個社會羣體而言,這些資源與做法的可獲得性各不相同。
與正式的行政制度不同,清代衙門當中的那些慣例性做法具有適應性。的確,這些慣例性做法在清代衙門當中的存在本身,可被視作是對它們運行於其間的那些廣闊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的一種回應。在某種程度上,縣級行政活動的非正式面向,在中國帝制晚期伊始便已出現。它是正式行政制度與縣級政府的各種實際需要之間的初始差距所導致的一種結果。
然而,縱然正式制度保持靜止不變,清帝國在18世紀與19世紀初發生的人口總數激增與經濟快速發展,導致非正式行政方式的範圍也隨之急劇擴大。而非正式行政方式的範圍擴大所造成的必然結果,便是地方衙門的各種資源被私人挪用的可能性隨之大增。
19世紀中葉以降,由於清朝中央政府將其政令貫徹到帝國境內基層社會各個角落的能力逐漸下降,地方精英們與國家之間的矛盾不斷加深,以及社會動亂的普遍增多,上述局面更是雪上加霜。
故而,雖然那些非正式的行政方式有助於清朝在這一動盪不安的世紀當中維繫其統治,但這種局面所付出的代價則是朝廷對其行政機器的控制能力日益遭到削弱。
這就引出了本書要討論的最後一個問題,它同時也長期困擾着當代那些研究中國帝制晚期政府的學者們。這個問題就是,當在我們看來彼時存在着大量證據表明現實情況並非如清朝中央政府想象的那樣時,朝廷的政令為何還固守着那種認為正式行政制度足資可用的假象?
此問題的答案,至少有一部分在於,從那些身處廟堂之上的官員們的角度來看,那套正式行政制度似乎足堪滿足需要。正如曾小萍在她那本研究18世紀清政府財政改革的著作中所描述的,各級地方政府當時利用各種法外的辦法增加財政收入所取得的成功,遮蔽了進行任何體制性結構改革的需要。
在朝廷所規定的地方衙門經制吏役額數這一問題上,也同樣如此。本書前面幾章當中所描述的那些非正式行政方式,為清朝所有的縣衙提供了足夠的延續性、穩定性與靈活性,從而使得知縣們能夠履行他們的基本職責,並讓中央政府感到滿意。由此,地方秩序通常能夠得到維持,而絕大部分的錢糧賦税也能按時上交朝廷。
因此,當偶爾有某位知縣或省級官員抱怨自己可利用的資源太少時,往往就會被解釋為是該官員自身能力欠佳、勤勉不足或品德有缺,而不是被看作意味着需要對原有的那套正式制度加以徹底改革。如果説正式制度的所謂健全在很多方面實際上都是幻覺的話,那麼即便如此,它仍然是一種容易被維繫下去的幻覺。
就像此前的那些王朝所做的那樣,清朝在此方面的立法重點,仍然集中於通過就經制吏役的額數、服役期限及對吏役違法行為的刑事懲罰措施加以規定,來對衙門吏役進行控制,並同時規定那些被發現怠於行使其管束手下吏役之責的知縣將會因此受到懲罰。
故而,儘管清朝早期的幾位皇帝曾採取舉措試圖進一步強化集權,並挑選性地針對帝國行政的某些方面進行了體現出理性化的改革,但無論是那幾位皇帝自己,還是他們那些承襲皇位的後代們,都沒有嘗試着對清朝地方政府的結構加以重塑,或者對那些將中央任命的官員與衙門吏役區隔開來的社會界線與制度界線進行改變。
不過,從另一個層面來看,清朝中央政府為何始終沒有通過對正式行政制度進行結構性改革的方式來解決地方政府所遭遇的那些困境,這一問題本身便是成問題的,因為這種提問方式預設了那些有權力這樣做的人們可以不受意識形態與政治性考量的束縛。

在中華帝國晚期那種中央集權的官僚制結構當中,政府是作為一種制度化的支配工具而發揮作用。
自宋代以降,歷代的朝廷都在利用此種支配工具,逐步從地方社區的領袖們那裏奪取更大程度的對行政活動的控制、權威與各種資源。中華帝國晚期在此方面所做的那些努力所取得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儒家意識形態中那些使其得以正當化的效用。後者使得地方精英們能夠長期維持其社會統治地位,即便它們同時也在為國家權威在地方行政事務當中的擴張保駕護航。
根據宋代理學家們所創立的那個形而上學基礎,帝國的政府並沒有而且事實上也不應該作為一種赤裸裸的支配工具而存在。相反,以儒家的理念與價值觀作為其統治準則的帝國政府,在其所奉行的那些制度當中,以及官僚們與君主那裏,被描繪成同時也是至高無上的道德規範的化身及其實現工具。因此,帝國政府權力的實施及其正當化,既非通過法律的強制性力量,也不是依賴行政技術的功利性效用,而是通過運用那些被普遍化了的道德正義準則對權力加以校準的方式來實現的。
清朝的法律—行政制度本身就是此種理念的結晶。不論這套制度在實踐當中是被做何種用途,在正式的層面上,《大清律例》從來就無意充當一種在帝國政府與皇帝的臣民們之間或者在天下萬民之間調和各種關係的實證法體系。
相反,清帝國的法律被建構成一個裝滿各種刑事懲罰規定的貯藏室。它通過對一種靜止不變的政治秩序與社會秩序加以維繫的方式,來維持正義在宇宙當中的平衡。作為皇權的代表,知縣之影響力的發揮,不能僅靠積極主動執行法律規定的方式,而是要藉助其官員身份所具有的那種令人敬畏的權力,以及他自己的個人行為。如前所述,從這個意義上講,縣衙公堂作為儀式的中心,將國家、社會與宇宙秩序全部勾連在了一起,並用一種超驗的道德觀念對其整體進行薰陶。
如同上述論述所意味着的那樣,在那些社會性的規範與理念和政治性的規範與理念之間,並不存在斷裂;各種在本質上相同的道德律令,要求普羅大眾服從於皇帝、皇帝的代表們,以及社會精英。在很大程度上,政治精英與社會精英們所共享的那些正當性原則,造就了中華帝國在制度方面令人難以置信的穩定與長壽。
不同於啓蒙運動之後的歐洲,在帝制晚期的中國,並沒有發展出對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的清晰劃分(更加不用説將那種劃分予以神聖化),正如在古漢語當中看不到任何不帶貶義色彩的、用來表示“私”的意思的術語這一事實所證明的那樣。由於上述這種道德維度的存在,帝制中國晚期的政府也缺乏那種去人格化的功能性理性主義,而正是這種功能性理性主義標誌着官僚制國家在歐洲的誕生。
11世紀王安石變法的失敗,在部分程度上可被看作是官僚們與社會精英們針對此種理性化的創生共同進行抗拒所造成的結果。最終,判斷一個人能否勝任某官職或者是否配得上某種社會地位的標誌,既非技術能力,亦非現實效用,而是其對儒家所推崇的那些社會政治價值觀的認同。
自宋代以來,帝國政府的穩步發展及其在地方上的行政權威擴張,於是便在社會關係與政治關係之間未有任何重要的分離跡象的情況下發生了。隨着知縣之類的地方官員們的職責與政務負擔在明清兩朝不斷加重,此過程也發生在同一套意識形態框架的內部,而這一意識形態框架先前所維繫的,乃是一個在疆域上要比明清兩朝小都得多的帝國。(譯者注:作者在此處是將明清兩朝與宋代進行對比,這三個朝代都將儒家思想奉為國家的正統意識形態。元朝的疆域雖然遠比宋明清三朝遼闊,但因蒙古人入主中原的緣故,儒家思想在元朝並不受推崇。基於上述原因,本書作者在討論儒家意識形態與價值觀時,有時會將明清兩代與宋代進行比較,而不談元朝。)
由於這個緣故,當書吏和差役們的人數逐漸增多,並且其在衙門中的這份工作從一種勞役發展成為一種半技術性的營生方式時,這些人依舊處於官方所認可的正當性之外。吏役們那種作為功能性專家的功利性角色(他們既沒有受過讀寫能力的訓練,譯者注:嚴格來講,作者此處的這一描述適用於差役,但並不適用於書吏。正如作者在本書第二章當中曾討論過的,書吏們所從事的工作性質,要求他們必須具備並不低的讀寫能力。亦無功名在身),使得他們只是純粹的行政工具,故而顯然並不適合充當朝廷權威在地方上的直接代表。
到17世紀中期清朝統治全國之際,中華帝國的擴張業已使得那套正式行政制度的各種缺陷日益明顯地暴露出來。到了19世紀,清朝定鼎中原後150多年來的持續發展,使得其所奉行的那套行政理論與行政實踐之間的矛盾變得更加突出。
雖然衙門吏役的活動很難被當作造成出現當時人們所逐漸意識到的那些地方政府危機的首要原因,但這些人的各種不當行為,以及大量非經制吏役在正當性界限之外的存在本身,導致他們很容易受到帝國官員與地方精英們的口誅筆伐,而此類抨擊又將會發展成帝國官員與地方精英們之間的一種衝突。
當然,對於應如何改革當時的地方行政制度,在19世紀並不缺乏此方面的建議。所有的這些建議都強調吏役們在地方衙門事務處理過程中的重要性,並且皆將所謂的吏役貪腐當作亟須解決的重點問題予以關注。

《爪牙》書影
當時的一些經世思想家,對顧炎武在明末清初就衙門吏役問題所做出的那些觀察進行了回應。例如,馮桂芬認為吏役問題是政治權力過度中央集權化所導致的一種惡果。在他看來,當知縣面對着其幾乎無法完成的大量行政任務時,真正的權力就不可避免地會落到那些貪婪成性的衙門吏役手中。馮桂芬建議,解決此問題的辦法是把行政管理的權力下放,讓地方上的士紳領袖們重新具有一定程度的權威,由此就可以消除對衙門吏役的依賴。
另一些提出改革地方行政制度的建議的人們,是當時的一些省級官員,例如曾任江蘇巡撫、福建巡撫等職的丁日昌。丁日昌認為,此問題起因於地方衙門吏役從中作梗,以至於官員們與當地民眾之間缺乏直接溝通。然而,他們所提出的解決方案,是要加強中央集權,以及官僚制度對基層的滲透,而不是相反。
在這些發表其見解的省級官員們看來,被強化後的中央集權,可以通過將書吏與差役們整合到官僚序列之內,進而讓這些人的利益與大清王朝的利益更為明確地息息相關,如此一來,便能夠將那些對皇權在基層的權威與影響構成妨礙的吏役們從地方衙門當中清除出去。
**上述這兩種改革建議,最終都沒有被清廷採納。的確,這兩種改革建議當中的任何一種若被付諸實施的話,都必然會破壞社會精英們與政府權威之間的平衡。**究其特點而言,這些改革路徑要麼是通過激進地將大清王朝的權力予以下放,要麼是同樣激進地擴大官僚人員的規模。就算清政府擁有足夠的財力來擴大官僚人員的規模,只要帝國政府的權力與權威之正當性是與恪守儒家所推崇的那些原則緊密勾連在一起,那麼書吏和差役們就無法在不破壞整個原有結構的情況下被吸納到官僚序列中來。
與此同時,經濟的增長、社會的發展,以及清帝國內部發生的各種叛亂活動與外國列強的入侵,正在共同塑造着新的社會形態、新的精英階層及新的地方權力擁有者。這些新的地方權力擁有者,在維持傳統現狀方面投入的精力很少,更加不關心利用儒家意識形態將其擁有的此種權力予以正當化。
但是,當時正在發生變化的,並不只有大清王朝的社會根基。到了19世紀末,地方社區與行政人員之間在法律之外展開非正式互動的各種模式,當時已經成為地方政府架構的組成部分之一。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重建政府的過程中,這些模式並未被加以明顯改變。
相反,辛亥革命破除了對衙門吏役與私人個體將各種地方行政資源挪為己用的行為加以約束的最後一些殘餘因素。伴隨着帝制時代的壽終正寢,這個舞台於是被設置為迎接一種權力更加分散且分權更為徹底的新支配形式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