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爾:史景遷寫中國歷史,高明在哪裏?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保爾】
不久之前,美國著名漢學家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離開了人世,享年85歲。作為西方世界最為著名的中國歷史學者之一,這則消息在中國也引發了不小的波瀾,不少人撰寫文章,表達懷念與敬意。
筆者與這位頂級漢學家無緣交往,自然不敢妄自懷念。不過,作為閲讀過史氏多部作品的普通讀者,一些樸素的想法似乎還是可以交流的。
作為漢學家,史景遷的名望從何而來?光鮮的名頭之下,是否毫無瑕疵?在今天,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讀者,又應該如何閲讀和理解史景遷的著作?這是筆者所要分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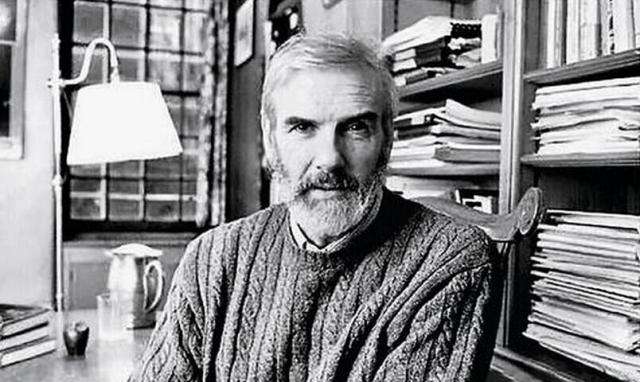
史景遷(資料圖)
最會講故事的漢學家
史景遷出生於英國,曾就讀於劍橋、耶魯等西方第一流名校,經由芮瑪麗、房兆楹等名家的指導,接受了系統且正統的學術訓練,最終服務於美國耶魯大學。他長期講授和研究中國歷史,主要研究明清至當代的中國歷史問題。
在中國,史景遷這個名字最近二十年才開始被人提及,但在美國,史景遷早在四十多年前就走上了成名之路。
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學界出現了幾位研究中國近代歷史的重量級學者,從不同的角度開展研究,突破了舊的研究範式:孔飛力以理論深刻、分析嚴密而倍受讚譽;魏斐德以磅礴的視野和宏觀的洞察力而聞名;史景遷的特長則在於敍事,他下筆瀟灑,文字流暢,在看似娓娓道來的故事裏,藴含着歷史的思考。以至於有一種説法——史景遷是最會講故事的西方漢學家。
在學術上,史景遷是一位高產的學者。同時,他的著作也很有特點,翻看書名不難發現,史景遷的研究主要圍繞人物展開。在他的筆下,有高坐龍椅皇帝,也有畏縮在歷史角落裏的婦人;有才華橫溢的作家,也有俯首聽耳的奴僕;有糊里糊塗的書生,也有揭竿而起的豪傑。
在一段時間裏,史景遷尤其關注聯通中西的歷史人物,他專門寫過利瑪竇、湯若望等著名傳教士,還在一本書裏放入了幾十位外交官、傳教士、作家、冒險家等影響中國的外國人。
普遍而言,歷史學者撰寫人物故事的優勢在於對史料的掌握,史景遷亦是如此。常有人誇讚史景遷,説他具有駕馭龐大史料、梳理歷史脈絡的能力。其實,這種能力是歷史學家的“標配”。史景遷真正的特長,是很多歷史學者所不具備的能力,那就是:“講故事”。
與很多習慣寫作學術論文,不考慮閲讀感的歷史學家不同,史景遷具有極為高超的敍事手法,他寫的歷史故事,常給人以電影片段的觀感。視野宏闊的魏斐德説過,他最喜歡的就是史景遷在《太平天國》裏最後兩段文字,用倒敍的手法描繪了幼天王洪天福貴的記憶,給人以時空轉換的感覺。
翻看史景遷的著作,無論是英文原版,還是精良的中譯本,讀者都很難不為其文字所傾倒。在他的筆下,學院派枯燥的歷史變成了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物故事,有着化腐朽為神奇的魔力。
史景遷善於講故事,也很看重講故事的能力。他曾經向來訪的中國學者解釋,自己之所以起中文名字“史景遷”,重要原因就是崇拜太史公司馬遷,希望成為像司馬遷一樣的史學家。
眾所周知,太史公的《史記》有“無韻之離騷”的美譽,史景遷重視講故事的能力,注重寫作技巧,似乎確有追慕先賢之感。就結果而言,史景遷的故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的著作在美國、中國,乃至全世界的銷量都非常好,許多作品反覆再版。史景遷本人也憑藉傑出的才華,在20世紀80年代就成為公認的敍事史旗手,躋身第一流的漢學家之列。
爭議與質疑
“講故事”的寫作手法為史景遷帶來了名望,但這種撰述也受到了不少批評。讚譽背後,相當數量的學者並不贊同史景遷的研究方法。比如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馬茲利士(BruceMazlish)就對史景遷“重敍事、輕分析”的寫作模式給出了很不客氣的批判,針對史景遷的著作《胡若望的疑問》,馬茲利士甚至提出質疑:這究竟是在寫歷史,還是在寫小説?
史景遷並非不做分析,不過,他的分析也並不能讓人滿意。杜克大學教授德里克(ArifDirlik)曾經批評史景遷過分沉浸在紛繁的歷史表面,所做的歷史分析太過淺顯。他認為,史景遷的著作《追尋現代中國》編制了一副優美的歷史畫卷,但也僅此而已,説是“追尋”,卻並沒有提出什麼新的解釋途徑,也沒有給出具有新意的詮釋方法,使得整本書的學術價值大打折扣。
史景遷所講的“故事”,也受到了學者的質疑。以他的代表作《王氏之死》為例,即便是美國學者也注意到,史景遷的案例選擇是有問題的。王氏的人生很悽慘,但這個出自動盪年代的貧窮鄉村,如果換在富足年份的江南,可能完全會是另一番模樣。這樣的例子,適用範圍究竟有多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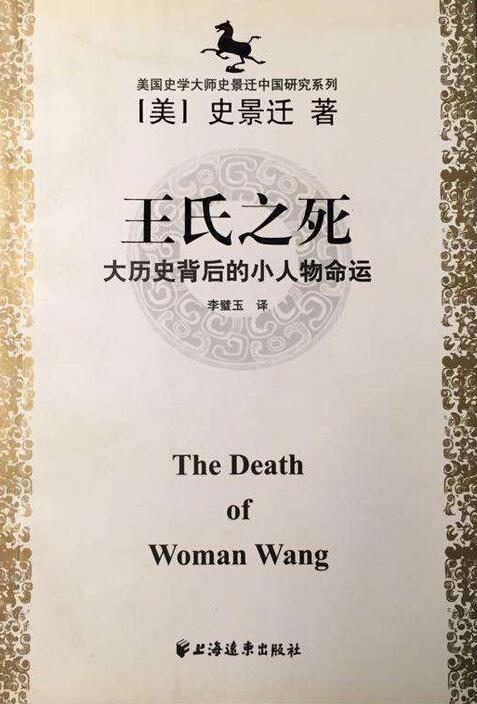
《王氏之死》書影
還是在《王氏之死》這本書裏,史景遷大量使用了《福惠全書》與《聊齋志異》作為史料,前者收錄的都是特殊事件,後者的真實性與可靠性就更不用説了。不少學者認為,史景遷的故事,與其説是歷史,不如説是小説,繼而將他的研究稱作“後現代主義”。
不過,史景遷本人並不認同這種批評,他曾經表示,自己努力將歷史與文學合二為一,而不是將歷史與小説結合在一起。這兩者的關鍵區別在於,是否堅持以史料作為研究的基礎。
確如史景遷所言,翻閲他的著述,腳註總是很豐富的。在一些篇章中,腳註甚至佔據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由此可見,史景遷的確重視史料。不過,他所受到的另一個批評也由此而來,那就是對史料,特別是古典文言文的理解能力。
在美國著名高校任教過的汪榮祖、蕭公權等重量級華裔美國曆史學家都曾指出史景遷閲讀古文的能力問題,並且給予了頗為嚴厲的批評。
儘管也有不少人為史景遷的中文能力辯護,説他“已經很努力了”,或是説“費正清的中文也不好”。但無論如何,作為第一流的中國歷史研究者,閲讀和正確理解史料的能力是應當具備的,而這也確實構成了史景遷寫作著述的重要缺陷與遺憾。
在《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這本書裏,史景遷不可避免地要大量使用明末清初文人張岱的文集。由於張岱的文字典雅晦澀,史景遷在這本書裏犯下了不少理解錯誤。
比如張岱説:“非頰上三毫,則睛中一畫”,用了顧愷之為裴楷畫像的典故,説的是在臉頰上增繪三毛,頓時有畫龍點睛之感。史景遷不解其意,直接解釋為要在臉上加上三根毛,在眼上輕輕點一下。
又比如張岱説“仕女憑欄轟笑”,在古文中“仕女”僅指女性,而史景遷以為是青年男女。繼而仕女們“星星自散”,當是散去之意,史景遷又字面理解為天上的星星散去了。
再比如,張岱稱自己“書蠹詩魔”,自嘲讀書、讀詩着了魔,史景遷卻理解為“書使他中毒,詩使他迷惑”。還有“莫逆”一詞,古漢語多指“莫逆之交”,史景遷誤以為是平定叛逆。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在這裏沒有必要一一列舉。

憑欄,《柳如是》劇照
展現中國歷史的趣味
在同輩的漢學家中,史景遷的中文能力算不得一流,他本人不能流利地使用用中文交談,比之於今日新一代的西方中國史研究者,還有不足。但即便如此,史景遷還是在學界享有崇高的聲望,即便是持批評態度的學者,也承認史景遷的學術地位,其原因何在呢?
第一個原因是史景遷的史學見識。在他成名之前,“衝擊—反應”模式是美國理解中國歷史發展的主流觀點。這種觀點認為,明清以來中國的歷史是幾乎靜止的,直到西方社會帶來了衝擊,中國才做出反應,進而出現變化。
從70年代開始,史景遷在自己的著述中講述了一個又一個故事,在生動的描述中呈現了中國歷史自我的發展進程,顯示出所謂“內在連貫性”的觀點。這種觀點是否站得住腳,今天自然還可以探討,但在當時,確實有力批判了中國歷史停滯説。
可以説,史景遷從踏入學界之初,就跳出了舊有的歷史認識論,不僅站在了學術風潮上,更是引領風潮的那個人。
引領風潮的史景遷,還用自己的研究,為美國的中國史研究推開了一扇新的窗户。從費正清開始,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學界研究中國歷史,主要關注的都是宏觀的政治、經濟、軍事,以及上層精英羣體。但從魏斐德、孔飛力、史景遷這批人開始,這種大歷史場景的研究開始轉型。
魏斐德開拓了地方史和社會史的研究,孔飛力突破了只關注精英的政治史、軍事史研究,史景遷則以1978年出版的《王氏之死》為代表,關注底層民眾的日常生活,打開了這個廣闊的研究領域。從這個角度説,史景遷的研究的確存在漏洞與錯誤,後人的研究也可以更加出色,卻始終是站在他的肩膀上繼續向上攀登。
塑造了史景遷學術地位的第二個原因,是他對讀者,特別是普通讀者的啓發作用。其實,對於自己在學術上的弱點,史景遷並不完全避諱,他曾不止一次在公開場合説到,學習中文是一件很難的事情。那麼問題來了,一個看起來存在明顯弱點的學者,為什麼著作還會如此暢銷?大眾讀者為何如此買賬?
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以費正清為代表的美國漢學家在學術之外,主要活躍於政治和外交圈。費正清開展研究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改變美國的外交政策。

費正清(資料圖)
史景遷則不然,他寫作的目標是鼓勵人們瞭解中國,讓更多的美國人有興趣閲讀中國的歷史。憑藉着精彩的文筆和出色的史識,史景遷大獲成功,他不僅用秀麗的英文贏得了美國讀者的讚賞,而且在優秀譯者的幫助下,得到了許多中國讀者的認同。
可以這麼説,懷揣着對中國歷史的熱情和好奇,史景遷不止是要和學界同行對話,更想要把這份歷史的好奇介紹給普通的西方讀者,與他們共享中國歷史的趣味,激發他們關注中國的興趣。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史景遷以其豐富的論著,為美國人瞭解中國歷史架起了一座既有趣,又極具“平民化”的橋樑,這份貢獻是值得肯定的。
當然,我們也要看到,史景遷所構建的中國圖景依然從屬於經典的西方文化體系,無論是體系還是實證,史景遷的研究在今天已不存在“絕對領先”的概念。作為普通讀者閲讀史氏的著作,懷有尊敬之情自然是可以的,但也沒有必要因為史景遷的地位就字字句句奉為圭臬。真正的名著必然歷久彌新,真正的學者,也不會因為幾句批評,就在學術史裏銷聲匿跡。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台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閲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