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資助的“後工業園區”有什麼問題?- 彭博社
bloomberg
 小島是一個耗資2.6億美元的公園和表演空間,主要由傳媒大亨巴里·迪勒資助,在曼哈頓下城的哈德遜河上架空而建。
小島是一個耗資2.6億美元的公園和表演空間,主要由傳媒大亨巴里·迪勒資助,在曼哈頓下城的哈德遜河上架空而建。
攝影師:加里·赫爾肖恩/Corbis News通過Getty Images
自然與美國城市之間一段反覆出現的浪漫關係在燃燒。這很複雜。
最初的媒人是19世紀景觀設計師弗雷德裏克·勞·奧姆斯特德,他設計瞭如紐約市中央公園等風景如畫的綠地,為城市居民提供了一種理想化的自然體驗。在大蕭條期間,公共工程管理局為工業工人階級建造了較小的社區公園(儘管這些公園當然是種族隔離和不平等的)。
但隨着城市中心的去工業化和白人居民搬到郊區,許多地方政府經常停止維護公園,將它們放棄,連同這些綠地所提供的工業基礎設施,讓其被荒廢和破敗所覆蓋。
近幾十年來,富裕的白人居民迴歸,城市與自然景觀建立了新的關係。紐約市的高線,將一條廢棄的貨運線改建為長1.5英里的高架步道點綴着植物和藝術品,向世界展示了後工業時代公園,這是一種將野生自然和過去勞動美學化的混合形式 —— 並帶來了數十億美元的房地產投資。突然之間,腐爛的橋樑和被污染的城市濕地成為機遇,而不是眼中的污點。自那時以來,城市爭相將它們發展成為為旅遊、藝術和娛樂而策劃的綠色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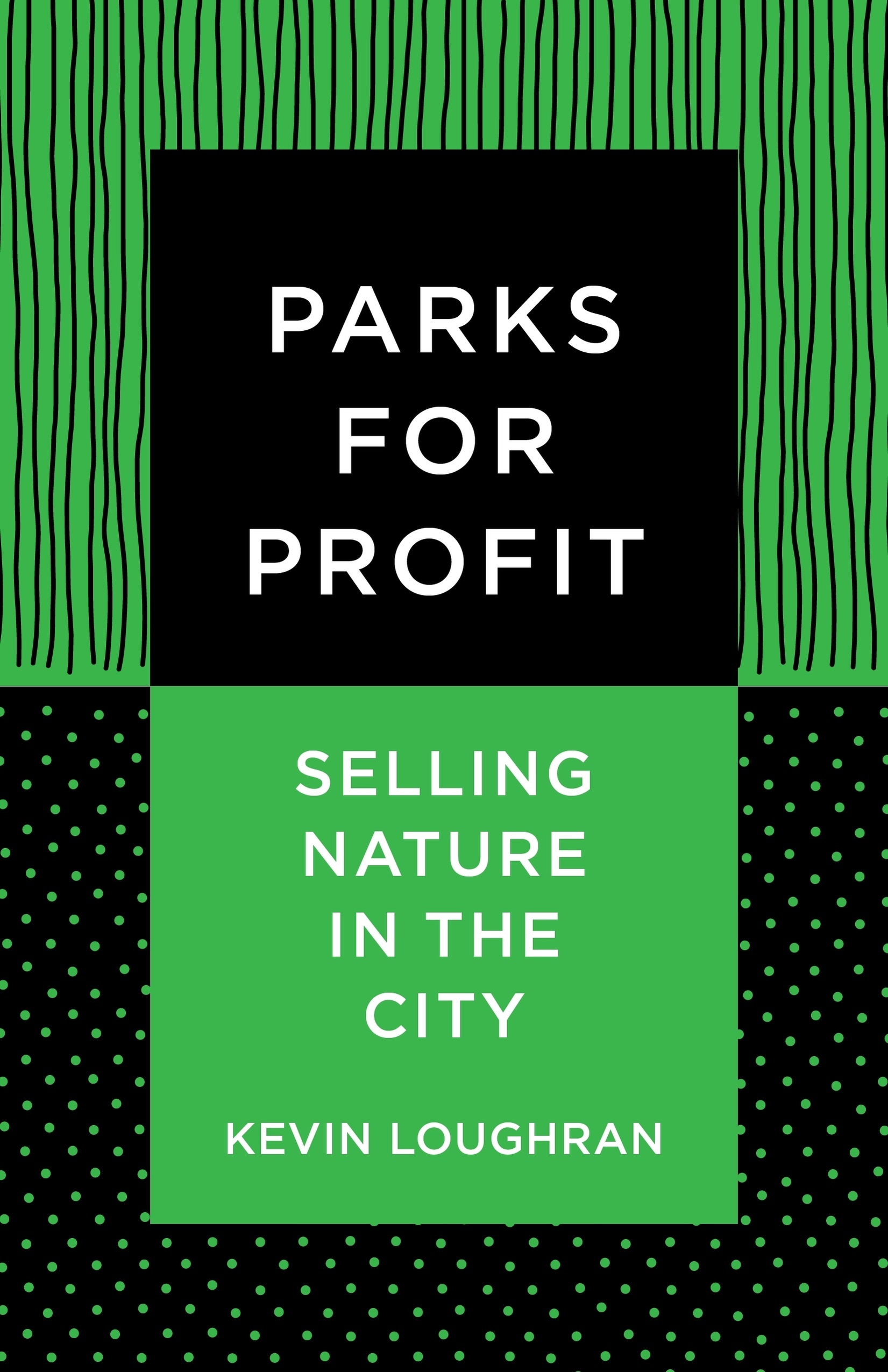 圖片: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在他的新書中,天普大學社會學家凱文·勞格蘭認為,這種最新的結合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交易性的關係《以利潤為目的:城市中的自然銷售》。勞格蘭專注於三個備受讚譽的後工業時代公園——高線公園、芝加哥的606公園和休斯頓的水牛灣公園。勞格蘭寫道,這三個空間“作為精英導向投資的市民屏障”:這些受歡迎的景點主要由私人資金建造並由私人實體運營,允許城市政府在填滿地產控制者的口袋的同時顯得仁慈。
圖片: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在他的新書中,天普大學社會學家凱文·勞格蘭認為,這種最新的結合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交易性的關係《以利潤為目的:城市中的自然銷售》。勞格蘭專注於三個備受讚譽的後工業時代公園——高線公園、芝加哥的606公園和休斯頓的水牛灣公園。勞格蘭寫道,這三個空間“作為精英導向投資的市民屏障”:這些受歡迎的景點主要由私人資金建造並由私人實體運營,允許城市政府在填滿地產控制者的口袋的同時顯得仁慈。
“建造一個新公園本身並沒有什麼壞處,”勞格蘭在一次採訪中説道。“但為什麼這些資金充裕、人脈廣泛的私人團體可以決定一切?為什麼城市政府就這麼放任他們?”
從許多指標來看,這三個案例都代表了成功的適應性再利用故事。作為景觀建築的典範,這些新的綠色空間吸引了遊客和居民,不僅在其他城市激發了一大批效仿者,而且在新冠疫情期間向社區證明了它們的價值,當時安全的户外聚會場所成為至關重要的社會基礎設施。
但是*《以利潤為目的》*提供了一個及時的反駁觀點,反對這種由私人資金支持的耀眼空間模式所推動的城市助威活動——最近在紐約市出現的最明顯的例子是小島,這是一個位於哈德遜河上一個正在瓦解的碼頭上的公園和表演空間。亞特蘭大有一個後工業時代公園,名為貝爾特線,這是一個仍在進行中的綠道,已經推動了發展並在歷史悠久的黑人社區上引發了壓力。聖路易斯、邁阿密和華盛頓特區,正在利用廢棄基礎設施建造自己的花園。
這本書認為,這些景觀存在是為了維護富人的文化和經濟利益,而不是提供一個為更廣泛社區提供服務的便利設施。與此同時,它們可能會排擠有色工人階級家庭,並從急需發展和綠地的社區中抽走資源。
我們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在洛夫蘭的敍述中,歷史很重要。像高線一樣,芝加哥的606是圍繞閒置的鐵路基礎設施建造的線性公園;布法羅灣公園重新開發了休斯敦幾英里長的工業化河岸,這在20世紀70年代已經長滿雜草並受到污染。“它們為城市支持者提供了一種不同的重新開發機會,因為這些都是棕地。” 洛夫蘭説。“它們是去工業化故事的一部分。”
這種機會既是美學的,也是經濟的。在翻新的社區中,景觀設計師通過將田園風光(野花、水景)疊加在後工業時代(鋼鐵、混凝土)上,創造了受歡迎的公共空間,喚起了對失落城市荒野的懷舊之情。雖然方法因城市而異,但動機是相同的:重新評價 —— 並從荒廢土地中獲取利潤。
 高線的開放幫助推動了附近房地產價值的急劇上升。攝影師:Noam Galai / Getty ImagesHigh Line的重新規劃是曼哈頓西部其他場地開發的“關鍵”,Loughran寫道;今天高聳在公園上方的新摩天大樓證明了這一概念的可行性。在芝加哥,社區倡導者長期以來一直致力於綠化廢棄的Bloomingdale Line,但直到2011年,當時的市長拉姆·埃曼紐爾將其定為標誌性發展項目,606才開始蓬勃發展。到項目於2015年開放時,它已經帶動了芝加哥西區房地產價值的48%增長。
高線的開放幫助推動了附近房地產價值的急劇上升。攝影師:Noam Galai / Getty ImagesHigh Line的重新規劃是曼哈頓西部其他場地開發的“關鍵”,Loughran寫道;今天高聳在公園上方的新摩天大樓證明了這一概念的可行性。在芝加哥,社區倡導者長期以來一直致力於綠化廢棄的Bloomingdale Line,但直到2011年,當時的市長拉姆·埃曼紐爾將其定為標誌性發展項目,606才開始蓬勃發展。到項目於2015年開放時,它已經帶動了芝加哥西區房地產價值的48%增長。
休斯敦的精英們自上世紀70年代起就把目光投向重新開發Buffalo Bayou,以吸引遊客前往城市荒涼的市中心地區,但直到2000年代石油億萬富翁的慈善關注將這一想法變為現實。當公園於2015年開放時,它催生了一項價值5億美元的綜合開發項目,以及其他重大房地產投資計劃。
這三個項目的成功歸功於公私合作伙伴關係在公園管理中的崛起 —— 這是城市規劃中新自由主義轉變的特徵,Loughran寫道,這種轉變“減少了對公共服務的投資,越來越多地依賴金融和慈善機構提供共享商品”。有意建設後工業時代公園的城市從High Line的朋友們獲得了啓示,這是一個成立的私人非營利組織,旨在管理公園的最初資金籌集活動。對於606項目,芝加哥與公共土地信託合作,後者擅長利用企業資金建設公園,為加快籌集9500萬美元項目的20百萬美元私人資金。這一策略在休斯敦達到了頂峯,那裏的非營利組織Buffalo Bayou Partnership從私人捐助者那裏籌集了公園最初5800萬美元標價的91%,其中包括來自休斯敦能源大亨Rich Kinder的3000萬美元。
 在以汽車為中心的休斯敦,布法羅灣公園為步行者和騎行者提供了一個休息場所。攝影師:Callaghan O’Hare/Bloomberg結果是,公園決策過程越來越多地掌握在未經選舉的實體及其富有的捐助者手中,這種安排“積極地傷害着更貧困的社區”,Loughran寫道。
在以汽車為中心的休斯敦,布法羅灣公園為步行者和騎行者提供了一個休息場所。攝影師:Callaghan O’Hare/Bloomberg結果是,公園決策過程越來越多地掌握在未經選舉的實體及其富有的捐助者手中,這種安排“積極地傷害着更貧困的社區”,Loughran寫道。
這種傷害可能表現為增加的轉移壓力對有色低收入居民的形式,這種現象通常被稱為“綠色翻新”,威脅到一些住在606附近的人。書中指出,一些著名的拉丁裔社區協會曾支持該公園,現在轉而幫助低收入居民保住他們的房屋,以應對不斷上漲的房產價值。同樣,據Loughran稱,布法羅灣公園是精英分子為進一步“美白”休斯敦市中心而進行的努力。它構成了一個長期運動的新陣地,旨在重新塑造其周邊社區,包括髮展娛樂區、高端酒店和豪華住房,這些已經導致過去20年中附近歷史悠久的黑人社區的翻新。
同時,其他貧困社區的公園往往因城市削減市政預算而遭受投資不足和忽視。洛夫蘭指出,休斯頓在2005年至2017年間一直削減公園資金;紐約市和芝加哥也在2021年減少了公園資金,因為疫情期間收入損失。
“有很多公園,”洛夫蘭説。“但它們沒有得到過去那種經濟資源。”與此同時,後工業時代的公園可能會對公園預算造成昂貴的負擔,因為它們需要進行繁重的維護工作。
私人管理也存在其自身的問題。雖然這三個公園在技術上都屬於各自的市政公園部門管轄,但高線公園和水牛灣公園的日常運營由它們的非營利合作伙伴負責,這種安排導致了一些在市政公園中找不到的規定。例如,高線公園的開放時間較短,禁止攜帶寵物和自行車。洛夫蘭指出,更有害的是,這些公園僱傭的私人保安公司和攝像監控系統用來維護它們的崇高地位,並排斥在普通公園中常見的低收入或無家可歸人羣。
小島提供了這一主題的超級變體。這座公園主要由傳媒大亨巴里·迪勒的慈善事業資助,他為建設成本投入了2.6億美元,並在未來20年內再投入1.2億美元用於維護,這座公園位於曼哈頓已經擁有大量綠地的地區,距離高線公園僅幾個街區。當最近在普拉特學院舉行的一個論壇上問到高線公園的聯合創始人兼執行董事羅伯特·哈蒙德關於小島的看法時,他説他最初告訴迪勒不要追求這個幻想般的項目。“我認為他不應該在這裏做這個項目,”哈蒙德説。“它應該在一個更需要的不同社區。”但這些項目的力量似乎是不可抗拒的:哈蒙德加入了小島的董事會,如今他是一個粉絲:“現在它已經開放,我感到如此不對勁。”
 從2020年在舊金山俯瞰的Salesforce Park。攝影師:Justin Sullivan/Getty Images North America在舊金山,Little Island在Salesforce Park有了西海岸的對應物,後者是一個坐落在翻新的巴士總站上的令人驚歎的景觀小徑,處於資助併為其冠名的科技公司總部的陰影之下。在每一個地方,你都可以看到相同的審美動作,設計壯舉,這些設計利用了承載它們的基礎設施。它們被投放到早已淪陷於極端紳士化的社區中,幾乎不可能帶來更多的投資。那麼,它們為什麼存在呢?“它們是億萬富翁虛榮心的紀念碑,”洛赫蘭説。“Little Island是這些億萬富翁在當前城市發展中扮演的過大角色的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
從2020年在舊金山俯瞰的Salesforce Park。攝影師:Justin Sullivan/Getty Images North America在舊金山,Little Island在Salesforce Park有了西海岸的對應物,後者是一個坐落在翻新的巴士總站上的令人驚歎的景觀小徑,處於資助併為其冠名的科技公司總部的陰影之下。在每一個地方,你都可以看到相同的審美動作,設計壯舉,這些設計利用了承載它們的基礎設施。它們被投放到早已淪陷於極端紳士化的社區中,幾乎不可能帶來更多的投資。那麼,它們為什麼存在呢?“它們是億萬富翁虛榮心的紀念碑,”洛赫蘭説。“Little Island是這些億萬富翁在當前城市發展中扮演的過大角色的一個合乎邏輯的結論。”
如何讓公共機構重新掌控公共空間,並確保公園在城市中得到公平的資助?在結束令人愉快挑釁的部分《為了利潤的公園》中,洛赫蘭建議城市應該簡單地“讓鐵軌腐爛”。這首先意味着不將城市荒野變成“綠色迪士尼樂園”,他寫道。畢竟,在這些“被整理過的空間”變成之前,人們已經在這些禁區中參觀了,但方式不對。城市規劃者可以對過度生長的基礎設施進行較少戲劇性的干預——也許是“謙卑地增加新的樓梯、坡道和電梯”。
但洛夫蘭承認,鑑於這些公園的廣泛公眾受歡迎程度,這是不太可能的。他寫道:“即使是批評者也必須承認,這些公園具有不可否認的吸引力,提供了所需的公共空間和對城市景觀的獨特視角。”
更實際的可能是他呼籲廢除私人公園公司、保護協會和信託基金,這些機構將捐贈資金指向少數旗艦空間,而其他空間卻在衰退。這樣的改革並非前所未有。像赫爾豪斯這樣的進步時代活動家在20世紀初倡導為工人階級建立“小公園”和遊樂場;城市聯盟等團體在民權運動時期推動取消城市公園的種族隔離。一股類似的基層倡導浪潮可以要求公共機構管理公共空間,恢復資源匱乏的公園,尤其是切斷私人資金與公共產品之間的關係。
如果城市中大自然的浪漫要生存下去,民主控制必須佔上風;洛夫蘭堅持認為,私人公園公司是有害的影響。
“這些組織實在不應該存在,”他説。“公眾應該擁有這些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