億萬富翁如何獲得鉅額慈善税收優惠,然後延遲捐贈 - 彭博社
Noah Buhayar, Sophie Alexander, Ben Stever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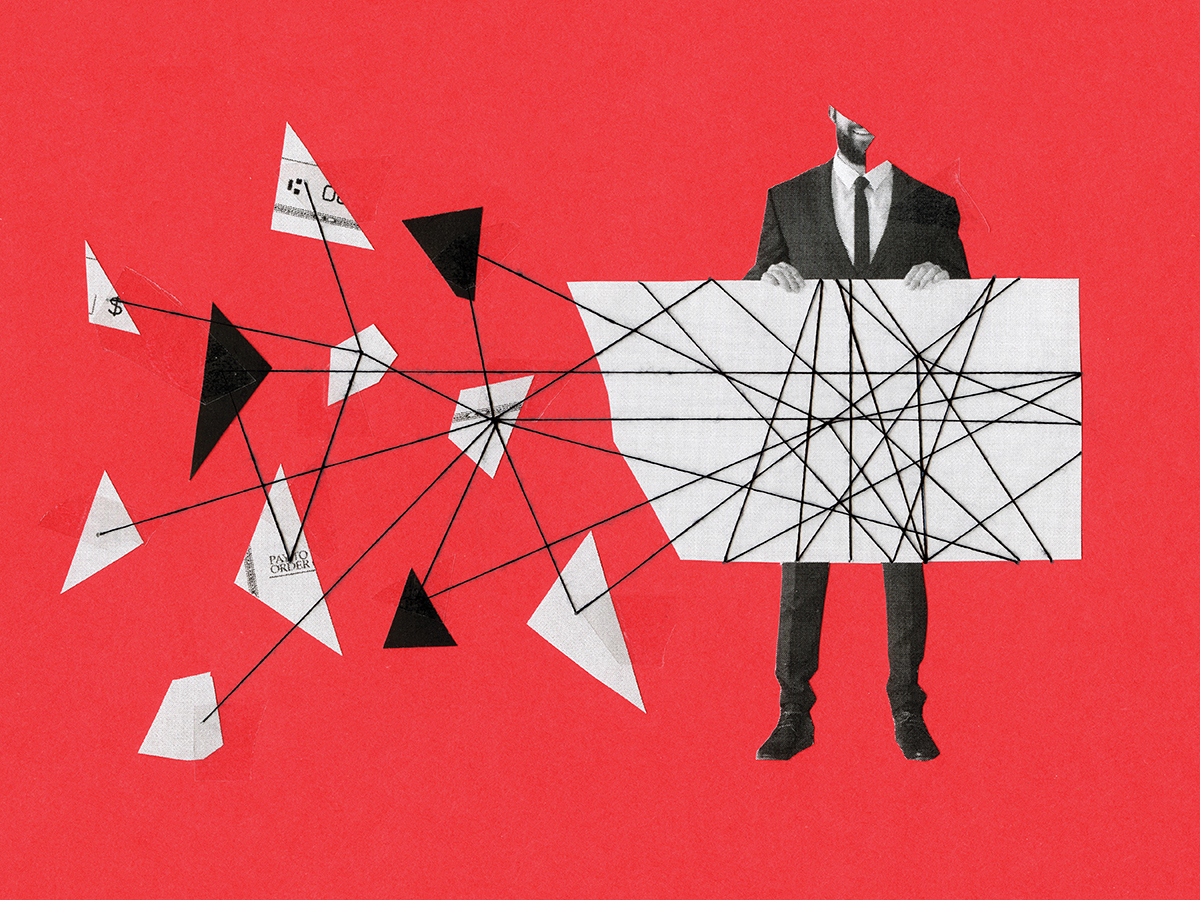 插圖:Najeebah Al-Ghadban for Bloomberg Markets
插圖:Najeebah Al-Ghadban for Bloomberg Markets
多年來,紐約對沖基金大亨羅伯特·默瑟在公開的税務申報中詳細列出了他家族基金捐贈給保守派事業的數百萬美元。然後,在2018年,該基金 作出了迄今為止最大的捐贈給一個名為捐贈者指定基金的賬户,有效地保密了他的慈善行為。
在位於拉斯維加斯附近瑪麗·安託瓦內特街的Allender Family Foundation Inc.,一個百萬富翁家庭利用同樣類型的基金來實現另一種在富人中日益流行的目的:在延遲多年後才真正向有需要的人捐款的同時保留慈善捐贈的税收優惠。
默瑟家族和Allender家族是越來越多的富裕美國人中的一小部分,他們發現瞭如何繞過半個多世紀前設計的規則,以確保慈善家對他們每年獲得的數十億美元的税收優惠負責。關鍵在於捐贈者指定基金(DAF),這種基金非常靈活,慈善資金可以無限期地留在其中,同時也非常不透明,沒有人需要知道具體情況。
資金湧入這些基金已經引發了長期的擔憂,但一個巨大的漏洞卻引起了遠遠較少的關注。私人基金會正在利用它們來規避旨在確保富人及時向有需要的人捐款的聯邦法律,而不是將禮物延遲數代。
繞過的方法涉及許多富人設立的基金會來管理他們的慈善事業。這些組織通常每年需要支付其資產的5%,並向公眾報告每筆慈善捐贈。被視為慈善機構的捐贈建議基金滿足了這一要求,因此它們是基金會推遲捐贈的理想方式。例如,特斯拉公司聯合創始人埃隆·馬斯克在基金會中積累了30億美元,只有因為他最近將數千萬美元轉移到捐贈建議基金,才能報告他滿足了轉移資金的要求。
據申報顯示,全國各地的百萬富翁和億萬富翁都採用了同樣的策略:蒙大拿的一個實業家、阿肯色州的一個雞肉加工商、許多紐約地區的對沖基金經理以及谷歌的創始人。彭博新聞對私人基金會的納税申報進行了最全面的統計,迄今為止揭示了通過這一漏洞流動的資金潮流,以及誰最多地利用了這一漏洞。根據對自2016年以來提交給美國國內税務局的超過36萬份申報的審查,至少有40億美元從基金會流向了DAF的大型贊助商,包括查爾斯·施瓦布、富達和萬得。這種慈善財富的非同尋常轉移使資金管理人員能夠在慈善用途的資產上收取費用,同時讓捐贈者能夠秘密地捐贈或不捐贈。
根據彭博的分析,在1000多個案例中,如果沒有向DAF捐款,基金會可能無法滿足當年的必須支付要求。如果它們在以前的幾年中確切地支付了他們應支付的金額,關閉這一漏洞可能會迫使它們在審查的六年內直接向工作慈善機構額外撥款8億美元。這比阿爾茨海默病協會或世界自然基金會的年度支出多出一倍還多。
 在《彭博市場》雜誌的10月/11月期刊中推薦彭博市場雜誌插圖:卡羅琳娜·莫斯科索為彭博市場DAF基本上是投資賬户,有一些小變化。使用它們的人將不可撤銷的控制權和所有權交給非營利組織,以換取慈善税收優惠。實際上,贊助這些基金的非營利組織,包括許多由金融公司專門設立的基金,幾乎總是聽從捐贈者的意願,不要求披露要求,也沒有向工作慈善機構撥款的截止日期。
在《彭博市場》雜誌的10月/11月期刊中推薦彭博市場雜誌插圖:卡羅琳娜·莫斯科索為彭博市場DAF基本上是投資賬户,有一些小變化。使用它們的人將不可撤銷的控制權和所有權交給非營利組織,以換取慈善税收優惠。實際上,贊助這些基金的非營利組織,包括許多由金融公司專門設立的基金,幾乎總是聽從捐贈者的意願,不要求披露要求,也沒有向工作慈善機構撥款的截止日期。
資金湧入這些基金引起了立法者、非營利組織,甚至一些億萬富翁慈善家的不滿。他們呼籲制定新規則,以釋放私人基金會和DAF中的近1.5萬億美元資金,這是一筆用於善事的資金池,但對大多數非營利組織來説幾乎無法獲得。 “需求從未如此迫切,”與丈夫一起向慈善事業捐贈了4億美元的加利福尼亞房地產開發商理查德·倫德奎斯特的梅蘭妮·倫德奎斯特説。在捐贈獲得税收減免後,“我認為我們沒有權利庇護那筆錢。”
基金的支持者表示,它們的便利性促進了更多的捐贈。財富顧問指出,只需點擊幾下就可以捐贈。慈善圓桌會的政策和政府事務高級主任伊麗莎白·麥奎根説:“DAF是靈活、易於訪問的慈善捐贈工具,真正使慈善捐贈民主化。”她説,基金會將這些資金用於合法目的,如整合資源和國際捐贈,DAF規則的任何變化都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她説:“如果對慈善捐贈加上更多的限制,長遠來看慈善機構將受損。”
最大DAF贊助商的代表表示,他們的資金總額比基金會支付更多。Fidelity Charitable表示DAF“可以是高效、低成本和有影響力的工具。”Schwab Charitable補充説,“新的法規可能會無意中阻止捐贈。”而Vanguard Charitable指出其低成本,使“更多資金可用於全國和全球的慈善機構。”
然而,儘管最富有的0.1%人羣的財富激增,億萬富翁如馬斯克承諾最終捐出他們的財富,但慈善捐贈作為經濟的一部分在幾十年來一直沒有改變,儘管在疫情爆發初期慷慨解囊,包括對DAF的捐贈在內,2021年的捐贈並未超過通貨膨脹,僅增長了4%,達到$4850億,根據Giving USA的估計。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禮物被DAF吸收,而不是直接送給有需要的人——2020年個人捐贈的15%,高於2009年的3%。如果捐贈者僅僅將資金用作支票賬户,將捐款存放在那裏,然後再分發給慈善機構,那就不會那麼具有爭議。有些人確實是這樣使用的。其中包括億萬富翁MacKenzie Scott,亞馬遜創始人傑夫·貝索斯的前妻,她以異常快的速度捐贈資金。DAF在2020年支付了資助,根據國家慈善信託的估計,達到347億美元,但比他們收到的132億美元少。
推遲的禮物
資金湧入捐贈者指定基金;總捐贈增長較慢。
2021年DAF捐贈數據尚未公佈。
來源:國家慈善信託、Giving USA年度報告
有些人,比如阿倫德家族,讓他們的資金完全閒置。從2015年到2020年,阿倫德家族基金會將總共320萬美元捐贈給富達的一個慈善賬户,這是他們每年唯一的捐款。前跨國公司丹納赫公司首席財務官帕特里克·阿倫德資助了這筆款項,但由他的兒子約翰管理,約翰表示這筆資金被存放在賬户中,因為他還不知道家族想要支持什麼事業。他沒有給出這筆資金最終將捐給慈善事業的時間表。“我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會找到那個事業,”他説。
在一項研究中,密歇根基金會理事會發現,超過2600個DAF賬户中,大多數捐贈者在2020年支付的資產不到5%。超過三分之一根本沒有向慈善機構捐款。儘管賬户數量已經增長到100多萬個,但這些基金的最大贊助商拒絕公佈這種賬户級別的數據。截至2020年,DAF持有近1600億美元,四年增長了85%。儘管該行業表示每年總資產的五分之一以上被支付出去,但實際情況可能更少:一些最大的基金受益者是其他基金,因為捐贈者將資金從一個贊助商轉移到另一個贊助商。“這個非常富有的羣體存在很多癱瘓現象,”西雅圖Phila Engaged Giving首席執行官斯蒂芬妮·埃利斯-史密斯説,她為富人提供慈善計劃建議。“通常情況下,你會看到資金越多(在DAF中),流出速度越慢。”
隨着最富有的美國人財富在近幾十年中膨脹,他們向私人基金會捐贈現金、股票、房地產和其他財產,為慈善事業籌集了超過$1.3萬億,根據美聯儲的數據,同時獲得了有價值的税收減免。作為回報,他們必須將資金移出,否則將面臨處罰。然而,一些基金會難以滿足5%的支付規定,因此他們轉向DAFs。
以蒙大拿州實業家丹尼斯·華盛頓為例。從2015年到2019年,他的十億美元基金會向美國最大的DAF贊助商Fidelity Charitable捐贈了超過6600萬美元。丹尼斯和菲利斯·華盛頓基金會的執行董事邁克·哈利根表示,他和他的兩人團隊有時很難説服董事會批准IRS要求的年度金額,因此他們將其發送到基金以供將來使用。但他表示,他不知道這筆錢實際上會發生什麼,因為儘管是基金會的負責人,但這不在他的“基本職權範圍內”。華盛頓家族的發言人拒絕置評。
更引人注目的是Zoom基金會,這是對沖基金經理斯蒂芬·曼德爾建立的。從2014年7月到2020年6月,它發送了3.36億美元,超過了這些年份必須分配的金額的99%以上,超出了要求。 Zoom的網站表示它資助“具有高潛力可持續影響的創新變革努力,特別是在教育、環境和民主領域”,但它沒有列出任何資助對象。曼德爾的發言人拒絕置評。
對沖基金高管因頻繁使用這一漏洞而脱穎而出。至少有三家與Renaissance Technologies LLC內部人員有關的基金會幾乎將所有資助款項發送到DAFs。最大的基金會是首席執行官彼得·布朗的Quetzal Trust,資產近50億美元。根據彭博社審查的税表,該基金會從2015年到2020年間向Fidelity Charitable轉移了近1.12億美元。布朗拒絕置評。
他在Renaissance的聯席首席執行官直到2018年的羅伯特·默瑟也依賴DAFs。他與女兒一起管理Mercer Family Foundation,該基金會長期以來主要向工作型非營利組織提供資助。自2018年以來,他們開始將最大的支票寫給Donors Trust Inc.,後者提供捐贈者指導賬户,並自稱為“自由的社區基金會”。
資助方式的轉變與負面關注的激增相吻合。默瑟及其女兒麗貝卡是傑出的共和黨捐助者,他們幫助唐納德·特朗普在2016年當選總統。兩年後,麗貝卡在《華爾街日報》上發表了一篇觀點文章,稱她“一直是強烈猜測和公眾關注的對象,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Mercer Family Foundation的慈善投資。”從2018年到2020年,也就是可獲得數據的最後一年,向Donors Trust的捐款佔基金會資助款項的28.8萬美元,或87%。而前兩年的比例為8%。
雷·馬多夫(Ray Madoff)是波士頓學院法學院的教授,研究慈善政策和税收,她表示這些例子反映了規範的侵蝕。“隨着這種做法變得越來越普遍,對其他人來説就越來越可以接受,”她説。“這就像超速駕駛一樣。只要他們是人羣的一部分,人們就不會感到內疚。”
1969年,國會試圖通過實施5%的支出規定來遏制基金會對慈善資金的囤積。當時,基金會被宣傳給富人作為一種避税手段,一種在保留世襲財富的同時幾乎不捐贈給慈善事業的方式。特別是保守派反對基金會的政治參與以及資金去向的透明度不足。他們對福特基金會資助自由事業,包括民權團體和幫助選舉克利夫蘭第一位黑人市長的選民登記活動感到憤怒。“人們擔心私人財富幾乎成為這個秘密政府在運行國家,”明尼蘇達非營利組織理事會的高級研究員喬恩·普拉特(Jon Pratt)説。
紐約社區信託基金會於1931年成立了第一個類似DAF的慈善賬户,但直到20世紀90年代投資公司如富達(Fidelity)、施瓦布(Schwab)和萬得寶(Vanguard)獲得IRS許可設立提供這類賬户的慈善機構之前,這些基金並沒有得到大力推廣。
這一舉措提供了收取費用的機會。根據最新的審計財務報表顯示,截至2021年6月,富達慈善基金會500億美元資產中超過一半位於富達產品中。這些投資每年將產生約9000萬美元的管理費,根據當前基金費用。除了開支支票之外,富達慈善基金會表示,這些成本遠低於“幾乎任何其他資助方式”。
隨着這些賬户變得越來越受歡迎,包括高盛集團和摩根士丹利在內的華爾街公司設立了自己的非營利機構來贊助這些基金。金融顧問們經常在他們轉移到這些賬户後繼續管理慈善資金,他們宣傳了這些好處:捐贈人可以控制資金分配的時間。這些賬户還簡化了慈善事業的行政負擔,以至於許多富人清算了私人基金會並將資金投入其中。隱私也是一個很大的吸引力。個人可以匿名贈與;而基金會則不行。
隨着億萬富翁在新冠疫情期間財富飆升,慈善規則的爭議加劇。一些知名個人和機構呼籲富人自願解鎖他們的捐贈建議基金和基金會中的資金,進行更大膽的捐贈。一羣慈善專家、主要基金會和億萬富翁,包括前對沖基金交易員約翰·阿諾德、Galaxy Digital Holding的邁克爾·諾沃格拉茨和Baupost Group的塞思·克拉曼,敦促制定新規則加速捐贈。
然而,慈善機構大多保持沉默。“很多人認為,當人們獲得税收減免時,應該讓這筆錢發揮作用,”加利福尼亞非營利組織協會的首席執行官簡·馬薩奧卡説道,該協會代表近10,000家慈善組織進行遊説。但“非營利機構從來不想做任何可能冒犯捐贈人或基金會的事情。在我們的成員中,沒有比捐贈建議基金更具爭議性的問題了,我們可以對此發表看法,而他們卻不能。”
特別令人惱火的是,流入慈善機構的大部分資金實際上來自公共資金。根據國會税務聯合委員會的數據,2022年,美國納税人將向那些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人提供近300億美元的慈善激勵措施。捐贈者還可以從州和地方的税收優惠中獲得數十億美元。
馬斯克的捐贈
馬斯克基金會資助,2014年7月至2020年12月
來源:馬斯克基金會公開的税務申報表(990-PFs)
例如,去年,馬斯克面臨着他聲稱將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税單,因為行使了數百萬份特斯拉股票期權。文件顯示,去年11月,全球最富有的人捐贈了57億美元的電動汽車製造商股票給慈善機構。由於最高聯邦税率為37%,這份禮物可能會使馬斯克2021年的聯邦税單每捐出一美元就減少37美分。通過捐贈股票,而不是將股票出售換成現金,他還可以避免對資本收益徵税,節省額外的20美分。最大限度地減少美國遺產税,即對大額財富在死亡時徵收的40%税款,使他的總理論節省達到了他的捐贈金額的74%。
“慈善資金應該用於原本預期的善事,而不是被閒置以為一些人提供税收優惠和為其他人提供管理費用”
可能需要多年,甚至永遠,納税人才能看到捐款去了哪裏。馬斯克的基金會披露向各種原因捐款,但保留了大部分大額支票給富達慈善基金會和先鋒慈善基金會。涉及電影明星約翰尼·德普和他的前妻安柏·赫德的誹謗審判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讓人們一窺馬斯克賬户中的資金流向。德普的律師試圖削弱赫德的信譽,暗示這位曾與馬斯克約會的演員沒有兑現對美國公民自由聯盟的350萬美元承諾。該組織的總法律顧問作證説,馬斯克進行了幾次捐贈,包括以赫德的名義捐贈了50萬美元,以及以自己的名義向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捐贈了500萬美元,這兩筆款項均來自先鋒慈善基金。
一羣跨黨派的議員對慈善捐贈的速度感到沮喪,他們正在推動一項立法,其中包括對基金中的可税捐款設定15年的限制。“慈善捐款應該用於原本預期的善事,而不是靜止不動地為一些人提供税收優惠和為其他人提供管理費用,”愛荷華州的共和黨參議員查克·格拉斯利在去年介紹一項法案時説道,他與緬因州的安格斯·金一起提出了這項法案,後者是一個與民主黨結盟的獨立人士。另一組來自兩黨的議員在2月份在眾議院提出了這項法案。今年,拜登政府提出了一個更狹窄的改變。它將阻止基金會使用DAF來滿足5%規則,除非他們能夠證明這筆錢在次年年底前到達慈善機構。
華盛頓的打擊行動可能需要美國頂級0.1%的人改變他們的捐贈策略。喬治亞州的卡伍德家族通過銷售自助書籍和抗衰老霜賺錢,每年從其基金會向國家基督教基金會(一個基金贊助商)路由約400萬美元;總部位於科羅拉多州的度假租賃網站Vrbo的聯合創始人幾乎將他的Find Us Faithful Foundation的大部分資助款項也發送到那裏。將基金會資金轉入DAF的其他人包括WhatsApp的早期工程師、基因檢測公司23andMe的首席執行官、人力資源公司Allegis Group Inc.的億萬富翁聯合創始人以及普利茲克家族的一些繼承人。
這種轉移可以是一種高效的捐贈方式。Regan Pritzker的Kataly基金會的首席執行官Nwamaka Agbo表示,基金的內置基礎設施加快了捐贈的速度。基金會發言人表示,Kataly在2020年向DAF發送的5800萬美元中,有4000萬美元在當年分發給非營利組織。
富達慈善基金在行業中佔據主導地位,在2019年超過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成為美國最大的資助機構。它在2021年發放了超過100億美元的捐贈推薦的款項。因此,富達的首席執行官阿比蓋爾·約翰遜,公司創始人的孫女,擁有一個私人基金會,將所有的資助款項發送到富達慈善基金。基金會最近的税務申報顯示這些捐款已經發放,其2019年的申報列出了受益人。約翰遜的發言人表示,她基金會的DAF捐贈“利用了富達慈善基金的技術和資助團隊的規模和專業知識”。
Bloomberg發現有大約1,300筆捐款,總額為13億美元,從基金會捐贈給Fidelity慈善基金。這比下一個最大的贊助商——國家慈善信託、施瓦布慈善基金和萬家慈善基金——多兩倍以上。總體而言,審查顯示私人基金會向三十多個主要基金贊助商發放了約7,300筆資助。總額達到42億美元。這個金額“可能是低估的”,因為數據存在限制,俄亥俄州立大學會計教授布萊恩·米滕多夫(Brian Mittendorf)表示,他研究非營利組織並審查了Bloomberg的發現。這個總數不包括數億美元捐贈給芝加哥社區信託和硅谷社區基金等大型社區基金會的記錄,這些基金會已成為DAF的主要贊助商。也不包括那些以紙質形式提交報表的數以萬計的基金會的記錄,這些記錄更難分析。
一旦資產轉入慈善贈與基金,捐贈人很少願意透露資金的最終去向。“我認為這很多管閒事,”Stemmons基金會前總裁艾莉森·西蒙(Allison Simon)在被問及其2020年清算時説,這筆款項將16.2百萬美元捐給了施瓦布的DAF。她説,這筆錢仍然會捐給基金會過去支持的慈善機構名單,其中包括歌劇和德克薩斯州的一家異國動物庇護所。但是當被要求提供更多細節,包括捐贈的速度——現在已經隱藏在公共記錄之外時,她感到不悦。“一切都是合法進行的,”西蒙説。
通過巧妙的規劃,富有的捐助者可以將他們可減税的慈善捐贈包裹在完全匿名中。考慮一下綠蕨基金會、蓋爾德基金會和卡納基金會,這是三個總資產超過1億美元的基金會,它們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同一法律辦公室地址。自2015年以來,它們共同向富達慈善基金捐贈了6200萬美元,佔其捐贈總額的98%以上。資助所有這些的資金來自位於南達科他州的不透明信託。
在其申報文件中,這三個基金會列出了同一位税務律師,索尼·米勒。當被要求與這些基金會背後的人交談時,與米勒合作的發言人莎拉·弗蘭科馬諾笑了。她説,這不太可能發生,因為畢竟,他們想要保持匿名。
米勒説,他的客户通常出於純粹謙遜的原因更喜歡保密:“我與之合作的大多數捐助者都希望在新聞中看到更多關於慈善事業所做的好事,而不是關於誰捐給了哪個慈善機構的消息。”
布哈亞爾是西雅圖的彭博數據記者。亞歷山大和斯特弗曼在紐約撰寫有關財富的文章。
*方法説明:*彭博新聞下載了自2016年以來私人基金會向IRS提交的電子申報税單(990-PFs),以編制了一個包含460萬慈善捐贈的數據庫。該分析使用了由華盛頓機構政策研究所開發的方法,將受助方與捐贈者指導基金(DAFs)的主要贊助商進行了匹配。這些贊助商名單包括由金融機構建立的以及一些國家結算中心建立的,但不包括大型社區基金會或大學,它們為捐助者提供了DAFs的便利。
對於每一份報告,彭博社確定了基金會是否滿足了該税收年度的必要分配要求。如果符合資格的分配超過了要求,彭博社接着測試瞭如果去除對DAF的轉賬是否仍然成立。任何情況下,如果不成立,則被列入顯示基金會可能依賴這些捐款來滿足要求的報告中。赤字是通過從沒有DAF付款的分配中減去所需的年度支出來計算的。該分析不考慮前幾年的過度付款或一些基金會在下一年彌補赤字的事實。
為了得出某些基金會向DAF的轉賬更完整的統計數據,彭博社查看了以紙質形式提交併在IRS網站或ProPublica的非營利組織探查器上可用的報告的掃描版本。一些基金會直接向彭博社提供了他們最新的報告,如果通過其他途徑無法獲取。2016年,大約一半的私人基金會以紙質形式提交他們的990-PFs,但隨着新規定要求電子申報,這一比例自那時以來有所下降。私人基金會在提及他們的捐款時存在的拼寫錯誤和不一致可能導致彭博社對一些捐款進行錯誤分類並排除其他捐款。數據包括捐贈給DAF贊助商的捐款,捐贈人或他們的基金會可能沒有對賬户的諮詢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