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蘇丹洪災造成一些首批永久氣候難民-彭博社
bloomberg
 蘇德濕地位於南蘇丹中心,面積大約是比利時的兩倍。
蘇德濕地位於南蘇丹中心,面積大約是比利時的兩倍。
攝影師:Patrick Meinhardt/AFP/Getty Images
身體虛弱只是其中最不重要的部分。是的,母親是一個癱瘓的人,躺在臨時筏上看不見,但孩子們眼睛明亮、身體強壯。小孩們淹到脖子,年長的女孩淹到胸部,拖着筏,上面堆滿了他們在世界上剩下的一切:幾隻雞,一些塑料椅子,桶,一把刀,一些破布和衣服。他們筋疲力盡,害怕在水中爬行的毒蛇,但他們不停地前行。他們的父親在前面涉水,帶着他們的嬰兒弟弟。
“我們受夠了水,”Nyalol Wang喊道。她28歲,是最大的姐姐。她不知道他們要去哪裏,他們只是想找到乾燥的土地。
這並不容易。
這個國家,方圓數百公里,都被水淹沒。
我們在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WFP)的兩棲車上旅行時遇到了這個家庭。這輛車有着大號輪胎,能在沼澤和濕地中運送一噸食品供應。我們犁過的水路一直延伸到地平線。在正常時期,這是一條從南蘇丹上尼羅州的本蒂烏鎮直通洛爾河的土路,全程約50公里。
這些並不是正常時期。南蘇丹在2019年和2020年經歷了百年一遇的暴雨。2021年8月,即使降雨量平均,土地仍然飽和,白尼羅河發生了洪水。洛爾河被水的重量阻擋住了。它開始倒流並衝破堤岸 —— 這是60年來最嚴重的洪水。這裏有大約一百萬人是世界上永久因氣候變化而流離失所的人羣之一,他們時常受到洪水和乾旱的威脅。
尼羅河有兩條主要支流。較短且水量更大的藍尼羅河從埃塞俄比亞高原跌落而下,而更長且更蜿蜒的白尼羅河從維多利亞湖流出,然後在蘇德的平原地區分成無數條河道,然後向北流入喀土穆與藍尼羅河匯合。去年的洪水淹沒了流入蘇德的所有支流和水道,蘇德是南蘇丹中心的濕地,面積約為57,000平方公里,是比利時的兩倍大。
廣闊的蘇德
濕地周圍的社區忍受着極端洪水和極端乾旱的循環
來源:自然地球
當世界領導人和外交官准備在埃及舉行本月的COP27氣候談判時,雨水再次降臨。根據聯合國駐南蘇丹特派團的説法,為了保護被洪水沖走的難民營地而修建的堤壩被沖垮並再次被淹沒。聯合國議程首次包括“損失和損害”,這是一個方法,根據這個方法,最容易受到氣候極端影響的發展中國家可能會向富裕排放國尋求補償。如果氣候損失的支付曾經存在過,它們很可能會流向這裏 — 也就是説,如果政府和援助機構有能力花這筆錢的話。
蘇德廣闊而停滯,難以穿透且危險。幾乎沒有建築物,甚至沒有英國殖民時期的磚結構。區委員會在樹下會見社區。南蘇丹外交部長邁伊克·鄧説:“我們辜負了那裏的人民。”
蘇德沼澤的每一幅地圖都已經過時:白尼羅河分成數百條充滿蒲草的河道,並且每個季節都在變化。關於水流和蒸騰的假設是基於2011年南蘇丹獨立前的建模。幾乎沒有運作良好的水文站,也幾乎沒有基於現場研究的科學。
然而,蘇德沼澤是地球上最豐富的生態系統之一,也是繼塞倫蓋蒂之後非洲第二大動物遷徙地。保護主義者的一項調查估計有8000頭大象,110萬隻白耳科布羚羊和豐富的鳥類。其下是相當於3吉兆噸碳的熱帶泥炭地。
南蘇丹數學家丹尼爾·阿克是一名領導區域保護倡議的人士,他表示:“更好地瞭解和保護蘇德對於人類和自然至關重要。”
 王氏家族將他們剩下的財物拖過水麪,距離洛河約10公里。攝影師:J.M. Ledgard世界糧食計劃署的援助人員繼續向洛爾前進,尋找需要緊急援助的偏遠社區。在每一個略微高起的乾燥土地上,他們發現成年人和兒童露宿其中。這些地方薄弱而危險,一米高,幾米寬,因燒木炭而變黑,散發着從水中捕撈的魚的腥臭,這些魚被剖開晾乾而未加鹽。
王氏家族將他們剩下的財物拖過水麪,距離洛河約10公里。攝影師:J.M. Ledgard世界糧食計劃署的援助人員繼續向洛爾前進,尋找需要緊急援助的偏遠社區。在每一個略微高起的乾燥土地上,他們發現成年人和兒童露宿其中。這些地方薄弱而危險,一米高,幾米寬,因燒木炭而變黑,散發着從水中捕撈的魚的腥臭,這些魚被剖開晾乾而未加鹽。
水是油黑色且靜止的。白蟻丘被淹沒數米深。小屋、坑洞、廢物和穿過灌木叢的赤腳小徑都從世界上消失了。那些明亮的綠色植被、鵜鶘、鶴、魚鷹、蜜蜂、蛇、拳頭大小的蝸牛,所有那些翠綠和生命,召喚出了與大眾想象中荒涼截然相反的景象。但這些人卻一無所有,也無處可去。
生存在沒有庇護所、足夠食物的情況下發生,並需要耗盡周圍的資源,因為能夠煮沸水的廉價能源意味着收集生物燃料,如糞便、草、木材和木炭。同樣具有破壞性的是牲畜的損失。家庭將需要六七年的時間來替換在洪水中喪生的牛。即使那時,許多家庭也將無法養活足夠數量的牛,以確保他們的任何一個孩子都能達成婚姻契約所需的20頭左右的牛。專家擔心,南蘇丹擁有的4000萬頭牲畜的季節性遷徙將在倖存的虛弱牲畜中傳播更多疾病。
不安全因素可能是一個更大的擔憂。隨着極端洪水和極端乾旱的循環在蘇德周圍加劇,僅僅保住牲畜就可能變得越來越困難。洪水意味着沒有莊稼、沒有動物、沒有庇護所,只能依賴食品援助。
負責緊急救援的聯合國官員表示,蘇德地區的許多社區無法到達,情況仍然緊張:運載食物到一些飢餓地區的駁船已被持槍歹徒駁回。隨着水位的下降,致命的搶奪牲畜活動已經恢復,丁卡人、努爾人和穆爾人武裝起來用機關槍殺死他們的敵人,有時還會帶走孩子和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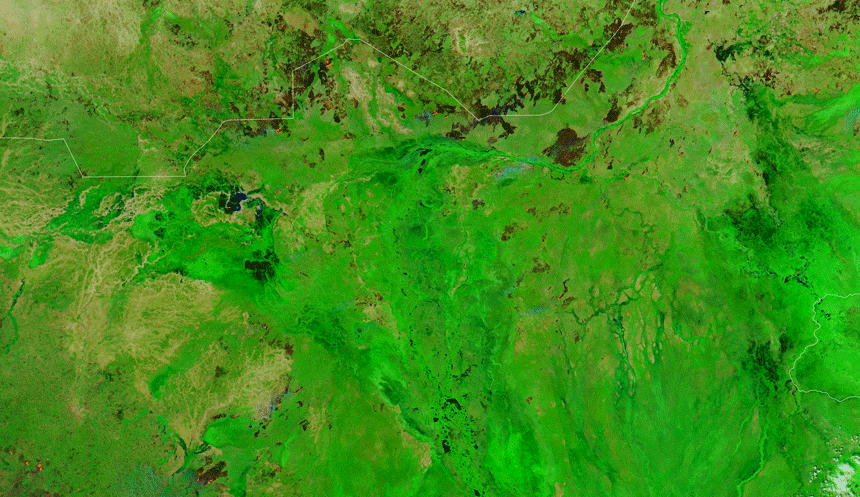 2019年12月6日(之前)南蘇丹的朱恩萊、聯合和上尼羅州的情況,與2021年12月6日(之後)的洪水相比。水域呈深藍色和黑色,飽和土壤呈淺藍色,植被呈鮮綠色。來源:勞倫·多芬/美國宇航局地球觀測站尼羅河流域的居民,被稱為尼羅人,一直在適應雨季和乾旱期,導致蘇德湖的擴張和收縮。但現在出現了一些問題。
2019年12月6日(之前)南蘇丹的朱恩萊、聯合和上尼羅州的情況,與2021年12月6日(之後)的洪水相比。水域呈深藍色和黑色,飽和土壤呈淺藍色,植被呈鮮綠色。來源:勞倫·多芬/美國宇航局地球觀測站尼羅河流域的居民,被稱為尼羅人,一直在適應雨季和乾旱期,導致蘇德湖的擴張和收縮。但現在出現了一些問題。
隨着印度洋表面温度的上升,白尼羅河的水流量增加,導致更多的雨水流入維多利亞湖流域。據聯合國稱,至少有80萬人因蘇德湖及周邊地區的洪水而流離失所。僅在本迪烏的營地就有約20萬人居住。
熱浪、瘧疾、腸道寄生蟲以及臘腸蠅傳播的睡眠病,解釋了本迪烏的海薩拉姆營地中人們的倦怠感。但主要原因是飢餓。每個人都飢腸轆轆。在南蘇丹,有130萬嬰兒患有營養不良,面臨着身體和智力發育的長期損害。孩子們早晚各喝一杯粥。成年人吃得更少。海薩拉姆的人們不願意烹飪在洪水中捕捉到的魚,因為有傳言稱附近的中國石油田污染了這些魚。更有可能的是,疾病傳播自人類和動物的糞便踩在灰塵中,隨着空氣傳播,以及死去的牛在它們倒下的帳篷外腐爛。
詹姆斯·馬尼亞羅普,51歲,展示了他的一頭牛蜷縮在自己的糞便中,快要斷氣。“我有200頭牛。50頭已經死了,還有更多正在死去。”
 蘇德地區的經濟和文化生活以牛為中心。在過去的一年中,大約有100萬頭牛死亡。攝影師:J.M. Ledgard他説,所有的牛都會同樣的走向:肝臟因飲用洪水而衰竭,腸道湧出直到動物倒下。
蘇德地區的經濟和文化生活以牛為中心。在過去的一年中,大約有100萬頭牛死亡。攝影師:J.M. Ledgard他説,所有的牛都會同樣的走向:肝臟因飲用洪水而衰竭,腸道湧出直到動物倒下。
在營地裏看不到一棵草。這也是氣候變化驅逐的特徵:人類擠在文化和經濟無法跟隨的地方。
聯合國援助組穿過了洛爾河,河水寬廣且在逐漸後退,發現河岸高地上有幾座小屋。它們是努爾人傳統的草屋,圓錐形且美麗。其中最大的是牛棚。在更幸福的時候,它本應該擠滿了牛,每頭牛都綁在木樁上。但那裏已經沒有活着的牛了,牛棚顯得詭異地空蕩蕩。
小屋的原住民已經逃走。幾名婦女和30個孩子被留在了那裏。他們幾乎無法生存。一個孩子因被蛇咬而患壞疽,另一個有顱骨骨折,其他人患有癲癇和哮喘。這些孩子從未上過學。他們靠魚、睡蓮的種子和野生胡椒果生存。婦女們最大的恐懼是孩子們會捱餓,但穿過洪水前往本提烏鎮(該地區唯一有效的庇護所)登記領取食物配給對他們來説太遠了。
目前尚不清楚像那些生活在蘇德周圍的人們未來會發生什麼。眼下的前景看起來災難性。
即使是一場平均降雨也意味着蘇德周圍的大部分土地仍然被淹沒,人們將無法返回他們的村莊或種植下一個季節的莊稼。在尼羅河東岸的朱瓦雷州,醫療慈善組織無國界醫生稱饑荒已經臨近,父母們只能用樹上的葉子餵養他們的孩子,無法獲得住所或清潔水。這種影響就像是一個緩慢而混亂的漩渦,蘇德周圍的人們被迫面對氣候變化和一個缺乏資金和能力為其人民服務的政府。
 蘇德東部邊緣的被淹沒的科利埃村。攝影師:J.M. Ledgard南蘇丹超過90%的收入依賴於石油收入。批評人士稱,大部分資金被用於償還債務和向政府附屬公司提供服務。國際危機組織估計,南蘇丹每天泵出的14萬桶石油中,只有4.5萬桶左右的石油產生收入。微薄的政府工資經常拖欠數年,並且基於未來多年石油銷售的預付款來解決。圍繞石油收入的爭奪是2013年導致40萬人喪生的內戰的部分原因。
蘇德東部邊緣的被淹沒的科利埃村。攝影師:J.M. Ledgard南蘇丹超過90%的收入依賴於石油收入。批評人士稱,大部分資金被用於償還債務和向政府附屬公司提供服務。國際危機組織估計,南蘇丹每天泵出的14萬桶石油中,只有4.5萬桶左右的石油產生收入。微薄的政府工資經常拖欠數年,並且基於未來多年石油銷售的預付款來解決。圍繞石油收入的爭奪是2013年導致40萬人喪生的內戰的部分原因。
未能從戰爭中走出去的失敗是美國等捐助國厭倦資助南蘇丹的原因之一。每個人都擔心安全問題。西方政府建議不要前往南蘇丹。很少有外國人能夠到達那裏,他們受到許可證、勒索和綁架威脅的阻礙。
全國各地都在發生戰鬥,包括南部的糧食產區。大部分殺戮是為了爭奪水源和牧場使用權,或者是為了明目張膽的搶劫,這阻止了人們在夜間活動。大約有10萬名士兵駐紮在沒有食物、藥品或工資的營地裏。
有充分理由認為,聯合國人道主義救援的中流砥柱世界糧食計劃是更具未來感的氣候適應途徑。世界糧食計劃為770萬南蘇丹人提供食物,占人口的63%,在受洪水影響的地區接近100%。在政府缺席的情況下,它必須修建道路和橋樑,清理和疏浚河流,將食物送到需要的地方。
世界糧食計劃擁有大規模的數字工具,包括400萬食品援助受益者的生物特徵識別。但它沒有足夠的資金來完成其工作。它希望為南蘇丹成年人提供每天2100卡路里的高粱、玉米、碘鹽、扁豆、豌豆和植物油,但它只能負擔每天分發1000卡路里。
這意味着在每個月的下半月,洪水受害者必須吃他們能夠找到的任何食物,否則就會捱餓。而且,由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使捐助資源緊張,這些半份配給可能會進一步減少:世界糧食計劃已向捐助國請求在2022年為南蘇丹工作提供11.5億美元,但只收到了約一半的資金。美國在7月份增加了額外資金,有效地使救援計劃繼續運作,即使它“哀嘆”南蘇丹政府的無效性。但氣候變化可能會使成本逐年增加。燃料和小麥成本的上升意味着世界糧食計劃將停止向170萬受益者提供食物,並終止之前被認為是挽救生命的兒童餵養工作。
“我們已經讓那裏的人民失望了”
這種人道主義分流將導致食品不安全性顯著增加,出現災難性飢餓的局部地區,根據世界糧食計劃署。危機狀態下沒有資源用於增強社區對氣候變化的適應能力,包括改善農業、排水、清潔飲用水、改善氣象和農業數據,以及發展共同資產,如井和糧倉。
缺乏資金和興趣使得更難實施大型基礎設施項目,這些項目可以在未來十年內控制白尼羅河並保護蘇德。大多數南蘇丹官員希望在靠近烏干達邊境的富拉急流處修建一座大壩。挪威顧問估計修建成本為14億美元,發電量為890兆瓦,是南蘇丹整個發電量的兩倍多。這也不到加利福尼亞州發電量的1%。但是,安全形勢進一步惡化和2030年之前氣温預計增加0.4攝氏度可能會使該項目難以融資和建設。相反,一套設計良好的堤壩系統,通過衞星數據進行適當管理並種植樹木,可能會有所幫助。疏浚、河道直線化以及將水引入渠道和水庫也可能有所幫助。
正在沙姆沙伊赫舉行的第27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預計將於11月18日結束,這應該是一個解決南蘇丹等地氣候變化危機的機會。首次在峯會上進行的有關損失與損害的正式談判得到了埃及東道主和最大的談判集團G-77+中國的緊迫性支持。在第一週,至少有三個富裕國家的參與者,丹麥、德國和奧地利,已經提供了數百萬美元的資金。但即使是推動這一舉措的國家也不指望在2024年之前支付款項 —— 甚至那也遠非確定。
支持損失賠償的人士中可能存在競爭性優先事項。埃及還表示優先確保從白尼羅河獲得更大的水流量,包括通過完成旨在繞過蘇德的瓊利運河項目。挖掘運河的機器在1983年的內戰中被摧毀。埃及認為該項目可以使其水資源增加7%。
這可能威脅到蘇德的存在,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估計,蘇德每年可以為南蘇丹經濟提供價值10億美元的服務,主要是在保護多樣性、調節水源和更好地管理升温方面。
人口增長也成為一個漩渦。當英國工程師在19世紀80年代開始控制埃及尼羅河水域以改善灌溉和防洪時,埃及的人口為700萬。現在已經達到1.05億,預計到2050年將達到1.6億。南蘇丹的人口增長甚至更快,從1980年的400萬增長到今天的1140萬。聯合國表示,人口增長與糟糕的治理和不安全局勢相結合,正在使人們面臨風險。
世界並非完全漠不關心。2023年,包括教皇方濟各和坎特伯雷大主教賈斯汀·韋爾比在內的宗教領袖將訪問南蘇丹進行和平使命。他們預計將強調氣候正義,以及儘管南蘇丹在温室氣體排放方面只是一個較小的排放國,但其農業、林業和交通都受到了氣候變化的影響。
但圍繞氣候危機的幫助並未及時到來。發達經濟體在2009年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承諾向新興經濟體提供每年1000億美元的資金,但這一承諾並未兑現。這只是轉型經濟體邁向零碳並使世界保持在工業化前水平以上增加2攝氏度的所需資金的一小部分,正如《巴黎協定》所規定的。
到2050年,非洲將有22億人口 —— 佔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接近一半的兒童。然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歷史碳排放僅佔0.55%。對於南蘇丹來説,這種差異甚至更大。自1850年以來,該國的歷史碳排放量為35兆噸,而美國為509吉兆噸。
南蘇丹有潛力,80%的國土適合種植經濟作物。但自獨立以來,大多數農業投資都失敗了,而且沒有跡象表明捐助者或政府準備在未來十年面對不斷升温的氣候時思考一致且緊急的新解決方案。
世界銀行表示,未來幾十年內,有8600萬非洲人可能因氣候變化而無家可歸。蘇德周圍的流離失所者是第一波。他們受到的對待方式可能會成為全球氣候變暖受害者的標準反應:提供足夠的資源維持生存,但沒有持久的解決方案。
J.M. Ledgard 是一位小説家和技術專家,專注於新興經濟體的可擴展人工智能和機器人解決方案。此前,他是《經濟學人》的非洲駐地記者。
本故事得到了普利策中心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