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器帶來的世界和平還能走多遠?_風聞
新潮沉思录-新潮沉思录官方账号-2022-01-15 21:12
文 | acel rovsion
“戰爭並非是與其他事物無關聯的行為,而是國家政策的表現,是推行國家政策的另一種手段。國家的性質改變了,政策也就改變了,因而戰爭的性質也改變了。”
——列寧《克勞塞維茨“戰爭論”一書摘錄和批註》
今年1月3日, 中、法、俄、英、美五個核武器國家領導人發表關於防止核戰爭與避免軍備競賽的聯合聲明。聲明一致認為,“避免核武器國家間爆發戰爭和減少戰略風險是我們的首要責任”,並申明核戰爭“打不贏,也打不得”。 這條新聞引發了全球輿論的討論,不管聲明背後的實際發起動機為何,很多人都願意將其視為在當前全球危機和衝突引發的不確定風險性大增的情況下,五常國家一起做的一個兜底性聲明。
後疫情時代,無論是中美在太平洋地區,中國和印度,還是美歐與俄羅斯圍繞烏克蘭和中東,這幾個地區的衝突風險都因為疫情帶來的危機而顯著升高。核戰爭“打不贏,也打不得”的表述,既是核大國的意願,也是變相重申了核威懾的有效性。 顯然,在達成了不會發生核戰爭,不會出現戰略誤判的默契下,常規衝突的可能性也將進一步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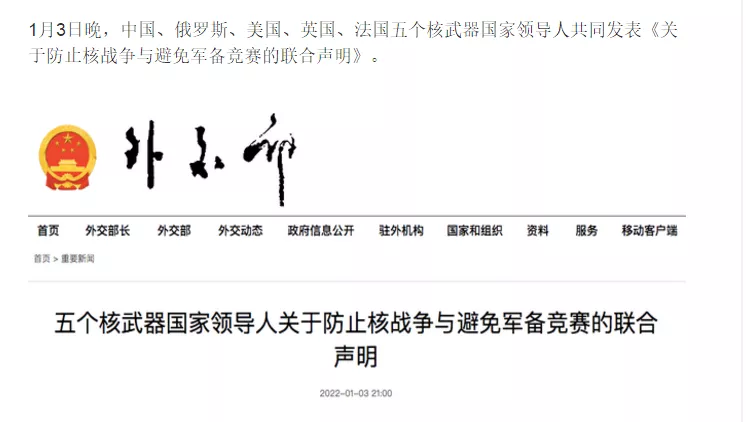
今天我們聊聊政治學和社會學視角中對於戰爭的發生和戰爭形態等等的分析。
近現代“政治——戰爭關係”理論起源
讀者們可能都知道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這本書是西方近代軍事理論的鼻祖,其中的核心思想“戰爭是政治的延續”更是影響深遠。早期的政治學和社會學學者們對戰爭的看法幾乎都是從克勞塞維茨這個論斷的基礎上去闡發的。
兩次世界大戰間隙中,產生了恩斯特·榮格爾的《總動員》(Totale Mobilmachung, 1930)和魯登道夫《總體戰》(Der totale Krieg, 1936) 。這類軍事思想著作也影響到了政治學界,像德國的卡爾·施米特這類政治思想家,就把進行一次總體戰爭的潛力**,或者説能夠進行一次戰爭總體動員能力視為一個主權政治機器最重要的特徵。**兩次大戰期間的這類思想家,把戰爭視為一種主權政治機器間必然發生的事件,這個前提下,政治就變成了能夠審慎地獲得多少迴旋餘的一種遊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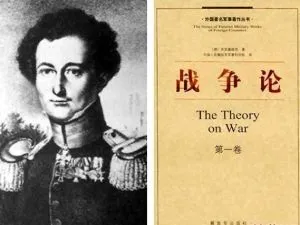
在施米特看來,陸戰的動員模式尤其是主權政治機器的象徵。陸戰總動員是一種共同體內部利益整合的總體化建構——內部政治代表性整合為一個機器,內部共同認同整合為一個整體人格,陸戰總體動員代表歐洲主權機器或者民族國家最大限度的內部政治整合能力和基礎治理能力。
海戰在施米特看來與陸戰有所區別。海戰的動員模式是利益驅動的外部性行為,無論是關於宗教的輸出、貿易網絡的安全還有最重要的利益條約體系的建構。在海戰體系中,主權機器更類似於一個服務於貿易網絡體系的公共參與者或者秩序締造者,尤其是殖民時代的全球海戰,無論是保護殖民據點還是貿易貨棧,或者是和某些地區的強制性條約,它都帶有更強的資本主義屬性和政治利益變現的特性。
對於歷來的海權大國來説,近海防禦和本土安全反而是整個海軍動員體系裏面最不重要的一部分,而是通過軍事存在保證其建構的資本主義總體世界體系的存續。相對而言,陸戰是關乎主權結構的,而海戰是關乎於世界體系的。
這也是英國和美國這類海權大國與傳統陸權大國的戰略擴張需求的本質差別。陸權相對於海外間接利益和世界貿易網絡更在乎主權的強度和本土的安全性,而海權反過來,行為上更在乎貿易網絡,世界框架和所謂的共同安全承諾。

冷戰後期開始,全球化成為主流趨勢,各國經濟貿易聯繫日益廣泛緊密。美國政治學家理查德·羅斯克蘭斯認為在全球化世界這個規範狀態下,主權機器國家的總體戰略定製要面向兩個基礎,一是國內政治基礎的財政-政黨聯盟,一是貿易網絡構成的全球化世界的規範性。
在全球化的規範狀態下,主權機器就不再是施米特理論中的抽象化個體或者説單一的行動主體,它是許多團體利益訴求的競合以及妥協,同時也存在組織內部結構複雜帶來的政策反覆和服務於國內政治需求的外交姿態,全球化規範狀態下,主權機器核心的基礎戰略能力是制度適應性(constitutional fitness),戰略目標需要服務於秩序的維持和有效的軍事風險管控,這依賴的是共同規範和安全底線承諾的不斷完善,這個理論也符合冷戰結束以後全球國要主權國家機器間的行動趨勢。
戰爭與秩序——脆弱的恐怖平衡
然而需要直面的是,戰爭從來既是秩序的破壞者,也是秩序的建構者。德國社會學家維爾納·桑巴特在其關於資本主義與戰爭關係的著作中對此有所總結。前現代的宗教戰爭對農業社會生產資料和土地增值造成破壞,但同時也成了資本主義催化劑,戰爭帶來的政治集中產生了絕對主義的王國和憲政主義的現代民族國家,集中性的政治整合帶來的對內產權制度保障和基本國土安全保障,曾經的自由商貿城市聯盟的模式被18-19世紀民族國家框架的權力所整合,帶來了更為完備的資產階級法權和所有制,並確立了穩定的生產模式和商貿信用體系,而戰爭本身也成為了這個秩序建構的始作俑者,同時驅動着這個體系走向更為瘋狂的殖民帝國時代。
國家間戰後秩序建立的約束從維也納體系開始延續到後冷戰時代,從聯合國框架到諸多國家集團峯會構成的戰後秩序,都是戰爭衝突(包含冷戰軍事對抗)帶來的兩面性的體現,冷戰史上的邊緣利益帶來的地區軍事衝突既導致秩序的鬆動,最終又縫合了秩序本身。大國協調機制和軍事控制體系被用來管控可能的核戰爭,但是核平衡和核威懾的邊緣博弈反而又成了大國協調的基礎——因為總體戰爭的後果被無限拔高,以至於國家間也必須建立總體性的可控關係。

**戰爭與秩序的辯證關係形成了一種脆弱的恐怖平衡,**同時靠着全球化幾十年的繁榮,給這種恐怖平衡蒙上了一層帶有普遍主義和世界性理想的所謂“和平”假象,這種“和平”假象又影響了諸多文化產物和人文思想。可以説,當今的跨國資本主義和全球化價值鏈模式本身,既是依附於這種脆弱的恐怖平衡之上,它們的存在本身也可能隨時摧毀這種平衡,成為新一輪戰爭的催化劑。
我們可以從當代政治學中的現實主義視角來窺見這種風險。美國國際關係學家戴爾·科普蘭在《大戰的起源》一書中認為當代戰爭最大的風險在於,戰爭能力(包含軍事能力和全球軍事態勢)尚且保持優勢,但是經濟、人口等綜合國力長時間來看已經慢慢趨於衰落的國家和新興超級大國之間的關係,説白了就是當代戰爭最可能的發生因素是潛在性衰退的先發國家(尚未全面衰退)對全面崛起的新興國家會採取預防性遏制策略,運用一切積極的強硬手段來維持自身的優勢,有強烈的軍事冒險主義傾向,從而捲入異常高風險的戰爭化衝突之中,即使這種戰爭只停留在戰略威懾上。
這種觀點和國際關係理論中傳統的“多極-兩極穩定結構”與霸權交替論者倡導的新興國家挑戰論都不同,但卻非常符合後冷戰時代的情況,**尤其符合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美國是後冷戰時代全球化和跨國資本的主導者,但中國藉着全球化趨勢快速崛起,被美國認為對自身造成了威脅,於是動用除熱戰外的一切手段對中國進行打壓遏制,甚至親自讓全球化趨勢出現倒退。

全球化時代一個很常見的論調是,全球化中各國經濟你中有我互相依賴,價值鏈供應鏈深度咬合,這種經濟依賴關係可以有效降低戰爭風險。但在科普蘭看來,當未來的貿易和投資態勢的預期趨於負面的時候,在利益和脆弱性的權衡之中,即使是理性國家假設下,也會考慮通過高風險和高損失的策略來發動上述提到的預防性戰爭,最起碼也有強硬且基於軍事行動基礎的外交威懾,通過增大不確定性來試圖尋求到扭轉負面預期的時機,經濟——安全之間來回搖擺的利益考量就出現在這種冒險主義激進策略中,尤其是在相互依賴性幾乎成為互補市場的國家間關係中,這種脆弱性-利益的考量就更為容易激進,並維持一種高度緊張的不信任和極度頻繁的經濟往來帶來的貌似矛盾的局面。這種預測分外符合貿易戰開啓後的中美關係。值得一提的是,《大戰的起源》這本書成書於上世紀九十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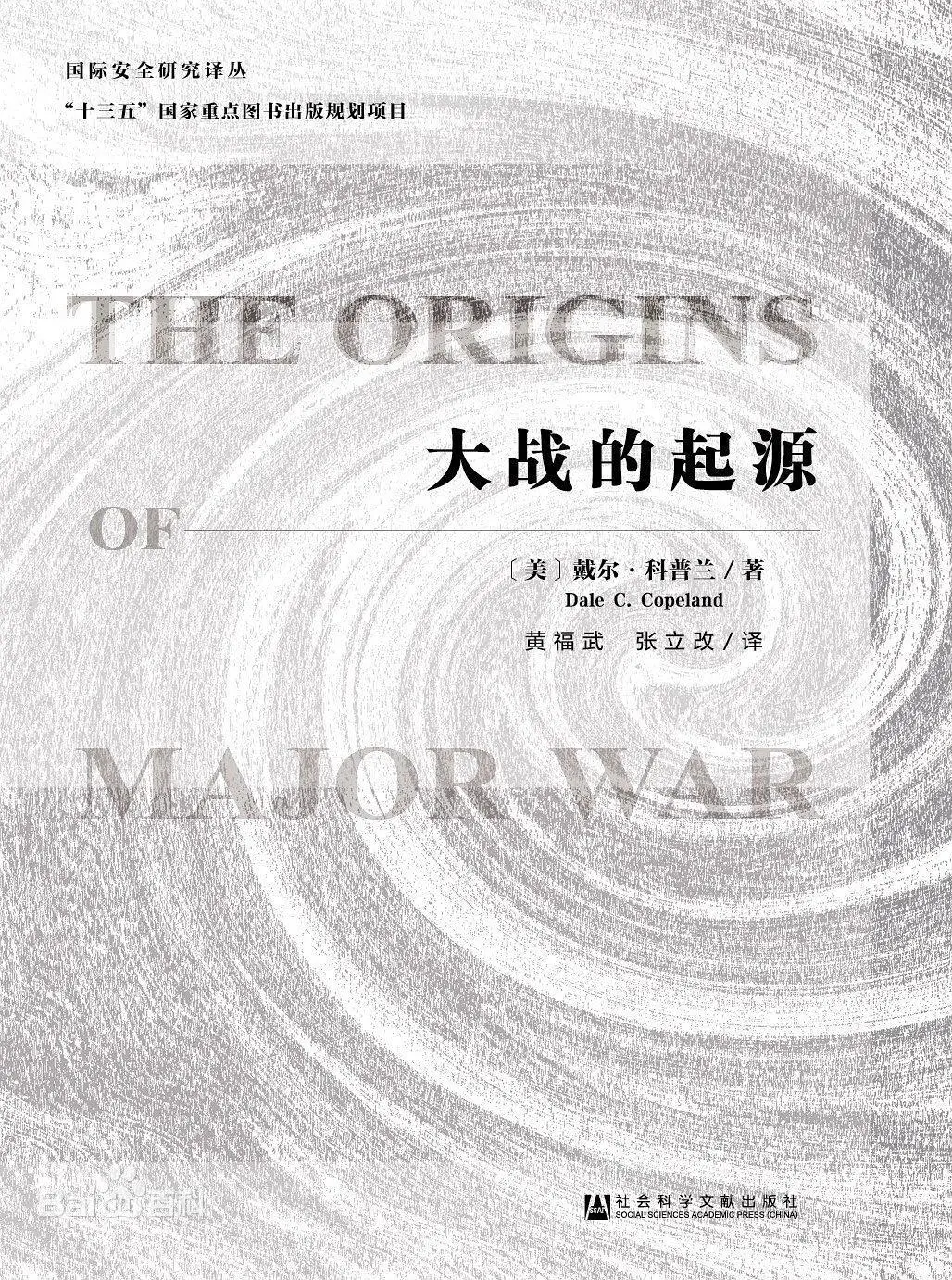
當代地緣戰爭風險
我們再從地緣政治的視角來考察當代戰爭的風險。當代國家體系中,地緣間的權力交疊至少包含這樣幾種形態,管轄權、資源利用權、邊境管制以及基於貿易開發和本土安全考量的衍生邊界。當代地緣政治的大體和平建立在殖民體系解體和民族自決後整體領土無爭議的基礎上,但也有大量因為歷史原因處於爭議狀態的領土歸屬及海洋邊界帶來軍事安全態勢引發的爭端。基於實在領土歸屬和戰略空間的衝突和外交糾葛仍然無處不在。
地緣政治中的戰略空間,是主權機器基於安全需求(包括防空識別區、經濟開發區歸屬等等)通過海洋公約、航行公約或者地區性共同行為規範以及共同安全承諾建立的邊緣。而這些建構性規範決定了地區內或者地緣間的戰略態勢、軍事行動規範、經濟合作框架、價值鏈體系以及地區整合議事規則,這些邊緣構成了各參與主體對本地區事務的基礎願景和共同決心。
而這些規範的存在,也使得我們探討戰爭的潛在性需要考慮至少三種利益衝突模式:**直接利益衝突、第三方關聯利益衝突和邊緣利益衝突。**如台灣問題,對中國來説屬於直接利益衝突,對美國屬於第三方關聯利益衝突。美、俄、中三方大博弈之間的印度和歐洲站位也屬於第三方利益衝突。
共同規範容易消解達成衝突控制的是直接利益衝突和第三方關聯利益衝突,雖然約束性和干涉能力不一定很強,但往往存在兜底的規則和共同表態。當代很多政治和國際關係學者認為,其中最容易導致風險管理失控和戰爭可能性的恰恰是邊緣利益的博弈。
所謂邊緣利益,這個概念可能可以接觸到核威懾理論時代的諸如布羅迪、謝林等人在核戰略上通過區分可置信威懾、確保相互摧毀、絆線或者風險生成器等基於核威懾平衡帶來的政治利益博弈和邊緣風險管控,基於核威懾平衡的基礎安全承諾,使得冷戰時期的軍事存在轉化成了相對可控的政治邊緣利益博弈。舉幾個具體的例子,美國在南海的各種小動作,中美在東南亞地區的博弈,以及島鏈和反島鏈戰略等都屬於邊緣利益。

持有邊緣利益的博弈藴藏巨大風險的國際關係學者們認為,邊緣利益的戰略預期很大程度上,決定於決策參與者對於中長期利益和短期利益的基礎願景、戰略決心,以及各方內部利益的競合,同時高壓和快速反應的決策模式也會帶來極大的偶然性,這使得邊緣博弈中導致的風險局勢會變得較為複雜,比如,**直接釋放敵意並合法化自己的越界行為,通過極限施壓或者製造政治議題脅迫對方放棄重要承諾等,這類基於總體目標的各種長時間的次生對抗和關聯國家對抗都會集中在我們的邊緣博弈中,**通過動態和長期性反覆挑戰現有規範,這使得邊緣博弈的對抗層面變得非常複雜,不僅包含經濟、軍事、外交、發展策略等大對抗層面,還有比如經濟層面的諸多次生層面,大到某個協調機制,小到某些貿易糾紛。
這種長期邊緣博弈帶來的決策資源高壓消耗反而容易放大博弈中的不確定性,短期戰略決心和政治願景的過度激進或者過度保守都可能在偶然層面導致戰爭,使得互相嵌合的規範體系和多層面對抗產生不可控的連鎖反應,這也是戰爭潛在性的發生機制。這使得,大國間地緣政治存在一種“極度危險的弧形反擊帶”。
當代國際體系崩潰可能導致的戰爭風險
這部分再以新制度主義國際範式的學術視角,談談當代國際體系崩潰導致戰爭的可能性。當代全球化體系的脆弱性來自於各國利益的動態變化以及內部發展不平衡,更重要的是還有體系內部對於原建構者的挑戰者出現,都會導致體系走向失衡,當體系走向失衡後,體系本身的承諾和預期被新的參與者利益預期所取代,在挑戰者那裏維持體系甚至存在長期的潛在損失。
而對於原建構者來説,維持現有體系的經濟收益、生產性投資以及防務投入都長期來看收益較低,也無力或者不再願意去維持現有體系,或者説對體系的義務遠高於體系帶來的現實收益。那麼體系內部的失衡就轉向變革狀態,變革的核心是新的規範要保障雙方最大限度的利益配置同時重新分配的權力位置。但是這種變革狀態會使得原有體系帶來的最低限度共同安全承諾不再有保障,重新配置過程中會誕生體系內部小團體的重新配置,無論是基於特定地區事務架構地區框架,或者基於特定目標建設特定盟友機制等等,而這些往往互相嵌合且利益複雜。

最重要的是,無論對於無力維持的建構者來説,與其坐視經濟和技術優勢進一步衰退導致的綜合國力衰退,以及基於安全承諾和政治信用不斷擴大的軍費維持,建構者會選擇退卻,留下體系內無法填補的政治空白,而這種行為會加劇建構者和挑戰者不斷對這種消耗戰博弈進行大規模投入,同時體系內的政治空白可能會誘發關聯性的體系內風險,這使得體系內部的相互依賴反而變成一種政治武器。**相對於維持長期戰略消耗的大規模軍事開支,軍事冒險主義反而會滋生在這種高消耗背景的戰略投機考量裏。**消耗戰博弈的戰爭風險雖然較低,但是反直覺的是,戰爭風險低是長期不間斷的防務投入和軍事科技競賽帶來的,它也是一種負的體系維持成本,如果這種消耗讓參與者進一步的退卻,放棄或者削弱風險控制承諾,這也會帶來極大的戰爭可能性。
結語
當代的戰爭很大程度是一種基於預期的極端政治行動,它誕生於既有的國際體系內部支配者和挑戰者之間的短期和中長期的勢力變化,戰爭的潛在要素涵蓋政治經濟等各個層面並覆蓋到次生領域,戰爭的選擇是在這種變化中基於成本-收益視角的投機性行為,現代國際體系的大國戰爭有風險管控失控的因素,也有體系失衡的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一種理性預期競合出來的非理性冒險行為,往往產生於高壓鬥爭中戰略決心和政治願景的研判結果。
秩序和破壞是永恆的辯證運動,沒有絕對的和平和戰爭狀態,在秩序的縫隙處永遠存在的戰爭的陰影,戰爭的有限性和潛在性也會帶來的新秩序的誕生和穩固。
我們不得不感謝核武器,因為核武器的存在,當代作為激進政治手段的戰爭是始終是有限戰爭,在不觸碰核戰略帶來的確保相互摧毀和最低限度的共同安全底線的情況下,基於有限政治目標、有限時間和有限停止點的戰爭。後面我們會再聊聊核戰略與現代性世界的形成。最後,讀者們也可以就着本文的標題,聊聊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