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製造“拽姐”宋智雅?_風聞
圈内新知-圈内新知官方账号-产业视角,资本逻辑,读懂文娱圈。2022-01-17 20:10

“拽姐”可複製,正是我們所要警惕的。
作者 | 李哩哩
編輯 | 月見
歲末年初,一位名叫宋智雅的韓國網紅,憑藉在戀愛綜藝《單身即地獄》中的“清醒言論”火爆全網。而隨着熱度越來越高,有網友扒出宋智雅疑似穿假貨,1月17號,宋智雅在ins上承認《單身即地獄》中所穿的部分衣物確實為假貨,併發出了手寫道歉信。一邊在節目內外營造富家千金人設,一邊又對“創作權和著作權的無知”道歉,“戀綜天菜”宋智雅還沒來得及發表更多“撩男語錄”,就要面臨人設崩塌的危險。
《魷魚遊戲》之後,這檔由Netflix操刀的韓國本土化戀愛綜藝節目《單身即地獄》再一次引起收視狂潮。而這次的流量密碼除了Netflix購買的高概念節目形式,就是成功打造了可愛又性感的“拽姐”宋智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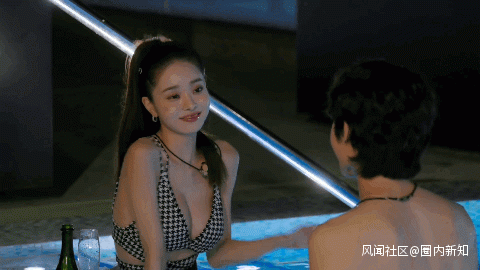
節目初始的五位男嘉賓,有三位都在第一天晚上將她視為心儀對象,一句“歐巴”讓男嘉賓立刻嘴角上揚。九天八晚的錄製時間,她三次組隊成功,獲得乘坐直升飛機從“地獄島”前往“天堂島”享受總統套房的待遇,在不能重複選擇的規則下,成為成功次數最多的嘉賓。
素人羣像節目容易使觀眾陷入“分不清臉”的觀看體驗,所以戀綜節目的解説普遍以女一、男一、綠茶姐、健身哥等標籤命名,而宋智雅則成了為數不多的在解説中也能擁有“名字”的嘉賓。
在她的灑脱下,一開始獲得好感的姜素妍成了“反面教材”,有異性緣的申芝燕第一晚投票一票未得,拽姐宋智雅在節目中遊刃有餘地大殺四方。在節目外,美妝博主研究她的妝容,時尚博主復刻她的穿搭,更多情感大師蒐集她的語錄彙總成“撩男攻略”,新一代“拽姐”冉冉升起。
一場資本與時代的陽謀迅速上場。宋智雅停更八個月的微博賬號,在第一期節目播出五天後宣佈迴歸。隨後12月28日,宋智雅在B站賬號更新了一期Vlog。29日,宋智雅入駐小紅書,不到24小時圈粉60萬。1月13日,入駐抖音,迄今為止發佈了一條視頻,粉絲量達到154.8萬。短短一個月內,僅在國內的社交平台上,宋智雅累計漲粉五百多萬。更有媒體爆出,宋智雅小紅書的一條廣告報價60萬,品牌代言費上漲到200萬—250萬之間。
爭議和追捧相伴而來,劇本、營銷、雌競……除了營銷與反營銷的激烈對抗,圍繞在宋智雅身上的話題也從節目本身宿命般地上升到兩性關係的探討。這樣一位深諳營銷門道、野心勃勃的“大網紅家”恰好踩中瞭如今東亞文化圈稀缺的女性價值,雖然不值得一比一效仿,但背後的邏輯值得深思。
假設這種追捧是營銷,那麼資本和市場已經把拽姐人設當成了新一輪的流量密碼;假設這場狂歡中真的存在大量“自來水”,説明的問題只多不少:不少人認可了這種雌競環境中的優勝劣汰。
歸根結底,當我們在討論宋智雅的獨立自由時,真的跳出了男性凝視了嗎?
拽姐們又回來了
男性凝視的討論在影視創作中由來已久,並且通常伴隨着“物化女性”“父權社會”等對立明顯的語境。在這種環境中誕生的宋智雅似乎打破了固化思維,她似乎擁有獨立審美,撩一撩頭髮坦蕩説出“這裏沒有我喜歡的類型”,並且這種拽姐形象還不是個例,在近期的國產影視劇中也是有跡可循的。
國產影視劇《小敏家》中秦海璐飾演的李萍,事業有成的中年富婆,關心女兒成長,八卦前夫戀情,在丈夫背叛、公司破產的雙重打擊下,選擇帶着丈夫的私生子重新再來,這個多少會被罵“聖母心氾濫”的舉動,在秦海璐的演繹下輕而易舉的獲得了觀眾的諒解,也塑造了一個複雜多面的“拽姐”,或者説“拽媽”。
同樣更符合“拽姐”定義的還有《愛很美味》中王菊扮演的夏夢,幫閨蜜在離婚現場懟小三,在專業領域吐槽劇本老套,遇到喜歡的男孩表白詢問“現在親你會不會……”時直接説“不會,親!”,還會在劇中自黑“現在連女團都開始演戲了”。這部30+都市女性羣像戲,工作、戀愛、生活什麼都沒耽誤,在豆瓣開出了8.4的高分。
再往前推,《司藤》裏智商和武力值都在線的司藤,不談戀愛能活得風生水起,談了戀愛也沒有人設崩塌;《突如其來的假期裏》不按常理出牌的榴蓮,將母親的骨灰暫放在花盆裏當養料;越來越多的非典型女性人物出現,影評自媒體切片計劃對近幾年的女性形象曾這樣總結道:“一種人性的複雜,一種對女人身上不同社會屬性的呈現,才是一個好的女性角色所應該具備的。”

從這一點出發,反觀宋智雅身上的矛盾感便不難理解。相比而言,宋智雅受爭議的點就在於女性的高光時刻出現在一檔戀愛綜藝裏,也就是這場追捧的弔詭之處:女性價值的體現仍然沒有逃離兩性關係的設定。這或許是“拽姐”形象最容易建立的戰場,卻不是有意義的參考答案。
來自男性的慾望凝視也並非完全全然是貶義,港片中奪人心魄的美大多出自男性導演之手,《花樣年華》中張曼玉32套旗袍的曼妙之美、《賭聖2》中邱淑貞烈焰紅唇的濃烈之美、《胭脂扣》中梅豔芳孤冷清絕的綺麗之美……在王家衞、王晶、關錦鵬等一眾導演的鏡頭下,成就了港片的黃金時代。
但現在我們需要更加豐富的女性模板,“拽姐形象”也需要更廣闊的定義空間。電影《兔子暴力》中,萬茜飾演的曲婷,年輕時是不良少女,生下女兒後遠走他鄉,在陰鬱的色調裏穿着黃色連衣裙風姿綽約,她擁有在為人母之外純粹的女性之美,雖然故事講得支離破碎,但並不妨礙意義的表達,更何況影片故事取材於真實案件。
電影《愛情神話》的最後,圍繞一個男人產生聯繫的三個女人,新歡、前妻、閨蜜,在失去好友後的恍惚與惋惜中,窩在沙發裏看那場牽絆好友一生的講述古羅馬時代的荒誕電影。當凡爾賽的片頭曲《Outro》響起時,恢弘壯大的背景音樂闖入了一地雞毛的現實生活,沒人關心晦澀難懂的劇情,三個女人在分享一支從屈臣氏購買的護手霜。誰又能説這不是拽姐當道最好的註腳。

由林心如主演並擔任製作人的台劇《華燈初上》也交上了不錯的答卷,或許懸疑色彩弱化了競爭的氛圍,從第一季的找死者到第二季的找兇手,《華燈初上》沒有苦心孤詣的惡女形象和千人一面的冗長敍事,卻刻畫了千姿百態的“美女”。在最易產生綺麗情色的酒吧場景裏,抽絲剝繭地暴露了少數女性羣體的生存現狀。從“女性製作者充分介入文化產品的生產過程”的角度來看,《華燈初上》無疑是成功的。
“大女主”是個偽命題
像宋智雅那樣在兩性關係中表現得遊刃有餘,至多隻是拽姐人設的一面而已,有探討意義的拽姐形象在國內影視劇歷史上並不稀缺。
劉曉慶主演的國內早期電視劇《武則天》、江姍主演的第一部國產偶像劇《過把癮》等經典女主都走出了探討女性社會屬性的第一步。三十年時尚輪迴,如今的拽姐形象還在長相、妝容、身體語言等外在條件上兜兜轉轉,畫皮不畫骨的創作比比皆是,經典如《甄嬛傳》也得用上挑的眼線強調王者歸來的事實。
儘管如此,這些大女主形象還是帶來了某種程度上的枷鎖鬆綁,在想象力朝着豐富和匱乏兩個極端無限延伸時,如今的大女主劇本陷入越來越深的固定套路:必須有纏綿悱惻的戀情主線、打怪升級的副本襯托,從章子怡的《上陽賦》到周冬雨的《千古玦塵》,三金影后的魅力在國產電視劇裏也得用三個男人同時愛她才能得以表現。反而不刻意強調“大女主”形象的《山海情》,有了真正的“大女主”意味。
拿着“大女主”劇本的宋智雅,在節目中表演了一整季拿捏男人的技巧,Vlog小課堂裏講的還是“什麼樣的女生最討男人喜歡”,跟風的一眾潮人執着兩性關係的明火又探討了什麼呢?八字眉和上挑眼線的搭配?還是宋智雅偶然提及的同款宣紙餃子?延續這一思路,“智雅風”刮到影視劇創作上,帶來的或許是影視審美的退化。
我們當然警惕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的僵化,討論女性價值從來沒有將情緒意義拒之門外,我們追求的女性獨立,也不是戰戰兢兢地繞開每一個男性喜好彰顯姿態,詩人餘秀華説,“女性主義怎麼了?女性主義難道就不能讓我為了一個男人而哭泣了嗎?”
也許從一開始“大女主”或者“拽姐”的意義就不純粹。在“大女主”的語境下,女性價值的討論權看似迴歸到了女性本身,實則是在主流風向裏進行了名為“獨立自由”的包裝後被精準投放了。北大教授戴錦華更是直言:所謂“大女主”只是一場復刻男性邏輯的幻夢。
黃蜀芹在談到《人·鬼·情》的創作時説,女性電影就像是在一個習慣了坐南朝北的建築裏開了東西向的窗。《人·鬼·情》是黃蜀芹1987年出品的劇情片。二十多年過去,當代影視劇探討的主題發生變化了嗎?
華中師範大學教授、影評人毛尖在採訪中提到:“回頭看國產影視,一些社會主義時期並不特別強調女性主義的電影反而特別了不起,比如《李雙雙》《女理髮師》《萬紫千紅總是春》,儘管女性問題仍然在家庭和男女關係之間展開,但絕不會在小情小愛上盤旋。每個女性角色都既是自己的主人公,也是別人的彈幕,她們彼此隱喻、彼此加持。每個人都沒有特別強調個性,她們有令人愉悦的羣體風格和形式。相比之下,我們今天的一些女性影視作品,實在有些美學倒退。”

從左至右:《李雙雙》《女理髮師》《萬紫千紅總是春》
警惕新一輪收割
另外需要警惕的是,宋智雅們不是沒有人設翻車的風險。在真正有作品、有實力的大咖面前,靠身材、容貌、氛圍感等營銷出來拽姐們剩下的只有華麗的表象。
拽姐風的次生效應無處不在,收割女性情緒價值的鐮刀已經悄然舉起。純欲、甜酷包括拽姐人設頻出的背後,是市場挖掘了更多女性獨特的閃光點,也是資本找到的另一種消費主義輸出渠道。
與其説這是女性意識的深度覺醒,不如説是找到了耽改被叫停之後影視綜藝新一輪的財富密碼。
比起宋智雅,另一個頗受國內影評人喜愛的韓國女演員金敏喜顯然更加豐富立體。韓國的輿論環境中,她多次與合作過的男演員戀愛,全民嘲弄男神“戀醜”;她高調宣佈與已婚導演熱戀,即使柏林影后加身也被追着罵。我們不主張有道德瑕疵的感情觀,但我們需要有彈性的討論空間。無論是宋智雅還是金敏喜,無論是韓流還是國潮,需要共同抵制的是以此做文章的人或羣體。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在影視劇市場上同樣適用。觀影人羣中女性地位提高是扭轉市場導向的因素之一。作為一個消費者,女性話語權在整個流行文化工業當中有着明顯提升,所以有越來越多的流行文化產品迎合這種趨勢被創造出來,大女主、耽美、甜寵劇都在這個框架內。但這種由消費能力所支撐,為了消費目的而生產的東西,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女性現實?
打着第一部聚焦獨居女性安全問題的翻拍電影《門鎖》,更像是販賣女性獨居恐懼,女主在面對未知危險不反抗、不報警的一系列操作被網友冠以“降智行為”,試圖從電影中共情的女性觀眾,眼睜睜看着後半段朝着越來越不現實的方向發展。包貝爾執導的《陽光姐妹淘》,一出為身患絕症的好友尋回青春回憶的劇情片,在“抄作業”式的翻拍中,沒有“girls help girls”的感動,只有爛俗的撒狗血套路。

打破這種以女性電影為名且由來已久的偏見,甚至比跳出男性凝視更加重要。戴錦華教授認為,電影行業在形成過程中成為了一個極端男權的產業,從產業結構、商業構造、勞動力結構意義上來説,成為一種結構意義上的父權產業。(這種結構)一直在鬆動,但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改變,向好的因素之一就是世界範圍內,文化產業中,女性工作者的全方位介入。
這與毛尖教授“真正的、來日方長”的女性主義不謀而合:女性創作者獲得掌鏡權,中年女演員獲得銀幕份額。這是與“大女主爽劇”的飽和式供給完全不同的邏輯,也是更值得期待的未來。
影視劇裏到底需要什麼樣的女性形象?文娛市場最通透的工作者或許也回答不了這個問題,但總有些“形而上”的東西可以一點點想象,就像毛尖教授在演講中所説:“我們的國產劇有自己的山、自己的海、自己的情感政策和自己的寬闊彈性,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