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學不起上海——疫情當下的基層困境_風聞
新潮沉思录-新潮沉思录官方账号-2022-01-18 22:24
文 | 劉夢龍
隨着春運的開啓,新一年的疫情防控又到了最嚴峻的時刻。如大家所知,在當前的疫情防控中,各地陸續出了不少問題。當前防疫所暴露的出的很多問題,不是防疫才有的,而是長期的歷史積弊。順便也針對如今網絡上頗有市場的如”上海等發達地區搞精準防控,不搞全民測核酸,值得全國學習”之類的論調來討論下,這裏面本質問題在哪,以及為什麼上海做法不應該推廣到一般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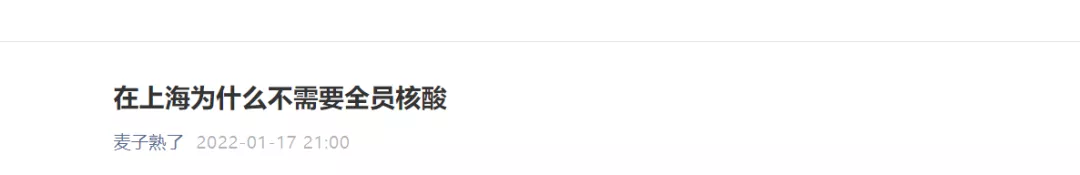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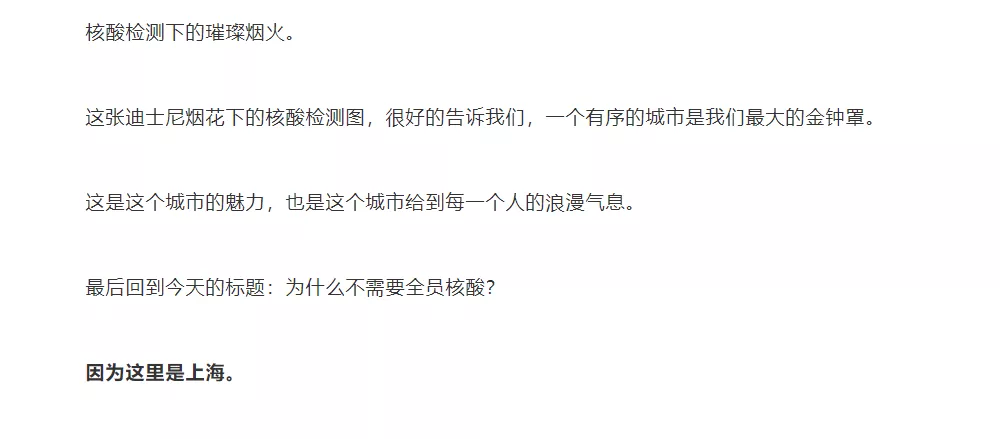

現在的大背景是過去那種烈火烹油的快速發展期已經結束,各個領域都進入了要啃骨頭的攻堅深水區。隨着高速增長轉變為高質量增長,大家所熟悉的傳統發展路徑與隨之而來的傳統治理方式都已經難以為繼。相對應的,就是中央挾空前的威望和力度,鋭意進取,不斷整頓,地方則在艱難磨合新型的彼此關係,而基層承受了轉型期的極大壓力,已經搖搖欲墜。疫情,作為黑天鵝,固然極大激化了這種轉型壓力,但説到底也只是把原來就有的問題強行逼到我們面前。
為什麼我們很多地方的抗疫在最近暴露出很多問題,説到底,疫情已經發展到第三年了,**但大多數地方在防疫上還是喜歡一廂情願地搞剛剛好,或者説叫最低限度的準備,這當然容易被疫情擊穿。**我們舉一個例子,疫情發展到今天,防疫預案各地都很完備了,參考吸收了很多一線的經驗。但從歷次的疫情來看,一切沒有實際運作過的預案,無論多完善都是會出問題的。而許多地方依然沒有實打實進行了全民參與的大規模防疫演練。不要説羣眾,幹部自己都不知道出事要去哪裏,做什麼。像某些地方,壓力一大罷工的健康碼,就是典型的剛好夠用產物。

這種情形,不是疫情以來才有的,更多是一種積習難改,是我們典型傳統地方社會治理的慣性。我們的地方行政,長久以來,總是在追求效費比,恨不得把政府當做公司來運營。最直接的體現,很多地方的安全生產,社會管理,有投入沒產出的領域,往往都是能糊弄則糊弄,老想着小錢辦大事,平時應付了事,不出事情不解決,一切等出事再説,硬生生把本應強勢的各種監察管理崗位逼成了極度弱勢的背鍋崗位。長此以往,就形成了我們的很多地方幹部賭性堅強,在面對新冠時也本能的選擇賭一把,甚至想賺一把。只是新冠疫情是不講政治,又難以掩蓋,才往往導致了一捅就穿的難堪局面。
當然,隨着國家督促體系的不斷完善,尤其是新冠疫情的不可控性,這種賭,很多地方的領導幹部心裏也是沒數的。但他們選擇的不是加大投入,夯實基礎,而是玩起了各種推卸責任的把戲。通過繁瑣又不切實際的重複勞動,這些中層領導既顯示了自己的重視,又把責任一層層加碼推給了下級,而這又進一步加劇了基層抗疫工作的消極怠工,混亂低效。
疫情是一個加速劑,把原來已經非常嚴重的治理積弊逼到人們面前。實事求是的説,近年來,一邊是基層減負的響亮口號,一邊是全方位的基層高壓態勢,給人的感覺,就是越治理,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反而越嚴重。這樣的情形,不能怪在疫情身上,更不會像某些人一廂情願的幻想,沒有疫情就恢復舊觀,天下太平了。而是隨着大環境的變化,中央治理體系改革進入深水區,過去的地方與中央生態已經維持不下去了。如今,地方已經沒有太好的應對辦法,在不知所措的情況下,只能儘自己所能的不斷加碼。
近幾年來,中央治理和過去有了極大差異,學界有人稱之為模糊化治理。過去,中央治理地方,主要依靠指標式的治理,你不管難不難,合不合實際,他都有一個明確的數字指標,做得到你就去做,做不到,你就去編,想做得好,你就去加碼。如今,典型像扶貧、宅改等領域,往往以一種任務式的命令下達,他給你一個任務底線,就像兩不愁三保障,具體的指標要由地方配套落實。而中央不斷強化的則是在落實過程中的監督,特別是垂直化監管,直接下到一線。
**隨着我國從高數量增長轉為高質量增長,一改過去那種唯指標論是有其必要的。但在這個轉型過程中,地方是很難受的,過去的平衡被中央帶頭揭破了。**表面上,地方獲得了一定的自由度,但越來越嚴格的監督,過去用來應付中央的舊辦法越來越不管用。地方常常摸不清中央的路數,它想做好,但不知道好的邊界在哪裏。只能靠過去的慣性,難免無限加碼,出現大規模的浮誇風,大躍進,這幾乎是一種官僚主義的本能。
類似防疫這種那些欠賬多,成本高的領域,過去往往靠賭,靠瞞,如今在中央的三令五申下,各地在近年來確實是進步了,投入了不少資源,但務虛逐利的行政慣性還是根深蒂固。而越來越嚴峻的經濟形勢,本就有限的資源越發收緊,結果就是聲勢大,雨點小,看似嚴厲的運動,真正落到基層,往往就停留在紙面上。
平時,我們常常覺得中央好,地方不好。好像社會主義的成分都體現在中央大政上,而地方更像開公司一樣,更加看重實際利益。中央看地方個個都像套取資金,陽奉陰違的貨色,但在地方看來,就是中央清貴,財政拿大頭,做事得好名聲,拿地方幹出來的功勞給自己進步,髒活累活都留給地方,吃肉喝湯是中央的,啃骨頭崩牙擦屁股都是地方的。幾百年來,京官和地方官的矛盾,彼此的看法,也差不多是這樣。
應該承認,和中央相比,地方有自己的困難,尤其是分税制改革奠定了中央的財政基石後,大部分三四線城市的縣域經濟嚴重依賴土地財政,往往是拆東牆補西牆。每一任官員,在不斷增長的指標下,要出成績,要推陳出新,就只能報喜不報憂,把成績拿走,把問題留給後任,逐漸積累成一座座無法收拾的屎山。
如今,肉眼可見的,中小城市所依賴的土地財政日益吃緊,內需整體不景氣,傳統的地方經營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了。在中央越來越強大的督查力度下,社會治理的投入卻在不斷增加,當前地方困難,根本上説,就一條,真沒錢了。
當然,這種沒錢是總的趨勢,而有些超級都市,經濟發達地區還是能維持,甚至分享全球疫情引爆的外貿經濟大景氣。一些發達的地區,他本身在社會治理上,因為資源餘量大,過去的欠賬就少些,可支配的力量就多些,所以他們的表現就好些,壓力就小些。就會出現,叫其他地區抗疫學上海之類的問題。**問題是其他地區,特別是佔絕大多數的三四線城市,現在是維持局面在咬牙死撐,處處吃緊,哪裏還有辦法學上海用超量人力,超量資源去快速堵漏。**而且話説回來,在當前疫情形勢嚴峻的情況下,上海的措施也不見得就沒有問題。當然這是另一個話題了,今天先不討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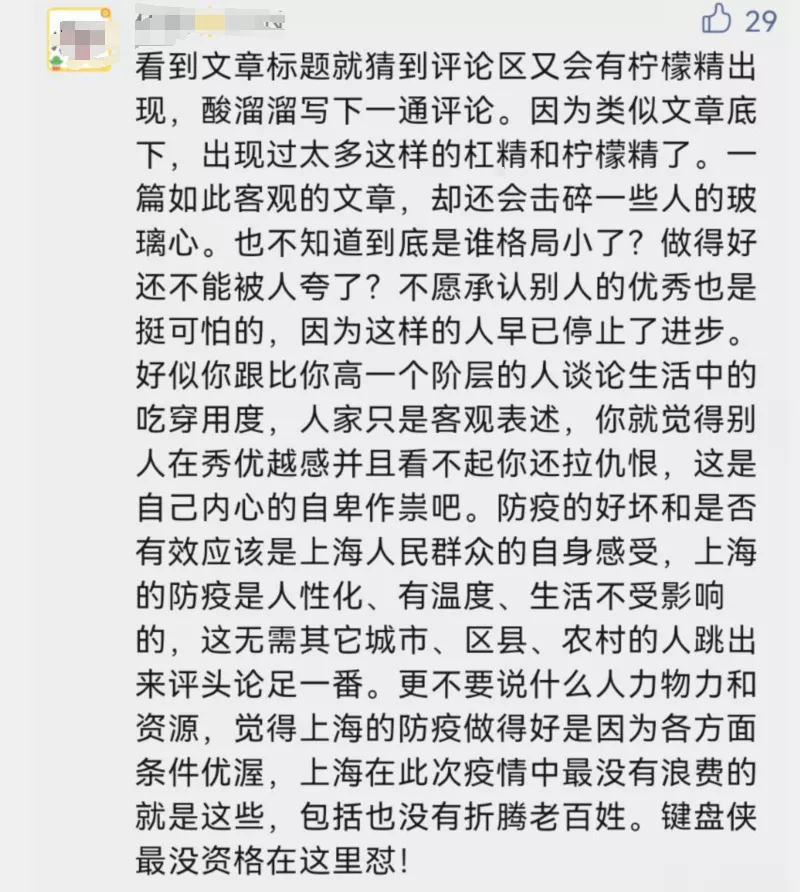
目前的大環境,就是地方想繼續苟,奈何中央不許,要逼地方去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去啃硬骨頭。
**應該説,當前中央地方都在搞治理轉型,但這種轉型還很粗糙,有很多不足,亟需磨合之處。**就像加強監督,尤其是垂直檢查,直接把中央意圖傳導的一線,肯定是大勢所趨。但哪怕中央治理從指標式轉向任務式,權責並沒有隨之分解,而是明顯的權力拿走,責任下移,使地方明顯感到壓力增大。現在的監察系統還是指標式的,就是奔着雞蛋裏挑骨頭去的,苛察之弊就更加明顯。逼的很多地方要把只能做到六七分的工作強行撐到十二分,就不得不作假,壓力層層傳導的基層一線,反而是苛察生弊。
尤其是在面臨解決歷史積弊這個難題上,地方本來就沒有好的辦法,又怕耗幹家底,得不償失,更經不起查。結果就是各地中層都在大搞上傳下達,責任分解,在把責任分擔給下級的同時,其實也削弱了自己的職能,任務都給下級做掉了?要你這個中層做什麼?幫倒忙嗎?於是另一個後果,就是很多中層,為了顯示自己的存在感,搞出亮點,**從不作為到亂作為,行政隨意性大,**拍腦袋作秀,進一步加劇了基層負擔,確實就幫了倒忙。
在中央對下管理日益扁平化的當代,動不動中央的會議就開到鄉村兩級,監督直接下到田間地頭。隨着技術的進步,監督的完善,中層的壓縮態勢在所難免。但以我們當前的管理架構來説,完全垂直管理還很不成熟,包括市縣一級的中層管理,還是必不可少的。只是中層往往積弊比基層更重,尤其是能上不能下,普遍存在看事的人多,辦事的人少。所以中層,尤其是中層的業務骨幹也苦,甚至不少比基層還苦。而現在,無論上層,中層,還是基層都一樣,説到底,都是缺人,都存在一方面人浮於事,一方面業務幹部極度緊缺。而越到基層,越內卷,越存在勞逸不均,選任不公的情形,逆淘汰越嚴重。
這種轉型的痛苦,最終都傳導到一線基層。於是,對待基層幹部就像二十世紀初推廣泰羅制,到處在搞極限施壓,試圖實現“在實行泰羅制的工廠裏,找不出一個多餘的工人,每個工人都像機器一樣一刻不停地工作。”這種擠壓,固然極大榨乾了基層的潛力,一時提高了業績水平,但勢必引起基層的極大反彈,從而造成以形式主義對抗形式主義,以消極怠工對抗極限施壓。這種緊繃的鏈條,試圖使幹部變成螺絲釘和數字,看上去一線幹部是一個個可以替換的螺絲釘,但所謂體制內,本身就決定了,基層幹部一旦躺平,並沒有好的辦法去應對,而大量長期在一線廝殺的基層幹部一旦崩斷,又是很難補充的。
經濟不景氣,使大量人試圖逃入體制內,而體制內新人沒有多久,就在往復折騰與疲軟中認清現實,失去熱情,開始分化。該跑官的跑官,該躺平的躺平,少量的老實人也越來越敷衍,各種編制看似迅速充實,但戰鬥力並沒有提高多少。隨着基層危機的不斷髮酵,與之對應的,就是一線工作開始越來越依靠體制外的力量,靠各種勞務派遣來試圖頂缺,應付的成分也越來越重。只要體制內的保底屬性不打破,這種情形就會不斷加劇,但要是連保底屬性都沒有,誰又會去一線基層自找苦吃呢?
説到底,這種狀態是不可持續的。現在的問題,主要還是面對中央的大調整,地方上連頭腦都沒有整理清楚,更不用説處置基層這種肢體末端。而處於改革的末端的基層,也只能是不斷小調保穩定,靠十個指頭去堵船板漏水,什麼時候出了大問題,什麼時候做大調整。
長久來基層的兩大痼疾,權責倒掛,長期過載,當前的地方困頓下,又極大加劇了這個問題。這不是靠每月加幾百塊錢能解決的。真正需要的是進一步規範行政流程,解決九龍治水的混亂,讓基層作為政策執行者回歸本職,並切實討論這種執行的合理限度在哪裏。
我們如果站在更長遠的角度看,就是整個地方體制已經不適應當代的變化了。烈火烹油,鮮花着錦的日子已經過去了。除了極個別的發達經濟圈還能依靠不斷流入的人才,資源,維持舊觀,絕大多數地區,日後難免要靠中央吃飯,而吃這口飯是不容易的。過去那種靠自我經營,自我發展追求進步,從而在中央手中維持一定獨立性,那種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局面已經持續不下去了。幾十年來,地方的公司化傾向,如今在不斷的整頓中,不得不收斂。未來,隨着行政的扁平化,中央的治理觸角將更深入一線,中央的權威不斷強化,地方更加依賴中央,也必須更加配合中央統籌發展,地方的自主性也將近一步收窄。
這種改變不僅僅是權力與社會治理結構的變化。在面臨越來越嚴峻內外部挑戰的當下,過去那種打補丁式的小修小補要讓步於更深層次的整體調整。更強的權威,才能帶動更深入的改革。面對長期積累的深層矛盾,過去很多被推給市場的東西,往往在地方治理中直接被忽略乃至變質分肥,而如今都被證明終究要回歸社會主義的本質。**這種整合不亞於在二戰風暴前夕的蘇聯所進行的努力,伴隨着巨大的痛苦,但不得不為。**而這一切,最終是要在越發急迫的未來歷史關頭的交鋒中見分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