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講壇】李盾:如果文化被抹平了,民族就沒了_風聞
CC讲坛-CC讲坛官方账号-创新引领未来,传播改变世界。2022-01-28 10:58
李盾
中國著名音樂劇製作人、德稻音樂劇大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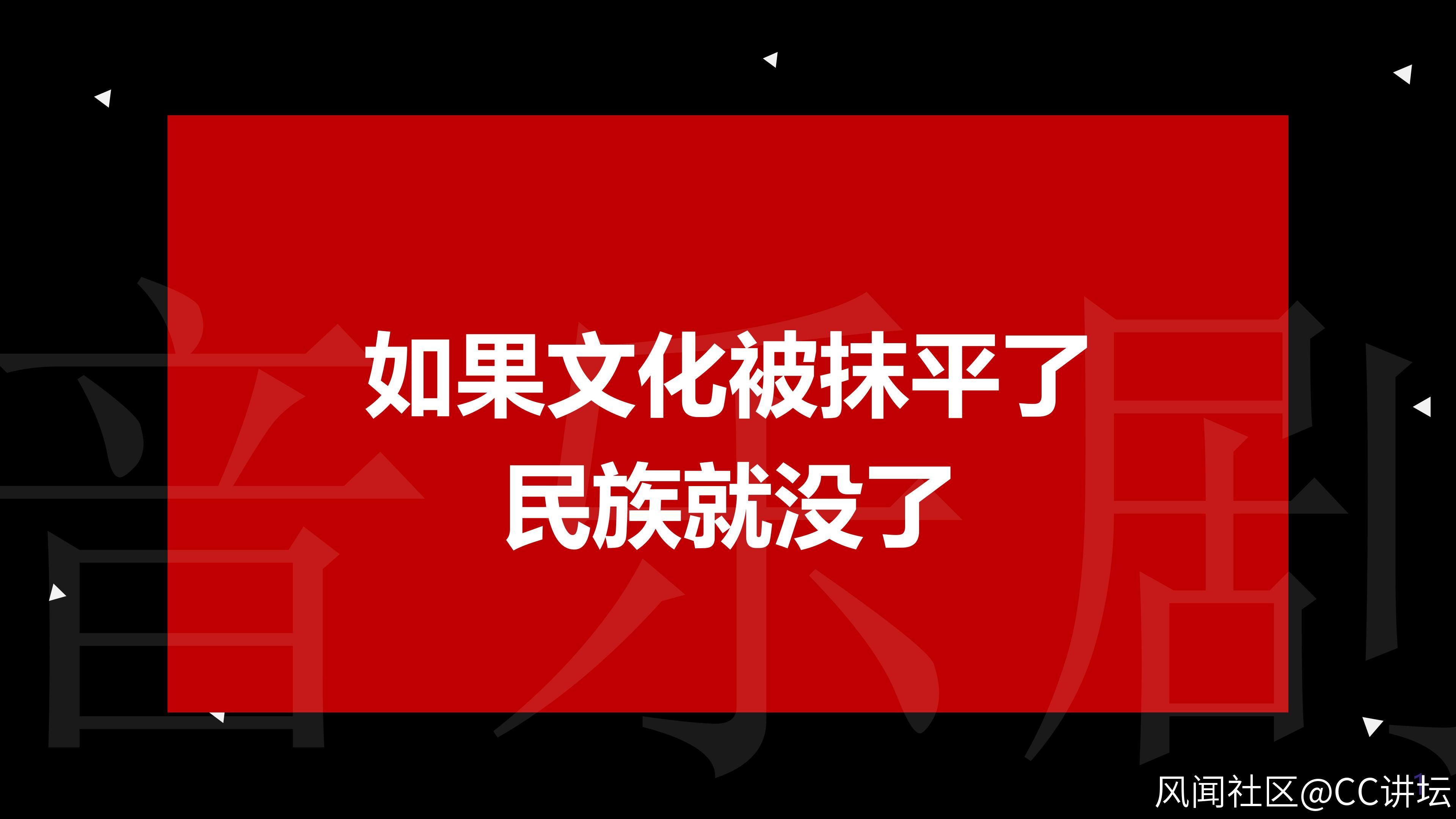
導語:
無論東西方,為什麼京劇、崑曲、歌劇、芭蕾等等這些偉大的藝術形式都不約而同的成為了“被保護者”?
李盾的回答很簡單:就像有了紙張,甲骨文時代就一去不復返了。
文化是需要載體的,不管你接受不接受,新的載體都會出現,就像李盾的音樂劇《西施》裏一句話:一個時代夢見了另一個時代,一羣人夢見了另一羣人。
我們該怎樣認識新的載體,該用新的載體講述怎樣的文化?文化的被抹平,從來不是危言聳聽,它是事實發生、正在發生的事,當然,這個被抹平的過程,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聽李盾的演講,聽他和三寶老師們故事,聽他們用生命去吶喊、去喚醒的思考。李盾們,在音樂劇中,在文化的思辨中等着我們。
CC講壇主編 富宇

2'40''
為什麼東西方傳承了上千年的文化形式滿足不了現在人們的需求?取而代之是的什麼?

9'24''
囊獲幾乎所有音樂劇國際大獎的《蝶》,發生了怎樣的故事,讓三寶幾乎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12'18''
文化的被抹平。關於韓國、日本音樂劇的思考。
演講實錄:

我們中國是一個戲曲大國,光劇種就有360個,因為不改變,現在剩下200多個了,我認為200多個不改變,還要繼續消失。
在五千年的文明史上有講不完的故事,在審美上東方和西方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就是一虛一實,巧合的是在哪裏呢?我們在四百多年前,東方出現了湯顯祖,西方出現了莎士比亞,這是巧合嗎?我認為這是必然。
我是舞者出身,1986年我從加拿大蒙特利爾現代舞蹈團回國,應該去東方歌舞團,但後來我選擇了自由,選擇了去深圳,我認為什麼是自由呢?自由就是孤獨地綻放。去深圳我是覺得有太多不確定性,人生之所以有不確定性,我認為才是很有意思的。

所以説剛到深圳,真的是充滿着神秘,充滿着改變,也不知道明天發生什麼,但是深圳改變了我。深圳是一個什麼地方呢?你在這兒你不覺得,你生活了一段時間了,回頭再看它的時候,你忽然發現你要向它説聲:謝謝,因為它成全了你。

深圳為什麼成全了我呢?我在深圳工作了一段時間,有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去英國學習現代舞,又一個偶然的機會在英國看到了音樂劇 《悲慘世界》,當時我真的是興奮極了。為什麼興奮呢?我覺得用這種方法來講東方的故事,一定是一個非常好的東西方文化的融合。

實際上音樂劇這種形式,“唱唸做打”在中國的戲曲上比比皆是,在中國的《禮記》當中,把音樂劇這種描寫實際在上千年就説得很清楚了,所以説西方也肯定借鑑了東方載歌載舞的表現形式,出現了東方和西方融合的時代。

實際上這麼多年來,我從看到音樂劇那天起,就開始學習東方和西方審美的轉換,三十多年過去,我認為現在我還是在路上。你完成不了轉換,你沒有辦法把東方的音樂劇推向世界去講。

在研究的過程當中,我發現中國所有的、古老的、傳統的京劇、崑曲和各種的藝術形式,已經滿足不了中國老百姓的現在需求了。但是在西方同樣出現了這樣的問題,包括歌劇、芭蕾、交響樂也是一樣,取而代之的就是電影、流行樂和音樂劇。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一個道理,就文化而言,東西方一切在農耕時代登峯造極的藝術形式,在大工業時代都不約而同地成為了“被保護者”,取而代之的就是更具備工業文明特徵的、新的表現形式和新的載體。音樂劇和電影就是工業時代新的文化載體。載體是否先進,決定了它的文化內涵過去、今天、未來的傳承,就像有了紙張,甲骨文時代就一去不復返了。今天我們應該怎樣運用這樣的載體,怎樣去理解文化的先進性呢?文化的先進性就是我們人類文明的尺度和標杆。
音樂劇是現場娛樂的終極表現形式。但是音樂劇也是人生,音樂劇可以重複幾萬次,人生只有一次,所以説我的人生是不能重來的,所有的人生也是不能重來的。所以説我選擇了音樂劇,我選擇了把我一生的時間都獻給這種藝術形式,我認為用這種形式來講中國故事,全世界都能看懂。它中西合璧,但是在學習的過程當中,我花了九年的時間。
我看到音樂劇那一瞬間,齊白石的一句話就跳到了我的腦海裏,“學我者生,似我者死”。必須學習,必須學習之後,用這種藝術形式來講東方的故事。所以説這漫長的九年,每年我都在美國待上三個月甚至半年,在英國也是一樣,學習之後在大型的演唱會里去試驗,在歌舞廳裏做試驗,一晃九年就過去了。
在1997 有一個機會來了,中航航都大廈要建立一個文化場所,後來我去看了之後,我發現這個地方很有意思,能創造一個沉浸式的戲劇形式。後來我就跟他們講,我説:我們能不能做一個介乎於劇院和娛樂場所之間的第三種感覺。他説:這種東西叫什麼呢?我説:叫“二十一世紀演藝中心”我們做沉浸式的音樂劇的演出。所以説中國的第一部音樂劇《白蛇傳》在深圳開始,中國的第一部沉浸式的音樂劇也在深圳開始。
一演就是1200場,整個的過程是很艱難,因為當時要做音樂劇沒有演員,所以説就找到了北京舞蹈學院社教系裏的音樂劇班,在那個班裏有60個學音樂劇的學生,同時又找到了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主任郭文景,又找到了三寶,找到了三寶是對中國音樂劇的一個對的開始。
我記得第一次聽《白蛇傳》排練的時候,在北京舞蹈學院,我説:我終於找到中國音樂劇的音樂了。我的眼淚是噴出來的,那個瞬間的感動,造就了中國音樂劇的一個對的開始。
我們東方的審美是什麼呢?是悽美。我認為我們不像美國二百多年它竟糟蹋別人了,我們東方經歷了漫長的苦難。倫敦西區又過分的藝術,百老匯又過分的娛樂,所以説我要找出第三條路來,創造第三種音樂劇的表現形式,用東方的色彩傳達我們自己的文化價值。
所以説在《白蛇傳》裏,我們最主要講的是青蛇,她既愛着白娘子也愛着許仙,當需要奉獻生命的時候,青蛇把生命獻給了白娘子,所以説我認為大愛就是犧牲、就是給予、就是成全。

音樂劇這種形式在現場上得到了非常好的反響,有的人看了六十多遍,這個劇在深圳連續演了1200場。這一路走來,從爬行到血淋淋地站起來到能演1200場,所以説給我們帶來一種新的思考。

在《白蛇傳》的成功之後,我們又排了《西施》,後來又進一步地研究,開始了《蝶》的創作,我是覺得《蝶》應該找國際團隊了,應該找到更大的資本來完成《蝶》的投資,所以説當時我們就找到了松雷集團。提前一年半就把演員招進來,訓練這些演員,那演員有了,我們又把全世界最好最對的藝術家找來。
我們既沒找百老匯的、也沒找倫敦西區的,我們找了法國的《巴黎聖母院》的整個創作團隊,這個團隊有全球六個國家的頂級藝術家,從蒙特利爾、到法國、到英國、到日本、到荷蘭,組織了一個很好的團隊。

但是團隊組織好了,矛盾也來了,就是這個劇本需要完成中西合璧,改劇本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我們中國藝術家把劇本寫了很多年了,這個劇本最早在餘華和陳紅的手裏寫了三年,三寶和關山又開始了七年的創作,馬上要開始了,他們對自己的東西已經有深深的感情了,所以説改是非常艱難的一件事情。
但是怎麼辦呢,我們請了東方的團隊不説,還請了一個劇本醫生,這個劇本醫生把改好的劇本就發到中國來,我是覺得如果説這個劇本發給我的中國的藝術家。可能在巴黎的會議就會取消。所以説我就想了一個辦法,我就給關山和三寶訂了機票,我説:我們去巴黎開會。但是劇本沒有發給他們,當飛機飛到了一萬多米,我説:關山,這是新的劇本;三寶,這是新的故事。他們兩個當時就臉色有點不好看,但是他已經下不去了。

到了巴黎乾脆不談如何創作,我們就去吃巴黎的生蠔、去喝法國的紅酒,一週之後大家彼此關係融合了,大家彼此之間有了感情了,我們才開始討論了,就已經不是以前那種火藥味很濃了。有人説:我們能不能不分東方和西方,我們能不能做一個作品,站在世界中心角度來講中國的故事。我説:這點太好了。所以説《蝶》又調整到了一個非常準確的軌道上來。
所以説《蝶》在2008年北京保利劇院首演的時候,我記得首演十一場,最後一場的時候,我剛到後台,他們説:不好了,三寶老師病了,我説:怎麼了?我一看三寶發高燒,燒了40多度,我説:三寶你不能指揮了,我找一個人指揮吧。他説:不行,找一個人指揮上半場,我指揮下半場。我説:你站都站不住,怎麼指揮呢?他説:這樣,你找兩個人把着我的腿。我説:好吧。

因為三寶是蒙古人,我是滿族,我擰不過蒙古人,我就找兩個人把着他的腿,然後我站在他的背後,我看見他的汗從頭髮、後背、褲子、鞋裏。
最後一個人結束呢,人是抬下來的,然後當時準備往醫院送。後來他的家人説:你不用送,你放心,三寶經常這樣發燒的,他交給我了。但是在第二天早晨,突然間他們在醫院給我打電話,説:李盾老師,不好了,他發現了血栓要截肢。我説:你讓三寶接電話,我説寶啊,手我可以給你,命我給不了。
在六點多鐘準備吃晚飯,他喝完水一頭就栽那了,心肌大面積梗死,就往手術室推,如果在家裏人就沒了,所以説三寶是慶幸的。

我記得三寶在病危的時候,我就想:兒子病了,萬一有什麼情況,我得讓媽看一眼。我就給三寶媽媽打電話,把他媽媽請到醫院來,可是他媽媽來了之後,三寶的病情就緩解了,但是有一個問題出現了。因為三寶的媽媽也是大作曲家《嘎達梅林》的作曲家,但是你怎麼把老孃打發走呢?然後老孃就看着我滿臉的虛汗,看着我很緊張、不知所措,老孃好像似乎看出來了什麼問題,老孃説:你不要緊張,盾,我以為你找我要簽字呢,沒什麼事我走了,我回去了。
然後我就送三寶的母親離開病房,她轉身的時候我發現老孃流淚了,但是她沒有讓我看見她的痛苦。三寶是慶幸的,他用生命譜寫了《蝶》的旋律。

後來我們在武漢演出的時候,韓國大邱音樂劇節的委員長帶了十個人,他想邀請我們參加世界音樂劇節的演出,而且我們是做開幕式的演出。所以説我們應邀請2008年就到了韓國,參加大邱音樂劇節的演出,當時我們心裏沒底,就請韓國的文化參贊,韓國文化參贊説:《蝶》是個大製作,不錯。我説: 是是是,我們是請了世界級的、頂級的藝術家來做的。他説:我真的沒有時間,真的不能去。我説:你看看這節目單。所以説看節目單之後,他覺得這是不同的,有《巴黎聖母院》的導演,因為他看過《巴黎聖母院》,他説:李盾老師,你給我兩張二樓的票。

在首演當天我心裏沒底,大幕一黑燈我就躲在角落裏發抖,幕間休息我也不敢出來。當演完了,當那幾秒鐘沒有掌聲的時候,我真的是覺得我的末日,完了,我的血液從腳跟底下都流走了;當觀眾起立,爆發出熱烈掌聲,我瞬間覺得血液迴流,然後我捋了捋我的長髮,擦了擦我滿臉的虛汗,就到人最多的地方去了。

我一到了前廳,就看見從二樓下來一個人,滿臉熱淚,那個人就是文化參贊朱英傑,他説:盾,你能讓我抱一下嗎?他説:我要寫一篇文章《感動之後的尊重》。所以説當年《蝶》在韓國大邱音樂劇節包攬了所有的大獎,也是《蝶》讓韓國和日本的音樂劇得到了一種思考。

因為韓國和日本的音樂劇的發展,一路licence 就是許可證的演出,但是幾十年過去回頭一看,發現自己的文化被抹平了。這種問題發生在單一民族的韓國和日本沒有問題,如果發生在中國,我認為那就是大逆不道,如果文化沒了,我相信民族也就沒有了。
所以説韓國從2008年開始,它的國家對國產的音樂劇很重視,大力支持它的原創音樂劇,音樂劇蓬勃發展,包括《英雄安重根》、包括他的英雄,就是很多音樂劇在韓國市場上得到了一種版權演出和本土音樂劇的平衡,這種平衡我認為對韓國市場是非常好的一個狀態,但是我們中國音樂劇發展到今天,我認為完全失去了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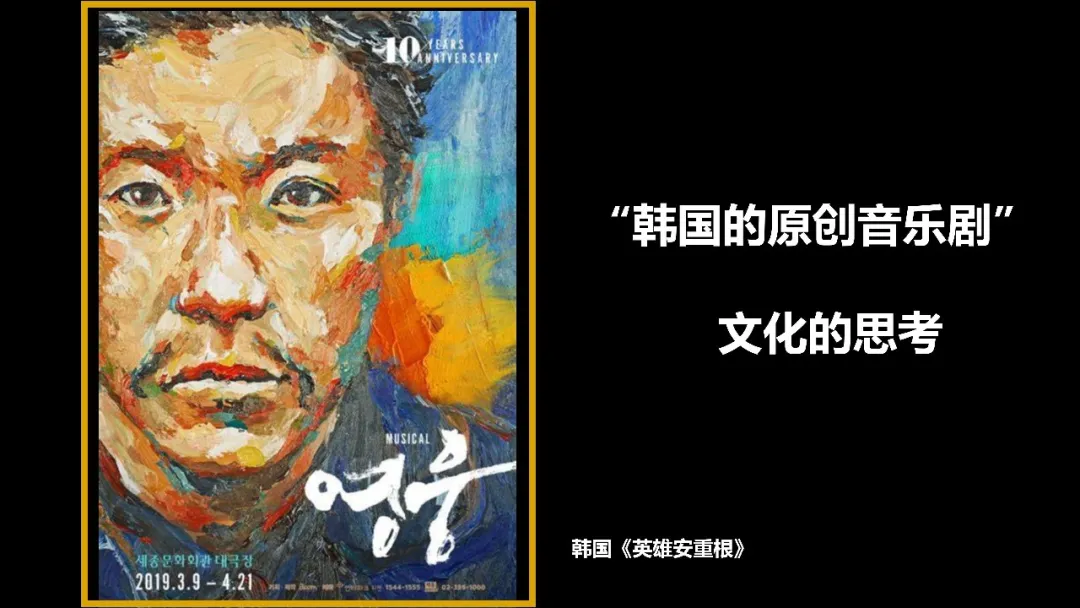
韓國是舉國家之力,支持本國的音樂劇走向世界,日本也是一樣,所以説它的這種市場,最大的市場就是中國。在中國的市場上,美國的音樂劇來了、英國的音樂劇也來了、法國的音樂劇來了、德國的也來了、日本的也來了、韓國的也來了,但是我們本土的音樂劇需要國家大力的支持啊。如果文化被抹平了,民族就沒了,在中國的市場上,在我們中國的時代裏,我們不能出現憾事。

就像當年我跟淺利慶太見面的時候,淺利慶太説:李先生,你是對的,説你看看我,牆上都是licence,只有一部《李香蘭》。他説:東方的音樂劇就靠你了,我的生命已經走到盡頭了。所以説淺利慶太先生這句話對我的鞭策更大,突然間我覺得有一種使命。
實際上我們現在中國很多經典的東西,都被國外拿走了,《功夫熊貓》被美國拿走了,《花木蘭》被美國拿走了,我們還有很多的故事被拿走了,如果説我們再不努力加強中國的文化,用這種先進的形式來表現的話,離文化被抹平真的是不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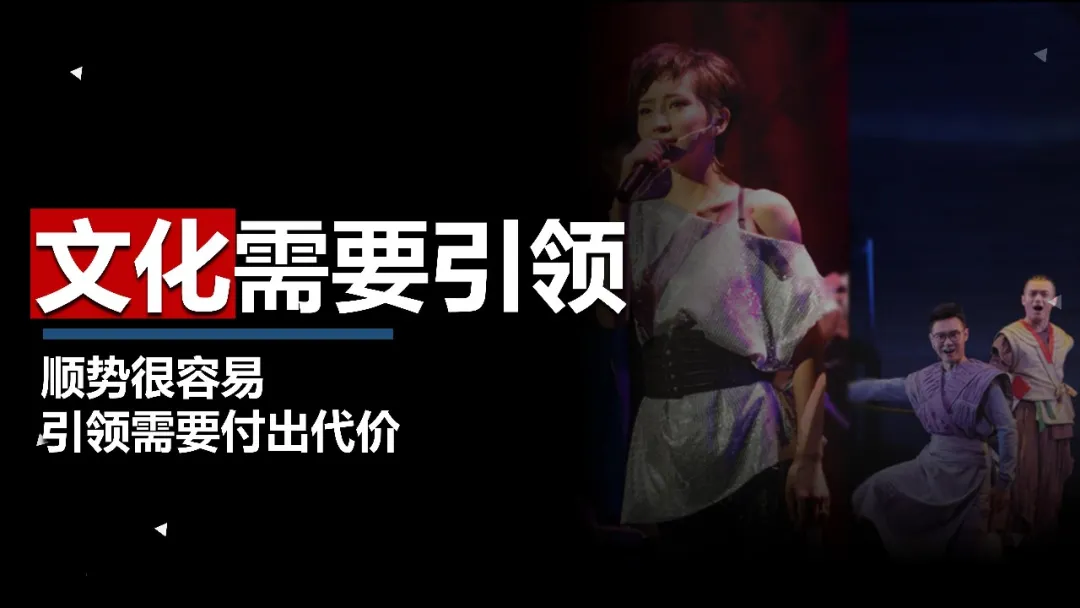
起碼來説中國的音樂劇市場應該像電影一樣,國家對引進音樂劇的版權要有一定的管控,現在所有的引進版權都是境外交易,在中國連買路錢都沒有,包括任何內容沒有任何審查就進來了,全是民間引進,然後在國外交易,我認為這是一個悲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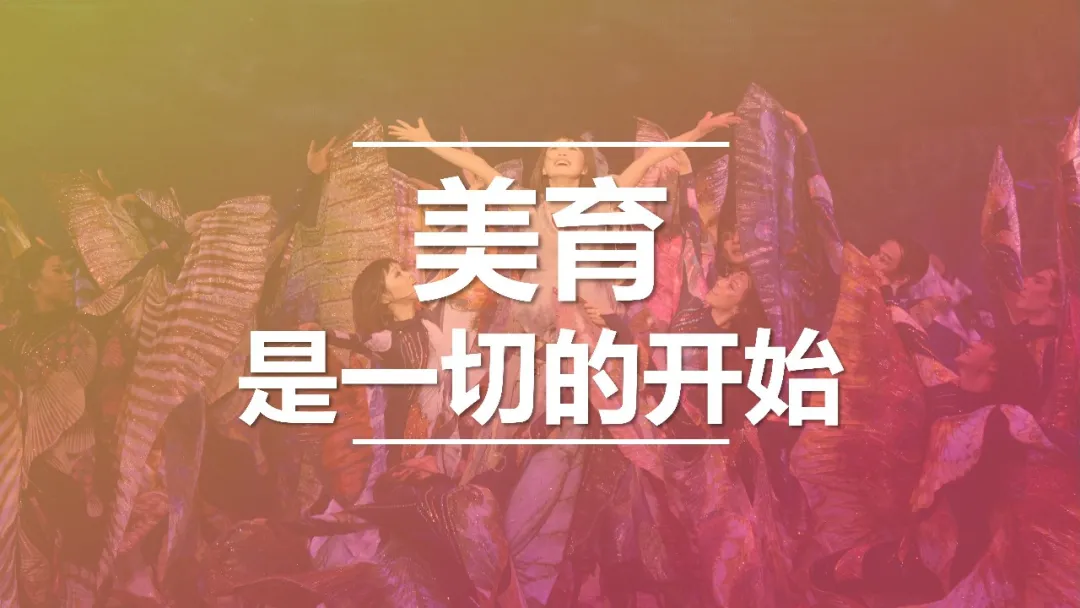
國產電影現在市場的繁榮,是舉國家之力支持國產電影,我希望舉國家之力來支持中國原創音樂劇,實際現場的影響遠遠會超過電影的,因為音樂劇是現場娛樂的終極表現形式,它的影響力要超過電影幾百倍,所以説現場娛樂的終極表現形式音樂劇對中國的文化傳播,對中國音樂劇走出紅牆、走向世界,是尤為重要的一種藝術的表現形式。

我認為在這個時代裏,文化覺醒不僅僅是我個人的使命,也是所有人的使命,是民族的使命,如果我們不再珍惜、珍視我們本土的文化,我們文化被抹平的那個時候,我們所有人都是罪人,所以説我們必須要做這種事情,用音樂劇來講中國故事,讓中國的故事站在世界中心,感動世界。

2022年是天道輪迴的年份,在這個年份裏有太多的不確定性,但是在這個年份裏“五星出東方利中國”謝謝各位。

編者語:
就文明而言,一切在東西方輝煌一時的藝術形式,在新時代來臨的時候,都會誕生新的表現形式和藝術載體。新的藝術載體承載了怎樣的文化厚度,這取決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幾千年積累下來,傳承下來的文明。文化的宣揚和傳承,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每個人的的使命,音樂劇是現場娛樂的終極表現形式,希望大家把目光投向音樂劇,能多多支持國產音樂劇,從發現它、到看見它、再到愛上它!
編輯:白玉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