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國華|從預防性抑制到現代性危機:躺平的前身後世_風聞
探索与争鸣-《探索与争鸣》杂志官方账号-2022-02-18 19:51
朱國華|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國際漢語文化學院教授
何謂“躺平”?要下一個定義並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本文談論的“躺平”,指的是這樣一種心境狀態,它意味着甘居下游,意味着對失敗的承認,意味着對通行社會遊戲規則的放棄。從這種意義上來説,某些動輒宣稱自己要“躺平”的人,如果依然按照某種晉升標準在打拼,其實並非真正的“躺平者”。他們的誇張語言,只不過是對其所承受壓力的情緒宣泄,情緒釋放之後,往往就達到了亞里士多德所謂昇華或者淨化之效果,也就是説被治癒了,他們其實是認可或接受現實秩序的。經常戲謔地説自己想躺平的人,其實往往是比別人更努力、更勤奮、更拼搏的人。
撇開具體的歷史條件,從抽象人性的角度來講,人的慾望總是無法得到充分滿足的。因為正如叔本華注意到的那樣,一個基本事實是,古往今來,某一具體慾望的滿足,不過是新生慾望的開始:温飽解決了,人們還想獲得鮮衣怒馬;即便貴為一國之君,已經達到了榮華富貴的頂端,還要追求長生不老。許多哲人洞察到慾望的虛妄,並順理成章為人類開出了躺平的藥方。老子認為“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天地之間的大道,最明顯地表現在水的本性上,因為“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水的特點是往下流淌,所以它隨處自適自在。但是人似乎在某種意義上是與水的特性背道而馳的,我們一心想往上爬。撇開身體的感官需要,如果往理念或崇高處説,可以認為,人處在社會中,不能不被鼓勵着有理想、有追求、有奮鬥,根據精神目標的達成度來確定自己在社會空間的定位,並由此評估生活的意義。就此而言,蘇聯作家尼古拉·奧斯特洛夫斯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的名言是值得被反覆徵引的,“一個人的生命是應該這樣度過的: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不因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因碌碌無為而羞恥”。
但是,對莊子這類思想家來説,事情的另一面,也就是更實際、更悲劇的一面是這樣的:“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莊子認為我們應該理解到萬物是齊平的,正確的人生態度應該是不譴是非,應當踐履的行動邏輯是怎麼樣都行:“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其實再推而言之,可能除了少數罕見的例外,人類的宗教在某種意義上,都持一種躺平觀。釋家講四大皆空、五藴非有:“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而基督教分明講此岸的人間世不過是“淚之谷”,雖説不至於棄之不顧,但起碼比起末日審判後的天國,是比較不值得過的。即便撇開宗教維度,西哲如此思考者也不乏其人,從犬儒主義者第歐根尼到悲觀哲學家叔本華,史不絕書。其中,最有躺平主義傾向的是伊壁鳩魯,作為一個所謂快樂主義者,他區分了三種不同的快樂:第一種是自然的和必需的,如食慾;第二種是自然的但不是必需的,如性慾;第三種則既不是自然的又不是必需的,如虛榮心。後兩種顯然都是可以割捨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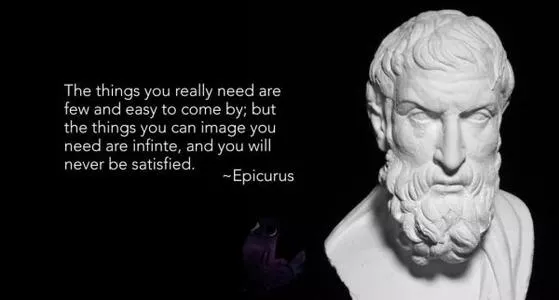
但是躺平在現實生活中並不容易實現。古代的智者們在觀念層次上嘲笑世人被蠅頭微利、蝸角功名所綁架,無法參透宇宙玄機,得到大解脱、大歡喜;中國文學中也有大量隱逸題材的作品,表達了對名繮利鎖的譴責。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我們寄寓在滾滾紅塵中的沉重肉身,有其獨立於精神之外的必然性物質要求,這使得我們無法在根本上躺平。不太富有的陶淵明宣稱要“息交以絕遊”,但是他為生活所迫,還是要“種豆南山下”。撇開隱士、修士或者高僧、高道,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躺平者,必須有萬貫家財作為物質保障:要真的遊心物外,也必須是富貴閒人。無論是曹雪芹《紅樓夢》中否棄仕途經濟的賈寶玉,於斯曼《逆流》中離羣索居的德澤森特,還是岡察洛夫《奧勃洛摩夫》中那位著名的睡神,他們擁有的優渥的貴族生活條件,才使得他們的懶散無為成為可能。
馬爾薩斯認為:“人口的增殖力無限大於土地為人類生產生活資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會以幾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資料卻僅僅以算術比率增加。”因此,人類的生長繁衍會因為食物短缺而受到抑制。這種抑制可分為預防抑制和積極抑制兩種。預防抑制主要是道德的抑制,例如選擇單身或者晚育;而積極抑制則是戰爭、瘟疫、饑饉等。從這樣的邏輯看,傳統社會的躺平主義也可以視為馬爾薩斯談到的預防性抑制的一種解決方案。將對慾望的自我閹割、對失敗的自覺承擔,昇華為一種人生理想的追求,主張清靜無為、清心寡慾、絕意進取,這表明了在前現代社會欠發達的物質生產水平無法應對人口增長壓力的時候,人類社會可以通過降低慾望要求的方式,獲取低水平的身心平衡。
隨着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社會文明的進步,絕對貧困現象在世界上一些地方,例如非洲,還有所耳聞,但早已經不是主流社會的主要方面。然而躺平現象在當今的國際社會似乎有增無減,這又該如何理解呢?我們不妨首先切入中國社會現實洪流的某個切面。我們都熟知躺平族的系譜:屌絲、殺馬特、三和大神、佛系等。其中,三和大神的生活理念是“幹一天玩三天”。對這樣的躺平者而言,除了維持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外,他們無慾無求,甚至寧願退出社會,甘居社會邊緣。這些人當然表明了某種極端,他們的存在算不上普遍性的現象級社會事實,同時,上述理念也未必是他們能堅持的一種恆常生活實踐。但無疑,他們代表了許許多多生活目標幻滅者的某種傾向。值得注意的是,與傳統社會中無望獲取充裕生活資料所產生的挫敗預期不同,這樣的幻滅,是一種現代性的幻滅,是基於對謀求更高層次需求——例如得到承認或自我實現等願望——的主動放棄。
“躺平即正義”口號的倡導者及支持者可能大體上是人生正在艱難爬坡的青年人。如果僅僅從代際差異的視角來看,也許我們可以獲得一個比較簡單粗暴的解釋,比如一些企業的“996”等制度設計,包括筆者在內的50後、60後的許多人,對其的容忍性可能高一點。這是因為對如今的中老年人而言,艱苦樸素、吃苦耐勞、義務奉獻、任勞任怨以及螺絲釘精神,曾經是一個社會主義勞動者不言而喻的基本職業素質。他們目擊了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變,而新時期市場的邏輯剛在中國萌生的時候,是與改革的政治理想結合在一起的,企業家等羣體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是作為時代英雄而出現的。市場的興起,帶來了經濟的繁榮和財富的增長,讓中國社會從貧困迅速走向富強。某些個體的失敗,則被理解為社會進步所不得不付出的代價。這代人中的許多人或許並不處在工商業領導者的位置,往往還是會從站在這個位置的角度上思考問題。
但是,如今的青年人拒絕將資本的邏輯予以合理化。他們腦中並沒有中老年人依然保有的物質極度貧乏的記憶。他們生活在生活資料相對豐富的時代,他們固然沒有那種慾壑難填的佔有渴念,但容易將由家庭和學校所提供的物質安全視為當然,而一旦踏入社會,這種安全感頓時煙消雲散,諸多心理上的斷裂會隨之產生。特別是他們的期待薪酬與實際收入之間,總是存在落差,因此必然會滋生被剝奪感。由於無法適應一些企業制度設置的殘酷性,曾經學習過的資本、剩餘價值等概念,就會從書本中被激活,由此產生道德義憤。對有些青年人來説,拒絕成為勞動力,拒絕升遷、漲薪等光明前途,也就是躺平,就相當於挫敗了這種“剝削”的陰謀。這些青年人已不能像其父輩一樣無條件順從市場的強制要求,他們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物質的或精神的需求,從而安於在社會空間中叨陪末座。對此,我們很自然會想起布迪厄的經典社會學理論,認為躺平者之所以躺平,表面上看是主體性選擇,實際上是被客觀可能性所決定的。威利斯在《學做工:工人階級子弟為何繼承父業》中寫道:階層固化導致英國工人階級的子弟付出再多的努力也無法有向上流動的可能,只能子承父業,繼續其父輩體力勞動的道路,因此,依然幻想可以通過自己的發憤圖強改變命運,在這些男孩眼裏就顯得可笑了。如果駱駝祥子早就看穿,買不到洋車是自己預先註定的命運,那他就不必那麼頑強拼搏起早貪黑了,或者可以調低慾望以適應自己的物質條件。
此類青年人使得躺平的敍事可能性得以凸顯,其實,社會不同羣體中的不少人也都表達了對於躺平的真實渴望,即便這種渴望本身更多反映了一種情緒,而非關涉一種未來行動圖景。實際上,筆者認為,我們應該把“躺平即正義”的聲音,納入社會的現代性轉換這個更大的背景中來考察。從這個視角來看,“躺平即正義”的呼聲不過是冰山一角,它折射出來的,是海平面下不可見的躺平主義冰山。關於這一點,加繆《局外人》中的默爾索可以視為現代性條件下躺平主義者的一個隱喻。
默爾索不僅拒絕升遷,取消了社會遊戲規則的全部有效性,而且認為萬物齊平,一種生活不比另一種生活更美好,一切的人和事都沒有差異。從一種角度來説,默爾索以及小説中所描繪的法屬阿爾及利亞社會,呈現了普遍存在的無差異性,也就是將一切觀念和實踐視為均等的狀態,這消解了意識形態所強加的二元區隔(例如,善/惡,貴/賤,是/非,聖/俗),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視為交換價值君臨天下的症候。在現代性語境下,在一切價值和規範都喪失特定意義的條件下,任何個體作為一個負責任的主體都是不可能的。從另一個角度來説,默爾索的行為,挑戰了自由意志這一現代性前提。康德認為,啓蒙運動的關鍵在於倡導擁有在一切事物中公開地運用自己理性的自由,但人們其實更願意處在受監護的狀態,這不僅是因為我們的怯懦與懶惰,而且是因為這讓人感到舒適:“如果我有一本書代替我擁有理智,有一位牧師代替我擁有良知,有一位醫生代替我評判飲食起居,如此等等,那麼,我就甚至不需要自己操勞。只要我能夠付賬,我就沒有必要去思維;其他人會代替我承擔這種費勁的工作。”默爾索的行動沒有動機,對諸多選擇可能性採取漠然順應的態度,他還通常聽命於生理慾望和他人意志的役使。就此而言,他其實是沒有道德自由的。藉助這樣的形象,加繆展現了自由意志的可能困境:現代性的自由,其實意味着負擔、勞動和責任。人們嚮往自由,嚮往堅持個體的自主性和獨立性,這當然是一個重要的現代性事實;但我們需要同時承認的是,人類還向往着對自由的逃避,嚮往着躺平舒坦,這也許是一個更具有決定性和挑戰性的事實。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躺平的聲音其實交織着歷史的投影、人性的奧秘和現實的挫敗,尤其是現代性的危機,難以對它進行簡單的現象學描述。從《局外人》中法庭的視角也就是社會主流的視角來看,一個人如果甘願躺平,甘願放棄自己的自由意志,這樣的行徑所帶來的心理感染,會威脅一個社會賴以維繫自身的根基。如果我們都拒絕在社會這個具有宇宙意義的戲劇中扮演自己的社會角色,拒絕執行確保社會常規運作的那些遊戲規則,那麼,這無疑意味着社會秩序的全面崩解。所以,我們必須堅持理性自決,堅持社會互動,堅持某些最低限度的價值和信念。正如魯迅指出的那樣,要時時意識到: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
躺平的呼聲此起彼伏,雖然它聽起來刺耳,讓人不適,但是它絕非毫無意義。它絕望的嘆息,讓我們在熱衷之際保持冷靜,它請求我們透過弱者的眼睛打量世界,企盼我們傾聽孤苦無告的聲音,並召喚我們轉換觀察事物的視角,比如對交換價值尤其是績效主義成為丈量一切的標準,應該嚴加防範甚至批判,應該尊重個體擁有可以不優秀、不出眾的人性權利等。
只要存在着物質或精神資源的稀缺性,存在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不平等性,甚至只要存在着富與貧、美與醜、長與幼、尊與卑,乃至生與死的差異,躺平主義就必然存在。我們當然不可能徹底剷除躺平主義——事實上諸多躺平主義類型本來也具有自身另類的風采和光芒,正如諸多哲學、文學大師所已經展示的那樣,但是,我們可以採取措施(例如推動共同富裕的理論與實踐)來改變躺平主義藉以滋生的社會條件,並由此儘可能多地消除社會的怨氣甚至戾氣。倘能如此,那麼躺平主義的底色依然不會變化,仍是將對於失敗的承認轉化為一種生活姿態或審美趣味,但其中的沉重和悲苦,將在不斷翻新的躺平主義話語中隨風飄逝或至少漸次蒸發。